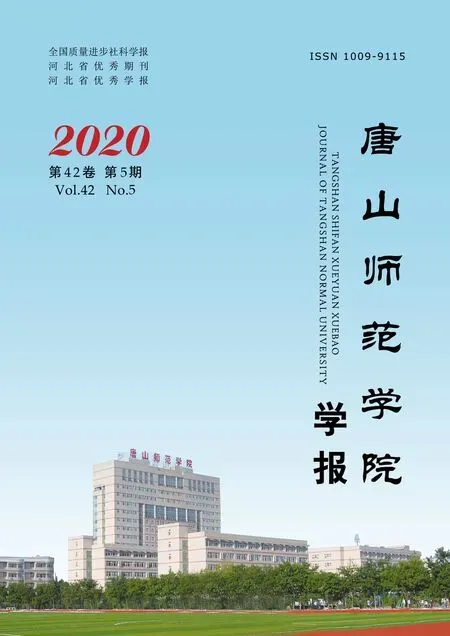1898-1919政治视阈下的女性报刊文学
2020-01-09郭建鹏
郭建鹏
文学研究
1898-1919政治视阈下的女性报刊文学
郭建鹏
(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西方女性主义介入中国,是以男性的价值趋向为坐标,结果导致女性的启蒙话语与女权运动被置身于政治视阈下进行。在男性的操纵下,1898-1919年出现的女性报刊始终没有脱离男权的限制,使女性以启蒙为主体的兴女学、废缠足等身体解放逐渐上升为国族救亡运动,经过轰轰烈烈的参政运动,在男性的干涉下,又回到传统的“贤妻良母”之范式。女性期刊出现女权主义与走向回归传统的多元建构,实为男权体系操纵文化建构的必然结果。
政治视阈;女性期刊;女权主义;回归传统
1898年7月24日,《女学报》在上海创刊,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由女编辑、女记者独立主办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女性期刊。由此开始,至1919年,在国内外创办的各类中文妇女报刊已近70种。女性报刊创办伊始,它倡导的是女性的思想启蒙,办女塾、倡游学、反缠足,成为这时期女性报刊宣传的主题。宗旨是号召女性从传统的相夫教子、精于女工的家庭生活中走出来,与男性一起承担起民族救亡的重任与义务。1900年,随着女权说的传入,女性报刊思想发生了变化,家庭革命、男女平等、文明婚姻成为女性报刊宣传的热点话语。1907年7月15日,秋瑾被清政府送上了断头台,“秋瑾案”引发了新闻舆论界的风暴,女性参与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的焦点成为女性报刊参与政治革命的起点。随着女子革命军、女子北伐队等革命队伍的建立,鼓吹女子参政的报刊逐渐增多。好景不长,南京临时政府及袁世凯政权对女权运动的打压,使女性报刊从参政、平权的主题转向社会与家庭生活。从袁氏政府到五四新女性的兴起这段时期,女性报刊出现明显的商业化走向,由个体创办逐渐转向个体与商办并存,有实力的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广益书局、中华书局等)参与进来,为女性报刊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这一时期的女性报刊在办刊思想和指导方针上出现新旧交替、道德评价与取向混乱,但为女性文学创作及从事社会职业提供了新平台。综观这20年(1898-1919)的女性报刊,其突出特点是中心议题与时局变动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一开始就被置身于政治话语下,面对西方思潮的涌入及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图景的憧憬与想象,女性办刊活动及在报刊上的言论表述始终围绕现实的政治环境,并成为获取社会舆论认同、国家机器认可合法化存在的关键。
一
关于女性办刊的缘由,《女学报》创办广告中说道:“中国女学不讲已二千年矣。同人以生才之根本在斯,于是倡立女学堂,现定四月十二日开塾,已登报告白外,欲再振兴女学会,更拟开设官话女学报,以通坤道消息,以广博爱之心。”[1]可见,办报人对报刊传播信息有着深刻认识,才创办《女报》以便行使启蒙之功效。在内容上“中国女学书善本甚少,本馆同人购译东西洋女学书外,又编纂白话浅文诸书,以饷海内。兹于报尾,拟续附女学书一页,先将潘仰兰所演、刘可青所绘中外古今列女传印出,以作巾帼师范之资”[2]。可见其以翻译外来女学思想为主体,在语言上倾向于白话,传统列女为典范,既有进步性,又存在一定的保守性。女学报的一项重大举措是“本报征录一篇,敬酬润笔洋壹圆。”虽然《女学报》其存在时间短暂,却是知识妇女在现代性思潮冲击下发出追求自身解放的第一声呐喊,它提出男女共构国家权力的要求:“夫民也者,男谓之民,女亦谓之民也。凡我同辈亦可以联名上书,直陈所见,以无负为戴高履厚之中国女子也。”[3]可以说是自阶级社会诞生以来女性对男性专政制度的直接挑战,也彰显了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女性迈向政治舞台的开始。
在《女学报》及之后出现的女性报刊中,出现了“社说”“论说”“谈丛”“演说”等栏目,为女性作者提供了发表诗文的园地,使女性的文学流传走出闺阁,获得与男性文学书写同等的地位。综观此时期报刊上发表的女性诗词,虽然没有突破传统诗词创作体式,却在内容上出现了“旧瓶装新酒”,开启了女性思想启蒙的萌芽。女性的思想启蒙运动是伴随着“废缠足”(如南社女社员张默君在八岁时作《天足吟》:“悲悯人天动百神,看从苦海起沉沦。秉彝毕竟同攸好,还尔庄严自在身。”)、“兴女学”(如刘靓的《中国上海女学堂落成开塾歌》:“古来才媛不乏数,每览青史神为追。况复生当盛明世,六洲万国齐追陪。耳闻目见日诙廓,中西文学争鸿裁。”)运动而兴起的。这些诗以铿锵慷慨之气表达出女性要求独立、自由的思想。将废缠足、兴女学纳入更广阔的政治语境中阐释,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探究造成种族、国家危弱的根源。女性在觉醒过程中将西方元素作为参照系,为其论说寻找政治依据,成为其强大的舆论支撑点。此后的报刊将视野集中到对西方女政治家、女教育家的介绍上,如1902年创办的《女报》(后改名《女学报》)发表的批茶女士、维多利亚女皇、罗兰夫人、俾士麦克夫人与涅几柯儿(即南丁格尔)等人传略①;1900年,日本人石川半山在《清议报》上发表了《论女权之渐盛》一文,他从欧美诸国女性参与社会职业取得独立地位谈起,进一步说明女子争取参政权、经济权的重要性[4]。随后,马君武翻译了斯宾塞的《女权篇》[5]与《弥勒约翰之学说》[6]。自此以后,有关女权问题的探讨逐渐兴盛。之后出现的关于女权的论述中,大部分为男士所译著,女性参与者很少,形成了“男性女权先声”[7]的独特场域。体现了男性倡导女性解放之政治意图,即寻求女性共同承担救国保种之责任,女性被男性的期待视野推向政治革命的浪尖上。1904年,《女子世界》创刊。由男性为主体编撰者的女性刊物,将男性引导的女性观强加于《女子世界》;《中国女报》强调“吾今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而欢呼。”②《中国新女界杂志》在第五期以《以身殉足》为题转载《宋观察康复为沭阳徐氏妇以身殉足事致江苏总会书》(原载奉天《通报》)[8],在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受到沉重打击下,女性主义文化传播的路径被引向“二十世纪之世界,女权昌明之世界也。”[9]“女权”成为民族国家被殖民与侵略后男性遮蔽羞辱的挡箭牌,成为男性“过量的政治焦虑”下自我释政治压力的途径。“相夫教子,使成功名,此间接以报国家者。若夫能进以为直接之行动,则为国家革秕政,如玛利侬之以血浴自由,苏菲亚之以身殉民贼,皆可师也;为国家御外侮,则冯媛之持节绝域,如木兰之执戈从戎,皆可法也”。“他日义旗北指,羽檄西驰,革命军中必有玛尼他、苏菲亚为之马前卒者。巾帼须眉相将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10]。此时期的女性期刊还发表了大量的女性政论文、翻译作品,但从这些不同题材、体裁的作品来看,它并未反映女性作为独立体应该具备的社会身份。
作为前20年女性解放典范的秋瑾,亦在国族话语之框架下进行民族革命、种族革命的女权宣扬,在其创办的《中国女报》第二期上,秋瑾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人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索手。”秋瑾倡导男女平权,其目的是号召男女并肩去拯救国族。1904年创办的苏苏女校,号召“注重兵操。练习体魄.提倡尚武精神,做女军人的预备。”[11]1905年1月,宗孟女学在建设新校舍后即组织国民女学会,“(成立)仪式有演说、兵式、体操、西乐、西国影戏、焰火等”[12]。在辛亥革命前,国族主义立场及男权话语下的女权言论并没有从女性的社会、政治权力需求出发来考虑女性被压抑的问题,而是完全服从于国族救亡这一民族叙事,并且女性一直从属于边缘地带。虽然女性期刊大肆宣扬女权、塑造新女性典范,女性在男性化的宣传中渐进为政治工具,女性本身具有的性别特征、内在主体意识被湮没,甚至出现鼓吹以牺牲女性身体来换取革命和救国的话语[13]。如海天独啸子的《女娲石》,虽然是在政治语境下的女性启蒙与女权革命之作,但其暗隐的性别歧视和奴役彰显了女性觉醒意识的缺失。
虽然也有女性指出“即有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志者,亦必以提倡望之于男子。无论彼男子之无暇专此也,就其暇焉,恐仍为便于男子之女学而已,仍为便于男子之女权而已,未必其为女子设身也。”[14]在《女学报》上,还刊登了一篇《讲女学先要讲女权》的演讲稿,它认为“讲女学是为救国起见,讲女权是为女学起见。”[15]龚圆常认为:“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日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日非巾帼。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且男子既可以权利赠人,必其权利之范围恢恢乎。”[16]尽管男性率先倡导女权,但一些女性却清醒地意识到男性无论怎么高呼女权、男女平等,女性依然摆脱不了依附于男性的命运。虽然男性在国族话语与女性启蒙的宏大叙事上,始终张扬着挽救国族命运与妇女平权共构的姿态。但他们把自身的政治缺陷归结到女性的身上,并对其提出批判,认为国族之积弱源自女性落后、愚昧的品性和对男权的依附性,女子的羸弱无知,既是“天下事之最难堪者,莫如以此较而生优劣”[17,p7]。也是男子“消耗国是之心,摧挫风云之气”[17,p8]的累赘,他们一方面痛心疾首地批判女性“柔顺”“愚鲁”等恶德,一方面又怕女性真地进行“造反”,破坏其高高在上的男权地位,这也正是两性之间性别冲突的根源。男性对女性启蒙话语的设计,是在男性陷入救国和治世的危机图景下对权力的转移言说。女性并没有完全陷入男性启蒙话语下的救亡运动中,而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早在《女学报》创办之初,先知的女性就提出了妇女参政的要求[18]。1903年,林宗素在《女界钟叙》上说:“中国女权之变,于今为极。虽然苟丧失权力者,仅我二万万之女子,而彼男子者,举凡参政、选举、代议、请愿、言论、出版各自由权,皆完全无缺,则吾国今日犹不失为日本。……女子者,诞育国民之母!……故今亡国不必怨异种,而惟责我四万万黄帝之子孙;黄帝子孙不足恃,吾责夫不能诞育国民之女子。”[19]女性要独立,首先要突破男性为其编制的“国民之母”的光环,希望女性能够“断绝其劣根性,而后恢复其固有性;跳出于旧风气,而后接近于新风气;排除其依赖心,而后养成其独立心”[20]。并且,在男性的操纵下,《女子世界》展开了关于女权与女学的争论③,虽然最终女权服膺于女学,但在之后的女性期刊中引起了波澜壮阔的女权之争。
在国族话语与民族生存出现突变几近断层的临界点,女性以启蒙者的姿态进入政治领域,并附带着强烈的男性特质,女革命党、女豪杰、女国民这些英雌形象成为女性报刊探讨的主流话语。在民族、女性双重弱势的时代,赋予弱势的女性拯救弱势民族的历史重任,不能不说是民族的焦虑,也是政治语境中呼吁女性启蒙的本因。丘逢甲为1902年陈撷芬主编的《女报》题诗时写道“唤起同胞一半人,女雄先唱维新”[21]。把女性的崛起与维新联系到一起,依然没有脱离民族救亡活动的话语权。1904年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杂志,其“传记栏”从国族的立场出发,宣扬、倡导妇女解放之路,极力宣扬“军人之体格”“军人世界”,提出女性新“规范”,并成为《女子世界》宣传的重点。此时的女性期刊,男性介入的成分占据着一定的比重,如《女子世界》的灵魂性人物金天翮、柳亚子等,虽然他们积极地参与、鼓吹女性解放,但其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22]将女性置身于国家兴亡高度,并直指“强国保种”的政治意图。同时,那些基于传统女性生存状态的剖析,对束缚其自然性发展“纲常礼教”的批判,提出一系列改造传统女性的论说,成为早期女性期刊的典范。虽然这些言论对女性的启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利于传统女性走出历史的窠臼,转向具有现代性的女国民身份发展,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其背后所涌动的男性话语权,此时的女性期刊(也包括部分由男性创办的宣传妇女解放的期刊),并没有真正地探讨女性自身真实的社会体验与政治诉求,那些兴女学、女子职业学校等倡言,只不过是女子参与国族革命的副产品。在民族救亡的宏大叙事下,这些女性报刊大肆宣传女性解放的主张促进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并促使女性做出了可行性的具体举措。在社会层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是女学及女性留学生的出现。如1898年5月31日经正女学堂在上海成立,虽然学生只有20余人,只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但它是近代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堂,开启了女性接受社会教育的新篇章。之后,全国自上而下提出兴建女学的主张,为女子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国家层面上的许可与保障。到1909年,国人自办女学堂有308所,学生14 054人[23]。女留学生最早的记载是由教会资助的金雅妹,于1881年留学美国。随后女性的留学是以伴读身份出现,如1899年浙江的夏徇兰到日本留学。1903年前后,自费女留学生,如秋瑾、林宗素、何香凝、陈撷芬等。1905年湖南官派20余名女性留学日本,此为官派女留学生之始。二是女性身体的解放:废缠足运动的兴起。最早的废缠足问题也是由教会提出,真正提到社会层面的是1897年全国各地出现的不缠足会④,之后是女性自身成立的杭州放足会(1903年2月)⑤,从此由男性倡导、女性报刊宣传转化为群体性的社会现实行动。到1905年,湖南、湖北、广西、江苏、浙江、河北、山东、山西、甘肃等全国10多个省都成立了不缠足会。三是女性成为社会的独立存在的个体:女记者、女编辑、职业女作家。最早刊登女性作品的报刊是《瀛寰琐纪》,开女性文学走出闺阁之先锋,而后到1898年《女学报》创办前,女性发表作品于报刊上属于无意识行为。随着晚清报刊商业化转型和稿酬制的出现⑥,成为文人身份转变的一个契机点,即职业报人、记者、作家、女翻译者出现,成为社会一个新兴职业群体。其中最成功的典范是黄翠凝,她靠稿酬来维持她和儿子张毅汉的生活,并将张毅汉培养成职业小说家。
从《女学报》到秋瑾就义之前,这段时期的女性报刊始终围绕着思想启蒙、参与民族救亡进行宣传。在报刊媒介与社会革新思潮的双重作用下,很多女性接受新学、走出家庭、留学国外、涉足社会职业,逐渐成为经济独立的个体。随着经济上的独立,媒体认知功能的开掘,新知识女性、报刊、政治权力构成她们思想嬗变的三个支点,她们以“新女性”的身份通过新闻媒介(报刊)来传播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女性独立之呼声。所以,在秋瑾就义后,报刊界形成了“秋瑾文学”的热潮,这种文学表述一旦被转嫁到政治层面,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
二
1907年7月15日,在徐锡麟案之后,清政府将秋瑾斩首。此案一爆发,迅速引爆媒介的舆论导向,报刊一面报道和追踪“秋案”的最新动向,一面问责清政府如此草率结案的根源。关于秋瑾一案的社会舆论纠结点,在于清政府“零供词”的酷刑和秋瑾革命定性问题。“零供词”必然引发舆论的批评,而“女性”“断头”“革命”成为秋案在报刊上的关键词汇,注定了女性引发的社会共鸣与反思。秋瑾一案在女性报刊界带来的影响是之前的政治启蒙运动转为女性自我身份的体认(“女国民”)与政治身份的认可(参政),争女权、求平等的诉求开始僭越男性独霸国体的公共空间,社会性别角色的融合、颠覆由此而生,在女性参与政治革命发生时,伴随其产生的是性别冲突。
1907年到民国建立前,此时期的女性报刊按办刊地点分国内和国外,在办刊上大多宣传国族主义。国外主要集中在日本,在日本创办的女性报刊主要有《中国新女界杂志》《二十世纪之中国女子》《天义》(1907年)、《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这些女性报刊大多是留学日本的中国女学生创办,她们受当时日本盛行的国家主义思潮影响,如《中国新女界杂志》以造就合格的“女国民”为办刊特色:“欧洲诸强国深知其故,对于女界实行开明主义,与男子受同等之教育,其爱国之理想,国民之义务,久令灌注于脑筋。故其女国民惟孜孜以国事为己责,至于个人私利,虽牺牲之不惜。”[24]而何震、陆灵素等主办的《天义》,则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代言者,它强调:“故欲破社会固有之阶级,必自破男女阶级始。所谓破男女阶级者,即无论男女均与以相当之教养,相当之权利,使女子不致下于男,男子不能加于女,男对于女若何,即女对于男亦若何。如有女下男而男加女者,则女界共起而诛之,务使相平而后已”[25]。在国内,主要集中在上海,大约有10余种,北京、天津、苏州等地也出现了多种,最有影响的是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和因秋瑾而创办的《神州女报》(1907年11月创刊于上海,至1908年1月共出3期)。《中国女报》仅出2期,第3期因秋瑾的就义编而未刊。从现存的2期看,启蒙与革命是其宣传的两大主题。女性独立的前提是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摆脱对男性的依附关系。“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札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26]从依附男性的“囚徒”与“奴隶”身份中解脱出来的前提,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不致坐食,累及父兄、夫子了”,重享“归来得家族的欢迎,在外有朋友的教益,夫妻携手同游,姊妹联袂而语”的快乐。追求平等与独立只是《中国女报》编撰思想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是对女权的诉求,它不同于之前女性报刊对女权的阐释,而是将女权的获得路径与实现目标上升到革命的手段与女性国民的身份并与国家发生关联。“国民者,国家之要素也。国魂者,国民之生源也。国丧其魂,则民气不生。民之不生,国将焉存?故今日志士,竞言招国魂,然曷一研究国魂之由来乎?以今日已死之民心,有可以拨死灰于复燃者?是曰国魂。有可以生国魂、为国魂之由来者?是曰大魂。大魂为何?厥惟女权!”[27]女权被誉之“大魂”,是因为“女界者,国民之先导也。国民资格之养成者,家庭教育之结果也”。而当今国家与民族的积弱,实女性沦沉于黑狱之过。解救女性出地狱之方法,非“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德育、“人人尽复其天足”的体育与“女子无才便是德”智育所能完成的,“故振兴女界,万绪千端,挈领提纲,自争女权始”。争女权的终点是“还以助男子,共争主权于异族,我女子之天职”。女权从小家中的平等上升到抵御异族入侵的民族国家之高度,这也是《中国女报》的独到之处。《神州女报》是为纪念秋瑾而创办,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轩亭断头死,神州女报始。神州女报始,头断心不死。我今题此偈,一泪凝一字。一泪凝一字,吁嗟我姑姊。”其实,《神州女报》的影响还在于它与当时宣传“秋瑾案”的报刊共同实现了新闻舆论干预政治的任务。首先,它在第一期设秋瑾流血之纪念专题(其一:临刑之惨状;二:冤狱之铁证;三:临刑绘影),首曝清政府之残酷。而后刊登的秋瑾诗文多宣传女权之作,可以看作是为秋瑾“反清革命者”身份的洗白。在“舆论”栏将清政府杀秋瑾之法与参与人员等进行质疑,而后大量挽联、挽诗的出现,从民众的角度深化秋瑾之冤,可以说,从编辑理念与宣传策略上率先占据读者心理,形成一个反清的读者群体。而后在全国媒介的推动下,清政府被迫妥协。舆论成功地颠覆了浙江官府判断秋瑾为革命者的事实,为女性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国族革命树立了典范。可以说,《神州女报》是女性报刊参加辛亥革命的预热宣传。
1912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女性报刊出现了一个分界岭。之前,女性报刊基本处在由改良与革命过渡与并存时期,受维新派的影响,早期女性报刊重启蒙宣传(倡女学、通女智、反缠足成为报刊核心词汇),而在秋瑾、何震等留学女性革命思想影响下,女性报刊走向运用革命与暴力的手段进行政治革命的宣传,女性与民族、国家、社会的关系成为核心词汇。尽管自戊戌变法之后女性独立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始终没有绕开或者说突破男性制衡下的“男权体制”,即使男性假借女性之名发出女性启蒙、革命、独立的性别叙事,但依然是带有强烈的功利性、策略性的男权话语。最为代表性的是《妇女时报》,它总共出版21期,根据它的编辑思想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创办到武昌起义前,共出版3期,“本报以提倡女子学问,增进女界知识为宗旨”。号召女子与男性“共担平分天下事”。着重宣传女子教育与职业的问题,还根据女界及社会现状提出在固守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西方:“贵于师人之所长,以补助我之所短。尤贵于弃人之所短,以保守我之所长。”[28]提倡女界宜结为团体和研究军事、武力救国[29]则为之前女性报刊所未有。第二个时期为武昌起义后到1914年前,共8期。此时国内女界发生了新变,曾经弃笔投戎亲自组织北伐队⑦的革命女性,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女子参政运动,受此影响,《妇女时报》鼓励女性参政的文章有20余篇。第三时期为1914年到1917年终刊,为《妇女时报》半新半旧时期,将在第三部分详述。还有部分女性期刊沿袭传统,但也出现革新的表象,即将启蒙时期的女学与革命时期的女权勾连起来,如南社曾兰创办的《女界报》,还有潘连璧主办的《女子国学报》、沈佩贞《女学日报》、亮乐月女士主笔的《女铎报》等。民国始肇,关于国家政权的建设,南京临时国民政府并未有一个科学的建构方略,在制定国家政权体系过程中将女性排除在外,与领导者早期倡导的男女“平权”思想背道而驰,必然引发参与国民革命的女性领导者和政界精英女性的强烈反对,她们要求在参与国家政权建设的过程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考查此时期关于女性参政问题的报道与论说,已经超越了性别界限⑧,是继“秋瑾案”之后报刊上关于女性问题的第二场舆论风暴。但结果却相反,女性参政的诉求并未在倡导“三民主义”之一“平权”的南京临时政府实现,到袁世凯政府,更无从谈起。酝酿了10多年的女性与男性平权、参政的政治诉求彻底失败。
虽然女性利用报刊鼓吹参政与女权⑨的理想失败了,但她们办刊与实践的策略却发生了变化。其一,部分女性报刊借助男性的力量或资助情况减少,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团体做支撑,如唐群英在北京创办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本部机关报《女子白话报》和通过湖南女子参政同盟会创办《女权日报》,张汉英等创办的万国女子参政会中国部机关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等。其二,为获取参政的合法性,西方女杰再次成为女性报刊宣传的对象,并与西方参政运动的女性联手共同推进女权运动。1912年4月5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南京成立前(4月8日成立)就收到英国女界赞同要求参政电:“全英急进女子参政团对于支那妇人之苦战奋斗,敬申祝意。并愿彼辈防止男子垄断政治权利,速见成功,使妇女政治上之平等,首为支那妇人得,开世界女子参政之新纪元,作全球文明各国之模范。”[30]1912年9月5日,神州女界协济社张昭汉、陈鸿璧共同拜会嘉德夫人[31]。9日,南京女界接待嘉德夫人一行[32]。20日,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嘉德夫人、马克维夫人、解古柏斯女博士到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召开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做演说[33]。女性报刊纷纷刊登相关图片进行报道⑩。其三,用实际行动推动女子参政运动的进展。1912年1月5日,林宗素代表女子参政同志会向孙中山提出女子参政权利[34],因孙中山迫于压力否认其当初的承诺,林宗素发表《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林宗素宣言》[35]以示反驳,她强调:“要求参政权,乃女界同胞同具之心理,乃谓系宗素个人思想、个人行动,宗素虽无状,亦甚耻独为君子也。”[36]林宗素宣言很快引起女界的连锁反应,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书参议院[37]、女界协赞会(后改名神州女界共和协济社)上书孙中山[38],1912年2月22日,女子同盟会发表宣言:“本会之设,以助民国促进共和、发达女权、参预政事为宗旨。”在其宣言后有大总统批词:“同盟会本为本总统所发起,今女子有同盟会之设,自是本总统所赞成。惟此简章未臻妥善,必当大加改良。申明本会之目的,尽力提倡民生主义,以继本会之进行,庶于吾国前途有所补益也。”[39]在回复语中,孙中山用民生主义替代了民权主义,否认女子参政的合法化。沈佩贞在《男女平权维持会缘起》中表达了女性对南京政府否定女子参政的愤慨:“民权复矣,女权犹未也。女子亦国民之一分子,女子无权,不特为文明国之缺点,即揆诸民权二字,亦有不完全之处。”[40]3月11日,南京政府公布《临时约法》。
女性由参政到共同建构国族体系,并将女性话语权置身于民主性要求,是在几千年来性别冲突发展到极点的另一种转向与替代,也是在现代性女性思潮冲击下对自我身份的体认。女子的参军、参政活动,实际追求的是性别上的平等,“吾人所求者为自由,而不平等则自由二字无意味,故求平等”[41]。1912-1913年间女性报刊有16种,这些报刊是当时社会女性发表政论的载体,其关注的焦点聚集在女权和获取女权的路径上。作为创办者或主编的唐群英、张昭汉、张汉英,她们曾加入以文学倡言革命的南社与辛亥革命的队伍,民初跻身到女子参政运动的核心,这些政治阅历与社会活动不仅给她们带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清楚地认识到性别意识是实现男女平权的最大阻力,而且认识到报刊舆论对当政者的影响。从晚清以来的女性报刊共构“国族革命”的责任意识转移到民初女性报刊参与“国家建构”的身份认同,进而以激进的甚至暴力的手段来抗争当局拒绝女性参政的政策。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语境下,实现女性、男性、社会权利三者之间平衡是女界在民国政体下所要建构的新秩序,可居主导地位的男性对女性的传统地位沿袭及认可与女性追求身份的社会体认构成不可协调的矛盾,并陷入对垒之境,晚清国民积弱源自女性之说、鼓吹女性参与及承担起国族救亡之责任的言论,已成为过期的旧船票,严重侵犯男性权力的女性参政、平权要求亦必在新政权下被打压下去,用“民生”置换女性的“民权”,成为民主政权的遮羞布。当妇女解放运动由启蒙思想上升到从性别层面重新分配社会权力时,性别冲突就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中的主要矛盾,主张三民主义的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女性参政,幻想复辟帝制的袁世凯政府更不可能答应,用强权封杀、压制对立的舆论成为当权者的首选。于是,在1914年后女性报刊出现了“复古”的逆流。
三
受“二次革命”的影响与袁世凯政府对报刊媒介“舆论”的严控,1914年到1919五四运动之前,女性报刊出版数量大大减少,办刊的旨趣与鸳鸯蝴蝶派主办的期刊一样走向了消闲。1914年3月2日,袁世凯政府颁《治安警察条例》[42],其规定女子不准加入政治结社(第八条)及政谈集会(第十二条)。3月11日,颁布的《褒扬条例》[43]第一条规定“妇女节烈贞操,可行风世者”。受褒扬。1917年11月20日,段祺瑞政府颁布《修正褒扬条例》[44],第一条褒扬“节烈妇女”,并在细则中规定褒扬的范围。这两次《褒扬条例》又将妇女拉回到封建时代,女性十余年的思想启蒙、女权革命运动遭遇到禁锢。曾经的女界精英在遭遇政治挫折后逐渐淡出,此时出版的女性期刊大部分出自男性之手,女权运动陷入低谷。
1914年12月,《女子世界》在上海创刊,1915年7月停刊,共出6期。此时正是袁世凯进行复辟帝制时期,给《女子世界》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编辑王钝根、陈蝶仙,主要撰稿人中有20位南社社友。此时的南社已经失去了早期的革命气息,大部分社友转向了文学创作活动,成为职业报人和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办刊宗旨出现了规避政治、迎合市民阅读需求和商业化的转向,反映了他们的政治态度。“前项各种文字类取高杰端丽之作,洵足以当‘优美高尚’四字之品评,于文学上取体尤称美备”。且在投稿润例上,“工艺、家庭、美术、卫生、杂俎分三等自三元至一元;闺秀文字附照片者照上例倍酬”[45]。“颇饶趣味,亦灌输文明发育道德之一助也”[46]。从上述《申报》的两则广告看,《女子世界》已远离女权话语,注重实用,将女性的言论重新拉回传统,从出版的6期杂志看,“意在榆扬中外古今贞孝节烈,敏慧义侠之女子,用作女界楷模”。尤其是“文选·扬芬集”栏,为那些节妇列女唱赞歌。在发表的闺秀作品上,亦大多是感伤离别的闺阁之作,缺乏了之前女性报刊所载女性作品的政治气息。1915年末至1916年初在成都创刊的《妇女鉴》与《家庭》,其宣传主旨可以说是女性解放思想的倒退。《妇女鉴》在发刊词上开宗明义:“不主妇女之当参政,不嚣然以倡妇女之权。……求妇女之行有德,求妇女知利害自爱自重,求女子之能孝亲,求妇女之能相夫、能教其子女,求妇女家庭之生涯,求妇女知爱国。故本集有论说,以道妇女之时弊;有古今女德轶闻纪录,为进德之模范;有家庭事业以助治家之道;有算学、文学以导妇女之未能进学者”[47]
到了1915年,《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等女性期刊在编辑思想上发生更大的变化。《妇女杂志》(1915年到1919年改组之前)将否定女权宣扬贤妻良母主义为编辑的核心思想,倪无斋在发刊词四中写道:“今新学进,矫激之徒愤而有作,亟亟以女权为倡,九年之水,挟沙决堤而行,固其宜也。……欲女权之振。必求女德之尊;智识者,德之基;文艺者,德之符。各努力学问职业之途,勿纷驰声华煊烂之场,以巾帼而并须眉,何多让焉。”[48]在《中华妇女界》创刊号首篇论说《妇德》中,同样否定女性参政运动:“争参政权,于事无补,徒资噱谭。余游绥远,有女士某,挟一客至,扬言将集巨资,开矿拓边,出入幕府,招摇无忌,盖其志益以荒矣。”[49]承认女性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作用,认为女性应该承担起国家的责任,前提条件是必须遵守妇德,尾随于男子之后。在《妇女杂志》第一卷第一期还发表了梁令娴的《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她指出:“妇人在家庭中实有莫大事业,苟能尽相夫教子之天职,即能为世间造福”“妇女最大之天职,岂非在相夫教子?而杂志发刊之本意,又岂非遵此天职,为国家中造多数之贤妻良母耶”[50]。同时,她在《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认为女性应恪守“女训”,“欧风东渐,女权论昌,而汲其流者乃至有参政权之要求,有法律学堂之建设,馐馐屡舞,良又足嗤。……今必事事与男子争道,谓必如是乃为平权,一何可笑。此俗论之当办者又一也。孔子曰,君子中庸知,彼两说皆非则中道从可择矣。外国女学常以养成良妻贤母为宗旨。吾国女训,亦在相夫教子。夫能相夫斯为良妻,能教子斯为贤母。妇人天职尽于此矣”[51]。女权主义倡导者曾留日学生朱胡彬夏认为:“学问为立身之基础。有学问而后心思灵巧,五官敏锐,感觉真确,道德坚厚。……为人也必圆通广大,无所不能,烹饪也,裁缝也,治家教子也,著书立说也,皆以极寻常之举动,演出极高妙之事实。”[52]《妇女杂志》与《中华妇女界》出现否定女权,倡导女性走上“贤母良妻淑女”之路,并不是当时女性期刊的个案问题,而是与整个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民国建立后的女权之争,并未促进女性继续走上人性解放、社会独立的道路,反而越来越趋向于保守,女子“不能参加政治结社”“不能参加政谈集会”[53],同时,女子要“一、孝行卓绝,着闻乡里者;二、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54]在政府的主导下,报刊开始报道贞女烈妇。如《妇女时报》针对接受新式教育殉夫而死的女学生评论到:“朱烈女之死,非特个人交谊上之光荣也,亦非我孝感一邑之光荣也,亦非我全国女学界之光荣也,是我中华古国对于世界上之光荣也,幸记者有以表彰之。”[55]“城内蓬莱路爱群女学校学生朱佑荣,因共夫黄廷在河南陕州电报局蓄病故邃以身殉,氏姑金氏禀请交通部从优抚恤并请旌表,近由该部批准。……此批到沪后,该女校现己拟就征文启,以期表扬烈妇,并闻氏之家属拟於江宁公所开追悼会”[56]“余对予女子教育之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可以维持家庭而已。惟对于智识技能之方面,则辈设法研究,以谋发展。则不能适应于文明日进之时势也。”[57]“以智育、德育为我诸姑姊妹道也,……以实业女工为家庭倡也。”[58]《妇女杂志》与《中华妇女界》出现褒扬贞妇烈女,显然与晚清民初女权思潮背道而驰,除了民国3年政治趋向于反动外,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依然是男权主导的社会,此时的国族话语叙事不再是主流,因此,男性“惧怕”女性的“觉醒”。与之同步的是,由先知引入的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走上了“本土化”的变异之路。“在接触某种新话语之初,人们是被动的、受话语操纵的,但是随之而来的则是操纵和篡改话语,先是教条主义,而后是修正主义。”[59]在女性期刊与女性文学共同发展过程中,女性逐渐由被动变成主动,即在期刊创办、出版过程中,女性由参与投稿、主笔某个专栏到自筹资金创办期刊。虽然女性从被男性书写的对象转变为书写者,但是“所写的女人多不免以男子的理想或成见为标准,或是贤媛,或是荡妇,都合于男子所定的范畴”[60],“女人在提笔写作的时,那些男性价值如何早已进驻其中”[61],还不能逃脱男性中心观,出现“贤妻良母”现象是女性创作题材反馈到文学主题的必然结果。
1915年的《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汇刊》与1917年的《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为女子学校创办,两个杂志侧重于家政与学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还侧重于传统女教宣传,仅第二期就刊登了27篇列女传。1916年的《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则与上两种杂志不同,在内容上比较丰富,设有论著、教授、课选、实验、游记、学术、演说、参观报告等栏目,上面刊载的作品基本上与教学活动紧密相关。但其“课选”栏所涉内容非常广泛,在蔡松坡逝世后,曾发表邓颖超的《对于蔡松坡先生逝世感言》。与同时期的学校女报相比,《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会报》的独特之处在于登载了9部学生创作的小说。这些小说在国家叙事下凸显了女性主体身份,贴近于生活。
从《女子世界》到1918年的《女鉴日报》,女性期刊集中于对女性身份的认定上,女性在社会中究竟处在什么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在政治场域的高压下,女权运动出现倒退及回归传统的逆流,女性身份在复兴传统“女德”与重构闺阁文学的路径上徘徊,即使在女性学校创办的女性会刊,也在隐形中排挤着女权的论调,以女性回归家庭生活的实用教育为主体进行教育活动。同时,曾经为女权运动活跃于政界的精英女士在参政运动失败后逐渐淡出政治场域,回到女性启蒙的女学教育活动中。用“贤妻良母主义”置换“三从四德”的女性观,成为此时期女性期刊的特殊符号,也是女性在民初新旧杂糅的社会中对自我身份即性别意识认同后无奈的妥协,也进一步加剧了本时期女子世界建构在中西、新旧之间的游移。陈蝶仙等建构的亦旧亦新的才女世界,将家政技能作为新女性的重要学习内容,而非提倡女性的智力教育或专业教育;强调女性为服务家庭学习,而非为个人独立和发展学习;强化女性教育的伦理性质而非智力性质,为传统妇德和女性价值观留下了生存余地。
结语
晚清以来,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条件有两个:一是西方妇女解放思潮,它为晚清女性走出闺阁参与国族建构提供了话语权。由男权搭建起的女性观“女子无才便是德”与女性失去自我主体存在生存意识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史,女性对男性的“包容”“忍耐”与生活的“幻想”、生命的“寄托”成为一生的追求,她们缺乏自我独立与自我批判的更新欲望,所以需要借助一个外力来实现。在中国整个民族语社会陷入困顿之境时,西方女性文化的介入为中国先知的男性提供了一个重新诠释女性与国家、社会的新视角与话语资源。亡国灭种的紧迫使得意欲革新的男性对西方学说来不及消化便进行了生吞活剥式的移植,女性在男性的“提携”下似乎寻找到了女性解放的机遇,于是同男性一起构建男女共建民族、民主国家的梦想。“国民之母”的身份与承担国族建设的重任共同成为早期女性期刊宣传的主流话语,在男性的引领下女性逐渐成为社会独立的个体,成为批判传统的女权主义者。二是处在亡国灭种危机中的男性,急需寻找解脱危机的支点。一方面需要女性强大起来,为其构想的新国度出份力量,另一方面又希望女性保持传统女性那种对男性的依附关系,所以在共同建构新国度时,女性与男性达到了平衡,男性为女性的觉醒而摇旗呐喊。当女性从国族话语走向女权话语时,传统男女社会权利分派模式演变成二者对抗模式。强大的男权话语终将刚崭露头角的女性性别意识打压下去,重新回归到传统女性服务于家庭与男性的“贤妻良母”的职位上。之所以出现这种处境,是因为它们忽视了承载几千年的传统与男权,违背了历史真实存在,只是简单地处理女性在传统与国家之间的地位,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共赢与裂变。
再回头看1898-1918年间的女性期刊,它们的出版发行始终没离开政治场域下的监督,并在政治话语的干涉下进行调整。从宣扬女性启蒙的兴女学与身体解放来实现国族救亡的政治目的,到参与国家政体建构与男性平分权利的女权运动与性别意识的深化,再到重兴女学与重塑女性传统道德。同时,在女性期刊中,由男性为女性代言的女性话语形态的普遍存在,使得晚清以来报刊上署有某某女士(女史)的作者雌雄难辨。在男性建构的女子世界中,女性却严重地缺席,在性别话语的政治生活中,女性无法摆脱男权下的附庸地位,女性只是男性进行国族救亡与革命过程中营造“他世界”的一个策略。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强烈的民族群体意识自觉的遮蔽下,性别意识下的自由、平等、权利等都被强制性地贴上了国族救亡话语的政治标签。有意的夸大或虚构女性在国家与家庭中的地位,促使传统女性脱胎换骨,成为女国民的真实企图是缓解男性的民族焦虑与压力。在西方女权话语的指引下,只强调女性的义务,抹杀或掩盖女性应该享有的权利,男性将凌驾于女性之上的男权如无形的指挥棒操纵着女性意识的发展。虽然女性独立呐喊之声充满着性别冲突的张力,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政治环境下,女性所引发的“性别冲突”是如此的弱小,以致在民族政治斗争的旋涡下很快被荡平。尤其是在妇女解放、民族革命、国家政权建构三者被搅到一起后,女性所追求的性别意识、独立意识失去了主体诉求的政治立场与存在空间,成为国族革命话语下的点缀。在男性参与者政治场域内不断左右着女性服务于社会需要和性别期待的特定时代,女性报刊出现女权主义与走向回归传统的多元建构,其背后实为男权体系操纵文化建构的结果。
①参见《女报》(《女学报》)1902年3、7、8-9期,1903年3、4期。
②具体论述见夏晓虹.晚清女性典范的多元景观——从中外女杰传到女报传记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6(3):17-45.
③相关文章有:竹庄.论中国女学不兴之害[J].女子世界, 1904(3)1-7;亚卢.哀女界[J].女子世界,1904(9)1-9;初我.女界之怪现象[J].女子世界,1904(10)1-4;丹忱.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J].女子世界,1905,2(3)1-3。丹忱这篇文章后,此次争论结束。
④报刊上出现大量相关报道,如谭嗣同.湖南不缠足会嫁娶章程[J].时务报,1897(45):6;黄世祚,黄守孚.嘉定不缠足会章程[J].时务报,1897(50):12-14;沈逝水.不缠足会广议[J].时务报,1897(50):14.
⑤关于此天足会,见1903年《浙江潮》(东京)第2期,江东:记杭州放足会,杭州放足会第二次调查信,杭州放足会摄影。
⑥最早的报刊稿酬制见1877年10月17日《申报》刊载广告“有图求说”:择其文理尤佳者一卷,愿送润笔洋20元,次卷送洋10元,便即装印成书出卖,余卷仍发还作者,决不有误,惟望赐教为幸。
⑦如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沈警音任队长;湖北女子北伐队,吴淑卿任队长;女子国民军,薛素贞发起;女子北伐光复军,陈婉衍发起;女子军事团,葛敬华发起;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吴木兰发起;女子尚武会,沈佩贞发起;浙江女子扫荡队,尹锐志姐妹组织;广东女子北伐队,徐慕兰、宋铭瑛组织;安徽女子北伐队,陈也月负责。
⑧除女性期刊外,发表女子参政的报刊主要有《亚东丛报》《东方杂志》《大同报》(上海)《新世界》《大共和日报》《浅说画报》《教育周报》(杭州)、《国民》(上海1913)《墨海》等。
⑨此时比较集中鼓吹女子参政运动的女性报刊有:1911年创办的《妇女时报》《女界杂志》《妇女日报》《女铎报》(上海);1912年复刊的《神州女报》《女权月报》《女权报》《中华女报》(上海),《女子白话报》(北京)《女子国学报》《女学生杂志》;1913年创办的《女权日报》《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上海)《神州女报》等。
⑩如:南京子女参政会欢迎嘉德夫人及解古柏斯博士马克维夫人大会纪念摄影[J].亚东丛报,1912(1):1;欢迎万国女子参政会长嘉德君图[J].万国女子参政会旬报,1913 (1):3.
[1]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历史资料[C].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133.
[2]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840-1918[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 134.
[3] 新会女史卢翠.女子爱国说[J].女学报,1898(5).
[4] 石川半山.论女权之渐盛(日)[J].清议报,1900(47-48): 3044-3097.
[5] 斯宾塞.女权篇达尔文物竞篇合刻[M].马君武,译.少年中国学会,1902.
[6] 君武.弥勒约翰之学说[J].新民丛报,1903(29)(30)(35).
[7] 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M].台湾学生书局,2000:81.
[8] 以身殉足.中国新女界杂志[J].1907(5):1-5.
[9] 自立.女魂篇[J].女子世界,1904(4):9.
[10] 亚卢.哀女界[J].女子世界,1904(9):7.
[11] 苏英.苏苏女校开学演说[J].女子世界,1904(12):5-7.
[12] 宗孟女学校特启[N].警钟日报,1905-01-12(3).
[13] 亚卢.女雄谈屑[J].女子世界,1904(9):10.
[14] 陈撷芬.独立篇(录女学报)[J].鹭江报,1903(33):7.
[15] 演说:讲女学先要讲女权[J].女学报,1902,2(3):10.
[16] 龚圆常.男女平权说[J].江苏(东京),1903(4):145.
[17] 金天翮.女界钟[M].陈雁,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18] 新会女史卢翠.女子爱国说[J].女学报,1898(5).
[19] 林宗素.女界钟叙[J].江苏(东京),1903(5):132.
[20] 亚特.论铸造国民母[J].女子世界,1904(7):3.
[21] 丘逢甲.题陈撷芬女士女学报[M]//岭云海日楼诗抄:13卷.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418.
[22] 金一.女子世界发刊词[J].女子世界,1904(1):1.
[23] 陈翊林.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M].上海:太平洋书店, 1930:100.
[24] 炼石.发刊词[J].中国新女界杂志,1907(1):1.
[25] 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 [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819.
[26] 秋瑾.敬告姊妹们[J].中国女报,1907(1):13.
[27] 黄公.大魂篇[J].中国女报,1907(1):7.
[28] 江纫兰.论妇女醉心西法宜有节制[J].妇女时报,1911 (3):13.
[29] 李煇.上海急宜组织女子青年会[J].妇女时报,1911(3): 81.
[30] 英国女界赞同要求参政权电[N].时报,1912-04-05(6).
[31] 女子参政会长之临别赠言[N].申报,1912-09-10(7).
[32] 南京电:宁垣女界昨日(九号)开会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长嘉德夫人荷兰部长解古柏斯女博士及墨夫人[N].申报,1912-09-10(2).
[33] 女界欢迎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纪事[N].申报, 1912-09-25(3).
[34] 女子将有完全参政权[N].申报,1912-01-08(7).
[35] 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林宗素宣言[N].天铎报,1912-01- 23(24).
[36] 女子参政同志会会员林宗素宣言[N].天铎报,1912-01- 23(2).
[37]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N].时报,1912-02-27(5).
[38] 女界共和协济会上孙总统书[N].时报,1912-03-04(5).
[39] 女子同盟会宣告[N].时报,1912-02-22(5).
[40] 沈佩贞.男女平权维持会缘起[N].天铎报,1912-02-26(1).
[41] 女界复报[N].民立报,1912-02-24(8).
[42] 法规:治安警察条例[J].内务公报,1914(7):63-72.
[43] 法规:褒扬条例[J].内务公报,1914(7):85-88.
[44] 修正褒扬条例[J].政府公报,1917(664):9-11.
[45] 优美高尚最新杂志[N].申报:1914-12-05(13).
[46] 介绍新著[N].申报,1914-12-13(10).
[47] 佘余焘.小启[J].妇女鉴,1914(1):1.
[48] 倪无斋.发刊词四[J].妇女杂志,1915(1):5-6.
[49] 汪长禄.妇德[J].中华妇女界,1915,1(1):7.
[50] 梁令娴.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J].妇女杂志,1915 (1):6.
[51] 梁令娴.所望于吾国女子者[J].中华妇女界,1915(1):1.
[52] 朱胡彬夏.二十世纪之新女子[J].妇女杂志,1916,2(1):11.
[53]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法令大全[M].商务印书馆,1924:18- 23.
[54] 褒扬条例[N].申报,1914-3-16(9).
[55] 陈左明瑛.孝感朱烈女[J].妇女时报,1916(19):77.
[56] 烈妇殉夫之哀荣[N].时报,1915-3-31(14).
[57] 汤总长之女子教育方针谈[N].申报,1914-6-28(6).
[58] 张松涛.中华妇女界祝辞二[J].中华妇女界,1915,1(1):1-2.
[59] 金元浦.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270.
[60] 知堂.佐藤女士的事[J].女声,1945,4(2):6.
[61]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4.
Female Press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1898-1919)
GUO Jian-pe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he entry of western feminism into China was based on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en. As a result, women's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and feminist movement wer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The female newspaper from 1898 to 1919 had never been out of the restrictions of male power, which made the women’s liberation characterized mainly as female enlightenment, such as the initiation of women’s education and the abandonment of foot binding, gradually rose to national salvation activities. After the vigoro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movement, it returned to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good wife and good mother” under the interference of men. The multi-construction of the emergence of feminism and returning to tradition in women's periodicals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manipulation of cultural construction by the patriarchal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s; women periodicals; feminism; back to tradition
I207.6
A
1009-9115(2020)05-0019-11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5.00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6ZDA183)
2019-12-19
2020-05-27
郭建鹏(1980-),男,河北昌黎人,博士,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晚清民国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王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