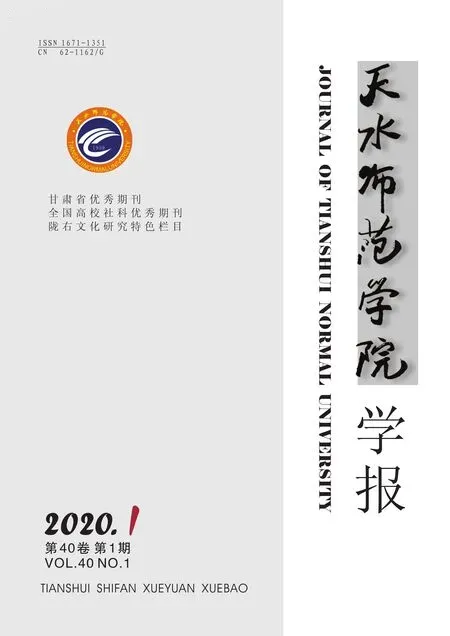儒家义利观的衍化述论
2020-01-09张卓
张 卓
(西北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自先秦始,义利问题就得到儒家思想家的高度关注和充分讨论。孔子提出“义以为上”;孟子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提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二程与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其中既体现了理论逻辑内在的一致性,又体现了各自不同的理论特点和历史衍化;既有理论思维经验需要总结,又有理论思维教训需要汲取。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
罗国杰认为:“义利观由义利概念、义利关系、义利取向三部分组成,其中义利概念是基础,义利关系是核心,义利取向是根本,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义利观的完整内涵。”[1]方克立认为:“‘义’作为中国古代的重要道德概念,从原有已知威仪、美善、适宜之意,后来逐渐成为表示‘应该’的道德准则与规范的总称。”[2]48“利”泛指利益、功利之意。对义利关系辩论的重点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而价值取向是其核心所在。对于“义”还有另外一层解释,即“义,理也”:[3]491“义”通“理”是为理性的追求,[4]109亦指精神需要。而“利”则表现为物质需要的满足及感性欲求。因而,义利关系又内在性地涉及到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张锡勤认为:“义利观所探讨的乃是道义与利益的关系,还包括了对公利与私利。”[5]22在传统儒家看来,“义公天下之利”[6]50义即整体之利,是为公利,而与之相对的利则是个体之利,是为私利。概言之,“义、利确实代表着特定的道德价值论与道德价值导向,从而广泛地渗透在经济、社会、历史领域中。从经济层面看,义利表现为双重内容:一方面分别代表共同利益与个人利益;另一方面则代表社会规范与经济利益。从社会层面看,义利分别表现为社会团结与个人自由。从历史层面看,义利分别表现为秩序与动力。”[7]由于义利问题包含了多重意蕴,所以其成为传统儒家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
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开启了义利关系问题的先河。众所周知,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是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代,“礼崩乐坏”是孔子视野中的社会现实。为了解决时代问题,重新整合社会秩序,孔子将义与利作为一对重要的范畴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孔子对义利问题的讨论是对“君子”理想人格的界定上肇始:“君子义以为质”、[8]214“君子义以为上”。[8]1241在这里,孔子将“义”作为“君子”的内在规定,并且认为“义”应该成为“君子”日常行为的最高准则。朱熹对此亦做了注解,认为孔子所讲的“义”是根据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理”而处事的。可见,在孔子看来“义”是普遍的道德规范,有其内在价值及普遍性。与“义”相对应,对“利”的讨论则与相反的人格“小人”相关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8]267义与利成为孔子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标准。由此不难看出,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对作为普遍、内在价值和道义原则的“义”的肯定与强调。实际上,在《论语》中,孔子十分赞赏的“孔颜之乐”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由此也形成了传统儒家在义利问题上基本的理论取向。
当然,对“义”的肯定与强调并不意味着对“利”的完全否定和贬斥。“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8]39追求富贵之利是人生而就有的欲望,渴望富贵远离贫贱是人之常情。“邦有道,贫且贱,耻也。”[8]540在一个有道的国家,贫与贱并不是什么荣耀的事情,而是可耻的事情。“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8]453只要行为自身合乎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做一个“执鞭之士”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可见,孔子并不是一般地否定追求财富与地位的欲望,他所不赞同的是为获得利而不择手段并且无底线。“放于利而行,则多怨”[8]253将“利”作为普遍原则,必然会引起诸多矛盾与不满,所以应该正确处理和调节义与利的矛盾。对此,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其一,“义以为上”。[8]1241“义”是普遍的道德规范,体现了普遍的公利,而“利”代表个人的私利,当义与利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应该“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8]80;其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8]1371重视“民之利”实际上就是重视整体利益和普遍利益,在这一层面上,孔子实现了“义”与“利”的转换与调和。正是对“义”与“利”的双重肯定与二者关系上的转换、调和,从而表现出在义利问题上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客观、冷静与宽容。
孟子对义利问题的讨论是以其著名的“性善论”作为基础的,他从“四端”出发,推论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心”,进而推论出仁义礼智四种基本的道德规范。我们且不论这种推论在逻辑上是否具有合理性,仅仅是这种推论本身已经表明,与孔子的义利观相比较,孟子的义利观已经发生较为重大的变化。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孟子明确表明立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9]1从其话语表达的方式上不难看出,孟子的思想是清楚明确的,“利”不在其思考和讨论的范围之内,言说“利”已经脱离正道,孟子思想表现出某种独断的倾向。“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9]206“义”是“正路”,是普遍的原则和当然之则,应该无条件遵守。当然,在《孟子》中也有关于“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9]301等等对物质生活的重视,尤其是关于“仁政”思想中“制民之产”的观点,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惟士为能,若民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9]113孟子的这一思想当然是十分可贵的,并且对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但是,从处理义利关系的角度而言,在孟子看来“恒产”即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是“恒心”即普遍道德意识的前提,但“恒产”本身只具有手段意义,是工具价值,只有“恒心”才具有目的意义,是价值本身。所以,建构起“恒心”这一普遍的道德意识,才可以防止“放辟”、“邪侈”等违反基本道德规范的行为发生。同时,孟子在面对义与利发生矛盾和冲突而需要做出选择时,明确强调“惟义所在”、“舍身取义”[9]205等价值取向,相对于孔子的义利思想,孟子的义利观已然表现出某种独断的倾向。从而表现出先秦儒家义利观在孟子思想中发生的重大转向。
荀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性恶论”的思想家,从“性恶论”出发,荀子明确提出“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3]59荀子充分肯定好利恶害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本性,由此在人性论上形成了与孟子截然相反的两种思维路径。当然,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荀子对人好利恶害本性的肯定并不是其理论的目的,而只是出发点,亦即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和途径解决这一问题。所以,荀子进一步指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3]434对于“好利”、“争夺”、“疾恶”、“残贼”、“耳目之欲”、“淫乱”等等本性不能简单地“顺是”,而应该加以改造。具体而言,“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3]440即运用礼义与法律制度加以规约,从而实现“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也”、[3]279“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3]502“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3]58的目的。
综上,不难看出,孔孟荀尽管出发点完全不同甚至相反,但目的却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在“义”与“利”的关系上,都强调“义”作为道德原则的普遍性、重要性。由于受“性恶论”的影响,与孔孟相比较,荀子更强调“义”与“利”之间的平衡,作为理论性结论,他明确提出了“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3]502的观点,从而表现出对孟子思想的纠偏和对孔子思想的某种回归。
二、汉代董仲舒义利观
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董仲舒的思想无疑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义利观亦复如此。
董仲舒系统建构了以“天”为最高概念的思想体系,他的义利观也是以天为最高依据而展开的。“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11]263“天生之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11]148义养其心,利养其体,孝悌指向的是精神的追求,衣食指向的是物质需要,而礼乐就是为实现成人的手段。如果以此来论证天生而有义利,二者的不可或缺性,这与荀子的“义利两有”无疑有相通之处。但是,义利两有只是董仲舒对义利并存所做的事实层面的说明,并非代表他义利观的基本理论取向。从先秦儒家开始讨论义利问题,对义利关系的处理就成为其实现社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董仲舒看来,义利关系的选择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根本,所以虽是义利两有,但它们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等的。首先,董仲舒从人与鸟禽之间的本质区别论证义利的区别,“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11]53人之与鸟禽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修内心,行仁义有羞耻之心,鸟禽生来只为利。其次,从“体”与“心”的关系论证了义利的区别,“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11]232对于人而言,心之养重于体之养,物质重于精神。基于以上论证,董仲舒明确提出其在义利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2]2194
于董仲舒而言,“谊”即“义”是为合宜、应当的道德与行为,所指向的是一般的道德原则。“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作为董仲舒义利观的总原则,表现出对义自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以及义作为普遍原则是判断行为正确与否的重要标准。“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11]81只要行为自身合乎义,无论结果如何,它都是有价值的、是善的,从而完全放弃了对行为效果的关注,具有较之先秦儒家更明显的动机论倾向。同时,从这一总原则出发,董仲舒将“义”看成是可以脱离“利”这一物质基础而独立自存的东西,“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11]233只要有“义”在,一切问题都能解决,理论显得十分空疏而苍白。由此出发,董仲舒将这一原则推向极致,提出“防欲”的理论:“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12]2188“义”的意义和作用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种提升一方面割裂了义与利的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将“利”或“欲”作为“防”的对象,并以“堵”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种倒退。
董仲舒义利观的出场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汉代在经过文、景之治的修养生息之后逐渐繁荣富强,但汉武帝时期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诸侯官吏奢靡成风,百姓被剥削“贫者无立锥之地”。[12]1042针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董仲舒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义利观,在政治上是为了警醒与规劝君主正确认识义利之间的关系,行仁义之政,以实现国家长久利益与整体利益。他认为“君人者,国之元,发言动作,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11]146“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12]2192“今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者,无怪民之皆趋利而不趋义也。”[11]234百姓更容易看到眼前的小利益,而不容易看到长远的大的好处,而作为圣人及君主更容易看到长远的好处,所以要“显德以示民”,[11]234行仁义作万民的表率,以行教化。因此“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12]2192君主好义则民好义,则国家大治;君王好利则民好利则国家大乱,故君主首先要遵循“义”的道德规范让百姓仿之,才能使君民上下一致共行“义”的道德规范。由此,董仲舒在义利问题上对以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提出了具体要求:首先,董仲舒的“义”主要在于“正我”,是对自我的审视与反省,君主首先要做到以“义”正自身,行仁义之政,正谊明道才能教化民众。其次,对于“利”董仲舒认为是有公利与私利之分的,公利重于私利,且公利可上升为“义”的高度。君主就应该如圣人一般注重长久与群体的利益(公利),而不是争一些眼前的蝇头小利(私利)。“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义)立礼以导之。”[12]2187圣人法天以立道,爱天下之利而摒弃个人私利。“故圣人之为天下兴利也,其犹春气之生草也,各因其生小大而量其多少;其为天下除害也,若川渎之写(泻)于海也。”[11]156-157“古之圣人,见天意之厚于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11]276要求统治阶层不与百姓争利,放弃眼前之私利,不谋求个人的利益得失,以实现长久及群体之利。
尽管董仲舒义利观的提出有其历史原因,但其理论本身的内在矛盾是明显的:从伦理道德的层面,董仲舒将“义”的地位和作用推向极致,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总原则,主张剔除一切功利因素,成为彻底的动机论者。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操作层面,董仲舒又提出了诸如“有功者赏,有罪者罚,功盛者赏显,罪多者罚重”;“百官劝职,争进其功”;“不能致功,虽有贤名,不予之赏”[11]157等等一系列“致功行赏”思想,成为彻底的效果论者。同时,从理论的进路而言,在义利关系问题上,先秦儒家尽管有孟子向“义”的偏转,但是总体上对“利”仍然能够采取较为客观和宽容的态度与立场。董仲舒的义利观尤其是“防欲”观点的提出,“强调道德精神的价值与作用,对于人们超越物欲的羁绊、提升精神境界有着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成为统治者销蚀人们正当物质欲望,只讲道义与服从的工具。特别是由这种义利观引导出的‘损情錣欲’的观点,更开了宋明理学存理去欲思想的先河。”[13]477
三、宋代程朱理欲观
宋代正统理学家程颢首先将义利问题在理论上作了提升:“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14]124并认为董仲舒是“最得圣贤之意”。[14]7朱熹接着程颢在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讲:“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二程在此基础上将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价值观推向极致,明确提出:“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14]124在这一“出”一“入”之间,“义”与“利”便被彻底地割裂并对立起来,成为不相融的存在。从表现形态上看,朱熹不同于二程的粗疏与独断,在义利问题的论证上更为精致。他指出:“正其义则利自在,明其道则功自在。专去计较利害,定未必有利。”[15]卷三十七强调义利不能截然分开,但是“正其义则利自在”实际上是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价值观的另一种注解而已。朱熹还强调:“为所当为而不计其功,则德日积而不自知矣。”[16]73当朱熹将“义”看成是“所当为”时,一方面实际上是对“义”作了理论上的提升,成为“应然之则”的普遍原则,所以是人们必须遵守的;另一方面“义”既然是普遍的原则就不应该有功利的计较,确立了这种普遍的道德原则,人们就会在“不自知”中“德日积”,是对董仲舒儒家动机论的进一步发挥。
从中国古代哲学争论问题的转换来看,先秦的“天人”之辩经汉代的“道物”之辩,魏晋的“有无”之辩,到宋代发展为“理气”之辩,与此相联系,义利之辩在宋代转换为“理欲”之辩。二程从其天理观出发首先对“心”作了区分:“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14]312“人心”与“道心”是人的两种知觉活动,“人心”是私欲,私欲流行是十分危险的;“道心”是“精微”的天理,所以要“去人欲,存天理”。[14]118朱熹对二程的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发挥,“人心是形气之私,形气则是口耳鼻四肢之属”;[15]卷六十二“道心者,兼得理在里面,惟精无杂。”[15]卷七十八“道心”因为有理在其中,所以是普遍化的伦理主体,是普遍理性的代表;而“人心”是耳目四肢的感性存在,从而将义与利、理性与感性对立起来。以此为基础,朱熹进一步将“义”转换为“理”,将“利”等同于“欲”,“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16]72义利之辩被引申为理欲之辩,这种引申首先使“义”成为脱离特殊时空且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存在,成为普遍的行为准则而具有超验性;同时,也包含着对“义”的进一步纯化:“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是所不论。”[15]卷一百二十七传统儒家之“义”经过朱熹的这种“提升”和“纯化”之后,道义论倾向得到进一步强化。
在传统儒家那里,义利之辩总是同公私关系紧密相关联,程朱也从公私关系上对义利问题作了阐述。二程明确指出:“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14]176那么,义与利、公与私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之中?“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则与众同利,无侵于人,人亦欲与之。若切于好利,弊于自私,求自益以损人,则人亦与之力争。”[14]917-918在二程看来,义作为“公”和整体之利是“正理”的代表,可以“无侵于人”,实现“与众同利”;利作为“私”和个体之利,如若“好”之,便会“损人”、“力争”。二程在沟通义利与群己关系的过程中确实看到了义与利、公与私、整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并且强调注重整体利益的重要性无疑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并贬低个体的意义和价值,必然会得出“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14]301的极端结论。与二程有所不同,朱熹从理性与感性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公私关系。朱熹认为,“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16]187在朱熹看来,义即公是普遍理性,利即私是感性欲望,并且进一步将人的感性欲望之私看成“疾疢”和“邪”即道德之恶:“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则其心私且邪”[15]卷十三从根本上否定了感性欲望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可见,从二程强调整体否定个体到朱熹强调理性否定感性,程朱从外在关系和内在关系两个维度实现了对宋代理学理欲观的理论建构。
四、结 语
从以上对儒家义利观历史衍化的简要回顾不难看出,义利问题作为价值观的核心问题得到儒家思想家们的高度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讨论,这种讨论经历了一个不断衍化的过程:先秦儒家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在讨论过程中尽管具有重义轻利的基本理论倾向,但总体上对利还是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态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上仍然是客观、冷静的,并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见解。汉代董仲舒在儒家义利观的历史衍化过程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转折意义,他从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的角度,提出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和“防欲”的义利观,是传统儒家义利观走向极端和独断的一个重要标志,从而也开启了宋代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理欲观的先河。宋代正统派理学理欲观是先秦儒家尤其是汉代董仲舒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这种发展尽管有其理论与历史的合理性,但总体而言是一种理论和历史的倒退,即从对“利”的宽容、客观、冷静到“防”再到“灭”,尤其是将义利之辩转换为理欲之辩,将“义”转换为“天理”,将“利”转换为“人欲”,一方面为“义”这一普遍的价值原则提供了形而上依据,另一方面将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理性与非理性完全割裂开来,从而使儒家的价值观走向绝对主义和权威主义。实际上,义与利、理与欲、物质与精神、理性与感性、理性与非理性是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该而且必须在动态中实现辩证统一,宋代理学试图割裂二者的统一,必然导致儒家价值观走向“空”和“假”,这是我们分析儒家义利观历史衍化所应该汲取的理论思维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