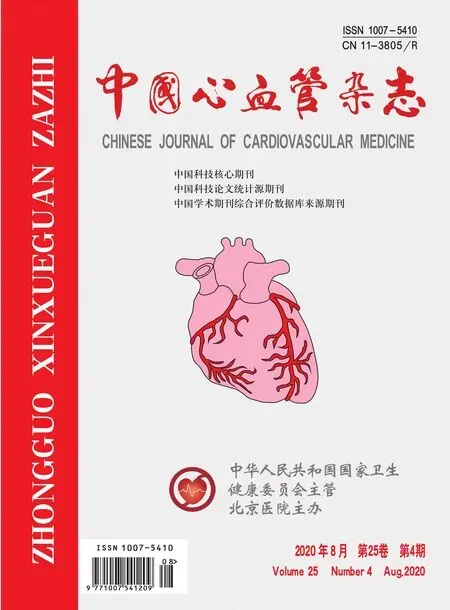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的临床特点及心肌损伤的病理生理机制
2020-01-09方创森何青
方创森 何青
100730 北京医院心内科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自2019年12月暴发流行以来,截至2020年8月23日,全球共计23 057 288例确诊,并已造成800 906例死亡(http://covid19.who.int)。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指出,心肌可能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2019-nCoV)侵犯的主要脏器之一,表现为心肌细胞的变性、坏死,间质充血、水肿,可见少数单核细胞、淋巴细胞和(或)中性粒细胞浸润。全身主要部位小血管可见内皮细胞脱落、内膜或全层炎症;可见血管内混合血栓形成、血栓栓塞及相应部分的梗死。主要脏器微血管可见透明血栓形成。因此,COVID-19的心脏损伤不容忽视,本文主要围绕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的COVID-19的临床特点以及发生心脏损害的可能机制进行探讨。
1 2019-nCoV感染与心血管疾病
COVID-19的临床表现多以呼吸道症状为主,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热(88%)和干咳(67.7%)[1],但心血管表现也不容忽视。哥伦比亚大学报道了1例心血管临床表现突出的COVID-19病例,患者为64岁女性,以胸痛为主要表现,入院心肌肌钙蛋白I(cardiac troponin I,cTnI) 7.9 ng/ml,心电图提示肢体导联低电压,Ⅰ、Ⅱ、aVL和V2~V6导联广泛ST段抬高,超声心动图示射血分数30%,左室壁显著增厚伴少量心包积液,冠状动脉造影示冠状动脉无狭窄,考虑非阻塞性冠状动脉疾病、心包炎或心脏淀粉样变。作者分析,即使无明显呼吸道症状而仅表现为典型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仍可能是感染2019-nCoV所致[2]。
1.1 心脏损伤相关临床表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一项单中心回顾性分析,共纳入138例COVID-19患者,急性心肌损伤、休克和心律失常的发生率分别为7.2%、8.7%和16.7%[3]。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报道了纽约6家医院共18例出现ST段抬高的COVID-19病例,患者中位年龄63(54,73)岁,危险因素方面合并高血压11例(61.1%)、糖尿病6例(33.3%)、血脂异常7例(38.9%)、冠心病史3例(16.7%)和吸烟史1例(5.6%);症状表现上6例(33.3%)出现胸痛;cTnI平均峰值为44.4 ng/ml(13.3~80.0 ng/ml);9例(50.0%)患者超声心动图提示射血分数下降,6例(33.3%)出现节段性室壁运动异常;9例(50.0%)行冠状动脉造影检查者中6例确诊冠心病,提示2019-nCoV感染可能导致急性心肌损伤或使原有基础心脏疾病加重[4]。钟南山院士团队的一项多中心回顾性研究显示,有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CK)数据的657例COVID-19患者中13.7%出现了CK水平升高,有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数据的675例患者中41%出现了LDH水平升高,更重要的是,CK和LDH的异常与预后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该研究未统计患者cTnI和CK-MB水平[5]。王福生院士团队报道了首例行病理解剖的COVID-19死亡患者检查结果,患者为50岁男性,出现发热、咳嗽等首发症状就诊于发热门诊,有难以纠正的低氧血症,于病程第14天心脏骤停。病理显示其肺部为弥漫性肺泡损伤和肺透明膜形成,符合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表现;在心肌间质可见少量单核细胞浸润,未见明显其他组织学变化。研究者认为,2019-nCoV感染可能不会对心脏组织产生直接损害[6]。刘茜等[7]报道的另1例尸检结果,死者男性,85岁,入院第28天因呼吸衰竭死亡,大体结果显示心包腔内中等量淡黄色清亮液体,心外膜轻度水肿,心肌切面呈灰红色鱼肉状,可能与患者冠心病病史相关,该病变是否与病毒感染直接损害相关不能确定。
Guo等[8]的研究共纳入了187例COVID-19患者,其中出现心室颤动或室性心动过速的患者共11例(5.9%)。纽约市的一项回顾性研究显示,与未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相比,接受机械通气的患者更容易发生心律失常[18.5%(24/130)比1.9%(5/263)][9]。一项纳入113例患者的回顾性研究提示,与治愈组相比,死亡组中血钾>5.1 mmol/L的患者显著增多[22%(25/113)比4%(7/161)],表明危重症患者更容易出现电解质尤其是血钾的异常,因此电解质异常可能是导致COVID-19患者心律失常的原因之一[10]。除此之外,针对COVID-19的治疗药物引起的心律失常也不容忽视。Kochi等[11]的研究指出,长期使用氯喹可能会导致去极化时间和浦肯野纤维的不应期延长,最终导致房室结功能不全[12]。此外,由于药物在溶酶体内积累,溶酶体pH值升高导致酶失活,从而引起心律失常,其中最常见的为高度房室传导阻滞。同时,在临床用药时由于药物引起的QTc延长也须格外注意。
Zhou等[13]的研究共纳入了191例COVID-19患者,与治愈组相比,死亡组出现心力衰竭的患者显著增多[52%(28/54)比12%(16/137),P<0.000 1],提示感染2019-nCoV的患者出现心力衰竭是预后不良的信号。Fu等[14]的一项荟萃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结论,共纳入43项研究的3 600例患者,结果显示与非重症组相比,重症组具有更高的心力衰竭患病率[17.1%(1.5%~42.2%)比1.9%(0.0%~26.0%)]。
1.2 合并基础疾病更易进展为重症
根据有限的研究报道提示,合并基础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更容易进展为重症肺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报道的138患者中,与非重症患者(102例)相比,重症患者(36例)年龄更大[中位年龄为66(57,78)岁 比 51(37,62)岁,P<0.001],并且更有可能罹患合并症,包括高血压[21例(58.3%)比22例(21.6%)]、糖尿病[8例(22.2%)比6例(5.9%)]和心血管疾病[9例(25.0%)比11例(10.8%)][3]。钟南山院士团队报道的中国大陆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 099例COVID-19患者的数据显示,与非重症患者(926例)相比,重症患者(173例)中合并高血压(23.7%比13.7%)和冠心病(5.8%比1.8%)的比例更高,提示高龄、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基础疾病可能是重症肺炎的危险因素[5]。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研究纳入了112例COVID-19患者,重症组(67例)与非重症组(45例)相比,中位年龄更大[65.0(49.0,70.8)岁 比 56.0(39.0,67.0)岁,P<0.01],胸痛比例更多[59例(74.6%)比14例(31.1%),P<0.01],CK-MB水平[2.2(1.6~6.7)ng/ml比1.1(0.6~2.1)ng/ml,P<0.01]和cTnI水平[0.10(0.01~0.77)ng/ml比0.00(0.00~0.01)ng/ml,P<0.01]更高,表明重症患者更易出现心脏损伤[15]。
1.3 出现心血管并发症提示预后不良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一项研究纳入2020年1月21~30日武汉21家医院共计168例确诊COVID-19的死亡患者,中位年龄70(64,78)岁,其中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和缺血性心脏病位列前三,分别为84例(50.0%)、42例(25.0%)和31例(18.5%)。研究提示,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缺血性心脏病可能与死亡风险增加相关[16]。黄从新教授团队报道了416例COVID-19患者,出现心肌损伤的患者死亡风险明显增高,心肌损伤组(82例)死亡率为51.2%,对照组(334例)仅为4.5%,校正后OR=3.41(95%CI:1.62~7.16)[17]。因此,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和缺血性心脏病的COVID-19患者将面临更大的死亡风险。
2 2019-nCoV感染导致心血管损伤的相关机制
2.1 细胞因子风暴
王福生院士团队报道的1例COVID-19患者,心脏间质可见少量单核细胞浸润,外周血中CCR6+Th17细胞数量明显增加,提示心脏损伤可能与炎症反应相关[6]。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报道的3例COVID-19死亡患者的病理学研究发现,心肌细胞均出现肥大,部分心肌细胞变性、坏死,间质轻度充血、水肿,少量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浸润,电镜下见部分心肌纤维肿胀、溶解;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心肌间质浸润的炎症细胞主要为巨噬细胞和少量CD4+T细胞,未见CD8+T细胞和CD20+B细胞;电镜观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和PCR检测均未检测到心肌组织内2019-nCoV成分,因此,2019-nCoV除了直接攻击心肌组织外,还可能存在间接途径,即通过炎症反应引起心肌损伤[18]。Zheng等[19]认为,2019-nCoV引起心肌损伤的间接机制包括由于呼吸衰竭和低氧血症引起的心脏应激以及继发于严重全身炎症的心肌炎症反应。
Huang等[20]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提示,COVID-19的心脏损害可能与细胞因子风暴相关,研究共纳入2019年12月至2020年1月41例COVID-19确诊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患者组的血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7、IL-8、IL-9、IL-10、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CSF)、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ranulo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干扰素 γ(interferon γ,IFN-γ)、肿瘤坏死因子 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干扰素诱导蛋白10(interferon-inducible protein-10,IP-10)、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tactic protein 1,MCP-1)、巨噬细胞炎症蛋白(macrophage inflammatory protein,MIP)1A和MIP1B的水平明显升高;进一步研究发现,重症组(13例)与非重症组(28例)相比,IL-2、IL-7、IL-10、G-CSF、IP-10、MCP-1和TNF-α显著升高。回顾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MERS-CoV)的研究发现,相关的促炎细胞因子也出现显著升高。Wong等[21]研究发现,感染SARS-CoV的患者血清中IL-1β、IL-6、IL-12、IFN-γ、IP-10和MCP-1明显升高,且上述细胞因子水平升高与肺损伤明显相关。Mahallawi等[22]发现,MERS-CoV感染诱导IFN-γ、TNF-α、IL-15和IL-17等促炎因子水平上升。IL-17通过诱导G-CSF介导粒细胞的生成和中性粒细胞募集,并诱导IL-1β、IL-6和TNF-α发挥促炎作用[23]。基于这些理论,针对上述细胞因子的单克隆抗体有望用于临床治疗,但目前仍需更多的临床和病理研究以提供更有力的证据支持。
2.2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2,ACE2)表达失衡
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AAS)是心血管系统中的重要调节系统。RAAS中血管紧张素转换酶-血管紧张素Ⅱ-血管紧张素受体1(ACE-AngⅡ-AT1)轴活性异常升高时会导致心血管损伤。生理状态下,ACE将血浆血管紧张素Ⅰ(angiotensin Ⅰ,AngⅠ)转化为AngⅡ,AngⅡ与血管紧张素Ⅱ-1型受体(AT1)结合,发挥介导血管收缩、促进炎症细胞增殖等作用;而ACE2作为RAAS的负调节剂,通过直接或间接途径促进AngⅠ向Ang(1-7)的转化,而非转化为AngⅡ,从而起到抑制ACE-AngⅡ-AT1轴活性的作用。ACE2可催化AngⅠ形成Ang(1-9),再经ACE催化形成Ang(1-7),或由ACE2直接催化AngⅡ形成Ang(1-7),而Ang(1-7)与G蛋白偶联受体Mas结合可发挥血管舒张、抑制炎症反应等作用[24]。
研究提示ACE2与2019-nCoV侵入相关,是感染人体的关键受体[25]。Xu等[26]的研究发现,2019-nCoV通过表面的刺突蛋白可与ACE2结合从而进入宿主细胞。Zou等[27]利用单细胞RNA测序分析生理情况下ACE2在人体的分布情况,提示除了Ⅱ型肺泡上皮和下呼吸道黏膜上皮,ACE2在心肌、血管内皮等也存在高表达,因此心血管也可能是2019-nCoV的靶器官。 Liu等[28]对COVID-19患者(12例)和正常对照组(8例)测定AngⅡ水平,发现患者组AngⅡ水平显著升高(P<0.001),还发现患者的血浆AngⅡ水平与病毒Ct值呈负相关(P=0.035),表明COVID-19患者体内存在AngⅡ蓄积,且AngⅡ水平与病毒载量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2019-nCoV入侵导致ACE2表达下降,AngⅡ相对增加,与ATR结合介导血管收缩、促进炎症反应并加重了氧化应激,从而引起心脏损伤。简而言之,RAAS中有正向的ACE-AngⅡ-AT1轴,其具有收缩血管、促进炎症反应的作用,且存在负向的ACE2-Ang(1-7)-Mas轴,发挥舒张血管、抑制炎症反应的作用,在2019-nCoV入侵时,ACE2表达下调,负向轴活性抑制,导致正向轴过度激活,引起心脏损伤。
目前,有关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ACEI)和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angiotensin Ⅱ receptor blocker,ARB)对COVID-19患者的作用尚存争议。一方面可能通过抑制ACE-AngⅡ-AT1轴激活缓解炎症反应,另一方面也可能通过反馈性上调ACE2受体促进病毒侵入[29]。Fang等[30]的研究指出,接受ACEI和ARB治疗的患者对COVID-19的敏感性更高,因此,罹患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或心力衰竭的患者应换用其他药物。这一观点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武汉大学李红良教授团队的研究显示,合并高血压的COVID-19住院患者应用ACEI/ARB可使全因死亡风险明显降低。该研究纳入了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2月20日共1 128例合并高血压的COVID-19患者,包括应用ACEI/ARB的188例和对照组940例。通过Cox模型分析,在校正年龄、性别、合并症后,与对照组相比,应用ACEI/ARB的患者全因死亡风险降低了58%。由于随访时间较短,该研究不足以证明ACEI/ARB在COVID-19中具有保护作用,但至少显示,罹患高血压、缺血性心脏病或心力衰竭的患者继续使用该药物在短期内是无害的[31]。Mancia等[32]通过研究对比意大利2019-nCoV感染者(6 272例)和有病历记录的其他人群(30 759例),未发现使用ACEI或ARB类药物会增加COVID-19发病风险。Mehara等[33]的研究纳入了北美、亚洲、欧洲共11个国家或地区的169家医院共8 910例确诊患者,统计结果显示,与未使用ACEI或ARB类药物患者相比,使用ACEI(2.1%比6.1%,OR=0.33,95%CI:0.20~0.54)或使用ARB(6.8%比5.7%,OR=1.23,95%CI:0.87~1.74)均不增加患者院内死亡风险。
3 小结
尽管COVID-19的主要靶器官是肺组织,但在临床实践中,合并心血管基础疾病的COVID-19患者仍然是一大挑战。这部分患者的临床表现往往更为严重,预后较差且死亡风险较高。临床上以心律失常、心原性休克和急性心脏损伤较为常见。目前,许多研究者提出了由ACE2介导的心肌损伤以及细胞因子风暴可能揭示了2019-nCoV对心肌造成损伤的重要途径。一方面,2019-nCoV在多种细胞因子作用下引起心脏炎症反应;另一方面,2019-nCoV通过ACE2侵入人体,引起RAAS中ACE-AngⅡ-AT1轴活性相对增强,导致心血管损伤。本文通过文献复习,对上述临床特点和机制进行总结分析,希望为临床治疗和下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作用。
利益冲突: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