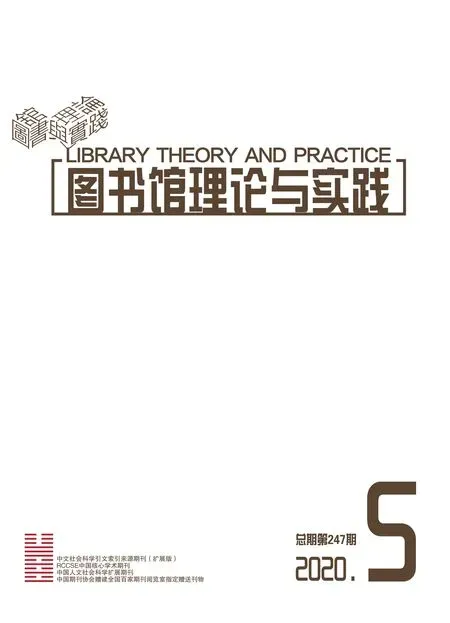《四库全书总目》的文献诠释机制分析
2020-01-09关思雨蒋永福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关思雨,蒋永福(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研究中心)
1 《四库全书总目》:文献诠释学经典
诠释从来不是一种单纯文本理解的技艺,而是一种裹藏着价值取向的建构行为。以施莱尔马赫为代表的传统诠释学派认为, “按照宽弛的诠释学实践,理解是自发出现的,而严格的诠释学实践的出发点则是:凡是自发出现的都是误解” 。[1]若是按照 “自发出现的皆为错误” 的观点来看,个体独自诠释的结果都是错误的,但没有任何诠释成果不是独立的个体(或者一个小团体)的成果。那么什么是 “正确” 的呢?我们知道,《诗经》的诠释作品历代层出不穷,例如东汉的郑玄认为 “《诗》者,弦歌讽喻之声” ,[2]而南宋的朱熹认为《诗经》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齐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 。[3]可见,郑玄与朱熹对《诗经》的诠释方向与结论大相径庭,这说明 “正确” 与否这一提法本来就是一个悖论。中国古代诠释学对此提出了重要的诠释原则,孟子所谓 “以意逆志” ,给诠释者以重构文本意义的权力,以读者之 “意” 逆作者之 “志” ,这种 “意” 和 “志” 相互作用的诠释过程,类似于西方诠释学所谓的 “视阈融合” 的过程。这也符合马克思·韦伯的论断: “我们在社会科学中所看重的是事件的性质色彩。”[4]文本诠释并非单纯地讨论文本本身是否符合原义,而是注重文本的延伸意义对人具有怎样的影响。我们拨开汉与宋对《诗经》诠释的学术迷雾,能够看到的是意识形态的迥异和历代皇帝的价值立场。伽达默尔在哲学诠释学范畴中谈及的 “效果历史” 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学者们看重的不是作为历史证据的文本本身,而是如何构造证据之间关联网络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的寻求以人的价值观念为中心,实际上构造的是人为判断正误的价值体系。文本(或者进一步称之为知识)当中,人们实际的诠释对象是思想而非事物,文本中所谓事物不过是思想的行为。
文本与时代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话,产生不同的诠释思想。正如保罗·利科尔所说: “诠释一篇文本,在本质上就是把它当做是某些社会文化需求的表达和对某些处于具体时空的困惑和反映。”[5]这与中国古代 “经世致用” 的诠释思想异曲同工。中国目录学与西方目录学起源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中国古代目录的编纂自西汉刘向、刘歆编纂《别录》《七略》起,至《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达到巅峰,与中国的中央集权政体从开端至辉煌的历程具有相似的发展曲线,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编纂官修目录必然具有政治和社会文化意义。政治环境不同,对目录编纂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相较于西方来说,官方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目录的编纂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目录(至少是官修目录)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意味皆大于文献整理效用,其中昭示着编目主体的政治意见、伦理观念和审美情趣。班固《汉书·艺文志》曾作出这样的评论: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西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通过复仲尼法度,兴儒家而抑百家之学,其价值取向即刻昭彰。后世书目序言因袭《汉志》者,有《隋书·经籍志》言 “昔日哲人萎而微言绝,七十子散而大义乖,战国纵横,真伪莫辨,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旧唐书·经籍志》言 “自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都是推崇孔子而斥责诸子的言论。显然,这不仅是整理文献之目录的代代相因,而是蕴含着编目主体对文化信念的一脉相承。诸如此类的价值评判蕴于中国古代书目的分类、提要、大小序中,成为我国古代帝王整饬思想意识的文化手段。
《总目》煌煌二百卷,集纪昀、姚鼐等名臣大儒之合力,历数十年而成,几易其稿。后来又有学者补其讹谬,发其旨微,实乃中国古代目录之集大成者。《总目》于后世是学术之瑰宝,但对清高祖而言,《总目》 “定千载之是非,决百家之疑似” ,表面 “稽古右文” ,实则以编纂书目的方式,将编目主体的价值取向与政治观点寓于文献诠释之中。《总目》由具有汉学倾向的纪昀担任总纂官,而分纂官中汉宋两派的学者皆有。于是 “以意逆志” 的宋学和 “征实” 的汉学两派的文献诠释成果都蕴于《总目》之中,相互牵制与调和,形成了独特的诠释景观。宏观层面,《总目》通过文献整序揭示文献价值,五经与五常相呼应,又于阴阳五行中找寻本体依归,使儒家 “仁义礼智信” 上达天道,下寓五经,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层面寻求存在合法性。微观层面,通过大小序和提要中对文献的诠释,建立价值二分话语的叙述框架,将是非对错先验地植入读书人的价值判断中,以达到教化人心的功能。本研究以《总目》为例,探讨中国古代目录作为文献诠释活动是如何以政教人伦为最终旨归揭示文献价值的。
2 《四库全书总目》分类体系的价值呈现机制
目录分类体系的建构体现了编目主体对知识分类的看法,是主流文化观念的表象。西方古代文化观念常孕育于神学,中国古代文化观念则与政治密不可分,故《总目》的分类原则自然要在政治文化中寻找依据。
2.1 类表结构:价值序列
中国古代书目的类表建构遵循着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模式,这使得书目类表结构的建立不仅是将文献放置在适当位置,也是所有文献单元和文献序列共同构成天人合一的宏大人文景观。类表结构建立的依据是具有多重维度的,如尊经思想、尊儒思想、重道轻器、社会地位序列、时间先后原则、酌篇卷之多寡等,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与本文主旨相关的尊经思想、尊儒思想、重道轻器和社会地位序列四点。
(1)尊经思想。尊经是中国古代目录类表建构共同遵循的思想之基。刘歆《七略》类目的安排以六艺略为首,体现了尊经思想。自此之后,在类表结构安排上,尽管经历了六分法到四分法的嬗变,也出现了很多完全摒弃正统分类法的其他建构方式,但尊经是共同社会背景之下中国古代学者遵循的思维秩序。这种经由千百年的锤炼在人的意识之中以逻辑的格式固定下来的思维方式具有公理的性质,所以尊经思想发展至《总目》,已经是天经地义的不二选择。
四分法传统遭到破坏最严重的时期是明代,降至清乾隆修《总目》严格按照四部分类,四分法的传统才得到恢复。乾隆认为: “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6]四分法以经为首是承续了六分法以六艺为首的类表建构格局。这源于古人重 “道” 的信仰取向,而且中国人所重之道是天人合一的人道,而不是西方所重的神道,这使得中国古代形成了崇尚圣贤的文化传统,而圣贤具有 “不在场” 的特性,圣贤所阐发的道理载于六经而代代流传,也就进一步使得古人尊经的思想成为学者们共同遵循的思维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很多挣脱六分、四分藩篱的目录本质上仍然遵循六分、四分的类表结构的价值序列,比如郑樵认为类目之间不应该有尊卑之别,他的《通志·艺文略》一级类目分为十二大类,前四类为经、礼、乐、小学,只是将四分法一级类目取消,二级类目变成一级类目,实际上仍然遵循着经为首的类表结构建构方式。
(2)尊儒思想。自汉代一统天下,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学术取向统一思想之后,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就一直不可撼动。在目录当中,最早体现这一点的也是《七略》,刘歆把论语、孝经、小学附入六艺略,又把儒家置于诸子略的首位。至《总目》尊儒思想达到巅峰,将属于儒家学派的《论语》《中庸》《孟子》《大学》合并为四书与孝经和小学共同列入经部,儒家依旧占据子部的首位。《总目》子部序将为何如此排序写得十分明晰: “儒家尚矣。有文事则有武备,故次以兵家。兵,刑类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附草木,不能免门户之私……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节以足自立,即其不合于圣者,存之亦可为借鉴。” 《总目》以 “尚” 字评儒家,足以见儒家的地位所在,对于其他学派,则以为民所用时的价值大小依次降序排列,并且认为其中有 “不合于圣者” 的方面。
(3)重道轻器原则。《周易》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首次点明了道器之间的关系,认为道比器更加重要,应该先道后器、先理后事。如《总目》经部分十类,易类、书类、诗类、礼类、乐类、春秋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孝经类、小学类。易学列为经部之首,其原因如经部总序所言: “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喻教。《诗》寓风谣,《礼》寓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也。” 诗、书、礼、尚书、春秋都属于人道之列,但易学包罗宏富,更是天人之统摄,是按照道器的轻重排序的。又如法律类书籍将韩非子、申不害等法家学派开创者的书籍列在前面,而后世依寻其道的法律书籍,附条别次,也是根据道器关系的排序。但名家与法家的先后关系似乎是一个特例,《总目》之前,大多书目都将法家置于名家之前,但名家论理,讲的大多是逻辑问题,法家论人事,讲的是具体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理,所以名家属于 “道” 的范畴,法家属于 “器” 的范畴。《总目》将法家列于杂家之前,而名家包含在杂家之中,似乎违反了重道轻器的原则,实际上这恰恰是编目主体有意摒弃儒家之外论道的学派,更加凸显儒家之道的正统地位,同样是重道轻器的表现。
(4)社会地位序列。根据文献作者的社会地位或文献所涉及人物的地位的分类原则,也是以价值逻辑建构目录类表的表现。例如《总目》传记类序言: “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从判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别录。” 人物传记书籍的排列顺序按照人的社会地位:先列圣贤,如孔子、孟子等为人所尊崇的先贤大儒;其次列名人,如正人君子、忠义之臣、贞洁之女等,能在仁义礼教等方面成为众人之表率;再次总录与杂录记载多人传记以及有关传记的资料等;最末则列乱臣贼子的文章与相关文献,昭示其罪孽,以儆效尤。又如《总目》批评《千顷堂书目》将记载君王之言的 “制诏” 类作为 “集部” 的下设类(《文献通考》为这类书籍设类为 “奏议” 也将其列在集部之下),而《总目》认为记载君王言论的文章为 “政事之枢机” ,不应将它们和词赋文章列为同类。这是明显以儒家价值体系评判人物的社会地位,再以社会地位之高低排列书籍著录先后的建构原则。
2.2 类目设置:价值选择
西方分类法为类名配置标识符号,依据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等逻辑原则,明确规定了每个类名的内涵与外延。中国古代书目类名与现代西方分类有明显的差异,它不是写实的而是写意的,并不仅仅是针对图书的分类,更具有联系文化与政治的功能,类名具有明确的价值内涵,并在改易与增减的过程中体现了政治与学术文化的走向。
(1)类名改易。《总目》承袭分类史上所谓 “正统派” 的四部分类法,四部分类自《隋书》确立之后就少有变更,所以在类名的改易中就能够发现朝代更迭所导致的文化变动。例如自《七录》起记传录就有伪史一类,是指记载称霸一方、割据一地的非正统政权历史的史书。自此之后,除《明史·艺文志》无此类之外,其他的书目或称为伪史或称为霸史。《总目》中也有此类,但将类名改成载记类,并解释为: “然年祀绵渺,文献散佚。当时僭撰,久已无存。存于今者,大抵后人追记而已,曰霸曰伪,皆非其实也。” 《总目》将非正统政权的问题转化为年代久远的文献散佚问题和后人追记的主观性问题,以此掩盖少数民族割据一方自立政权的行为是 “伪” 、是 “霸” ,其真实意图则是回避少数民族政权被判定为伪政权的贬抑色彩;以载记立名,是将这种带有强烈批判色彩的 “伪” 字改为中性词汇,洗脱清政府统治的 “非正统” 嫌疑。
(2)类名增减。相对于前代的目录,《总目》有详细的三级类目。三级类目的增加除了能将文献类别划分的更加清晰,更暗含了人伦秩序,具有强烈的价值色彩。例如,地理类分为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纪。《总目》地理类序阐明了地理类三级类目如此设置的意义: “其编类,首宫殿疏,尊宸居也。次总志,大一统也。次都会郡县,辨方域也。次河防,次边防,崇实用也。次山川,次古迹,次杂记,次游记,备考核也。次外纪,广见闻也。”[6]1243清廷认为皇室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才是含有大一统意义的广阔疆域,再次是各地郡县,是由权力中心向外延展的价值序列,是编目主体针对 “大一统” 思想的价值排序。相对于前代目录所减少的类目,《总目》体现了编目主体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与把控。例如,前代目录子部类名大多是儒家第一、道家第二、法家第三、名家第四、墨家第五、纵横家第六的顺序,少有改易,而至《总目》将二级类目名家、墨家、纵横家的类名舍去,归入杂家,改为儒家第一、兵家第二、法家第三、农家第四、医家第五,这里除了儒家具有论道的功能,其余都是讨论具体问题的目类,其他论道的诸子书目要么位列最末,如道家,要么舍去类名,如墨家、名家,这表现了《总目》 “独尊儒术” 的文化倾向。
综上所述,《总目》的类表结构与类名设立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遵循尊经、尊儒、重道轻器和按照人物社会地位排序的原则,同时也回避了少数民族政权非法性的传统认知,这是编目主体遮蔽自己尴尬身份背景的高明手段。
3 《四库全书总目》序言提要的价值呈现机制
序言和提要是中国古代目录学重要的组成部分。《总目》每一大类有大序,每一小类有小序,每一书目有提要,并占据大量的篇幅,是目录中文献诠释成果与诠释方法的文本呈现。如果说类表建构和类名改易是《总目》价值评判的隐性表达,那么序言和提要则是更为直接的显性表露。但中国古代序言提要式的 “宣之于口” 不同于现代摘要的客观直白,其中 “春秋笔法” 之处比比皆是,有必要细致研究。下文从经史(政治性)子集(学术性)四个部分说明序言和提要是如何以政教人伦为最终目的揭示文献价值的。
3.1 “我注六经” :官方话语权的确立
六经是天道下达于人世的文本呈现,从 “经” 的含义即可窥其一二。《说文解字》中言: “经,织纵丝也。” 后人为其作注曰: “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故天地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7]颜师古称 “经者,道出其中也” 。[8]道蕴于六经之中,并上达于天,下寓于人,是人能够感知天地浩渺和人伦彝常的渠道。
天道虽然是人们共同奉为圭臬的思想准则,但我们并非像西方供奉神明一样对待它,天道中所蕴含的 “人伦” 内涵,才是我们真正遵循的人生法则。《汉书·儒林传》云: “古之儒者,博学乎《六艺》之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 可以看出, “明天道” 的最终指向是为了 “正人伦” 。因此,统治者需要建构一条合法的传承渠道。对于中国古代的统治者来说,皇帝自诩为 “真龙天子” ,自然是天道的合法代言人,所以皇帝之言与六经的关系必然是互为因果,相互印证的。正如《总目》的经部总序所言: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经虽为天道,但具体呈现出来的六经文本仍然需要皇帝的裁定才能合法地在经的部类发挥其天道的职能。经部总序又言: “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皇帝裁定经义文本的过程,是人为的统一 “公理” 、由官方定义话语叙述方式的过程。
定义官方话语叙述方式必然形成尊奉六经抑制后世之学的学术倾向,因为后世之学大多数是具体的读者以自己之 “意” 逆圣人之 “志” 的产物,具有现实性的倾向。官方在这一方面需要夺取建构经义新内涵的唯一合法话语权,所以《总目》尊奉六经,实际上是确立官方话语权的表现。例如,在《易义古象通》的提要稿中,《总目》引多部经书与此经互证: “大旨谓文、周之《易》即象著理,孔子之《易》以理明象。又於汉、魏、晋、唐诸人所论象义,取其近正者,故名《古象通》” ,[6]49而在文末极力批判明代万历以后的经学要么 “局于文句,无所发明” ,要么 “鹜于玄虚,流为恣意” ,这种将 “去古未远” 的经义奉为圭臬而把后学之士的成果全部归入 “异端” 的做法,在学术立场上不免过于武断,但是在统一文化的立场上却是合理的。又如,《总目》在抨击宋学时,首先不满于宋学改经删经、为圆己说的做法。朱熹的疑经改经就遭到了《总目》的强烈抨击,在提要稿中批评朱熹 “诋毁此书,已非一日,特不欲自居於改经,故托之胡宏、汪应辰耳。” 王与之在《周礼订义》当中,没有详细精深的考证,采纳不尊先儒、疑经改经的诸本,《总目》批评其为: “然凭臆改《经》之说,正以不存最善,固无庸深考也。”[6]461表面上《总目》以不符六经本意以讨伐朱熹等人,实际上则宣扬了清代尊崇汉学的学术倾向,是抢夺话语权的表现。
经不仅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志,更是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清高宗以编纂官修书目的方式,用承载天道的经文之口说出有益于自身的价值观念。天道能为己用又况人事乎?《总目》史部类也是编目主体以 “春秋笔法” 写成的一部 “清代的当代史” 。
3.2 史评是非:统治合法性的宣示
史乃国君之家事。孔颖达疏《礼记》时,释史意为: “史,谓国史,书录王事者。” 比起渺远难解的天道,史与人的距离更近。所以,《总目》对史书的留存与评介更是慎之又慎。
《总目》认为史具有 “叙兴旺、明劝诫、核典章”[6]901的社会教化意义,所以对史部类书籍的价值评价也尤为重要。《总目》首先要确立 “大一统” 的正统史观。 “大一统” 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公羊释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 时认为,《春秋》在正月之前先说 “王” 字,代表着君王统摄天下万事万物的权威,意味着 “大一统” 。后世史家对这个命题加以发挥,逐渐演变成探讨王朝正统的问题。清廷作为少数民族统领全国,对王道正统观的构建是十分迫切的,所以在编纂《总目》的过程中,以诠释史书、评介史事的方式巩固满清皇帝的统治地位。例如,清廷在定义南明小朝廷是否具有正统地位的问题上,体现出了明显的主观倾向。康熙年间修《明史》时,并未将南明小朝廷作为南宋的正统,其相关史事皆被排斥在《崇祯皇帝纪》之外。而在《总目》的编纂过程中,乾隆一改清前期对南明唐王的伦理定位,认为 “不必概以排斥也”[9]提要稿中更是直言道: “若夫甲申以后,仍续载福王之号。乙酉之后,仍兼载唐王、桂王诸臣。则颁行以后,宣示纶綍,特命改增。圣人大公至正之心,上洞三光,下照万禩。尤自有史籍以来所未尝闻见者矣。”[6]641乾隆帝一改顺治以来对南明政权的定论,其原因也在这段文字中昭然若揭。清前期康熙帝不承认南明政权的合法性是要给清兵入关一个合法的理由,而乾隆帝已经稳坐江山,他首先是为了表明大清皇帝的 “大公至正” ,其次是为表彰南明忠于明朝的臣民,继而宣扬忠君思想,增强清廷的凝聚力。少数民族政权不得不面对史书中有关 “华夷之辨” 的问题。《总目》采取建立 “天下非一家之天下” 的观念,改易以往正统论中对少数民族的歧视词句。例如《平瑶记》,姚鼐在拟定分纂稿时作《平猺记》,纪昀改 “猺” 为 “瑶” ,也将姚鼐的评介性话语全部删去,重新拟定,避开敏感的 “夷情” 等词汇,只说 “今核其文体,乃勒石纪攻之作,非勒为一书上之於史馆者” ,[6]982仅论文体而回避实旨。
在价值体系的承续上,史书之人事上承六经之公理,以六经之是非定论史事之是非。但面对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问题上,《总目》则以 “春秋笔法” 重新诠释史事,以达到编目主体的政治目的。
3.3 儒为正道:诸子百家众星捧月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本源 “道” 偏向于对社会规范的认识,例如 “为君之道” “为臣之道” 。子部按学派分类,类似于现代的学科分类,但所依据的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依据价值判断构建学问体系。
《总目》在子部大序中明确提出 “儒家尚矣” ,言简意赅地表达出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的特殊地位,这也与类序上将儒家列在第一位的意味暗合。但这并不代表着儒家学派的必然正确,子部大序中又云: “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虽其间依附草木,不能免门户之私。” 这明确地表达出了《总目》虽然肯定儒家占学术之主流的地位,但也认为儒家学派中有 “籍词卫道者” ,不能与大儒相提并论,因此《总目》在评价儒家一派的作品时,也暗含一个价值差序的序列。《总目》如何建构儒学一派中的差序格局是我们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探讨儒家这一官方推崇的学问体系,我们应追溯古人对于学问的论断。《周易·文言》曰: “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 ,可以看出学问的目的在于建立君子的品格;《礼记·中庸》言: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近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进一步提出人若要成为君子,需用道问学的方式以达成尊德性的目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最早关于知识的认识主要在价值观层面上。尽管儒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分为不同的学术流派,但在人的思维层面建构统一的价值体系一直是儒学的学术目的。所以,能够体现君子品格、树立正确人生价值观的儒学作品具有更大的价值。相较于大儒,《总目》认为具有 “门户之见” 的儒学学者是不足取的末流,清廷以史为鉴,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结为党争,认为朋党之私能够祸及宗社,所以无论学问高低,只要内容上涉及朋党之间的攻讦,也会被斥为存目。如儒家类存目四《性理纂要》的提要云: “然同一先儒之言,何必分疆别界” ,认为冉觐祖将《性理》条之下程子诸人所著的《太极图》诸书评为经典类,而将胡广等所著之书评为文史类这种分门别户的做法不可取,故以存目。
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处于众星拱之的地位,也在内部呈现差序格局的态势,分为大儒与小道,诸子的序列也是编目主体对其学术立场的是非评价。子部大序用大量的篇幅明确地诠释诸子百家降序排列的诸种缘由:如 “有文事则有武备” 则儒家之后列兵家;如 “民,国之本也;谷,民之天也” ,所以法家之后列农家。《总目》将子部分为十四个二级类目,对其总体的价值意义也作了明确的划分:①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可 “治世者所有事” ;②术数、艺术是 “小道之可观者” ;③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为 “旁资参考者” ;④释家、道家二家为 “外学” ,最不入流。
总而言之,《总目》子部呈现出的整体价值取向是儒家为尚,诸子百家辅助儒家共同整饬的思想意识。具体细节上,编目主体以作品是否 “尊德性” 、作者是否 “类君子” 、是否有门户之见评判儒学书籍的价值,以诸子百家辅助功能的大小决定其具体价值。
3.4 情理之辨:儒学为本情重于理
集部在一级类目中处于最末端的位置,集书主要指文学作品集,包括诗文集和诗文评著作。因为其文学性,集书价值的判断虽然并不能逃出儒家的 “期待视野” ,但其评价标准比起前三部类明显要复杂的多,因为评价者的 “文学观” 往往是变化无常的。所以,我们在此探讨四库馆臣在评价集部作品时所显现的两种评判指向。
(1)文体雅正。四库馆臣遵从儒家 “文体雅正” 的文艺观,认为诗文应该具有载道言志、教化人心的作用。例如,馆臣在评价陈与义的诗时说: “尝作《墨梅诗》,见知于徽宗。其后又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句,为高宗所赏,……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托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6]1349尽管陈与义所作描写景色、刻画事物的诗句为皇帝推崇,也被后世的文学大家所欣赏,但比起格律与意境之美,馆臣更加注重陈与义在宋室南渡之后所表达出的悲伤与愤懑,体现出《总目》的审美观念的内核是儒家的忠义观。词本应该以抒情为本志,但《总目》为诗词歌赋套上了伦理枷锁,《总目》评骘文学作品常以人品定文品,认为只有作者本人是 “君子” ,他的作品才能够起到教化他人的作用。馆臣赞傅察、洪皓之流的文章绝好,并非夸赞其文辞,而是本着 “忠孝者文章之本” 的评价方法,认为他们使不辱命、抗节殒身的人格应当流芳百世。
(2)情理之辨。评价文学作品应该 “主情” 还是 “主理” ,在很早的时候就分为两个诠释流派。例如对白居易《长恨歌》的评价, “主情派” 认为《长恨歌》的描写直陈时事,宛如一幅水墨画展现在人的眼前,是古今长歌的第一, “主理派” 却认为《长恨歌》是荒淫之语。至《总目》, “主理” 的文学观渐渐退出主流的地位,如《总目》在评价真德秀《文章正宗》时引顾炎武语驳曰 “病其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 ,体现出四库馆臣在文学观上 “主情” 的判断倾向。
从《总目》在文本诠释时对于经史的尊奉和对儒家伦理的崇尚能够看出《总目》诠释文本的表象之中隐藏着统一价值观念的指向性,它承续了中国古代君主制大背景的共性价值观念,也体现了属于清廷的个性价值观念,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化解政治文化矛盾,使臣民明政教人伦,承认清廷合法性,确立人伦有序性,将忠君爱国、长幼有序等君子人格植入文献价值评价体系。另一方面,是学术立场视角下的褒贬评论,主要体现在子部对诸子百家不同的学术流派作品的价值评价和集部对文学作品的褒贬评论之中,这显示出《总目》的文献诠释机制的复杂性。
4 结语
本文分析了《总目》的文献诠释机制,首先探讨诠释学如何为文献诠释的价值建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其次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分析《总目》文献诠释机制的内在理路。宏观上探讨《总目》的分类体系,从《总目》的类表结构和类名内涵两个方面分析出《总目》尊经、尊儒、重道轻器等文献诠释思想和清王朝潜移默化改变少数民族非正统的性质、树立自身正统君权的权威、建立儒家人伦道德体系并削弱儒家以外其他论 “道” 学派的潜在目的。微观上探讨《总目》的序言提要,分析出编目主体在政治层面上重视经史的原因,认为经是《总目》借圣人之口宣读的自己的价值观念,史则不仅上承六经之理,而且被 “春秋笔法” 改头换面,是清王朝所认可的是非定论。在学术层面,编目主体则在学科分类上崇尚儒家,在文集评价上欣赏文体雅正、清重于理的文学作品,让儒家学说统摄九流十家,建立一元化的文化价值取向,将 “忠君” 意识植入人心,也改变宋学以理论诗的文学观念,树立重情重义的文学风尚。这证明了中国古代官修目录的文献诠释行为确实是通过建构价值体系最终达到明乎政教人伦的目的。并且在讨论子集的文献价值评判的依据时,认识到《总目》在诠释文献价值的时候,在细节上也具有其特殊时代和学术观点上的复杂性。
《隋书·经籍志》言: “夫经籍者也,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弘道德。……夫仁义礼智,所以治国也;方技数术,所以治身也;诸子为经籍之鼓吹,文章乃政化之黻黼,皆为治之具也。” 历史上没有纯粹的 “事件” ,而 “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就不是事件,而是‘历程’;事件有始有末,但历程则无始无末只有转化” ,[10]这种观念在我们探究文献诠释时也同样适用。在中国古代的历史语境下,我们不应脱离政治来看待文化,脱离政治的古代文化探究是畸形且没有意义的。由统治者主导的官修目录活动,以评骘文献为表象建造起不可撼动的价值观念,使臣民枷锁缠身却不自知,正是最高明的政治手段。总而言之,中国古代目录中的文献诠释活动表面上揭示文献价值,其根本目的在于明政教人伦。
我们在历史语境下探讨书目的意义,冲破西方目录学学科范式划定的标准,重新揭示中国古代目录学的本质。从西方目录学以科学性、逻辑性为书目体系评价标准的眼光看,中国古代目录学缺乏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目录学具有宏大的格局,勾画出文以载道、天人合一的圆融之境。这说明无论是西方模式还是东方智慧,都能够在人类社会多元发展的社会语境中站稳脚跟。我们应该改变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偏见,开垦中国古代目录这一巨大宝藏,这不仅能够给予我们更多的理论资料,也能够构建起中国目录学的学科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