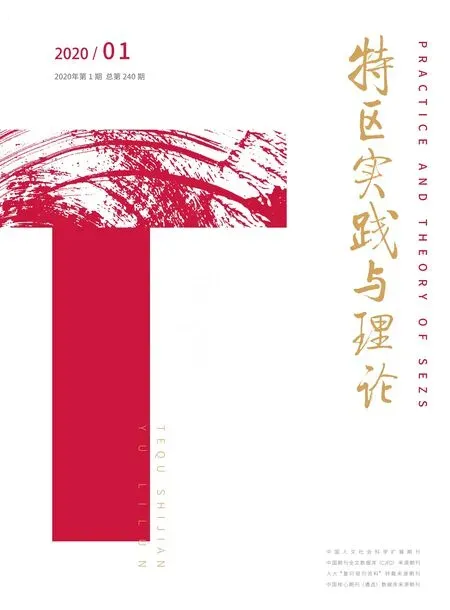道德与知识的张力
——论王阳明对朱子格物说的内在化转向
2020-01-08徐亚豪
徐亚豪
朱子之论格物,强调通过具体对象的认识过程而进致于明善成德的终极追求,事物之“所以然”和“所当然”不可偏废一方,实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而王阳明倡言立说亦有其独特的用意所在,明代科举取士与程朱理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到阳明生活的明中叶,业已成为人们猎取功名、谋求官禄的工具,学者不复讲求身心之学。王阳明认为朱子的格物说中隐含着一种理论危险性,在后世学者的实践中加以放大,从而出现了功利、词章等务外遗内的时代弊端,而真正危险的是,世人身陷其中而不自知,犹以为圣道在此,阳明认为这种流弊的发生,朱子要负一定的责任,因之,他对朱子的格物理论做出整合性的改造是必然的。①陈来教授认为,明代王学总体上固然是朱学格物方法的流弊引起的一种反动,但仅就王阳明“庭前格竹”而言,显然并没有真正理解朱熹的格物思想。(《朱熹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02页)他在《有无之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5页)中亦有论及,认为阳明把朱子的格物哲学理解为面对竹子的沉思,是对朱子思想的极大误解,就阳明的过人才智来说,这种误解不应该发生,因此对这一事件的合理解释就是,它是在阳明青少年时期思想不成熟阶段所发生的。笔者认为,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个问题,阳明在晚年回忆“庭前格竹”时仍采用否定向外格物穷理的倾向,而没有表示自己曾对朱子的思想存在误解,体现出阳明对于朱熹格物理论一贯的不认同态度,这说明他并不是不理解朱子的原意,而是有意为之,即从朱学流弊处入手建立自己的学理体系。本文便是以这种致思角度为基础展开的。
一、从朱子的格物说谈起
王阳明青年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是传统的程朱理学,自然对朱子所指点的为学路径做过一番笃实的践履功夫。朱子所强调的首要话头便是“即物穷理”,而“格物”在《大学》的功夫次第中亦是第一阶段的,作为初学者的青年阳明首先要做的便是在现实生活中穷尽事物之理。但王阳明并不能懂得“格物之学”的真义所在,他在回忆自己曾经冥思苦想“格竹之理”的经历时说道: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于三日,便致劳神成疾。当初说他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劳思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阳明深信朱子所说的“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一草一木,皆涵至理”,坚定地认为“格”得事物之理是学做圣贤的第一步,而在竭尽心思之后却仍不得其理,以至于积劳成疾,便发出圣贤有份的感叹,但是我们不难发现,阳明格竹子之理的行为并没有真正领会到朱子的意图。朱熹在《大学格物补传》中所作一段文字可以看作他对格物思想的纲领性的阐发: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页。
朱子的“格物穷理”与他所主张的“理一分殊”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朱子的格物精义着意于分殊之理,“密察于区别之中”正是分殊包含理一、下学进致上达的基本思路。③赵峰在《朱熹的终极关怀》(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108—119页)中谈到,朱熹在立志儒学、寻找下学上达的功夫入处之际,把重点放在了以理智密察分殊上。朱熹强调的“格物精义”将事物不可移易之定分作为学者的发端入手处,精义之至而上达,其用妙不可言而无所不利。因此,朱熹确定了下学上达必须的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带有明显的理性思辨色彩。作为“理一”的天理必须在“分殊”的“物理”上显现出来,而不能空空去讲“理一”,所“格”之物也并非仅仅是“存在之物”,“物”训为“事”,凡人所接一切事和物,都在所“格”之列。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朱子看来,具体的人、物、事中所含的道理虽千差万殊,但在根本上说都是天理大化流行、生生不息之理的同一表现,考察“事物之理”和内在于人的“性理”,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对“天理”的认识。想要体认作为本体的“天理”,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格物”功夫中加以证显,朱子讲穷理则落到格物上,否则所穷之理便会落空。
毋庸置疑,朱子的学说是伦理哲学,而不是穷究事物之理以用于科学研究。赵峰谈到,就“格物”而言,它当然包括天下万物,但重点是指人伦之事,此处无可疑。陈来指出,朱熹的格物穷理说主张从具体事物着手,但终极目的是为了把握所谓“天理”,而并不同于西方自然科学的指导原则。④包括陈来等学者在内的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理学中的“格物”思想虽充分肯定了人学习知识和研究外部事物的必要性,然而其重视知识主要不是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追求一种博学笃行的全面人格,追求圣贤境界。由工夫所达到的本体乃是一种超越于当下具体工夫的认识,“格物”的最终指向是明善,“穷理”的目的也是成就德性的修养,所以阳明“格竹”的指向并不是竹子之理本身,而是超越、点化了的“天理”。但朱子的学说是一个平衡完备的理性系统,既注重所以然之故,又强调所当然之则,即诚明两进、由明致诚。如此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天下事物纷繁杂乱、浩渺无穷,如何能够“格”得尽?具体事物的理如何上升到天理?
对于第一个问题,朱子说:“积习既多,自当脱然有贯通处。”⑤朱熹:《朱子语类》,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82页。这里的“豁然贯通”指的是一种由具体性的积累而上升到一般性的总结,“格物”并不是要“格”尽所有的物,通过具体实践的积累和贯通而达到一种超越性的认识。比方说,对于世界的概念,我们不需要去到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却能够拥有一个对于世界整体性的概念;又比如我们不必对孝之理所包含的全部节目践履实行,但却能够对孝达到一个超越的体认。①陈来教授用积累、贯通、推类的方法解释朱子“脱然自有贯通处”的说法,他认为朱子的表述是一个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特殊进入到普遍的过程。所谓穷尽物理,并不是说要把一切事物之理都转变为人心的现成知识,而是说贯通为人们用推类的方法了解未曾研究的事物准备了完全充分的条件。(陈来:《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第303—313页)
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解释便涉及王阳明质疑的焦点,即理在物中还是理在心中?当然,朱子的“格物”需要的是道德主体有意识的努力,力求将每一事物所“格”之理化为主体的养分,但这种功夫确需有一种识度和境界在,必须将所格之物获得的理经过一番归约、投射、咀嚼等精神活动的涵养功夫,否则便会沉溺于具体事物而不知所归,作为初学之士的青年王阳明自然不具备此种“化约”的识度,所以不知“格竹”所格者为何,亦不知“格竹”所得之理与“圣人之道”有何内在的关联。事实上,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的哲学思考,让阳明对朱子的学术路径产生了怀疑,这一怀疑所指向的就是“格物”与“成德”之间有无必然的关系,换言之,即知识的寻求如何保证时时指向道德的增进?②对于这一问题,赵峰在《朱熹的终极关怀》中批评了张荫麟、冯友兰等学者关于朱子“格物功夫与最高觉解之间存在着‘穷物理’与‘穷人理’的矛盾”的论点,并认为以往的学者过于侧重朱子格物功夫的理性认知意义,而没有正确把握其悟性体证方面的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朱子格物说中存在着物理转化为性理的曲折,这种曲折正是王阳明不满意的主要原因。
通过此番“格竹”的失败,虽说让阳明感到心灰意冷,自委圣贤有份,却并没有磨灭王阳明“立志成圣”的追求。事实上,这一事件背后蕴含的哲学思考,让阳明对朱熹的学术路径产生了怀疑,这一怀疑所指向的就是“格物”与“成圣”之间有无必然的关系,换言之,即知识的寻求如何保证时时指向道德的增进?“立志成圣”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在学做圣贤的过程中将“格”外在的事物之理作为首要一环,那么将很可能产生与自我改造的德行修养分裂开来的危险性。
“庭前格竹”的失败让阳明渐渐对朱子格物说当中主体与客体的二分感到不满。诚然,讲求学问在于人格的养成,人格的完满在于道德的增进,道德性必然地内在于人而不是外在于物,如果“格物”的实践不能时时在德性的统领和照管之下进行,那么就很可能导致陷溺于具体的客观事物的考索而迷失自我、游骑无归。使得所有的实践活动都具有自我完成和道德修养的意义,让具体事物时时服务于道德的要求,才是阳明所努力和致思的方向。
王阳明在评判朱子的“格物之说”时,将其中的理论缺陷总结为“少头脑”。“头脑”一词是他在强调为学方向时经常使用的话头,在阳明看来,朱子“格物之学”的最大弊端就在于方向不明,不能凸显出道德的统领地位,道德与知识是断为两截的。③张学智教授在《明代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733页)中谈到,王阳明发现了朱子的为学之方中存在着一种道德与知识断裂的弊端,因为从物理到天理的转换与主体的精神境界和知识素养相关,而一般学者并不具备此种转化的能力。从中可看出道德与知识的问题是王阳明牵系终身的,他所努力的方向便是如何保证每一次的格物功夫都能促进德性修养的实现。虽然按照程朱的说法,掌握的事物之理越多,对心体的障弊也就越少,而此心也就越明,但“物理”与“天理”之间的转化需要有自觉的能力,换言之,在没有得到这种觉解之前,“物理”与“天理”是不能归一的,正是这种疏离感导致王阳明对朱子的学问路径提出了质疑: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④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
可以说阳明提出的这一问题极其尖锐,它的真正义涵在于知识的掌握如何能够促进德性的培养。儒学或说宋明理学的根本精神是在道德修养中个体生命的不断精纯,这一过程的最终指向是道德人格的圆成,道德在于意志的培养和锻炼,而不能归结为事物之理的积累。虽然在宋明理学的话语体系内,天地万物之理与内心固有的道德意识在根本处是同一的,但物与我之间在王阳明看来仍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面对广博无边的大千世界,即物穷理的为学路径让他越发觉得力不从心,这样一种体道的方式缺乏了道德性的统率和主体性的创发,极易产生外在的制约感和强迫感。因此,将道德放置于统领的地位去“格”事物之理,便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阳明批评朱子“文公格物之说,只是少头脑”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12页。这个少头脑,毋庸赘言就是缺少道德层面的监察和归导。
强调道德的凸显,并不是完全舍弃知识,恰恰相反,道德修养正是通过知识的获得来实现的,王阳明想要强调的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以道德作为主导。阳明非常注重在已发上求未发,在不离日用常行的下学中寻求上达的超越性,虽然在许多时候他为了突出道德的独尊性,甚至贬斥具体知识,但是他如此做的真正目的是把人们从偏离道德修养的流弊中解救出来,以扭转记诵辞章、夸识斗智的不良世风。他将“物”看做道德主体参与的结果,只有让道德与知识时时发生关联,让“物”变为主体的有特定价值和目的指向的“事”,方可避免出现支离鹜外的流弊。“格物”在阳明这里是价值与事实的合一,道德性的价值原则是“格物”过程中的先决条件,进而以此作为指导因应客观对象,则所“格”之物必然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
二、内在化转向
王阳明对于朱子“格物之学”内在隐含的理论缺陷已经产生怀疑,如果在“格物”过程中不能将所得之理时时与主体自身发生联系,则会导致“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沿着这一方向追寻下去,必然地要由外转向内,由物转向心。这一理论问题真正得到解决的是他三十七岁时的“龙场悟道”,这一次彻悟使他真正走出了朱子“格物说”的影响,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为学方向,而这一方向中最重要的便是主体性的回归和内在本心的确立。
我们只有真正意识到阳明内心所关注的问题时,才能更好地把握何以会出现这次彻悟。在此之前,阳明按照朱子所设定的达圣之方恳切笃行,认为成就圣贤与现实中的有所作为紧密相关。但龙场之变让他丧失了现实中的一切,艰难的环境不仅让他看淡得失荣辱,生命的意义亦变成了一个可以质疑的问题,这种痛切的体验使他进一步追问:如果真正的圣人面临这一处境当做何为?
阳明此问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意义,这就是无论外部世界变得多么不尽如人意,都不应该丧失做圣贤的志愿,在与外部世界切断关系的境遇中,如何成就圣贤,就变为如何通过内心的力量达到自我实现的问题。因此,“成圣”就变成自我反省以获得内心的真正转变,而这种自我转变的动机就内在于人之自身,“成圣”的实现只需要通过自我的努力便可达成,在这种意义之上再去与外部世界产生关系才是有意义的。
据《年谱》记载,阳明在龙场时“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强烈的“成圣之志”使他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终于在某天深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最终得出“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5页。的结论。在这充满神秘色彩的经历中,阳明宣示出一个全新的道理:天理并不在外部世界中,而是内在于人的主体自身。事实上,“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内在理路就是“圣人之道,吾心自足”,因此他感慨说:“及在夷中三年,颇见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③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6页。由此可见,阳明龙场所彻悟的道理仍然以“格物”为核心,通过对“格物”做出创造性的诠释,以内心本有的道德理性去统贯知识理性,只有这样,“格物”才能有益于身心性命,他说道:
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①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页。
在理学的范畴下,事物之理与本心所含的性理具有同一性,在根本处说,皆为天理的体现。王阳明在这种全新的“格物”诠释中,知识时时受到了道德的观照,物理时时指向那个超越性的天理,在阳明看来,他的心与理是时时合一的,从而避免了朱子“析心与理而为二”的弊端。阳明对于“格物”的定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内在自我的实现和完成,在这个意义上,格物就是正心、诚意的不同说法,也是明德、止至善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阳明通过对“格物”理论的内在诠释,使得《大学》中各个次序明列的条目统为不可分割的一体。抓住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懂得阳明立论的“头脑”所在,他的学说并不是对于朱子的完全颠覆,而是犹如用一条线一般将朱子学说中“平铺就列”的条目贯穿起来,充当这一条线的便是天赋的道德理性,因而,我们应当把阳明心学看作是朱子理学的“融通”与“消化”,将朱子强调的各个为学次第全部“化而为一”。任何功夫的实践都要作为道德增进的媒介,使得道德主体能够时时参与其中。
三、格物之理的不同侧重:道德事实与客观事实
在朱子构筑的理性主义大厦中,试图将宇宙万物均纳入一个终极价值原则的框架中,求索客观事物之理是明了性理进而体认天理的必要过程,因此就格物之理的范围而言,朱子既强调伦理层面,同时又关切客观事实,宇宙万物尽在所“格”之列。而王阳明所关注的乃是道德主体的内在超越,没有人的精神意识参与其中的道德实践便是无意义的,因而对纯粹客观对象的考察则不在其考虑范围,以下这则材料集中反映了这一点: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凊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知亦须请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凊,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请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②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3页。
在这一段话中,王阳明实际上是在和朱熹对话,徐爱作为朱熹学说的代言人,提出了他对“心即理”的疑问:至善之理如果只存在于心中,那么恐怕会对天下之理有所遗落,也就是说,心中的至善之理并不能完全包含天下事物之理,这是朱熹“一草一木,皆涵之理”的思路。但王阳明所要指出的是,做为至善的道德本体应存在于人自身,而不应求之于外部世界的客观对象,正如他所举的事例一样,忠、孝、信、仁的内在根据在人心中,而不在这些至善之理所指向的对象身上。这种表述实来源于孟子批驳告子的义外说,当告子说尊敬长者是因为他的年龄处于应当尊敬的地位时,孟子一句“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便道破玄机,明确地指出尊敬长者是出自内心而不是长者自身。同样道理,王阳明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的伦理实践不应该去对象中寻求至善,因为孝心必然存在于孝子身上,忠心必然存在于臣子身上,信与仁亦然,如果把这些至善的原则放置于对象之中,必然会导致“义外”的错误结果。道德原理既然内在于心,那么在“纯乎天理之心”上讲求至善,以天赋的道德意识去践行至善之则,那么行为必然地符合天理,这正是王阳明提出“心即理”的基本思路。
王阳明以内心先验的的道德理性去界定伦理实践的根据,明确至善是人心的本质所在,这毫无疑问是符合道德事实的。但是徐爱的疑问所隐含的朱子理学的实质在于,就算道德原理出自本心的至善,也不能说明“天下事理”都在人的心中,即至善无法包含自然、科学等领域的客观道理,因此徐爱才说“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按照朱子的说法,只有对于客观事物有全面而又深入的掌握,心中之理才能逐步明朗,天理的终极意义才会显现,这无疑也是符合客观事实的,但是王阳明列举的全是伦理层面的理,而对于事物的客观之理并未做出正面的回答。需加以说明,王阳明与徐爱的对话之中包含着“道德事实”与“客观事实”的区分,两人所指“理”的侧重有明显的不同。王阳明以“道德事实”代替“客观事实”的做法亦并未在同一学理层面上对朱子达成有效的批评。①陈来教授在《有无之境》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清晰的阐释。阳明指出道德法则并不存在于道德行为对象之中,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就范畴而言,天下事理除却道德行为规范准则之外,也包括自然具体事物的规律、属性、法则,阳明显然对此并不关心,这是他不同于朱子的重要特点。在正确理解思想家的哲学命题时,我们必须了解他所面对和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才能不迷失他所要表达的主要意向。在体证天理的终极意义上,朱子所侧重的是由事物之理的转化而涵养为至善的道德之理,而王阳明侧重的是在天赋的至善之理的指导、归引下陶铸事物之理,而二者的最终目的皆是达到对于天理的认识。
小结
就王阳明的学问宗旨而言,将道德的增进看做学问的根本,知识只有在道德价值的指向中才能拥有其积极的意义,知识的获得以保证德性的不落空,两者构成了相互促发的有机体,每一次“格物”的完成都包含两个方面的实现:道德性的促进和知识性的积累。这种统一使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得到了极大地阐扬,同时也避免了在“格物”过程中的游荡无归。可以说,王阳明坚持的是一种道德与知识结合的路线,在道德原则为首务的视域下实现内圣,同时又以内圣开出外王的事业,只有在这种致思框架中,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阳明将格物说内在化于主体的真切意图。
阳明对于“格物”的解释在于用道德去统贯知识,而并非舍弃物理,但阳明所指的“物”仍有新的内涵,将“物”训为“意之所在”,即无时无刻没有道德理性的参与。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只有让道德与知识时时发生关联,让“物”变为主体的有特定价值和目的指向的“事”,才会避免心与理的割裂,从而出现支离鹜外的流弊。“格物”在阳明这里是价值与事实的合一,道德性的价值原则是“格物”过程中的先决条件,而且在道德理性自身之中就含有主动获取知识的驱迫力。因此,在扫去私欲的障蔽后,“纯乎天理之心”便会自然呈现出来,进而以此作为指导,主动地因应客观对象,则所“格”之物必然是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