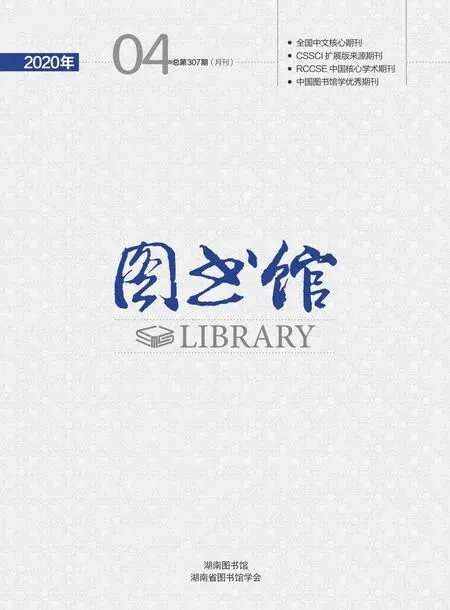现代图书馆空间变迁逻辑与再造实践*
2020-01-08闫小斌
范 红 闫小斌
(1.西安文理学院 西安 710065; 2.陕西科技大学 西安 710021)
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给图书馆空间观念和空间再造实践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空间和时间是人类感知物质世界的两个基本维度,传统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以时间为主线,空间往往只是叙事的“背景”。19 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空间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空间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独立的研究对象,阮冈纳赞关于“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1]的论述,也肯定了图书馆空间具有自主发展的生命力。从传统图书馆“书的空间”定位、到复合图书馆“数字空间”重构、再到现代图书馆“第三空间”共识,图书馆空间始终处在运动和变化之中,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2],其中以多元、开放、共享、公平、包容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图书馆空间理论框架,深刻影响着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的发展。
1 空间认识论对图书馆空间观念的影响
1.1 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
在早期西方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空间既不是一种“社会的”现象,更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通常只是作为事物或事件的“背景”出现。直到20 世纪下半叶,后现代主义社会学家完成了“空间认识论”转向之后,空间才从“幕后”走向“前台”,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新兴分支学科。
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最早发现了空间具有自然与社会两种属性,认为空间的社会属性高于自然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以转化为空间与空间的关系[3]。这个观点颠覆了人们对空间的传统认识,也为空间研究敞开了新的大门。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的代表作《空间的生产》被誉为空间分析、研究的经典著作,他认为人类社会中的空间已经不是那种自然的空间,人类生活的主宰是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就是一种空间存在,它存在于空间,又“生产”空间[4]。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甚至认为:在我们的时代,空间关系已经取代了时间关系成为把握人类现实的核心范畴[5]。
列斐伏尔的学生爱德华·索亚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中发展出“第三空间”的概念,认为“第三空间”既不同于物理性的第一空间、也不同于精神性的第二空间,它是两者的结合并超越了两者,可以用来探索传统空间理论没有认识到的新问题[6]。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也从生活实践角度提出了“第三空间”的概念,他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自由、宽松、便利的公共空间[7],没有第一空间(家庭)角色的束缚、也没有第二空间(职场)等级的限制,人们只有在这个空间中才是平等和自由的。
从齐美尔空间属性的划分、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福柯空间关系“核心范畴”,再到索亚和奥登伯格的“第三空间”,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不仅重塑了空间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与人、空间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而且推动了时间哲学向空间哲学的转变,为现代图书馆空间观念变迁和空间再造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1.2 中国古代的空间观
人类早期的空间观念是伴随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而逐渐建构起来的。尽管宇宙自然空间在人类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只有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对自身赖以生存的空间环境有了一定认识,如“天人合一”的思想或者对太阳、月亮、北极星等具有标识性星体的发现和观察[8]。
“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对人与自然空间关系的基本认知。无论是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还是董仲舒的“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以类合之,天人一也”[10],亦或是易学的“阴阳五行”,都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论述,体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古老智慧,同时也对中国古代建筑选址规划、设计理念、空间布局产生了深刻影响:古代建筑中强调的“对称”和“中正之美”,就是追求人与天地的和谐同步、建筑与环境的协调统一;而“前低后高、错落有致”的建筑布局,既贯彻了“礼”的理念,是不同身份的象征,也是采光、礼让的体现[11]。如果说儒家文化在建筑中强调的是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而道教文化在建筑中则更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家的建筑多为修行和供奉神明所用,“留空”是道家建筑的显著特点,要求空间保持一种清净和谐的状态,让修行者在自然的“空”中感受“天人合一”的真谛。
西方的空间社会学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尽管在理论渊源、概念体系和研究范式方面有诸多不同,但都为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指导原则,践行了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发展理念。
1.3 国内图书馆空间理论的构建
2005年,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吴建中先生在其《开放存取环境下的信息共享空间》一文中,首次将信息共享空间(IC)的概念引入国内学术界。他从图书馆的三要素“人、资源、空间”出发,提出“要挖掘图书馆作为场所的价值”,通过拓展图书馆作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功能推动图书馆服务转型[12],对国内图书馆空间理论研究和“再造”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2006年复旦大学视觉艺术学院图文信息中心正式建立起国内首家信息共享空间(IC),拉开了国内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的序幕。
在2009年国际图联会议上,“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成为会议讨论的主题之一,标志着图书馆界对空间价值的认识有了新的提升,带动了图书馆空间理论研究的发展。
2014年4月,中国图书馆学会高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举办了“空间管理与环境建设”专题培训班,系统讨论了高校图书馆空间的“组合性、伸缩性、移动性和体验感”等问题[13]。顾建新认为,图书馆空间“再造”就是要从“作为场所的图书馆”转变为“作为空间的图书馆”,更多地关注“人”的感受,更多地重视空间资源的价值[14];姜世峰认为图书馆的建筑设计,要适应数字化、信息化发展,以多样化的空间形态,体现“城市会客厅”的社会职能;褚树青提出了“第三文化空间”概念,希望将杭州图书馆打造成为“市民文化娱乐最想去的地方”[15];段小虎在系统梳理图书馆空间“逻辑边界”和“文化形态”之后,提出了“重构图书馆空间认知体系”[16]的基本理论框架;闫小斌从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入手,分析了图书馆服务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本身生产的转型趋势[17]。
如果说空间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揭示空间的本质属性、社会功能和演变规律,那么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的根本任务,就是将空间的应有价值转变为实际应用价值。
2 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价值取向
国内外图书馆空间理论研究具有密切结合空间再造实践的特点,但理论与实践毕竟不完全在同一个话语体系之中,无论是对空间理论的片面理解还是将空间再造简单地看作某种空间观念的现实再现,都可能违背空间发展规律或导致新的空间矛盾。因此,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以空间理论为基础,处理好空间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与人、空间与空间的关系。
2.1 处理好空间与社会的关系
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有关空间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阐述,为理解图书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严格地说,图书馆与社会、图书馆空间与社会是两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前者是图书馆作为一个整体与社会既有关系的总结和概括,集中表现为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后者是图书馆特定资源——空间资源与社会关系的阐释,具体涉及到现代图书馆空间的社会性质、社会价值。
首先,现代公共图书馆空间是无条件公共空间。无条件公共空间也称绝对公共空间,具有公共性和非竞争性两个基本特征。公共性和非竞争性是用来描述公共资源社会性质和使用规范的一种基础性分析工具,这里特指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财政支持下的公益性服务机构,其空间资源的性质是由公共机制而非市场机制决定,不支持市场化的竞争和私人、部门利益诉求。
其次,现代公共图书馆空间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正义空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1994)明确提出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平等享受公共图书馆服务的权利,而不受年龄、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国籍、语言或社会地位的限制”并为“特殊群体提供特殊服务”,这是维护图书馆空间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除此之外,国内图书馆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处理好基本服务与非基本服务、共性化服务与个性化服务、传统服务与新兴服务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要根据中国具体国情处理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致力于消除“城市中心主义”[18]倾向。
现代图书馆空间的公共性、公正性价值追求,会受到地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制度体系、人口结构、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空间布局结构、空间资源配置、空间供需匹配、空间资源利用率等问题,又涉及到公共空间中的利益关系。例如当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城乡二元格局”,导致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与乡村公共文化空间严重分裂,表明事实命题与价值命题分属于两个不同领域,加上效率与平等之间难以回避的冲突,就必须采取特殊手段——将更多的优质空间资源向农村基层倾斜,实现事实意义上的空间正义。
2.2 构建空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中国古人很早就有“天人合一”的观念,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身处现代都市之中,人们对于自然还是有很强的生理依赖和心理向往。因此,构建空间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就是要秉承低碳、节能、环保和生态融合理念,通过对自然风、自然光、绿色植物和环保材料的综合利用,为读者营造自然、健康、舒适的“第三空间”,使读者有回归自然的感觉。
芬兰被誉为“千岛之国”“千湖之国”。芬兰的赫尔辛基是世界排名第二的高纬度首都,冬季漫长、日照短暂。赫尔辛基中央图书馆的设计者根据这种自然环境特征,将自然采光最好的顶层设计为全开架阅览学习区,在波浪形的白色吊顶中,不规则地布置着圆筒形天窗,很好地解决了采光和空气对流问题,被誉为 “书的天堂”“读者天堂”。美国西雅图位于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之间,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每年降雨量将近1 千毫米且多为小雨,因此有“雨城”之称,每年平均阴天数226 天。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设计者根据西雅图雨水多、阴天多、光照短等特点,专门设计了雨水采集装置和循环灌溉系统,凹斜的采光玻璃顶棚使室内光线充盈,温馨舒适,营造出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的空间体验环境,堪称现代图书馆空间设计的典范。
“借景”也是构建空间与自然和谐关系的重要手段。借景是中国传统园林重要的造园手法之一,《园冶》中提到:“夫借景,园林之最要者,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借者,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须远近。”[19]也就是通过视点和视线的巧妙组织,把本来在范围之外的景观纳入观赏者视线之中,创造出一个尽可能广大的“天地”。如阿那亚的“孤独图书馆”“借”来了浩瀚大海,成为著名的“网红”打卡地;颐和园昆明湖“借”来西山的一座座山;沧浪亭沿山而建的长廊通过上百个漏窗将园内的假山和园外的水景融为一体,实现了“一步一景”“移步易景”,颇有几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趣味[20]。通过景物融合可以突破场地的限制,使空间与自然景观相互呼应、相互融合,将空间境界无限延伸,既丰富了园林景观风格,又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11]。
当然,除了“借景”之外,“造景”也是图书馆空间改造中的常用手法。“造景”通常是直接将山水、花草树木等自然景观置入室内,取代传统建筑墙面的空间分割方式,既能将大自然的气息带入空间内部,也可产生通透的视觉效果,令读者赏心悦目。
2.3 发挥空间塑造人的积极作用
早在空间社会学理论形成初期,米歇尔·福柯就注意到空间与人的关系,认为空间对人具有约束力和管制作用;戈夫曼进一步强化了空间对人的支配作用,甚至认为空间在人之上,为人的行为立法[21]。
与上述理论有所不同,以齐美尔为代表的古典社会学家,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空间理论,他们认为在人与空间的关系中,人是第一位的,空间最终是为人的交往活动服务的。在齐美尔看来,空间具有排他性、分割性、内容固化性,空间接触能够改变社会互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空间中的群体流动有助于削弱空间的分化[17]。例如研讨空间的设立为读者提供了与以往静态学习完全不同的空间体验和心理感知,增强了人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了互动式学习方式的推广;创客空间的出现将有着共同兴趣与爱好的“创客”(Maker)聚集在一起,培养他们的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力,使他们能够利用开源硬件和互联网,把更多的创意转变为产品。这些案例反映出空间与人的基本关系:“人是空间的创造者,但空间也在塑造人、改造人。”[22]
空间塑造人还表现在空间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爱德华·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就充分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在索亚看来,第一空间是物质化的“实践性空间”,第二空间是精神意义上的“构想性空间”,而两者结合产生的“第三空间”才能表现出城市空间的真正活力和复杂性[23]。
空间社会学理论表明,现代图书馆空间不仅具有物理空间的基本属性——是图书的栖息地,是新旧媒体共存、多元需求交织、实体与虚拟共融的文化消费场所,同时也具有精神空间的属性——是“人类思想与观念活动的领域、一个探索未知并获得想象和智慧的场所”[24]。两者的结合对人类精神世界有着重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图书馆被阿根廷文学家博尔赫斯称为“拜神所赐”的作品[25],被印度诗人泰戈尔喻为“人类精神的河流”“自我解放的灯塔”[26]。
2.4 合理化解空间内部矛盾
现代图书馆空间具有学习、交流、娱乐、休闲等多元化社会功能,学术界也有“信息共享空间”“社会公共空间”“第三文化空间”“知识共享空间”“社会创新空间”“学习交流空间”“知识生活空间”“休闲娱乐空间”等多种空间特征概括。然而,空间功能多元化和空间结构复杂化,将会使空间矛盾更多,米歇尔·福柯所说的空间对人的约束力和管制作用,就需要通过点、线、面、块的科学设计形成合理的空间秩序。
点、线、面、块是建筑空间表现的基本形式。点是建筑空间最基本、最简单和最灵活的设计元素,在空间中起到场的凝聚作用;线具有重要的造型功能,可形成某种心理暗示或表现空间的动态美、秩序感,最短距离、最美视觉效果和最好的服务体验都需要流畅的线型设计;面和块是相对独立的二维、三维空间,是能够满足某种具体功能或具体需求的空间单元。
美国西雅图公共图书馆(以下简称SPL)在化解空间矛盾方面的设计独具匠心。SPL 从上至下共分九大体块,每个体块按功能差别,有着不同的大小、流线、色调、结构。在每两个相对私密的体块之间设立一个活跃的公共活动空间,增强了图书馆整体空间的互动交流功能。顶层的体块为办公区,向下依次是螺旋书库、采编、仓库及设备停车。中心阅览区作为单独的一部分悬浮于建筑的上部,下面的开敞空间用来演出、交流、开展文化活动等,彰显出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中心的职能属性。在流线设计方面根据基地现有高差,在不同标高层设有不同入口,主入口由三层进入,就近设有残疾人电梯;少儿和外文入口则设在相对一侧,避免了对儿童的干扰。各个功能体块之间均有电梯或自动扶梯相连,并用明亮的黄线强调了主要的交通流线。不同的人被分流到不同的体块内,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自己的借书过程[27]。整个建筑空间虽然规模宏大,但通过点、线、面、块的合理设计,巧妙安排形成一种福柯所说的“微观的权力机制”建立起的一种高效的空间秩序,最大限度化解了多元文化形态共存条件下各种空间矛盾。
3 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发展趋势
空间社会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改变了图书馆传统空间观念,也为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拓展空间。然而,作为现代图书馆服务创新的重要手段和空间发展新的“增长极”,大规模、持续性的空间再造实践,也影响了传统图书馆空间的稳定性和结构的单一性,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出现的空间边界模糊化、空间互嵌多元化、空间矛盾复杂化等新趋势,对现代图书馆空间理论构建以及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安排形成了新的挑战。
3.1 空间边界模糊化
以往说到图书馆空间,通常是指一个有着固定位置、固定边界、固定尺寸和独立的、静止的“物理空间”。空间社会学理论关于空间社会属性的研究,重构了图书馆空间观念,推动着空间再造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馆中馆、馆外馆、总分馆、联盟馆以及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上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新的图书馆空间形态的出现,将图书馆空间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图书馆空间布局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深圳、东莞等发达地区的“书香城市”建设,已经将“城”与“馆”融为一体,甚至出现了“城市在图书馆之中”的景象。另外,以往图书馆只能在传统界限分明的公共空间中找到自身的栖息地,但如今却延伸到商业空间、私人空间乃至家庭空间……如温州的“城市书房”就是依托商业用房建造的,实现了商业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融合;温岭的“家庭书屋”既是私人空间也是公共空间。程焕文教授曾经说过,“图书馆的空间有多大,图书馆的舞台就有多大”[28],而空间再造实践的发展似乎表明“城市空间有多大,图书馆的舞台就有多大”。从空间社会学理论的角度看,图书馆空间边界的模糊化并非一个独立的现象,而是整个社会空间格局的重塑:拓展了现代图书馆空间理论研究领域,深刻影响现代公共图书馆制度安排,甚至改变政府、社会、市场之间的传统利益关系。
3.2 空间互嵌多元化
空间互嵌是现代图书馆空间发展的又一显著特点,具体有两种表现:一是在传统图书馆空间格局中,嵌入新的空间。如果说1992年美国爱荷华大学在图书馆里建设的“信息拱廊”,随后又演变形成信息共享空间(IC)、学习共享空间(LC)、知识共享空间(KC),还属于传统图书馆空间内部的价值挖掘,那么21 世纪以后,很多图书馆将众创空间、咖啡厅、剧院、音乐厅、实验室、展厅、技能培训中心等引入图书馆之中,就属于空间互嵌的新发展。如美国的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儿童图书馆,除了为婴儿和青少年提供大量书籍外,还设有一个计算机实验室、一个教授儿童烹饪技能的教学厨房和一个拥有165个座位的剧院;芝加哥图书馆的托马斯·休斯儿童图书馆不仅设有木偶剧院和婴儿花园,还为年龄较大的孩子提供数码媒体设备,以方便他们创造自己的数字艺术。二是在其他公共、商业或私人专属空间中嵌入图书馆空间,如温州的城市书房,就是图书馆空间与商业空间的结合;温岭的家庭书屋,就是图书馆空间向家庭私人空间的延伸。其中温岭市还尝试在渔民的渔船上建立船上人家图书馆,渔民驾着渔船,即使在远隔千里的大海上,也能享受到公共图书馆服务。另外,企业分馆、学校分馆、机关分馆、部队分馆、监狱分馆、众创空间分馆等,都是空间互嵌多元化的具体表现。
3.3 空间矛盾复杂化
空间边界模糊化和空间互嵌多元化自然地派生出空间矛盾的复杂化。一是图书馆空间理论与再造实践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图书馆空间的稳定性;温州的城市书房、温岭的家庭书屋以及各种类型的分馆、自助图书馆,都曾出现过终止合同、改迁、撤销的情况,甚至图书馆在内部空间格局调整中,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空间秩序,出现了决策失误或资源浪费;二是图书馆空间与商业空间互嵌过程中会产生一些法律或利益分配问题,加上现行政策体系中免费基本服务边界不清、可以收费的非基本服务政策不明,也给一些希望打政策擦边球的图书馆带来违法风险;三是在多元文化形态共存条件下,空间边界模糊化和空间互嵌多元化派生出新的空间矛盾,对以公共性和非竞争性为基本内涵的“无条件公共空间”价值体系以及图书馆传统社会职能、图书馆核心竞争力构成新的挑战,体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空间公平正义也需要有新的阐释。
3.4 空间发展智能化
随着5G 时代的到来,人工智能技术已逐步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工智能被认为是“第四次产业革命”[29]、 图书馆界的未来六大创新技术之一[30]。我国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未来十年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要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人工智能时代用户的信息需求和空间体验将更加多元化,更注重空间的个性化和体验感,智能化必将是图书馆空间再造的发展趋势。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作为“第三空间”的图书馆将能更好地满足用户的体验感和获得感,而空间再造从信息共享也转向创客空间、学习空间乃至智慧空间的内涵式发展。国内最先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是深圳图书馆的RFID 系统,实现了馆藏系统的精准定位,改善了馆藏流通状况,降低了人力成本。目前,基于感知技术的WIFI、RFID、人脸识别智能系统在许多公共图书馆得到广泛应用[31]。如江苏常州“魔力书屋”[32]、株洲市图书馆“智能书屋”[33]、上海杨浦区图书馆“信用智能借书柜”等[34]。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以及神经网络、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未来图书馆将有望构建立体化的智能空间。从灯光、温度的智能控制,到文献采集、自动盘点,再到各类资源、服务的智能推送,图书馆将加速实现转型发展与服务创新。
如果说馆中馆、馆外馆、总分馆、联盟馆以及数字图书馆、复合图书馆、网上图书馆、移动图书馆、流动图书馆、自助图书馆等新的图书馆空间形态的出现,使图书馆的物理空间边界得以延伸,那么人工智能技术将使图书馆的虚拟空间边界再度扩展,真正体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图书馆服务。
4 结语
空间社会学研究,有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即从实践出发或立足实践研究空间与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与空间和空间与人的关系。相比而言,图书馆“第三空间”观念的成熟并不意味着其空间理论体系的成熟,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居住城市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平与空间问题相互交织、共同作用,使得仅仅从图书馆发展角度理解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已经无法解释或解决当前公共空间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也难以推动有关图书馆空间变迁、空间矛盾、空间权利、空间正义、空间治理、空间秩序的研究。特别是,现代图书馆空间再造如果没有系统理论的支持,很容易出现盲目、无序、攀比现象,甚至制造出新的空间矛盾。因此,在研究和学习空间社会学理论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和地域文化构建现代图书馆空间理论框架,对于推动图书馆空间再造实践发展,形成理论构建与空间再造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