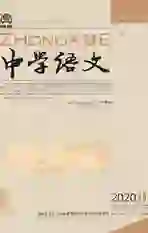音象:诗在用文字歌唱
2020-01-07佘蜀强
佘蜀强

用文字驾驭《雨巷》之美,真难!
《雨巷》不是用文字,而是用音乐写成的。我相信,无论是大学教授,还是一线教师都会认同我这个观点。然而,作为《雨巷》艺术首要特征的“音乐性”,一走上讲台,就变得混沌不清、无法言表。诗人用音乐浇灌文字,感染我们,轻而易举,因为他相信自己的文字;我们用文字分析音乐,传递给学生,难上加难,因为我们不知道该讲些什么。这是一个坚硬如墙的教学现实,似乎多年都不曾改变。
一、文本细读
1.音象:诗歌解读中常被冷落的概念
这里先介绍一个概念——音象。黑龙江大学韩伟认为:“‘音象是对中国文学中声音之象的泛称,是指文学(诗歌)作品在音乐或格律的参与下形成的声音效果,以及由声音效果产生的形象体验。”苏州铁道师院徐于认为:“诗歌的语言音象包括词语的语音音象(声、韵、调及其书写形式)和诗律音象(体制、韵式和格律)。”
声音是有形象的,这与我们惯常的思维大相径庭。用适宜的教学手段让学生体验这种形象以及相关艺术效果,是我们诗歌教学应有的内容。目前,音象教学只有大致方向,缺乏方向下具体且明晰的内容支撑。我认为,一线诗歌教学不妨先从“五音(喉、舌、齿、牙、唇)”“四呼(开、齐、撮、合)”中厘定出具体的教学内容。
“五音”(喉、舌、齿、牙、唇)侧重从声母发音部分考查声音,特别是发声的特点,“四呼”(开、齐、撮、合)侧重从口形角度考查韵母发声特点。了解发音部位以及口形特点,还仅仅停留于对声音形式的把握范畴。事实上,每一种部位、口形产生出的声音形象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喉音”因发音部位较深隐,所以音调偏深沉,音长最长,并带有一定的颗粒粗糙感以及明显的挤压感;“齿音”因发音部位较之“喉音”靠前,空间较小,所以音调偏浅尖,音长较长;“舌音”较“齿音”发音部位进一步靠前,音调较为洪亮,音长次短;牙音发音部位在舌尖前,音调柔细,音长居中;“唇音”因发音部位最前,口腔囤聚气流,所以音调较浅浮,音长最短。
清代朴隐子在《诗词通韵》中这样描述四呼:“开口呼”舒颊引喉,音疏以达;“合口呼”聚唇开吻,音深以宏;“齐口呼”交牙戛齒,音窒以敛;“撮口呼”敛颐蹙唇,音奄而藏。
2.意象都是魔咒
分析《雨巷》,自然绕不开“雨巷”“丁香”“姑娘”这三个关键意象。
从音象角度来看,“雨巷”声母组合为“喉齿音”(因“雨”属于零声母,一般归“喉音”),韵母组合为“撮齐呼”。低沉且绵长,窒敛而掩藏。“雨巷”有何特点?“悠长”“寂寥”。文本中写得明明白白。但这就是戴望舒想传露的全部心绪?静心再念念“雨巷”二字,除了“绵长”,还应有“狭仄(气息敛窒)”“曲折(声气遮掩隐藏)”之感。诗人未用文字言明,自待音乐进入读者内心,自感自明。当然,“狭曲”之感还与诗境暗合。试想,若雨巷“宽广”“笔直”,“姑娘”不是能一眼望到?如此,诗境便逊然不少。
再看“丁香”。声母组合为“舌齿音”,韵母为“齐齐呼”。浅尖洪亮之中又不乏窒敛掩藏。基于音象,至少有如下三层分析:“丁香”花纤柔浅艳;诗人心中、口中迸发出这个意象时,多有“欣喜”之情;然而很快又有“遮掩难言”之意。“丁香”两字可谓深蕴情脉!正如戴望舒诗友戴杜衡在为其诗集《望舒草》写序时说:“望舒开始写诗时,诗坛通行自我表现,坦白奔放,写诗要直说,而戴对此加以反叛,认为诗是个吞吞吐吐的东西,重在暗示,其动机在表现与隐藏之间。”
最后看“姑娘”。声母组合为“喉舌音”,韵母为“合齐呼”。细细读完后,仍有敛窒,还有深宏之感,基本上延承了“丁香”二字的音象特征。
所以,如果说“雨巷”二字在“长度”上为我们营造出了一幅绵仄、曲幽自然背景的话,那么,“丁香”与“姑娘”又在“广度”与“深度”上完成了对全诗主体情感的建构。而这一切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诗人悄无声息地将音律魔咒散播进读者内心,并在我们的潜意识中生根发芽出一缕缕难言的艺术共鸣。
3.细节最难读
第一个细节在文本开篇。“撑着油纸伞”。诗人开篇便将“我”隐藏得很深。为何要“撑着”,而非“打着”?“撑着(齿齿音,开开呼)”读来浅尖疏达,一则表明“我”举伞动作之轻柔,二则似乎还在暗示伞柄细短,伞弧扁平;而“打着”虽在韵母上也是“开开呼”组合,但声母变为“舌齿音”,较之“齿齿音(撑着)”,多了些洪亮之感,却无法在音韵上与后文“油纸伞”谐拍。
“油纸伞”。“伞”为“油纸”(喉齿音,齐齐呼),深沉浅尖窒敛,既反映出“油纸”本身质地之轻柔,与“撑着”形成音谐,也留给我们想象空间:“油纸”颜色繁多,诗人避而未谈,读者愿为其着染何色?既然声音如此“深沉”,不妨着以朱红或暗黄吧!柔小而单薄的朱红(暗黄)伞面,远远望去,在狭仄的“雨巷”中,塞闷拢聚,与其说在遮挡什么,不如说在倾诉着什么。如此一来,“油纸伞”与“撑着”的轻柔形成龃龉隔阂。这又是一番别样的审美意境!
第二个细节“我希望逢着”与“我希望飘着”。“逢”(唇音,开呼),“飘”(唇音,齐呼)。“唇音”浅浮;“开呼”疏达,“齐呼”窒敛。其一,无论如何,在“我”的希望之中,“丁香一样的姑娘”总是飘忽不定。其二,两处都是“希望”,诗人却用音韵掩藏住了两份不一样的情绪。前处多少还有“憧憬的欣悦”;第二处,随着“女郎”“走尽这雨巷”,“憧憬的欣悦”中披上了“阴郁”的色调。
当然,“女郎”(舌舌音,撮开呼)较之“姑娘”(喉舌音,合齐呼),念起来少了一份“深沉”,多了一丝“洪亮”,更多了一番强烈对立——“撮”“开”,先是“奄藏”,后竟“疏达”!音象落差极为巨大。统观整首诗,出现“女郎”一语的第五诗节是“我”距离“姑娘”最近之时。“最近”似乎代表着“我”复杂情绪博弈至高潮。此时的“我”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苦恼!为何?
一般认为,《雨巷》是戴望舒书写自我的文字。众所周知,戴望舒天生忧郁。1928年,他爱上了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虽寓居施蛰存处,日日与绛年相见,却羞于启口,借诗表白,而绛年偏偏不应,最后他只得以跳楼相挟,才得以让对方勉强答应。《雨巷》作于前一年,也即是1927年。可以说,那时的戴望舒就在为自己的所爱受着折磨,虽然那时他可能并不熟识绛年。这便是一种性格。
诗中“我”见着“所爱”走近,既激动欣悦,又苦恼!苦于“所爱”的易逝,也恼于自身本就忧郁不善表达的心性。这是多大的痛苦与矛盾啊!而这一切竟凝缩于“女郎”一词中,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事实上,“撮呼”“开呼”如此富有落差的搭配在诗中还并未只此一处。
第一、七节“愁怨的”,第二节“在雨中哀怨”以及第六节“在雨的哀曲”均为“撮开呼(或开撮呼)”的韵母发音组合。
惯常分析,姑娘的“愁怨”,雨的“哀怨(哀曲)”就是诗人忧郁心性的诗化投射。这只分析对了一半。在“撮”“开”的强烈反差中,诗人是“矛盾”的:姑娘啊!愁怨的姑娘啊!你为何愁怨?可不可以不再愁怨?这些就不再是单纯的“情绪投射”分析,而是自我的“纠结”与“挣扎”。
第三处细节,“到了颓圮的篱墙”。为何不是“颓败的篱墙”?“圮”(唇音,齐呼),“败”(唇音,开呼)。显然,“败(开呼)”发音疏达,如入平旷之地,没有“圮(齐呼)”发音时窒敛带来的紧压狭细之感。“篱墙”二字也是“齐齐呼”,进一步与“颓圮”完成了音合照应。再联系“雨巷”的发音,也有窒敛之感。所以,“我”之于“雨巷”,似乎“姑娘”之于“篱墙”,颇有《断章》诗的运思韵味。
统观整首诗,还有不少“排比”或类似“排比”的句式。
“丁香一样的颜色(齐齐齐齐开开开呼),丁香一样的芬芳(齐齐齐齐开开开呼),丁香一样的忧愁(齐齐齐齐开开开呼)”“像我一样(齐合齐齐呼),像我一样地(齐合齐齐开呼)”“像梦一般的(齐开齐开开呼),像梦一般的凄婉迷茫(齐开齐开开齐合齐开呼)”“消了她的颜色(齐开开开开开呼),散了她的芬芳(齐开开开开开呼)”“太息般的眼光(开齐开开齐合呼),丁香般的惆怅(开齐开开齐合呼)”。
仅从韵母组合看,一些词语“颜色”“芬芳”“忧愁”虽词意各异,但发音上却有相似。同时,大量“齐”“开”呼的运用,让整首诗在“疏达”“窒敛”的音象中,完成了诗气的跌扬与流转,形成了一种说不清言不明的矛盾诗境。
所以,我一次次努力地读着《雨巷》,越读越发现,在每个被音乐浸透的文字骨缝中,除了“寂寥”“凄婉”“迷茫”之外,都是“矛盾”而“焦灼”的诗者魂灵。
二、教學思考
教学概念需要用概念周圆与支撑,深化与延展。“音乐性”就是众多文本赏析与解读中不可回避的概念之一。然而很多时候,这个概念仅仅停留于概念,缺乏更多概念的周圆与支撑,深化与延展。因而,一碰到“音乐性”,我们要么一语带过,让其成为文本分析时孤零零的套语惯词;要么仅仅停留于“轻重缓急”分析上,错失了文本深处那一片片绚烂的景致。
“音象”也仅仅只是一个概念。“五呼四音”是周圆与支撑,深化与延展“音象”的一个概念,因而,在今后教学解读与实践中,我们还可以开掘出更多概念去丰厚“音象”,进而不再让“音乐性”成为文本解读、教学实践的一副空壳。
分析至此,借助“五呼四音”,我们不仅能走进《雨巷》,还能重温《再别康桥》,乃至《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只不过,我们更习惯听诗歌用文字歌唱。
[作者通联:四川乐至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