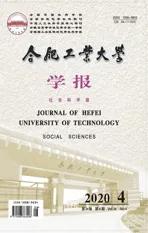边缘人物知多少
——论伊丽莎白·乔利《井》的多重空间叙事
2020-01-07杨甜甜
杨甜甜,戚 涛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伊丽莎白·乔利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混血家庭,成长于二战后的民族主义盛行时期,因为带有奥地利血统,她备受社区的歧视和孤立,而母亲的跋扈冷漠加剧了乔利精神上的伤痛,使她进一步滑入社会的边缘。而边缘化的生存体验使乔利更深入地感受到社会边缘群体的无助与困苦,并力图在文本中表现出来。她的作品主要关注那些处于社会边缘的人,小说《井》为乔利捧回了澳大利亚文学最高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乔利也凭此成为“澳大利亚小说领域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井》讲述了独居的跛腿老处女与年轻漂亮的孤儿凯瑟琳在与世隔绝的居所内纵情欢乐,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打破了表面和谐的生活,两人之间的关系由亲密无间变得猜忌怀疑、剑拔弩张的故事。
国内外学者对小说《井》的研究还相对较少。国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偏重于乔利小说的主题、人物和结构模式的分析,90年代以后的评论则把文本放在后现代语境下,结合现代文学理论和叙事理论探讨乔利小说的意义[2]。国内学者则分别从小说的符号学、边缘意识、女性主义等方面对文本进行阐释,或揭露男权文化体系对女性的压迫,或解读海斯特的人格符号。
但上述研究大多停留在文本本身的分析,很少涉及乔利对空间的运用。本文以空间叙事理论为基础,聚焦乔利在《井》中搭建的多重空间以及空间叙事策略,通过分析以揭示乔利如何在文本中借助物理空间的转换、叙事的碎片跳跃与虚实交错,以及有意的运用文本留白和意象重复等手法,达到艺术地展现并引导读者理解边缘人物被压抑的生存状态、矛盾扭曲的心理状态的目的。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下空间叙事的基本理论。
二、空间叙事与乔利
20世纪后半叶开启了文学话语的空间转向。约瑟夫·弗兰克在1945年发表的《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中首次提出“空间形式”这一概念,并将其定义为“试图克服包含在文学结构中时间因素的补充物”[3]。福柯在《小说中的时间和时空体形式》中也表明叙事是由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组成。埃里克·雷比肯在《空间形式与情节》一文中指出“小说、故事创作的最佳的叙述方式都是空间性的,空间叙事可以有效地对读者的感知进行建构”[4]。在文学批评领域空间转向的大背景下,现代作家纷纷参与到空间表征的建构中,借助文学话语进行空间化的创作。“在安排事件之间的关系时, 不是遵从时间的次序性、流动性或因果逻辑, 而是遵从空间逻辑, 或者说遵从空间分布和空间性联系。这种分布不是线性的, 而是块状的, 分散的, 甚至是交叉的, 可逆的。”[5]
伊丽莎白·乔利在后现代空间叙事潮流影响下,也将空间性的建构引入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把叙事的焦点聚焦在过去与现在的交替瞬间,表现现时与未来之间的割裂,时空倒错。”[6]她在小说创作中结合后现代实验主义,突破传统叙事的次序性和逻辑性,构建立体的空间网络,成功实现文学话语的空间转向。
除了文学潮流的影响,她对破碎空间的使用与她边缘人的身份,也不无干系。作为一个游离在奥地利文化与英国文化边缘的文化浪者,她时常感到精神上的压抑与错位。乔利坦言“写作是她宣泄内心哀伤,苦闷,焦虑等情绪的出口”[7],因此她在作品中选择用空间叙事的质素碎片和隐秘零散来再现内心的矛盾、迷失与不安。《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在小说中大量运用空间元素,建构了一个多维立体的空间结构,以展现人物的边缘状态,其中包括物理空间、文本形式空间以及读者心理空间。
三、多重空间的搭建
1.物理空间
“文学中的物理空间通常指故事叙述事件所发生的地点”[8]。在现当代文学作品中,空间不再只是僵化的背景,更投射出人物的情感色彩,体现了人物的身份认同。个体总是在空间中确认自我的存在,因此,能否实现对空间的占有,成为个体身份建构的关键。《井》中,海斯特经历了由父权压制空间到开放流通空间,再到自我重生空间等几个物理空间的转换。空间的转换实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个体与自我的交互,在此过程中也揭露了主人公们边缘化的生存处境。乔利通过家庭空间的暴力占有折射出海斯特边缘化的“他者”地位,通过流通空间的开放、包容揭示边缘人物的情感诉求,并通过重生空间内的权力失衡表现人物边缘性的自我异化。
海斯特是当地最大农场主的女儿,最初生活在农场边的古老庄园里,此家庭空间作为意识的隐喻,象征着父权的压制。整个宅子虽然高端奢华、条件优越,但是却处处充满了固定的模式、传统与仪式[6]28。海斯特在此空间内是无声的存在,是边缘化的“他者”。身为中上层阶级的女性,海斯特享受着优渥的物质条件,然而女性的性别身份以及跛腿的生理缺陷使她一直游离在男权社会的边缘。这种边缘性首先便体现在家庭空间内。家庭空间本该是一个人身心放松的场所,然而海斯特却只感受到淡薄冷漠和绝对的权力压制。父亲哈伯先生喂牛排给狗,却不顾及吃水煮面粉的女儿,他严格控制着海斯特的开销,否定着海斯特的一切。他是家庭空间内的绝对主宰,“他总是在屋里巡逻,试图想起自己藏匿手枪的地方。顽固地坚持要家人为她准备成分复杂的特殊食物。”[9]16在父权系统主导的封闭空间内,海斯特处于被压抑的边缘地位,被剥夺话语权,陷入自我封闭的牢笼。菲尔德教师是唯一一个呵护爱惜海斯特,给予她温情的人,是海斯特在父权管制与压抑中的情感寄托,然而连这唯一的朋友都被父亲霸占,海斯特目睹着菲尔德浸染在鲜血中,却无能为力,只能呆愣地回到房间“拉开毯子,用毯子包住了自己的头”[9]145。海斯特作为空间内边缘化的存在,根本无法挑战中心话语,只能麻木自我意识,屈从于父系权威,空间也由此变成了一个权力运作场所。
海斯特禁锢在父权空间中,只有牺牲自己的女性特质,才能获得某种平衡。她学父亲的样子“用一条金链子把所有的钥匙串起来挂在脖子上……钥匙并不是用做装饰的,而是一种安全感……她从不佩戴戒指或其他首饰,只戴着钥匙”[9]8。而且不同于一般的女性形象,海斯特柱着根丑陋的拐杖,衣着打扮偏男性化,经营农场时意志坚定、精明能干,行事思维都充满了男性色彩。边缘人物在面对强势话语时,不得不压抑真实自我,来换取社会中心的接纳,这种性别角色的无意识模仿是边缘人物面对异质压迫而自发产生的防御机制。而对男性气概的模仿实际上进一步封锁了她自己真实的情感诉求,内在地加剧了海斯特边缘化的“他者”身份。
边缘人物的情感封锁是迫于主流话语的压制,而流通开放的空间恰恰能暂时消解中心话语的权力压制,使得边缘人物得以在此释放情感渴望。格罗斯曼太太的小商铺正是这样一个流动性空间,个体与群体在此产生交互,这是海斯特联结外部世界的通道。每次她来此采购,格罗斯曼太太都对她十分殷勤,放下其他顾客,先招呼海斯特小姐,当她离开时,他们夫妇会恭敬地立在街上,目送她离开。海斯特在这个流通空间内感受到他人的尊敬,得到了在家庭空间无法获得的慰藉与温暖。在熟悉安宁的环境中,个体更易放下防备,回归内心的感性多情,此时出现的孤儿凯瑟琳便一瞬间唤起海斯特的怜爱,唤醒了她的女性意识,在情感上与之产生互动。她欣喜地将凯瑟琳带回家,教她弹琴,一起跳舞,纵情欢乐——凯瑟琳填补了海斯特压抑多年的情感缺口。边缘人物由于社会规范和外在权威的限制,会刻意隐藏自我非正常的感情,但是他们并非一定如同外表一样冷漠怪异,边缘群体也十分渴望外部亲密关系,释放情感需求。乔利正是借助商铺的流通空间表达边缘人物隐秘的情感诉求,从空间的维度深入海斯特边缘化的情感世界。
哈伯先生去世后,海斯特和凯瑟琳移居到农场最边远角落的草屋,这标志着边缘女性暂时摆脱了男权系统的压制,进入重生空间。空间不仅仅是一个文本的容器,更蕴含着某种意义,传达着情感和价值判断[8]。位于角落的草屋是整个社会的边缘空间,映射出了主人公们边缘化的个体身份。一个是跛腿的老处女,一个是困苦无依的孤儿,两个被世界遗忘的人在草屋内相依为命,草屋周围“到处都是一片荒凉、光秃秃的,丑陋难看”[9]30。置身于这样一个贫瘠、破败、陌生的环境中,她们却感到一种私密感和安全感,“一回到这里,海斯特就觉得绝对安全,就好像在这块地方,没有什么能伤害到她。”[9]68因为“在相对独立的世界中,那些犯有自我强迫症、缺乏自信的边缘人物可以创造一个能释放自我欲望而不被中心惩罚的安全空间,这些错位的场所就是他们恣意释放潜藏欲望的庇护所[10]。她们兴奋地规划未来,“想象着用色彩艳丽的花丛和迷人的绿草筑成花园的城墙……院子里还养着长脚的公鸡,胖胖的猫咪。”[9]31没有了父权的桎梏,女性开始从话语边缘走向话语中心,从禁锢空间转移到重生空间。
然而这个看似自由的空间,却充斥着隐性的权力,人与人的等级关系建立在金钱之上,凯瑟琳属于从属地位,经济上依附于海斯特。海斯特在这个边缘的物理空间内又建立了类似于父权社会的模式来控制凯瑟琳,她阻止凯瑟琳与外界交流,所有的信件都由她过目,言语上威胁她,对她施加压力。意图摆脱传统男权桎梏的海斯特又无意识中成为施加父权压迫的一员,在自己的重生空间内压抑弱小的女性。海斯特与凯瑟琳之间的关系在权力失衡中逐渐走向崩溃,凯瑟琳最后甚至尖叫着说我恨你,海斯特最终也无法在这段特殊感情中完成主体身份的建构。
空间确认着自我的存在,物理空间的挪移对应着人物主体身份的转换。从古老庄园到路边商铺再到农场草屋,海斯特从中心走向边缘,试图在空间的移位中确立自己的身份。然而由于长期处于父权话语的边缘,情感诉求被忽略,海斯特陷入心理偏执与异化中,企图通过控制凯瑟琳以释放自己在社会边缘的压抑或与挫败感。而无论是在父权压制下的奢华庄园,还是在自由掌控中的简陋草屋,海斯特都无法认识自我,找寻到确定身份。因而,乔利构建多重物理空间,在不同空间的相互连结中完整再现了海斯特边缘化的生存状态以及心理异化。
2.文本形式空间
“叙事学中的文本空间常常呈现为打断时间流的‘描述’,或者作为情节静态背景的‘布景’,或者叙事事件在时间中展开的‘场景’”[11]。也就是说,文本叙事的时间功能在弱化,多线索的空间结构在强化。立体交叉的复调叙事手法将文本从有限的时空内解放出来,叙事视角转变更加灵活,也更能体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
伊丽莎白·乔利在《井》中便有意地违背传统的线性叙述,通过情节的破碎化、叙事的断裂跳跃、叙事元素的并置以及叙事脉络的迷宫化等空间化的叙事技巧构建立体的文本形式空间。“空间性语言和叙事手法的使用不仅可以隐喻外在压迫还可以将人物内在心理具体化”[12],乔利正是借助多维的叙事空间揭露了边缘人物的心理恐惧与自我迷失。
乔利通过情节的碎片化来表现边缘人物内心隐秘的焦虑与安全感的缺失。小说开端就是一个情节的碎片,只有随意的一个对话,“‘你给我带什么回来了?’……‘我带来了凯瑟琳,不过她是我的。’”[9]11没有情节,也没有因果,就如同碎片般零星分散,让人产生破碎感和不确定性。海斯特在父权文化中是从属的、边缘的,她无法颠覆中心话语,只能通过模糊的对话表达隐秘的心理,空间的碎片投射出海斯特对情感的渴求,意图摆脱强势话语,建构一个自己主宰的小社会。乔利借助频繁穿插、多次重复的叙事方式阻断情节发展线索,使其变得更加零散无序。各部分故事片段之间的跳转毫无铺垫,情节被随意放置,成为一堆混乱的碎片,乔利在情节的碎片中呈现出边缘人物的孤独感与焦虑感。海斯特在背离人群中获得精神的归属感,却也时刻恐惧着外部话语的侵入,担心自己失去在边缘空间内获得的主导权,因此陷入内心的矛盾焦虑中。
同时乔利还有意地割裂情节,使整个文本叙事在回忆、想象、现实中间不断跳跃。在开篇的对话以后,没有任何过渡,画面直接跳转到海斯特和凯瑟琳驱车回家的情景,物理时间在此断裂,文本停顿,产生叙事空白。她们在归家途中发生了车祸,撞倒了路人,但乔利未交代如何处理尸体便中断原有的故事情节,而将笔触聚焦到海斯特初次见到凯瑟琳的场景。叙事的扭曲混乱对应着边缘人的内心焦虑与精神错位,海斯特在与世隔绝的农舍中贪婪地独享着凯瑟琳的爱,而乔安娜的即将来访无疑会扰乱这个私密的小空间,甚至夺走凯瑟琳。边缘人群对于外界的闯入十分敏感,他们害怕失去自我掌控的安全空间,因而产生心理恐惧,这种矛盾、焦虑的边缘意识体现在文本内就是叙事结构的零散与混乱。
乔利在《井》中多次运用了并置的现代创作技巧来搭建小说的空间结构,在文本中并列设置多重线索与暗示,在前后参照中突出立体化的整体叙事。“并置是在文本中并列地置放那些游离于叙述过程之外的各种意象和暗示、象征和联系,使它们在文本中取得连续的参照与前后参照,从而结成一个整体。”[13]乔利在《井》中扭曲时间的流动性将文本加工成多维并置的空间,主体的外部叙事以海斯特和凯瑟琳的共同生活为主线,内部叙事辅线并置了凯瑟琳在修道院的故事、海斯特的生长经历,生活在同一物理空间的人物以不同的生活经历组成两条并置的空间辅线。内叙事辅线又包含着更小的叙述单元:凯瑟琳与乔安娜过于热烈的“友情”、乔安娜入狱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原因、菲尔德教师与父亲的婚外情、凯瑟琳将井底死尸视为爱人。每一个叙事单元都充斥着边缘的疏离感,凯瑟琳对异性之爱的自然情感被压抑,菲尔德教师无法掌控身体的所有权。各个小的叙事单元相互独立,又彼此连结,并置在同一个大的意义单元内,展现了不同人物被排挤到社会空间的边缘,无法确立自我主体性后遭受的压抑与异化。小说从传统的叙事模式中解脱出来而趋向共时性与并列性,呈现出一副共时交叉融合的边缘人心理图景。
《井》的叙事脉络十分模糊,像迷宫般让人捉摸不透。乔利使用意识流将时间分裂扭曲,从连续的、不合逻辑的思维跳动中窥探主人公内心的挣扎与分裂。意识流的特征是往往因为某件事、某个场景而引发人物的零散无序的意识活动。小说中海斯特将死尸抛下枯井,独自一人驱车赶去买绳索时,无数记忆与想象一涌而上。她回忆起凯瑟琳神情紧张地打扫房间,又跳转到以前她生病时两人之间俏皮可爱的对话,想象着凯瑟琳独自在家的无助与害怕,又想到院子里养的那群大鹅,忽然头脑中又出现凯瑟琳一个人站在井边竖耳倾听的画面。“不,不,不要去井边!正在开车的海斯特被自己吓了一跳。”[9]11海斯特陷入心理意识的错乱中,无法保持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知。这些互不关联的意识碎片映射出了主人公内心的分裂与混乱,展现出边缘人内心的冲突。海斯特是个跛脚的老处女,性取向模糊,位于社会的边缘,她将凯瑟琳当作情感的寄托,试图以自己的所拥有的权力、金钱、地位将凯瑟琳留在身边,而凯瑟琳对异性情欲的追求及对她的若即若离使她陷入心理的崩溃,车祸事件更是将表面的和谐撕碎,暴露出两人关系的裂隙,这让竭力维护两人情感的海斯特备受打击,陷入精神的错乱,无法分清现实与幻境。文本在内部自我与外部自我的叠加中展现出乔利从边缘走向自我分裂。乔利有意模糊叙事脉络,使整部小说显得杂乱残缺,从中投射出人物多个分裂的自我,表现出人物位于社会边缘的孤独或分裂感。
3.读者的心理空间
读者构建心理空间的过程就是“建构和更新大脑中的认知模式的过程”[14]。“读者在阅读过程将个人经历、情感与文本内容进行动态整合”[15],由此构建一个具有增补性的心理空间网络。伊丽莎白·乔利在《井》中运用了后现代的碎片化叙述,并不断地跳跃叙事的焦点,有意地延长读者的审美时间,并通过文本留白、意象的重叠来引导读者阅读,帮助读者在心理空间内构建对边缘人物的整体感知。
在小说中,乔利通过多处的文本空白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的阐释,利用省略、结局的开放性为读者提供了多角度的阐释空间。小说刻意省略了多处情节,造成意义的断裂,产生一种不确定感:凯瑟琳在孤儿院到底经历了什么?乔安娜到底会不会来访?车子撞到的到底是人还是袋鼠?井底的男人是死是生?凯瑟琳到底有没有偷钱?小说结尾又提到海斯特在构思一部小说,是否这又只是她虚构的故事?这些相关的叙述都被作者刻意隐藏起来,由此产生一种意义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应着人物在社会边缘的迷失与困惑,寻求不到一个确定的身份。海斯特拥有地位、金钱和身份,却因为跛脚的生理缺陷和模糊的性取向被流放到社会边缘;凯瑟琳年轻漂亮却身无分文、居无定所,只能依靠讨好海斯特保证基本的生活。她们都是主流社会的他者,游走在话语中心之外,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折射出她们对自我的怀疑和强烈的身份困惑。乔利通过文本空白引导读者自主填补缺失的信息,促使他们借助自己的认知结构构筑网状的心理空间,深入全面地感受主人公们的边缘身份。
除了使用文本留白与读者互动外,作者还利用特定意象的反复出现,帮助读者编织起立体的空间之网,形成对人物边缘处境的整体感知。首先,书名的设置便向读者提示了重要的意象——井。井本该是一个地下连通的空间,然而文中的井却是口干涸的枯井,读者会发现井就暗示着主人公们闭塞的、边缘化的现实处境,是人物边缘身份的空间表征。海斯特与凯瑟琳的亲密关系始于井也毁于井,初次到草屋的两人在院落里发现了这口枯井,“石块堆积的井沿高出地面很多,可以让人舒适地坐上去歇歇脚。”[9]46两人也忍不住坐在上面沐浴阳光,井沿带来一种放松舒适之感,在全知的外视角下聚焦井的整体印象,读者在阅读时,会跟随外视角的叙述而在认知系统里构建一个基础空间,承载着即将开启的美好生活之梦。井再次出现便是她们移居小屋后,凯瑟琳想象着井底有一个王子,从外视角切换为人物的感知本身,读者会跟随着凯瑟琳的视角透视她的心理活动,以此为支撑点在头脑中又重新建构认知空间,即枯井承载了她内心对异性之爱的渴求,这与后文凯瑟琳对死男人的痴恋构成参照,读者在意象的引导下拼接叙事线索,构建事件的全貌,从中感受到凯瑟琳被强制压抑的情感。而当海斯特把尸体投井后,井所承载的美好记忆便荡然无存,两人间的信任也随之消逝,此时海斯特眼中的井洞口黑乎乎的,让人看着后怕,海斯特把井口封死,以图扼杀凯瑟琳的异性之爱,实现对她的完全控制。读者跟随着海斯特对井的感知生成新的认知模式,逐渐掌握海斯特边缘性的复杂人格:既渴望柔软的同性之爱,又在强烈的掌控欲中陷入专制与冷漠。读者在特定意象的重复中不断更新认知模式,在跨空间的不断交互中得到一个动态的心理整合空间,这种鲜明的空间感引领着读者跟随人物的心理轨迹构建对边缘群体的整体感知,在心理空间的不断构建与调整中深入感受海斯特的边缘性人格。
四、结 语
伊丽莎白·乔利在《井》的创作中突破传统的线性叙事,大量运用空间元素,在情节描述上,不再单纯依靠时间上的因果联系,而是设计片段之间相互融合、渗透、交叉,利用语言结构编织出立体的空间之网,这种后现代的空间结构能够深入边缘人物的内心,全面展现边缘群体的生存状态。乔利利用物理空间的转变揭示人物边缘化的生存处境以及心理异化;运用多种空间叙事技巧建构立体的文本形式空间,在情节的碎片中和结构的无序中投射出边缘人物内心的分裂与混乱;更利用文本留白和意象的重复来构建读者的心理空间,了解边缘人物的矛盾人格。 作者利用空间叙事将内容和形式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文学作品呈现出绘画造型艺术的空间感,不仅创新了文本建构模式更通过空间性的绘制全面地展现了边缘人的心理图景,加深了人们对边缘群体的了解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