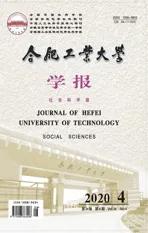论《苹果树》中阿瑟斯特的自我认同选择
2020-01-07刘蓉
刘 蓉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州 350007)
约翰·高尔斯华绥 (John Galsworthy,1867-1933) 是20 世纪初期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鉴于其“描述的卓越艺术”,瑞典皇家学院于1932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共创作了17部小说、26个剧本,还有散文、诗歌和书信集,是“爱德华时代三巨头”之一。“在我国,虽然高氏的很多作品都已被译介过来,但相比其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关方面的研究却进展缓慢,近二十年来发表的论文大多聚焦于《有产者》和《福尔赛世家》中所体现的‘物质’意识,以及对于其作品的‘现实’与‘现代’主义写作手法之争。高尔斯华绥的传记作者杜德利·巴尔克认为,高氏作品最大的魅力在于他‘用温和的笔调触及到了人们对社会最为本质的不满’”[1]。然而,高氏的艺术成就除其长篇世家小说及其戏剧作品之外,其短篇小说的成就也值得关注,因为他对短篇小说这一形式非常重视,他曾说过,篇幅长的短篇小说是“所有小说形式中最好的形式之一……使用这种形式,作家……最接近于诗人、画家、音乐家[2]3。
创作于1916年的短篇小说《苹果树》以回肠荡气的抒情笔触与细腻真切的心理刻画,讲述了一个始乱终弃的老故事:青年大学生阿瑟斯特在旅行中遇到天真纯朴的农村姑娘梅根,因彼此爱慕,随即在苹果树下定情。后因偶遇来自同一阶层的文雅漂亮的斯特拉,阿瑟斯特在经历多次的心理挣扎后将梅根抛弃,而没有实现所憧憬的爱情的梅根伤心而神乱,最后殉情。阿瑟斯特在时隔多年后得知而抱憾不已。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殉情的老套故事,却在叙述的前后都穿插了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塞浦路斯女神作为本能欲望力量的参照背景,在阿瑟斯特备煎熬的选择中,优雅理智的斯特拉——被喻为罗马神话中的月亮与狩猎女神狄安娜,给阿瑟斯特战胜爱神欲望的力量。基于这样的一个互文叙述基础,本文以小说中的“爱神”与“狩猎女神”的隐射为分析对象,运用快感美学概念,解释阿瑟斯特的爱情选择实际上是自我认同的选择路径,现代人在启蒙理性驯化人类本能欲望时表现出来的社会身份归属意识和个体道德自律倾向。
一、爱神与“快感”
小说《苹果树》开头引用古希腊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中的语句:“那苹果树啊,那歌声,那黄金。”[2]1不仅点题,而且引出了希波吕托斯(Hippolytus)的故事。在此悲剧中,希腊神话中的爱神与狩猎女神的个性特点以及二者的力量较量又成为小说《苹果树》的背景。希波吕托斯是雅典国王忒修斯的儿子,追逐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为能够与女神有非凡交往而自豪,拒绝与其他女性交往,藐视爱神阿弗洛狄忒(Aphrodite)。这使爱神十分恼怒,于是她让希波吕托斯的继母费德尔疯狂地爱上他,而费德尔被拒蒙羞自杀,留下遗书诬陷希波吕托斯对她不轨。忒修斯看到遗书气急败坏,放逐希波吕托斯,并用海神的诅咒处死了他。
爱神阿弗洛狄忒意味着“爱”“爱的快乐”。福柯在研究古希腊人的性观念时发现名词化的希腊形容词“ta aphrodisia”算是涵盖一切类似于爱的事物、爱的快感以及性关系等整体重组起来的概念[3]307。由于爱神的活动与人的“快感”所产生的吸引力及其欲望力量是一个统一体,于是“快感”一词便成为一个与性、爱、爱神及其活动与事物相关的综合性表述,它基于肉体,以快感为中心,具有较大的指涉范围。
爱神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代表着最自然的生存力和控制力。小说的结尾再次引用《希波吕托斯》里的话,“爱神的心疯狂,爱神的翅膀闪烁金光;在他造设的春天里,万物都似醉似迷……是啊,还有人类;统治万物的/是你,爱神,塞浦路斯人!”[2]105在万物生发的春天,万物(包括人类)都在爱神的掌握之中,甚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一种忘我的地步。爱神的巨大影响力不仅存留在借神话而虚构的古希腊戏剧中,也会世世代代地影响被称为“人类”的现代人们。
小说以回忆的叙述形式,描述了在二十六年前的五月,年轻的阿瑟斯特和他的朋友加顿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农村徒步旅行的情形。春天与荒野一般的农村,象征着自由而无拘无束的自然力量,使得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具有无限的想象和勇气。借加顿之口,情感“怜悯”和“快活”之间的对立关系得以讨论,这对情感的胶着关系关乎一种自我意识的良知与自律性。“怜悯无非是随着自我意识而来的产物;这是近五千年来的一种病。没有它,世界要快活得多。……让我们返璞归真,不再为任何人感伤,生活得更快活些吧。”[2]7加顿竭力主张要抛弃良知以获得快乐。接着,加顿还肯定了对感情的不加约束是成长的必然。“一个人要充分发展成长就不能谨小慎微。在感情上忍饥挨饿是个错误。任何感情都是有益的——它使生活丰富多彩。”[2]7加顿的这些浪漫放纵的想法,并未得到阿瑟斯特的认可,他认为,怜悯是人类五千年来文明中“蚌壳里的珍珠”,而立马抛弃它,却“永远也做不到”。至于“谨小慎微”的态度是对感情的自我约束,是成长中的道德自律。抛弃它,难免会“违反骑士精神”。
然而,阿瑟斯特对浪漫放纵的警惕心却在英格兰西南部偏远的乡村,在苹果花开的春天,在漂亮的乡间姑娘梅根的友善护理和爱慕中消散了。他欣赏梅根的美就像欣赏一朵盛开的鲜花,幻想着一种献殷勤的冲动。在乔纠缠梅根时他像骑士一般挺身而出之后,便于深夜和梅根相约在苹果树下,互诉衷肠,想得到梅根的本能欲望在微弱的理性对抗中占据了上风。这样,阿瑟斯特和梅根都成为爱神的俘虏。然而这种令他们陶醉的快乐持续不长,因为阿瑟斯特必须思考如何要像一个骑士一样安置梅根的现实问题。
在和哈利迪兄妹相处的日子里,阿瑟斯特更是备受本能欲望与理性克制的对抗煎熬。“他又一次想要她,想要她的亲吻,她柔软娇小的身体,她不顾一切的爱情,她的全部急切、热烈、异教徒式的情感;想要那天晚上月亮照耀的苹果树下那奇妙的感觉”[2]89。这时的梅根已经被描述为爱欲的化身,充满了诱惑。慢慢地,这种被诱惑又转化为怜悯,使得心存良知的阿瑟斯特因为要去欺骗一个未成年的农家少女私奔而怀疑自己的品德。“她仰望的脸,她惘然若失的脸和哀求的眼睛,乌黑的湿头发——这一切萦绕着他,折磨着他,使他失魂落魄。”[2]91不管是爱欲还是怜悯,这些情感都成为阿瑟斯特自我批判的对象。
阿瑟斯特的这种自我批判的叙述压力,可以从快感美学概念的梳理中找到答案。大众文化中的“快感”研究一方面沿袭了古典美学的审美知识体系,把生理性的快感剔除,留下作为审美对象的快感;另一方面,在福柯的权力话语体系中,“快感”又成为权力争夺的运作场所。“快感是权力规训技术所面对的重点区域。要驯服、控制与规范快感,首先要做的是使权力本身审美化,以便让权力进入到人的经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之中;其次是给予人的社会关系及交往方式以审美化的外表,体现为整个社会在追求其共同精神目标时的无功利形式,这实际是审美实践的权力化;最后,经由审美,权力最终在人们心灵深处建立起一种极为有效的政治霸权形式,启蒙理性因而体现出其合乎人性需求的力量来。”[3]因此,“快感”在美学建构中从先前古希腊的合人性与目的的地位转变为美学的理性规训中的权力运作场。要想使快感能够持续存在,就要对它进行有效的控制,使之进入到一个与个体道德及普遍理性密切相关的领域,从而使得它具有道德与理性内涵的审美价值。
阿瑟斯特所受的教育来自快感审美以及社会关系被权力化的土壤,故他的理性不仅能够而且必须对自己的“本能欲望”进行现代批判,使之获得审美化的外表,获得道德上的合法性。首先对梅根的原始之爱被他想象为一种“骑士”去救助和保护梅根免受低俗的乔的纠缠的英雄行为。这就给自然的爱神穿上了一件道义的外衣。其次,他打算暂时离开农场去托基小镇取钱购物,为私奔计划冒险地迈出第一步,以期与梅根的同居符合社会可接受的边缘。那个曾经在希腊神话中具有毁灭性支配力量的爱欲女神就这样被现代理性审美降格为被囚禁的观赏物。
二、狩猎女神与“中性”气质
与希腊神话中爱神阿弗洛狄忒相对应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是日神的孪生姐姐,弓箭是她最主要的标志。她时常身穿兽皮的无袖短裙猎装,在仙女宁芙侍从的簇拥下,穿行于丛林中狩猎,是猎人们祭祀的女神。同时,她也是处女之神,象征着贞洁、克制与静穆。在《希波吕托斯》中,狩猎女神是爱神阿弗洛狄忒嫉妒的对象,因为她不仅拥有众多的追求者,也是一个不受情欲束缚的处女神。她在罗马神话中的对应者是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Diana)。
小说的另一个女主人公斯特拉的出场,就被定位为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狄安娜——“真像一位标准的狄安娜和她的侍从仙女们”[2]63。而且,哈利迪兄妹们的活跃而热切的谈话,以及妹妹们安详、优雅、自然流露的典雅风度令阿瑟斯特觉得特别,又觉得自然,使他觉得乡间的一切一下子变得遥远起来。他的注意力很自然地转移到她们身上。而斯特拉身上的这种气质对阿瑟斯特产生了一种不同于爱神的吸引力,原因就在于她具有一种亲切的、没有欲望诱惑的“克制”气质。
马尔库塞在分析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与社会关系时认为,像母子父女亲情、朋友之谊以及夫妇之爱这样的社会本能只有通过一种文化或体制的克制才能成为社会的冲动,而这一社会冲动为文明提供了大量的、共同的物质和思想财富的源泉。在这个意义上,“文明的主要领域都表现为得到升华的领域。而升华又意味着非性欲化。即便升华所依靠的乃是自我和本我中储藏的‘中性的可替换的能量’,这种中性的能量还是‘来自力比多的自恋储藏’,也就是说,它是一种非性欲化了的爱欲。”[4]依据马尔库塞的分析,这种“中性”气质是一种被升华过的冲动,即“非性欲化了的爱欲”,可以显现为文明中的合理情感,其升华的能量动力是“自我”和“本我”之间的一种可转换的协调机制。
在斯特拉身上体现了这种“中性”气质,它是一种非性欲化的爱欲,是一种升华的克制。在阿瑟斯特三番五次地想着梅根、想回到农场、拒绝和哈利迪兄妹同行时,斯特拉都以狄安娜女神的沉静模样出现在阿瑟斯特的眼前。“他蓦然意识到这另一位年轻姑娘沉静的目光正在仔细观察着他,他努力镇静下来。”[2]66一方面,阿瑟斯特不希望自己的内心秘密被洞穿,落个被耻笑的下场;另一方面,阿瑟斯特似乎被斯特拉的那份沉静与克制的优雅给提醒了过来,暂时摆脱了爱欲的纠缠,回归到理性的轨道。斯特拉不仅具有良好的克制品德与中性气质,同时也善解人意。当她感觉到阿瑟斯特的沉默时,便打开话匣子避免尴尬,又给人一种娴静纯洁之感。在了解阿瑟斯特不相信《圣经》时,斯特拉略有失望,但并没有妨碍她的沉静优雅。“她流畅地弹奏,但不流露多少感情;然而,她多像一幅画,那朦胧的金色光辉,某种安琪儿似的气氛——萦绕着她!在这位有着天使般美丽的脑袋、摇摆着身体的白衣姑娘身边,有谁会产生带有情欲的想法或者疯狂的欲念?”[2]82就在那个夜晚,阿瑟斯特开始怀疑自己对梅根之爱的真实性,开始否定对梅根的爱欲。
正是斯特拉的那种宗教一般的克制与理性的冷静,让阿瑟斯特感受到了内心的平静,打算“用她美好的、冷静的、姐妹般的光辉当作一件保护衣裹住自己”[2]86,去抵抗他对梅根的爱欲,也坚信斯特拉会因他抵制心中的魔鬼为他祝福。阿瑟斯特对斯特拉的这种依赖与信任源于以下两点:首先,斯特拉是以朋友的身份理解阿瑟斯特所经历的某种烦恼,却不窥探。这种友谊是一种爱欲升华后的中性情感,它借助宗教的约束和理性的分析来展示文明中可以接纳的合理情感,关心而非性欲化,亲切而有空间,从而使得被规训过的“快感”比原始爱欲更成熟、更稳定、更持久。其次,斯特拉作为“非性欲化了的爱欲”的载体,其情感本能通过文化或体制的克制成为一种具有“中性气质”共同的社会冲动,这一社会冲动升华后的普遍性为现代社会人提供了一种情感的协调机制,使个性欲望的表达既合理又得体,更利于社会关系的健康发展与稳定。就这样,在希腊神话的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或罗马神话中的狄安娜一改以往被追逐与被仰慕的客体形象,在现代社会成为完胜爱欲女神的理想主体,成为一个具有“中性”气质的理性象征而参与个人情感的协调与社会关系的良好构建。
三、关系网与自我认同
阿瑟斯特离开农场去托基小镇取钱购物,本是为着给他和梅根的爱选择一个可接纳的现实空间,为他和梅根的同居寻找一个可为社会所接受的边缘途径,却因为路上偶遇哈利迪兄妹而彻底改变了原来的打算。在与他们相处的几天里,阿瑟斯特经过几番心理斗争,最终产生了对爱欲的内心恐惧,痛苦思量后抛弃梅根,选择了斯特拉,再也没有回到农场。这种爱情选择表面看是本能欲望与理性的道德自觉之间的较量,实则也是阿瑟斯特作为一个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我认同的选择。
法国哲学家扎尔卡在《权力的形式》中指出,“自从我们从物理的个体过渡到人性的个性,我们就假定了一个认同过程的存在,这个过程只有在一个关系网中才能实现。……正是在关系网中,个体得以确认,因为它的存在联系到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涉及个体与家庭、工作或者社会上的他人的关系。”[5]一个独立的个体在一个社会关系网中总是不断肯定与自己相同或相似的价值,在否定与自己价值不相容的部分的选择中去实现自我认同,获得身份的独立。而这个选择的过程或者说是认同的过程必然涉及其家庭背景、工作环境以及社会上的关系网。
小说中对阿瑟斯特影响最大的社会关系网无疑是哈利迪一家。第一天和哈利迪兄妹在岩洞小池边玩耍的时候,阿瑟斯特一面想着要按时赶回农场见梅根,另一面却又担心他的内心秘密被洞穿。“如果他们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如果他们知道这天晚上他原来打算……唉,那他就会听到一声轻轻的表示厌恶的声音,他就会被孤独地留在山洞里。”[2]66阿瑟斯特的第一反应就是担心被他所处的阶层所抛弃。随着和哈利迪一家相处的日子越久,父母双亡而身为独子的阿瑟斯特更是被家庭亲情所吸引,甚至忘记了他在农场的那段初恋。“这两天来,他似乎被这种热烈的家庭亲密关系,这种强烈的哈利迪家庭气氛团团围住了,使得农场和梅根——甚至梅根——仿佛都不是真的了。”[2]83到最后,阿瑟斯特虽然对梅根恋恋不舍,但毫不怀疑自己的内心决定。“自从他遇见了哈利迪一家以后,他渐渐地越来越确信他不会和梅根结婚。这只能是一次疯狂的恋爱期,一段不得安宁的、带来悔恨的艰难时期。”[2]87阿瑟斯特这时坚信他如果和梅根扯上什么关系是不被社会所接纳的,只会让他因自己的欲望没有被文化与理性所约束而对自己悔恨不已。
此外,还有什么东西在同怜悯和狂热的渴望斗争,使得阿瑟斯特变得冷静无情,抛弃了梅根?除了哈利迪一家那种健康、幸福的英国家庭气氛,赶走了阿瑟斯特的初恋热情,“此外还有一种似乎像一座有围墙的古老英国式花园的气氛,花园里有石竹、矢车菊、玫瑰,还弥漫着薰衣草和丁香的芬芳——一种凉爽、美丽、洁净,几乎圣洁的气氛——这一切是他从小受的教养所认为是纯洁和美好的。”[2]90英国气氛与教养这个更大的社会背景支撑着阿瑟斯特遵循而不是背叛其所属阶层的选择:让他回到农庄,在一片荒野的环境中和梅根相爱,是绝对不行的;把梅根连根拔起关在伦敦的一间小房子里也是做不到的。这样的社会归属感就是阿瑟斯特对自我身份认同的选择心理。而且,来自同龄人的影响对于阿瑟斯特更具有关系网的水平参照特点。前有加顿的浪漫放纵与民族阶层优越感的言论,后有哈利迪的自我阶层认同的遇险感悟。对于前者,阿瑟斯特由最初的反驳与否定,变为实际行为的趋同,他的怜悯心并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强烈。而后者的遇险感悟使得阿瑟斯特彻底将梅根之爱剪除干净,以完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选择实践。哈利迪感到庆幸,对于一个曾经在剑桥可以到手的姑娘,“总算没有真让她占有我的心”[2]75。这种庆幸得到了阿瑟斯特的默认,这不仅是理性把本能欲望的“快感”推向被拆解与被审视处境的最好例证,也是自我认同过程中理性选择的隐蔽宣言。非理性时代,对于两情相悦的青年,相处的快感是自然的、合人性的。而在现代理性时代,“占有我的心”的表述将肉体的快乐与理智的内心独立分离开来。“总算”一词的情态说明,相较于单纯的肉体快感,让理智的内心和快感一同捆绑的行为更会遭到社会的嘲笑与唾弃。这样,理性将“快感”分解为肉体快乐与理智的二元对立。自然,一个沉溺于快感中的人,无异于一个存在于动物界的人,是无法取得其社会主体地位与身份的。为此,阿瑟斯特只有选择把对梅根的爱欲剥离开他的内心,他才能确立理性上的自我认同,获得其社会主体性。因此,阿瑟斯特的爱情或婚姻对象的选择表面看是本能欲望与理性自觉之间的较量,实则是阿瑟斯特对社会自我认同的选择。
总之,阿瑟斯特的选择,离不开“快感”在理性时代被驯服、控制这一文化背景,在古希腊人那里最初呈现出来的快感的力量感、合乎人性与其基础性的地位被美学理性逐步消解,使得脱离了理性约束的快感成为低下、淫荡或无耻的感受。同时,与梅根为爱殉情相对照的是,代表月亮与狩猎女神的斯特拉则体现了现代理性在驯化人类本能欲望时的宗教与理性共同作用的克制。她对阿瑟斯特的友谊,给予他们的社会关系及交往方式以审美化的外表,其对待感情也表现为追求共同精神目标时的中性气质。最后,阿瑟斯特在理性与社会关系网的影响下,逐步改变其感觉世界的基本内容、结构及其关系,脱离以快感为中心的、追求享乐的感官王国,进入到一个以理智、道德及其相关的权力规训所共同构建的理性世界,完成身份的自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