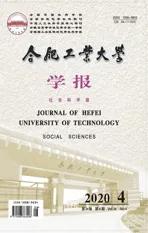船山诗学“远近之间”论的美学阐释
2020-01-07郭鹏飞
郭鹏飞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1]63是船山诗学的重要美学思想,“远近之间”形容的不仅仅是情景之间的距离关系,更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距离关系,情景交融之意象正建构于此之上。西方美学有审美距离说,认为审美活动中存在空间距离、时间距离与心理距离三种距离关系,并把心理距离作为距离的总的内涵,前两种距离关系都可以从中推演出来,以此来说明审美或艺术的经验特性。船山“远近之间”的诗学思想是判断一个作品是否具有艺术价值的重要标准,“他的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意图是通过具体的艺术作品例子来确立这个标准,把其中的艺术与非艺术、审美与非审美区别开来”[2]。两者共同的着眼点在于如何把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提炼成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审美经验。本文从审美距离说的角度对船山“远近之间”论进行美学阐释,把“远近之间”视为一种实现审美主客体统一的心理距离,阐发“远近之间”论所蕴含的当代美学价值。
一、“远近之间”:审美距离原则
中国古代审美文化思想中普遍存在着对审美距离的自觉体认。“近取诸身,远取诸物”[3]是中国古人观物取象的重要方式,审美空间距离之自觉由此而来。宗白华认为:“俯仰往还,远近取与,是中国哲人的观照法,也是诗人的观照法。而这观照法表现在我们的诗中画中,构成我们诗画中空间意识的特质。”[4]中国古人一方面有意识地缩短审美主客体之间的空间距离,在画论中有“可行、可望、可游、可居”之论,另一方面也自觉地保持着这种距离,主张对一些事物“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由此形成了“远近之间”的空间距离体认,所谓“摊烛作画,正如隔帘看月、隔水看花、意在远近之间,亦文章法也”[5]。中国古代诗歌中既有陶潜《咏荆轲》等述古之佳作,也有杜甫《北征》等以诗记事的“诗史”。更为常见的是《登幽州台歌》等大量吊古伤今的诗歌,它们无不是把对过去历史的思考和对现状的感慨统一于诗篇之中,形成了“远近之间”的时间距离的体认。
空间和时间距离的远近差异,会导致主体对客体产生不同的感受。我们对眼前熟悉的事物往往会倍感亲切,对看不清甚至看不见的事物则常常会觉得隔膜。同样,相较当下发生的事情,我们对过去的事情更容易做出理性的思考而不是感性的认知。布洛是西方审美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根据布洛的观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心理距离:
这距离就介于我们自身与我们的感受之间,这里使用感受这词儿是就其最广泛的意义上说的,指的是一切在身体上或精神上对我们发生影响的事物[6]94。
我们虽然可以通过调整再现空间距离来消除这种差异,使我们对远距离的事物也能产生亲切感,如“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7],“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8]。但再现空间和时间距离缩短的最终结果还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的缩短,空间和时间距离只是作为心理距离的特殊形式而存在。船山诗学“远近之间”论所强调的正是心理距离这一距离的总的内涵,请看船山所云:
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才着手便煞,一放手又飘忽去:如“物在人亡无见期”,捉煞了也;如宋人咏河豚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饶他有理,终是于河豚没交涉。“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含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1]63
戴鸿森先生将这种远近关系解释为一种诗意的情景关系:“写景逼真,宛然在目(近),而情味深长,引之使远;情意虽深,难可捕捉(远),而景象鲜明,拉之使近。”[1]65而正是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距离关系,将情感主体引入审美领域之内,建构起情景交融的意象,才产生了这种审美效果。布洛认为“说距离是介于我们自身和这些事物之间与说距离是我们的这些感受的源泉或媒介往往是同一个意思”[6]94,即心理距离的远近差异导致了我们对事物产生不同的感受,心理距离是审美活动开始的前提。“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指的是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的思维活动,理应是心理距离的不同导致了主体对事物产生了不同的感受。“物在人亡无见期”与“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都是心理距离丧失的结果。“物在人亡无见期”失之于“距离太近”,过近的距离使得诗人李颀完全沉浸在对旧人的思念之中,这种情感是纯粹的个人经验,不够超脱,脱口而出,显得过于急促。“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失之于“距离太远”,过远的距离使得主客体相分离,过于孤立。诗人完全按照客观规律对事物加以描写,所获的是对知识的认识而不是审美体验。因此这种纯客观描写即使完全符合大自然的客观规律,也会因脱离审美客体而无法进入主体的情感活动之中,最终被排除在审美活动之外。“远近之间”可以被视为在审美活动中必须要遵守的原则。首先我们要避免心理距离过近,要“外周物理”,从客观的角度对客体进行观照,要摆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现实利害关系。其次我们要避免心理距离过远,“内极才情”,客观的关照并不意味着主客体的决然分裂,审美活动必然有情感的投入,以区别于科学认识活动。只有做到以上两点,审美主体获得的情感才是提炼后的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
船山诗论中很多观点都可以看作是对“远近之间”审美原则的阐发与补充。船山在评谢灵运的五言古诗《游赤石头进帆海》时说:
人之海亦如是耳,心不为溟涬所摇,而幽情自适,方解操管长吟。比见登岳观海之作,惟恐不肖,而为恫精骇魄之语。使尔,则已目眩百疾,水浆不能入口,而何敢作诗邪?[9]241
船山之论与布洛所举海雾的例子十分相近,当人们沉浸在与客观事物的现实利害关系时,对大海或海雾只会产生紧张和恐惧。因为人们担心着自身的安危,所以“目眩百疾,水浆不能入口”。只有当我们与大海或海雾之间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利害关系被消解时,我们才能感受到大海的波澜壮阔和海雾的虚无缥缈,才能对客观事物产生美的感受,所谓“心不为溟涬所摇,而幽情自适,方解操管长吟”。王夫之认为谢诗比陶诗更加恬适,称“乃世人乐吟陶而不解吟谢,则以陶诗固有米盐气、帖括气,与流俗相入,而谢无也”[9]250,也是源于同样的道理。满足食欲以及争取功名都是一种现实利害关系,都会消解心理距离,损害诗歌的美感。同样,船山也不认同以诗言理和不投入主体情感的纯客观描写:
诗入理语惟西晋人为剧。理亦非能为西晋累,彼自累耳。诗源情,理原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不因自得,则花鸟禽鱼累情尤甚,不徒理也。取之广远,会之清至,出之修洁,理固不在花鸟禽鱼上邪[9]101
诗歌是用来抒发诗人内心真挚情感的,不是传教布道的工具。说理诗是心理距离过远的产物,与情感活动毫无关联。像“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这样的诗,虽然努力寻求一种概念的普遍化表达,却因为其抽象性,无法引发人们的共鸣。正如布洛所言:“它们面向一切的人,所以也就无法打动任何一个人。”[6]104心理距离过远虽然能让人们对事物进行静观,对事物做纯客观的描写,但这种描写即使再细致入微,也会因缺乏主体情感的概念化表达而仅仅被视为认识活动而不是审美活动,所谓“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1]157。我们不能把主客体截然分离开来,正如船山所言“诗源情,理原性,斯二者岂分辕反驾者哉”。只有符合“远近之间”的心理距离审美原则,情理方能相合,主客体才能统一起来。
二、“万物之情统于合”:距离内在矛盾的解决
布洛认为心理距离具有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的作用:
它有其否定的、抑制性的一面——摒弃了事物实际的一面,也摒弃了我们对待这些事物的实际态度——也有其肯定的一面——在距离的抑制作用所创造出来的新基础上将我们的经验予以精炼[6]95。
朱光潜先生将其概括为“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10]。“超脱”是对主体个人经验的超脱,“孤立”则是对个人经验的提炼和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的获取。我们独特的生活经验与体会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艺术作品、进行艺术创作,艺术作品所描绘的场景、表达的情感等和我们的个人经验越吻合,我们对其把握得越深。另一方面,这种高度吻合也会使我们分不清艺术与现实,把艺术看成自己现实生活经验与体会的一部分,不利于审美活动的开展,如观赏者因把舞台上的反面角色当成真正的坏人而对其进行殴打,诗人因陷入悲伤痛苦的情绪之中难以自拔而无法继续创作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将纯粹的个人经验加以提炼,获取具有普遍性但又能被我们切身体悟的个性化经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主体如何在超脱个人经验的同时对客观事物和艺术作品产生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呢?对艺术欣赏者而言,他一方面要从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挣脱出来,一方面又要用从现实生活中获取的常识与经验去观照艺术作品。同样,对艺术创作者而言,他一方面要抒发内心真挚的情感,一方面又不能陷入其中,要努力寻求客观化的表达。这便是布洛所说的“距离的内在矛盾”:
这种有人情但又有距离的关系(我将冒昧地把它称之为我们的视野的无名特性)把人的注意力导向一种奇异的事实,它乃是艺术中的许多重要谜团之一:我建议把它叫作“距离的内在矛盾”。[6]98
布洛希冀审美主体具有一种协调矛盾的素养,能够在矛盾双方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这一矛盾则在船山诗学思想中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解决。“以神理相取,在远近之间”的“理”既不是纯然的物理也不是纯然的伦理,而是天地万物共有之理,所谓“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1]129。诗人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也不纯然是诗人自己的感受,而是天地万物共有之情。在船山看来,纯粹的个人经验只是“意”和“欲”,不是“情”和“志”,所谓“意有公,欲有大,大欲通乎志,公意准乎情。但言意、则私而已;但言欲、则小而已”[11]。人情物理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船山有言为之证:
苏子瞻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体物之工,非“沃若”不足以言桑,非桑不足以当“沃若”,固也。然得物态,未得物理。“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乃穷物理。夭夭者,桃之稚者也。桃至拱把以上,则液流蠹结,花不容,叶不盛,实不蕃,小树弱枝,婀娜妍茂,为有加耳[1]17
船山之所以称赞“桃之夭夭,其叶蓁蓁”,“灼灼其华”,“有蕡其实”三句穷尽物理,是因为其没有停留在对事物外部形态的摹状上,而是把诗歌所要表达的情感与桃树的生长规律结合起来,以尚未成材“婀娜妍茂”的小桃树形容新婚女子,既形象地描摹出女子美好的姿态容貌,又寄托了人们对女子美好的祝愿,达到了人情物理的统一。我们作为欣赏者,如果仅纠结于桃树如何才能在尚未成材之时果实累累,只能得到“此诗夭夭、灼灼并言之,则是少而有华者”[12]这般自相矛盾的解释。只有像船山一样,“内极才情,外周物理”,才能感受到诗歌之美。
在船山诗学思想中,人情物理是内在统一于诗歌这一整体之中的。船山有言曰:“古人为诗者,原立于博通四达之途,以一性一情周人情物理之变而得其妙,是故学焉而所益者无涯也。”[13]从这个意义上讲,主体情感本身就具有个人经验之上的意义,客观物理本身也具有认识论之外的意义。“鸟兽草木并育不害,万物之情统于合矣”[13],这是“天人合一”的自然状态。心理距离的内在矛盾正是在这种统一中得到了解决。由于“情”、“志”对“意”、“欲”的自觉排斥,诗人与个人经验之间始终保持着距离,现实的欲望和要求得到了“净化”。又因为“理”为人情物理的统一,心理距离不至于过远,所以并不排斥诗人的情感。对于读者而言,大可用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的常识与经验把握诗歌,所谓“人情之游也无涯,而各以其情遇”[1]5、“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1]5。读者获得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体验,而是天地万物共有之情,具体表现为“兴观群怨”四情,“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窒”[1]5。值得注意的是,船山在获取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时,所实现的是一种主观的普遍性,而不是客观的普遍性,与康德“一个客观的普遍有效的判断也总是主观上的普遍有效的”[14]论断相近。在王夫之的诗学中,审美主体对外在事物的切身体验,即“身之所历,目之所见”[1]56,最终是要被纳入“心”中的,所谓“只于心目相取处得景得句”[15]117,“心”在“目”之前,外在体验最终要转化成为带有主观情感色彩的内心体验。审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表现为“身”与“心”的合一,从而获得一种主观的普遍性。因此王夫之强调:“元韵之机,兆在人心,流连泆宕,一出一入,均此情之哀乐,必永于言者也。”[1]1又因为“意”是“心”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的表现,所以船山诗学中又多次提到“以意为主”、“立主御宾”、“以主待宾”,“情”与“景”最终要统一到“心”和“意”之中去。
那么布洛所纠结的“距离的内在矛盾”何以在船山这里迎刃而解呢?船山诗学何以将主观上的普遍性真正实现呢?布洛提出心理距离的目的在于协调审美活动中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将主客体统一在情感理性之中,“距离与形式都不单纯强调主体一方或者客体一方,它们都注意于可分析的中介存在”[16]。因此布洛反对在审美思辨中使用“人情的”与“非人情的”,“主观的”与“客观的”这类非此即彼的词汇。他称:“它们并不是为了审美思辨的目的而创造的。因而一旦将它们使用于它们那特殊含义的范围之外时,它们的意义就会变得含混不清而模棱两可”[6]97。儒家强调“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17],把“生生之德”作为情感的来源,因此船山有“鸟兽草木并育之不害,万物之情统于合矣”之论。这种情感在人身上具体表现为仁,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18],情感既是个人体验的又具有普遍性形式,由此形成了一种情感理性。正如蒙培元先生所言:
按照儒家的天人之学,情感绝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个人的情绪反应之类,也不能仅仅被理解为纯粹主观的兴趣、爱好之类。人类最伟大最崇高的情感是仁,它既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活力,又是人生的目的追求[19]。
正是这种情感理性使我们在以自身的经验把握事物时,能够不仅仅满足于个人经验,去寻求更具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
三、“情中景”:距离极限
布洛在以审美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素养来解决“距离的内在矛盾”的同时,对距离的理想境界也进行了阐发。布洛称:“无论是在艺术欣赏的领域,还是在艺术生产之中,最受欢迎的境界乃是把距离最大限度地缩小,而又不至于使其消失的境界。”[6]100心理距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身具有易变性,“它不仅依照能够形成程度大小不同的距离的客体的性质而发生变化,而且还依据个人保持程度大小不同的距离的不同能力而有所变化”[6]101。布洛虽然把心理距离的变化归结于审美主体与客体两方面。但他主要探究的是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家和普通公众在素养上的差异,对不同艺术种类之间的差异探讨的较少。他认为:“在普通人的实践中,确实存在着一个极限,它表明在欣赏领域,这个人的欣赏力能以保持的最低界限,而这一般人的最低界限比起艺术家的‘距离极限’来要高得多。”[6]102由此可见,面对同一个对象,具有良好艺术素养的主体的“距离极限”更低,更容易达到理想距离的境界。布洛探讨距离问题时主要从戏剧、音乐、舞蹈、建筑中举例,而王夫之“远近之间”论则是围绕诗歌展开的。相对于前者对现实的“模仿”,后者因其“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特点而更具人情,在更容易感动我们的同时也更容易丧失距离,对诗人“距离极限”的要求也就更为苛刻。
船山有言曰:“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粹之迎,互藏其宅。”[1]34情景“互藏其宅”具体到诗歌之中,有“情中景”、“景中情”两种形式。在船山看来,“情中景”相较“景中情”更难实现:
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则有情中景,景中情。景中情者,如“长安一片月”,自然是孤栖忆远之情;“影静千官里”,自然是喜达行在之情。情中景尤难曲写,如“诗成珠玉在挥毫”,写出才人翰墨淋漓、自心欣赏之景。凡此类,知者遇之;非然,亦鹘突看过,作等闲语[1]72
状景状事易,自状其情难,知状情者,乃可许之绍古[20]10。
古今人能作景语者百不一二,景语难,情语尤难也[20]311。
“景中情”易于实现是因为在诗歌创作之初,诗人与外在事物就保持着较远的心理距离,诗人“触物起兴”,通过将情感投射到外在事物的方式把距离拉近,外在事物是显性存在,诗人的情感则是隐性存在,是谓“无我之境”。除非蕴含诗人情感的外在事物消解,否则距离永远存在。因为存在长安城和月的意象,“长安一片月”相较“物在人亡无见期”,能够不局限于诗人纯粹的个人情感体验,而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孤栖忆远之情”。“情中景”则要求诗人在抒发真挚情感的同时,能不流于鄙俗、“作等闲语”,用写景的方法曲折婉转地将情感表现在诗歌之中。诗人是从距离近乎丧失的条件下提炼自己的情感以产生距离,“景中情”中的景是已经存在的外在事物,“情中景”中的景则是从主体情感中生成的。由情产生的景是隐性存在,是要靠我们去体悟的,诗人的情感则始终是自然流露的显性存在,是谓“有我之境”。“景中情”中的距离理论上可以无限扩大,直至对事物的纯客观描写与抽象概念的表达。由于距离过远,我们无法从中获得具体的认识,我们只能根据个人的体验去理解,从而又会陷入距离过近的困境之中。因此归根到底,主体方面最终是因为距离过近而丧失欣赏力。在“情中景”情境之下,主体更加突显,心理距离也就更容易丧失。但正如布洛所言,艺术家的“距离极限”之所以更低,恰恰是因为艺术家对最富于个性的情感也能保持有足够的距离。在船山眼中,杜甫就是一个能达到这一理想境界的诗人:
情语能以转折为含蓄者,唯杜陵居胜,“清渭无情极,愁时独向东”,“柔舻轻鸥外,含凄觉汝贤”之类是也。此又与“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更进一格,益使风力遒上[1]95。
俗目或喜其近情,毕竟杜陵落处全不关近情与否,如此诗篇只是一雅[15]74。
每当近情处即抗引作浑然语,不使泛滥。熟吟《青青河畔草》,当知此作之雅。杜赠送五言能而有节者,唯此一律[15]75。
“近情”就是贴近常人的情感,陆机有“远节婴物浅,近情能不深”[21]之言,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纯粹的个人情感体验虽然易于引起情感共鸣,却因不具有普遍性而不够深刻,往往流于表面。杜诗却能够做到“虽近情而不俗”,在打动人的同时,不让情感过度泛滥以至于失去理智,能够把纯粹个人经验提炼为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在最大程度上缩短了心理距离,所谓“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1]12。由于艺术家与平常人在“距离极限”上的差异,一般人只能在杜诗中获取个人的情感体验,无法理解深层次的含义,所谓“俗目或喜其近情”。由此而言,“情中景”是挑战“距离极限”的尝试,是只有少数天才艺术家才能达到的理想距离境界。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的思想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并不局限于使客体摆脱人们实际利益和现实需要的审美无利害性。布洛企图在距离概念中实现理想与现实、感官与精神、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协调审美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重点探讨了情感在审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企图将审美活动中客观的态度与切身的情感统一起来。在布洛心中,心理距离是审美判断标准、艺术创作活动和审美能力的主要特征之一。船山诗学则围绕“远近之间”的“万物之情统于合”、“情中景”、“景中情”等论述形成了更多地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阐发心理距离存在的必要性的“远近之间”论,把心理距离视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原则,希望在心理距离中实现“情景合一”的主客观统一。受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这种统一更容易实现,“距离的内在矛盾”也就更容易解决。“距离的极限”的高低把艺术家和普通人区分开来,只有天才的诗人才能把最具个人的体验加工成具有普遍性的个性化经验,抒发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万物之情”。船山诗学“远近之间”论继承发展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主客交融的心理法则和“诗缘情”的审美中心论,发展了中国古代心理距离思想,相较西方的“心理距离说”既有理论上共通,也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质,丰富了中国古典文艺心理学的思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