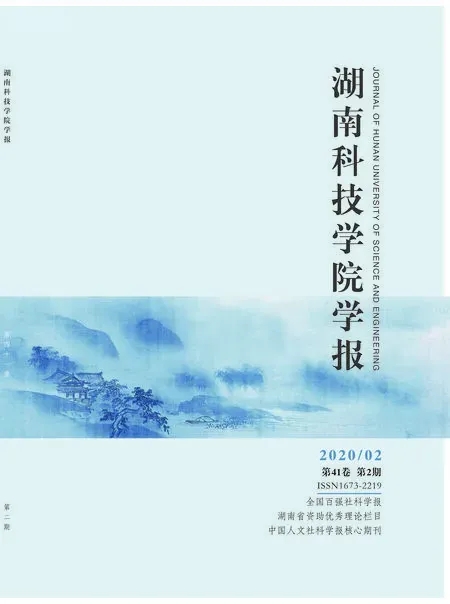论杨万里的传记与史传文学传统
2020-01-07骆云义
骆云义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传”本是解释“经”的文字。《春秋》是经,《左传》释经,二者都是史书。正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云:“传者,转也,转授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1]128-129《尚书》、《战国策》等史书也被刘勰论及,故“史传”的含意,原指对史书中的经典进行解释。后来司马迁《史记》将七十列传与八书、十表、十二本纪、三十世家并列,“列传”遂成为史传文学的主要代表。魏晋以后,文学自觉性更强,人物传记兴起,自我特色鲜明,与史传文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杨万里与范成大、陆游、尤袤合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讲求活法的“诚斋体”诗歌对后人影响较大。他不仅在诗歌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在四六和散体文方面也表现不俗。其中,他的传记善于刻画人物形象,关注现实,并且寓论断于其中,对史传文学的艺术手法与思想内容都有发展。本文所论杨万里的传记,是指以“传”为名的人物纪事或拟人纪事作品,主要涉及《张魏公传》《张左司传》《李侍郎传》《蒋彦回传》《李台州传》《刘国礼传》等篇目。
一 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
史传文学以人为中心,人的客观活动与主观意识构成了历史过程。史传文学的特质,就是把人置于天地万物的中心,写出来活生生的人,以具体的人物行动构成的事件情节所展示历史画面。[2]90杨万里的传记同样运用丰富的叙事手法描绘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展现了一段南宋偏安的历史,传达他们的意志与精神,体现他们独特的风貌。
首先,杨万里善于通过个性鲜明的语言描写来刻画人物形象。语言描写是表现人物最重要的手段,言从心出。《战国策》苏秦游说六国,范雎论远交近攻,辩论时紧紧抓住对方的心理,时而委婉柔和,时而锋芒外露,形象地表现了人物的智慧与个性。《冯谖客孟尝君》写冯谖的行为与语言,如“倚柱弹其剑,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复弹其铗,歌曰:‘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复弹其剑铗,歌曰:‘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3]98等等,都鲜明生动的反映了冯谖的自信与智慧,暗示其超越常人的能力。赵白生先生认为,“对话”作为传记文学虚拟形态之一,即技术性虚构,是传记中最吸引人的部分,也是显示传记家功力的部分。[4]76杨万里的传记也擅长语言描写。《张魏公传》中张浚盼望国家稳定,弥留之际以国事为家事嘱托后人:
以家事付两子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即死,不当归葬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后七日,呼其子 栻等于前,问:“国家得无弃郡乎?”且命作奏企致仕而薨。[5]1838
此段语言悲壮激越,震撼人心。张浚是主战派,朝廷曾因为他放弃过“弃地求和之议”。杨万里没有写张栻的应答,却意味深长,或是张栻不忍告知,读者不得而知。这里再一次强调张浚的强硬态度,将一个时刻挂念国家安危、誓死保卫国土的忠臣展现在历史画卷之中。杨万里在其《故少师张魏公挽词三章》中也重点突出了张浚的爱国爱民、忠诚志士之形象,他这样写道:“出昼民尤望,回军敌尚疑......心从画前到,身在《易》中行。忧国何缘寿?思亲岂欲生!”
张浚的儿子张栻是理学家,他实事求是,目光紧盯当下要解决的问题,以所学用于所难。《张左司传》中,宋孝宗曾问张栻“虏中事”。张栻坦然回答:“虏中之事,臣虽不知,然境内之事,则知之详矣。”接着他指出国家“道多水旱”“民贫日堪”“兵弱财匮”“官员诞谩”的问题。杨万里通过传主对国家内政的分析,刻画了脚踏实地、忠厚诚实的文官形象。李椿是一位深受张浚重视的将才。当时朝廷有“北讨之议”,李椿不认可这种看法,他以一连串的事实论证“虽得地,必不守,未可动也”,即“藩障不固,储备不非,将多而非才,病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论议未定,彼逸我劳。”此段语言体现了李椿善于分析形势的能力、谨小慎微的性格。后来他回到合淝,张浚已经带领军队出发,便上书言:“大将勇而无谋,愿授成筭,俾进退,毋损威重。”结果“后皆如椿言。”一个“皆”字,前后呼应,体现了李椿政治目光长远,智慧与胆略并重。
其次,杨万里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凸显人物性格特征。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记叙历史事件、描绘历史人物,是史传文学最常用的手法。《史记》中,矛盾冲突越是激烈,人物性格越是鲜明。刘邦赴鸿门宴,落座方位现局势之紧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伯亦舞剑,意在护沛公。樊哙瞋目入宴,局势方有缓解,气势陡然而下,刘邦得以出逃。场面由松到驰再到松,将项羽的“不忍之心”,范增的“恨铁不成钢”,刘邦的从容淡定,一一表现而来。
杨万里也通过重大的历史背景、艰难的生存环境来刻画人物,展现他们的品格。《李侍郎传》首段即言李椿丧父,侍奉后母南走,生活中满尝艰苦,为其成才不易埋下了伏笔。《张魏公传》中,张浚母亲去世,因为边境荡乱,他“与大臣义同休戚,不敢以居丧归蜀”。自古以来,“孝”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是立身之本。朱熹言:“臣之所贵者,忠也。父之所贵者,慈也。子之所贵者,孝也。”[6]13多事之秋,张浚不敢为母亲守孝,彰显了他一心为国的高贵品格。而他在不同历史环境下的流泪,以点带面,将南宋王朝的动荡状态展示了出来。“浚顿首泣谢”,是为感动,因高宗对他的信任,“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朕将有为,政如一飞冲天而无羽翼,卿为朕留”。朝廷动荡,苗傅、刘正炎作乱,“高宗退处睿圣宫”,因受知遇之恩,“浚恸哭”,奋力起兵讨贼,是为忠。遇张俊,见到与自己一样忠诚厚实之人,“握手泣语之”,苦等打败敌人之日;又遇一猛将,“世忠至,相对恸哭”,“世忠等搏战,大破之”,这才将乱臣贼子打败。“翌日,浚与颐浩等入见,伏地涕泣待罪。”仅仅是讨伐内部之人,就已经显得波澜壮阔,事情层层推进,主人公的情绪也逐步变化。这几段叙事,有温和之情,有悲壮之意,饱含对君上的忠心,对敌人的痛恨,将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起起伏伏的情感通过这一声声的哭泣传达了出来,使得传记文学色彩更加浓厚。杨万里对于张浚的军事失利也如实记载,在平和、严峻、激烈、艰难等环境之中,主人公的形象也越来越立体,他所拥有的品质如忠诚,爱才,热血,镇静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正如赵白生所说:“认识的全面性(史的要求)和艺术的完整性(文的指归)是传记的双翼。”[4]121
最后,杨万里长于细节描写,通过细节来展现人物人格。史传文学作品大量运用细节描写,深刻地把握了人物性格特征,挖掘出深层的历史内涵。《史记·张仪列传》写张仪到各国游说,被怀疑在楚国偷了相国的玉璧,被打了一顿。回到家中,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7]2279张仪既然能问话,就说明他的舌头还在,他却还要问舌头是否还在,看上去似乎很矛盾,其实不然。通过这一细节,可以看出游说之人把“说话”当做取得功名成就的工具,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从文学上说,重视细节描写是叙事文学成熟的标志,擅长细节描写是作家成熟的标志之一。从史学上说,丰富的细节与情节,说明作者所掌握的历史材料的深度和广度,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纵横驰骋的创作自由,表现出作者鲜明的个性特征,同时也说明作者已经将视角深入到一般史家所不屑或未加注意的实践之中,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本质,丰富了历史著作的内涵。[2]116《张魏公传》中有很多细节描写,以此来凸显传主的德高望重。如孝宗即位,起初与其他大臣谈起张浚,是“咨嗟叹息”;召见张浚,孝宗便“改容”;当张浚谈到“人主以务学为先”的道理之时,“上悚然”回应。而无论是高宗还是孝宗,每次召见大臣,都会问张浚的“动静饮食颜貌”,显示对张浚的重视。再如,两次侧面描写外敌对张浚的恐惧,“虏闻浚来,亦檄宿州之兵归”“虏亦俱”,以简单的语言从动作与心理方面描写敌人,突出了张浚的威望,内能教君,外能镇敌。《蒋彦回传》中,蒋彦回与黄庭坚偶然相识,后来“党禁密甚,士大夫有顾望心”,黄庭坚“宾客落而朋友缺”,只有蒋彦回仍然跟随黄庭坚,并为其收藏诗文字画。文中写传主优雅的生活“弃而归,市书数千卷,阁以藏之。筑囿,植花木,葺亭榭,以读书与其间”,这一细节描写,似乎与主题没有之间的联系,细细分析,一是写传主不愿走仕途之路,爱收藏书,有好学之心。二是写传主有天然之性,与自然亲密接触,不随波逐流,彰显独立人格。这两个方面与后文传主跟随黄庭坚、收藏其书画、不私自要其书紧密联系,并不是无用之文。
二 经世致用的思想内容
经世致用主要是指士大夫的学问必须作用于国事,是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体现,强调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以求达到国泰民安。史传文学的目的就是资政通治与借古鉴今,史传文学从产生之初就带有很鲜明的现实性与功利性。《尚书》反映了殷商至西周时代政治思想观念的演变;《春秋》微言大义,“以一字寓褒贬”;《左传》批判暴君,颂扬功臣。这些史书刻画人物、撰写事迹都是为君王治理国家服务的。《史记》以人为中心,记黄帝至汉武初年历史变幻、王朝更替,兼载礼乐制度、天文等各方面,以鉴当代后世。正如齐树楷云:“《史记》一书,综若千年之事,而审察其终始中间递嬗转化之迹,令人详观,而有以处之至当,则亦经之用矣。”[8]40
风雨飘摇的南宋时期,杨万里主张抵抗外敌、勤修内政、举贤任能。他的传记秉持实录的原则,面对现实,同传统史传文学作品一样,他将经世致用的思想贯穿传记之中,反映了一代士大夫的政治需求。《张魏公传》《张左司传》《李侍郎传》记名臣丰功伟业;《刘国礼传》记传主忠厚实在,治家有方;《李台州传》赞颂孝子之心;《蒋彦回传》写“士穷乃见节义”的主题;而另外两篇假传《豆卢子柔传》《敬侏儒传》,前者表达作者排佛思想,后者强调重视人才,不拘于外貌。赵白生先生曾说:“传记写作的三个主要动机是纪念、认同和排异。”“传记作者试图用文字为死者树立一座高耸入云的纪念碑,使死者的伟大来鼓起生者的勇气。”[4]122以上八篇传记都从不同方面将作者经世致用的思想表达了出来,传主所说即是作者所想,他对传主表现了深深的认同感,通过事迹的描写、人物的刻画以达到当世后世借鉴的目的。
张瑞君先生说,面对南宋偏安一隅的政治局面,有远见的政治家必然考虑两点:第一,求生存;第二求发展。求生存,就是能够保住南宋王朝。求发展,便是使这个王朝逐渐强大,进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9]324杨万里深入分析南宋政治形势,提出自己经世致用的政治见解。现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主张积极抵御外辱,取得国家生存的首要条件。他在《国势》指出“今也内无敦、峻、谯、卢之猖獗,外无刘、石之英雄,而独当一未亡之金虏”,然后引经据典以浩荡的气势力陈南宋的有利形势,指出屈辱求和的结果只能是像六国一样灭亡:
而又以全楚为家,吴越为宫,此楚庄、吴阖闾、子胥、种、蠡之所以强霸用武之国也;西控全蜀,南拥荆、襄,北据长、淮,此高帝、先主、孙仲谋杨行密之所以兴起之根本也;钜海限其东,而三江五湖缭其南北,此古之六朝所恃以为不拔而不可兼得者也......昔者秦之灭六国,非秦能灭六国也,六国实自灭也。不思久长之计,而苟一日之安,争先割地以求和于秦,地朝割而兵夕至。
张浚生于宋朝南渡之前,“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虏”,因此《张魏公传》全文围绕传主“誓不与虏俱存”的决心,描绘他“艰难危疑,人所畏避,则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动其心”的坚定意志,以巨大的篇幅展现其主战行为,而且反复强调,也不会令读者觉得繁杂。文中少有战争场面,多写议和派与主战派的矛盾,从侧面表现国家形势的严峻。如每见高宗,必“深言雠耻之大,反复再三,高宗未尝不改容流涕”。再如奸臣秦桧准备议和,张浚前后五次上书据理力争,以致于“武夫健将言浚者,必咨嗟叹息”,“每使至虏,虏主必问浚安在”。杨万里生于南渡之后,南宋偏安之势大体稳定,虽然他不是主战派,但他以长篇传记写张浚、张栻、李椿的英勇与魄力,传达他们的思想主张,这本身就表明了杨万里积极保卫国家、抵制外辱的信念。他多次在诗中表达了迎送金国使节的无奈与痛心,如《郡中上元灯减旧例三之二而又迎送使客》:“北使才归南使来,前船未送后舡催。元宵行乐年年事,儿女嗔人夜不回。”
其次,修明内政,使国家得以稳定发展。孝宗即位不久,便仓促北伐,由于准备不足,致使符离之败,张浚也因此病逝。随后孝宗摇摆于战、和之间,主意不定。此时,多数士大夫并不希望轻启战事,主张勤修内政,杨万里便是如此。《国势》篇云“是故为今之计,和不如战,战不如守。和则懈,战则力。故曰和不如战。战则殆,守则全,故曰战不如守。”《张左司传》中并没有对“战”与“和”等问题作过多议论,而是将论述的重心放在张栻内政业绩之上。他不厌其烦论述张栻“守”的思想,以大段的文字写孝宗与张栻的对话。如:张栻讲《诗·葛覃》,进说:“治生于敬畏,乱起于骄淫。使为国者每念稼穑之劳,而其后妃不忘织红之事,则心之不存者寡矣。周之先后勤俭如此,而其后世犹有休蚕织而为厉阶者。兴亡之效,如此可见。”因推广其事,上陈祖宗自家刑国之懿,下斥今日兴利扰民之害。
在这里,他以《诗经》为论据,主张以勤俭为本,注重农业生产,不可骄奢淫逸,像这样的描写,多次出现在文中。为了突出张栻的政治功绩,杨万里在史料的选择上颇为用心,多选择他任职地方所作出的成果,即梳理财政、消灭匪患、振兴乡学等。这些问题是南宋普遍存在的,因此杨万里的《张左司传》不仅仅只是为了纪念传主,也是为了使当时之人有所启发与借鉴。《李侍郎传》中,传主李椿政务方面多有实干,如让兵民杂耕,分田地给不同部队的军队,自收其利,切合民生凋敝、物资不足的现实状况。
最后,举贤任能,重视人才,高扬品格高尚之人。他在《上寿皇论天变地震书》中明确指出备人比备粮食、备士兵更重要。《张魏公传》里提到了张浚对人才的重视,且每次作战合理分配将士的任务:
命韩世钟据承楚,以图淮阳;命刘光世屯合肥,以招北军;命张俊练兵健康,进屯盱眙;命杨沂中领精兵为后翼,以佐俊;命岳飞进屯襄阳,以窥中原。
接下来的作战描写即是围绕这些将才来开展的,快节奏的战争趋势,描写每个部分的战况,体现了将才对战争全局的重要作用。《李侍郎传》亦是如此,杨万里将其奏议载入文中,论述“能人之臣”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天下国家,譬之一身,君为元首而在上,臣为支体而在下,故有腹心之臣,股肱之臣,手足爪牙之臣,耳目口舌之臣。”大臣各施其才,各尽其职,才是国家运转的根本。而假传《敬侏儒传》描绘了其貌不扬的“人”,即油灯,但他胸中有才识,亦有丞相敬他为上客,他献上《三足记》,认为抵御匈奴的策略便是“足兵、足食、足士”。这不能不说反射了现实,符合当时南宋形势特点。
三 对史传议论传统的发展
传记的议论功能主要源于史传文学。史官做史,尽力隐藏自己主观态度,使作品显得客观,但是却又不得不传达自己的态度。正如章太炎先生在《文史通义·传记》一章里说:“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脱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10]128为了调节两方面的矛盾,他们便开创了此类方法,结尾单列一段,或借他人之言评论,或直接说出自己见解,使得后人看待这些事实时,能够有所参考。
《左传》中常托君子对史事进行评论,间接表达自己对人物事件的认识。《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就是直接说出自己的见解,表明自己的态度。当叙述完项羽的一生,他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7]339
司马迁对项羽是充满的敬佩之意的,更有遗憾之感。
宋人好议论,各种文体都有所体现。韩兆琦先生认为“结合写人叙事发议论”是宋代“散传”主要的艺术特征。[11]3-4杨万里传记对史传议论功能有继承发展,一是传记中直接载入传主奏议论说,二是在篇幅中插入自己的看法,三是结尾评价人物。议论的功能使得传主事迹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意义,是恰当而充分的传达作者思想必不可少的途径。
首先,载入传主奏议对话。杨万里《张魏公传》《张左司传》《李侍郎传》等作品,虽叙一人之始终,然文中插入大量的对话,论说直指时政之弊,且直接将他们的奏议纳入文中。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说:“为政治家作传,第一要登载他的奏议同他的著作,第二,若是政治家同时又是文学家,而政论比文学重要,与其登他的文章,不如登他的政论。”[12]67录入奏议不仅符合传主的身份,也间接传达了杨万里的看法,如上文的经世致用思想,作者希望通过传主议论的文字为传记增添资政价值。
其次,在文中插入自己的看法,叙事者显性介入,阐发义理。这些传主多是士大夫,士风与国家政治的好坏有直接的联系,因此士人精神是杨万里传记讨论的重要话题,如《蒋彦回传》。《李台州传》述了孝子寻母之事,作者联系自己幼小丧母之经历,发出感叹:“予生八年,丧先夫人,终身饮恨。闻之,泣不能止,感而为之传”。《刘国礼传》尤其体现了讲述人在叙事中的重要作用。作品虽名“传”,但全文没有传主太多的事迹,更像是回忆性的散文,作者“现身”于作品中,处处对传主进行评价。传主的两次落泪是特色,一次因上司薛季宣病故,“每言及薛侯,国礼未尝不泣也。”紧接着,作者抒发议论:“夫世之相与,利焉而已矣。曰义彦者,非性焉则学,非学焉则伪。”一次是与杨万里离别,“及其别,国礼又泣。谓其泣伪乎?施之余则可,施之薛侯亦伪乎哉?”两次落泪皆可见国礼真性情,是“泣不可伪”也。刘国礼去世之后,作者落泪感慨国礼家风优良,妻妾和睦相处,从侧面彰显国礼的高尚品质,刻画其端正为人的形象。在回忆中缓缓而谈,作者充分利用传主的生平史料,在潜移默化中讲述人逐渐变成了主角,起到了组织叙事的作用,传主边缘化,成为作者传达理学的载体。
最后,在结尾表达自己的见解,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传主。杨万里传记评价传主字数的多少与正文的篇幅长短有关,《敬侏儒传》为一假传,全文精炼简洁,结尾字数亦不多,作者这样写道:
太史公曰:“公孙丞相开东阁以延贤俊,天下之土辐辏,而敬承登为上客,每至,则一坐皆起,亦可谓能不以貌取人矣……亦何以议公孙为哉!”
《李台州传》的结尾更是短小:
孔子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若李台州,生而不知失母,士而知求母。求母而不得,不得而不懈,遍天下之半,老而乃得之。”
以上两文,借太史公、孔子来评价传主,增强了文章的可信度与说服力,且强化了传主的形象,借圣人传达了记传人的情感与态度,一曰不以貌取人,要看内在品格;二曰孝乃是君子根本的品质。《张魏公传》《张左司传》《李侍郎传》三篇传记结尾评价都较长,或再次叙述传主生平大事,从各方面出发串联起完整的传主形象,如《张魏公传》。或以传主思想精神为主,如《张左司传》的结尾:“栻为人,坦荡明白,表里洞然,诣理精,信道笃,乐于闻过,勇于从义,奋厉明决,无毫发滞吝意......”从学识到品质精神,皆包含于议论之中。或以倒叙的手法,补充传主的事迹,如《李侍郎传》,对他的品格仅用“庄重简淡,佚嶷然不动,淡泊无欲,夷易平直,廉不异重,介不绝物,不比权贵”来描述,其他几段文字补充叙述其职守地方时的政策,这使得人物形象更加完整,也间接表达了杨万里的政治思想。
杨万里散文中,与传记相近的文体还有墓志铭、行状等,他的传记与这些作品相比,真实性更强,感情更为深挚浓厚,也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传主。杨万里写的墓志铭数量较大,但多受人委托而写,客套之词较多,少有真情流露。与杨万里同一时代的陆游,也有《姚平仲小传》《族叔父元焘传》与《陈氏老传》等传记,传主为社会底层人物,承载着资政理想。与杨万里《刘国礼传》《蒋彦回传》等短篇传记相同,陆游在其传记中,不以传主始终事件为发展线索,而是围绕传主某一特点进行扩展,散文化叙事明显。在二人的传记中,他们都将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感情体悟直接注入其间,传记的议论功能加强,其中所体现的思想内容贴近社会现实,有供当世借鉴之作用。
总之,作为儒学大家的杨万里,他的传记充分吸收史传文学的传统,继承史传文学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刻画出有个性的人物形象。杨万里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精神,在传记中酣畅淋漓表达经世致用的政治思想。在他的文体观念之中,传记的文章属性非常重要,“文以载道”的思想增强了他传记的议论功能,突破了史传文学囿于文体限制不能尽情发表议论的遗憾。除了继承传统的“史赞”,他更是在文中直接对事件、人物进行评论。作者主观意志的参与,使得史传文学中的人物描绘转变为人物塑造,作者以自己所知晓的事来刻画心目中的他人形象,传记更具个性色彩。当然,其中的史学价值并不因为个性色彩的增强而降低,在杨万里传记中,实录的原则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因而其传记多被元脱脱编写的《宋史》直接引用,有着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