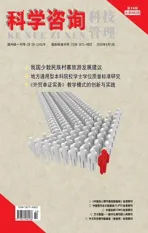从“碎片意象”探析本雅明的现代性思想
2020-01-07左晓晨
左晓晨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重庆 400044)
不同于齐美尔对现代性审美的关注,以及克拉考尔试图在历史和现实中还原现代性的本真面貌。碎片对于本雅明来说,更多地意味着是一种重构现代性理论的有效途径。弗里斯比指出,“本雅明后期著作受某种十分明确的意图激励,那就是发展一种现代性理论。”[1](p253)本雅明重构现代性理论的尝试体现在他的“拱廊街计划”之中,这一庞大的计划囊括了诸多社会领域,众多计划方案在政治、哲学、文学和个体关怀的语境中被不断重塑和建构。
阿多诺认为,碎片在本雅明那里仅仅是类似蒙太奇的简单堆积。但他没有意识到,本雅明作为一个“拾荒者”,在废墟之中捡拾碎片化的因素、垃圾,正是他揭示现代性史前史的必由之路。废墟概念的出现,明显受到费希尔“颓废的现代性宣言”的影响。作为费希尔忠实的拥趸者,本雅明对现代性的理解持有消极和批判的态度。他将十九世纪的巴黎看作是给人以迷幻梦境的“现代神话”,而揭开神话的面纱后呈现出的却是破败不堪的废墟世界,他的工作正是将废墟世界化约为碎片意象,并通过研究废墟中“辩证意向式”或“单子式”的客体碎片来指点迷津、解释现代性的含义。因此,对于本雅明来说,“是碎片为总体保留着通道,而不是总体投射于碎片”。[1](p256)
也许是因为致力于对波德莱尔的研究,本雅明有关现代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与波德莱尔是重合的,但又有相异之处。弗里斯比评价道,“本雅明乃是致力于研究现代经验的一个重要维度:那就是经验的极端不连续性,它植根于瞬息万变、短暂无常和偶然性,而且表现为由日新月异而带来的震惊或轰动。”[1](p346)本雅明对于碎片的关注明显受到了波德莱尔以及齐美尔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又提出了自己崭新的观测世界的方法。辩证意象、古今关系、巴黎城市、技术论证、商品消费等等新鲜元素,都在本雅明的研究里发挥巨大作用。
“现在关怀”与“过去比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本雅明关心的命题之一,“这种古代性与现代性的辩证,以及古代性存在于现代性本身之中的认同,已经赋予本雅明的现代性概念以独到的特征。”[1](p259)若将本雅明的“拱廊街计划”看作“现代性考古学”,那么现代性的起源和意义其实依附在十九世纪作为“当下实际时间的即刻实际存在”之中。换言之,即现代性的价值寓存于现在时刻、现在场域中的古代性因素。碎片在这种辩证的古今关系中凸显其价值,作为现在存在与古代记忆的连接纽扣,它在被人们感知的同时,又带领人们重返历史意象的深邃之处。本雅明认为,能通过碎片接近历史真实面貌的是城市中的“收藏家”和“考古学家”,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在繁杂的日常生活中剥除掩盖现代性碎片的迷乱幻象,并从这些零碎的素材中重新理解现实世界。
现代性的一大特征是时间研究转向空间研究,摒弃了传统宏大的时间叙事模式,现代大都市带给人们以支离破碎的散漫体验,这一感觉只有在空间中才能被察觉。像波德莱尔流连于波西米亚社区,齐美尔考察都市对人们精神生活的冲击以及克拉考尔对空间意象的专注,本雅明同样注重空间展露出的现代性带给人们的心理体验。本雅明以十九世纪的巴黎作为考察对象,以闲逛者、收藏家的姿态徘徊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不断收集、审视着散落于巴黎城市的各种碎片化意象。城市街道的迷宫、城市建筑物的遗址、大众、艺术品、赌徒、妓女以及商品世界中的林林总总都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他试图通过捡拾这些空间中不连续的瓦砾式碎片,予以其重新排列整合,从而捕获碎片之间共含、贯通的现代性含义,并在现代性的变迁中观测巴黎整座城市的历史性内涵,以期撼动这座沉睡的现代迷宫。“本雅明的起始点是超现实主义的‘世俗幻象’,超现实主义面对的是‘拼凑状态中的被曲解的世界’,是存在的真正现实主义面貌突破的世界。”[1](p309)作为现代性着落的巴黎世界,它不仅仅是考察现代性的空间集合,更是一个交织着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令所有人陷入集体梦幻的特殊场域。本雅明对巴黎这一现代性神话的态度是历史的、批判的。不论是研究拱廊街,还是巴黎城中其他的“梦幻屋宇”,本雅明所做的不是称颂,而是一种削减。正是在这种不断地贬损、刺激中,被麻痹的现代性史前史记忆才得以逐渐苏醒。换言之,本雅明所关心的“新奇与辩证同一”的现代性“瓦砾和碎片”,正是其提出的现代性史前史的起点。
诸如摄影术、照相机、电影、印刷品、广告牌等现代技术的标志物也在本雅明考察的碎片序列之中。弗里斯比指出,技术对本雅明而言,不能被化约为“自然的统治”,它属于纯粹历史变量的一部分。本雅明虽然对现代性持有批判态度,但他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拥抱者。他在肯定技术为人们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看到了现代性技术招致的弊端。这一思想体现在他关于艺术品的论述中,“在机械复制时代凋委的东西正是艺术作品的灵韵。”[2](p236),“如果能从灵韵的凋委这方面来理解当代感知手段的变化,我们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2](p237)新的技术改变了“感知物本身”以及“人类与物之间的关系”,本雅明正是在技术带来的改变中,看到了现代人与社会生活之间既迎合又对峙的紧张关系。技术作为现代性的碎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足够多的震惊体验。本雅明擅长放大、还原生活中这些被人们忽略的“最小物”,赋予散落碎片以新的意义,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技术成就令人惊跳和残酷的本质,从而在更替、变化的世界中捕捉现代性对大众日常生活冲击的蛛丝马迹。
本雅明在《中央公园》的一则笔记中详述了“游手好闲者”与“人群”的关系,他认为“游手好闲者”是受大众和生产商品化威胁的临时现象。在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生活本质及商品化生产削弱了消费者的个性,批量生产、倾销以及广告文化应运而生,商品对人们生活的殖民扩展至全部领域,在机械般精确的生活节奏里,人的价值被压榨和替换,由此产生了凌驾于人性之上的商品拜物教。本雅明将这些“商品的表达”视作窥视现代性的有效利器,他在商品中发现了“新奇”这一特征,而这一特征正是商品与现代性的之间共同的重要取向。“事实上,最新的感觉、最现代的东西就是那些像千篇一律的永恒轮回一样的众多事件的梦幻形式。”[1](p341)本雅明这段关于“新奇物的永恒轮回”的言论恰好揭示了现代性转瞬即逝、不会恒久但本质上永远同一的特点。在不断重复的溯流中,时间不再具有意义,一切历史都是当下,唯有“将过去从遗忘中拯救出来使我们能够从过去中读出现在”[1](p352),才能重返现代性史前史的古老记忆。
本雅明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建构是侵略性、革命性的。他对十九世纪西方社会盛行的工具理性持有明显的排斥态度,他企图通过中止人与社会之间精确计算的“关系”来达成自己的反叛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本雅明的现代性革命更多的不是前进和跃升,反倒更像是向人性本质的复归和回溯。从他对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认同能够看出,本雅明对现代性的挑战和不满态度。他认为达达主义用奇谲、怪异的文字和图片给麻木的都市大众带来犹如炮轰般的震惊体验,这是向传统理性秩序的有力挑战。同样,超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革命虚无主义”的思想,其离经叛道式的文艺美学观亦被本雅明当作拒绝现代社会的伟大力量加以运用,他期望在现代性的梦幻中觉醒世界。面对现代性的迷幻梦境,“本雅明没有选择保留在‘梦的园地’,而是在历史领域里通过‘摧毁神话’创造‘觉醒的星簇’。”[1](p282)原本断裂、不连续的碎片在本雅明的思想中被串连在一起,在弥赛亚时刻的感知里被救赎,并闪烁着现代性冷暗而耀眼的光芒。通过重拾现代性碎片,本雅明在现代工具理性的纷杂世界中,重新填补起十九世纪巴黎社会与现代性史前史之间的巨大裂痕,并揭示了蕴含其中的现代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