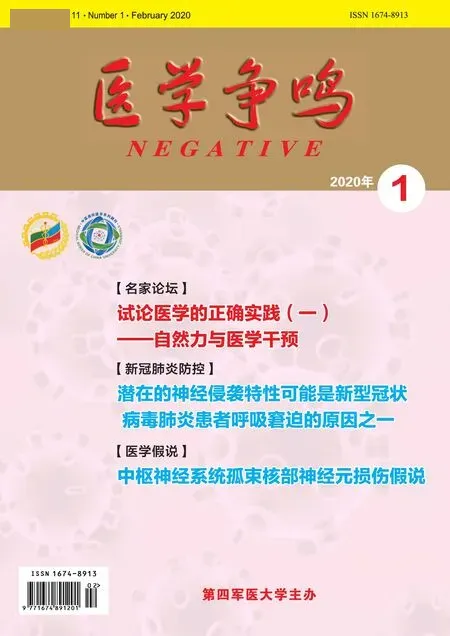对《外科学》第9版骨折治疗原则的商榷
2020-01-05许明熙汪礼军黄珍谷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骨科重庆402360
许明熙,盛 雷,汪礼军,黄珍谷 (重庆市大足区人民医院骨科,重庆 402360)
我国本科教材《外科学》每五年一轮修订,笔者学习其2018年第9版的“骨折的治疗原则”章节[1],并与《外科学》第5~8版的相同章节对比[2-5],认为其修订片面强调骨折的解剖复位而忽视功能复位,不符合医学文献的逻辑和临床实际。现就涉及问题提出商榷,并对骨折治疗谈点感悟,以期及时纠正误导,同等重视骨折的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6-7]。
1 功能复位标准必须保持完整性和严谨性
移位性骨折的复位标准有解剖复位(恢复正常的解剖关系)和功能复位(虽未恢复至正常的解剖关系,但骨折愈合后对肢体功能无明显影响者)。功能复位标准是就常见的五种骨折移位提出复位要求,对分离、旋转移位必须完全矫正,对成角、侧方、缩短移位的复位均有最低要求,且上肢与下肢、儿童与成人骨折的复位要求存在差异,具有不可缺少的四项完整内容[2-5]。而《外科学》第9版对功能复位标准的修订主要存在两个问题[1]:一是把缩短移位删除,使得整个标准残缺不全,是否容许缩短成为无章可循的规则漏洞。因为无论是否手术治疗,骨折断端有自身吸收的可能,这是医者不能完全控制的,尤其是带锁髓内钉固定的动力性负重加压,可造成骨端缩短;如原功能复位标准中容许成人下肢骨折缩短程度不超过1.0 cm[2-5],其删除将存在隐患,若患者对缩短不满意引起医疗纠纷,再缺乏此项标准的支撑,则不利于维护临床一线医生的合法权益。二是对长骨干横行骨折的对位表述不严谨,文字表述为骨折端对位至少达1/3、其示范插图的标注则变化为对位1/3以上、插图显示绘成了对位已超过2/3[1]。如此简单的量化数据弄成了三个样本,其复位的最低要求又以谁为准呢?标准讲究精细,具有可操作性,保持文图一致是基本常识[8],不能随意变样。
2 手法复位达到功能复位标准往往无须手术
骨折治疗宜简不宜繁,对易于手法复位外固定的骨折应首选非手术治疗,主要缺点为若外固定管理不严或患者不配合,将发生再移位。为此,手法复位也有适应证,如下肢长骨干不稳定性骨折一般无需手法复位,因为单纯小夹板或石膏外固定不能维持复位效果,应选择持续牵引、骨外固定器复位或切开复位内固定等方式。手法复位有达到解剖复位、达到功能复位、不成功(未达到功能复位即失败),也就是优、良、差三种复位结果。而《外科学》第9版对手法复位的修订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要求:骨折应争取达到解剖复位,否则必须手术复位[1]。其“否则”的用语意思很明确,即使手法复位已达到功能复位,但没有达到解剖复位为不成功,也必须手术复位。如此误导手术治疗,完全置功能复位的标准于不顾,临床不可盲目遵从。众所周知,手法复位不同于切开复位,有其局限性,毕竟常较难达到解剖复位,但多数骨折可以达到功能复位,不能为强求解剖复位而反复多次的复位,加重软组织损伤导致并发症。若患者有追求解剖复位选择手术治疗的确切意向,也应根据具体情况尊重患者的选择权;若患者愿意接受已达到的功能复位,医者哪有“必须手术复位”的道理?如儿童骨折、成人常见的桡骨远端骨折能够达到功能复位应适可而止,医者要有换位思考和执行标准的规则意识,往往无须骨科医生越俎代庖采取手术治疗[7]。
3 修订切开复位指征不能否定功能复位标准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以广泛剥离减少骨端血供获得解剖复位,但并不保证患肢功能都能够恢复,其严重并发症为骨不愈合和骨感染,且处理困难及功能差。有些粉碎性骨折即使切开复位也不能达到解剖复位。经过长期实践的总结,《外科学》第5~8版的切开复位指征中,有一项重要的限制条款——手法复位未能达到功能复位的标准,将严重影响患肢功能者[2-5]。很明显,手法复位已成功达到功能复位的标准,不具切开复位的指征。诚然,这一项条款也存在不足有待完善,由于复位与固定是一并的,如有的骨折虽然手法复位成功,但外固定确实不能维持复位则不应受限。而《外科学》第9版修订的切开复位指征中,已经完全删除了这一项条款[1],目的是解除涉及功能复位的限制,以期手术复位达到解剖复位。它忽视了其删除必然使功能复位的标准成为没有实质意义的摆设,所制定的标准还有用吗?骨折治疗原则是前后内容贯通的整体,修订切开复位指征不能自相矛盾地否定功能复位标准,因为两者均是规范临床行为的不可缺少的骨折治疗规则。功能复位标准对切开复位指征具有规则性的制约作用,体现临床治疗规则体系设置的科学性和治疗策略先简后繁的严谨性,有利于严格掌握手术指征,防范治疗偏差及贸然手术,怎能轻率地将限制条款删除了事?
4 骨折治疗原则更应注重体现非手术治疗
骨折治疗原则是复位、固定、功能锻练及康复,复位标准和复位方法具关联性。而《外科学》第9版对骨折治疗原则的修订思路欠缺原则,总体缺乏功能复位的概念及规则意识。其修订的标准不但缺乏完整性和严谨性,更主要的问题为手法复位和切开复位这两个自然段的内容片面强调解剖复位,与功能复位标准毫无关联性[1]。完全忽视了功能复位标准的存在价值,视为闲置的摆设,既不符合医学文献的逻辑,也不符合临床实际,这对以达到功能复位为主要目标的非手术治疗有失偏颇。骨折的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同等重要,各有优缺点、适应证及禁忌证[6]。重温“如能以非手术疗法治愈的,即不应采取手术治疗”之大道至简的外科学初衷[9-10],就骨折的治疗而言,更具直接的针对性。骨折治疗发展的方向不仅是手术[6],非手术治疗更值得我们重新加以审视[7]。
非手术治疗对儿童骨折、成人易于手法复位的骨折依然是简便有效的理想选项,这在内固定技术的发源及盛行的国家亦是如此[6-7]。对不同意手术或有手术禁忌证的患者,更能体现出以中西医结合疗法为主的非手术治疗的重要性,其对多数四肢骨折病种的不稳定性骨折仍具应用及替代价值,多数患者同样可以获得满意或基本满意的效果。尤其是有些拟行手术的下肢长骨干骨折患者,在术前的常规辅助检查发现了深静脉血栓形成,使得手术时机超长延迟且难以确定,不宜消极等待手术时机,也应酌情积极采取非手术治疗替代策略。显然,我们不能缺乏非手术疗法处理复杂骨折的经验及技巧。只有坚持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条腿走路”[11],才能通过实践掌握内、外固定两大类技术,因为我们不应是医学知识碎片化单纯的“内固定医生”[12]。我国西医骨科学会虽然自纠取消了违背医学规律的“内固定学组”之名称,但遏制医学知识碎片化仍需提高认识、长期努力。
5 骨折治疗的相关思考
我国骨科客观上存在着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骨折治疗趋势是学术界长期关切的热点,似乎形成了“手术派”和“非手术派”,这容易助长医学知识碎片化[12],不利于骨折的合理治疗[6]。我们必须具备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两套本领,才能切实体验不同疗法的优缺点,根据骨折部位、类型及软组织条件、患者年龄及全身状况等进行具体分析,从而选择相应措施。骨折治疗的根本目的是功能恢复,骨折愈合是初步目的,两者不可主次颠倒。功能恢复比影像学显示的解剖复位骨愈合图征更现实。如闭合性指骨骨折虽然通过手术内固定获得解剖复位骨愈合,但多数患者并发了指间关节僵硬,反而不如非手术治疗所获得的轻度畸形愈合,且功能无明显障碍。由于手术治疗的本身缺陷亦可影响功能恢复,对有些骨折一味追求解剖复位,为影像图征而手术,其结果将是“中看不中用”丢失功能。非手术治疗对功能恢复的影响较小,功能恢复永远是硬道理,这正是骨折的功能复位能够从古传承至今的价值所在。当今微创手术已不强求解剖复位而趋于功能复位[13-14],其复位理念的反省体现着功能复位不可低估的价值回归。骨折治疗必须敬畏医学的客观规律,充分考量患肢功能预后的得与失,恪守临床规范慎重出牌。
6 结语
医学实践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而理论的正确性需要实践检验。笔者认为《外科学》第5~8版的骨折治疗原则是成熟的[2-5],行之有效的应用理论应当被坚持并不断充实。事实上,《外科学》第9版的各相关骨折病种章节,依然坚持了成熟的骨折治疗原则及功能复位标准,依然保留了手法复位不成功才具手术指征的条款及策略[15-16],并没有接受其同版教材中所修订的骨折治疗原则之相悖观点[1],表明对功能复位的认识存在明显差距。教材是面向医学生的,在原则问题上同版教材应当发出协调的声音,而非各自为政。如何保持骨折总论与各骨折病种章节之间的相互照应、统筹协调[8],如何注意功能复位标准与切开复位指征这两个核心规则之间的衔接与有机整合[12],值得我们思考及学术争鸣[17]。我们确实需要把骨折治疗原则的理论工作做好,使之贴切国内临床实际,担当起表率作用,有利于科学、规范引导临床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