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罪为何认定难?
2020-01-03曾那迦
曾那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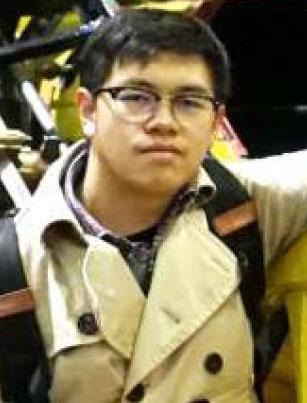
前段时间,记者在外省采访了一起涉嫌刑讯逼供罪案件。3名被告原是公安干警,涉嫌在2001年的一起伤人案中对多名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致使其中多人被诬陷为案件的“凶手”。
“恳请法庭在量刑时,考虑下案件发生时整体的司法和办案环境。”其中一名被告人在庭上的一番辩解引起了记者的注意。按其言下之意,案发当时,刑讯逼供行为似乎曾被当地一定程度下默许。
刑讯逼供是典型的國家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使用肉刑、变相肉刑或精神折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刑法第247条早已明令禁止。但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长期处在灰色地带,难以完全禁绝。近年来,“聂树斌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具有代表性的冤案陆续被披露并昭雪。这些冤案酿成的背后总有刑讯逼供的存在。
究其原因,虽然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早已吸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但“有罪推定”的潜在意识还植根在一些司法人员心中。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筛选出了39篇刑讯逼供罪判决书发现,在一些案件中,被害人被认为涉嫌盗窃、诈骗等罪名。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对“嫌犯”作了有罪推定。讯问无果后,他们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则,对嫌疑人“上了手段”。
据法律界人士介绍,除开个别案件中办案人员存在主观故意的刑讯逼供外,刑讯逼供更多产生于一种办案者对口供的依赖心理。因为口供历来被视作定罪的“证据之王”,“办案就是要突破口供”。还有“命案必破”等观念也促使办案人员必须拿下口供。
2013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坚持刑事诉讼基本原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应当排除,这体现出了法治的进步。
但这并不意味着刑讯逼供的问题能彻底得到解决。近年来,因刑讯逼供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司法人员仍是少数。在此前提到的39篇刑讯逼供罪判决书中,有的被告人被判处一两年有期徒刑,有的获缓刑。若受害者只是受轻伤,被告人还有很大几率被免予刑事处罚。
为何涉嫌刑讯逼供的司法人员较难被追责?主要是由于刑讯逼供罪认定难。有研究表明,在被告人提出遭受刑讯逼供的案件中,绝大多数案件被认定为不存在刑讯逼供。“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实务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对于刑讯逼供的认识并不到位。”
法院对暴力型刑讯逼供的认定较为容易,而对变相刑讯逼供的认定较为困难。在许多案子中,证据缺乏成为法院不予认定刑讯逼供的主要原因之一。对此,有法官表示希望能出台帮助其认定变相肉刑和精神折磨的指导性细则。
在办案的实际过程中,的确很难让嫌疑人“自动招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办案人员可以“甩锅”给司法办案的大环境。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文件提出加强对刑讯逼供的源头预防,这正是解决刑讯逼供的关键,但要落实好,并不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