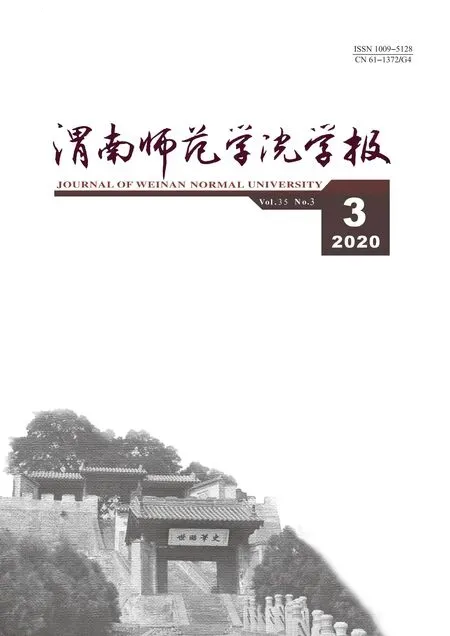《史记》人物独白与特殊话语
2020-01-02魏耕原
魏 耕 原
(1.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0;2.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与现代史学意义的历史著作最为显明的区别之一就是记载人物话语。《尚书》是记载高层人物的讲话或谈话记录;《左传》的人物话语有很重要的叙事意义,记事与记言并重,即就写战争,甚至于以对话为主体;与之差可比肩的《国语》即纯属“记言体”,人物与《左传》同样扩大到臣属;《战国策》以策论为主,即以人物合纵连横的言语为主,人物扩展到布衣策士;只有《春秋》是编年记事体。《史记》全面继承此前史学的特点,而带有总揽性质。一是把此前带有断代史倾向的性质一变而为通史,二是《本纪》与《世家》属于编年记事体,《书》亦以记事为主。而包括《本纪》《世家》一部分在内,以及占主体的《列传》,人物话语占到重要位置,而且描写之生动,远迈前此所有史书,以后更是望尘莫及。
一、人物上场独白的经典性
《史记》的人物语言可以分为四类:一是自言自语式的独白;二是人物之间的对话;三是特殊语境中的人物话语中断,包括以非语言的其他方式表示说话;四是众人所说之言。人物语言的独白往往是只言片语,而选择精当却最能透出人物心中秘密与性格的特征,先秦史书很少见,以后史书无多亦不见精彩。《史记》人物独白一般放在人物出场,或者生命结束之时。也有见于文中主要部位。这些独白,往往是内心世界的窗户,犹如人物画之眼睛,人物之精神、个性、为人等,全都聚焦于此,光芒四照,全篇为之生辉。
人物出场时的独白,往往一句话既要概括其人人品主体,而且还要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且也是一篇之大纲,笼罩全篇。对于反秦三大人物项羽、刘邦、陈涉性格揭示都采用独白,而为人艳称。项、刘见到秦始皇,一言“彼可取而代也”,一言“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虽然都未直接见于出场,但都有同样的力度。项羽的话是放在“少时”之后,刘邦的话见于“好酒及色”之后,然两本纪都是大文章,都位于开头的部分。最早注意者王鸣盛谓“气象自是迥别”(凌稚隆《史记评林》语)。看到他们独白的典型意义:“项之言悍而戾,刘之言则津津然不胜其羡矣。陈胜曰:‘壮士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项籍口吻正与胜等,而高祖似更出其下。”[1]4右面约略比较出性格之差异。姚苎田谓项羽语:“蛮得妙,与高祖语互看,两人大局已定于此。”[2]5吴见思却谓刘邦语:“雄浑冠冕,气局阔大。项羽亦尝为此语,未免天渊。”[3]67论项羽为以成败论人所囿,谓刘邦却不无道理。牛运震说:“(刘邦)语极雄浑耸动,较‘彼可取而代也’,自然气概不同。”[4]37或者看出项羽语“是前半篇暗眼”(程馀庆语)。已觉察篇首人物独白与前半篇内容之关系。
今人对刘项这两句话更为看重,已经上升到经典意义上的观照。《史记》凡是人物独白,往往能看出性格、身份、职业、情感等。“彼可取而代也”,这是仇恨语。视秦始皇为仇人,以楚为最,“楚虽三户。灭秦必楚”就是埋在项羽心中的种子。他的叔祖父项王“为秦将王翦所戮”,家仇国恨集于一身,推翻秦王朝自少年即成为终极目的,故此言爆发出复仇主义者的强烈火焰;出此言者必为尚武的将军世家,“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自少“学万人敌”——即兵法,以武力征服天下,便成为唯一手段,直至兵败垓下,还以为“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所以只配作为时不长的“万人敌”的西楚霸王;出此言者必是摧枯拉朽的暴力者,以强悍蛮横手段摧毁了一个旧世界,却不能建立一个寓有生命的新时代,只是出色的悲剧式英雄,而非喜剧性政权的领导者。复仇主义英雄情结与尚武精神,与没落贵族的将军世家意识,以及剽悍暴力都在这句独白的名言中闪动着刺眼的光芒。只是那样的裸露率直不加掩饰,就像鸿门宴上一见面就说“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而不加任何思索。刘邦所言“气象自是迥别”。当时天下苦秦久矣,然而就是“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至于像陈婴母所言:“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应当是一种社会思潮。刘邦却不同,他早就专门制作了自己是“龙种”的神话,即使醉卧后也会让人说“上常有龙”,这当然是以“酒雠数倍”代做的广告。他到咸阳服劳役,看到秦皇,自然“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对他来说这是发自内心由衷之言,但说得控制而不直露,不像项羽之“取”,把本义“捕取”,“执获罪人”,割取俘虏耳朵[5]116,以其引申义抢夺,都蕴含其中,显露以暴易暴的强横。而刘邦以轻松的“当”,加上模糊的代词“如此”,就是站在身边的人也抓不住什么把柄,可见他具有一定的政治头脑,非草泽英雄草莽可比,他见过政治世面,起码接近《水浒传》宋押司那样的小吏;“大丈夫”不带政治色彩,含义的外延却带膨胀性,连县级风尘小吏还差一些的亭长,大约相当于今日之乡长,却以此自居,性格的豁达则不言而喻;而且“当如此也”对九五之尊万人之上的皇权是如此的企慕,不,应当是艳羡,大有过屠门而大嚼的垂涎相,“津津然不胜其羡”,但也看出其志量之不小——想冒族诛的危险,造反而敢做推翻皇帝而自己来做的大勾当,“气局”是够“阔大”的了。由不够小吏的亭长而直欲奔到皇帝,在这人心思乱,稍有权力者便欲为王时代,刘邦的“皇帝欲”也是必然产物。于是至高无上的皇帝欲所代表的权力主义,豁达的性格,甚至连项羽那样家世背景也缺无,却还要作“空手盗”的一番大事业,自然不会出蛮力的,构成带有几分无赖相的大政治家。
无独有偶,而且有三,比刘邦亭长不如,比项羽那样的将军后裔更不如的陈胜也有同样“经典的话语”。《陈涉世家》说: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陈胜的浩叹,是对讥讽他的拉长工的哥儿们说的,还是受到刺激后的自我仰天长叹,无论怎样,这篇大文开端就写这场田头对话所引发的“独白”。“燕雀”也好,“鸿鹄”也罢,此非衙门内人的标语,而是“野外作业”——拉长工者的话头。活动的场所是田间地头,冲天之志的豪言,分明带有露天劳作的“农民语言”的色彩,将军后裔与亭长对鸟儿都不会感兴趣。出此言者同样像刘邦那样向往“富贵”,除了造反别无他路,这同样需要更大的气局,属于草莽英雄。然而视同耕者为“燕雀”而己为“鸿鹄”,骄傲自大之个性也孕育在这句豪言里,这既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造反者的自信,也是自认不凡的狭窄,哥儿们后来也因此被他杀掉,他亦因自傲而“鸿鹄”折翅。农民理想与个性自傲集中于这句话,所以,这句话贯穿全文始终,就像刘项的话贯穿两篇本纪一样。
论者说:“人间正道先是唾弃了嬴秦,后又淘汰了项羽,最后则选择了刘邦。”[6]245还应当说人间乱世激发了陈胜的“首难”,这位自视不凡的布衣,敢为天下先,无所顾忌,导引了刘、项崛起,“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其历史的首创作用不在刘、项之下,虽然时仅半年而结束于傲横引发的暗杀中。
英布是秦汉之际欲为“王”的“二级人物”,本传记载:“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此传开头这个传闻,他的自信是比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过之而无不及,雄心勃勃,英气逼人。别人对他的戏笑,亦如庸耕何来富贵那样。而“英雄热中富贵”(牛运震语),气局也就有所限定。后之归汉,“上方据床洗,召布入见,布大怒,悔来,欲自杀。出就舍,帐御饮食从官如汉王居,布又大喜过望” 。如此忽喜忽怒就未免以富贵为中轴。他的造反也是逼出来的,刘邦问“何苦而反”,回答“欲为帝耳”,刘邦对他的造反不明原因,他的答话并非真实的目的,不过是对已有富贵的无奈的自卫,也是用刘邦的话语来回敬刘邦“当刑而王”者是不会有“欲为帝”的野心!
与张良可以比肩的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不视家生产”,喜交游,“门外多有长者车辙”。乡里庙会为主宰,“分肉食甚均。父老曰:‘善,陈孺子之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是肉矣!’”让陈平分社肉是杀鸡用了牛刀,然而却说让他“宰天下”,也会像分肉一样甚“善”!换句话说,“宰天下”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自负为宰相的料子。对陈平这种智囊人物,把这话看作“对话”,不如视为“独白”,更合乎他的性格。他要在乱世中以求为宰相,犹如英布自信“当刑而王”,也是有作为的二流人物。他的话不仅只是自负,而且是自信。叙写其人在秦末乱世之中,只不过是“小小点缀”,然而意态“迈远”,“自有一种高远之气,矜贵之姿,与人自别”[3]59-63。读书交游的身份,多智商的才能,不露锋芒的个性,均能俱见。
战国距汉不远,司马迁写来也是如此切近。吕不韦是跨州越国贩贱卖贵的大商人,家累千金,至邯郸见到了被赵国作为人质的秦国太子之子,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兴奋地说:“此奇货可居!”这样的自白,把王孙视作“货”,可以贩于赵而卖于秦,可以作“一本万利”的大买卖,这只能是商人的话语。把一个王室的“储庶孽孙”要拨弄成一国之君,这又显示出大投机大阴谋的政治家的眼光。如此居心叵测的“钓奇”,需要经过三代人的继位时间才能达到目的。深谋远虑还要加上数十年的耐心,这又需要多么阴狠隐忍的心理素质。吕不韦成功了,做了宰相,门客三千,使之作《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牛运震说:“‘大贾人’三字,一篇之纲。不韦一生,全是贾贩作用,篇中点其见子楚而曰‘奇货可居’‘以千金为子楚西游’,又云‘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又‘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又悬《吕氏春秋》咸阳市门……孰非以利啖天下哉?’阴钓国人,显盗圣言,真贾人矣。太史公处处点逗,眼目分明,意思贯穿,亦奇传也。”[4]213李景星说:“吕不韦是千古第一奸商,尊莫尊于帝王,而帝王被其贩卖;荣莫荣于著作,而著作被其贩卖。幸而鸩死结局,使人知始而贾国,继而贾名者,其终也归于贾祸。不然,以令善路梗塞矣。”[7]78当春申君黄歇与李园合作如吕不韦的政治投机而被刺,《春申君列传》说:“是岁也,秦始皇立九年矣,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正如朱英提示春申君所言:“世有毋望之福,又有毋望之祸,今君处毋望之世,事毋望之主,安可以无毋望之人?”对于吕不韦来说,秦始皇既是“毋望之主”亦是“毋望之人”。他的“奇货可居”“贾国”大买卖经营了数十年,终于遭到“毋望之祸”的惩罚!
与吕不韦政治投机相近似者为李斯。“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厕鼠与仓鼠同为老鼠,因处境不同,生活差异则不可同日而语。他由此触发人之有才能与否,和老鼠的所处不同境况相等。他要优化自己的人生,决然要选择“仓中鼠”那样的生活方式。李斯是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大书法家集于一身的卓出人物,然而他人生的终极目的,却出于仓鼠式的“硕鼠哲学”,唯富贵是求,甚至于采用任何龌龊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就未免等而下之,也为此促成诛灭三族的悲剧。聪明智慧、唯利是图的个性,人格之低下,二律背反地构成了他全部的人生。《李斯列传》由五次感叹贯穿起来,他出场独白感叹,是他的人生基调,也是另外四叹的“发源处”。他的出场独白和以上所有人物一样,在全文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
以上的人物独白,有叱咤风云的霸主、豁达而羡慕皇权的亭长、铤而走险的草莽英雄,也有不愿居人之下的小吏刑徒,以布衣而欲做宰相的穷书生,还有钓奇贾国的大商人,以绝顶聪明的才智以求富贵显达的政治投机家,以仓中硕鼠为人生终极目标的小吏而导致惨死。从他们的“独白”,可以看出不同的个性与身份或职业、才能与追求。其中性格与追求最为显露,他们话语是战国与秦汉之际乱世的产物,凡是富有才能而出众者,在少年时代都有自己的追求,尽管追求的目的与手段各异,胸怀志量却是共同的。从不同的气局理想,展示人自各异的鲜明性格。同是小吏的李斯与刘邦的话语不能互移,虽然都是热衷权势和富贵,但目标有高低,志量有大小,语气有矜持与低下之别。同是刑徒或为长工的英布与陈胜,地位连布衣也不如,草莽之人与亡命之徒也迥然有别。商人的话语带有职业的烙印,宰相自然是穷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复仇主义的将军后裔的豪言,自然要爆仇恨的火花。
在职业或出身不同的类型化中,精选出个性焕发的独白与话语,犹如从事物意义的外延发掘内涵,是那样的确切不能移动,是那样的个性分明。这些性格分歧的独白,也是五光十色的豪言壮语,都是发自言说者内心深处,充斥着人物的不同情感,往往与他们传闻、轶事、小故事,为人的特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仅使读者过目不忘,也深深打动读者,触及内心的共鸣,显示了《史记》人物上场独白话语的魅力与经典的艺术性。
二、最后与临终的喟叹
《史记》是一部倜傥非常人物的悲剧史,尤其是战国与秦末及西汉初年,都是该出手的时代,凡是要干事业的人,往往都会遇到坎坷不幸,甚或遭遇悲剧以结束生命。不幸与不平且又面对生命的被迫结束,就不能不有发自肺腑之言。这是人性的最后显示,以刻画人物性格为能事的司马迁则予以特别的关注,记录了种种使人感慨瞩目的“遗言”,使人物性格最后得到展示与升华。这些人生最后的话语,或为自言自语的独白,或有诉诸听者的对象,后者按理不符于彼此之间的对话,然也无须听者要回答什么,不妨也看作一种“自白”,和“独白”放在一起讨论。
有不少人物在《史记》里,没有记述人物临终的话语,但却有传主最后的话语,这些最后的话,不一定出现临终之时,而以后再也没有记述,这是属于作者对人物语言的取舍,同样带有最终的性质,而值得关注。
《廉颇蔺相如列传》合传中的廉颇,因赵王中秦之反间计,使乐乘代廉颇为将,廉颇怒而攻之,后廉颇只好奔魏,居梁久之得不到魏之信任。赵王因被秦兵数困而思廉颇,廉颇亦思再用于赵。他因没有打点探视的赵王的使者,而使者又受了廉之仇人郭开之金。尽管他当使者面“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以示尚可大用”。使者还报却说:“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结果“赵王以为老,遂不召”。这是多么遗憾,失去了东山再起的绝大机会!后又被楚迎之为将,“无功,曰:‘我思用赵人。’廉颇卒死于寿春。”这句话,让人不胜惋惜,一代名将就这样郁郁寡欢地离开人世!对最后交代因无事可述,简洁到这么几句,中间却蕴含着作者不尽的嘘唏感慨。“他老人家是一位忠厚的军人”(梁启超语),从他这句最后的独白“我思用赵人”,犹能看出,对故国是多么的思念,而他内心的伤痛也融注在这简短的一句话里。在赵王赴渑池之会时,而且“观其与赵王诀,如期不还,请立太子以绝秦之望,深得古人社稷为重之旨,非大胆识,不敢出此语,非大忠勇不敢任此事”[8]105。他勇于战斗,忠于赵国,在人才流动的战国尤显可贵。居楚老将这一声叹息,虽“只一语,感慨之极,回望故国,黯然伤神,可抵一篇《恨赋》”[3]6。姚苎田说:“惟廉将军沉毅深远,而一生无大奇节,史公着笔颇轻。及乎晚节被谗,一不得当,而犹有‘思用赵人’之语。夫钟仪既絷犹鼓南音;范叔西游,无忘近壑。廉将军于此遐哉!弗可及已,而惜乎赵之不终其用也。”[2]156这句凄切的独白而引发人多少扼腕之叹。
《商君列传》以“法”字为纲,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商鞅蒙遭“欲反”罪名,通缉捕拿。“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待客之人,即店主)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秦自商鞅变法国势强大,司马迁对严刑苛法没有好感,谓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不免失于个人情感的偏颇,这个故事就带上作法自毙的色彩。住店要有验证身份的凭证,否则罪及店主。商鞅逃奔连客店也不能容身,如此法定盖由其定,故有“为法之敝一竟然至此哉”感叹,这当然不是说给店主的,只能是一种自白。这是本传记他的最后一句话,很有些忏悔性质,或许有些作者想象的“代言”成分,然毕竟切合人物的处境与性格。而且吴见思说:“抽出一闲事,以见商君之法刻薄操切如此,通篇用法之敝,借此一语结尽。”[3]27可见这句独白,具有回光返照和通篇结穴的双重作用,亦非可有可无之文字。
在《鲁仲连邹阳列传》里,鲁仲连助齐将田单劝降固守聊城的燕将,事成后,齐王欲爵之。鲁仲连逃隐于海上,曰:“吾欲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此传也就以此结束,海岛上语当然是自白了。这和他却秦救赵“为人排患释难纷乱而无所取也”的名言,前后相应,熠熠生辉。以人物独白为结语,“结法萧洒出尘,超然远态,此外不可再着一语”[4]209,这也成了最终之语。这种甘于布衣,飘然肆志的独白,是“澹荡人”的英风浩气的自然流露,没有做作,只有磊落。其人亦如李白所说的“明月出海底,一朝开光耀”那样,而使“后世仰未照”!
至于人物临终的话语,很为司马迁看重。“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终,其言也善”,最后的话语,应该是心声的流露,最能显示内心世界的隐秘。李斯为了保持富贵禄位,妥协赵高,篡立二世,由协秦王朝建立者一变而为秦王朝和自己的双重掘墓人,身受五刑,腰斩咸阳时,“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这与其是说给儿子,不如看作一种“自白”的感慨,这是人生最后的发言机会,绝顶聪明的人,却发出悔不可及的痛忏,至死才明白了所秉承的“硕鼠哲学”,是会毁掉一切的,包括爵禄之重的丞相与生命在内,如此凄怆激楚的话语,是对他辉煌而又自作自受的悲惨人生的反拨。这发自肺腑的一叹与篇首喟叹对比照应,自成起结,又给人们带来多少深沉之感慨。
而被李斯与赵高逼死的蒙恬与蒙毅兄弟,《蒙恬列传》后半篇全是蒙氏兄弟被逼死前与行刑使者的谈话。蒙氏三代有巨功于秦,赵高犯大罪,秦王令蒙毅依法判处,处以死罪。秦始皇又以其办事有能力而赦之,并恢复内府宦职,赵高因设法置蒙氏兄弟以死罪。此传记述了蒙氏兄弟被赐死前大段鸣冤的话,蒙恬对行法使者先言其功:“自吾先人,及至子孙,积功信于秦三世矣。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矣。”蒙毅死前列举:“昔者秦穆公杀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号曰‘缪’。昭襄王杀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杀伍奢,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四君者,皆为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为不明,以是籍(记载)于诸侯。故曰‘用道治者不杀无罪,而罚不加于无辜’。”使者知胡亥之意,不听蒙毅之言,遂杀之。蒙恬则对使者言周公辅成王而被流言所伤,后冤情大明,成王悔过而杀谗者,返回周公。又言“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而国亡”。并言:“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将以谏而死,愿陛下为万民思从道也。”使者同样不敢传言于上。“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堑万余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蒙恬最后的两番话,一是“无过而死”,一是“罪固当死”,看似矛盾,实则无别。“太史公曰”则谓秦轻百姓之力,蒙恬“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邵晋涵说:“轻百姓力易见也,阿意兴功难见也,深文定案,使贤者不能以才与功自解其罪,此史家眼力高处。”[8]632郭嵩焘说:“蒙氏有功无几微过差,其北备匈奴,方秦并天下时事无急于是者;起长城为防,至汉兴犹蒙其利。而蒙氏固将也,以任边事,其职应然,观其临死绝地脉之言,何其言之沉痛也?史公责其‘阿意兴功’,而以其遇诛为宜,不亦过乎!”[9]306蒙恬言筑长城“此乃恬之罪也”,实际上是言其功,正言若反,自鸣其有大功而冤死,“此与《白起传》末临死自明其罪之语同,乃故作扬落跌挫以尽其势,而波折决胜”[4]224。司马迁当然会看到这一点,不然何以近半篇幅记述蒙氏兄弟冤语。至于“阿意兴功”“遇诛固宜”,似为责难蒙恬,实为一种“反批评”,即正话反说,与蒙恬临终的“自白”并无区别,故为“深文,亦正其识力高处”(牛运震语)。对于临终语,吴见思说:“终以不了语竟收,以明蒙恬之无罪也。”[3]43“太史公曰”往往正话反说,深文寓言,寄寓慨然不平之意。就人物性格刻画而言,蒙恬在《史记》中不为上乘。然就其临终的自白,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记。
早于蒙恬同样冤死者为秦昭王时名将武安君白起。白起长平之战坑赵卒四十万,韩、赵震恐,施行反间,使秦相应侯范雎接受赵地六城而罢秦兵,因此与范雎有隙。半年多以后,秦复发兵攻赵而败,秦王几次使白起为将,则不肯行。攻赵又败,秦王怒,“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称病笃,应侯请之,不起。于是免武安侯为士伍,迁之阴密。武安君病,未能行。居三月,诸侯攻秦军急,秦军数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阳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昭王与应侯群臣议曰:‘白起之迁,其意尚怏怏不服,有余言。’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武安君引剑将自刭,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诈而尽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杀”。这临死的自白和蒙恬逼死前的两番话,何其相似乃尔,无罪与“固当死”的用意如出一辙。如果联系李广寻思不能封侯的原因,在相面王朔的诱导下,说是由于杀俘,实是批评汉武帝用人唯亲。而此处坑赵卒亦有表功之意,同样正话反说。
李广讷口少言,《李将军列传》也没有记他多少话语,然而被逼到上法庭,对自己部下说:“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于是自杀。这是李广唯一的一番长语,也是最后的倾诉与自白。他一生受尽委屈,不被重用,带兵兵少,装备更少,所以被匈奴俘虏过,射敌射虎一定要逼近,因为给他的箭少。这次跟从大将军卫青出击匈奴的“哑战”未打响,匈奴逃遁,罪责都要推在他的头上,他的满腔不平,就只说了这几句话,而且不能明言武帝之过,而推之于“天”。一代名将还要再度逼上法庭,只好以自杀的方式以鸣其冤。于是“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司马迁未尝不在哭,他以最简朴的叙述,以普天下的悲痛,痛悼李将军的不幸。
在将军被逼赐死中,伍员之死与李将军一样,最为痛伤哀悼。《伍子胥列传》说,吴王听信谗言,以为“其怨恐为深祸”,乃赐剑命其自裁,伍员仰天长叹说:
嗟乎!谗臣嚭为乱矣,王乃反诛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时,诸公子争立,我以死争之于先王,几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
而且他给门下舍人的遗命是:
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
他的话不幸而言中,吴国由此灭亡。《吴世家》说夫差亡国自杀时有言:“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也算是对被盛之皮囊沉尸江中的伍员英魂的忏悔。伍员临终第一番语“我”与“若”络绎而来,他扶持阖闾、夫差父子两代称霸,而被屈死,这无异于遥指夫差痛心裂肺的指责!而且最后的遗嘱是看不到“越寇之入灭吴”,这死不瞑目的话让人战栗,令人发怵,千古之下,都可想见这位烈丈夫的怒目而视,忠魂咆哮!
伍员死后,“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山”。这是吴人的悼念,也寄托着司马迁的哀思。而且,还有“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于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这是对其人最高的礼赞,跌宕悲壮而又紧凑!
总上临终之语可见,这些话语都给人物自己画上最后的句号,结局都是以悲剧而告终,揭示了人主与功臣之间的矛盾,都是因听信谗言而导致逼使忠勇者自杀,这是过去历史的一条规律,由商周以至春秋,由战国以至秦汉,无一例外。司马迁在这条规律的突出链条上,记录了悲剧人物最终的自白,这些话虽没有上文讨论的人物上场自白只言片语生动,个性也赶不上那样鲜明生动,因为那是付之于不同传闻、故事的性格化话语。而被屈死者忠勇之士,本身具有共性的规律,临终自白甚至有相近之处,但这些话语,却有让人深长思之作用,甚至有震撼人心的效果,而且也显示出各自特殊语境的复杂性,面对君王行刑的使者,说话不能随心所欲,就是最后的留言也是如此,所以白起、蒙恬的话都带皮里阳秋的意味。就是李广对属下所言,把不幸也要归之于“天”,实际上都是对悲剧制造者的谴责!
三、仅有的一次性对话
在《史记》的传记里,尤其是附传里的人物,事件无多,记述亦少,往往记述了人物的“一次性对话”,这就要求选材上精心取舍,选择最能代表人物精神面貌的最佳切合点,能够窥一斑而知全豹,而使次要人物也能 “活”起来。
《伯夷列传》为七十列传之首传,具有特殊意义,人物事迹也没有用多少,对话自然无多,甚至几近一次性。孤竹君欲立叔齐,父率叔齐让位伯夷,伯夷曰“父命”,遂逃去。这是第一次对话,实际只有两字。武王载父亲“木主”,东伐纣。兄弟俩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之而去。”这是最后一次对话。伯夷为长子遵父命让国不立,故反对武王革商之命,并非明智,而司马迁看重的是“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太史公自序》)。伯夷这次对话,带有伦理性质。他的史料太少了,不可能把他写 “活”,司马迁借他要为所写的“俶傥非常之人”树一标尺,传中因而大半都是议论,此篇是列传之别体。
他所写的《老子韩非列传》中的 “庄子传”,因为短到不足三百字,借助唯一的一次对话,改写了《庄子·秋水》神龟宁曳尾涂中寓言:楚王以厚币与相位使人聘请庄子。庄子笑谓楚使说:“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独不见郊祭之牺牛乎?养食之数岁,衣以文绣,以入太庙。当是之时,虽欲为孤豚,岂可得乎?子亟去,无污我,我宁曳尾于污渠之中而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秋水》寓言原是神龟“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以此让楚使选择,而选了后者庄子就自然不去做宰相。司马迁的牺牛被宰割为祭品,则出自《庄子·列御寇》,而予以扩写,属于移花接木。更显富贵而有灾祸,也非常切合庄子不为外物所累的思想。这段话占了“庄子传”的少半,以此展示庄子“王公大人不能器之”的精神。
更值得一提的是,“老子传”里记述了老子与孔子一次见面谈话,也是“老子传”中唯一的对话,孔子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若飞蓬转徙)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此与《孔子世家》差异迥别。儒道开宗立派两大师思想交锋,撞击出不同凡响的光华。孔子把老子比作人中之“龙”,“乘风云而上天”,自在而行,人不能知。《史记》记述两大师见面,出于《庄子·天运》,然庄子多寓言,就不一定是实录了。反正老子这一番高论同样切合他的思想,换句话说,司马迁想用人物自己的语言,表示思想家的宗旨。老子的传闻不多,连姓名都不能确实,司马迁只能做到这样,反正给我们留下了老子神秘多智的声音。
在《魏其武安侯列传》里,汉武帝的母亲王太后也只有一次性发言。汉武帝对田蚡的专横很不满,东朝廷辩时,朝臣畏缩不敢表态,武帝恼怒而罢廷。因事关王太后弟田蚡,武帝问太后安。“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今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前面四句话表面上骂群臣,实际上是批评武帝不支持田蚡。所以“帝宁能为石人”就直接骂起来。后四句是说你也有“百岁后”,哪些朝臣又怎能信得过?王太后的话盛气凌人,以太后和老娘的双重势力挤兑儿子,蛮横不讲理,活生生揭示了拥有特权而专横孤行的老太后面孔。汉武帝在主持廷辩时就窝了一肚子火,转过身又碰上了太后冷钉子,气不打一处出。于是“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辩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这与其是说“道歉”,还不如说是“回敬”。是说你老人家不能只护你之弟,窦婴也是窦太后之侄,都是皇家外戚,不能偏东袒西,故让朝廷共议。否则使一狱吏即可裁处。娘儿俩对话真是刀兵相对,火星四溅,娘硬子强,顶得老娘肯定憋不出气来。“太后语凡数转,层层驳折,真如推墙排壁”[4]272,而武帝语只一转却如排山倒海。母与子于此成了太后与皇帝的交锋,千载之下,声口如闻。
武安侯田蚡曾与淮南王刘安勾结,表示将来欲拥其为帝,刘安因此送他很多财物,后来武帝闻知,愤然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4]272一篇大传,于此戛然而止。“语特冷峻,恨声不绝。以此结,田、窦曲直判然矣。昔人以为如此作史,真老狱吏手。良然。”[4]273若就做文言,以“冷峻”语结束,却有余音袅袅的效果。
李广讷于言,故《李将军列传》没有多少对话,然在《李广传》文首尾又记述了长短不同的几次对话,均属一次性。汉文帝对他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又有公孙昆邪对景帝哭说的“李广才气,天下无双”云,合观则言才气无双的李广是不会有出头之日的,预示命运屯蹇,为全文笼罩了一片悲剧气氛;而且才气无双为全文明线,“不遇时”为暗线,明者实写,暗者虚写,两线交错并行,贯穿全文。“一篇感慨悲愤,全在李广‘数奇’‘不遇时’一事。篇首‘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时”’云云,已伏‘数奇’二字,便立一篇之根。”这正是“太史公操笔谋篇时所为激昂不平者也”[4]275,也正是从结构上看到对话起到极为重要作用。
除了用对话提示中心外,对话在首尾呼应上也有重要作用。《李斯列传》开篇即叙观厕鼠与仓鼠而叹:“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不仅刻画了唯利是图的性格,他的如此“老鼠人生观”,演出一部轰轰烈烈以至毁灭的悲剧。而在临近结尾,父子被腰斩,“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这不仅是对追逐富贵的“老鼠哲学”的悔悟,也刻画了一个性格完整的绝顶聪明人的自我毁灭,同时在结构上首尾呼应,使一篇大传连成一气。
或者以人物之片语只言回光返照,使其中若许疑云一扫而清。《淮阴侯列传》里,刘邦时时猜忌韩信,处处控制。当他平叛归来,知韩信被杀时说“恨不用蒯通计”,此用补叙,从吕后口中道出。便把韩信谋反罪名一语戳穿。
综上所论,凡是《史记》名篇,没有对话不精彩的;凡是对话精彩处,人物性格没有不鲜明的。司马迁继承先秦史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尤其是《左传》《战国策》记言特色,而把它渗入一篇篇人物传记,以之刻画性格,以之推动情节发展,还用于提示中心,又用于首尾呼应。人物对话之语言,不仅符合人物之个性,而且传递出当时之情景之气氛,为后世之小说、散文、戏剧提供偌大法门。他对人物语言的选择、提炼、加工,体现了绝大的才能,也发挥了在结构上的各种功能。《汉书》作为附传的《苏武传》,其所以可以与迁史比肩,就是取法《史记》以及善记人物语言的特点。然《汉书》像这样的记叙并不多见,这也是比《史记》逊色的原因之一。名列“前四史”的《三国志》生动性最弱,其原因也在这里。以后的史书就很少有这样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