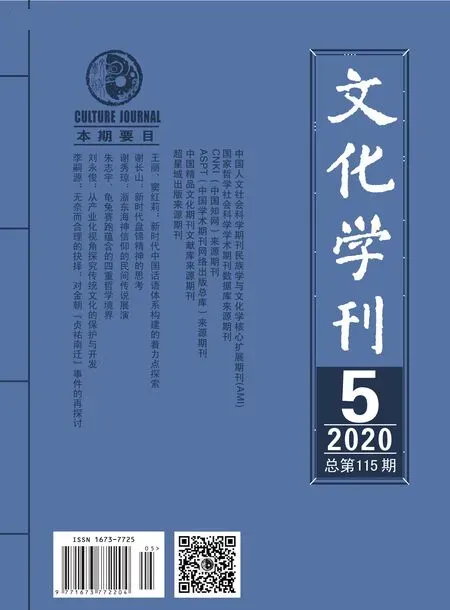《人性的枷锁》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2020-01-02陈小凡
陈小凡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是英国文坛上一位雅俗共赏、深受广大读者青睐的作家。毛姆无疑是幸运的。他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历程,那是一个由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思想碰撞而迸发出无数智慧火花的年代,因此,他的作品拥有了融合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特殊风格和魅力。毛姆更是成功的。他拥有众多忠实的读者。早在1961年,他的作品销量就已经超过了4千万册。美国著名作家德莱塞这样赞美《人性的枷锁》(1)各个译本的中文译名略有不同,本文选择“人性的枷锁”这个译名是因为其是最早的译本的译名。:“它使空气中充满了蓓蕾般的音符,花一般的音调,带着难以捉摸的信息在那里漂浮、隐现。”[1]本文将综合翻译界和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的关注和评论,介绍其在我国的研究状况。
一、《人性的枷锁》在我国的译介
在我国,对《人性的枷锁》的关注和介绍最初源自翻译界。最早的全译本是1981年发行的《世界文学全集 第七卷》,经我国台湾地区名家出版社编辑部翻译、编纂完成。1983年,张柏然的译本发行面世。较之前者,张译本在风格上略有不同之外,小说名被译成“人生的枷锁”。同年,徐进的译本也与广大读者见面。1984年,宋树凉在我国台湾地区出版了小说的又一中译本。20世纪90年代之后虽然没有新的译本,但张柏然、张增建以及倪俊在1983年版本的基础上合译的《人生的枷锁》被不断再版发行。数十年岁月的洗礼并没有磨灭这部佳作的光彩,反倒见证了它历久不衰的魅力。
对这部作品最早的评论也来自翻译界。张柏然在译本的译后记中既点明了小说的题意,又予以了客观的评价。“生活毫无意义,也不可能改变成另一个样子。只有摒弃人生的幻想,挣脱精神上的枷锁,才能成为无所追求、无所迷恋的自由人。”[2]在张柏然看来,这一处世哲学实为一种自欺欺人的精神麻药,无法使人摆脱资本主义的桎梏,更无益于改变造成人世间种种不幸的社会现实。刘宪之在其翻译的《毛姆小说集》译后记中也给予了作品类似的评价。笔者认为,毛姆略显虚无的世界观同其生活的时代密切相关。该书完成于1914年,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社会早已露出动荡不安的端倪。1915年,《人性的枷锁》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时局中正式发表。战争给世界和人们带来死亡,更带来了对未来的迷茫与绝望,这无疑影响了毛姆的世界观。
同时,毛姆传记中译版的发行也促进了我国学者对《人性的枷锁》的研究。最早的译本是梁实秋主编的《名人伟人传记全集·毛姆》。1987年,波伊尔所著的《天堂之魔——毛姆传》的中译本也相继出版,其中有一个章节专门介绍了《人性的枷锁》的创作背景,即“婚姻与《人性的枷锁》”。1988年,罗宾·毛姆的《盛誉下的孤独者:毛姆传》出版。相较特德·摩根既权威又平实的《人世的挑剔者:毛姆传》以及波伊尔《天堂之魔》那种孑然事外的苛刻与冷嘲热讽,《忆毛姆》有着更多的人情味。读到最后,看到毛姆先生行将离世的种种言行,让人有说不出的辛酸。毛姆的自传《毛姆写作回忆录:总结》也为《人性的枷锁》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资料。1977年,该书的中译本由我国台湾地区志文出版社发行面世。
二、《人性的枷锁》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在翻译热潮的影响下,国内文学评论界也掀起了《人性的枷锁》“研究热”。1982年,潘绍中在《外国文学》发表了国内第一篇引介《人性的枷锁》的文章。此后,我国对该小说的关注和研究长达三十多年之久,断断续续,却不曾终止。
(一)20世纪80年代:对小说的引荐
这一阶段的文章特点是以毛姆以及《人性的枷锁》的简单介绍为主。首先是潘绍中在1982年发表了《在国外享有更大盛誉的英国作家——萨默赛特·毛姆》,向国内读者再一次引荐了这部自传体小说。此后,明静、薛相林和张敏生先后都在《外国文学研究》向读者介绍推荐了毛姆和他的作品《人性的枷锁》,并高度评价了毛姆对文坛的贡献,把他称作“英国现代文坛泰斗”“为民众写作的艺术大师”。这一阶段,国内评论界对《人性的枷锁》的关注并不及毛姆的其他作品,如《全懂先生》以及其他短篇小说。
(二)20世纪90年代:对主题与人物的重点关注
这一阶段的研究集中在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的研究上。在人物形象方面,学者的关注重点无一例外地都落在小说主人公菲力浦身上。研究者认为,毛姆通过对菲力浦这一人物的刻画,成功地再现了人在特定时代背景下以及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展现了主人公竭力探索生命意义与价值的心路历程,研究者也试图在主人公身上寻找毛姆生活与思想的影子。较有代表性的评论是李践的《毛姆〈人性的枷锁〉主题浅谈》和陈春生的《挣扎中的迷茫——从〈人性的枷锁〉看毛姆早期的人生观》。李践[3]认为,毛姆人生道路上的各种羁绊、束缚、矛盾与斗争都被突出、全面、生动地反映在其代表作《人性的枷锁》中。他还从个人与世界的矛盾、个人与人群的矛盾、个人内在因素之间的矛盾具体分析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陈春生[4]分析了人物形象塑造背后暗含的主题思想,即“生活虚无”,并将毛姆这种人生态度同莫泊桑消极、灰暗的人生观、叔本华的“生存空虚说”以及我国两千多年前老庄思想联系在一起。随后,丘雪帆和余柳娟在《〈人性的枷锁〉主人公菲力浦的分析》中,陈春生在《论毛姆的精神探索及创作观》和《试论毛姆小说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中,也就菲力浦虚无主义的生活哲学展开一番论述,将《人性的枷锁》概括为“对旧世界的坍塌和失去精神家园的惶惑”[5]的真实描述。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观点。其中,陈秋红[6]认为毛姆是在“从看似虚无的生活中,发掘人的真正价值”,这种虚无与存在的双重主题在《人生的枷锁》中体现得最鲜明。同样,陶萍[7]发现了《人性的枷锁》中另一种声音的呼喊——挣脱爱欲的精神枷锁。小说中的菲力浦就是这么一个为爱欲枷锁束缚的人。他孤独而不幸,倾尽全力追求真爱和幸福,却总是被爱和幸福所抛弃,并一次次陷入情感的深渊,在情感和理智的边缘挣扎,最终又面临新的毁灭。
(三)21世纪:多角度分析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学者从多个角度对作品进行深入探究。这一期间,它尤为得到在校研究生的青睐,出现了大批与此相关的硕士论文,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评析了这部百年力作。
这里重点介绍几篇从全新角度分析《人性的枷锁》的文章。首先介绍的是申利锋的《论毛姆小说创作的自然主义倾向》和董淼的《论毛姆〈人性的枷锁〉中的自然主义特色》。申利锋[8]将《人性的枷锁》中极度写实的自然主义风格追溯到19世纪法国三大小说家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福楼拜对前者的影响之上。董淼[9]试图通过对《人性的枷锁》的自然主义特色的研究,得出毛姆在创作中力求保持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眼光,同自然主义提倡主体态度的客观性、情感的“零度介入”及原汁原味地描绘现实的主张相符。她还强调,毛姆并未受自然主义理论的束缚,而是通过对生活冷静深刻的分析,突破自然主义理论的局限,大胆舍弃其不合理的成分,从而发展了自然主义。此外,评论家将焦点转向该小说叙事特征的研究上。朱慧芳[10]在《毛姆小说叙事特征研究》一文中,从《人性的枷锁》的叙述视角、叙述者功能、情节类型、功能性人物观以及心理性人物观这几个方面,具体阐释毛姆的叙事特点。比较研究方面有韩蕊的《张爱玲与毛姆小说比较研究》和丁俊香的《残酷与悲悯——世俗与虚无中相遇的张爱玲与毛姆》。她们都把《人性的枷锁》列为毛姆影响张爱玲创作思想以及“张爱玲体”文风的一部力作。这些新角度的批评分析推动了《人性的枷锁》在我国的研究发展。
三、结语
我国对《人性的枷锁》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不断拓宽的过程,从作品译介到简单的作品引荐,到对主题与人物的关注,再到对作品多角度、全方位的分析。但是,现有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研究还不够系统,比较零散,尚无优秀的专著出版。第二,研究受文学批评标准和方法的束缚,难以突破理论刻板的限制性。第三,当下的研究拘泥于“文学史家的偏狭与局限”。正如英国作家H·E·贝茨所说:“毛姆只是延续了一个传统——直接、客观地讲述故事,这大部分是源自法国的自然主义,所以毛姆的影响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深远宽广。”[11]
笔者认为,毛姆作品的意义在于它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但更在于它的趣味性和重读率,这部延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直到今天仍长盛不衰的作品,不是有些极端的评论家定义的“畅销书”或者“通俗文学”所能解释的。正如邵燕君[12]所言:“一个经久不衰的畅销小说大家吸引读者的魅力不在于情节而在于趣味,前者可能影响发行量,但后者决定了重读率,而重读率正是区别一般的流行作家和雅俗共赏的大师的标志……我们说的文学史其实只是批评家的文学史,还应该有一个文学史,是读者的文学史。”所以,研究这样一个备受读者喜爱、雅俗共赏的作品必定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