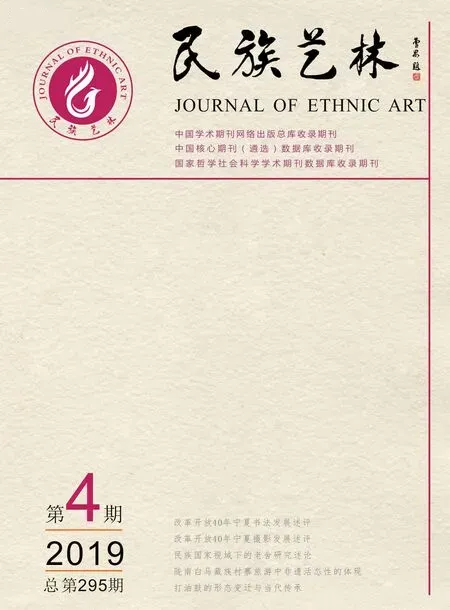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的喜“雀”文化解读
2019-12-30夏进宽
夏进宽
(红河学院 音乐舞蹈学院,云南 蒙自 661100)
缘物寄情、托物言志,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中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借助某一物体来表达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或对某一优良品质的追求体现,如汉族寄“竹”以示不屈不挠之精神,彝族视“虎”为先祖而喻本民族如虎一般英勇雄武。远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哈尼族,也在其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中,多次以“雀”比拟,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民族情怀、处世之道的借喻比描。
哈尼族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以下简称《聪坡坡》)是在红河两岸哈尼族群众中广泛流传的传统史诗,它以哈尼哈八(酒歌)的形式系统地吟唱了哈尼族祖先曲折而漫长的迁徙历史。[1]整部迁徙史诗言语朴实、形象生动、脉络清晰,全书长达5600行的史诗,以七个章节记载哈尼人从“远古的虎尼虎那高山”从“什虽湖”到“嘎鲁嘎则”,从“惹罗普楚”“好地方诺马阿美”“色厄作娘”到“谷哈密查”,最后定居在“森林密密的红河两岸”的一路由北到南的迁徙故事。
通读整部迁徙史诗,笔者发现哈尼族人在这一路的迁徙与发展中,始终有“雀”影随行,且意蕴深远。作为一个从游牧民族到山地农耕稻作的民族,哈尼族世代与自然为伍,通过自己的双手改造自然,在自然之中获取生存与生产的所需之物以谋求发展。“山雀”,作为森林中常见的小精灵,它已陪伴哈尼先祖走过千百万年,所以哈尼族人有着“有雀不停歌唱的地方,才是哈尼族人理想的居地”的质朴择居观。哈尼族对于各种类的“山雀”有着浓厚的深情,从迁徙史诗《聪坡坡》中的数十次提及,不难看到它不仅是哈尼族人对美好生活的寄托与表达,更是哈尼族人热爱生活,对生活细微观察的体现。
一、美好生活的象征
在《聪坡坡》的第一章中,在古老祖先最初居住的“远古的虎尼虎那高山”,龙子雀的身影便已出现。“远古的虎尼虎那,先祖的古今是这样讲:双脚的马鹿结队奔驰,大嘴的老虎到处窥探……山边的木姜子林里,龙子雀上下奔忙……虎尼虎那的飞禽走兽数不尽,虎尼虎那的游鱼跳虾数不完,绿色大地到处充满生气,哈尼先祖就出生在这个地方”。[2]《聪坡坡》的开篇,先祖出生的地方虎尼虎那,龙子雀以“上下奔忙”的活泼形象出现在这原始荒蛮又充满生机的地方。“龙子雀”的上下奔忙,烘托出哈尼族最早祖居地的勃勃生机。这一时期的先祖,尚未“人形化”,先祖还是“人种在大水里”“发芽在老林”的人类进化早期。“最早的人种是父子俩,布觉是腊勒的阿爸;布觉像水田里的螺蛳,背上背着硬壳,腊勒像干地上的蜗牛,嘴里吐出稠稠的浆”。在人类还未成“人”时,“雀”便已先人成“鸟”,出现在了虎尼虎那,在《聪坡坡》中,它是比哈尼祖先更早现世的精灵,有着比哈尼祖先更古老的生命,它和祖先出现在同地,将“虎尼虎那”点缀得生机盎然。
在全诗第四章中,因为瘟疫的流行,人口的大量死亡,哈尼先祖不得不离开“惹罗普楚”,为了可以找到像惹罗普楚一样美好的地方,头人派出七队人马找寻可以落脚安居的新地方,最后,一队人马找到了河水环绕的美丽平原“诺马阿美”。当这一队人马返回驻地,向高能的头人阿波阿匹(阿爷阿奶)汇报寻地情况时,好奇活泼的娃娃们叽叽喳喳地问道:“那里有没有花花雀,有没有惹罗山上的树多,有没有惹罗坝子好游玩?”[3]在哈尼族孩子的眼中,有“花花雀”的地方,才是可以玩耍的地方,才是可以承载童年欢趣的好地方。接着,寻新居回来的男人们听完孩子的问题,呵呵笑出心里的欢喜,高声回答:“水牛一样的宝贵儿子呵,让我告诉你们:那里的高山,像树林头发一样密,山下的坝子里,鲜花一片挨着一片,那里的小河边,乌黑乌黑的血娜雀不停唱歌……好儿子啊,等阿爸开出大田栽出秧,你们就能绕着田埂尽情地玩”[4]。从哈尼族男人口中,那个有血娜雀不停歌唱的地方,是可以给子孙带来欢乐的地方,更是可以开出大田、栽出秧的地方。粮食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稻谷作为哈尼族人最为重要的粮食,它的耕种生产是一切生产生活的重要保障,一个可以拓田栽秧,粮食宜长的地方,自然是哈尼族人最为理想的美好地方。而乌黑乌黑的血娜雀不停歌唱的地方,正是可以开出大田栽出秧的好地方。
当史诗来到最后一章,如神一般存在的哈尼族女英雄戚姒,在白鹇鸟的带领下,和族群来到尼阿多(今红河州元阳县),文中这样描写这个美丽的哈尼家乡:“再看山头和山箐,野物老实多啦:……披着黄衣的龙子雀,在树枝上跳上跳下。这边瞧过瞧那边,上方听过听下方,水淌雀唱的山窝,戚姒把它爱上。”[5]最后,戚姒和哈尼族人选择了这个有“龙子雀”活跃的地方长久定居,直至今日。
从上述史诗内容中可见,“雀”的有无,成了哈尼族人评判一个地方是否适宜族群居住的重要标准。雀的存在,让哈尼族人的寨子充满生机,让哈尼族人的生活变得热闹而美好。雀的存在,也决定一个地方可以从事农耕生产,这是族群繁衍壮大的标准。一只小小的山雀,承载着哈尼族人对于居住地的选择标准,更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
二、赐福神灵的象征
众所周知,白鹇鸟在哈尼族人的心中是至高无上的神鸟,它是吉祥的鸟,是哈尼族人的伙伴,更是引领祖先找到最后定居地方的精灵。但是,在史诗《聪坡坡》中,我们也可以看见雀的神性描写,它不仅是前来道贺的灵鸟,更是天神的替身。
在《聪坡坡》第四章中,当哈尼先祖定居诺玛阿美,选宅定基,新建家寨后,“高高的房子新落成,谷雀就来祝贺寨人,扇动着棕片般的翅膀,来把勤劳的主人叫唤”[6]。在这里,谷雀,是前来道贺的灵鸟,将祝福与美好送上。这是哈尼族人寄“谷雀道贺”来显示自己的寨子,是最适宜居住的理想地,是被神灵祝福的地方,是安居乐业的幸福地。安居乐业,是任何一个民族始终追求的理想生活状态,它是一切事业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传衍的根基。饱受瘟疫、战乱、迁徙之苦的哈尼族,在暂得安定后选址定居,自然期望新居可以让族人安居乐业、繁衍发展,所以“它物”的祝福与肯定才显得新居地理想恰当。“谷雀”的道贺,让哈尼族人的新家园住得踏实心安,因为在这里“谷雀”不只是单纯的“鸟儿”,而是自然与神灵的象征,是自然神灵对于哈尼族人居住地的祝福和道贺。
在第六章中,哈尼先祖定居在“谷哈密查”,二月来临,哈尼祭祀祖先,祭祀完毕后,在酒席间,咪谷(哈尼族人全寨推选的德高望重、深懂祭礼主持祭祀之人)阿波唱起哈八(酒歌,一人唱众人合唱的形式,在庄严的场合歌唱),哈尼族众人端起亮亮的酒碗听到:“快拿尖嘴的花雀,来做喝酒的天神,雀嘴插上黄饭,雀脚伸进竹筒,献过的雀头放进碗,它把喝酒的令来传,雀嘴对着哪一个,哪个就把碗喝干。”[7]在这庄严而隆重的哈尼族祭祖仪式后的席间,花雀成了喝酒天神,代替神灵享受众人的酒献。在“献过的雀头放进碗”这句话里,雀,成了祭献祖先的祭品,足见它已是不凡之物。“它把喝酒的令来传,雀嘴对着哪一个,哪个就把碗喝干”,作为传酒令的雀头,它是神圣美好的象征,所以,当它指向谁,谁就把神赐的祝福酒喝干。
三、生活的纤悉体察
因为频繁战乱、迁徙等历史原因,哈尼族没能形成自己的文字,千百年来,哈尼族的文化经典只能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世代沿袭,所以,在系统、完整且具有典型意义的口述史《聪坡坡》中,不仅有哈尼族的历史、祖源、风俗演变,更有诸多具有教导意义的生活哲理。这些哲理是祖先在生活中的经验所得,是智慧的体现,更是具有指导意义的人生百科。善于观察大自然中一花一物的哈尼族人,把人生经验与智慧,通过诸多通俗易懂的比拟化言语给予总结并传达灌输给子孙后人。在《聪坡坡》中,哈尼族先辈多次以“雀”比拟,以“雀”育人,从这些细节里,足见哈尼族人对于生活的热爱,正是因为这分热爱,才有他们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
在“什虽湖”,由于自然灾害而导致森林起火,浓烟笼罩四方,烧过七天七夜的天地彻底变了模样。“栽下的姜杆变黑,蒜苗像枯枝一样,谷杆比龙子雀的脚杆还细,出头的嫩芽又缩进土壤,天神地神发怒了,灾难降到了先祖头上”。[9]善于观察事物的哈尼族人以龙子雀细长的腿,比喻因灾害而无法茁壮的稻谷,形象地呈现出了天灾来临下的“什虽湖”,进而告诉族人和后人哈尼先祖不得不再次迁徙、离开的景象与原因。
“阿波(阿爷)哦,我从远方来到诺马,就像瓦雀歇在屋檐,腊伯怎会要哈尼的宝贝,只想等兄弟长大再归还”。[10]当哈尼族先祖定居在美丽的诺马阿美,过上“如香椿,不煮便香味四处飘散”的美好生活。诺马的美名传进腊伯的城中,腊伯率族群跋山涉水而来,在经过与哈尼族头人乌木阿波商量周旋后定居在哈尼寨边。腊伯后续经过多方巧言令色与行动,成为哈尼族头人乌木阿波的女婿,并且经过行计谋划,将象征哈尼权势的头人专属权帽绥带从阿妈那里诓骗到手,闻讯而至的乌木头人找到腊伯讨要权帽绥带。腊伯以“瓦雀”自喻自谦,贬低自己身份,表示哈尼才是诺马真正的主人,而自己和族群只是暂避屋檐下的一只小小瓦雀。腊伯最后以这样自轻自贱的比拟,蒙蔽住了乌木阿波,将哈尼族人的权帽绥带占为己有,最后发动战争,将哈尼人驱赶出诺马阿美。
在第六章中写道,哈尼先祖与蒲尼在“谷哈密查”发生了战争。哈尼先祖们在智勇双全的族群女英雄戚姒的带领下,将蒲尼罗扎杀得人仰马翻。“罗扎跳上快马,一直跑到海边,像被鹞鹰追赶的鱼雀,朝着刺蓬乱飞乱钻”。[11]在此,哈尼人以被鹞鹰追赶的鱼雀,形象比拟了被追杀而四处逃窜的蒲尼罗扎,更表现了族群女英雄和先祖们如鹞鹰一样英勇矫健之姿。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对自然界的周到观察,哈尼先祖怎能用到如此形象的双方胜败战况的比拟?
“好看的扎密(姑娘),心爱的妻子,你像河边的龙子雀,听见水响也飞上天”[12]。当蒲尼罗扎计划要将女儿马姒嫁给哈尼头人纳索时,纳索妻子戚姒已察觉此次联姻别有图谋,所以思量劝阻,但最后却换来纳索以“龙子雀”来形容妻子戚姒的小题大做和临深履薄的言行。
“‘比’就是比喻,是以乙物喻甲物,把两种或者多种具有相似点的事物互相作参照,以利于清晰说明道理或形象描写事物”[13]。哈尼族人在进行现象的比喻比拟时,以本民族的思维反思为切入点,选择事物的相似点为切入式的比喻,将各种“雀”象给予了充分的表达运用。古时的哈尼族,因为未能形成自己的文字,一些抽象的概念还未形成时,人们需要形象生动表达一些客观的事物时,比喻就成了不可缺失的认知事物的重要方法与手段。但是,在表达对象与认知对象相似点的寻找里,是一个民族对于周遭事物性格性情、物貌样式的细心观察与缜密概括,所以,《聪坡坡》中的以“雀”喻人喻物,正是哈尼族在与大自然的相处中,在对各种“雀性”“雀象”具有深刻认知的基础上,才可拥有准确、形象的比拟。在这份准确与形象的比拟里,是哈尼族人对于自然万物的热爱,更是哈尼族人对于自然、人性、生活的悉心体察。
四、结语
作为哈尼族传统的口头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讲述了民族迁徙的经历与文明发展史,5600行的文字间尽显先祖的智慧与磨难,也在这5600行的传说里,有着数十次的“雀”影出现。这一小小的“精灵”,伴随先祖从“远古虎尼虎那高山”到最后的“红河两岸”,足见哈尼族人对于“雀”有着特殊而深厚的情感。正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哈尼族人才会有对生活与环境细微入至的体察,也才会有将大自然的花鸟鱼虫引入生活的哲思。这样的比拟,除了具有通俗易懂的教育意义外,更有对先祖神勇的崇拜。这样的“缘雀寄情”和“托雀言志”,经过迁徙史诗在族群间千百年的口头传唱,无形中已起到了族群凝聚力、自豪感以及民族认同感的培养,更有着教育作用与价值,教会世世代代的哈尼族人敬畏生命、尊崇自然、珍惜和平,热爱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无独有偶,哈尼族地区广为流传的扇子舞、棕扇舞,以及红河州元阳县新街镇地区的哈尼族木雀舞,其起源传说均与“雀”有关,而且其舞蹈形态均是以身体为媒介,手持扇子为道具来模拟“雀”的生活百态,翩翩起舞。从事哈尼族舞蹈教学与研究的舞蹈圈中,在多年的资料引用与舞蹈编创中,均认同“白鹇鸟”在棕扇舞、扇子舞中的主导地位,认为跳棕扇舞是对哈尼族吉祥鸟白鹇鸟的赞美与模仿。可是笔者在哈尼族地区的田野走访与众多文献材料阅读中,发现了一大现象:一些学者将许多民间传说中“雀”的概念换为“白鹇鸟”,借白鹇鸟的“高洁神圣”来佐证自己之“作”。在云南,人们习惯性地把“鸟”称为“雀”,所以白鹇鸟是“雀”不假,但“雀”一定特指白鹇鸟吗?
“史书记载,人类最早食用的稻谷等粮食是在烧焦的鸟胃里找到的,由此追寻鸟类的踪迹找到了稻田。这一说法虽带有传说的意味,却也有迹可循。如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早期Ⅰ式陶盆上就刻有两组凤鸟纹样,一组凤鸟相对而立,守护中间一丛生长中的水稻;另一组凤鸟竞相环绕着盛有粮食的器皿,取祭祀丰收之意。为了不被温饱问题所困扰,人们总是祈求五谷丰登,并把希冀寄托在守护稻田的鸟类身上”[14]。哈尼族是一个信仰万物有灵的民族,其在史诗中虽将“白鹇鸟”奉为吉祥的鸟,但是白鹇鸟于哈尼族,不该是文化研究者对哈尼族全族皆宜的“图腾化”普及和强行扣帽。喜好多样性,崇敬多样性,信仰多样性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这个多样性中就该有“雀影”的出现。哈尼族迁徙史诗中喜“雀”现象的提出,可以为哈尼族民间仿生性舞蹈提出多种仿生对象的可能性参考与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