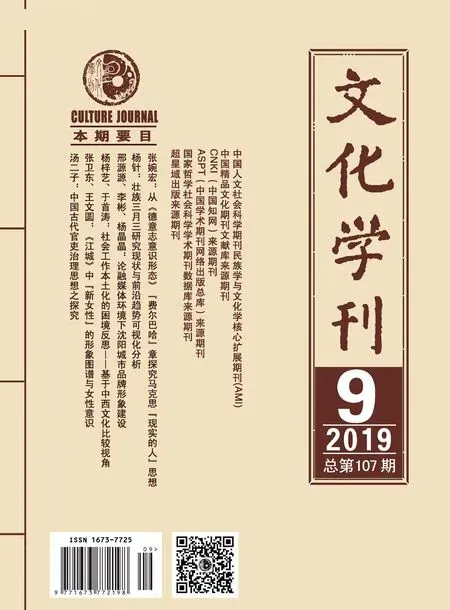柏拉图的美学构想
——审美文化的一种创意式解读
2019-12-27王泽
王 泽
一、美与真
真正的哲学王首先是一个正直向善的人,并且他应该是一个拥有审美力的人,不会被事物光鲜亮丽的外表迷惑,进而才能够不断追求世间万物的真实本性。真善美三者相辅相成,既是专注于真实存在的人应该具有的品性,又是立志于探求真实存在的人的永恒追求;同时,三者循环往复,后者以前者为基石,最终是为了达到使自己不断追求的外在实有理念内化成自身性格的境界,故我们可以说智者是真善美的统一集合体。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构想了一个由真正哲学王管理的国度,在这样的一个理想国度中,集爱智慧、求真、公正、有节制、胸怀宽广、无所畏惧等诸美德于一身的哲学王,为城邦制定如同哲学“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1]。为了确保哲学王是一位真正的哲学王,柏拉图进行了真假哲学王的论证:世间万事万物的本质是永恒不变的,真正的哲学王是真善美的集合体,因而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故那些被纷繁多样的世界模糊了双眼、看不清方向的人也就不能够成为哲学王——心智的盲者与感官的盲者没有任何差异,反倒有可能会导致更差的结果;假使是已经成为哲学王的人也不可避免会有变坏的风险,那么这些所谓的哲学王就违背了由美而善者从小所具备的天性,所以这些人也就是与假哲学王无异的江湖骗子。
柏拉图认为一位真正哲学王的养成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需要个人一生诸多要素的聚合才能够实现,如公正温良的天性、博闻强识的记性、热爱哲学的耐性等。“天性的不和谐、不适当只能导致没分寸,不能导致别的什么。”[2]然而,真理与有分寸的品性是一致的,故天性的不和谐、不适当会导致人从一开始接触哲学就偏离了正确的航向;健忘导致的是劳而无功,劳而无功最终危及穷索真理的积极态度,故良好的记性是使哲学研究进行下去的重要因素。这些内在要素是哲学研究的先天基础,有了这些先天基础还不够,后天良好的教育在哲学研究的过程中同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柏拉图看来,如此这般有好的天分、有热情同时接受了良好教育引导和良好环境熏陶的人是无可挑剔的,所以,他认为将整个城邦交给真正的哲学王来管理是理所应当的。
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时间的永恒性被视作唯一的真实。至真至善至美的不可达所产生的现实缺憾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被放大,心思最为缜密、意志最为坚定的哲学王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年老力衰、力不从心。
为此,在那样一个已经十分高扬人自身理性的希腊时代里,柏拉图也不得不将许多美好愿景的实现付诸于神力,不仅奉哲学为“女神”,同时希求“神力保佑”,希求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受到神的感化”……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憧憬。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完美的,或许这样的国度仅仅是一个意念之中的乌托邦、一个“神圣的原型”,而谁又能够真正担当得起描画、塑造这个“神圣国度”之艺术家的重任呢?
二、维纳斯与金鱼——关于“伤残艺术”与“病态美”的美学研究
可能会有人问,为什么将维纳斯与金鱼这两个毫不相关的东西放到了一起?它们有什么联系吗?两者都属于艺术品的范畴,是人类为了达到某种观赏心理欲望的满足而对“石膏”这个客体以及“鱼”这个客体所施加的艺术加工。然而,前者是人工抽象的艺术品,后者是人工生物的艺术品之外。我们还会发现两者的一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伤残美”“病态美”的观念以一种极为显著的方式展现在两者身上。
(一)维纳斯双臂的去处
米洛斯的维纳斯是人间爱与美的象征。她曾是希腊诸神的一员,后来她的形象被艺术家制作成雕塑,作为人性的偶像受到顶礼膜拜。如今的人们透过她那奇美优雅的面容以及缺少双臂却依旧灵动美妙的身躯,反观到了自身——是一种超越,亦是一种回归。
世人欣赏维纳斯之美的时候,总会有一个问题萦绕在脑海中,即她的双臂去了哪里。自1820年维纳斯雕塑被发现至今,众多艺术家都尝试过为维纳斯设计一双手臂,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人们发现,无论是左手拿着金苹果右手挽着裙子的姿态,是左手抚着头右手贴在腿上的姿态,还是其他任何姿态,都没有维纳斯断臂的姿态美。这种美是一种残缺的美,她美到极致,美到让人浮想联翩,美到无法再用后来人的审美取向去为它增添冗余的注脚。
维纳斯的断臂之美无法复制,据说是因为维纳斯在被创作的过程中就被截去了双臂。如今,人们已经无从考证那个年代创作者这一行为的意图。然而,人类本真的希望追根溯源的心理冲动往往会诱发自身不断地追问过去。
艺术品是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在创作材料上的投射,维纳斯的创作者首先是心中有对于一个至上美丽理念的追求,由此而生发出来对美神的崇拜。在那个由神灵支配人类精神世界的年代里,人们想要追求某一现实所不能够得到的理念的方式便是依附于神灵。于是,维纳斯雕塑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人们想要获得“美”的精神慰藉或欲望满足具体可感、可崇拜的偶像。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神圣的偶像,被截去双臂岂不是对神灵的亵渎吗?当然,这个问题在当今宗教功能和偶像崇拜被弱化了的时代里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人们关注更多的往往是维纳斯的雕塑有或无双臂所引起的审美感受有多么不同。
在这样的审美过程中,每一位欣赏维纳斯之美的人会同当初的创作者一样,把自己心理喜好的倾向投射到维纳斯的雕塑这个客体之上。同时,缺少双臂的雕像又给予观众无限的想象空间,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给维纳斯添加双臂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展现出不同的审美心理倾向。这便是“残缺美”的魅力所在。“残缺美”的艺术品既会让人产生出一种怜爱之情,又会给人的想象力以空间,类似于中国画中的留白艺术。想象力属于审美活动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它让观众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客观艺术品归为自身思想力的一部分,自身意愿也被加之于艺术品之上,于是艺术品发挥了既超越现实、又回归内心的作用。
健全、完美无缺的艺术品固然更能体现艺术家高超的技艺,然而观众的审美能力却被限定在了艺术家设定好的固定框架内,这样的作品因而缺乏深刻的“群众基础”,极易于沦为千篇一律的俗套,所以,“伤残”的维纳斯给予审美主体以健全的审美能力。
维纳斯的双臂去哪里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存在于每个人的思维里,正如同一千个观众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
(二)病态的金鱼
病态的金鱼实际指的是相对于纯自然的鱼种而言,金鱼属于病态的种类。在这里,人类又一次将自身的审美取向作用到了自然的客体之上,如此分析会显得略微残酷一些,毕竟未被改造过的金鱼的祖先是生命有机体,它们有自由生存和运动的方式,也就是鱼之所以为鱼的存在。
起初自在之物的那一批鱼类,接受了自为的人类爱美心理的强力意志的改造之后,成为符合标准的审美对象。形象一点来说,散养在水缸中的金鱼和为了达到目的而维持它们生命延续的人类成了一种稳定的主奴关系,金鱼只有生存在这样的语境下才有意义,金鱼的生命在最原初的状态下就被人完全地定义了。
人类依照自身喜好或是审美取向,将自身认为是美的概念投射到鱼类的身上:认为大眼泡是美的,于是那一批由于病变而生出大眼泡的鱼被保留了下来,它们的大眼泡基因因此得到了遗传;认为红色鳞片是美的,于是鳞片产生病变而成为红色的鱼的基因被遗传了下来;认为冠状的鱼头是美的,于是畸形的鱼的基因被保留了下来……最后,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水中那大肚子、大眼睛、金黄色、憨态可掬的金鱼。
正常的鱼类经过人类的改造之后成为金鱼,准确地说,是人类打乱了自然所谓“优胜劣汰”的基因遗传规律,进而使自身的审美活动在这样的过程中完美地完成了。对于最初那批变成金鱼的鱼类以及它们的后代金鱼而言,却好像是被受到了“原罪”的诅咒一般,变成了一种美的代名词,并且仅仅是美的代名词的这一名相而已,它们的实相早已不复存在。生存对于金鱼而言已无意义,人们有时甚至不会为了几条死去的金鱼而惋惜,即使金鱼被放归大自然的河流中,它们也只能沦落为食物链最底层被捕食的对象。
前述人类审美活动完成的这一过程,恰恰是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过程,一切都是为了发现美、发现真,一切又都是为了创造美、改变真。每当人类将自我意志的触角伸展到全新的自然领域,自然也就成了为了美的对象,因而自然也就丧失自我,变成对自身而言“病态的美丽”。
或许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视角重新解读这句话:世界上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世界上的美只是用来让我们去发现的,并且仅仅是发现就足够了,一旦施加人为的作用力,为它添加上人类的价值取向,那么真正的美就永久地被剥夺了。
三、寻“美”,人类永恒的课题
其实,有关“病态美”的例子还有许多,如中国古代女性的“三寸金莲”“楚王好细腰”现代的整容以及高跟鞋等,都反映了人类想要追求美的价值取向从而施加改造自然状态的作用力这一现象。
通常意义上讲,纯自然状态下的生存对拥有理性、善于反思的人类而言缺乏意味。纯自然的生存状态是指生命体维持正常身体机能的行为活动缺乏个体意志下的目的性,缺乏主观选择性,不存在做、不做或是如何做的区分,一切行为按照自然规律稳定地运行。人类运用理性反思这种纯自然生存状态会发现,纯自然状态下的活动仅仅是机械性的循环与重复。由纯自然的生存方式表现出的纯自然的生物状态也是单调乏味的,于是人类开始寻求一种区别于正常状态的异常状态,异常状态与正常状态形成的反差造就了人类特殊的价值取向,进而人类开始筛选符合这种价值取向的生物状态,对同类是如此,对其他种群甚之,这个过程便是寻“美”的历程。
何为“美”?美学中研究的“美”并不局限在人人都认为是被看起来能够引发身心愉悦的、所谓真正美的事物上,美学的研究在于一种对原有价值的评判、扬弃,所以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美学,新生的时代都在力图打破旧有时代的价值观。“伤残美”与“病态美”也属于时代的价值观,它既是对原始常态美的价值观的破除,也是常态美的价值观到达一种顶峰的跌落。病态美起源于常态美,当常态行至极端之时,由于量的巨大,便不再是常态,而是常态的极端之态,是为病态[3]。维纳斯与自然鱼,在起初人类决定对它们施加改造之前,完整的维纳斯雕塑与自然鱼身上还都散发着常态美的光辉,但或许是由于缺乏个性和异态美感,于是艺术家们造就了“残缺”的维纳斯以及“病态”的金鱼。
接下来谈谈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品的动机。可以说,艺术家创作一件艺术品是为了追求一种偶然的契合:心目中关于美的概念无限趋近于至美的境界。这种偶然的契合性的产生并非源自于刻意,而是源自于灵感。灵感,也就是非刻意、非纯理性,它是情感与理性的复合物,是大脑中原有的知识积淀偶然性的思维组合。通过灵感产生出的作品是纯粹的,因而也是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种最高境界的产生是真实内心心理活动的描摹,也是情感没有受到其他因素(如理性)抑制所表露无遗的时刻。断臂维纳斯的雕塑也许就是这样产生的,抛开人性的残酷性不谈,金鱼这类艺术品也是如此。
何为追寻“美”的目的?由于人类是理性的动物,长期的理性生活会使其精神处于一种过度紧张和亢奋的状态,紧张和亢奋的状态抑制了人类生发出伟大的艺术品来反观自身。由感性和灵感产生的艺术作品是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它可以让人类去感受和亲近世界,而不是长期以一种思考和探求的方式看待世界。这种视角可以缓解过度运用理性引起的思维亢奋,进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人类因长期运用理性而积累出的猜忌、多疑、焦虑等一系列社会负面情绪。
现实中的人无法摆脱周围的环境、无法不建立起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而独立存在,这也就意味着人无法做到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真实存在中去,必然会涉及到人事与人际。参与了人事与人际,也就被卷入到他人的心智当中。当各自有别的心智发生碰撞,分歧与偏见就容易产生,这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根源。化解人类矛盾的契机在于,不论人类心智如何不同,世间真善美的理念是恒常不变的。真善美的理念不因人类的思想方式产生变化,把握住世间不变的理念,有助于秉持自身恒常的品性。正如柏拉图所极力提倡的:追求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追求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有助于扩展纯然的人性,有助于发觉纷繁事物背后的纯然理念,面对琐碎的人和事也能够保持镇定自若、波澜不惊的心境,并且使自己的心智不断趋向于纯然的理念,最终成为塑造自身人格的艺术家。
自然即是真,现实的缺憾并不代表不美。看到世间的缺憾,却依然追求至善的境界,是在将集真善美为一体的哲学王奉为偶像。人类探求世间的真实存在可以激发出内心趋向至善的情感,理性反思加上感性调节,方知美的理念恒常不变,异态美和常态美都从属于美的范畴,美在维纳斯与金鱼这里是完全等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