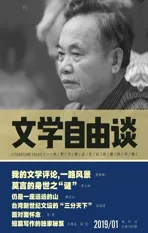我的文学评论,一路风景
2019-12-27黄惟群
□黄惟群
从不信开始
从来只想当个作家,没想到,有一天,也会写评论。
第一篇评论,评的是余秋雨的《借我一生》。
当时正想尝试写个长篇,觉得我父母双方家庭均很特别,太多与中国历史命运紧密相联的故事。朋友介绍说,《借我一生》或可一读,以为参考。曾经读过《文化苦旅》,有份好感,于是,找来,认真虔诚地阅读。
开始,仍被余秋雨的才华吸引,书中所述,也基本相信。但读着读着,变了,越来越多的不信;读到后来,连先前信过的,也都不再信了。
自传体小说要尊重事实,要有诚意。然而,这里太多装腔作势、涂脂抹粉、强词夺理,始终在狡辩、吹嘘、炫耀、自我塑造、自我拔高。人都会有错。有些事,良心上过不去,又无法直面,可回避;但既然提了,就该老老实实。
也是从这本书中发现,余秋雨的写作不像他自以为的那么好。优秀作家的文字,要“放得开”“收得拢”“扬得起”“沉得下”。可他的笔,永远在“放”,在“扬”,没有“收”与“沉”的一刻。读他的文章,耳边始终听到一声拖得长长的“啊——”。
写作至关重要的一点,即是分寸感的把握。作家水准越高,分寸感就把握得越好;而这一点,恰是余秋雨的弱项。
《于细微中看余秋雨》全文约一万字。写好后,文友推荐给上海一家报社。主编看了说好,但不能发,说余秋雨太难缠;却推荐给了《山西文学》,不久刊出。可惜,被删了不少。好在那时已有网络,我就将原稿贴上了网。
余华和他的《兄弟》
余华被誉为中国第一作家时,我已出国。他的作品看过些,没觉得那么伟大。比如《许三观卖血记》,感觉干瘪,人物没皮没肉,只有几根骨头几根筋。有人认为写出了历史的民族的什么什么深意,但我实在看不出。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个小镇人用小镇人的眼光看小镇上的人和事。
《兄弟》是余华沉默十年后的作品。当时的宣传铺天盖地,他自己也很高调,认为《兄弟》是他最伟大的作品,乃至是当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品。这使我产生强烈的阅读愿望。于是,一方面,托人从国内带书,另一方面,把能找得到的他的小说都找来一阅。等拿到《兄弟》,便迫不及待地一字一字细读。读着读着,却叹起气来。
一个作家,看清自己不易,看清另一作家及作品则不难。写作过程中,每个作家都会碰到并解决过各种几乎相同的问题。因碰到过,解决过,看另一作家的作品,一眼就能看出问题,能看出这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得好不好。
《兄弟》的阅读感受是:没咀嚼没回味的文字,不厌其烦自以为是的重复,没有层次的递进,人工制造的细节,不合理不可能的情节,不必交代的交代,不好笑的笑话,不幽默的幽默,孩童式的兴趣,低品位的审美……
对《兄弟》的评论,分了几个标题:“难以置信的浅薄”,“几个写作中的基本问题”,“无处落脚的强度叙说”,“对丑陋和残暴的酷爱”,“余华的窄门”。
举个小小的关于浅薄的例子。小说一上来,大写小孩厕所里偷看女人屁股。一个被偷看过的,竟当着满街人对丈夫大喊:“我的屁股给他看到了”,“我的屁股从来只给你一个人看,现在被他看到了,这世界见过我屁股的就有两个人了”。世上会有一个正常女人在大庭广众这般喊叫?而这个孩子,则因此得福,镇上男性公民纷纷自掏腰包为他买三鲜面,就为听他描述一个叫林红的女人的“真肉屁股”,甚至派出所警察也“闪亮着通电灯泡似的眼睛”,想从这小孩嘴里打听那个屁股……浅显得让人不敢相信。
《兄弟》中,作者花了大量笔墨写血,写粪便,写蛆虫,写月经,写打人杀人,写割死人头……总之,写常人感到恶心的一切,不惜生编硬造、强行插入。
作者的用心很明显:往丑里、恶里使劲、拼命地写,写到读者因丑、恶而反胃,因反胃而难忘。这方法其实是学来的,是那个时期文学艺术领域的世界倾向:美的、善的写多、写厌了,想出新,没好招,便反其道而行之,盯住丑的恶的,穷凶极恶地写,刺激感官。
余华如继续他的现代派,继续他擅长的从事物中提取核心,强化、放大、推至极点的写法,那么,即使他不深刻,也会有人为他找出深刻。不幸的是,他对自己的先锋称谓已享受得不耐烦了,想将传统写作领域一并占领。然而,“现代派”可蒙人,可护短,可天花乱坠无凭无据地自我解释、吹嘘,可云山雾罩地把人说得云里雾里,可因自己的不懂不通,把人说得不懂不通并以为高明;但现实主义不行。现实主义写作有一点很过硬:不管是谁,只要沾上,才能高低,一目了然。因为,现实主义是有确切参照物的。
《读〈兄弟〉,看余华》一文完成后,立即贴上一个文人扎堆的网站。我是准备被骂,甚至被围攻的。余华太有名,拥有太多“无可商榷”的拥戴者。
想不到的是,文章贴出不久,看到了第一条留言,是位颇有名气的作家、学者兼评论家写的:
鼓掌,献花。
难得一见的杰出批评!
文字本身,以及对文学的理解,都足以做被批评者的老师!
强烈建议有品位的国内名报大刊全文发表……
不敢当,但万分高兴,感谢他给予的信心和力量,非常感谢。紧接着,又一条留言:“黄兄竟敢挑战余华……”这话挑明一个事实:余华地位实在太高。
不久,文章在《山西文学》刊出。可惜,又删了不少。所幸后来《海上文坛》再发一次,上海《劳动报》还为此做了专门报道,标题很醒目:《余华新年遭遇最凶猛批评》。
有意思的是,评余华和《兄弟》的文章,曾给几个文学界的朋友看过,其中一个表现得颇为不屑,说:评《兄弟》的文章,我们这早已有了,还专门出了本《给余华拔牙》的书。不少人像这位朋友一样小看海外写家。
都不好意思告诉他,《给余华拔牙》一书的第一篇,就是我的《读〈兄弟〉,看余华》,一字未改。同样一字未改的,还有《小说选刊》全文转载的《来自余华的启示》,是从网上转来的。
余华批评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文坛第一次对咄咄逼人的现代派文学做出了集体反弹,从根本上动摇了它们的长期“统治”。大家开始怀疑、反对,说出自己的心声,不再一如既往地俯首称臣。
即使今天,我还坚定地认为,现代派文学中很多很好的元素,应被高度重视,学以致用。
王安忆作品论及《天香》批评前后
我写的评论中,有关王安忆的,特别值得一提。“王安忆现象”非常典型。
来澳后,陆续重读的新时期文学作品中,就有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小说是用现代派手法写的,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很高,也是作者本人自认写得最好的中篇。
鲁迅有段非常精彩的话,说:“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集外集·通信》)
王安忆自己说好,著名评论家都说好,还会错么?他们田地就有二百亩。
在我看来,本质上,王安忆是个没丝豪现代派气质的彻头彻尾的传统写实主义作家,对现代派领域的涉足,在她是个根本“错误”。
当时,却不想公开写文。
不久,《启蒙时代》出版。一如既往,只要是王安忆的,必有一场有组织有纪律的追捧。这不关我的事,我只关心写作,只关心作品好坏。我很想看这书,因为和她是同龄人,想知道她是怎么被启蒙的,她的启蒙中能看到多少自己、多少那个时代。
然而,书中对我所熟悉经历的那个时代的气氛描绘、特征捕捉,几乎谈不上准确。整本书,像个好学青少年留下的日记。太多认识了谁、读了什么书、做了什么事的记录。作者脑中,只一段生活、一些人物,想到哪写到哪,完全没结构,没剪裁,没整理,记忆中听过、看过的,不分青红皂白统统一网打尽。只有一把米,却要烧出一锅饭。
《启蒙时代》和王安忆另一本书《69届初中生》,写的是同一年代,却远不及《69届初中生》。《69届初中生》中有一份纯、一份真、一份自然、一份亲切,有准确传神的人物,有和心态绝配的细节。《69届初中生》中有的精华,《启蒙时代》中统统没有,《69届初中生》用过的细节,《启蒙时代》倒有拿来再用,却用得索然无味。
《启蒙时代》还严重暴露了王安忆写作技法的单调、刻板、简陋。她的笔下,难以穷尽地出现一个个人物和人物携带的故事,一个没讲出所以,又开始另一个。所有人物,都有个千篇一律的模式——一张长长的家庭背景清单:兄弟姐妹、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亲戚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朋友……不是一笔二笔,是成段成章。还有就是人物的长相、穿着、眼神、皮肤的描绘。一个重要作家,“手法”单调乏味如此,也算穷尽想象亦难及。
为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王安忆,我把找得到的她的小说统统找来,一本本认真阅读,在每本书的边上,密密麻麻写满批注。重读这些批注时,大吃一惊:它们大多差不多。说明什么?说明我已失控,越看越火,说过的想说,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次比一次说得尖锐;说明王安忆写作上的毛病,是顽固不化、反复出现的:啰嗦、混乱、笨拙、没逻辑、没结构、七拉八扯、无趣无味、不懂装懂、冒充高档……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出自一个根本问题,即心中没有一个成熟作家对世界、对生活应有的稳固成形的思想感情体系。“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心雕龙·原道》)。“心”不“生”,何以“文明”。
《一个缺少自我的作家——王安忆作品谈》一文谈了她六篇小说,评得细致,毫不留情。重读一遍时,又犹豫是否太狠,故删了不少。后来又觉其中一些删了太可惜,会使文章不足以反映我的饱满感受;扪心自问,所说句句真话,出自真性情,故又补回。
写过此文后,自觉该说的都已说完,这辈子再不会评她任何作品。然而,许是老天安排,后来又看了她的《天香》。
《天香》刚看完,接到一作家朋友电话,问在干吗,说在读《天香》。问写得怎样,叹而道之:差不多被搞疯,脑神经有崩裂感。问为什么,说:不管文字语言、结构布局还是思维逻辑,几乎没一样通顺;她的没条理是真没条理,她的简单是真简单,她的堆砌、生搬硬套,那是疯狂的堆砌、疯狂的生搬硬套。我还说:这部作品,是王安忆将她所有写作毛病集中起来进行的一次加倍发挥……当然,也说了,王安忆确有写得不错的作品,尤其早期。朋友听后大为感慨,说她一直不喜欢王安忆的作品,读不下去,却不知为何这么多人说她写得好。那天聊到最后,我说准备写篇《天香》评论,朋友问,你敢把刚说的话写进文章吗?我说,为什么不敢?
比如,评《天香》的第一句就敢这么写:“读王安忆长篇小说《天香》,简直有种大脑神经绷断的感觉。”
写这篇《〈天香〉算不算小说》,已失去写《一个缺乏自我的作家》时条分缕析的耐心,写了八九个小时,一气呵成,都顾不上去看一下自己写过的批注,只想分秒不停地让心中积郁、脑中思索,连同胸闷气堵的感觉痛痛快快一泻千里。
《〈天香〉算不算小说》一文指出了《天香》的三个“巨大”的、文学创作万万不能容忍的毛病:严重的比例结构失调,严重的缺乏灵性、体悟的资料堆砌,严重的写作技能的简陋、低下。小说中,三分之二的篇幅,是与故事基本无关,甚至完全无关,不够一百也差无几的故事穿插和难以例数的物象介绍;太多没经消化、听来看来、现买现卖的资料;至于写作,已到难以置信的地步:用笔单调、写法机械、多有语病,创作思路可被百分之百准确无误地预测。
这样的小说,被作为优秀作品推崇,受害的不只是王安忆,更是整个文坛。推崇的错误理由,将严重扰乱大众视线,增添困惑,使大家看不清真正的文学标准,分不清优劣,迷失掉方向。
《〈天香〉算不算小说》一文在《文学报》刊出后,我将文章传给众多文友,有作家,有批评家。有的传去的是原稿,把发表时被删除的部分,用红色做了突出显示。
很快,回信一封封来了。这里选几段,摘录如下——
痛快痛快!终于有人敢说实话了。王安忆最多能说是个文字匠而已。她的文字没任何感情,是个三流技术工。
现在批评界说好话的太多,说些批评意见,往往不敢点人,尤其不敢点王安忆这样的成名作家。红笔删掉的地方,够猛。不过目前现实下,真的很难发。文坛亦江湖,文坛的造神运动不自今日始,只是至今仍在流行。
一口气读完,的确是人所未言!《文学报》刊发这篇文章,看来是投下了一块大石头啊,您也要准备好迎接浪涛,呵呵。
大作收悉,果然够“狠”,但鞭辟入里,我看了觉得身上也冒冷汗……
报纸到了,我还没看,朋友就发短信叫我看,说《文学报》很久没这么好看的文章了。我放下手头的工作拜读了。写得很痛快!看得出,您是真受不了了,所以句句打在“七寸”上。
看了《天香》批判,觉得毒辣,酣畅,过瘾。您形容她推着载满卡片和笔记本的手推车走来的形象,让人笑喷了,可又多么本质。她的最大毛病就是叙述上的恋物癖,与人的心灵和意志无关的诉说欲。
红字被删,在上海语境可以理解,但很多妙句,删了着实可惜。
祝贺您写了一篇爆炸性的文章,不知有何反馈?会有不少气急败坏的反响,我猜。
当然,百倍千倍这样的真实看法,我看不到,大家也都看不到。这就是中国现实。看得到的是什么?文坛先后开了两次《天香》作品讨论会,规模很大,特别是上海那次。有作家朋友来信说:“讨论会就是针对你那篇文章的,为的是‘肃清流毒’。”
《文学报》还专门刊登了反驳文章,是篇典型的当代评论,空话大话套话成堆,只有两点说得明确:《天香》可与《红楼梦》媲美,因为它表现了巨大的“悲悯”;曹雪芹没看到历史的归宿而王安忆看到了。后来,在一篇讲稿中,我曾予以回复:“悲悯”如果是评论一部小说的尺度,那么,菩萨是最悲悯的,菩萨写的小说,怀有菩萨心写的小说,就是最好的小说;看到归宿的作家写的小说一定比没看到的写得好,这逻辑如成立,那就不单王安忆比曹雪芹写得好,每个活着的作家写清朝、明朝、宋朝、唐朝,都比曹雪芹们写得好,因个个都已看到了“归宿”。
《天香》的批评,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文坛神经,带来一定的反省,其潜移默化的作用,相信不久将会看得更清。
《繁花》批评的风波
金宇澄的《繁花》及其反响,也是个特别的现象。
不断听人说,《繁花》写得非常好。然而,若问说这话的人看过没,所有的回答不是“没看过”就是“没看完”。
我是直到《繁花》得了“茅盾文学奖”,才看这部小说的。为学习,为了解,都必须看。看着,觉得有话要说,看完,觉得不能不说,于是,写了《我看〈繁花〉》一文。
毫无疑问,《繁花》不无优点,但完全没好到“众口一词”“没商量”的地步,其中错误或说不足,实在太多、太大、太明显。
一部完全没有结构的小说,材料没取舍、没安排,想到哪写到哪,无轨电车乱开,人物形象模糊,事理情理文理欠通,文字别扭,节奏疙瘩,叙说啰嗦,颠三倒四,思想浅薄,感情缺失……所有这些毛病,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就是“堆砌”,和王安忆一模一样。
《繁花》的写作方法分外简单。作者脑中有个仓库,其中林林总总很多收集,所做的只是不管不顾地将所有收集统统写进小说。故事一个接一个,故事中夹故事。
这样的小说无需作家。
作家写作不仅需要感性,还需要理性。所谓理性,不论整篇,还是整章、整段,都需清楚,为什么这样写,目的是什么,作用起到没有。作家笔下的每句话每个字都该是有用的、必需的,绝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写出的文字也不是想放哪就能放哪。
《繁花》中一个重要部分,即性。不错,两性关系的确吸引人,生活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两性关系之所以动人,除了“性”,更重要的是“情”。《繁花》中,写了这么多男女关系,却没写出过一丝一毫的“情”。作者始终站在故事外,始终用眼在看这些男盗女娼、偷鸡摸狗,仅仅用眼,而没有用心。书中男女不分昼夜地说“下作话”、做“下作事”,这些“下作话”“下作事”,既无美感,又不动人,好似看段子,看古今中外性事手册。
有人统计,《繁花》从头到尾出现一千五百多个“不响”,阿宝不响,沪生不响,小毛不响,连婴儿也不响……多时,一页纸上有八九处“不响”。据说,这些“不响”,有人以为拥有丰富内涵,是被用来体会的。或许,它们中的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确实表示沉默、同意或不同意——且不说这样的表示太起码,即便起码的“不响”,书中有得也太有限。大多时候,它们毫无意义,完全可跳过不看。
作家非作家、高明非高明间的区别,往往在于能否写出“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文学的微妙,往往体现在作家写出了常人能感到的却表达不出的。什么都“不响”,是将作家该有的能力与职责推向负数。小说中,人物的心理、性格、形象,最合适的,就是在这些“不响”的位置,通过语言、语态、表情、动作,或细微、或巧妙、或直接、或婉转地完成。能不能准确写出被“不响”所掩盖的内容,是作家的能力,尤其在写实主义手法中。
文章中,我还谈了思想深度、人物形象等问题,谈得很具体。
评论写好后,传了几个作家、评论家,都是名家。深感惊讶的是,所有人的回答像通过气般,几无区别:这本书,我努力了好几次,拿起又放下,怎么也读不下去,实在不知好在哪,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说好。
文章在我的博客和朋友圈贴后,到处听到、看到的话也都几乎一样:实在读不下去;几年了,至今还没读完。即使今天,谈到这本书,人们还不断这么说。
为什么读不下去?就因写作中毛病太多,文字不能顺利进入读者大脑。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叙说、这样的文字,对输送感觉是起到破坏作用的。
人类总结了一千多年的那些写作方法,所以成立,因其切实可行,确实能制造、传递感觉。《繁花》“制造”的感觉,不是一人两人接受不了,而是太多人接受不了,连最内行的作家、评论家,都接受不了。
然而,小说得了最高文学奖。
可谓历经艰难,我的评论最终刊出,立即引来轩然大波。这“大波”,值得大家认真一看,认真一想。
一个曾经好像火过的上海评论家,磨刀霍霍,杀气腾腾,在网上对我进行了连续三天的“驳斥”。这里摘上几句,大家看看,开开眼界——
今天我要拿黄惟群先生开刀了……他哪里配来谈《繁花》更不要说配说上海。
我靠!……反驳黄惟群一类的粗人我必须使用粗口……
黄惟群不过是一只嗡嗡嗡的蚊子……必须拍死它。
我不怕肮了我的手,我决定来收拾这条疯狗。
他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一个笑话,他的每一个辩驳都是无理取闹……
语无伦次的黄惟群在他这篇令人作呕的文章中……
出言不逊动机阴暗语言粗鄙愚狂蠢笨下流龌龊,这种下三滥文字……
相信吗?这竟是一个评论家写的所谓驳斥文字。古今中外,恐怕罕有堪与之匹敌的文人之文字。
这还不算,他还要“表扬与自我表扬”。他说,他当时只是读了《繁花》的“卷首、中腹与尾声”,“即起身拍案道:此乃经典也!”“彼时《繁花》尚未面世,《收获》杂志已经准备隆重推出了……随后,吴某主持的《上海文化》连续发表了……四篇重要评论。”
这段话的内涵其实很浅显:《繁花》的面世,他是第一功臣,《收获》只能屈居第二;他“吴某”把持下的杂志,发四篇“重要”评论,够给力,讲义气;更厉害的是,他只读了《繁花》前中后三部分(莫非他也觉得不堪卒读?),就一拍桌子,断言这是部经典。
——介绍这些,想让大家看清一点:他和我,一个是写评论的,一个是骂大街的。
之所以骂街,是因为他自认为《繁花》是他发现并捧出的。
我评《繁花》的文章,发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羊城晚报》,发了原稿三分之一;第二次是在《文学自由谈》,发了原稿三分之二;第三次发在《雨花》,全文登载,一字未改。
说明什么?说明这年头的文坛,害上“老大狂想症”是你自己的事,别人没有义务管你大不大、二不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