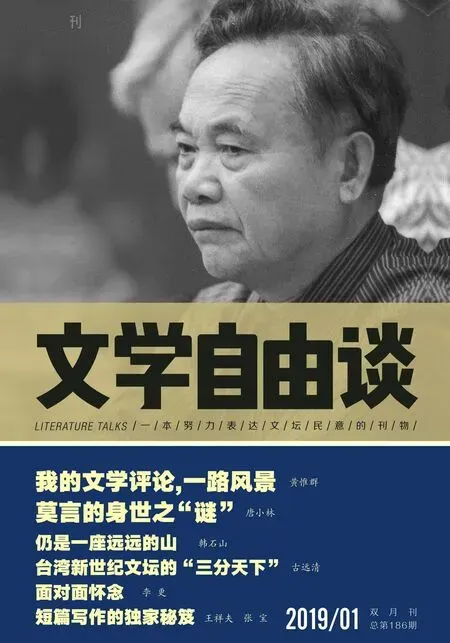仍是一座远远的山
2019-12-27韩石山
□韩石山
能在王府井大街上,一个这么高雅的地方,讲讲徐志摩,是我的荣幸。有这个机缘,是商务印书馆出了《远山》这么一本好书。这本书,还有个副题,叫《徐志摩佚作集》。这种书,平常都叫“佚文集”,而他们叫“佚作集”,想来是考虑到里面收有好几种体裁的作品,不全是文。这是一种慎重,也是一种多余。
这本书是我介绍给他们出的,前面有我的序。序里除了对编者给予称赞外,还说取名《远山》,似乎在暗示我们,徐志摩仍是一座远远的山。
我甚至想过,当年徐志摩去世后,陈梦家给他编了本诗集叫《云游》,用徐志摩的一首叫《云游》的诗做书名,也是有深意的,意思是,志摩先生只是上云端游玩去了,不定哪天就会回来。那是1932年。过了八九十年,再出一本集子,又用了一首诗的名字做书名,叫了《远山》,意思更深些。会不会是,徐志摩故意留下了这么两首诗,让后人给他编两本书,一本说我走了,你们好好地活着吧;一本是说,我还惦念着你们,在远远的山上,而我们呢,只能远远地看着他,走呀走,总也走不到跟前。
在当今学术界,无论从哪方面说,我都算是一个对徐志摩有研究的人,写过《徐志摩传》,编过《徐志摩全集》,至今仍关注徐志摩材料的发现。若有人问我,现在的徐志摩研究,是个什么水平呢?我只能说,仍在低水平上徘徊,绯闻逸事,才子风流,基本上不知此人的真面目。写起论文来,硕的博的,论起革命文学家,这个是人格如何,那个是思想如何。你见谁写文章,说徐志摩的人格如何、思想如何?最普遍的评价,这是一个优秀的诗人。我以为,这样的评价,对徐志摩这样的人来说,跟说他是个人,是个男人一样,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他不是个优秀的诗人,莫非是个平庸的诗人?
不说气话了。且将徐志摩跟他同时代的三个人作个比较,就能大体估摸出此人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坐标位置。我要说的三个人,都是跟徐有过交集的,一个是郁达夫,一个是胡适,一个是鲁迅。他们与徐的关系,分别是同学,朋友,对手。
先说郁达夫。郁和徐,是杭州府中学堂的同班同学,略称“府中同学”。徐是1911年春天考上,是念完了的。郁也考上了,嫌学费贵,又考到嘉兴府中学堂,念了两个月,嫌路远又转到杭州府中,没念完,辛亥革命爆发,再没回来。1922年,徐志摩回国不久,郁也来北大教书。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两人交往甚多。徐死后,郁写过两篇文章,表示怀念,主要有两个意思,一是称赞徐中学时学习好,虽不怎么用功,却老考第一;二是赞美徐与陆小曼的爱情,仿照电影《三剑客》里的说法,说他就是马上要死,也要做一篇伟大的史诗,颂美志摩和小曼的爱情。郁是才子,很早写小说,获评甚高,旧诗尤其好,被人推为现代作家第一。而徐,一点也不次于郁,新诗可称第一,散文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从思想观念上说,郁留学日本,新旧思想混杂,娶王映霞为妻,视为纳妾,多次称王为“王姬”。徐接受的是欧美的伦理观念,开中国文明离婚之先河,善待前妻,视为好友。大体上说,徐与郁可打个平手,徐略胜郁一筹。
再说胡适。胡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极为尊崇,有“现代孔夫子”之誉。胡与徐是好朋友,徐视胡为大哥。但平心而论,徐有三点超过了胡:一是学术训练。胡有博士之称,但学校的经历,却乏善可陈,在国内上过中国公学,考上留美官费,到美国在康乃尔大学,先学农科,后转文科,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徐就完善多了,国内在北京大学,学的是法学;到美国在克拉克大学,学的是史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的是政治学,毕业论文为《论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到了英国,跟上拉斯基学过经济学,跟上狄更生广泛接触英国名流,参加过英国的基层选举活动,为工党拉票。作为一个社会学者,徐的训练更全面些。二是见识上,有的地方徐比胡高。1926年胡经苏联去英国,路过莫斯科停了一两天,便著文赞美苏联的教育成绩。徐在《晨报副刊》发了胡的三封信,同时给以批评。气量上,也是徐比胡大。新月书店刚成立,胡一时气不顺,要抽出自己的股份,徐劝后收回。三,文学才华上,徐明显高于胡。胡的《尝试集》,只能说是新诗胎儿期的牙牙学语,而《志摩的诗》,则已朗朗成诵。
末后说鲁迅。鲁迅的最大成绩,是小说,徐是新诗,在这上头可打个平手。鲁为人称道的是杂文,徐有许多社会问题的随笔,实则是杂文,也别有风采。鲁中年之前,在社会理念上,看不出什么高明的地方。徐则不然,尊崇科学与民主,办社团,办刊物,为中国社会的进步着实努力,从不放弃。他最初的理想,是要做个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开国元勋),一直到死,都是个赤诚的爱国者。鲁曾作诗,讽刺徐,颇狠毒,徐未回应。再偏向的人,怕也只能说——不是说而是感到,在徐的毫不在意的宽容面前,鲁是个颜面尽失的败北者。鲁的晚年,信奉共产主义学说,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这是鲁的光荣与进步,不可多说什么,但我们总可以说,徐也是一个有理想、为社会负责的文化人。
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到《远山》这本书上了。
看书,要会看。不要老想着学知识。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那是学生娃说的。小学生是学生娃,中学生是,大学生是,硕士博士,都是学生娃。娃就是还没长成人。三四十岁的人,工作了的人,看书要抱着欣赏的态度,才能轻松自如,也才能坚持下去。这世上唯一能坚持下去的事,只有玩。寓教于乐,寓学于乐,就是要把学习渗到你的骨子里去。能从欣赏中得到教益的书,才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也才是真正的好书。
前些日子,在现代文学馆参加一个新书发布会。会上,一个常去日本的学者,很是赞赏日本的“口袋书”,说是价廉物美,便于携带,如何的好。说我们的书太贵了,又是精装,又是塑封,如何的贵,让人买不起,看不上。轮到我发言时,我委婉地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我认为,书的装帧设计,一定要贵相,要讲究。好到什么程度呢?要好到平日插在书架上不丢份,过年清理杂物时,舍不得卖了废品。不说内容了,光封面设计,整体制作,这本《远山》,也是达了标的。你看这色彩,多柔和,多入眼;这设计,多简洁,多典雅。听说设计者是吕敬人先生的学生,看来这学生没白当。
内容,就更不用说了,是我看上眼,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不是事中人,绝然想不到,这些年来,研究者们翻腾出这么多徐志摩的佚作。当初两个编者之一的陈建军先生,将电子文本发给我看。我觉得够多的了,足够出本书,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没想到的是,在等待出版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又增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达到141篇(首)。另一个编者徐志东先生,也参加进来。当然,这些佚作,不全是他俩搜集的,好些是汇集过来的。容量大了,质量也更高了。我敢说,这本书的出版,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往更深的向度发展。一本书的好坏,在研究上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绕得过去绕不过去。《远山》在往后的徐志摩研究上,肯定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
编过全集,写过传记,对徐志摩研究的脉络,我还是清楚的。
改革开放之前,对徐基本上是泼污水,讽刺谩骂。改革开放后,好长时间也无人插手。最早着手研究徐志摩的,是他家乡海宁市的一位文化人,叫顾永棣。我去海宁时,见过这位先生,高个子,像个北方人。他编了本徐的诗集,交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后来还写了本传记。现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全集,就是他编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事。直到九十年代中期,徐都没有热起来。要热也是暗地里热,没有明着热起来,只冒烟,没明火。
颇能说明这一现象的是,1997年我的《李健吾传》出版,朋友圈都知道我能写传记。在山西工作过的老熟人丁冬先生,趁空儿给他妹妹组稿。他妹妹叫丁宁,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正在编一套现代作家传记丛书,已到尾声,名单上还有三个人,找不到写手,问我能不能写一个。我问是哪三个要写,说是冯雪峰、何其芳、徐志摩。我连想都没想,就选了徐志摩。如果是现在,一长串名字摆在那儿,都会争着写徐志摩。
在徐志摩的研究上,我的“徐传”是个标志。这个标志说来可笑,甚至被人攻击是下流。什么地方下流呢?我考证出徐志摩和陆小曼发生性行为,突破男女之大防,是在哪天晚上,是在什么情形之下。举了许多证据,写了好几百字。接下来说,没有更为确凿的证据出现之前,基本上可以断定,是1925年1月19日。这天晚上,在北京松树胡同七号,新月俱乐部的院子里,胡适做东,客人有章士钊、林长民、陆小曼等。酒宴之后,大家都走了,陆小曼留下了。徐志摩不能叫做客人,他就住在这儿。就是这天晚上,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前不久,有位青年学者采访我,说揭示性生活,是当今世界传记文学的一个新走向,你怎么能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注意到了?我说不是我意识超前,是我尊重人性,觉得这不算个事儿。这个盖子揭开了,徐的好些“艳诗”,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我是从我写传上考虑的,没有顾到世界传记文学的什么什么。
我把我的“徐传”,作为徐志摩研究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且是这样的内容,有人听了会暗笑。不要暗笑,明笑好了,大笑好了。只是笑过之后,要想一想,这不是个胆量问题,更不是个品质问题,而是个见识问题。对那些批评我、挖苦我的人,能说什么呢?再厚道也得说句“智不及此”吧。
从2001年“徐传”出版,到现在十好几年了,徐志摩的研究,并没有大的进展。卡在哪儿了?卡在材料上了。傅斯年说过,历史学就是材料学。研究人物也一样,材料起很大的作用。这么多年,没有新的材料发现,徐志摩的研究,就一直处于“平不塌”的状况。
现在不同了,《远山》出版了,发现了大量的新材料,必将推动徐志摩的研究向更深广的层面进展。这本书里,诗啦,日记啦,没什么新鲜的,有看头,但意思不大。会看,才能看出点意思,不会看的,也就是那么回事。最值得关注的,是散文里的三组文章:一组是1920年8月发表在《政治学报》上的《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等文章,一组是1916年发表在沪江大学校刊《天籁》上的十一篇文章,一组是1921年到1924年间,给英国人奥格登的六封信。
《社会主义之沿革及其影响》等文章的发现,可以确立徐志摩传播社会主义先躯者的地位,这就不用多说了。《天籁》上的文章,是华东理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的。沪江大学的地方,解放后给了华东工学院,华东工学院如今成了华东理工大学,这样一来,沪江大学的资料,就归了华东理工大学的图书馆,这样研究者才能在校刊《天籁》上找到这一批文章。这一批文章的发现,补充了徐志摩学历上的一个盲点,确认徐志摩的学历里,有沪江大学这个环节。
在这上头,我是丢过人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研究徐志摩的时候,编年谱,写传记,对徐有没有沪江大学这个经历,一直持怀疑态度。在陈从周的《徐志摩年谱》里,确实写着哪一年冬天,肄业于沪江学院。记得是这么句话,不一定准确。在梁锡华的《徐志摩新传》里,还有梁锡华从克拉克大学图书馆查到的,沪江大学开出的成绩单,按说不该怀疑了。我的疑点在什么地方呢?既然在这个地方上过大半年的学,就该有同学。徐志摩的名气那么大,怎么死后没有一个沪江大学的同学写纪念文章呢?于是我便怀疑,徐的沪江大学的成绩单,是徐申如为了儿子赴美留学,下了点功夫,从学校走门子开出来的。这样想了,也就这样写了,写在一篇名为《徐志摩学历的疑点》的文章上,又收入《寻访林徽因》这本书里。此书流传到台湾,台湾的一位名叫秦贤次的先生看到了。此人是个史料专家,做学问很是严谨。不知是查了资料,还是手头就有材料,他著文斥责我胡说八道,以臆想代替史实。文章发在2009年某期的《新文学史料》上。我刚看时,也挺恼火的,想写文章回击。后来一想,做学问嘛,就是要弄清史实,谁弄清就听谁的。正好这时候,《徐志摩传》要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要我写个新序。写了,也就六七百字,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感谢这位台湾学者的指谬。再后来,我买到法学家吴经熊先生的自传,上面说到跟徐志摩是沪江的同学。这次这批《天籁》上文章的发现,不光确认了,也充实了这段经历,有人再写“徐传”,可增加一章。
最最重要的,还是给奥格登的六封信。这是近年来,徐志摩研究的重大发现,也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主要内容。
先说发现的经过。这几封信,是北师大学者刘洪涛,在英国访学时发现的。他写过一本书,叫《徐志摩与剑桥大学》,台湾秀威书局印行,给过我一本。书中说,发现这组书信,纯属偶然。他看过梁锡华的《徐志摩英文书信集》,想看徐的原信,但书中未注出处。他去英国,是做访问学者,名义上是研究罗素与中国。找到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地址,写信问罗素的档案,得到许多收藏有罗素档案的机构名单,其中有加拿大的一家,是马士德大学图书馆罗素档案馆。写信去问,馆长复信说,他们这儿还收藏有徐志摩给奥格登的一些信,问他要不要。刘先生大喜过望,不久便得到复印件。这批信件,成为他后来研究徐志摩的核心资料。
现在来看看奥格登是个什么人。他1889年生,1957年去世,比徐志摩小两岁,活了六十八岁。他是剑桥大学的学者。这些信怎么到的加拿大,就不多说了。奥氏1912年创办《剑桥杂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有关战争与政治的国际论坛。奥氏又是剑桥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组织的创办人之一,这个组织叫“邪学社”,成立于1909年,起因是奥氏等人对校方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挺反感,想营造一个能自由讨论宗教问题的空间,推动宗教、哲学和艺术的自由讨论。主要活动方式,是邀请文化、思想、文学界名人举办演讲。奥氏先任学社干事,后长期担任主席。他是个天才的组织者和鼓动者,搞得有声有色,吸引了大量的剑桥学子。从徐志摩1922年1月给罗素的信看,徐在剑桥,虽没有加入邪学社,却能够参加演讲会,可见徐与奥氏及其他邪学社成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对徐志摩在英国留学期间所受的影响,刘先生是这样说的:上世纪一二十年代,是剑桥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以三一学院、国王学院等学院为代表的剑桥大学,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人文学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属于英国上层知识分子团体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成员,是英国现代主义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徐志摩与他们中的许多成员都有密切的交往。徐志摩与英国当时汉学界的代表人物卞因、翟理斯、魏雷等人有深厚的友谊,与作家威尔斯交情甚笃,拜访过哈代、曼斯菲尔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徐志摩全方位地介入到了英国当时的思想文化运动中。
我的感觉是,以往谈徐志摩与英国文学的关系时,往往强调浪漫主义对他的影响。因为这样的影响,就说他是个浪漫派诗人。反正不是革命诗人,挑个不好不坏的名头给他算了。看了刘先生的文章,我觉得,这种影响当然很重要,但徐志摩在英国,亲身经历的这种文化、思想的活动,对他的影响可能更大些。最为明显也最为可贵的是,他把这种人际交往,这种组织方式,带回了中国。在北京办新月俱乐部,在上海办新月书店,都有邪学社的影子。
可惜的是,国内的研究者看不到这样的承续,也看不到这样做的意义。在现代文化人物的研究上,用的最娴熟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相面术,二是看出身。徐志摩长了个好模样,招女人喜欢,也喜欢女人,又写诗,当然是个浪漫诗人;留学美英,当然是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这不是相面术是什么?
徐志摩的父亲是大资本家,也是大地主。中国的乡镇资本家,没有不是大地主的。有这样的出身,必然有许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恶劣品质。好的品质是遗传的,坏的品质也是遗传的。于是,徐志摩不花花公子,也花花公子了,何况他看着还真的就像个花花公子呢。是花花公子了,怎么不是革命的对象呢?于是对他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乃至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众多作为,就打了很大的折扣。比如早在1929年,他就组织并主持“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这事若是“鲁郭茅巴老曹”中任何一个人做的,早就喧到天上去了。
在中国文化里,评价人时候有个奇怪的规律,可称之为“转移性泄愤法则”,就是,对一个文化人,若他有某一方面的苦难或是缺憾,对他的另一面,就特别的宽容或宽厚。比如胡适,有个小脚太太,就觉得他的品质一定特别的好,不好也是好。郁达夫嘛,死得那么惨,别说是个进步作家了,说是个革命作家也不为过。鲁迅嘛,婚姻那么不幸,思想怎么能不深刻呢?就这个徐志摩,要钱有钱,要貌有貌,要学历有学历,要情人有情人,哪样都比自己强,怎么会是个好人呢?殊不知,中国文化有个强大也特殊的规律,就是“世家子现象”。多少代的积聚,到了某一代,常会出现极为杰出的人物;徐志摩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这个,别的解释,都说不通。
单说徐志摩的让人不服气,再举个例子吧。两弹元勋邓稼先,这可是个英雄人物。一般人说起来,只说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毕业于西南联大。实际上,他的身世要显赫得多:祖上是中国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父亲邓以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学美学的,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与胡适、徐志摩都是好朋友。这样的身世,才会有邓稼先这样优秀的子弟产生。不要动不动就说,信了什么才会什么什么。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说,评价徐志摩这样的人,要有持平心,要放在中国文化史、社会进步史的层面上衡量。只说他是个优秀的诗人,实在是小气了。
我写“徐传”时,每每有这样的困惑:徐在国内啸聚友朋,抱团结社,南征北战,兴致勃勃,从不气馁。后来有些疲累了,但意气未衰,只能说是苦撑待变。这一套学谁的呢?我先前想的是学汉密尔顿。这个美国开国元勋,办过报纸,写过政论,精通宪政的一套。但总觉得太大了,也太远了,有点“八竿子打不着”的感觉。又想,会不会是剑桥国王学院的狄更生呢?也不像。徐志摩去找狄更生,狄外出活动,回来见这个中国青年坐在门前台阶上等他。都不带他出去活动,能是怎样的亲近?连亲近都没有,又能怎样的效仿?至于罗素、哈代、曼斯菲尔德等人,就更不着边际了。
奥格登,只会是奥格登。你看嘛,奥氏是组织社团的高手。刘洪涛在介绍文字中说,在邪学社成立之前,剑桥已有了一些类似的组织,如著名的使徒社便是其中之一。邪学社后来居上,风头甚至盖过了使徒社。徐回国后,与各色人等的交往,更是尽显奥氏的交际本领。还有,奥氏对出版的兴致,对徐志摩不会没有影响。奥氏组织出版的“国际文库”,徐曾参与其事,推荐了梁启超和胡适的著作入选。徐后来接受中华书局的聘任,当特邀编辑,一套一套地编书,未尝不是仿效奥氏的胸襟与做派。正赶上国内新文化运动狂飙骤起,又有梁启超预先为之布局,这个年轻人便借风扬沙,施展身手,三拳两脚,便把自己打造成新文化运动的明确的倡导者,切实的组织者。
这样说,只是我的一孔之见,是不是这样,且往前走着看吧。好在那座山,离得虽远,山上的纹路,却越看越清了。
《远山》中有许多佚文,从欣赏的角度看,还是蛮有意味的。比如《结婚日记》,若细看,就知道不应起这么个名字。徐志摩是1926年10月结的婚,日记里的是1926年3月底到9月初的事。实际情形是,两人结婚前,在北京中街的一所房子里,有过一段同居的日子。这束日记,该叫《同居日记》。既是同居日记,其亲热也就不同寻常了。还有《远山》这首小诗,细品一下,是不是有《沙扬娜拉》的味儿?好书是可以把玩的,能把玩的书,才能激发读书人的灵性。
不多说了,在这秋雨绵绵的日子,有这么一本书,可以消磨你许多的闲暇。地铁上拿出来亮一下,会收获许多羡慕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