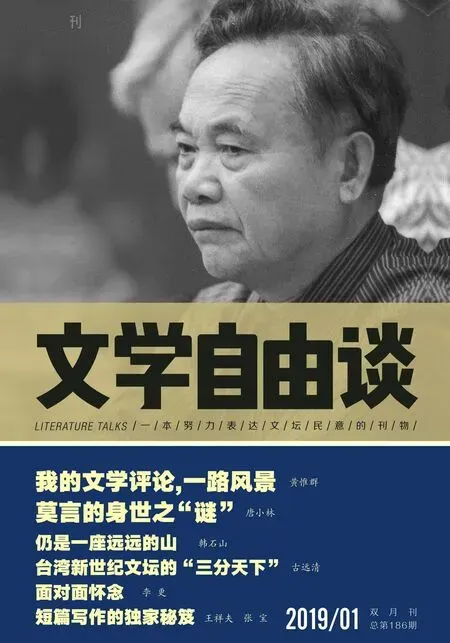柳青研究:论从史出,全面看人
2019-12-27邢小利
□邢小利
今天这个会的主题是“柳青精神研讨会”。我提前写了一个发言稿,叫《柳青的人格和精神》。我对柳青人格和精神的概括是:勤学笃行,知行合一;坚守底线,实事求是;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这几个观点都有事实论据,限于时间,我就不念了。
我是柳青的研究者,我想谈谈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和体会。
柳青研究,现在来看,大致有三个方面或三个角度:一个是文学和文学史的角度,这是专业的角度;一个是历史的角度,把柳青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研究;还有一个角度,就是政治宣传的角度——当然,政治宣传也有它的意义。虽然是三个角度,各有侧重,各有自己选取的面,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是一个历史的人。这样,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就必须重视历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就是“论从史出”,这就是说,一个观点,一个看法,需要史实的支持,必须是从史实中得出的。而这个史实,又需要由真实可靠的史料来支持、构成。目前关于柳青史实和史料方面的研究,主要的成果,一个是1988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蒙万夫等人写的《柳青传略》,一个是201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写的《柳青传》,还有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柳青年谱》,这是我和邢之美合作的。
我和柳青也可以说是一个单位的人。他当年在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我后来在陕西省作家协会,而中国作协西安分会是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前身。柳青是我的前辈,我没有见过他。虽然是一个单位的人,我也读过他的不少著作,对他的生平也有一些了解,但真要说清说准这个人,我觉得还很没有把握。如果根据一些片面资料,胡拉乱扯地谈一些似是而非的看法,也可以,但我觉得这样既不严肃,也是对柳青的不敬。所以决定先编他的年谱,尽可能地找一手的资料,可靠的资料,把他的一生,特别是生命中那些关键节点的细节,都尽可能地弄清楚。把他的一生全部排列下来以后,才有可能看清一个人,认识一个人。所以,我认为,史实的基础,史料的真实和可靠非常重要。
近年来,在关于柳青的文章和书籍中,有些说法和故事不准确,有些则没有根据。比如,有种说法是,当年柳青为了深入生活,辞去了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保留了“县委常委”的职务。但是据我看到的当年的有关资料,说的是“县委委员”,不是“常委”。1953年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致信长安县委书记李浩,信中说:“柳青同志因工作需要,离开长安县委,移住常宁宫写作,原任长安县委副书记职务撤销。但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
今天会议上发了《柳青在人民中生根》这本书,我看到一则关于柳青的故事说:“1958年,柳青出访日本,给皇甫村买了5000斤稻种。”这本书的主要编者今天在座,我想请教,这个材料是从哪里得来的?前年就看到一本名为《人民作家柳青》的书,其中也写到柳青出访日本买稻种的事,我看了感觉诧异,因为我没有见过柳青曾出访过日本的记录。我打电话问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刘可风老师今天也在座,刘老师肯定地告诉我,她父亲没有去过日本。
2015年,陕西作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柳青精神研讨会,会上有位北京的评论家说,“柳青是九级干部”。我当时负责对发言纪要整理稿进行修改和把关,就打电话给这位评论家,问这个“九级干部”的说法得自何处。因为据我所知,柳青当年评的是十级。《柳青年谱》中写,1956年,在干部级别评定中,柳青最初被评为九级。但是在一次关于提级的讨论会上,有工作人员汇报说,统战部提出民主人士郑伯奇的级别低了。郑伯奇是老资格的创造社成员,是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柳青就提出把自己的一级让出,给郑伯奇提一级。这样,郑伯奇就提高了一级,成为十级,柳青降了一级,也成为十级,两人平级。“文化大革命”中,此事也成为柳青的一条罪状,造反派说柳青“招降纳叛”,包庇“反共老手”郑伯奇,证据就是柳青把自己的一级让给了郑伯奇。此后又有一次提级,柳青也让给了别人。所以,柳青的行政级别一直是十级。我当年为了查明这一点,费了好多工夫,掌握的就是这些情况。我不知道这位评论家所言是否另有根据,为了尊重这位评论家——我不能擅改评论家的意见,特别是这种史料,也为了不致出现史实方面的硬伤,我就电话请教他。评论家说,他也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就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使用史料时,有的还需要考证。不准确、不真实的史料,会改变史实,改写一个人的历史。而从这样的“史”中得出的“论”,也就不可靠了。论从史出,以免游谈无根。
研究柳青,要准确、全面地概括和提炼柳青的精神,还要有整体观,要研究柳青的一生。和很多同代作家一样,柳青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思想和精神世界也是从相对的窄狭和单一不断地迈向广阔和丰富。所以,只从一个阶段,比如只从长安十四年来谈柳青,还是难免片面。就比如陶渊明,他从二十九岁到四十一岁,十三年间五次入仕,如果我们不看他四十一岁以后,单从这十三年看,那我们可能就会认为陶渊明是一个官迷,而且不是一个好官,因为他每次出去当官,时间都很短。可是陶渊明却是以一个隐士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上的,还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这就是从他四十一岁以后的生活和精神着眼的,是从他的一生整体来看的。择取人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看到的很有可能是一个片面的人,只有全面地看一个人,才有可能看出一个完整的人。
从方法论意义上说,我有一个体会,在文学研究,特别是对一个作家的研究中,只凭有限的资料,只看取他一生中的某一个片断,是很难全面、准确地把握一个作家的。根据有限的资料或部分资料,谈一些观点,管窥蠡测,难免片面。有一句话叫“窥一斑而知全豹”,这种“知”,基本上是猜测和想象,很难准确。而你如果知道了“全豹”,再来看这“一斑”,就有可能对这“一斑”有特别深入的理解,也才能知道这“一斑”在“全豹”身上的地位和意义。还是以陶渊明为例,只有全面地看一个人,认识到陶渊明其实是一个隐士,我们才能明白他那十三年的不断做官,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另一方面也是他决心当隐士前的必要历练和挣扎,诚如他自己所说的,“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并不以五次做官为荣。
到底什么是柳青的精神?这个问题我琢磨了很长时间。刚才有人说柳青的精神就是“深入生活”,我觉得“深入生活”只是一个方法,是柳青为了创作而采取的一个方法,以此来概括柳青的精神,似乎不太准确,不够全面,高度也不够。
我们概括、提出的柳青精神,应该今天能站得住,多少年以后也要能立得住。柳青曾经红过,也曾经黑过,今天又红了起来。这种红与黑、黑与红的变化,一方面折射出时代的变化和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研究柳青,需要秉持历史学的态度,运用历史学的方法。这就是我前面讲的,一要尊重史料,论从史出,二要全面地看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