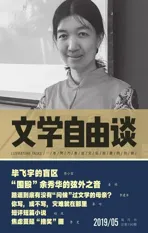《大树小虫》:不成功的隐喻
2019-12-27沈嘉达沈思涵
□沈嘉达 沈思涵
一
说到池莉,人们自然会想到她的“人生三部曲”(《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想到《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弹指一挥间,这位在上世纪末引领文坛“新写实主义”潮流,凭着中篇小说《生活秀》,就能让武汉市创设一条 “吉庆街”,并促成三家鸭脖子公司上市的小说家,不知不觉竟然“隐身”文坛十余年了。尽管这期间,她零星写过中篇《她的城》《爱恨情仇》,为上海的纸媒《新民晚报》也开过专栏,甚至出过诗集《池莉诗集·69》和散文集《石头书》《立》,然而,当年那位高产稳产、叱咤风云的小说家池莉,似乎变成一个渐行渐远的符号了。
就在今年五月,池莉携带着一部40万言的长篇小说《大树小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第1版)“重返”文坛,再次引发“轰动”。湖北某杂志7月号的专栏推出四篇评论文字,称赞“《大树小虫》好比一出喜剧”,是“当代犬儒主义者的传神写照”,作者“呼应当下热议的二胎问题”,企图破解“家庭关系的现代性难题”云云。新闻媒介也是不遗余力,指认小说“从日常又不失戏剧化的生活镜头切入……把写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推至一个新的高峰”(陈曦:《池莉最新长篇〈大树小虫〉:以数十段生活秀谱写中国现当代百年史》,《现代快报》2019年5月12日);“两家三代人近百年的跌宕命运与现世纠葛,以标志性的历史事件串联人物性格及命运,多线并行地展开了中国现当代百年历史的壮阔画卷及社会图景”(曾子芊:《池莉的〈大树小虫〉 谱写中国现当代百年史》,《北京晚报》2019年6月14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作者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
从书尾文字可以看出,池莉还真的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该书“构思于2010-2015年”,历经“初稿”“二稿”和“完稿”,最终“修改于2018冬-2019春”,年头岁末,加起来长达十年。对于这样历经磨难的“孩子”(该书初稿有70万字),作者当然是疼爱有加,信心满满。“好看。有趣。新颖。耐读。灵巧。不笨。反传统结构。不对称审美。活力动感。视觉性强。现场感强。带入感强。如果用网上流行语说,就是力争全文无尿点,只有泪点,笑点,痛点。”(丁杨:《“写人,写民,写他们不可言说的内心深处”——访池莉》,《中华读书报》2019年6月5日)总之,让池莉感慨颇深的是,“写一百年、三代人乃至四代人的大跨度小说,在我,必须熬到现在的年龄,年轻写不了”。(同上)现在,终于写成了。
显然,池莉已经将自己这些年来的深度思考灌注在这部小说之中,“大树小虫”的命名本身已经彰显了作者的苦心孤诣!小说扉页,作者就醒目地引用爱因斯坦的话语称:“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
这,是一个关乎“文眼”的重要问题。
二
小说《大树小虫》唯一一处明确标识“大树小虫”文字的,是在第二章第三节。作者写道:惊蛰之夜,春雷阵阵,尽管人们早已对自己的身体“浑然不觉”,但是,“内在苏醒的万钧之力,还是会突破重重隔膜,来到人间,大树小虫齐齐被震撼。惊蛰之时,俞思语醒了。”身体“苏醒”、一心想要再次怀孕的女主人公俞思语触动了自己的隐秘私处,享受到了身体的欢愉。不过,欢愉之后,小说写到,俞思语还是没有怀孕。
不难见出,这里要突出的只是“结果”,即俞思语怀孕不成。作者想表达的是:即便春天来了,人们的身体意识觉醒了,人这样的“小虫”跟世界万物(当然包含了池莉所言的“大树”)一样,获得了觉醒与自我突破,却依然无法享有自己想要的结果。这里,“小虫”也好,“大树”也罢,指涉的都是同类项(都是被春天触及的生灵),包含的是同一个生物层面的意蕴,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是池莉“大树”与“小虫”的内在意蕴么?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做个简单统计:《大树小虫》共两章,第一章占到全书87%的篇幅,第二章只占13%的篇幅。池莉也一再提醒读者,可以从第二章看起。究其实,作者是在告诫我们,小说的重头戏、重点、中心在第二章。那么,第二章又写了什么?在这极其有限的篇幅里,作者叙写钟鑫涛俞思语这一对小夫妻全年12个月“努力怀孕”,最终不成。仔细思来,作者有意营造这种“反传统”“不对称”“动感”十足的“倒置”结构,其实是在“隐喻”着什么。
然而,第一章大书特书钟俞两家三代百年奋斗史,第二章心心念念钟俞两家后代求子不成,这中间有着什么样的逻辑关系呢?它们真的能构成“隐喻”吗?
三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作者有意将两家姓氏命名为“钟”和“俞”,也许隐喻的就是当年钟子期和俞伯牙的知音故事,以作反讽。还可以作为参考的是,作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与记者对谈中言及“大树”与“小虫”,称“生活就是一棵巨大的树,我们人类都是小虫,在奋力地生活,奋力地爬行”,“这个社会非常的复杂,我们生活在宇宙决定论当中、社会决定论当中,我们都被(外界所)决定、被(外界所)设计……”(白洁、池莉:《我们都是生活里的“小虫”》,《山西晚报》2019年6月11日)一言以蔽之,在这个社会“大树”面前,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虫”;我们的人生道路之所以弯弯曲曲,是因为“大树”本身是“弯曲”的;人们仅剩下可怜的“盲目”而已。
现在,我们来探究一下“大树小虫”这个“隐喻”的可行性。
小说第二章第12节(也就是最后一节,曲终奏雅),叙写钟俞两家查找俞思语不能怀孕的病因。令人尴尬的是,并不是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俞思语有病),“恰恰相反,钟鑫涛有病。”怎么回事呢?小说非常专业地写道:“钟鑫涛的精液分析结果是:前向精子15%,精子密度1000万。”四年前,俞思语怀上女儿时,钟鑫涛的检查单上显示前向精子是70%,精子密度4000万。不仅如此,钟父还找到了一张晚报,上面用大标题写着:《40年来全球男子精子数量暴跌六成,武汉男子精子质量6年降低15%》。至此,“真相大白”:是男人出了问题,而且是全球的男人都出了问题。质言之,社会的繁华与家族的兴盛,带来的却是人性的异化,所以,男性的生命力、创造力在衰减。
这里面其实是有着明显的逻辑误区。作为繁衍后代承接人类的生儿育女,既有着社会因素的制约(譬如环境污染,譬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麟式的政治压抑),更是个体的生命冲动行为。换句话说,在不是政治小说,也不能认定为“问题小说”的《大树小虫》中,如何能将作为个体行为的生儿育女责任迁移到社会层面上来?作为男人的钟鑫涛,有着良好的家境和丰富的人脉关系,其生命力递减与大社会的百年变迁、其家族的血腥奋斗,有直接关系吗?
学者徐勇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大树小虫》中,作者采用的是虚化或淡化公共空间和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以凸显家庭单位的象征意义。”然而,池莉“把现代性的宏大命题包裹在最具传统特征的元素中展开(指的是生儿育女——引者注),结果是夫妻关系演变中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涵被遮蔽,也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其虚妄与无奈,自是难免,也可想而知。”(徐勇:《家庭关系的现代性难题——关于池莉的〈大树小虫〉》,《长江丛刊》2019年第7期[上])很明显,《大树小虫》的“大社会”(钟俞两个家庭的三代百年史)与钟鑫涛俞思语这对“小夫妻”的怀孕生男孩之间并没有建构起逻辑关系,当然,也就不能构成某种隐喻。
那么,是钟鑫涛工作沉重社会性压抑了人性从而导致生命力孱弱?我们无法从小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钟鑫涛既不是忧国忧民的思想者,也不是葬身于现代社会声色犬马中的花花公子,他的生命力的衰减如何归罪于社会呢?
那么,我们能不能将“生男孩”本身看做是某种隐喻——譬如“目标”“希望”等?不能。因为在小说中,作者完全将生儿育女坐实,成为了生活的本质,从而缺乏隐喻所需要的发散性和虚化特质。
四
其实,思想的紊乱才是小说隐喻不成功的根本。池莉在《大树小虫》中设置了两性关系,其中的男性基本上仍处于被审判的地位。作为成功企业家的钟永胜,他的“人生表情,有流氓,有土匪,有伪君子,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有嘴上叫哥哥暗地摸家伙,也有背后使绊子”;他欺骗妻子高红,在家暗通保姆李雨青,在外养了广西女子格瑞斯,甚至与格瑞斯的妹妹韦漪也有一腿。其他,如46岁贵为副厅长的俞亚洲,同样与格瑞斯有染;钟欣婷的丈夫董金泉虽为清华博士,却满脑子的乡下小农意识;俞思语的上司梁总呢?一介见了女人直接就上的衣冠禽兽……甚至,在小说中,作者借高红的母亲詹鄂湘之口,称:“你就当男人是条狗吧,你在家里备了世界上最好的狗粮,它出去还是要吃屎。”由此可见,在作者看来,是男人的本性决定了男人的行动及其结果,而不是社会使然。
隐喻的不成功还在于作者主体性的过度溢出。本来,池莉早期的人生三部曲等新写实小说,一度被贴上“零度情感”、缺乏社会批判性等标签。时过境迁,池莉在求变。《两个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预谋杀人》等,理念异常突出。而在《大树小虫》中,池莉还在求变,她特意借助影视化剧本做法,在每一小节前面,对所要叙写的人物直接推出“人物介绍”和“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对人物性格尚未盖棺便先进行认定!小说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尽管全知全能,但仍避免过度地“介入”,然而作者常常无端展开“议论”,将人物的“人生表情”强行塞给读者。至于某些情节细节,也常常令人啼笑皆非——小说不是叙写生男孩故事么,作者在书中写到作为钟鑫涛母亲的高红(曾经是人民警察),竟然怂恿自己在大学本硕连读的儿子“试情”!什么意思?就是鼓励儿子在读书期间多次找女同学巫山云雨,以考察儿子的生育技巧以及生育能力。这种随性所为、任性发力的行为,完全消解了小说可能的内蕴,实不足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