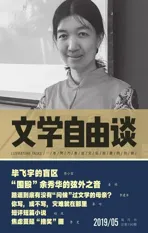林斤澜和唐湜
2019-12-27程绍国
□程绍国
现当代,浙江的温州,有不少文学大家,如夏承焘、王季思、郑振铎、赵瑞蕻、琦君……林斤澜和唐湜,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星星。
林斤澜生于1923年;唐湜比林斤澜大三岁,1920年生。林斤澜父亲创办沧河小学,当了几十年的校长;唐湜父亲也当过一段时间的小学校长。林斤澜小学和初中各跳一次级;在省立第十中学(温州中学前身),林斤澜和唐湜是同学,唐湜比林斤澜高一年,他们互相认识。林斤澜13岁在学校发表第一篇作品《新路》。次年抗战爆发,山河震荡,金鼓连天、风石火球、热血化雾的时候到了,林斤澜毅然到平阳山门,进入粟裕当校长的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后来加入地下党,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受阻于重庆。在重庆,他曾给远在新疆的茅盾写信,要求赴疆读书,茅盾回信叫他就近入读。1946年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有一个事情非常触目。在同辈作家中,和林斤澜关系密切的,有数不清的右派:汪曾祺、邓友梅、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唐达成、王蒙、叶至诚、高晓声、陆文夫……可林斤澜不是。唯独林斤澜“漏网”,何哉?1957年新春,一个星期天,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也就是中国作协《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的丈夫,把林斤澜、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叫到自己家里,要求“青年作家要带头鸣放”。林斤澜没有“鸣放”。没有“鸣放”并不是林斤澜没有材料。北京市作协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赵坚,当面把一封信推给林斤澜。林斤澜见信是福建省一个剧团寄来的,这个剧团要改编排练林斤澜的小说《台湾姑娘》,问北京作协有什么意见。那个时候某地要改编什么,征求原作者单位意见乃普遍情况,根本不问作者。因此,这是一封很正常的信。可是,林斤澜看到不正常的情况,这不正常就是信的上方有一行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田家的批示:“此人正在审查中。”林斤澜说:“我非常愤怒。‘此人正在审查中’,这是什么话!当年并不是没有审查,几乎所有人都被审查过,审查全是例行审查,是老规矩,是正常的审查。可是,田家在这样的信上批上这样的字眼,就是把正常审查当作政治事件了!田家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林斤澜想到了赵坚这个人。他对赵坚这个时刻递来这样一封信感到头疼。两派斗争,林斤澜决不参与。结果是林斤澜把信推回,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封信不是给我的。”——后来事实证明,那天他如若“鸣放”,打成右派无疑。
而唐湜却是右派,是无天理。那是唐湜在北京任《戏剧报》编辑的时候。在《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中,我终于找到了答案。杜高说:“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赵寻作为戏剧家出访尼泊尔。一天,唐湜来找我,他对赵寻改编的这个剧本获奖很有意见,提议以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写一张大字报,我正想发泄对赵寻的不满情绪,于是立即提笔对赵寻大加讽刺(那张大字报叫《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可以想象蓝光看到这张大字报时是如何恼怒。她克制住自己的愤懑,一直等到鸣放终于转向反右派的进攻,她才得以猛烈反击这两个胆敢报复肃反积极分子的凶恶敌人……”唐湜遂被划为右派。
有句看似平常的话:“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万里路,实际上是说作家的经历、经验、经受。唐湜“读万卷书”恐怕是有了。他读完高中,1943年考取浙江大学外文系,开始真正的诗艺探索。1946年,他在上海认识了杭约赫和陈敬容,后来参与《诗创造》的一些编辑工作,经常往来于上海和杭州。“行万里路”,恐怕就不够了。他对世人、世界的了解实在是非常有限。他的世界里有正义,但更多的是艺术,他纯粹是个艺术人。他涉世不深,右派帽子差不多是自己找来戴在头上的。
林斤澜和唐湜,个性不同,人生道路不同,都会在作品中反映出来。
林斤澜的写作是从1950 年开始的,先写剧本,后改为写小说。《台湾姑娘》是他的成名作。即使是成名作,现在看起来也只是比别的作家写得聪明一些、艺术一些,不能和他1978年以后的作品相比。
在漫长的岁月里,林斤澜没有写作。杨沫在《自白——我的日记》中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易暴露人的真面目。当人处在“危险”关头,保护自己第一,还是坚持真理第一,常是考验一个人的试金石。文联中,除了浩然——他为保护我这个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人,受了不少委屈和打击。我最佩服的还有林斤澜和骆宾基(他们二人还都是党外人士)。第一,林决不看风使舵。那些造反派曾经努力拉他,但他却和我这个半专政的人成立了“战斗队”,决不倒向得势的造反派那一边。尤其当无辜的浩然,被没完没了地挨批时,他竟敢在文联大庭广众中高喊“浩然是好人!”而且他也看透了那些“革命”的文艺理论。他向我说过,他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写作品。但是我却做不到。(也许他比我年轻的缘故?)
杨沫的一生,是“革命加文学”的一生。她视写作如生命,她要写。她写《青春之歌》下部,至1975年1月,《东方欲晓》初稿完成,五十多万字。后来也出版了,但没有艺术价值,我当时根本读不下去。“清规戒律”在那里,框框多,许多东西不能写,怎么写得好?好比一个人带着镣铐,怎么跳舞?
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泥土开花,万物鲜朗。林斤澜复苏,唐湜从“地下”(他在痛楚岁月里偷偷写了历史诗《海陵王》;我想起老舍,他也偷偷写他的《正红旗下》)转入“地上”,俩人大展身手,才有了后来的文学成就。
刘心武说,1978年,他在《十月》杂志,到林斤澜家约稿。林斤澜女儿准备高考,要用写字桌。林斤澜坐在小板凳上,稿纸铺在椅子上,就这样写,写着小说《阳台》。我想起列宾的画《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书斋里》,托尔斯泰一条腿盘着写,但写作条件还是比林斤澜要好。写作条件对林斤澜来说并不重要。作家能够自由写作了,就是小鸟飞入了天空。他的代表作之一——小说集《矮凳桥风情》,就是写故乡温州的,里头的《溪鳗》《李地》是短篇杰作。而小说集《十年十癔》更多的是审丑,把溅血的天幕撕开来给人看,惊世警世。他的《门》是抽象小说,时空隧道,世象人间,变形荒诞……刘心武读罢,立打电话:佩服佩服……
唐湜和辛笛、陈敬容、唐祈、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这些诗人,上世纪四十年代都已出名,现在又从“地沟”里爬出,拾起了笔。他们主张“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和“生命的文学”的综合,既反对逃避现实的唯艺术论,也反对扼杀艺术的唯功利论。1981年,他们出版了《九叶集》,“九叶派”从此诞生。九叶派中,唐湜是新时期创作产量最大的一位。他不仅是诗人,而且是最重要的诗评家之一(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还是最早评论汪曾祺的人)。除《海陵王》之外,他还出版了《飞扬的歌》《九叶集》(合作)《遐思诗之美》《霞楼梦笛》《春江花月夜》《蓝色的十四行》《英雄的草原》,出版了评论《意度集》《新意度集》《翠羽集》,以及论文集《民族戏曲散论》等。
唐湜先生是不朽的。
2003年10月,温州政府邀请林斤澜参加“世界温州人大会”,林斤澜9日抵温,即让我安排个时间,去看看唐湜。我说,“廿一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二届研讨会暨唐湜诗歌座谈会”11月3日在温州举行,你会碰到他的。林斤澜说先去看看。唐湜住在花柳塘发臭的河边的三楼。二楼有垃圾道,垃圾道口有人写着“在此小便,老太狗生”。再上一楼,就到了。他的家东西无窗,很是昏暗。家门洞开,唐湜坐在门内的藤椅上,看来是等了好一会儿了。他一见林斤澜,放在膝盖上的手跳弹了一下。他有些兴奋。林斤澜进门,立即搀唐湜起身入内,说“门头太冷,门头太冷”。唐湜蹒跚着一步一步地挪,咕噜说“腿不方便,腿不方便”。走到书房兼卧室,坐下。唐湜好一阵没说什么话。林斤澜自我介绍这一次回温的行程,又问唐湜的岁数。唐湜想了大半天,最后还是他夫人来解答。
“他们都要来了,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林斤澜说。唐湜说:“牛汉……老朋友。”又微笑着,说了一句令林斤澜莫名其妙的话:“周扬这老兄。”我的理解,他大约是说,周扬打胡风,往下一层一层牵连到他,又或者是对文坛冤案的总的感慨。林斤澜问:“九叶还有几叶?”唐湜答道:“一个我……”他在那里想。我帮他想出来,对他说:“四个,你,辛笛,郑敏,袁可嘉。”唐湜才憨厚又难为情似地笑起来。林斤澜又问:“你还看书吗?”唐湜说:“少,少,用放大镜。电视有看……”然后又补充一句:“我一听京戏就发抖。”林斤澜一愣:“哦?”唐湜说:“激动,激动。”当年他在北京编辑《戏剧报》,接触最多的当是京剧,喜剧悲剧,大难落头,“苏三起解”,人变成鬼,一生痛楚……
唐湜的发抖,理由充足。
林斤澜把好人做到极致,天心月圆,华枝春满。他通透世事,看人周全。与九叶派另一位诗人马骅相比,唐湜非常单纯,非常天真,他的手上没有一个处世哲学的本子。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他不知道;温良恭俭让,他好像没有听说过。他的一生,像是葛朗台的临终,脑中无他,只有金子;而唐湜呢,只有艺术和写作。
教授姜嘉镳说:“有回,两人吃汤面,我吃了一半就放下筷子。老唐问我:‘你不吃了?’我说不吃了。他就把我的半碗端了去,呼呼倒下。”有一回,一个女孩拿着苹果,吃前先玩玩。家长要培养她的好客,对她说:“递给唐爷爷吃,递给唐爷爷吃。”女孩凭感觉知道唐爷爷不会吃的,大方地递给了唐爷爷。不料,唐爷爷拿来就吃,害得女孩哇哇大哭。他不会社交,在熙攘温州,市政府不知道他是谁,连文联也很少留意他。他80岁诞辰,由我提议,我们《温州晚报》的部室在顺生大酒店摆了四桌酒,为他祝寿。他一过来就吃,好像这个活动与他没有关系。最后没有人打包,就他打走一个包,却是两段排骨。2003年11月3日,“唐湜诗歌座谈会”在温州师范学院召开,林斤澜、牛汉、屠岸、邵燕祥、谢冕、吴思敬……济济一堂。林斤澜回到住处均瑶宾馆时对我说:“这老唐,哎呀哎呀,座谈会上只管吃糖,吃葡萄,吃苹果,好像是别人的作品座谈会一样——别人的座谈会,也不能这样吃啊。”
而且,唐湜有糖尿病,他夫人每天定时让他吃药。但是没法子啊,唐湜有北大荒饥饿的经历,对食物的攫取哪能由得他呢?由不得他。先生所有不合时宜的、非世俗的举止,原因只有两个字:苦难。
温州文联有个刊物,从前是公开发行的《文学青年》,旭日夺目,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韩少功、张承志都是顾问,莫言、何立伟的稿子屡投屡退。后因封面女郎乳房偏大,改成内刊,叫《温州文学》。唐湜偶有投稿,走到文联,拿很多的稿纸和信封,然后郑重地对编辑讲,稿费我自己来拿,不要寄到我家。问为什么,他说:“我老婆很厉害,寄到我家我一分钱也拿不出来。”其实呢,他不会花钱。他夫人对我说过,他有钱放在身上,过一会儿就是小偷的了。这是我相信的。
唐湜非常率真,毫无城府。他不会社交,不会寒暄,只凭直觉,只凭感性。当年我的一个学兄(后来做了某报社的副总编)学写诗歌,拿去请他指点。他看后,说:“你不会写诗。你今后不要到我家来。”学兄同我说起此事,并没觉得唐湜先生有什么不对。在温州文坛,有三位算是泰斗:马骅、唐湜、金江,简称“马唐金”。一次,浙江作协评选老作家奖,先由市里推荐。唐湜当着一堆人说,童话作家金江没名堂,是小儿科,而马骅也不如他唐湜。马骅听到传话,哈哈大笑:“这唐老,这唐老……”金江记住这件事,则很是难受。唐湜这次虽然是背后说人,但倘若马骅、金江在当面,他也会这样说的。
“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的林斤澜,却不是这么简单的人。他看人精准,做事圆润。后期的小说,一篇比一篇深刻,一篇比一篇惨淡,匠心独运,极具艺术的震撼力。可惜世人很少读他的书,懂他的更是寥寥。
从唐湜家离开的时候,唐湜执意要送林斤澜。他的腿实在不方便,可林斤澜按不住他。走到门口,唐夫人说:“可以了,好了好了。外面墨黑。”他才止了步。
隔年,唐湜先生逝世。2009年,林斤澜先生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