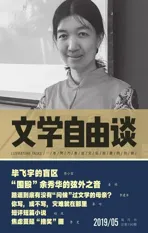毕飞宇的盲区(外一篇)
2019-12-27蔡小容
□蔡小容
毕飞宇有一个盲区,因为他看到的东西太多。
他的优秀是有目共睹的。他的小说充满了对人心世相的深刻把握与描摹,语言水平也是第一流,文字携带气场而来,精准、独到,语境配合情境,他总是找到了最贴切的语词和最巧妙的表达。他的理解力,既宽广又深邃,作品引人入胜,引领读者将自身潜藏的智性与感性都充分激活。
我读他的作品不算早,最先看的是小短篇《唱西皮二黄的一朵》,它是《青衣》的旁枝,或曰蓓蕾,颇为不凡。我认为他是从《青衣》开始成了“角儿”的。我因《青衣》而买了他一本小说集,那本集子也是此篇最可读,前面的他还在“先锋”“实验”时期。道听途说,毕飞宇早年也有读自己的小说给人听的经历——写的小说没人读啊,那我读给你听。作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成长阶段,他自己也说,假如他一直是十八岁,那么他三十八岁时的作品谁替他写?“没有一个聪明人愿意变得年轻些”,乔纳森·斯威夫特说。写出《玉米》《玉秀》《玉秧》,毕飞宇大概就是三十八岁吧,我花了许多工夫盘桓这三部曲,那时候我有闲工夫。《平原》在《收获》刊载是2005年7月,当时我刚生了孩子,每天夜里熬着不睡,图那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时间,靠在床头读这篇——毕飞宇写过一篇获鲁迅文学奖的小说《哺乳期的女人》,所以女性在非常阶段以他的小说为读物的待遇他受得起。《平原》真是才气横溢,纵横捭阖,气吞山河,我在昏天黑地的日子里读来尤其惊叹。迄今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作品,但下部逊于上部。
但有一个问题逐渐显现,在读得多了之后。上世纪五十年代,善写农村题材的周立波在《山乡巨变》里写过一个叫菊咬金的人,说他“是一个念过《三国》的角色”,心机深,做事狠。毕飞宇笔下的人物,则个个都是这样的狠角色,心气太盛,心机重重,事情做绝,他们的日子天天上演《三国演义》。玉米的父亲是村支书,她作为长女,绝对不答应谁家比她家过得强。她一方面辅佐母亲哺育幼弟,教养一大群妹妹,一方面逐一对付她父亲利用权势遍地风流招惹的女人们。她父亲的行为埋下祸端,一朝失势,她的两个妹妹就遭人暗算,她自己订下的理想婚事也化为泡影。十多岁的少女玉米,决意不惜代价,找一个有权势的丈夫为自家翻盘。十来岁的少年端方身处生母继父异姓姊妹的复杂家庭,要维护母亲,要跟继父较劲,要做农活立身,在同伴中要树立威信,危机来临时要当门立户杀伐决断,连继父都忍不住在心里赞叹“养儿如羊,不如养儿如狼”。《玉米》中的玉米和《平原》中的端方像是一个人,分了雌雄,本质上都“是鹰,是王者”,是毕飞宇的内心投影,是那个苏北少年唐·吉诃德。可是他们身边的人物,一个个也都是这样,内心无一刻松弛,时刻张满弓,箭上弦,算计着局势和对手。看《推拿》之前,我想他写盲人的世界会不会舒缓些,读来却是别一番险峻,甚至更险,那是看不见太阳挣扎于黑暗中的一群人啊,在黑暗中开辟的只属于他们的蹊径,仍然有残酷的竞争和倾轧,连一份盒饭中的肉有几块都需要有人脉打偏手,怎么怪得有人当众大声呼喊出这个真相:我的肉,我的饭,我要活!毕飞宇确实是在探测极限,他把所有人都写到了最极端。他的人物“脚下和心中横亘着铁一般的生存极限”,我放眼望去,只觉满目黑暗,竟然没有一个单纯的、无心机的人,或者这样的人被作者认为是缺心眼儿的,庸常的,不值一写,从而他们完全不在他的注意中,也就不在他的视域中。
毕飞宇谈《红楼梦》,他对一个细节的分析恰好说明了这个问题。王熙凤探望过了病重的秦可卿,哭了一阵后出来到园子里,恰好园中秋色正佳,曹雪芹甚至还描绘了一番:黄花满地,红叶翩翩,小桥清流,景色如画,凤姐于是“一步步行来赞赏”。这一细节却让毕飞宇“毛骨悚然”,他说:
“上帝啊,这句话实在是太吓人了,它完全不符合一个人正常的心理秩序。这句话我不知道读过多少遍了,在我四十岁之后,有一天夜里,我半躺在床上再一次读到这句话,我被这句话吓得坐了起来。”
他说他被这个叫王熙凤的女人吓着了。这个女人,刚刚探望了将死的闺蜜出来,转眼间就是“一步步行来赞赏”,甚至还“款步提衣上了楼”。“这个世界上最起码有两个王熙凤,一个是面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一个是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把我吓着了的,正是那个背对着秦可卿的王熙凤”,他说;把我吓着了的,是他这句话,令我毛骨悚然。
我觉得《红楼梦》中那段非但没有问题,相反还很好。凤姐方才哭过了来,她与可卿最是要好,哭是真的,但出门看见园中景致,不觉心情一换,这是生活常情,也是小说调整节奏、连缀段落的极佳笔墨。女作家闫红的分析更精彩:曹公这段写景,是找到了一个表达凤姐当时心情的最好途径。黄花红叶,溪水清流,在平日是寻常的,而此时在为可卿而起的悲伤里,方才过眼经心。更高一着的是,这样写,是要“在凤姐的悲伤与日常之间造成间隔”,一猛子写凤姐悲伤不已,那作者就成了琼瑶。对的,这一笔是日常,是突兀,是顿挫,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的逻辑和反逻辑兼具啊,毕飞宇,想多了。他倒像秦可卿,“心又细,心又重,不拘听见个什么话儿都要度量个三日五夜”。他把凤姐与秦氏的关系看成了这样:王熙凤是荣国府办公室主任,秦可卿是宁国府办公室主任,秦一死,王就当上了两边的办公室主任。所以,王熙凤的步态说明了问题,合乎了逻辑,与她办公室主任的身份高度吻合。你信服这个解释吗?毕飞宇信服金圣叹的评点,在评王熙凤时,借用了金圣叹评点林冲的一段话说:“王熙凤自然是上上人物,只是写得太狠,看她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害怕。”这句评语也正可用来评毕飞宇笔下的人物。
心机是小说家的必备条件,否则他就无法设出那个局。兵者诡道也,小说诡道也。“所有好的小说家都不可能是纯洁之人,他必须心中有鬼……太光滑的内心对艺术是不具抓力的。”此言甚是!可是,生活中事实上是有不少单纯的人,忠厚的人,良善的人,不计较的人,凡事先替别人考虑的人,这些让人省心舒适的人,毕飞宇忘了世上还有他们。一分为二地看,毕飞宇经营小说密不透风,假如他带着同样的思维在生活,他也很累,心力交瘁。他身边的人也得留心,很可能一个无心之举,被他看出太多意味,再连缀成一个逻辑极其严密、走向出乎意料的结论。
《玉米》《平原》这样的小说,因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力、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写得紧密紧张是种必然。而传统的乡村小说让人宁静,即使写的是阶级斗争,里面总有些人是安静的,那种淳朴宁静的风味是乡土小说的魅力。与其让所有的人都动,不如留几个人静,一张一弛,以静制动。
2019.7.16~19
莫言是一瓶什么酒
去年十月,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来武大外语学院讲座。他讲:“Translation is original.”——翻译是原创,而不是对原文的复制。德谚有云“翻译即背叛”,所以你不能指摘译者的翻译错误。“没有什么原文,我们不犯错误”,他这么说未免偏颇了,没有原文何来译文呢?这么说则是中肯的:“原作与译作的关系不能如双手合十,而应如交叉紧握,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
他很爱中国文学。多年前,李白的诗让他从神学转向文学,具体说,是那首“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杜牧的抒情诗》,想必那句“十年一觉扬州梦”也令他动心不已。他说唐朝的诗可以破坏德语的语法,至少是一两行。这句赞美很含蓄,想想看,德语语法何其坚固——论语法,法语远强于英语,德语更强于法语,而汉语,我们中文的语法是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他讲完了有人提问,问题听来有趣,内里锐利:是否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是茅台,下半叶的是二锅头?顾彬答道:诗歌仍然是茅台,王安忆的小说是茅台,而莫言等人的,只是汾酒。台下欢然,笑语荡漾到了网上:那,谁是五粮液,谁是泸州老窖?还有郎酒、仰韶、宝丰、杜康……好像讨论这个话题需要先熟悉中国不同酒的品级与风格。它们都是什么品级?我一概不知,但从字面语感上觉得莫言与二锅头挺相配。
我没看过莫言的书。国内几位与他大致在同一重量级的男作家的书我也没看。如果不是考试或学位压力,文学作品尽着自己爱读的去读就好。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论文题做的是严歌苓,从而莫言余华刘震云们都被我漏掉了。对于专业现当代文学研究者,这几位大作家都是研究重镇,但为什么我却不想看呢?我读到孙郁先生的一篇文章《文体的隐秘》,他的论说令我豁然开朗。他说,余华、莫言这些重要作家,他们的长篇的成功之处并非文本里的深层语态,而只是故事本身。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写曲折、宿命的人间,隐含着中国的人间哲学,小说在深度上令人刮目,但文字却有“西崽气”,仿佛是翻译文体。莫言、格非等人也与他类似,他们的文字不是古中国认知血脉的延续,故尔他们的作品像一种海外舶来之物。这些优秀作家深受西方成熟的小说体系的影响,在结构和人物等方面多有受益,而本土文化的内功,因为忽视而减弱,他们从西方文学学来了小说的结构,却不幸将中国文字的传神功夫抛弃了。——对啊,正是此理!用西方的模式写中国的故事,难免与国人的思维经验相悖离,显得“隔”,不“贴”。为什么中国古典小说那么好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儒林》《聊斋》,一代代的中国人百读不厌?因为它们集中了国人对文学、历史、社会、人生最精妙的感悟,包含着民族生活的隐秘与汉语的魅力,是我们血脉里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有所了悟和着力的作家也同样深具吸引力,如汪曾祺,他不像酒,他更像茶。
莫言获诺贝尔奖后,评论蜂起。有一篇《莫言的“染病的语言”》,作者叫孙笑冬(Anna Sun),她不谈文学牵涉到的陷阱密布的政治,而谈文学的天然血肉——语言。她认为莫言的语言没有美学价值,重复、老旧、粗劣。与孙郁先生的观点类似,她也说莫言的语言脱离了中国文学过往的几千年历史,不复优雅、复杂与丰富。这位作者我恰好知道,她1990年赴美留学,2001年在国内出了本随笔集《蓝色笔记本》,我当时应出版社之邀写了一篇书评。一个十九岁的少女,心爱的作家是“雪芹”、“爱玲”、里尔克、普鲁斯特与帕斯捷尔纳克,行李中带着一部书页发黄的《红楼梦》,带着中文写作的愿望到一个不讲中文的国度里去生活。二十多年后,已是俄亥俄州凯尼恩学院助理教授的她写出这篇评论,真是自然而然,初心不忘,篇末她提出期许:“作家必须始终沉浸于更为纯净的中国传统文学的溪涧,即使遭逢最荒芜的环境,也从未断流。”
严歌苓说国内的作家她比较关注这三位:王安忆、林白、毕飞宇。这三位我也读得较多,这证明我对严歌苓的理解大致不差,我们的关注点都在文字、文体、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