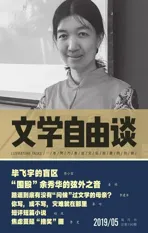“文学群”的圈子文化(外两篇)
2019-12-27□狄青
□狄 青
我的手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安装微信,不是因为玩个性,而是觉得有了微信大概会比较麻烦,需要不需要的链接和信息都会被人发送过来;再一个嘛,就是我知道自己比较无聊,别人不给我点赞我可能会着急,自己其实又懒得给别人点赞。所以当我似乎“不得不”有了微信的时候,好多人已经不怎么玩微信了,好多人也懒得再发朋友圈了,而我看到与微信相关的很多事情后却还新鲜到不得了,以至于起先被人拉进了好几个“文学群”也不懂得拒绝,反倒觉得好玩,多少有一点儿类似初进大观园时的刘姥姥,所有被我大惊小怪的,都是“群里人”早就习以为常的了。
对依附于QQ、微信等社交软件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文学群,我的最初认知并没觉得它们与我年少时便熟悉的各种现实中的文学社团有什么不同,本质上应该都是文学爱好者们凑到一起谈论文学、谈论读书、切磋写作技巧等等。然而,当我置身其中才发现,许多“文学群”其实没那么简单,里面的人相互间真正谈文学的极少,多数是借“文学群”来拉关系,来闲聊天,来卖自己积压的书,来搭讪异性或求异性搭讪,甚至有人公开宣称就是来寻找某种类似于暧昧的感觉的。了解得越多就越觉得奇怪,越觉得奇怪便了解得越多,发现原来混哪个圈子的都没那么容易,哪里有圈子哪里就是名利场。我还发现,“文学群”大抵上也可以分成两类,那便是“低端的”与“高端的”。前者更多的是打着文学的旗号,或抱团取暖,或组团自嗨;后者大多是只谈具体问题,或红包多少,或稿费几何。
咱先来说“低端”的。特点大约有如下几样:
首先,其数量极其庞大,以至于多到难以计数。这些大大小小的文学群几乎将从事文学创作的所谓“低端人口”一网打尽。这种群里的成员的共同特点是,作品多数只是“发表”在小网站抑或张贴于个人博客,很少有机会在纸媒上发表作品,即使发表了,也很少能上所谓文学“省刊”,更少“国刊”;即使上过“省刊”乃至于“国刊”,也基本上属于一次性的过客,很难给文坛上那些大大小小有话语权的人等留下印象。
其次,所谓“低端”的文学群,其群主多半属于游移于主流文坛内外的“边缘人”。所谓“边缘人”,也就是——你说他不出名吧,似乎人们还多多少少听说过他一点儿;你说他出名吧,肯定不是文学核心圈儿里的人,也肯定不是当下大红大紫的人。或者这类人虽然普遍都很能折腾,但因为其个人作品的影响力以及作品之外的一些因素,却很难被文坛的核心圈儿所接受。但这些群主一般都有比较唬人的身份标签,比如某某研究会、某某学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等等等等,这些研究会抑或学会往往前面都标注有“中国”“某省”字样,群主户籍地也会是北京抑或某一二线城市,给人以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印象,至少不像我年少时,经常收到的要求加入其“组织”的来信都发自某些崇山峻岭中的县城与乡镇,小一点儿的地图上都查不到。
再次,这种“文学群”的群主全数皆为男性,年龄普遍介乎于中老年之间,而群成员多半是以文艺女中年支撑的。她们许多人热情而浪漫,执着而天真,对他人警惕性低,对群主忠实度高,对文学娱乐性强,因而经常有因为群主对某某女群员过分“关注”与“关照”,以致引发其他女群员的攀比乃至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群主只要发朋友圈,群员们于第一时间回复“抱抱”“玫瑰”都是标配,有外向、敞亮的女群员,甚至还要给群主送“么么哒”。
另外,此类“文学群”的群主有时候也会发展几个“副群主”,毕竟动辄几百人的群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有人经常出来替群主“踢一脚”。但微信有规定,微信群只能发展三个“副群主”,于是群主也就有了待价而沽的机会。在一些“文学群”中,能当上“副群主”,当然就得和群主搞好关系,其次要么是相对文学成就更高一些的,要么就是比较有“活动”能力的,要么就是被传和群主各种“暧昧”的。
还有的虽然不是群主、副群主,但因为系报刊编辑,可以给人发稿,于是在群里也会排名靠前。倘使其人还在含有“中国”两字的报刊供职,在该“文学群”也就有了尊崇的地位,不仅可以时刻接受群成员的各种恭维与搭讪,还能够时不时接受一下女群员的各种“献花”与“拥抱”,虽然他们所服务的报刊是某些部委办局下属的专业技术类报刊,与所谓纯文学远隔千山万水。
群主可以拉人入群,也可以踢人出群,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还有“@所有人”之类的“特权”。比如群主想跟群里的中年女粉丝们起起腻了,或是发现群里有点儿沉闷了,就吐血发个一二百块钱的红包,于是乎,一些文艺女中年便又欢呼又起哄,群主万岁,群主抱抱,群主么么哒,此起彼伏。当然,几百人的“文学群”里,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活跃的、尤其是嘴上缺看门老汉的,无论是男群员还是女群员,都是少数,但示范作用十分明显。他们使人觉得,文学更像是玩玩闹闹打情骂俏,而群主有时候跟分散于各地的女群员“群聊”,商量开某某会的时候,挨个拥抱这些女群员,而先抱谁后抱谁需要提前排序派位……说不好这种“调笑”里有几许娱乐的成分,但肯定包含了某种意淫的味道。
“文学群”的群主手里最好掌握有某个奖项,且是该奖项的设立者和操持者,他想让谁获奖谁就能获奖。这些听起来貌似十分“高大上”的文学奖项,往往只是挂靠某一皮包学会或某一空壳单位,实则就是群主个人说了算,喝一顿酒,就能趁着酒劲儿“预定”出去好几个奖的名额。这样的结果,自然会让女群员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群主周围。
至于“高端”文学群,则是另外一番景象。这一类文学群的成员往往地位相近、处境雷同,比如都是一些相对知名的文学期刊的编辑,或者都是作协系统的同级官员,或者同为某一届高研班同学、某一次作代会的代表,大家你好我好半斤八两。如果同为文学杂志的编辑,就互换发表阵地,你挣我的稿费我赚你的稿酬;如果皆系作协系统的官员,就互给机会,你找我到A省采风,我请你来B市研讨。苦的就是那些既无文学刊物的阵地可交换,也非作协系统内能说说道道的人,对不起,大概率是进不到这种圈子里来的,就算偶然间进来了,也不会有人理你,大伙心照不宣地“淡”着你,直到你自己知趣地“退群”为止。
当然,上述也只是所谓“高端”文学群当中的一种。还有那种因评选某某文学奖而偷偷给评委与想要参评的作家建立的群,也有因同为某某届某某委员某某代表而建起的群——后者往往更高一个层面,你想啊,能够靠写小说、诗歌成为委员、代表的,那可不是一般的文人啊。在这种所谓“高端”的文学群里,难觅文艺女中年女青年的身影,这倒不是因为“高端”文学人士不需要与女粉丝搭讪、调侃、互动、暧昧、互相送温暖,而是他们一般不会太没顾忌,毕竟,与“低端”文学群的群主比起来,“高端”文学群里的人士身份接近、水平相当,谁也难成别人的“头领”,谁都不会甘当谁的喽啰。而且因为多少都算是文坛中的知名人物,在公共场合——哪怕是文学群里——爱惜羽毛,显然也是必要的。
时代变得飞快,但我发现,快的只是科技,只是工具,只是表象,而人心实际上是没怎么改变的,即使变也是变得非常缓慢。所以,不要因为文学爱好者凑到一起,由实体的文学团体变成了网上的“文学群”,就唬人了,就“高大上”了。人性的很多东西是没怎么变化的,甚至,因为网络的随意性,一些人反倒更加没了顾忌。就像文学,不是说科技发展到一塌糊涂,文学也会随之发展到一塌糊涂,说很多文学创作的成色根本比不上以前的光泽,这话,我想一点儿都不过分。
文人的好日子与坏日子
唐朝多数时候,文人活得都比较自在。所以李白才会让高力士给他脱靴子,且能“天子呼来不上船”;白居易才会调侃“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段成式才放着闲官不做,回家写那些盛世背后奇奇怪怪的人与事;高适也才能想归隐了不打招呼就走,想做事了马上出来当官……这一切仰仗的都是彼时大唐高度的物质文明与文化自信,所以才会以博大的胸怀包容天下知识精英。而且这种包容往往还是全方位的,因此,大唐的历史天空才出现了群星璀璨的辉煌景象。
能与唐相提并论的唯有宋。两宋同样是大家辈出,文化、艺术极为繁荣鼎盛的时代。宋是奉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赵匡胤兵变篡位起家;依后周柴氏的视角和尺度,他乃败坏政治伦理之乱臣贼子,老赵深知给他黄袍加身的那些武将随时也能把黄袍披在他人身上,于是他首先做的便是“杯酒释兵权”,摆明了抑武扬文的立场。两宋于不同时期推出了一系列优待文人的措施,包括大量增加科举考试登科名额及提高文人待遇。当时的太学,每位太学生都有餐补,且每有新君登基,餐补标准都会提升一截。
叶梦得于两宋四朝为官,见多识广,学识渊博,其《避暑录话》记载,赵匡胤曾立碑于太庙密室,后世君主祭祀及新皇即位,均须恭读碑文: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对文人不加田赋之税。当年,范仲淹就曾多次赞叹,大宋开国以来就没有杀过大臣,是史上从未有过的盛德。
然自唐宋后,文人的好日子就基本过完了,接踵而来的多是坏日子。元明清三朝,文人要么脑袋搬家,要么脊梁打断,剩下的只能做个犬儒苟活着,依靠写点颂圣诗文来讨赏过日子——其实,“犬儒”这词儿就是于唐宋后流行开的。读书人蜕变成只为功名利禄光宗耀祖而读书,成为依附于皇权的寄生阶层。结党营私,奢靡腐败,权谋术、厚黑术渐至高峰。如明万历前十年,首辅张居正独揽大权。万历十年二月张居正病重,消息一经传开,从官府到民间立马掀起为他祈福高潮,官衙工作瘫痪,官员支出公款,争着跑到道观寺庙为张居正做法事,祈祷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除此之外,官员还用公款雇文人写贺词。彼时,汤显祖就曾在文章中提到,张居正病重期间,有京城文人靠代笔写贺词,仅月余,竟赚白银三千两,令人瞠目结舌。
在张居正失势被清算期间,大量原依附张的人反咬一口,安在张居正身上的罪名更荒唐可笑。御史杨四知指责张居正欲趁皇长子诞生之机加九锡,仿效曹操篡权。他还说张骄奢淫逸,家里有银盆三百多个,每次吃饭,都要不停地听着打碎玉碗的声音才能下咽。他的奏折连皇帝朱翊钧都看不下去,下诏说: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你们一句话都不敢说,现在他倒了,一个个却胡说八道。而这些所谓的“言官”,哪一个不是文人出身?就说杨四知吧,于彼时文人中也曾被冠以“著名”二字。
明清萨尔浒大战,努尔哈赤崛起,明朝局势岌岌可危,而有能力力挽狂澜的,非辽东经略熊廷弼莫属。萨尔浒战后,熊临危受命,严惩败兵,整顿军备,又选拔精锐组建兵团,对努尔哈赤进行反击。万历四十八年,他更亲自率兵击退努尔哈赤进犯,辽东战局转危为安。但熊廷弼千不该万不该得罪了文人团体“东林党”。随着万历皇帝驾崩,东林党遂成为揭批熊廷弼的急先锋,先弹劾熊廷弼,后捧上东林党人袁应泰接班,哪怕袁丢了沈阳,被迫令熊廷弼复出,仍不依不饶,扶持王化贞,继续与熊对着干,直到辽阳沦陷,宁远以东国土尽丧。
天启年,阉党魏忠贤当权,清算东林党,一批被东林党排斥的文人马上依附过来。整东林党人最起劲的,就属阮大铖等几个文人。那时,于不少文人而言,即使国亡了,也得把与己对立的文人踩于脚下。以至于清兵围南京城,城内弘光朝廷的两拨文人还在为某个名分高低争得你死我活。如此斗来斗去,明不亡已无天理。
所以说,文人有没有好日子过,固然有明君暴君、盛世乱世的外部因素,但文人的坏日子里,却难说就没有自己“作”出来的成分。
天才的文人
有天赋的人很多,但可以被称作天才的却很少。叔本华认为,这个世界上一亿人当中只会有一个天才。他说:“有天赋的神枪手能打中别人打不中的目标,而天才神枪手是可以打中别人看不到的目标。”他还说:“天才是我们从他那儿学习而他未曾向别人学习过的人。”这门槛未免太高,如果照叔本华的意思,我们这世上能够被称作天才者恐怕凤毛麟角,因为门槛横在那儿了,绝大多数人怕是迈不过去。能迈过去的,亚里士多德算一个,他在逻辑学、自然科学、修辞学方面都是开先河者;苏格拉底、荷马、萨福等人也沾边。这些人多是两千年前的人物,而近现代嘛,“自称”抑或“被称作”天才的人,可谓汗牛充栋,但公认的却极少,爱因斯坦或许算一个。
1882年,奥斯卡·王尔德到达美国。过海关的时候,他对美国海关人员说:“除了我的天才,我没有什么需要申报的。”近代美国著名作家格特鲁德·斯坦因说,历史上犹太人只出过三位天才:怀特海,毕加索,还有一个是她自己。而另一位美国作家约瑟夫·爱泼斯坦针对此则说:“王尔德和斯坦因都算不上天才,他们所拥有的只不过是宣传自己的天才罢了。”这话未免不留情面,但也不算错。虽然我喜欢王尔德,但倘若使用叔本华的标准,他难说就是真正的天才。
那么,除了爱因斯坦,谁才算真正的天才呢?比较近的例子,肯定有人会想到霍金,因为不止一个人说他是“第二个爱因斯坦”。但霍金生前却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讲:“或许我符合一个残疾天才的形象。至少,我是个残疾人,虽然我不像爱因斯坦那么天才。因为公众需要英雄,当年他们让爱因斯坦成为了英雄,现在他们又把我造成了英雄,尽管我远远不够格。”
记得很早前曾读过福楼拜的一篇名为《布瓦与白居谢》的小说。描写的是两个想要获得全部知识的人布瓦与白居谢,二人一起学画、种菜、培花,又一起研究化学、解剖学、生理学,还攻读历史、哲学、宗教等,并钻研催眠术,而结果却是一事无成。加拿大学者曼努埃尔说:“福楼拜笔下的这两个人发现的是我们一直知道但很少相信的,那就是对知识的累积并不是知识。”这话想来倒是颇值得玩味。
的确,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保存其想知道的所有知识,人脑虽然拥有1000亿个神经元,却没有哪个人的大脑曾被填满过。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一个人达到处理能力的极限之前,这个人就已经达到了生命的极限。有人计算过,假使让一个人在70年寿命中所学知识的速度基本恒定,那么,即使把这一数字乘以10倍,那么这个人的知识量最多也只有1G,而一块儿小小的移动硬盘的容量,也要比这多上几百上千倍。所以,寄望于靠“填鸭式制造”产生天才是不现实的。
1978年3月9日,来自全中国的21名少年被选拔进入中国科技大学,成为中国首个少年班的首批大学生。他们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11岁,被媒体称为“少年天才”。而今,40年过去,有媒体探访这些“小天才”们后续成长发展之路,其中曾被誉为“中国第一天才少年”的宁铂,19岁成为内地大学中最年轻的助教,但在21世纪初却辞职,遁入空门,潜心礼佛;还有的“天才”,上大学后被劝退,有的则销声匿迹。少年天才们进入社会后的发展,无疑是面镜子,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审视这种所谓“天才”教育的内在问题。
霍金几乎拥有一个天才所需要的全部传奇因素,比如他生于伽利略的忌日,死于爱因斯坦的生辰,拥有聪明的大脑与多舛的命运等等,但他同样认为天才不是靠“训练”获得的,比如通过一些匪夷所思的技巧和重复性的训练,教会人们快速记忆、撰写文章以及计算数字的套路。在霍金看来,天才的出现更像是某种化学反应,比如一种元素与另一种元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突变”,这可以从对高斯与爱因斯坦的大脑研究中得到旁证,因为至今都没有科学结论说,他们的脑结构与常人存在明显差异。
许多人最多只是有点天赋,却被奉作天才。踢一百场球终于踢进一粒进球的运动员都可能会被称为足球天才,出版了一两册诗集的少年会被称为文学天才,刚演了一出戏的“小鲜肉”会被捧成表演天才……于是理解了我们如今为何能那么轻易地便称谁谁谁是大师,降低的看似是门槛,实则是我们对许多事物的尊崇与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