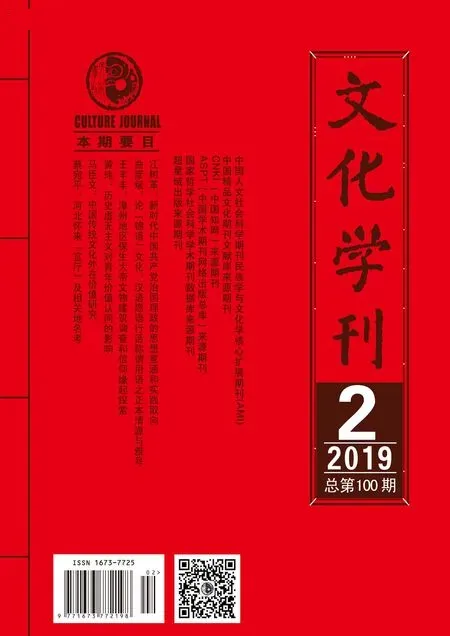论我国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法律制度的完善
2019-12-27刘贝
刘 贝
近年来,由于劳务派遣的机动性和灵活性,因此很多企业都采用了这种用工方式,但是,当前法律法规的漏洞导致在劳务派遣过程中经常出现纠纷,同工同酬问题更是矛盾的聚焦点。我国劳动法明确了同工同酬的基本原则,其合理性和合法性显而易见,但在实践操作中,对于该基本原则的贯彻仍然不足。调查显示,劳务派遣员工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上的缴纳概率分别是66.5%、72.1%、63.2%、80.4%。除了失业保险,其他险种的缴纳率都低于正式员工。部分劳务派遣员工甚至都无法正常享受社会保险,一些劳务派遣公司钻地方制度的空子,更加加剧了同工不同酬的情况。
一、同工同酬的概念和重要性
(一)同工同酬的概念
同工同酬是我国劳动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劳动法对于工资分配的重要规定,也是劳动者平等的体现,劳动者在劳动中提供了相同的工作量,就能够获取同样的劳动报酬。同工同酬问题涉及以多个方面,如不同性别员工同工同酬、正式员工与合同员工同工同酬、编制内员工与非在编员工同工同酬等,劳务派遣员工付出与正式职工相同的劳动时间和同等质量劳动,取得了一样的工作成绩,就能够得到相同的劳动报酬。这里的劳动报酬包括基本工资以及奖金和福利等。同工同酬体现了公平劳动的基本原则,我国《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
(二)同工同酬的重要性
劳务派遣员工与合同工存在一定区别,劳务派遣员工通常需要承担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有时也作为正式员工的补充和辅助,但当前来看,很多单位将劳动派遣工当作正式员工使用,令其承担与正式员工相同的工作,并要求其取得与正式员工相同的工作绩效。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派遣员工通常工资待遇偏低,用人单位出于节约成本考虑,喜欢聘用劳务派遣员工。
在很多实行劳务派遣制度的单位,劳务派遣员工的待遇通常偏低,同工不同酬情况普遍,这种现象与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要求相悖,也侵犯了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同样,大量存在的劳务派遣员工也给当前我国的劳动制度带来了冲击和挑战,这种现象如果继续下去,必然不利于我国和谐社会劳动关系的建立,甚至影响社会稳定,因此,有必要针对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问题进行研究,用完善的法律制度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保障劳务派遣员工的切身利益,进一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二、我国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实施面临的法律问题
(一)对“同工同酬”缺乏明确定位
对于法律规定来讲,清晰无歧义的定义,对于概念的界定明确是法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虽然从立法实践看,为了体现法律的普适性,各国在进行立法时,通常会采用一些模糊性语言进行表述,但这些模糊性表述的前提是涉及的法律事实无法明确。如果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缺乏明确细致的范围界定,就会为该法律内容的运用设置人为障碍。通过对我国以及域外国家的“同工同酬”概念进行分析,发现大多数国家并未作出明确定位。《劳动合同法修正案》(以下简称《修正案》)针对“同工同酬”问题仍然缺乏详细的立法解释;除此之外,后续出台的《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也并未对“同工同酬”问题进行明确阐释,基本只是照抄修正案内容,这样的立法现状就给“同工同酬”的适用带来了隐患。虽然《修正案》中规定将“岗位”因素作为“同工同酬”中相同工作的界定标准,并且具体区分了单位内部同类岗位的认定标准,但在实践中的运用仍然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广州市的劳务派遣用工企业,它们口中的“同酬”只是基本工资相同,而年终奖金、福利津贴等,劳务派遣员工仍然远低于正式员工;对于与正式工相同或者相似的工作内容,设置不同岗位,实施不同薪酬制度。因此,我国法律亟待对“同工”标准进行细化。同理,“同酬”概念的理解和延伸也有很多,《暂行规定》等并未对其明确化,这样造成“同酬”的适用在实践中存在很多问题。
当然,从立法层面看,针对“同工同酬”进行准确界定存在一定困难。因为“同工”和“同酬”本身就具有丰富的含义,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参照不同的判断方法,就会对其所表达的内容产生迥然不同的理解。因此,相关立法人员必须基于劳务派遣制度所彰显的价值目标着手,在劳务派遣实践中对现有规定进行明确和完善。无论立法者采取何种立法技术,以下问题都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容易困惑的地方,必须从立法层面给予明确:第一,“同工”的判定标准;第二,“同酬”的具体范围;第三,《修正案》中“相似或相近岗位”的判定标准。
(二)义务设定不明导致推诿
《修正案》中关于“同工同酬”的立法原意是为了保障在劳务派遣中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同工同酬权”,维护弱势方的合法权益。由此,我们能够确定,在劳务派遣中,工人是权利主体,而劳务派遣单位以及用人单位是义务主体,因此,针对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进行明确义务规定是“同工同酬”原则得以落实的重要保障。从《修正案》和《暂行规定》的相关规定来看,其设计义务主体义务内容的法条屈指可数,单从数量分析,立法对于义务主体的义务规定非常少;从法律规定的具体内容看,大多数都属于原则性规定。这样的立法现状必然造成“同工同酬”的实践困境。以公积金的缴纳情况为例,《修正案》第六十二条与《暂行规定》第九条规定用工单位负有支付劳务派遣员工与工作岗位相关的福利待遇的义务,由此可以推测用工单位应当承担缴纳劳务派遣者公积金的义务,而《暂行规定》第八条又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有支付劳务派遣员工劳动报酬的相关义务。从上述规定可以认定,劳务派遣单位为公积金缴纳的义务主体。立法上对于义务单位的设定不清,容易导致司法实践中劳务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相互推诿的情况。
立法上对于“同工同酬”义务主体的义务内容规定不明确也是当前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障碍。《修正案》和《暂行规定》对于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这两个义务主体的具体义务内容并未细化,在劳务派遣协议履行时期,虽然对于具体的义务内容进行了规定,但相关规定仍然不详细,不够明确。立法上对于具体内容规定的粗漏,给司法实践中义务履行带来了障碍。例如,某国有企业在2017年依照《暂行规定》第八条的内容履行了为劳务派遣员工缴纳社会保险的义务,但从义务的具体履行情况来看,与正式员工相比,劳务派遣员工的社保费用缴纳要低很多。出现上述情况的根源正是立法上存在漏洞,虽然立法对相关义务进行了规定,但对义务的具体内容,如社保费金额的缴纳、社保费用缴纳的地区等都未明确规定,从而给用人单位提供了规避空间。
(三)监督机制欠缺
参照《修正案》第六章“监督检查”部分的内容,其针对监督的具体实施机制进行了初步建构,但受制于法律规范特性,其监督条款的设置绝大多数都是原则性内容,并没有涉及具体的监督办法。由此可以发现,当前我国劳动法语境下的监督机制仍然欠缺。此外,参照上述监督条款的具体内容,其中能够被用于“同工同酬”的规定更是稀少。立法上针对“同工同酬”的适用缺乏监督规范,由此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适用的各类问题便有其必然性。监督机制的缺失导致当前对于“同工同酬”成效的监督缺位,这也是当前“同工同酬”实施中的又一法律问题[1]。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
1.监督主体的不明确造成监督缺位
前文提到,针对“同工同酬”的监督,实践中只能依靠劳动法语境下的监督机制。劳务派遣的主要监督主体应当为各地的劳动行政部门,而根据《修正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工会也被纳入了劳务派遣的主体监督范围。但对于该规定是否能够用于“同工同酬”的认定,仍然存在一定疑惑。工会作为监督主体的话,其主要监督用人单位的相关合同履行状况,由于劳务派遣自身的特殊性质,使得雇佣与使用分离,那劳动单位的监督主体就包括劳务派遣单位和用人单位,而用人单位是支付劳务派遣员工相关报酬的最终主体,因此,在“同工同酬”的监督中,工会是否能够承担监督责任,并没有相关立法明确规定。《修正案》中相关规定的不明确,使得在“同工同酬”司法实践中工会的监督地位缺失。
2.监督范围不明确导致监督缺位
立法上对于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监督范围并未进行明确规定,只是在七十四条的规定中略有涉及,这种规定不详的情况,是我国当前“同工同酬”实施过程中监督缺位现象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这就会造成司法实践中出现下述问题:第一,监督力度较小,实践中履行监督义务的积极性差;第二,监督层次不高,当前我国对于“同工同酬”的监督仍然停留在较低层面,这就会造成正式员工与劳务派遣员工的待遇差别。
3.缺乏相应的监督程序规定
我国当前立法对于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实施缺乏具体的程序性规定,只是进行了原则性说明,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上相关具体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措施的欠缺,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监督主体主要是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对于“同工同酬”的鉴定也只停留在书面报告上。监督程序的缺失,监督的形式化,给了劳务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法律空档。例如,某公司将劳务派遣员工集中到基层岗位,且该岗位仅安排劳务派遣人员,不安排任何正式员工,这就造成“同工”前提的缺失,“同酬”也就无法实现,这就是实践中相关监督程序规定缺位带来的不良影响[2]。
(四)法律责任不明确导致问责难
法律责任是法律最重要的组成要素之一,也是保证某项法律规定顺利实施的前提。同样,在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实施过程中,立法上明确其法律责任也是该制度实施的重要前提。参照我国当前的法律规定,关于“同工同酬”的法律责任规定很少。只有《修正案》第九十二条第二款涉及了上述内容,从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可知:第一,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责任主体是劳务派遣公司和用人单位;第二,立法上更偏向劳务派遣单位的责任;第三,责任承担方式主要为行政责任,但具体的细致规定欠缺,导致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难。《修正案》中为了保障劳务派遣员工的合法权利,单独设置了连带责任,这样的规定也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履行“同工同酬”义务,但是,连带责任同样可以分为一般连带责任与补充连带责任,在不同的连带责任形式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的方式存在很大区别,而立法中针对上述内容并未说明。
三、我国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立法对策
(一)明确界定“同工同酬”的内涵
立法上对于“同工同酬”具体含义的界定不清晰,是阻碍“同工同酬”制度切实落实的主要障碍。法律的一致性是法律的内在要求。因此,针对“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界定,必须建立在当前《修正案》规定的基础上。因此,对于“同工”内涵的界定,也需要建立在《修正案》的现有规定之上。由于“岗位”的内涵十分丰富,因此在“同工”用岗位相同进行初步界定后,还需要对这个标准进行细化。在生活实践中,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岗位可以有很多不同分类,依照其性质可以分为职门、职组、职系;依照岗位工作的困难程度,可以进行职级、职等的细致划分。笔者看来,我国的岗位分类是以国家规定的职业分类为准,但具体岗位设置方面,各单位仍然具有主导权。为了避免实践中用工单位钻制度的漏洞,增强“同工同酬”的可操作性,更好地保障劳动派遣员工的合法权益,在岗位的立法方面,不应当过于严格,否则容易被用工单位“合理规避”。对于“同工”的界定,应当采取横向的分类方式,这样的选择出于下述原因:第一,如果采取纵横结合的分类方式,则需要满足岗位性质、内容等不同要求,这种选择太过严格,不利于司法实践;第二,如果选择纵向分类方式,忽略具体的岗位性质、内容等,这显然不符合“同工同酬”的基本要求;第三,选择横向分类的方式,以“相同岗位”为基础,避免用工单位采用重新定岗等方式规避义务,符合当前司法实践要求。对于用工单位设置相同或相似岗位的问题,笔者看来,为了增强“同工同酬”的司法实践性,顺利实现立法目标,更好地保障劳务派遣员工的基本权利,在立法上需要设置较为宽松的认定标准;对于“相同岗位”界定,以职组作为准则;对于“相近”岗位界定,以职门为准则。
对于“同酬”的界定,则要坚持“全部工资收入”准则,该工资内容包含员工全部的收入及福利事项,包括基本节日福利、岗位工资、加班补贴、话费餐费津贴以及其他项目补贴等。尤其对于下述种类福利,用人单位必须一视同仁:第一,法律规定的具有强制性的福利待遇,如社会保险费、独生子女费、防暑降温费等,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给劳务派遣人员;第二,单位集体福利,如夏天的冷饮、员工的健康检查、餐饮福利等,用人单位需要同样提供劳务派遣人员。
(二)明确同工同酬义务主体的具体义务事项
确立劳务派遣公司作为第一义务主体,劳务派遣公司与劳动者签订用工协议,是我国劳动合同关系中规定的“唯一雇主”,劳务派遣单位需要承担其法定义务,如支付劳务派遣人员的酬劳、为劳务派遣人员办理社会保险等,还需要履行相关默示义务,确保双方信任关系等。从实践方面看,将劳务派遣单位设置为第一义务主体符合“同工同酬”实践的具体要求。在我国当前劳务派遣形式下,劳务派遣员工处于弱势地位,如果将用人单位规定为第一义务主体,劳务派遣者在维护合法权益时,需要与用人单位进行谈判。而生活实践中,用工单位通常力量雄厚,个人很难与之抗衡。将劳务派遣单位设置为第一义务单位,则便于维护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劳务派遣单位与用人单位相对均衡,具备更强话语权。
对于具体义务事项,在劳务派遣协议签订阶段,需要严格依照《修正案》和《暂行规定》的内容要求,依照“同工同酬”原则,对于派遣岗位的名称、工作内容以及明确的薪资待遇进行明确说明,并要求被派遣人员实地调查,在协议中细化具体事项的不同标准。在劳务派遣协议的履行阶段,劳务派遣单位需要及时提供相应劳动报酬,不得拖欠或者拖延支付,监督用人单位是否切实履行“同工同酬”义务,面对劳务派遣人员的质疑必须履行调查义务,在劳务派遣人员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时,必须协助维权[3]。
(三)健全监督机制
首先,明确监督主体。监督主体的确定要在劳动合同法的语境下,将劳动行政部门设置为“同工同酬”的监督主体,实施监督。将工会作为监督补充。其次,明确监督范围,包括劳动报酬以及相关福利待遇情况等。最后,科学设置监督程序。明确将劳动监察程序设置为登记立案、现场取证、事项处理、下发处理决定书、送达五个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