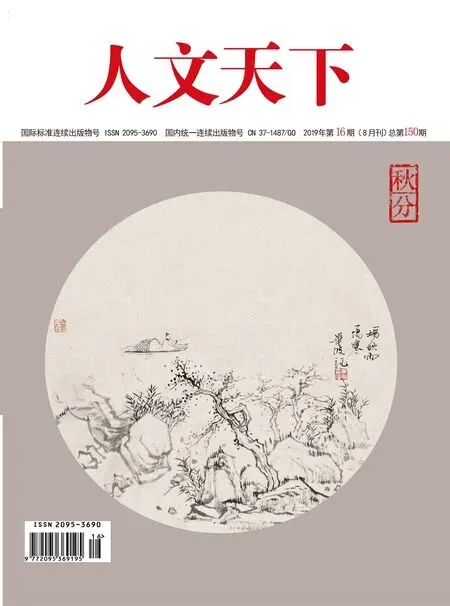《林泉高致》蕴含的儒家生态美学观念论析
2019-12-23车荣晓
车荣晓 戚 静
生态美学作为我国学术界一个新兴学术命题,在中国古代艺术理论中寻找生态美学的学术资源并加以阐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当前,对《林泉高致》的研究尚未有学者提到书中作为理论基底的儒家思想呈现出的生态美学观念。从儒家思想的视角来看,书中呈现出极为丰富的生态美学观念,值得深入研究。
在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也难免产生倦怠紧张的情绪。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解决方式便是从自然山川的审美中缓解情绪。但他们毕竟无法抽身而出,真的走进自然山川。郭熙在山水画艺术中构建起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世界,让文人士大夫能够“不下堂筵,坐穷泉壑”,从而获得心灵的栖息。
一、自然的人格化象征
北宋是儒家思想得以快速发展的时期,郭熙的宫廷画师身份和他的绘画理论构建,都体现出其儒家思想观念,其理论中理想的山水画形态正如当时的社会形态一般以儒家“礼”的规范构建的。郭思在该书《序》中写道:
《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谓礼、乐、射、御、书、数、画之流也。……《论语》“绘事后素”,《周礼》“绘画之事后素工”,画之为本,甚大且远。[1](P3)
在郭思看来,其父的山水画理论正是依托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借用孔子“绘事后素”的观念,郭思确立了“礼”与绘画都是后起之事,同时也肯定了后起之“礼”与绘画作为艺术存在的必要性。
郭思《序》中着意强调了其父郭熙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且肯定郭熙真正的成就在于其良好的道德修养,而并非艺术技巧的卓越:
咦!先子少从道家之学,吐故纳新,本游方外之家,世无画学,盖天性得之,遂游艺以成名焉。然于潜德懿行,孝友仁施为深,则游焉息焉。此志子孙当晓之也。[1](P3)
可见,呈现在郭熙山水画艺术中的精神内涵正是儒家的审美观念,这一生态美学观念和儒家对人类社会规范的“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郭熙通过对自然生态表达的对象加以选择和主观改造,构建起一个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画面形态。在画面布局中,通过上留“天”,下留“地”的方式,也呈现出一种人类社会形态的象征;在对山水和林石的布局中,也以“君臣上下”和“君子小人”[1](P72-73)譬喻,这正是对自然生态的人格象征。
在郭熙的艺术理论中,自然生态的价值只有同人类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能实现。天然的、本真的自然生态缺失了人的参与并不能够产生独立的审美价值。而在人对自然生态的参与过程中,审美首先是从人格精神的象征入手,而非感官快感。郭思在书中不断强调儒家思想的重要性,其原因在于,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而言,感官快感并非真正地审美来源,最伟大的审美形态恰恰隐含于道德的崇高之中。因此,在山水画的艺术构建中,道德暗示才是其真正意义上“美”的来源。据此,《林泉高致》所呈现出的生态美学观念最重要的一点便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构建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理想“自然”。
二、“坐穷泉壑”的审美观照
虽然郭熙将山水画的审美形态在最本质上归结于儒家道德规范的暗示。但是,山水形态的审美意义却是儒家道德规范得以实现的最重要因素。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礼”的规范与“乐”的调和是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协调统一,共同构建起和谐的“礼乐共同体”。儒家的道德规范也必须要通过“乐”的调和才能够成为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的艺术形态。“乐”要求“礼”以某种愉悦的方式表达出来。《林泉高致》中“坐穷泉壑”的审美观照正是以“乐”的精神对“礼”的规范加以调和,让严肃的道德规范有了艺术的审美形态,进而成为人们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循。同时,“乐”的表现形态更是为因“礼”(节义)而产生的紧张焦虑情绪提供了缓解的通道:
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手郁然而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本意也。不此之主而轻心临之,岂不芜杂神观,溷浊清风也哉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大都不能真正走入自然山川,隐逸生活只存在想象的精神世界。而山水画艺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走向自然的途径,对山水画作品的欣赏也就成为掌握自然生态之美最为便捷的通道。
“不下堂筵,坐穷泉壑”是宗炳“卧以游之”一说的发展。宗炳喜爱山水,但因晚年身体不佳无法亲身体验山水之乐,便将山水画于墙壁之上,只需卧于家中便可游览山川。郭熙的这一理念与宗炳相近,在他们这里,绘画中的山川都作为自然山川的替代,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由此产生愉悦的审美情感,从而获得生活的兴趣与动力。因此,郭熙的“坐穷泉壑”是以“林泉之心”对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照,在这样的关照过程中,目力所及不再是真实的自然山川,而是心与自然的合一。如此境界之中,审美关照不再纯粹建立在人的主体意识上,而是在将人的主体意识消泯于自然生态之内。自然拥有了人的主体意识,人也忘乎自我的存在。
但是,本然的自然生态本身还不具备足够的感染力和典型性,这便需要艺术家对本然的自然生态进行选取与加工,从而构建更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艺术创造,以在有限的画面构成中展现出比真实自然生态更具感染力的视觉形象:
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入善品;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何者?观今山川,地占数百里,可游可居之处,十无三四,而必取可居可游之品。君子之所以渴慕泉林者,正谓此佳处故也。[1](P16)
所谓“可游可居”之处,正是从自然生态的广袤世界中选取最具有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的部分进行的创作表达,从而使山水画作品容纳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情感内涵。这种对自然生态中本然的山川进行的选择恰恰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体现。
因此,可以说“坐穷泉壑”的审美观照是人与自然生态在艺术世界中的共融。这一过程中,审美情感决定了创作者对创作对象的选择,也决定了艺术接受者在接受过程中的联想和想象。通过艺术的精萃与典型化,中国山水画中呈现出比自然山川更具感染力的生态之美,从而为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在艺术世界提供了一个心灵休憩之所。
三、对山川林壑的“远观”态度
郭熙在书中提出的“三远”山水画理论,其意义不仅是山水画创作的理论指导,更有着深远的形而上意义。所谓“三远”,即要求山水画创作中采取远观的态度,而不是即身就之,深入到自然山川之内感受自然带给人的快感。郭熙这样阐释了“三远”的观点:
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高远之色清明,深远之色重晦,平远之色有明有晦。高远之势突兀,深远之意重叠,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缥缈缈。其人物之在三远也,高远者明了,深远者细碎,平远者冲淡。[1](P51)
从儒家美学观上来看,“三远”的艺术创作方法深受儒家美学影响,并体现在对待自然生态时的“远观”态度。因为远观,人的个体情感被淡化,不深入到真正的自然山川之中,而是在远处观望,人的审美情感便不至于由淡远平和的心境走向“酒神”式的狂喜。在对自然欣赏中产生“酒神”式的狂喜形态在中国直到明代袁宏道等人才提出。
郭熙所处的宋代,对自然与艺术审美欣赏的追求是“中和之境”。与郭熙同时代的理学家邵雍将艺术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认为“理”是世界的本源,对于艺术而言,也要体现出作为世界本源的“理”才能够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理学家们普遍承认艺术要表达情感,但是他们却反对强烈的情感抒发,认为情感的表达应当受到克制,以利于用一种客观的态度对待世界万物,探求作为本源的“理”的存在。针对如何摆脱自身情感的束缚,而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体现出“天下之大义”,邵雍提出了“观物”[2]的观点,认为在艺术活动中人不能够有过多的思想情感,而需要以“观物”的方式探索客观存在的“天理”。正如王国维所说:“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即是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来创造“无我”的“意境”。
郭熙的“三远”正是在实践上将中国山水画引向悠远的“无我之境”,但“无我”又绝不是“我”的全然消失,而是“我”的主体性隐匿于自然生态之间,不露痕迹。这样的审美追求是走向“中和之境”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儒家美学中,“乐”的精神是对“礼”的调和。在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指引下,“乐”贯通了人类情感与宇宙万物的联系,将外在的“境”与内在的“情”联系在一起。正因为“境”,“情”才被激发出来,从而使“情”“景”交融的“意境”最终完成。
郭熙以“远观”的视角完美地解决了愉悦与狂喜之间的矛盾。自然生态之美在山水画艺术中于远处被欣赏,欣赏者因审美视角之“远”,在获得情绪愉悦和心灵安憩的同时又不至于走向“失其正”“害于和”。如此,“远观”呈现出来的对于自然生态的态度,是在艺术中进行选择和典型化,以“中和”的审美欣赏之态度对待,而不是对自然生态本身加以修正。由此,人与自然生态之间达成和解,矛盾消失在“远望”的朦胧之中。
四、“天人同构”的生态观念
在汉代儒学思想体系之中,“天人合一”或“天人同构”的思想已突出地表现出来。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天”与人类社会拥有同构性,“人”也可以通过一定方式与天进行沟通交流。董仲舒说:
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人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3]
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出,这里的“天”成为高于“人”存在,“天”与“人”在精神与行为上共通,人必须顺应自然才能够得以兴旺。但在“人”与“天”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同时,人也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情感。董仲舒将自然人格化,让自然拥有了“先于人”的人格。因此,当接受者在接受自然生态之美的时候,也能够由自然自在的人格特征,把握到自然的生命迹象。郭熙在《林泉高致》中也将自然山川比拟为人,这种比拟的方式本身便是人与自然生态“同构性”的暗示:
山以水为血脉,以草木为毛发,以烟云为神采。故山得水而活,得草木而华,得烟云而秀媚。水以山为面,以亭榭为眉目,以渔钓为精神,故水得山而媚,得亭榭而明快,得渔钓而旷落,此山水之布置也。[1](P49)
这样的比拟本身便具有了“天人同构”的生态美学意义。在董仲舒那里,自然的春夏秋冬与人的内在情感共通。而郭熙将自然山川比拟为人,则是从形态与精神两个方面实现了自然生态与人之间的“同构性”。人之形态与精神在山水画艺术中以自然生态的审美形式呈现出来,让人与自然生态达成统一。
如此,因为“天人同构”的生态美学架构,人即自然,自然即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功利矛盾便在此艺术世界中消失。在山水画艺术世界中呈现出来的,也就唯有审美的精神境界。在这一精神境界中,自然生态生发出人的情感动态,让人在自然生态中感受到丰富的生命体验,这也便成为郭熙绘画理论中山水画生态美学的“景外之意”:
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秋山明净摇落,人肃肃;冬山昏霾翳塞,人寂寂。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见青烟白道而思行,见平川落照而思望,见幽人山客而思居,见岩扃泉石而思游。看此画令人生此心,如真即到其处,此画之意外妙也。[1](P26-27)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从传统儒家思想的角度出发,在山水画的自然审美形态之中,人不是以自身的本质力量投射到客观物象之中,而是感受“天”、“景”、“境”所表现出的人格特征,从而将“天”的这些情绪与精神以人的方式表达出来。通过画家的艺术创造,自然呈现出人的生命情态,让人在自然中感受到悠远的审美情致。
因为“天人同构”,自然生态在艺术中被视为生气蓬勃的生命体,也就获得了让人亲近的品性。因此,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将自己的心性寄托于山水之间,从而暂时忘却“尘嚣缰锁”,获得心灵的休憩:
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其旨安在?丘园,养素所常处也:泉石,啸傲所常乐也;渔樵,隐逸所常适也;猿鹤,飞鸣所常亲也。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1](P9)
君子对山水的喜爱在郭熙这里不但合乎儒家道德观念,还是对儒家思想的一种贯彻和维护。
因为中国山水画中“天人同构”的生态美学观念,自然生态成为具有生命体征的存在,也成为文人士大夫知识分子亲近而且“可游可居”的心灵休憩之所。“天人同构”的意义在于将自然生态赋予了人格的道德情态,使之具有了道德的崇高感。但同时,“天人同构”在赋予自然生态道德崇高感的同时还赋予了其审美特性,使得穷观极照下的山水形态在山水画的艺术世界中呈现出深远悠长的审美意义。
《林泉高致》一书的山水画理论皆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为基底,呈现出丰富的生态美学观念。通过在山水画艺术中赋予自然山川以人格化象征,本然存在的山林泉壑成为人的外化,也就同时被赋予了原本属于人类社会的“礼”的规范。由此,人类社会的规范也便成为山水画构图和山林泉壑布局的规范,道德含义被赋予其上,呈现出具有崇高感的艺术感染效果。而在“坐穷泉壑”的审美体验中,自然生态之美被画家深度挖掘并予以典型化,从而使自然生态之美在中国山水画中以更具感染力的方式出现,体现出“乐”的精神。这“乐”的精神调和了因“礼”的规范而带来的强制性,让“礼”通过使人愉悦的方式渗透于山水画艺术,从而达成“乐教”的道德引导效果。并且,通过对自然生态的审美,士大夫知识分子在“修齐治平”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倦怠情绪也得以消解。但在儒家美学的指引下,郭熙在其山水画理论中对自然生态的审美采取了“远观”的视角,这一视角指向了艺术审美的“中和之境”,既在远处因自然生态之美产生愉悦情绪,又不即身就之,让愉悦的“中和之美”不至于走向极端。由此,“天”(自然生态)与“人”在精神上达成共通,在情感上达成共鸣,实现了“天人同构”的境界。因此,在郭熙《林泉高致》中,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不是通过人力改造自然,以物理方式使自然从属于人,而是通过“天人合一”的方式,在艺术审美中实现人与自然生态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