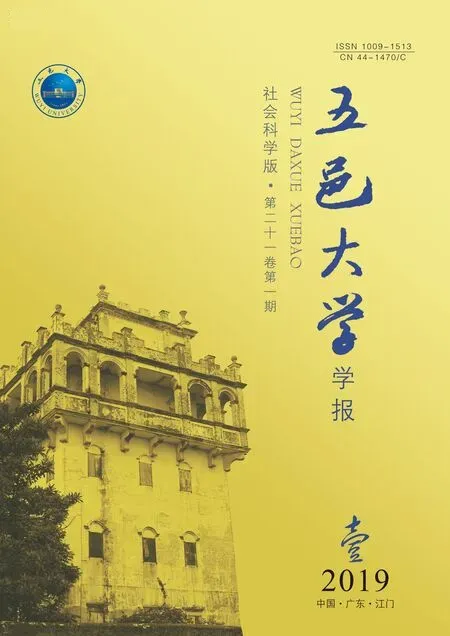代际冲突与华人移民的“无地方”
——再议《安乐乡一日》
2019-12-21许锬
许 锬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 英语教研室,安徽 合肥 230601)
一、引 言
华人移民家庭内的代际关系历来是美华作家关注与书写的重要内容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1937- ),便选择由“代沟”问题切入,藉日常生活场景叙写华人移民家庭中复杂多变的代际关系。在展示华人移民精神世界迷惘与无奈的同时,也传达了对于这些处于困境中家庭的理解与体认。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西方(主要是美国)的遭遇,多探讨华人移民家庭在种族、国族认同问题上的困惑与痛苦。研究者倾向于从文化断裂与移民第二代的背离、华人移民的漂泊离散(diaspora)以及小说文本空间的涵义等角度探析在美华人挣扎于文化冲突、身份认同、家国想象之中的特殊生存经历。 相较而言,研究者较少关注代际冲突与这些华人欲于新地寻求重生却终不得其所(out-of-place)的现实之间的关系。空间地域的移动、社会文化的差异,对所有的在美华人都是重大的冲击。相较于成年后方才移民至美国的父母,华人移民第二代多视美国为安身立命之所;但事与愿违,后者“依旧感到生活在不同的世界”[1]。本文拟以《安乐乡一日》①为例,借用人文地理学的“地方”概念,透过人—地(man-land)关系解析在美华人的生命体验之一:郊区华人在社区内的抗争与妥协,以探究这些人于美国“无地方”(placelessness)的根源。
二、 代际冲突与“地方”概念
从华人移民在美国的生存经验来看,20世纪60年代便居住在纽约近郊的安乐乡(Pleasantville)的伟成、依萍一家无疑是成功的:伟成事业有成、依萍在家相夫教子、女儿宝莉活泼可爱。然而,正是在这个安乐乡中,伟成一家三口却历经了心灵的迷失。其中,依萍母女对“中国人”(Chinaman)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引发的家庭矛盾便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一些研究者也曾指出,依萍母女的分歧与冲突需要放置在美国社会的大环境中加以解读[2],应当考虑到社区内的人际关系对于依萍的影响[3],而非单纯地论述两代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或其所秉承的价值观的冲突。换言之,人—地关系不失为解读华人移民家庭内部代际关系的新视角。
如果说,位于安乐乡白鸽坡的房子是伟成与依萍在美国安居乐业的象征,那么,从纽约城到安乐乡的移动、居住地的变化则预示着与此前不尽相同的地方经历与体验。与早期华工不同,身为华人新移民的伟成一家并没有被拘囿于唐人街的封闭社区中。相反,他们穿透了纽约的地理区隔,在美国民权运动崛起之前即置身于美国“中上阶级”[4]205的城郊社区。与繁华、多元且五光十色的纽约城相比,安乐乡显得安逸而又纯粹。于是,人—地关系就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安乐乡会对伟成一家产生怎样的影响?而后者又要如何与新居所建立有效的联系?毕竟,美国国会到1965年才废除歧视华人的入境限额[5]。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在美华人才逐渐搬离唐人街,分散到其他接受、尊重他们的社区之中。而美国的郊区,直到1980年,还是个排外地区。[6]149也就是说,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看,自定居伊始,安乐乡便不仅仅是一个高档的住宅区,当纯白人社区尚不是华人可以自由居住的领域时,伟成一家还要思考自身的处境、厘清其进入新地的方式以及他们所应当拥有的位置,以期于人—地的协商与磨合中将安乐乡转化为一个“建立了价值体系宁静的中心”[7]68。
依据人文地理学的观点,“地方”是一个“有意义的区位(a meaningful location)”[8]14,人们会“以某种方式附其上”[7]19。换言之,人、地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人对环境首先由识觉而获得经验和概念,再评价此经验概念,而后产生对待环境的意象和行为”[7]绪论:9;在认识空间并赋予其价值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找到内心对于地方的归属感、形成对于地方的认同,即人文地理学家阿格纽(John Agnew)所提出的“地方感”[8]14-15——人类对于地方的主观与情感上的依附。因而,从人—地的关联与互动分析伟成家中的代际关系,不难发现:依萍与宝莉之间的矛盾、分歧都与其“地方感”的形塑有关。母亲依萍来美国的时间本就不长,且在国内时就因“世家出身”而“受过严格的家教”[4]210;年幼的宝莉则是众多土生华人中的一员。不同的成长背景决定了二人在安乐乡中迥异的空间体验,而这恰恰也是依萍内心苦闷、与宝莉亲子关系紧张的根源之一。
三、白人社区里的“无地方”
对于依萍而言,五年的时光尚不能抹去内心对于安乐乡的陌生感。小说开篇的空间描写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依萍看来,安乐乡“与其他千千万万座美国大都市近郊的小城无异”[4]205,幽雅、静谧,但是,目之所及全然一片“异己的缺少人情味的景观”[9]。言语之间尽是对于新居所的疏离与抗拒,而这其中透露出的反讽意味[3]亦证明安乐乡其实是名不副实的。由于相关的地景描写折射出的往往是人们对于社会与生活的信仰,我们可以认为:宁静、宜居的环境并没有拉近依萍与安乐乡之间的距离,相反,置身于这个冷漠空洞且毫无生气的安乐乡,依萍很难对其产生主观上的情感。倒是无处不在的碰撞与失落尽显华人与安乐乡——一个纯白人社区之间的隔膜。初到安乐乡,不善交际的依萍曾经参加过一些社区的活动,社区里的其他太太也努力“尽到美国人的地主之谊”[4]209。只是,每逢聚会,刻意的中国人装扮、程式化的中国人模样总会令依萍痛苦不已;可除了“托辞推掉”[4]209,依萍似乎并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
作为社区里唯一一位中国女性,依萍的穿着、姿势与仪态全部都在白人太太们的凝视与监督之下,并受制于后者所谓的“美国习俗”[4]209。只要生活于此,依萍便没有逃脱安乐乡社会价值规范的可能,她所能做的就是呈现华人在主流社会/文化中被接受的形象。在安乐乡,依萍外在的身体行为都是其“东方‘他者特性’(otherness)的典型再现”[6]268,其存在被更多地用以佐证或演绎居民们所设想的中国人形象,而非一个真实地生活于此的个体。就依萍而言,如此不平等的人际关系当然是毫无人情味的,她也不可能会心甘情愿地依附于其中。而且,由于她无法从这种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找到恰当位置,也就谈不上什么情感上的连结。此外,考虑到以“情境为中心”[10]135的中国人主要是通过对他人的依赖“获得社会地位与心理上的双重安全”[10]262,我们能够预见:依萍是无法从安乐乡的太太社团中找寻到其面对新的生活环境所必须的安全感的,更奢谈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立足于其中的人格与尊严。简单地说,依萍不过是一个无法与安乐乡进行日常交往、互动的“局外人”[8]302,除了疏离感与“格格不入”(out of place),被孤立、被他者化的她不可能与新地发生什么有效的联系,深植人心的华人刻板印象更是阻碍了其内心、情感上对此地的依赖或认同。因而,安乐乡之于依萍仅仅是个没有实质性意义的、具体的区位(location)或位置(site)而非生活的中心,亦不是可以维系与确认自我的地方。
如果说,“地方”概念关注的是人们对于空间或地方的感觉与体验的演变,那么,读者便不难理解无奈退守至家庭的依萍对于其自身“中国性”(Chineseness)的强调与重申:中国不仅是生身之地,更是她可以依恋的空间,那里保存着她的过去亦承载着她的全部情感与人生的意义。如段义孚所言,藉由直接和亲切的经验可以在符号与概念上对地方和物体有更多的理解[7]24。与此同时,读者也大致明了宝莉拒斥“中国人”(Chinaman)称呼的缘由。作为华人移民的子女,宝莉在纽约城长大,三岁时即随父母搬至安乐乡;作为土生华裔,宝莉自然是要落地生根的。一来,“中国”对宝莉来说,既陌生又遥远;二来,自搬至安乐乡,宝莉便彻底失去了与中国人的一切联系,因为父亲根本“不肯进城”[4]208,母亲也就“与纽约城中几个中国朋友都差不多断了来往”[4]208。换句话说,中国终究不是宝莉的出生地,仅有的血缘关系不可能掩饰切身的空间体验及身体记忆的缺失:在不肯讲中文之后,这个“连父母的中国名字都记不住”[4]210的孩子即完全丧失了熟悉、了解祖籍国文化体系与历史脉络的机会与可能,相关的空间感觉/知觉几近为零,至于其对祖籍国的情感依附便也就无从谈起。在宝莉的认知中,“中国”注定将沦为一个地理位置,而非其所应依恃的生命意义的源头。时空阻隔、加之中美双方迥异却又实力悬殊的文化,宝莉与祖籍国之间的人—地关系的建立遂成为一种不可能,而这也是她不喜欢“中国人”(Chinaman)称呼的重要原因。
那么,对于安乐乡,宝莉又是否真切地感知到其“独特性或特殊感”[6]导论:5,并从具体生活实践中获得“地方感”(sense of place)呢?宝莉积极参与、试图融入安乐乡的努力是显而易见的。自小“就自称是爸爸女儿”[4]209的宝莉跟着父亲伟成一起,全面接受了美国的社会习俗,在日常生活、亲子关系等各个方面都模仿周围的美国小朋友,亦步亦趋地去做。例如,因为在夏令营中见到朋友“叫她们妈妈的名字”[4]210,宝莉回来便口含着棒棒糖、“冲着依萍大声直呼她的英文名字Rose起来”[4]210。应当说,深受安乐乡影响的宝莉正竭力忘却自身所携带的华人背景。由此,人们可以觉察到“都市区位对个人认同之社会建构的重要性”[6]145。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伟成执意迁入安乐乡的初衷:此处不单单“适合于孩子的教育”[4]208,更有利于孩子直接且紧密地参与到主流社会之中,尽快地完成其美国化的过程。可惜,同学Lolita的一声Chinaman打破了宝莉与小伙伴之间拥有的表面上的快乐与和谐,也间接地说明伟成对于白人所抱有的幻想的破灭。孩童间的争执本是无心,但它确实再现了华人/裔群体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社会中的空间经验。如前所述,在1965年的移民及国籍法案颁布之前,华人/裔群体是被隔离在美国社会以及城市的中心地带之外的,其聚居的唐人街或“中国城”又因高度的文化聚合性而具有了空间意义上的地理分割性。这就是说,在民权运动所彰显的“多元主义”(pluralism)价值观得以普及之前,华人社区与主流社会的鲜明对比佐证了华人/裔群体身为美国的“内在他者”(outsider who are inside)[11]的弱势边缘人形象。当然,在20世纪40、50年代,美国民众对于华人的态度有所好转,甚至将华裔誉为“忠诚的少数民族”[12];但是,鉴于空间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小小的安乐乡实为唐人街外的白人世界的一个缩影,而Lolita于言语之间流露出的优越感与排斥姿态则体现了美国社会对于华人/裔群体的真实情感及认知,它在本质上不过是依萍在太太社团里遭遇到的、善良却好奇的问候的翻版而已。因此,与母亲依萍的处境相类似,安乐乡也不会成为宝莉的安居之所,因为宝莉终不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一则当时的中产阶级白人社区尚不能包容与接纳华人移民;二则是宝莉与其父亲伟成过度地追求美国化,反倒为主流价值规范所操控而不自知,所谓的纯粹/真正的美国人便是很好的说明。“内在性”[13]的缺乏、被隔离于他人之外的孤独与忿恨表明安乐乡不会给予宝莉情感、意义或价值。
追根溯源,不尽如人意的人—地关系的确是难以建立地方认同的依萍母女发生激烈交锋的重要原因。同为安乐乡的“他者”(the other),依萍与宝莉都遭受着来自于社区的划界排斥,区别是,二人如何在这一空间内重置自己的位置、应对内心的焦虑感并缓解自身与新居地间的紧张关系。对于依萍而言,安乐乡始终都是一个暂居之地。但是,与之前的纽约城不同的是,居于安乐乡的依萍已被迫从与中国相关的所有场域中抽离,不能再经由外在的社会网络来确认或巩固其对于自我的认同。于是,读者们看到,依萍试图通过说中文、喝牛尾汤等文化或习俗的持续展现与操演来重温、维系故国的社会与文化经验,尤其是透过母女间的情感纽带延续族裔的生活实践与文化脉络,在家庭之内营造出一个有别于安乐乡的、属于华人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不仅是依萍的怀旧之地,也是被动退缩至家庭中的她能够展开地方想象的唯一依靠:通过故国记忆的再现与分享,为自己与宝莉谋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未来。然而,正如丈夫伟成所指出的,依萍忽略了宝莉作为土生华人的特殊处境与在地的体验。毋庸置疑,美国是宝莉的童年故乡,后者对于多种语言、多元文化的认知程度预示着其对安乐乡的熟悉感。因而,宝莉自然会以融合的姿态走进安乐乡的社区空间,于举手投足之间争取所居地的接纳与认同。问题的症结在于,在宝莉看来顺理成章的“内在性”并没有获得其所在社区的支持;后者其实是一个并不友善且无法亲近的空间,它既无视华人移民内部的代际差异,亦否定华人生根于此的可能,让宝莉在现居地与血缘故国的拉扯之中重蹈其母依萍的覆辙。
四、结 语
人—地的关系不单是个体的空间体验或感受,更是一种群体或社会层面上的实践与再现过程,显然,后者有着更为强大的影响力。在安乐乡这个纯白人的中产阶级社区中,依萍与宝莉能否安居于其中并切实地参与到周围的生活空间里去,这完全取决于居住于此的白人们的态度。即,依萍与宝莉二人都不曾拥有过安乐乡:邻居们的关心以及Lolita颇具歧视色彩的语言表明此地只是华人的暂居地,而非其与白人群体互信互敬、凝聚共识的场所。长此以往,面对着这一“以包纳和排外的机制创造的”[6]137社区,依萍母女的情感与心灵都将无所寄托,人—地之间的不融合或连结的失败注定了所谓的地方依恋或认同无从谈起,她们注定会陷入“无地方感”(placelessness)的困境之中。
不可否认,在个人的认同问题上,在美的华人移民与土生华裔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一如深具怀乡情怀的依萍与执意西化的宝莉。但两代人之间之所以会坚持各自的抉择,不惜导致家庭内部的短暂混乱,实则是因为双方均深陷困境而无法自拔。不论是生活环境的变迁与适应,还是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的弱化与重建,安乐乡之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过于强大,严重阻碍了依萍母女与周围的人及环境之间的互动,以至于二人的所有努力都逐步地消逝于对新家园渴求却不可得的巨大失落之中。毫无疑问,“无家”的深刻体验会消除在美的华人/裔的对现居地的地方归属感,而内心的无所适从将加剧不同代际的华人/裔在认同问题上的对峙,其实,这也是华人移民在地化过程中最为痛苦的阶段。
注释:
①国内研究《安乐乡一日》的相关文献如下:殷国明:《一个世界性主题:种族的困惑——兼从比较的角度评论白先勇的<纽约客>》,《当代作家评论》,1988年115-122页;郑伟雄:《孤雁的困惑——读白先勇的<纽约客>》,《华文文学》,1991年2期第68-69页;陆春:《“围城”中的迷失与沦陷》,《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5年4期第85-87页;盛周丽等:《守望、妥协还是遗忘?——从白先勇的〈安乐乡一日〉探析身份认同》, 2008年2期第46-49页;池美红:《中美流散文学中的文化身份研究》,延边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盖建平:《 “融入”之外:〈安乐乡的一日〉的现实意义探析》,《 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4年4期第17-21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