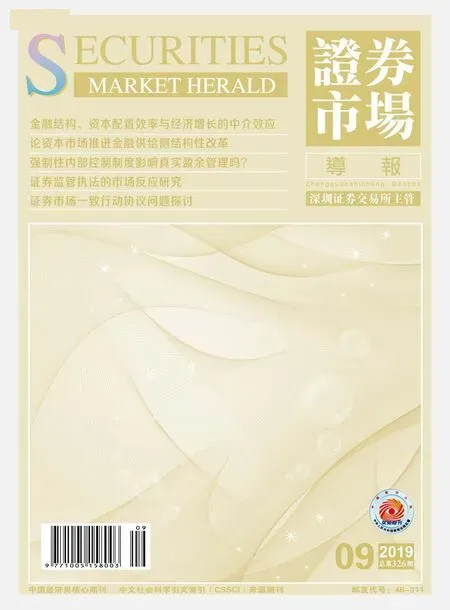证券市场一致行动协议问题探讨
2019-12-19蒋学跃
蒋学跃
(深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广东 深圳 518038)
实践中,我国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以下统称“公众公司”)较为频繁地出现了股东之间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并由此引发如规避监管、效力认定、解除及违约责任承担等一系列争议,而理论界与实务界之间对此存在较大的分歧,如公司能否直接按照一致行动协议直接改票等问题。故笔者不揣简陋,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名实论:表决权拘束协议、股东协议抑或一致行动人协议
对于股东之间签署协议的名称问题,我国法学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存在分裂状态,前者倾向于使用“表决权拘束协议”1或“股东协议”2,而后者使用“一致行动人协议”3,以下分别阐述。
一、表决权拘束协议
顾名思义,表决权拘束协议(voting agreement)是指拥有表决权的主体之间对如何行使表决权进行约定的协议,是从协议的客体视角归纳出的定义。由于这种协议使得多个股东的股票成为一个共同的单位来行使表决权,也被称为“联合投票协议”(Pooling agreement)。4表决权拘束协议的目的是为了保持控制权,或是累积使用投票权使得股票的表决权最大化或者达到特定的目的,协议通常会约定支持或反对股东(大)会的某项提案,而且会约定无法达成一致情形下决定如何投票的表决事项。5
二、股东协议
从签署主体角度而言,由于表决权的拥有者是股东,表决权拘束协议也被称为股东协议6,因而表决权拘束协议肯定是股东协议,但股东协议并不必然与表决权拘束协议重合,因为股东除了签署行使表决权的协议以外,由于闭锁公司中股东人数较少,管理机构与股东重合程度较高,股东还会签署关于如何行使公司管理权以及董事职权方面的约定,也就是说这些约定已经超越了股东行使表决权的范畴,由于这涉嫌损害到公司治理基本结构和其他股东利益的问题,因而可能会面临着被法院认定无效的危险。7基于上述原因,美国《标准公司法》在7.31和7.32条中对表决权协议和股东协议作分别规定,其他股东协议受到更多的限制。
与此对应,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股东之间约定股权转让时的“一致行动”,即一方转让时另外一方也有义务卖出,事实上此案涉及的不是表决权拘束问题,本质上是股东之间关于拖售权约定的股东协议。8因此可以说,股东协议的范围比表决权拘束协议更大、涉及的问题更为复杂,其效力也更容易被法院所否定。
三、一致行动人协议
与学界相反,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无论是一级市场的发行环节,还是二级市场的持续性信息披露阶段,都更加偏爱使用一致行动协议(action in concert),而非表决权拘束协议或者股东协议,主要原因是我国从境外移植的一致行动人概念已经发生了嬗变和功能异化,原本适用于上市公司收购领域的概念,被泛化应用于IPO、重组上市、二级市场减持中的监管活动。
从形式上看,我国证券市场中的一致行动协议基本等同于境外的表决权拘束协议,但从具体内容上来看,正如下文所实证分析的那样,我国一致行动协议不仅仅约定表决权的行使,还会约定超越股东表决权的董事表决权的行使问题,因此,我国一致行动协议更加接近于境外的股东协议。
四、公司作为缔约主体的广义概念问题
除了上述三种不同的概念以外,还有一种所谓的广义概念,即公司成为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主体。9从法理上讲公司成为缔约主体让人匪夷所思,因为既然是表决权的行使,应该是表决权的拥有者股东签署协议,而公司是不具表决权的。对此,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公司参与的情况下,法院考虑到撤销股东大会决议会影响到其他股东的利益而可能不会撤销,从而使得表决权拘束协议的目的落空。但通过公司成为缔约主体,等于通过股东让渡了一部分权利给公司,使得公司能够强制改票”。10事实上,这个解释存在三个方面错误:首先,混淆了股东协议与表决权拘束协议的区别,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32条只是规定“股东协议”可以对公司发生效力,而不是指表决权协议;其次,对公司发生效力的“股东协议”是有严格限制的,即必须全体股东同意的;最后,股东协议对公司发生效力的根源,并不是因为满足了公司签署协议形式性要求,而是因为记载于公司章程中。事实上,美国《标准公司法》上的这种股东协议已经实质上成为公司章程了,因为其满足了全体股东一致同意的条件,使得单纯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转为公司内部秩序,成功实现了合同对组织的替代功能,使封闭公司中的合同和组织之间的边界消失。一个假想案例,A公司仅有的两个股东甲和乙签署一致行动协议,与此同时,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也在该协议上签名或盖章,但此时这个协议并不因为A公司签署协议而受到约束,而是A公司必须将甲乙股东签署的相关协议并入公司的章程,这个协议由此成为公司章程的组成部分,将来方可约束公司,即单纯的股东之间的协议转化为了公司的章程。
效力论:一致行动协议的效力判断维度
如上文所述,我国的一致行动协议主要是股东协议,不仅仅约定表决权的行使,而且还约定表决权以外的相关事项,这就涉及到一致行动协议效力判断的问题。理论上而言,一致行动协议属于股东的意思自治范畴,只要遵循民法上意思表示的基本要求,原则上就应该有效。但事实上,与一般的民事合同相比,一致行动协议由于涉及到非合约股东和债权人等其他主体的利益,因而需要在更加宽广的维度中去考察。
一、判定维度
一致行动协议虽然是股东之间的协议,但不能简单套用合同法的逻辑,即仅仅以相关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判定协议有效是非常危险的11,因为它涉及到组织法与合同法的交叉,需要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考察。
1.公众公司与封闭公司12的不同语境
公众公司由于股东人数众多,其所有权成本较高,基于效率的原因而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董事对公司和全体股东承担信托责任,股东多数情况下做甩手掌柜,只对重大事项决定采取“资本多数决”的表决机制,但也由此造成股东与管理层之间代理成本较高。13封闭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其所有权成本较低,股东通常直接管理公司,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成本很小。此外,由于公众公司的股份具有高度流动性,股东可以用脚投票,也同时造成了股东之间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各国公司法对于公众公司的治理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封闭公司则缺乏相应的流动性市场,股东更容易锁定在公司中,不会形成集体行动困境,因此,各国公司法一般都愿意承认股东之间的协议。
综上所述,如果是公众公司领域,由于表决权拘束协议更容易影响缔约方以外其他主体的利益,因此,对其效力审查应该更加严格。以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作为董事在董事会会议表决时保持一致”为例,因为公众公司赋予了董事对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信托责任,如果允许股东约定其控制的董事在董事会会议中保持一致,则可能会危及董事的独立性,违背其对全体股东承担的信托责任,下文将对此详述。对于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如果公司的所有股东签署协议,应该更加倾向于认可其效力,如作为某有限责任公司各自持股20%的甲股东和80%的乙股东约定,双方未来重大决策不再召开股东会而直接依据乙股东的单方面决定,此时应该是有效的,因为这种股东之间的协议与我国《公司法》第37条规定的“对前款所列事项(股东会的职权)股东以书面形式一致表示同意的,可以不召开股东会会议”具有暗合之处。14
沿着上述逻辑,就不难理解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32条d项的规定“一旦公司上市后,原本的(全体股东签署的)股东协议应立即失效”。15
2.是否破坏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采取设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等决策机构和相应的表决机制来解决公司中不同利益主体之间代理成本问题,如果股东协议破坏了上述治理结构,就可能违背设置公司治理结构的初衷。如德国《股份公司法》第136条规定,合同约定股东依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指示投票,则合同无效16,因为这将使得被监督机构反过来控制了股东,导致公司治理中的约束机制失灵,将极大地增加代理成本。同样道理,如果我国公众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中出现两个控股股东之间约定,在未来董事选举中确保双方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定的席位,便会严重影响董事的独立性,导致董事会的虚置,应该认定为无效。17
3.是否损害相关主体的利益
在法律上,将公司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而将各个股东的人格隐藏起来,其根源是交易成本问题。首先,公司拥有独立法律人格,而不再以各个股东名义与交易对手方谈判,可以节省交易成本;其次,公司独立人格有助于降低融资成本,特别是债权融资成本,因为债权人不再与每个股东打交道,而只与公司打交道;最后,公司的独立人格有助于建立其财产的独立性,使得股东承担有限责任,这样就可以降低股权融资成本。但是这种成本的降低也同时会产生控股股东与公众股东的利益冲突以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如果表决权拘束协议涉嫌逃避债务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或涉嫌滥用控股股东权利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应该认定为无效。18
事实上,一些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公司法采取了保护第三方利益的技术手段,那就是让表决权拘束协议通过在公司存档的方式向外界公开19,接受其主体的审查,这样潜在的投资者如股东和打算给公司贷款的债权人都可以对此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进行交易。但遗憾的是,这种技术方法被我国学者误解为公司成为签署协议的当事人,继而错误地得出“公司改票可以得到法院的支持”的结论。20
二、具体案例考察——以华电公司案为例
华电公司案应该属于我国非上市公司表决权拘束协议具有代表性的案例21,我们以此案为例探讨其效力。2009年12月,作为被告华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第一大股东胡达与原告张国庆签署《股份认购协议》约定“华电公司向张国庆增发股权,在华电公司上市交易前,张国庆承诺其持有的股份在投票时与胡达保持一致”。2015年8月,华电公司召开股东会对增资扩股事项进行表决,结果由于张国庆没有与胡达保持一致而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无法满足增加注册资本的表决权要求,华电公司根据协议将原告的反对票改为赞成票,由此通过决议,张国庆随之起诉华电公司和胡达,请求法院撤销本次股东会决议。我们先分析本案中的协议效力问题:首先,本案是有限责任公司,在效力判断上应该更加宽容,应该认定其原则上有效;其次,本协议没有破坏公司治理结构,只是单纯股东表决权的约定,也应该是有效的;最后,本案中协议没有损害相关主体的利益。综上,本案的协议应该是有效的,一审、二审及再审法院也都认为协议是有效的,对此没有分歧。
实证论:我国公众公司领域的一致行动协议问题
鉴于我国公众公司领域较为普遍出现一致行动协议,故通过WIND资讯对其进行实证研究。
一、违背常理的“主动”签署
美国上市公司的股东一般不会主动签署表决权拘束协议,如果是IPO前签署的也会在上市前主动解除,否则可能由此被认定为发行人的“关联人”而在减持、信息披露等领域受到较多约束。22但我国情况则相反,仅自2019年初至5月15日的不到半年期间,WIND资讯中公众公司领域的关于股东签署、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多达51个,这些股东似乎想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而主动接受更加严格的监管和约束。这种有悖常理的现象,是由我国发行审核监管理念、重组上市监管套利、股东大会中心主义理念下的巩固控制权需要等三个因素所共同导致的。以发行审核为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首发办法”)第12条要求“发行人最近3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理论上这是一个依据个案的具体判断问题,并且在一般意义上股权分散不应该成为上市的阻碍,但是证监会《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认为“首发办法第12条的规定的立法本意是保持控制权的稳定性”,实际控制人的认定是发审委的关注重点,实践中如果拟上市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可能构成上市的障碍。为此,实践中保荐人一般会让前几大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的方式,满足审核要求。
二、协议约定的内容空泛
理论上讲,表决权拘束协议约定的内容是如何一致行使表决权的问题,因此,协议内容重点是约定不一致时的处理机制,但我国公众公司领域的一致行动协议却内容空泛,主要有以下几种约定方式:
1.仅空泛约定保持一致
新三板挂牌公司阳光中科在2019年3月28日公告23:“对阳光中科进行决策及经营管理过程中,凡涉及一致行动事项时,双方应先行协商一致,以保证双方在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中做出相同的意思表示”。
2.空泛约定以某一方意见为准
如瑞伯德公司的一致行动人协议约定“自本协议签署后,乙方同意在公司的事务决策(包括但不限于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担任董事的个人在董事会行使表决权、提案权、提名权等、及其他决策事务)时,与甲方采取一致行动,如果甲乙双方的意见不一致时,以甲方的意见为准。在乙方不能参加公司的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时,应委托甲方或甲方指定的人参加会议并行使投票表决权”。
3.空泛约定解决方法
新三板挂牌公司六合股份在2019年4月11日公告的“如果双方未能达成一致表决意见时,在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合法的基础上,双方按照以下方式对审议的议案形成表决意见:(1)如一方拟在表决时就某一议案投赞成票,另一方拟在表决时就同一议案投弃权票时,则双方均只能投弃权票;(2)如一方拟在表决时就某一议案投反对票,另一方拟在表决时就同一议案投赞成票时,则双方均只能投反对票”。
上述空泛约定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既然是契约就必然会出现违反的情形,一个值得推荐的方法是将一致行动协议与表决权委托结合起来,事实上也就是事先将表决权让渡给一方,可以有效避免后续的违约出现,如金科股份在2017年4月1日公告的一致行动协议中明确:“在保持一致行动期间,乙方同意就自己及其在金科控股对金科股份行使股东权利之表决权、提案权委托给甲方行使,乙方不再向甲方另行出具授权委托书”。
三、缺乏对违反约定时的处理措施
既然表决权拘束协议是股东之间的协议,而不是公司章程,因此,当缔约方违反协议时很难要求撤销股东大会的决议,而只能主张违约责任,这也是契约与章程之间最重要的区分。这意味着表决权拘束协议应当重点约定当一方面不按照约定履行时的救济措施,但我们发现上述协议中绝大多数都没有约定违约责任24,似乎都不约而同的认为契约能够自动实施,而遗忘了违约的问题。如果结合我国一致行动协议多数是因为规避监管而作的安排,就可以理解这一怪异的现象,即协议目的是为了监管套利,而不是真正为了确保表决权的一致行使。以重组上市为例,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13条,重大资产重组中涉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则需要依据IPO的审核标准,如果是创业板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动本身就成为一种法律障碍。实践中,部分公司采取现有大股东借助一致行动协议,形式上实现控制人不变,以此规避重组上市的规定。25
四、其他“创新型”约定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一些公司违背公司治理和法律基本原理创设了很多“创新型”约定。
1.约定董事的表决
理论上而言,由于我国的一致行动协议实质上是表决权拘束协议,其只能约定股东在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时保持一致,而一些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竟公然约定在董事会表决时保持一致,如嘉应制药2018年12月12日公告:“对于非由本协议的一方或双方提出的议案,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召开前,双方应当就待审议的议案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尽快达成一致意见,并以自身的名义或一方授权另一方按照形成的一致意见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会议上做出相同的表决意见”。首先,股东与董事的身份是不同的,股东因为出资而获得资格,而董事是因为经过股东的选任而获得资格,因此,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董事的表决属于人格分裂;其次,股东和董事的责任存在极大差异,股东通常不对公司和其他股东负有信托责任,而董事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有信托责任,因此其在董事会会议上行使表决权应该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如果股东预先约定董事的表决有可能会损害董事的独立性,继而侵害公司治理结构,如一个并购明显对公司不利,但由于一致行动协议的存在,其他董事也被迫投赞成票。因此,这种约定是严重违背公司治理基本原则的,应被认定损害了公司治理结构而被认定为无效。
2.随意突破合同相对性
新三板挂牌公司铁大科技在2019年2月15日公告:“如果甲方持有的公司股份转让给除乙方及乙方指定的第三方之外的其他方时,其他方须继续履行本协议”。也就是说该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创造出了可以突破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争议解决论:违反、解除协议或股份转让的应对
一、违反一致行动协议能否强制执行
我们认为必须将其区分为投票前和投票过程中违约两种不同的情形,即合同法理论中的明示毁约与默示毁约,因为不限定范围和条件,简单得出的结论都难免偏颇。26
1.明示毁约
如果股东事先就明确表示不履行协议,境外法律规定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具体程序上,一般是申请法院颁布禁令或诉前行为保全,阻止当事人违反协议投票。如美国《标准公司法》第7.31(b)条规定表决权拘束协议是“可以实际执行的”,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也判决强制执行。27根据德国的司法判例,当事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照契约约定进行表决,并根据《德国民事诉讼程序法》第894条的规定,对判决进行强制执行。28但事实上,这些措施耗时费力,德国学者建议采用约定违约责任的方法。29
因此,我们认为当股东明确表示不履行一致行动协议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然法院必须先确认协议的效力,再作强制执行的判决,当事人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0条申请“行为保全”。30
2.默示毁约
如果股东在股东(大)会没有按照约定行使表决权,那么理论上在股东(大)会的表决应该是有效的31,因为股东协议与公司表决机制是两种不同的秩序,股东之间的内部秩序不应该影响股东(大)会的外部秩序。但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哪个国家会允许公司依据契约而改票,因为这会产生损害股东权利的严重后果。在美国,公司股东投票由公司的投票监察人计票,除非他收到法院相反指示,否则会完全按照股东的投票来计票。32因此,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我国学者所说的“无法强制履行”的问题33,应予赞同。
二、股份转让后协议适用问题
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表决权拘束协议仅约束缔约人,如果缔约人将其股份转让给第三方,受让人是不受契约约束的。面对这一问题,我国证券市场中出现了一些荒唐的约定,即受让人继续承担义务。事实上,我国市场主体已经设计出较为完善的解决机制,如约定各方不得随意转让他人,否则构成违约;以及约定股份转让时的,另一方有优先受让权等。
美国《标准公司法》和《德州公司法》利用另外一种方式解决股权转让后协议约束力的问题,即要求将协议记载如公司章程或在公司备存(deposited)34,可以对潜在的受让方产生一种警示作用,避免其被原股东欺骗而损害利益,这也是法律协调合同(具有私密性和非公开性)和股权流动性之间冲突的重要途径。在1980年Zion诉Kurtz案中,一个债权人取得了一家非公众公司的部分股权以作为其对该公司贷款的担保一部分,他还与大股东达成协议,公司在没有得到债权人同意的情况下,不可以从事交易或进行新的业务,而根据特拉华州的公司法是允许非公众公司达成这样的协议的,但是要求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明确这种限制,而该公司并没有这么做。法院最终判决这个协议有效,认为公司的不作为只是一个技术性的缺陷,无关紧要,但三名法官对此强烈反对,认为章程记载的目的是向利益相关人进行公告,而法院的这一判决使得这一功能丧失殆尽。35
三、协议能否解除
理论上,上市公司股东之间一致行动协议是股东自愿签署的,双方自然可以一致解除原协议。但在上市公司不同的是,既然一致行动协议公示了,其他股东以及利害关系人都会对其产生信赖,特别是原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期限较长,经过短暂时间后即解除且没有合理理由,很可能为其操纵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提供机会.因此,从监管的角度而言,如果当事人提前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可以认定为其信息披露违规。
四、公司能否强制改票——再论华电公司案
前述华电公司案中,一审、二审以及再审法院都认为公司基于股东协议约定可以强制改票,驳回了原告主张撤销股东会决议的诉讼请求,因此,案件的争议焦点就是公司能否更改股东投票的问题。
1.投票权的主体
原则上,投票权的主体是股东,境外实践中股东可以通过代理或表决权信托方式将投票权交由第三人行使,但股东必须通过某种方式让公司的计票人员知道投票权行使主体的变换,如股东出具授权书或表决权信托记载于公司的股东名册上。因此,公司即使参与到股东之间关于表决权约定的协议,也不能改变股东拥有投票权的事实,更不能荒唐地认为股东将投票权让渡给公司了。36退一万步讲,即使认为股东将表决权让渡给公司了,公司也不可能享有表决权的,因为公司作为一个法律主体完全是基于效率所作的法律拟制,其内部还是必须有相应的表决机制,并经过相应的内部机制,即董事会会议或者股东(大)会决议37,如果公司拥有股东的表决权则会产生意思表示的悖论,最终走向内部人控制,而在我国实行法定代表人制度的背景下,更会导致公司治理的整体沦陷。具体到华电公司案,如果想要将股东内部的约定转化为公司表决机制的一部分,可以由原告事先向公司出具授权控股股东代为行使表决权的授权书。
2.表决机制与股东合同的区分
股东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个部分,即组织内部秩序,而股东之间关于投票权的协议是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是股东之间的秩序,二者存在较大的差异,即使公司参与股东之间的协议,也不能改变二者的区分。
3.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与公司改票的区别
如前所述,多数国家是允许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表决权拘束协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允许公司改票,因为申请法院执行是在司法监督下进行的,法院会首先审查协议的效力再做是否强制执行的裁决,而公司改票仅是公司单方面的行为,缺乏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在协议一方当事人控制公司的情况下,很容易侵害其他股东的权利。
4.赋予公司强制改票权力的危害
如果赋予公司可以强制改票,则事实上就承认了公司可以随意侵害股东的表决权,而在我国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和法定代表人制度下,这会使得大股东更加容易侵害中小股东的权益。可能会产生的疑问是,既然原告已经事先愿意与被告保持一致,在其违反承诺时如果不赋予公司强制改票的权力,则事实上会产生鼓励原告违约的激励。客观而言,上述说法是有道理的,但这主要依靠当事人妥善约定违约责任(如约定违约金或表决权代理),以及利用司法的诉前行为保全制度来解决,而不能武断地通过侵害股东基本权利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如果法院基于所谓维护既有秩序而对公司强行改票行为不作纠正的话,会让其他公司产生潜在的机会主义,激励它们改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华电公司强行改票行为,法院应该支持原告撤销股东会决议,被告可以对原告违反协议的行为主张违约责任。当然,可能由于原协议中没有明确约定违约责任,导致被告很难对原告的违约主张赔偿责任,但这正是这一判决所要产生的后果,让当事人“长记性”,激励其他市场主体对相关问题做出更为详细的约定。
监管论:一致行动协议的监管建议
在上市公司监管过程中目前经常遇到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解除、履行以及公司依据协议强行改票的问题,存在较多的争议。
一、司法与监管的不同路径——公法与私法的区分视角
如前所述,股东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是一个私人之间的法律关系,通常适用合同法,至多也只涉及到公司法(组织法)的问题,但总体而言仍然是一个私法问题。因此,当一致行动协议产生效力、履行等争议时应该通过民事诉讼司法程序来解决。
在上市公司领域,一致行动协议可能涉及到股东之外的其他主体,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此时就涉及到监管的问题,即转化为公权力机构介入到私人关系之中,即公法的问题。相应地,监管机关只是从保护证券市场秩序的角度,而非协议当事人的角度介入一致行动协议。因此,监管机关不应当纠结于一致行动协议的效力、履行争议,而是从其行为是否损害证券市场的秩序和中小股东的权益角度,对其进行行政处罚,否则就混淆了公法与私法的边界,容易导致“公器私用”的问题。38
二、美国的经验
在美国,由于股东之间签署类似于一致行动协议可能会被认定为公司的“关联方”,会导致在二级市场减持、信息披露、责任承担等环节受到更多的约束,因此,美国上市公司的一致行动协议非常罕见,目前主要在我国中概股中涉及一致行动协议,但美国的监管目标仅是信息披露,要求发行人完整披露上述协议的内容以及可能产生的风险。39此外,表决权拘束协议主体的律师会协助各方草拟争议更少、更容易履行的合同,如在表决权拘束协议中会同时附加表决权委托的协议。
三、具体监管建议
首先,基于一致行动协议涉及到上市公司控制权问题,因此,必须要求签署主体披露如主体、期限、一致的内容、目的等相关信息。
其次,如果当事人提前解除一致行动协议,这就类似于违背了股东的承诺,其之前的信息披露存在误导投资者的问题,监管机构可以依据信息披露违规进行行政处罚40,但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解除并不是监管机构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由双方走司法程序。
最后,监管机构可以发布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一个非强制性示范条款,既能够有效减少实践中的争议,又能够严守监管边界。示范条款主要针对的是实践中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如因为超越表决权范围可能导致无效、股份转让后导致协议无法履行、违约的强制执行等问题。建议示范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一致行动协议最好限于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不涉及到董事职权的行使问题;约定一方当事人转让股份时,另一方拥有优先受让权,以保障股份转让后的一致行动协议的履行;在约定一致行动协议的同时,签署一个表决权委托协议并提交公司,确保公司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的“计票”正常进行,以保障一致行动协议能够“实际履行”;41在一致行动协议中明确违约金或损失的计算方式,便于后续争议的解决。
注释
1.参见梁上上.表决权拘束协议:在双重结构中生成与展开[J].法商研究, 2004, (06): 94-106.
2.参见张学文.股东协议制度初论[J].法商研究, 2010, (06): 111-118.
3.目前在上市公司公告中出现的都是“关于控股股东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的公告”。
4.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德国公司法(第5版)[M].齐东祥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208.
5.同前注4.
6.See Graham Stedman, Janet Jones , Shareholders' agreements,Previous ed.London: Sweet & Maxwell, 1998: 57.
7.在美国公司法司法实践中, 1934年的Mcquade诉Stoneham案中,股东之间约定聘用特定股东为公司的财务总监;1936年的Clark诉Dodge一案中, 股东之间达成聘任某个股东为公司总经理的协议;罗伯特.W.汉密尔顿.德国公司法(第5版)[M].齐东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 186.
8.某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作为原告与W签署一致行动协议,约定双方在对外转让股份是遵守原告的意愿。后原告在涉及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交易中,向重组方转让了股份,但被告未转让相应股份。因此,原告主张被告构成对于一致行动协议的违反。参见王光明、朱敏怡:“一致行动人为什么可以’不一致’?”,载北大法宝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art&Gid=399b812a7 17be0a576812beaf4bef1c7bdfb&keyword=&EncodingName=&Search_Mode=&Search_IsTitle=0。原文作者认为这个协议构成拖售权的约定,因而是无效的。对此,笔者赞同原文作者对其性质的认定,但因为本案中的这种约定没有损害其他股东和上市公司的利益,应该是有效的,因此可以追究小股东的违约责任。
9.See Graham muth and Sean Fitzgerald, Shareholders' agreements,5th ed.London: Sweet & Maxwell, 2009:5.
10.参见何昕.表决权拘束协议的初步研究——兼评“华电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J].金融法苑, 2019, (01).
11.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著,齐东祥译.美国公司法: 第5版[M].法律出版社, 2008: 185.
12.这两个概念只是为了便于分析产生的技术性概念,并非法定概念。我国公众公司主要指上市公司和新三板挂牌公司,而封闭公司主要指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股东人数较少的股份有限公司。
13.参见亨利·汉斯曼著, 于静译.企业所有权[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55.
14.类似的案例也出现在美国。在1936年的克拉克诉道奇案中,两个分别持有公司25%和75%股份的股东达成协议,约定其中一名股东作为公司的总经理,法院最终判决该协议有效。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德国公司法(第5版)[M].齐东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86.
15.美国学者仅在闭锁公司领域讨论股东表决权拘束问题,参见史蒂文·L·伊曼纽尔.公司法[M].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3: 139.
16.参见托马斯·莱塞尔著.德国资合公司法[M].高旭军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52.
17.事实上,这种行为在我国上市公司重组上市过程中非常普遍,有人由此得出其合法合理的结论,这也恰恰反映了我国公司治理理念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对董事会虚置和公司治理形式的无视。参见邓峰.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J].中国社会科学, 2011, (44)(1): 164-176.
18.参见许德风.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J].法学研究, 2011, (03): 94-111.
19.See Val Ricks, Strategic Shareholder and Member Voting Agreements Under Texas Business Entity Law, 68 Baylor L.Rev.33,Spring, 2016.
20.同前注10.
21.相关案件事实参见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赣05民终328号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赣民申367号中判决书。
22.参见张巍.资本的规则[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7: 11.
23.下文相关公告都是从WIND金融资讯中获取,不再赘述。
24.目前,仅在一家公司的协议中看到约定违约金的内容,但却不是对未按照约定投票的违约,而是对约定方转让股份的违约。参见乾照光电在2018年11月1日公告:“如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则违反本协议的任何安排或协议均无效。如任何善意一方因该等安排或协议取得与该等违约方所持公司股权的相关权利,则该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人民币500万元违约金,并如可能应尽量促使该违约的交易回复原状”
25.2013年,创业板的天瑞仪器并购宇星科技案中,宇星科技作价29亿元,按发行价16.01元/股计算,发行数量约为1.8亿股,高于天瑞仪器总股本,这意味着,控制权变更与购买资产总额两项硬指标或将双双“触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刘召贵持有公司6,552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2.57%。而重组完成后,刘召贵的持股股权则将大大降低为32.33%。为保持绝对控股,刘召贵与妻子杜颖莉、妹妹刘美珍、以及公司总经理应刚达成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超过8.78%。在三位一致行为人的协助下,刘召贵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表决权比例超过41%,超过权策管理、安雅管理、太海联、福奥特、和熙投资等5名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26.我国学者对此问题呈现出截然对立的观点,一种以许德风为代表的,主张全部支持强制履行,甚至允许以此为理由撤销股东会决议,参见许德风.组织规则的本质与界限——以成员合同与商事组织的关系为重点[J].法学研究, 2011, (3): 94-111.另外一种观点陈洁以为代表,主张统统不能强制履行,参见陈洁.股东表决协议的法律问题[J].法学杂志, 2008, (04): 133-135.
27.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德国公司法(第5版)[M].齐东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209.
28.参见托马斯·莱塞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M].高旭军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252.
29.参见托马斯·莱塞尔.德国资合公司法(第3版)[M].高旭军等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5: 253.
30.我国有学者认为一致行动协议不应该强制履行,理由是当事人只有在投票后才能知晓其违约。我们认为这忽视了明示毁约的情形,其结论并不妥当。参见陈洁.股东表决协议的法律问题[J].法学杂志, 2008, (04):133-135.
31.参见格茨·怀克.德国公司法[M].殷盛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47.
32.参见罗伯特·C·克拉克.公司法则[M].胡平等译, 北京:工商出版社, 1999: 643.
33.参见陈洁.股东表决协议的法律问题[J].法学杂志, 2008, (04):133-135.
34.同前注19.
35.参见罗伯特.W.汉密尔顿.德国公司法(第5版)[M].齐东祥译,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188.
36.同前注10.
37.境外一般是董事会会议的决策,我国由于实行股东(大)会中心主义,一般要经过股东(大)会的表决。
38.有学者认为证监会和交易所在ST新梅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中无所作为,由此助长了上市公司治理的混乱。事实上,在该案中证监会和交易所本身就不应该介入公司治理,因为本案中涉及的是违规收购的表决权有无的问题是一个私法问题,其解决途径就是司法。如果非说存在问题的话,应该是我国司法环境的问题,而绝非(行政和自律)监管的问题。参见为为乔.ST新梅重组表决困境[J].董事会, 2016, (01): 78-79.
39.如2014年赴美上市的阿里巴巴的大股东软银和雅虎与阿里巴巴的合伙人委员会达成一致行动协议,约定两大股东将支持合伙人委员会提名的董事。参见阿里巴巴在SEC的F1文件,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577552/000119312514347620/d709111d424b4.htm#toc709111_16。
40.参见陈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反公开承诺的民事责任分析——以虚假陈述型违反承诺为中心[J].法律适用, 2013(10):34-39.
41.前述阿里巴巴一致行动协议案例中,为了确保该协议的履行,软银、雅虎与马云等主体另外签署了表决权委托协议,将表决权委托给合伙委员会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