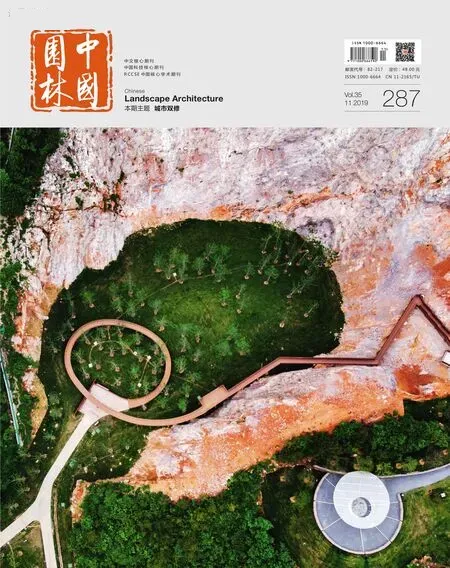陈植《园冶》研究述评
2019-12-18张青萍
张青萍
李 霞
刘 坤
陈植先生(图1)为中国的造园学和林业科学贡献了许多科研成果,是我国园林界在学术理论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1],在《园冶》的研究和传播上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园冶》为明代造园家计成所撰,“为我国最早具有系统性的造园专著”[2]。陈植对《园冶》的研究,一贯受到学界的关注,如王绍增在论及研究《园冶》的前辈学者时,认为“诸先生中,当以陈植先生功绩最伟”;赵兵梳理了陈植的造园研究文献,认为“陈植造园研究的突出成就在于‘造园历史与理论研究’”[5];段建强则探讨了陈植在近代造园学学科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6]。
然而,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也需要从各个时期的学科建设,从陈植一生学术事业演进的整体视角,去探讨他在《园冶》研究领域的建树。本文试图将陈植对于《园冶》的研究,放到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学术语境中来考察,从而深入理解陈植的造园思想,客观评价其学术研究成就。也借此梳理自民国以来,以陈植为代表的造园学先驱,在整理、发掘、研究造园典籍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的研究路径,从而对当前的研究有所借鉴和启发。
1 树立中国造园体系的认知标杆
1900年,哈佛大学设立了风景园林专业,被认为是现代风景园林学科诞生的标志。在我国,20世纪20—30年代为造园学的学科初创期。作为造园学的奠基者,陈植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同时也强调在构建学科体系时,对于本国传统的重视,“我国之造园术,在世界各国学术界中,占重要之地位,实有发扬光大之必要。[7]”终其一生,他将《园冶》作为能集中代表中国造园艺术成就的专辑去研究和弘扬。
1.1 对《园冶》研究价值的认知
《园冶》成书于崇祯四年(1631年),第一版刊行于崇祯七年(1634年)。刻印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只在民间流传,声名不显,却辗转流入日本。据考证,《园冶》最早于江户时代,约在18世纪初(即清康熙末年)进入日本,并受到日本园艺界的推崇[8]。
陈植是近代中国最早认识到《园冶》研究价值的学者。他留学日本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现为东京大学)农学部学习,师从本多静六教授。1921年,陈植在本多静六的造园研究室见到《园冶》,“始见此书,为木版本三册,闻系得之北京书肆者”[9]。据陈植撰文回忆,日本高校造园课程创立于1916年,初设之时,东京帝国大学的2位权威学者,本多静六和原熙教授,为学科定名而起争执,“一院之中,不相统一”,乃至影响到学科发展。后经双方在《园冶》中的郑元勋《题词》“凡百艺皆传之于书,独无传造园者何?曰:园有异宜无成法,不可得而传也”,发现“造园”一词,如获至宝,认为言简意赅,含义甚广,庭园、公园及天然公园等均可包含在内,由此一致同意以“造园”来命名,“七十余年来不特为日本全国通用,且作为英文Landscape Architecture的同义词”[10]。
《园冶》中的一句话,竟使日本造园界的权威学者为之叹服,乃至作为解决学科命名争端的权威资料,陈植对此深有感触,他意识到《园冶》作为被认可的“最早造园古籍”,其国际影响力和对于世界造园学的贡献,尤其了解到日本之造园源于中国,使他更感自豪,由此,他下定决心要弘扬祖国之造园艺术。
1.2 对中国营造学社重刊《园冶》的关注
1923年留学归国之后,陈植为了寻觅《园冶》,“遍索此书于京、宁、沪各大书肆中,以便潜心攻读,探其究竟,讵求之数载,杳无所得”[11]。1931年,陈植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讲授造园学,曾致信请在日本的上原敬二博士雇人抄录《园冶》,但因“一·二八事变”而中止。
所幸就在同年,朱启钤以当时北平图书馆所购之《园冶》明刻本前二卷,参考家藏抄本补成3卷,由陶湘录入《喜咏轩丛书》。陈植“闻之欣慰若狂”,立即托人求购[11]。1932年,阚铎在“喜咏轩本”的基础上,参阅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代刻本,校正图式及文本,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是为“营造本”。陈植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三百年前之世界造园学名著,竟能重刊与国人相见,诚我国造园科学及其艺术复兴时期之一大幸事。[9]”与陈植的孤军奋战相比,中国营造学社的团队协作效率更高,且朱启钤、陶湘、阚铎等人,此前在《营造法式》的收集和刊印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能调动各方资源,推进《园冶》重刊。
但是中国营造学社并未继续推进《园冶》的相关研究。学社早期工作的重心是营造相关的文献考据和研究,范围较广,《园冶》只是诸多古籍之一。在梁思成和刘敦桢加入之后,学社转为专注建筑学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对建筑古籍《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则开展对现存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刘敦桢于1933年任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也开展了对于苏州区域古园的调研,但其重点在于考察古建筑。相对而言,陈植作为造园学的研究者,对于《园冶》的重视程度更高。
1.3 以《园冶》作为学科定名的依据
在学科初创阶段,中国和日本一样,也面临学科定名的问题。陈植执教的“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是民国时期国内高校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农学院,早在1921年就创立了园艺系。在该系1927年的课程表中,已有庭园制图、观赏植物、温室花卉、庭院学和苗圃学等设置,但当时称为“庭院学”。1934年,“国立浙江大学”的园艺专业,课程设置则称“造庭学”[12]。
1928年,陈植倡议成立了“中华造园学会”,“以图国粹之复兴,及学术之介绍”,并出版《造园要义》(1929)和《造园学概论》(1935)(图2)。《造园学概论》出版后,被列为“大学丛书”,作为教材使用。在序言中,陈植开章明义,指出“造园学”的学科名称出自《园冶》:“‘造园’之名,余于拙作《观赏树木》《都市与公园论》”,以及关于造园问题各种短篇论著中,“屡与国人相见矣。不谙其辞源者,当亦以我为日本用语之贩者耳!抑知日人亦由我典籍中援用耶?斯典籍为何?乃明季崇祯时计成氏所著之《园冶》是也。[13]”
在书中,陈植将造园史的研究放到重要地位,分述中国造园史、西洋造园史和日本造园史,在“中国造园史·明清时代”一节,陈植概述《园冶》之内容:
“崇祯七年吴江计成氏(字无否)所著《园冶》一书,共分3卷,计析为:相地、立基、屋宇、装折(栏杆)、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和借景10篇……各种景观,布置之方,及太湖、昆山、灵璧等各种石类,选用之法,靡不记载详备,颇切实用,为世界造园典籍中最古者也”[7]。

图1 陈植先生晚年在南京林业大学校内(陈植家人提供)
陈植对造园史的研究和对《园冶》的弘扬,使得造园学在发轫之时,就与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相融合,并获得了诸多有识之士的认同。在以陈植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极力主张下,193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统一高校必修课程训令中,“造园学”成为官方颁布的课程名称。“此学之名为造园学也,余不揣固陋,主之最力,经历载笔争舌战,业已成为定案,由教育部于大学课程中,明令颁布,不可谓非我国学术界一大幸事”[11]!
1.4 增进公众对《园冶》的了解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校内迁,陈植辗转迁居昆明,执教于云南大学农学院。1939年秋,他在该校图书馆查资料时得见《园冶》,遂撰写了《记明代造园学家计成氏》一文,发表于1944年的《东方》杂志。该刊是当时社会影响较大的综合性杂志,陈植发文于此,目的在于增进公众对于学科的了解。造园学在当时被视为“新兴学科”,陈植认为不是“新兴”,而是“中兴”,因中国自古就有造园之学,以《园冶》诞生来算,“自崇祯迄今,亦已三百余年”[11]。而《园冶》自营造学社重刊以来,并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查该书印行,亦已二十余年矣,惟环顾宇内,知造园学者固少,知《园冶》者尤罕,知计成氏者更不多见。余以对于造园,略窥门径,尝读《园冶》,深慕计氏对于造园艺术之精博,用告国人,俾获咸知我国三百年前,已有此造园专家所著之造园专著,而谋所以祖述先贤,不致长此湮没而终乞灵异域也”[11]。
他批判了造园学界崇洋媚外的习气,指出英、美、日等国家的造园皆受到我国传统造园的影响,“我国好学之士,相继负笈前往者,实繁有徒,归国后,每好以西洋式庭园相标榜”,而对于中国传统造园技法如掇山之术则茫然不知,是为数典忘祖[11]。
在1944年发表的《筑山考》中,陈植对于计成的筑山技艺予以高度评价,将其与张南垣并列,“无否、南垣两氏之变化也,皆能从心而不从法,且常复指挥运斤,使顽者巧、滞着通,此所以令人叹服,而引为不及也”[11]。
2 坚守《园冶》的研究与注解
2.1 《园冶注释》的撰写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之后,受苏联建筑教学体系的影响,建筑类高校重视建筑史研究,并掀起了调研测绘古典园林的热潮。如刘敦桢主持的中国建筑研究室,从1953年开始,对苏州古典园林进行全面普查。
在此背景下,陈植也积极寻求《园冶》的再版。他在1956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及:“两年来我曾先后商请古籍出版社及商务印书馆印行,都没有得到结果,现在北京城市建设出版社决予重版,定于4月出版,以广流传。[11]”城市建设出版社并没有《园冶》的底稿,陈植四处搜寻,从园艺学家陆费执处寻得“营造本”,交付该社刊印,并作《重刊园冶序》,是为“城建本”。
“城建本”问世后,陈植深感古籍难以满足以阅读白话文为主的读者群体的需求。而《园冶》难读难懂,囿于明代文章的风格,文体特殊,用词古拙[4],“骈四骊六,并杂陈当日苏州土话”,不利于研究和普及[9]。在刘敦桢等人的支持下,陈植以“城建本”为底本,开始着手《园冶》的注释工作。刘敦桢以其丰富的古建筑调研测绘经验,对书中建筑名词的注释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在建筑科学研究院的刘致平,也对书稿进行了校补。刘敦桢、刘致平都曾是中国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营造学社虽已解散,《园冶注释》依然获得了其成员的支持,延续了治学传统。
但陈植的工作也面临种种困境。1958年召开的全国建筑理论及历史讨论会,对以梁思成、刘敦桢为代表的营造学社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批判。陈植注释《园冶》,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下,是冒风险的。所幸他在“文革”之前就已完成初稿,并于1964年6月撰写了《自序》。在文中,陈植替计成辩解:
“计氏生当封建社会,挟其卓越的造园艺术,奔走四方,自食其力,终其身,竟致‘贫无买山力’,而‘甘为桃源溪口人’,充分反映了旧社会艺术家可悲的境遇,晚年仍不甘自私其所能,而亟欲公诸于世,其胸襟磊落,尤属难能而可贵,岂能不顾事实,妄肆抨斥,与当日一帮阿谀帮间之徒等量其观,而使一代艺术大师,冤蒙不洁,宁可谓平”[11]?
但此时已是“文革”前夕,《园冶注释》的出版被搁置。1965年,陈植又作《长物志校注》,依然未能如期出版。陈从周评论陈植的“文革”岁月:“观其于艰难困顿之时,胸怀坦荡,屏世事而寄于丛残卷帙之中,人所难堪者,而先生恬然安之,毅然任之。[14]”
2.2 《园冶注释》的出版与修订
1971年春,局势略有好转,陈植将《园冶注释》书稿寄到上海请陈从周校阅,“以饷同好,兼备不测”[9]。陈从周受此托付,因当时公开出版无望,只能油印留作副本,在小范围内流传。有了油印本的基础,1978年,“文革”刚结束,此书得以提上出版日程。1981年,《园冶注释》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图3);1988年经过修订,又出第二版。
《园冶注释》第一版问世后,迅速引起了学界关注,在中国台湾地区由明文书局翻印(图4),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此为契机,学术界对《园冶》的研究,在沉寂多年后开始复兴。
然而,许多学者也提出了不同意见。多数的批评意见,并非针对园林或建筑学的专业知识点,而是针对其中涉及的历史文化相关内容。曹汛从编排体例、断句标点、文字及图式校勘等方面,列举了诸多意见[15];赵一鹤则指出该书存在译文和校勘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译文方面,多有直白翻译,而未提及典故出处和文化含义[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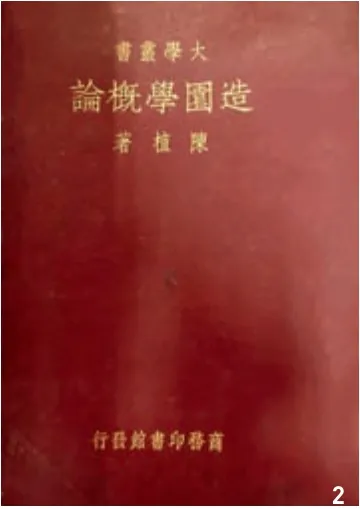
图2 《造园学概论》(1935年版)封面(作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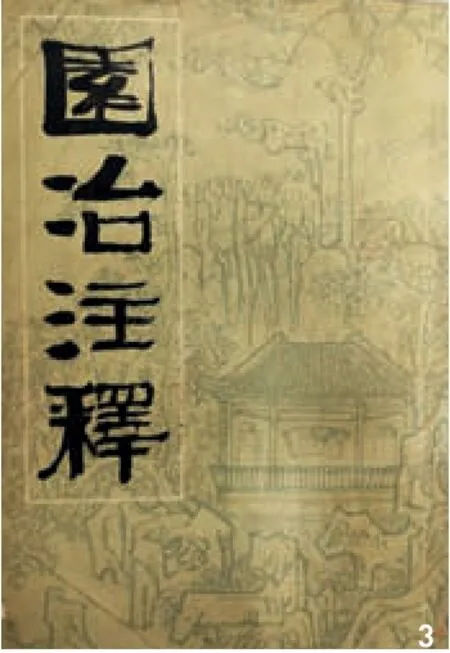
图3 《园冶注释》(1981年版)封面(作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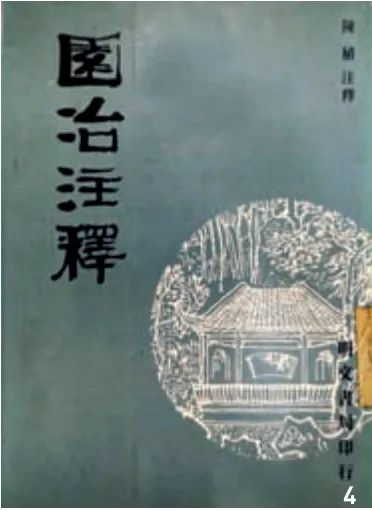
图4 《园冶注释》(台湾明文书局1983年版)封面(作者摄)
陈植一贯治学严谨,但因《园冶注释》成稿于特殊历史时期,且参考资料有限,确有不足之处。1985年前后,陈植着手对《园冶注释》进行修订。此时,他已87岁高龄,病体沉疴,执笔困难,只能口述。他在病榻上坚持完成了修订工作,并将重点放到校勘和注释方面,“逐字校对并补充或修订注释300余处,经年完成,益臻完善,裨使《园冶》一书之艺术光芒,永世长存”[2]。
3 开创《园冶》研究的新阶段
《园冶注释》是现代第一部对《园冶》进行整体性、系统研究的专著,“是中国园林理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17]。该书出版后,引发了对于《园冶》和中国园林文化的研究热潮,并推动了《园冶》研究向纵深化发展。
3.1 梳理了民国时期的研究脉络
《园冶注释》是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园冶》研究的综合整理和展现。陈植对于诸位前辈学者重刊《园冶》的工作予以充分认可和尊重,他以“营造本”为研究基础,并在书中全文附录了朱启钤的《重刊园冶序》(出自《喜咏轩本》)和阚铎的《园冶识语》(出自“营造本”)。“喜咏轩本”和“营造本”存世较少,后世的研究者难以获取。陈植将朱启钤、阚铎的原文附录,保存了2个版本的重要信息,使这一阶段的研究脉络较为清晰,朱启钤等学者所作的贡献也能够广为人知。
3.2 奠定了《园冶》文本研究的基础
在《园冶》文本的校勘上,陈植和协助其工作的杨超伯,以“城建本”为底本,用以校勘的版本,主要是《园冶》明刻本的照片、“喜咏轩本”,还参考了《云林石谱》。校勘之后修订的章节,包括序言、“相地”篇、“屋宇”篇、“铺地”篇、“掇山”篇、“选石”篇和“借景”篇等。值得注意的是,陈植对明刻本的一些错漏也作了校勘。
由此形成的《园冶》文本,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大限度还原了计成的原著,并加入了注解和白话文翻译。自《园冶注释》出版之后,近40年来,学术界以此作为研究《园冶》的通行文本。直到2018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原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崇祯七年刻本的影印本,国内读者才得以见到《园冶》明刻本的原貌。
3.3 影响了《园冶》后续研究的议题
陈植对《园冶》的解读和研究涉及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对《园冶》的考据,陈植对《园冶》相关的明代人物、明代园林作了考证,如计成及其交游的阮大铖、郑元勋、曹元甫和吴又予等人,以及寤园、影园、石巢园等园林,勾勒出了《园冶》作者及相关晚明士人的背景信息。
2)对《园冶》文化内涵的展现。《园冶注释》一书中附录的引用古籍书目达142部,涵盖了经史子集及方志等各类文献;注解涉及的传统文化领域,包括诗词歌赋、文献典籍、绘画书法,并援引了历代名园案例,如吴王消夏湾、石崇金谷园、王维辋川山庄和司马光独乐园等,以及诸多名人高士的典故,使得《园冶》所表达的文人园林的意蕴得以展现。
3)对《园冶》营造技法的解读,包括叠山理水、植景设计等。如 “相地篇”“墙垣篇”,为编棘、编篱、花屏等词注解,这是明代园林常见的以植物作为空间隔断的理法,陈植于此注解,展示了园艺学的深厚功底。
上述内容,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迄今依然是《园冶》研究的重要议题。
3.4 推动了《园冶》的广泛传播
陈植的校勘、注解和白话文翻译,使《园冶》这部内容艰深的造园古籍得以普及推广,不仅成为风景园林、建筑、艺术设计相关学科的必读书,甚至跨越学科的壁垒,成为普及性的古籍读物。
《园冶注释》出版后,对于海外学者研究《园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学者佐藤昌在所著的《园冶研究》(1986)序言中写道,正因为有《园冶》的现代版本,特别是陈植本的注释和白话文,才使他的研究成为可能[8]。
在西方,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1879—1966)是最早介绍《园冶》的欧美学者,他在著作Garden of China(1949)中翻译了《园冶》的部分章节,“但Sirén本人承认,由于语言难度,他的译文不太确切”[18]。而陈植的工作为《园冶》的翻译带来了便利。20世纪80—90年代,《园冶》的英译本、法译本相继出版,西方世界对于《园冶》以及中国传统园林文化的认识也得到迅速发展。
4 结语
迄今为止,陈植是《园冶》研究领域坚持时间最长、贡献最突出的学者,从20世纪20—80年代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始终保持对《园冶》研究的热忱,为弘扬传统造园文化而不遗余力,如陈从周所言:“先生60年来,致力于我国造园事业,为海内所宗仰。[1]”
作为造园学的奠基者,陈植强调学科发展要重视本国传统,认为《园冶》代表了中国传统造园文化的光辉成就,对于世界造园学具有重要贡献。正是由于陈植的不懈努力,《园冶》在营造学社重刊之后,几经变迁,仍能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引发关注,被学界广泛认知和研究,由此引发了研究古典园林的热潮,推动了相关园林文化遗产受到珍视。
陈植由研究《园冶》而扩展为关注其他造园文献,如出版《长物志校注》(1984)、《中国历代名园记选注》(1983)等。陈植的造园理论和思想对于学科发展影响深远。在以陈植为代表的前辈学者的推动下,中国风景园林学形成了重视史论研究、造园文献典籍的传统,《园冶》也成为研究传统造园的重要典籍,对于中国传统园林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