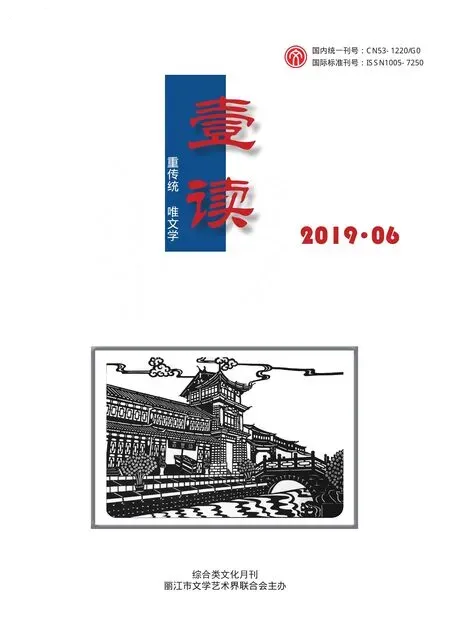用岑寂的目光读城
2019-12-18杨春山
◆杨春山
“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永胜为遂久县地,属越巂郡;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改属云南郡。唐贞元十一年(795年),南诏置北方赕。两宋时设善巨郡,属大理。元至元十七年(1280年)称北胜州,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升为北胜府。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降府为州。二十九年(1396年),置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正统六年(1441年),升北胜为直隶州。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升为北胜府。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降为永北直隶厅。民国二年(1913年),再降为永北县。民国22年(1933年)更名为永胜。”当我就着书房里明亮的灯光,翻阅着《永胜县志》里这段简洁的文字时,我真切地感觉到了历史的风云变幻。短短的200多字,就浓缩了滇西北永胜县2000多年的时光。其实,一座城,总会用它的包容,掩饰着时光和风雨的侵蚀,把征战、劫难、安乐、书香、酒气、民俗、家风、传奇都镌刻在一条条街道和一座座民居建筑里。2000多年,只有少量的人物和重大的事件才能进入典籍,在其中留下寥寥的几行印迹,更多的则被民间以传说、俚语、技艺、小调、习俗、趣闻等形式保存下来。而来自民间的记忆,往往却比书本里的记载更加长久。永胜小城的这些街道和民居,虽数度改换容颜,却见证了这个小城的朝风暮雨和朝代更替。在历史的面前,文化才是最后的获胜者。文化有着和蔼可亲的面孔,如同邻家长者一样慈祥,它深蕴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在这个小城里扎下了繁复的根系,这种不知不觉的浸润,却细水长流,当官员、商贾、术士、盗贼、流寇、土司、枭雄、酒徒纷纷谢幕之后,它们却和时光紧紧联系在一起,继续隐藏在这个小城的最深处。才子、佳人、儒生、进士、画师、工匠、农夫、马帮,将一个个故事,一段段经历,一首首小调,汇聚成了小城的传奇,在人们口口相传中,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并一直延续下来。在生活里,我们总是期待着走向一座座城市,看直耸云天的建筑,看耀眼璀璨的霓虹,看摩肩接踵的人流;或是走向一个个古镇,在新旧建筑交织的夹缝里,追寻一种短暂的舒缓生活方式,让心灵得到适时的休憩。但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自己居住的小城,总是认为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对那些漫洇四溢的文化气息视而不见。我和永胜小城厮守了20多年,虽然也曾出去看过外面的风景,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这座小城的一个院落里蛰居。20多年,在人生中是一段多么漫长的路途,但好像不经意间就从我的眼前消逝了。才记得是刚走上讲台的热血儿郎,转瞬间就已经进入阅尽沧桑的不惑之年。人到中年,心情开始走向沉静,步履开始变得从容,目光开始变得温和,不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纠结,不再为工作和生活中的得失而窃喜惊惶。拥有了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谢的精神状态,才有可能在小城里一个清风唱和着花香的院子里,守着一壶茶,让一段孤寂的时光逐渐变老;才有可能用岑寂的目光,阅读这座我已经生活了7千多个日夜的小城。
沧阳是永胜县城的代称,从内心和情感上来说,我虽然认可“永胜”的外露与直接,但更喜欢“沧阳”的淡然和温婉,“沧阳”一词所蕴含的文化韵味绵长且毫不张扬,但有着自己源源不尽的底气。县城曾经宏伟的澜沧卫古城已经消逝了,但小城依然保持着旧有的格局。“东街”“西街”“南街”“北街”,在十字街交汇,每条街道长约1公里,又被环城路拥在了怀中,形成了棋盘式的布局,方方正正,街道两边栽上了垂柳,柳梢上冒出的点点鹅黄和一抹翠绿,总是让我能够感觉到最早来临的春意。小城里容纳了不少的巷道,纵横交错,曲径通幽,收藏了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这样的小城是充满了人间烟火味的。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历史事件。从西汉武帝开发云南起,永胜就已经纳入了中原王朝大一统的版图。正是这次开发,让永胜这个边陲之地较早和中原文明实现了对接。蜀汉时期,诸葛亮五月渡泸,七擒孟获,在永胜民间留下了大量的传说与地名,成为当时那段历史的佐证。比如期纳谷宇村的祭锋台,据传就是在诸葛亮率军进入金沙江南岸的涛源、期纳一带后,见到期纳当地有老虎成精作祟,危害人间,为了帮助人民消除虎害,诸葛亮在谷宇村的后山上设立祭坛,登坛作法后挥舞宝剑,只见一道白光闪过,老虎瞬间被斩为两段。虎头滚落田间而虎身异处,当地虎患从此平息。在谷宇村的田地里,现在还有一个形似虎头的山包,而后面的老虎山则仅有虎身的形状,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传奇。当前,祭锋台遗址尚在。唐朝开元年间,皮罗阁兴于巍山,统一六诏后建立了南诏政权,永胜成为了南诏国的属地,后南诏主异牟寻从洱海周围、金沙江上游移来僰人、罗罗、傈僳、阿昌等种族,设北方赕。公元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封高方为岳侯,分治今永胜一带。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大理相国高智昇使其孙高泰慧统治善巨郡,从此,永胜进入了高氏土司统治的时期,达800年之久。而对永胜历史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当属“洪武调卫”。洪武十四年(1381年),由于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恃云南山高林多地险,置朱元璋的多次劝降于不不顾,屡杀明王朝派来的使者,朱元璋决定南征。30万征南大军在傅友德、沐英、蓝玉率领下进入云南征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1月,梁王兵败,率家眷自沉于滇池,元朝对云南的统治就此终结,“宋挥玉斧”的云南归入了大明王朝的版图。云南初定,世守永胜的高氏、章氏、子氏土司降明,但由于各地土酋不断反叛,明王朝在云南实行了“寓兵于农,屯民实边”的政策。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北胜州改属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并修建了澜沧卫城,调派云南中卫的大量军户、民户进入永胜屯田戍守。“洪武调卫”以来,随着来自湖南、江西、江苏、四川等地的汉族军士及家眷大量进入永胜,一些中原商人看到了商机,便通过茶马古道,开始和这里的人们互通贸易,有些商人也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这些军士、家眷和商人的进入,使永胜的民族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汉族军士们由于拥有朝廷派驻的背景,便得以在水草丰茂、土壤肥沃的坝区屯戍,而原住民族则向山区迁徙,这样,先进的农耕生产方式和中原文明顺利进入了边地,逐渐和少数民族文化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永胜“边屯文化”。由于永胜是连接滇川藏三省的重要通道,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元朝蒙古的铁骑弯刀,就是从永胜打通了攻占大理国的通道,革囊渡江攻取大理,史称“首捷此土,故名北胜”。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在朝代更迭之际,永胜总是被卷入战争的漩涡,无数的征战,让永胜饱经沧桑。明朝正德六年(1511年),北胜大地震,城北大树坪旧州城全部倾塌,民房被毁5000余间,人口伤亡千余人,土地冲塌、淹没者1万多亩。城北的红石岩震塌,三川坝的西山草海形成。这次地震,让永胜在战争的罅隙里,又经历了一次自然灾害的劫难。在清朝和民国,土司、义军、民团混战,清道光元年(1821年)的华坪傈僳族唐贵起义,咸同年间的杜文秀起义、片角水冲土家人朱明新起义,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傈僳族丁洪贵起义,都让永胜一次次承受了巨大的创伤。民国更是一个各路枭雄并起的年代,各色人物粉墨登场,在永胜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场血雨腥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艰苦的剿匪战斗,于1950年永胜全境全部解放,历史终于翻开了崭新的篇章。历史的特质就是真实、冰冷,回顾历史,那些文字总是掩藏了毕露的锋芒,显得波澜不惊。但透过文字的背后,我们总是可以看到狼烟、箭镞、战马、刀枪、鲜血、生命、饥饿、哭泣、死亡和无数人的流离失所。这些在人们身上发生的悲惨境遇,化为了典籍里最简短的文字,遮盖了战争和刀光剑影的无情与惨烈。只有这片土地上年复一年生长出的庄稼、鲜花、野草,还会记得那些让人心颤的过往。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文脉风流。“洪武调卫”以来,由于中原汉族军民、商贾的大量涌入,他们所带来的先进中原文化在和少数民族文化的碰撞中占得了先机,开始向少数民族文化里逐渐渗透,让边屯文化应运而生。永胜坝区的地名、村庄,多以官、伍、营、场、哨、湾、所、驿命名,深深地打上了边屯文化的烙印。千年的茶马古道,这条被称为南方古丝绸之路的大通道,进一步促进了文化和经济的交流。永胜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了茶马古道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于是,清水驿、他留山、金龙桥、金江渡……构成了茶马古道上的一个个要塞,让这条悠远的古道在永胜的群山和江湾里穿行,为这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积淀。中原军士在带来了先进农耕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崇文重商、知书达礼、耕读传家的文化传承。边疆稳定之后,屯边军士刀枪入库,化剑铸犁,让永胜的土地上长出了遍野的庄稼,让永胜的村庄里升起了不竭的炊烟。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一颗印,各式中原建筑在这片土地上华丽现身,让一个个村庄开始承接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这些把异乡当作故乡的中原军士,用忠诚与躬耕,让昔日的偏僻蛮荒之地,变成了粮丰水美的家园。当今的永胜汉族,说到先祖的来历,大多都说来自湖南、江西、江苏。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出,很多永胜汉族人的口音里,虽历经了几百年数十代人的定居,都还流露出浓重的湘音。有了茶马古道,有了中原文化耕读传家和诗书礼仪的滋润,永胜的文脉开始流动。文庙建了起来,地方所有要员都要参加每年隆重的祭孔大礼,让尊重文化、热爱读书的传统开始在这片僻壤上萌发。有了这样的环境,不出几个文化人似乎再也说不过去了。在明清两朝,永胜历史上一共出了八个进士(含一个武进士),举人、贡生、秀才更是不胜枚举。这在江南富庶繁华之地当然算不得什么,但在“孤悬江外”的云南边地,确实让人震惊。据《永北直隶厅志》载:“永郡虽地处边隅,而人文蔚起,郁郁济济,代不乏人,凡庙貌之巍峨,胶庠之造就,实有兴于未艾者……”在永胜的文脉风流里,有几个名字是注定要被记住的。谭昪,澜沧卫人,明天顺七年壬午(1462年)中举,为滇西北第一名举人,明成化二年丙戌(1466年)进士,曾任江西太和知县、四川合州知州等职,为官期间清廉纯正,两袖清风,死后遗物仅有数卷书、一张琴,琴上刻有“清风古琴,遗吾子孙”八字。刘慥,期纳清水人,乾隆丁巳恩科(1737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四任知府,后任福建按察使、河南布政使,两次署理巡抚职务。因病辞官回乡后,撰写《乾隆永北府志》,兴修水利,造福乡梓,书院讲学,写诗著文,为乡人称道,成为后世人们为官做人的楷模。其后的期纳清水进士黄恩锡、杨嵘、黄耀枢,也继承了刘慥清廉为官的禀性,颇有政声文声,为永胜的文脉风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期纳清水驿因“一村四进士”的荣光,被称为滇西北“文风之地”。此外,还有被道光帝称为“正经读书人”的王寿昌,拾金不昧、德寿还金的刘思善,参加戊戌变法和纂修《永北直隶厅志》的刘必苏,也成为了永胜土地上亘古流传的口碑。时间到了民国乱世,依然有徐抡元、高玉柱、张瑞贞、冷照明、单镜等众多名士才女,续写着沧阳文风之地的辉煌。徐抡元,字冠三,别号介山子,晚清民国时期永胜的著名文人。为人耿直,不畏强暴,不趋势利,家境贫寒,好饮酒,有陶白遗风。他吟咏诗章甚多,而时人以得其书法为荣,除豪强外,每有请其作对联、匾额、屏风、碑文者,无论贫富贵贱均乐意书写,现仍有较多诗文书屏传世。高玉柱,原名高擎宇,永胜末代土司高长钦的女儿。自小聪明伶俐,才智过人。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骑马射猎,无不通晓,时人称之为“滇西才女”。时逢乱世,高玉柱为实现心中的报国之志,毅然离开永胜前往昆明,后又辗转到达南京,多次请愿,并得到国民政府赏识,命她充任西南彝族驻京代表,抗日战争爆发后,民国31年(1942年),国民政府任命她为西南边疆宣慰团少将团长,对云南、贵州、广西、西康等省的土司和少数民族头人宣传民族团结,巩固边疆,共同抗日。后在滇南工作时因气候炎瘴,积劳成疾不幸去世,年仅36岁。高玉柱用她未嫁的女儿之躯,献身于伟大的民族抗日大义,实践了她“英雄半属女儿家”和“不复民族心不死”的铮铮誓言。这些出自永胜的文人士子,用他们的骨气、正义、善良和与世无争、淡泊名利的品格,为后世文人士子立身存照。及至现在,依然有谭碧波、海男、海惠、冯娜、刘汝璋、习应玄、李理、马霁鸿、陈洪金、木祥、黎小鸣、毛诗奇、马瑞翎、胡继惠等一大批文人墨客,在沧阳大地上续写着无尽的文脉风流。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民歌小调。如果说历史典籍是一个板着一副冰冷面孔的垂暮老者,那民歌小调就是一个满脸洋溢着笑容的明媚女子,活力四射,八面玲珑。一个地方的文化,总是会不经意地在民歌小调里驻扎,长久不会散去,成为人们现实生活、情感、习俗、思想的固定剂。作为边屯文化浓郁的县份,那些来自中原地区的军士们,在屯戍的同时,心头定会涌起对远在万里之外家乡的深沉思念。在一个个月光朗照的夜晚,他们坐在田间地头,或是树丛竹林之中,定会轻轻哼唱一曲忧伤的小调,来缓解自己心中无尽的乡愁。即将出征时,他们会在《出兵调》的悲苦中辗转反侧;辛勤劳作中,她们会让《采茶调》的旋律响彻在山间;尽兴喝酒时,他们会用粗犷的《划拳调》来展露心中的豪情;受到欺凌时,她们会用《苦媳妇》来倾吐内心的郁闷;外出奔波时,他们会用《赶马调》来排解对家人的思念;得到帮助时,她们会用《报答调》来表达对恩人的感谢之情……民歌小调,是民风民俗最真实的体现,通过一首首民歌小调,我们可以体会到悲伤、快乐、甜蜜、苦涩、忧郁、哀怨等各种不同的驳杂人生况味。读懂了民歌,就读懂了一方水土一方人文。那些从现实生活中信手拈来的歌词,完全扣合了当时的情境,往往会让人内心为之一颤,再华丽的语言,在丰富的民歌小调面前,都会黯然失色。永胜的民歌小调,以抒情和反映男女之间情感的曲调为主,或甜蜜,或忧伤,或直白,或委婉,赋、比、兴手法运用自如,旋律流畅优美,让这些民歌最贴切地表达了人们内心丰富的情感世界。“手捧凉水来喂你,妹的良心见得天”“妹在房中闷沉沉,听得小郎要出门,掉了奴三魂”“正月里来正月正,大理都督来调兵,千军万马你不调,调下奴的命肝心”“七送小郎墙拐角,哥养鸭子妹养鹅;歌养鸭子打失掉,妹养白鹅还在着”……劳动人民的智慧,在民歌小调里得到充分彰显,他们冒然不懂得现代修辞手法,但比喻、夸张、反复、拟人、顶真、对偶、移情、拈连、排比、反饰、双关、通感……任何一种现代修辞方法,都能在这些民歌小调中找到典型的范例。这些来自乡间野土的民歌,用浓郁的真情营造着乡村生活的气息,倾吐着乡村爱恋的味道,质朴真诚、不加掩饰地表达着这方水土孕育出的蓬勃生机。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技艺传承。在永胜小城,中原汉族带来的技艺,早已经在每一片沃野上生根发芽。农耕自是不必言说,由于永胜海拔高差大,水稻、玉米、蚕豆、小麦、花生、高梁、苦荞、甘蔗、棉花等各种作物和林果,都能找到一片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而中原军士们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改变了这里古老落后的刀耕火种,一片片曾经贫瘠的红土地,被精心耕作成了一个个米粮仓。每一个坝子里,庄稼都在年复一年茁壮的成长,让永胜充满了稻麦和瓜果的香味。繁忙的农事之余,精于工艺的匠人们,开始致力于用他们的技艺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面对遍野的竹林,边屯汉子用精巧的竹编技艺,编制了各种农具、渔具、生活用具,让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散发出竹子的淡淡清香;面对多彩的生活,边屯夷娘用灵巧的刺绣工艺,绣出了明艳的服饰、精美的床上用品,让每一个梦境,都绽放出花朵一般的温暖。还有制作铜器、陶器、瓷器、石器、铁器、纸马、花盆、井栏、马帮用具的工匠们,或收徒或父子相传,让这些技艺一直传承至今。在永胜,人们还用智慧和经验,腌制出了色香味三绝的三川火腿,制作出了美味可口的腊参、肝花酱、水酥饼、油茶、麦兰酸菜等充满了边屯特色的美食。随着时代的发展,竹编、刺绣、铜器、铁器、陶瓷的实用性已经减弱,但它们曾经在很长时间里,温暖了永胜人的生活,成为了每个永胜人心里最为亲切且不可替代的记忆。这些曾经辉煌过的技艺,开始逐渐进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这里,我不得不提的,是永胜最具特色的珐琅银器。珐琅银器因其色彩绚丽,具有宝石般的光泽和质感,耐腐蚀、耐磨损、耐高温,防水防潮,坚硬固实,不会氧化褪色,历久弥新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喜爱。永胜珐琅银器又称“掐丝珐琅彩”,是景泰蓝的一个品种。珐琅银器工艺自元初由蒙古族军士传入永胜后,一直传承至今。据《新纂云南通志》“工业考”记载:“永北厅之珐琅银器,自来擅长,清代以前,妇女首饰以金银珠翠四者制成,翠者翠鸟之羽毛也。永北厅制珐琅杯碟,华艳夺目,与直省所出无异。”永胜珐琅银器制品在造型和纹样设计上,遵循民间 “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突出掐丝,融入珐琅。色彩以青蓝朱砂为主,配以适量的黄、绿、白、赭等色,显得精美、雅致,其胎体轻薄,工艺制作极为繁复,造型实用美观,图案生动,色泽艳丽,主要有茶具,酒具、餐具、首饰等几大类上百个品种,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产品曾畅销海内外。随着时代发展,珐琅工艺的传承也历经沉浮,但还是有极少的工匠,用家族相传的方式将其顽强传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创新。唐建安、谭志平,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用不断创新、勇于探索的工匠精神,用手中的小锤敲打出了无比精彩的人生。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人文风俗。 知书识礼、崇文重教是边屯遗风。敬重读书人,让文化传承成为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坝子里的每户汉族居民,不管家里有没有读书人,都会把采光最好的房间设置成书房,平时兼作客房,这是永胜一贯的传统。在这样的环境里,读书、写文、绘画、吟诗,赏花、饮茶,让内心浸润在美好的事物里,一茬茬的文化人就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白手起家的边屯军民,自然不乏勤劳坚韧的品性。好的家风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对这个家族产生深远的影响。受得住气,吃得了苦,挺得住身,立得稳脚,这是边屯后裔的谋生之道。做生意的精明,为人处世的和善,沉浸在骨子里的血性,就这样矛盾而又统一在了永胜人身上。出门在外的永胜人,通过做点小生意发家致富的,不在少数。而更多的人,则是通过读书上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为了各个部门的管理者、建设者,他们的工作能力、吃苦精神、责任意识常常被人称道。永胜人又有着深厚的家乡情结,年轻时背井离乡在外打拼,暮年时回归故土叶落归根,是很多永胜人内心最为坚定的选择。因为出门在外,就没有了火塘边喷香的油茶,就只能在异乡的土地上,感受到故乡和妈妈无尽的牵挂。
用岑寂的目光读城,要读这座小城的明日辉煌。如今,永胜正像一只即将腾飞的苍鹰,向着广袤的天空挥动翅羽。站在西山顶上,俯瞰永胜县城,楼房鳞次栉比,田野郁郁葱葱,青山静美含笑,一个个园区正在成型,一条条高速公路已拉开建设的序幕。我们有理由相信,曾经的沧阳城,如今的永胜,必将在未来的时日里迸发,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吹响前进和胜利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