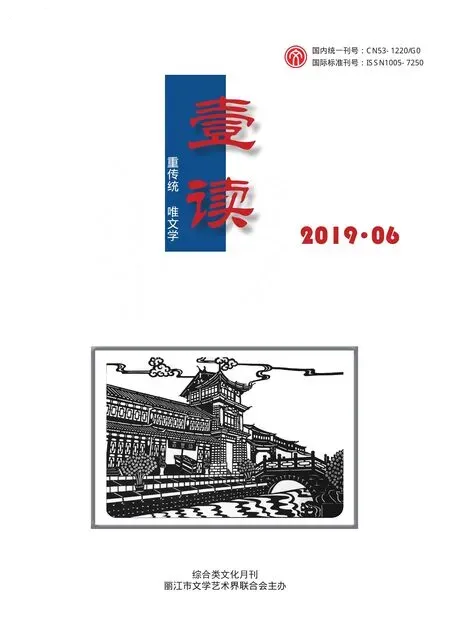枸杞(外一篇)
2019-12-18李方
◆李方
1
在最早的时候,它是野生的。现在依然还有野生的枸杞,大约生长在海拔2600米到3800米的青藏高原上。但是人类对于自然万物的认识和富有创新精神的繁殖培育,确实也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种野生的、低矮的植物,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可观的根、茎、叶,以及缀满枝叶间如同夏夜繁星一般的花朵和犹如红宝石一般香甜的果子。它现在的身份是“枸杞树”。野生在沟壑渠畔、田埂道旁的枸杞树的祖先,故乡的人一直把它们叫做“狗牙刺”。特别形象和准确的称呼。因为它们身上长满着细小的、白硬的、尖利的刺,确实很像恶狗露出的牙齿。但是它们所结出的果实,虽然艳红着,饱满着,闪耀着诱惑的光泽,但是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能吃,仅仅可以小心地摘下来,用细线串起来,戴在脖子上,当作钻石项链。贫困年月的山村孩子,对于拥有这样一串上天赏赐的宝贝,也是很满足的,很值得炫耀的。
2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人工培育后栽植的枸杞树,也从未尝过枸杞果的味道。但是我已经隐约地知道,固原七营乡张堡村有人在种植枸杞。多年之后,因为该村要立一块石碑,记录枸杞在张堡村的栽植历史,将碑文拿来请我修改斧正,我才有了基本的了解。据碑文撰写者贾仁安先生介绍:最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的父亲曾从宁夏中宁县带回来几根枸杞树苗,栽植在自己门前的菜园子里。但是这种形似漫山遍野生长的“狗牙刺”的“树”,结出的果实人人都认为是“狗牙刺”,没有人敢食用,当然也就没有销路,更谈不上有收入。只能当作一种“花树”来观赏,所产的果实,收摘晾晒后也只有他父亲自己泡茶喝。就是这样的不足十棵的枸杞树,后来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强行割掉了。贾仁安参加工作之后是在林业系统,对枸杞的认识产生了飞跃。而且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大集体到土地承包,从吃大锅饭到独自单干。张堡村大面积引种枸杞,基本上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直到现在。
3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的故乡开始栽植枸杞。但是作为一个常年在外工作、很少与土地打交道的人来说,无论老家的田地里种植什么作物,我其实是很淡漠也很少去关注的。但是因为栽植枸杞,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一方面是因为好奇:人们怎么会对“狗牙刺”如此热衷?而且枸杞果的价格已经攀升到了每市斤干果接近10元的程度。就算我辛苦工作一个月,不请假,不迟到,月薪也不到300元。每亩枸杞的收益,大大超过了我十个月的薪水。另一方面,是枸杞果的采摘,竟然会让一个才上小学一年级的儿童也得到令人眼红的报酬。大约,孩童们的好动天性,使得他们感觉这种从树上摘取果实的劳动,其实是有着大乐趣的,同时那小小的五指,要比成年人更灵动敏捷,确实易于摘取那些小小的红宝石。还有一点:当时并没有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孩子的学杂费也是家庭里不小的一笔开支。放暑假的时候,也正是枸杞采摘的旺季。如果哪个家庭贫困的孩子还想在秋季开学安心地坐在教室里听讲,那么在暑假里为自己打一份工,干自己力所能及的活,赚取自己一年的学费,恐怕就是最理想的暑假生活了。
4
三叔父是庄子里最早栽植枸杞的人。就像他是庄子里最早手腕上戴着明晃晃的手表,最早拥有照相机为村民拍照,最早学会手风琴在村戏班子里演奏的人一样。他虽然是个农民,但是他有着一般农民所没有的超前思维和开拓创新精神。按照村里人的话说,他有着一个“化学脑袋”。所以他率先在自己的二亩承包地里栽上了枸杞,而所有的村民都在等着看他的笑话。最终,是村民们三三两两、偷偷摸摸、露出憨直和羞涩的神情到他家里去讨要枸杞苗、求教栽植术。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对文学痴迷,并且不知天高地厚地交往全国各地的“文友”。因此在暑假期间,回到乡村,来到三叔家里,用每公斤26元的价格,买了5斤纯正的、已经晾晒炮制好了的干果,然后返回城里,通过邮局,寄到了遥远的湖南。随后写了一封文绉绉的信,并天才地将宁夏的枸杞和南国的红豆相比,以寄托虚无缥缈的“相思”。而湖南的女文友在回信中提出了一连串让我难堪的问题:这种果子是吃的,还是看的?如果吃,怎么吃?放到什么地方比较合适?放的时间过长,会不会生虫子?要知道,湖南远比宁夏的雨水多得多!
5
宁夏原来有五宝,红黄兰白黑。红的枸杞,黄的甘草,兰的贺兰石,白的二毛皮,黑的太西煤。这应该是五十年前对宁夏本地特产的一种高度概括。黄色的甘草是中药的重要原料,但正是毫无节制地刨挖甘草以追求短暂的眼前利益而极大地损坏了草原和植被,后来被禁止;九曲黄河孕育出丰饶的宁夏平原和河套平原,在平原的田间林网间吃嫩草饮黄河水长大的滩羊,其洁白的羊毛有如九曲黄河一般,所以也称一宝。但后来羊只改良换代太快,加之“退耕还林草”与“封山禁牧”政策双管齐下,羊只的养殖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这个优势已不存在。所以现在宁夏并不提倡还有这五种宝贝。但是枸杞,依然别称为宁夏的“红宝”。中国是最早利用枸杞植物资源的国家。从《诗经》往前追溯,在甲骨文中都可找到枸杞的踪迹。甲骨文卜辞中的“杞”字,就是枸杞。先人以“杞”树作为植物图腾,正是源于枸杞的果实对人的生命具有神奇作用的崇拜。这种崇拜,甚至在后世演绎为姓氏、地名、国名。仅在古代诗歌总集的《诗经》中,关于对枸杞的歌咏就有七篇,从《国风将仲子》“无折我树杞”的诗句看,早在西周时期,庄园主已经拥有自己的枸杞园了。“我的枸杞是不允许别人折摘的”,这说明在西周时期,人工种植的枸杞已成为一种私有财产。从《诗经》以后,枸杞,这颗小小的红果,在唐诗宋词里也获得了众多名家的溢美之词。唐代诗人孟郊《井上枸杞架》写道:“深锁银泉甃,高叶架云空。不与凡木并,自将仙盖同。影疏千点月,声细万条风。迸子邻沟外,飘香客位中。花杯承此饮,椿岁小无穷。”诗豪刘禹锡也写过一首《枸杞井》:“僧房药树依寒井,井有香泉树有灵。翠黛叶生笼石甃,银红子熟照铜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还知一勺可延龄。”从诗句中可以看出,唐时人们就对枸杞的药用价值有深刻的认识,有意把枸杞树种植在水井边,以期望健康长寿。古诗文对枸杞的记载和称颂,也解释了古人乃至皇家贵族对枸杞的重视程度和对枸杞药用价值的肯定。甚至在当时,枸杞的采摘成为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可以这样说,枸杞从4000多年前的殷商起,就以其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功能,成为人们心目中十全十美的极品、神品。它源远流长的历史,扑朔迷离的传奇,神奇功效的药理,养生保健的饮食,红红火火的吉祥,早已超出了单一的地方名优特产和特殊的药食两用的植物,而演变成璀璨的中国枸杞文化。
6
枸杞在宁夏的人工种植,应该从北魏天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算起。当年,薄骨律镇刁雍将军奉命在今中宁舟塔乡田滩村黄河南岸设置船坞,每年建造船只200艘,首开河套航运。那时黄河岸边生长着许多的野生枸杞,每到六七月,黄河岸边红彤彤一片,有造船的士兵不慎受伤,闲来无事,就在黄河边采摘野生枸杞果吃。没想到,吃了野生枸杞果之后伤口愈合很快。这事被薄骨律镇刁雍将军知道后,为做长期打算,他就组织士兵开垦土地种植枸杞,并把采摘的枸杞果晒干,运往京城酿酒制药。后来枸杞酒成为王公贵族保养身体的贡品。算来,枸杞在宁夏的人工种植历史最少也有1600年了。
枸杞最早只在宁夏黄河平原地区种植,并以中宁为重镇,品质也最好。一颗小小的、红红的枸杞,被中宁做成了大文章。不但枸杞节年年举办,而且形成了独特浓郁的红枸杞文化,直到成为中国枸杞之乡,誉满神州。而中卫香山酒业对枸杞业的发展助推,更是将枸杞文化传播到了全球。“每天喝一点,健康多一点”的“宁夏红”,通过国际巨星成龙的演绎,让地球人都知道了宁夏,知道了宁夏的枸杞。
7
枸杞在宁南的种植,跌宕起伏,辛辛苦苦地栽,满含愤怒地挖;挖了又充满希望地栽,栽了又挖。根本原因还是市场销售存在问题。而且对于劳动力较少的家庭来讲,种植枸杞真正是“一亩园,十亩田”,它的采收,晾晒,储存,都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人力。如果产量上不去,或者遭遇连绵的阴雨天气,或者某一年枸杞市场疲软,都有可能挫伤茨农的积极性。而一些家庭如果承包地原本就少,而栽种了几亩枸杞后却没有明显的收益,则连基本的吃饭都成了问题,他就只好挖掉。但是这近十年来,由于宁夏枸杞的深加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其是中卫市“宁夏红”枸杞保健酒的研制成功,市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增强,开创了枸杞产业的新局面。枸杞市场一直比较稳定,而且价格也很平稳,仅在宁夏区域内至少带动了10万农户依靠枸杞产业增收致富。在枸杞收获季节,枸杞采摘雇用劳务收入就达5000万元,有100万人加入了枸杞种植和深加工领域,使枸杞产业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致富增收的黄金产业。所以在固原城以北的清水河流域,枸杞的种植面积在逐年扩大。每当枸杞采收的时候,东西两山的农民,都会来到川道里采摘枸杞赚钱。一些村、镇还有比较好的传统,根据各自村庄种植的作物不同,而相互帮助。如海原县三河镇是一个回汉民族相融合的大镇,回族主要居住在镇西面,汉族主要居住在东面,他们的劳动力资源、物质资源在季节等不同条件下有明显差异。多年来,回汉民族和睦相处,资源和谐互配。尤其在近几年,东西互相帮助,谁也离不开谁。在每年冬灌季节,汉民村及时组织劳力帮助回民村完成修渠、打埂工作。而在六、七月份,大面积种植枸杞、玉米等农作物的东面汉族几个村,采摘枸杞达到高峰时期,只靠自家劳力,无法完成枸杞采摘,西面的回族村村民大量涌向东面采摘枸杞,而且个个都是采摘能手,每天能挣到几十元到上百元现金。枸杞采摘接近尾声,又是玉米收获的季节。玉米秸秆是牛羊的好饲料,以养牛养羊为主的西面回族村,又要帮助东面汉族村砍倒玉米秸秆,付给秸秆费用,源源不断地把玉米秸秆拉回西山里的家中。
8
中国人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对“野生”“生态”“天然”“绿色”如此疯狂和迷信过。透过表面现象,我们深知的是:一切以获取金钱为目的的造假手段的花样翻新,人工合成的毒素对人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是无法弥补的。从青海数千人疯狂非法采摘黑枸杞事件,我才知道村子里为什么突然间大面积培育黑枸杞苗了。
也只是近两三年的事情。原来栽植的枸杞,正在成熟,且早已被村民们所熟知。虽然经历过栽栽挖挖的曲折,但是如今基本上平稳了下来。栽植面积、亩产、价格、每亩的收益,这些都是明确的,心中有数的。但是突然,来了一股培育、栽植黑枸杞的风潮。
尚在老家耕种的三个弟弟,无一列外,都处在一种茫然和盲从的境地。把种植好的芹菜拆挖掉,全都栽植上黑枸杞苗。我看不出这种黑枸杞与红枸杞有什么区别,更看出不它和野生的“狗牙刺”有怎样的不同。但是一年过去,苗子长大,却无人认购。每棵黑枸杞苗,贱到只有几分一毛的地步。那么当初是谁带的头,说是要培育枸杞苗呢?谁也说不清。谁都不记得了。当初雇佣人工,从青海、兰州按每斤3000多元钱购买籽种,通过浸泡、点植、覆膜、间苗、灌水、除虫等等的劳作,其劳动力成本不计外,什么不用花钱呢?但是现在投资出去了,却没有收益,还得再雇劳动力,将这些“狗牙刺”清除出原本应该种菜长庄稼的土地。看看无望,只好挖掉。七弟心疼这些好不容易才栽培出来的黑枸杞苗,全都按四五寸的长度截断,用草绳捆起来,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院子的一角。母亲每次做饭,都抱来四五捆,三两个人的饭,也足够燃烧的。哪知风云突变。去年黑枸杞的苗子,价格一路飙升到每株三四元,并且有多少要多少。三个兄弟相视一看,只有苦笑。我回家看母亲做饭,就给在外地工作、回家探亲的五弟说:你吃妈的这一顿饭,有点吃不起了。太贵。五弟不解。我给说了黑枸杞苗的近乎于传奇一般的过程,五弟算了算,说:饭倒不贵,就是做饭用的燃料有些太贵了,贵得人心疼。
老家邻居是小两口,养着些下蛋的母鸡和每天清晨高声啼鸣的公鸡。受黑枸杞苗的风潮影响,也在偏远荒凉贫瘠的一亩承包地里育上了。苗子价格贬低到不堪的时候,夫妻两个也是你埋怨我,我诅咒你,谁都不愿去地里挖,况且养着那么多的鸡,很忙,是个很好的借口,就赌气没有处理,就让它们那样在荒地里长着。结局已经知道了:由于他们的懒,由于他们的忙,由于他们的互不相让和赌气,今年,他们的一亩黑枸杞苗,带给他们五万元的收入。我一直在想:这小两口,晚上睡在被窝里,是否还会争吵?因为这简直是丢了又捡回来的钱。
9
当然也有育成的。去年三个弟弟多多少少都育了一些。我问:不再挖了吗?他们还是苦笑。不育黑枸杞苗,再弄个啥好呢?管它价格好不好,育上,相当于把地荒着,再也不摊什么本钱,等着。等一个好价钱的年份。
但是已经栽培出来的黑枸杞苗等不及。去年才育的苗子,今年已经结果了。黑枸杞结了果远处是看不出来的。就是走近了,不弯腰、不细看也很容易被忽略。只有你蹲下身子,小心地用手指头捏起它的还显得柔软的苗稍,细看,你才会发现,在一片片稍微卷曲的叶片下,在一个个细小的尖刺旁,结着像豆子一样大小的圆圆的黑色的果实。
因为这不是枸杞树上结的果实,这其实是苗子的营养过甚或者是发育得太早了的缘故,也或者就是黑枸杞旺盛的生命力的证明,所以它结果了,而且非常繁密。我细细地采摘着这果子。外表看,它是黑色的,其实稍一用力,它就破裂了,它的汁液是紫色的。采摘不长时间,几个手指都会被染成淡紫。据说这种黑色的枸杞,干果的价格每公斤已经接近于万元,它的青色素含量是比红枸杞高,但并没有科学可靠的实验证明它具有天然的“抗癌”的作用。但我还是存了私心,慢慢地、认真地采摘了几天,然后,把它们晾晒干净,带走了。
我的私心是:但愿它有着巨大的功效,那么它就有了广阔的市场前景。有了这个市场前景,三个弟弟的苗子就不愁卖不出去,不愁卖不上个好价钱。
至于我采摘晒干的这些如花椒一般的黑枸杞,我就送给一个女人吧。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懂得爱情,以为爱情就像红艳艳的红枸杞一样,是明亮的,耀眼的,甜蜜的,艳丽的。但是现在,我们知道,再绝妙的爱情,犹如这枸杞一样,要想摘到它,还是需要小心谨慎,因为,它往往伴随着尖刺,会伤害到手指。
十指连心啊。
玉米地
一步宽,乘以二百四十步长,等于一亩土地。五亩玉米,如果地宽为一步,要收完这片玉米,我一个人,需要走一千二百步。仅仅走完这一千二百步,并不是很难。在城市的霓虹灯下,用皮鞋的硬跟和更硬的水泥路面相接触,那是散步。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不过是超过了健康所需的锻炼步伐的十倍而已。但事实上远远不是这样。还需要双手的劳作。我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尽管不是一双养尊处优、白皙娇嫩的手,可是自从双脚从故土的田野走出去,穿上皮鞋,在马路上学会走路之后,这双手,已经习惯于翻书本和揭报纸,或者在电脑的键盘上灵动地舞蹈,生疏于锄把,疏远于稼禾,厌倦于沾染上泥土了。而现在,这双手,作为一种保护,被套上了不透气的橡胶手套,在右手中,紧握着一枚五寸长的铁钉。
我所要面对的,不仅是五亩等待收割的玉米,还有久违了的对土地的感情和对劳动的热情。我并不拒绝这种感情,也不惧怕这种热情的复苏,我所需要的,只是对持久劳作所带来的疲惫的抗拒和抵抗肉体疼痛的毅力。对此,我在心理上已做好了准备。
现在开始。
基本的劳作程序是这样的。你站在两行玉米秆的中间。放心,这中间的距离恰好容得下一个成年人的身躯。从春到秋,我的兄弟一直都在这样的两行玉米之间穿行。点播。间苗。除草。施肥。灌溉。你的左右两手,对付的是两行玉米秆半腰上所结出的玉米棒。先左后右。用左手抓住玉米棒的中间部分,抓稳。右手握着的铁钉,很容易就能插进玉米棒的顶部,用力向上一挑,将玉米棒的外包皮一分为二。左右手紧密配合,抓住分开的包皮,同时快速地扯下来,玉米棒金黄的裸体,直直地,硬硬地挺立着。你想象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其实它就是真实的、尚未脱离母体的玉米棒。用右手轻轻一折,包皮的底部,呈现出一个湿润、细腻,好像充满着一定温度的圆窝。无论握在你手中的这个玉米棒是长是短,是粗是细,是颗粒饱满还是籽粒瘪秕,你都必须承认,这里,是这根棒子受孕、子房膨胀、棒芯变粗、籽粒成长的地方。如同我们面对老屋地上那面当初呱呱坠地的土炕的感受。且慢,收住思绪的缰绳,赶紧把手中的玉米棒子扔到地上,转过身去,用同样的动作,收拾右面的那一个。
不是所有的玉米棒子都可以这样来收获。个别玉米,从它一出生,就遭遇到了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意外与天灾。如果它恰巧处在地边,每一次浇水,清流都没有到达它那里,那么注定,它不可能和其他玉米一样,也结出粗长壮实的棒子来。那么,它的棒子,就只有一二寸长,甚至只是一个圆形的疙瘩,上面缀着零零星星的几颗玉米,颗粒也不是金黄的颜色,而是呈现出一种尚未成熟的青白。个别玉米,长到一定时候,害了癌症,又没有得到及时地医治,在整个棒子的身上,满布着黑色的肿瘤,撕破肿瘤,里面是黑色的灰包夹杂着白色的细丝。这棵同样被赋予了结出饱满颗粒希望的玉米,就这样混杂在无数的玉米中间,痛苦地度过了一生。一些玉米,在快要成熟的时候,也许是因为风,也许是因为人的脚,被吹折,被踏倒,秸秆倒伏在地上。不能忽略和轻视它们。弯腰扶它们起来,你会看到,它们同样奉献着硕大的棒子。还有个别玉米,怀了别样的心思,在结了正常的棒子之后,又结出一个小的棒子来。小的棒子,都结在大的棒子下面。尽管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观察到,凡是结两个棒子的玉米,要么是处在低洼处,根部可以多存住一些雨水;要么,它与其它玉米之间的株距和行距都超出了正常的距离,那么,它是营养过剩了。条件好的,环境允许的,可以多生一胎。这是我的结论。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多耽误一点时间,来采收这个小棒子。我把这些小棒子,一律称作“二道毛”。因为这时候玉米棒子顶上的缨子,已经从当初的嫩黄,变为黑色,干枯而卷曲,很像许久没有洗涤和梳理的毛发。
掰玉米的劳作过程,基本上就是这样。剩下的,就是机械的操作。如果人是一台机器,输入了这样的程序,并且在操作的过程中不出故障,完全可以放心地投入使用。但人,毕竟不是机器。玉米缨子上挑起的灰尘,会飘入鼻腔,凝结成黑块;落到臂膀上,会引起红疹发痒;持久而机械的劳作,对一个平时并不注重锻炼、猛然间参加劳动的人来说,也极容易产生疲劳。
从变得闷热的玉米行子里出来,迎面是一股轻微的凉风。这片玉米地的东侧,紧挨着铁道,一列电气化火车正呼啸而过。坐在田埂上,脱下手套,在衣服上胡乱地擦一擦手,就可以喝一口水,抽一棵烟,看着火车。喝了,抽了,身心得到了短暂的放松,白面饼就着西红柿,可以补充一些体能。吃完了,马上返身回到玉米行子中,这是一条基本经验。初次劳作的人,越缓越乏。必须像上紧发条的玩具,继续奔跳。而一千二百步,连零头都没有走过。
这时候是正午。虽然秋天的阳光没有盛夏那样暴烈,但高过我头顶的玉米,显得密不透风,闷热就是这样产生的。阳光强起来的时候,那些早上还沾着露水,非常柔软的玉米叶子,也变得干硬和锋利起来。每掰下一个玉米棒子,手臂和脸上,都会被叶子的边缘划出几道白痕。汗流下来,经过这些白痕,就像酒精洗涤伤口,有一种凉意的蜇痛。钻在玉米地里,我唯一能够看见的,就是玉米地旁边为火车输送电能的电线塔的塔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坚持,一定要坚持。哪怕再苦,再累,也要坚持掰到下一个塔顶。那种惯有的软绵绵的疲惫,席卷全身。我低着头,故意不看那个塔顶。就好像那个塔顶并不存在。我只注意看趴在玉米棒子外面的那些细小的虫子,在包皮被猛然撕扯的时候,是怎样地惊慌失措,四散分逃。但我并不担心它们会被摔坏。它们那样细小的身体,既是从一米高的地方摔下,落到地上,依然完好无损,且又快速地逃掉了。那一个个被紧密包裹的棒子,在双手的配合下,露出它们金黄的、一丝不挂的裸体。但是我的手,已经不太听从我的指挥。一次又一次,把手中的铁钉,悄无声息地滑落到了地上。而地上,脱落的干枯的玉米叶子,在努力地做最后挣扎的杂草,往往会掩蔽了黑色的铁钉。你只能蹲下身去,拨开落叶乱草,并且不断地扩大范围,才可能找到。这时候,回头一望,走过的地方,也就是两行玉米秸秆的中间,铺成了一条细细长长的金黄的道路。那么笔直,那样耀眼。
常常要从繁密闷热的玉米行子里钻出来,透一口气,吹一吹凉风。就是手套,也需要脱下来,让双手通一下风。十个指头,都是湿漉漉的。在两根手指之间,已经起了细嫩的皮。这样的不经劳作,使我替自己的双手感到羞耻。
在休息的时候,我仔细数了一下手中的几个棒子上的颗粒,取了一个平均值。每个成年的棒子,大约可以结四百颗玉米粒。投入与产出比,应该是一比四百。每亩播种四斤,产量应该在一千六百斤左右。但你不能保证所有的种子都发芽,发了芽都能顺利地长大结出棒子来。就算是苗出的很齐整,也不能做这样的估算。气候,土壤,水肥,虫害,有许多因素在影响和制约庄稼的收成。因此,一亩玉米的最好产量是一千五百斤。而种植的品种,是登海3672号紧凑型。在玉米杂交之父山东李登海的土地上,亩产可以达到二千斤以上。紧凑型是相对直板型而言的。紧凑型玉米的叶子是按照40-50度角生长的,更有利于进行光合作用,因而种植密度大,抗倒伏能力更强。但也正是这种密度,使我的“行走”更为艰难。当你站在两行玉米秆的中间,左右会有七八个棒子在等待你。也就是说,每挪动一小步,起码要收拾干净二三十个玉米棒子。在这里,种植的密度等于劳动的强度。
听到四轮拖拉机的声音,我停止了劳作。我知道,收工回家的时间到了。抬头看看塔顶,正好和我对齐。一早上,我已经看到了三个这样的塔顶。
从玉米的行子里把那些棒子背出来装车,并不比掰那些棒子轻松。闷热更甚,但必须一次又一次钻到玉米行子里去,把那些金黄的棒子一个一个装进背篼,然后,把玉米干枯的叶子刷得像流水一样响,把它背出去倒在车厢里。来来往往中。我粗略地算了一下,从我开始掰这根棒子开始,掰的时候摸一次,背的时候摸一次,垒到架上摸一次,脱粒的时候再摸一次。要见到一颗一颗的玉米粒,每个玉米棒子最少得摸四次。五亩地的玉米,一共有多少棒子?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不管它有多少,我都会将它们一一摸遍。
装完玉米,我点燃了一棵烟。顺着铁轨,我从一座电线塔走向另一座电线塔。它们中间的距离是四十三步,也就是说,从露水打湿衣背的早晨,到汗水蜇疼脸颊的中午,我走过了大约一百二十步。等吃过午饭,我再来地里,从太阳当顶劳作到夕阳西下,那么我将走过二百四十步。我还将看到三座同样的塔顶。顺着电线塔望去,看似密密麻麻。站在玉米地里,它们便等距离散开。我只需低头劳作,总会把它们一一看遍。
等到国庆长假结束,五亩玉米的秸秆都已被人砍伐干净了。那是西山里养牛的人家,以每亩八十元的价格买去了。最后的那一天,我不但看到了塔顶,也看到了塔身。它们整齐地排列着,静默无声。但是它们所输送的电能,正把一车的旅客运往目的地。坐在车上的乘客,看到一地的玉米都已被收割干净,一定会在心里想:秋天快要过去了,看,玉米都被收完了,田野,已经空旷起来了。
而这时,种地的兄弟,却有了新收获。他加工的第一批五吨粉条、粉皮,业已晒干、装袋,准备出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