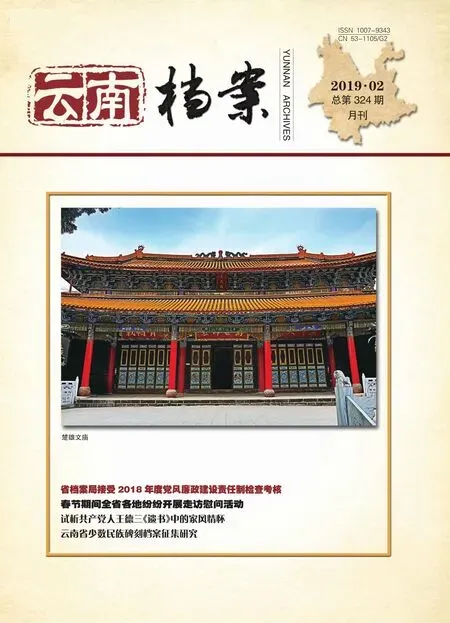救亡名曲《五月的鲜花》诞生始末
2019-12-17王祖远
■ 王祖远
1963年12月,诗人光未然在北京意外地接到北京二十六中学校方代笔的一封“诀别信”。信中说:遵从本人临终委托,今由我校来信奉告:本校特级教师阎述诗先生已于本年11月23日病逝。一见阎述诗的名字,光未然如见其人如闻其歌,惆怅之情,难于言表。想起他所谱的救亡名曲《五月的鲜花》,如烟往事,浮现眼前,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1937年夏,救亡歌曲《五月的鲜花》传播到上海,那正是“抗日有罪”,救亡运动“触犯王法”的黑暗年代,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查禁及时推广传播这支歌,好心人给她编织了一则故事,在上海歌咏界传为美谈,上海《立报》曾载文作了介绍。故事大意是,东北青年阎述诗擅长写诗作曲,因不堪东北沦亡之苦,约集12位热血青年立下盟誓,生生死死共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次宣传街头时,阎述诗与12位青年同被日军拘捕,关押了不久,12位青年中许多人历尽严刑惨遭屠杀。阎述诗九死一生,为了痛悼战友,他在狱中写下歌曲《五月的鲜花》,委托难友展转传递,后来经探监者从狱中携出刻印散发。于是《五月的鲜花》便在北平、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传播,各地歌咏界争相传唱,成为一首著名救亡名曲。
7月中旬,冼星海与张曙以上海歌联名义发动4000余工人、店员、学生、市民,假市郊大场山海工学团操场举行群众歌咏大会,公开推广教唱《五月的鲜花》。真是碰巧,光未然当天也按通知带领读书会一行参与盛会。大会开始,冼星海、张曙便轮流登上方桌,不顾汗流浃背,连续挥舞双手指挥群众学唱。教唱中途,光未然因去操场旁边教室会见各团体带队人,正好被在场的山海工学团老师李雷(原东北大学学生、诗人)发现。李雷与在场者一样,也急于了解这支歌的真实情况,因此便向场内群众挥手高呼:“《五月的鲜花》词作者光未然来了,快请他来介绍创作经过……”顿时场内掌声骤起,群情振奋。几个青年自告奋勇疾步奔到操场边教室,把光未然全身托起,前呼后拥抬到操场正中……就在此时此地,光未然与冼星海相识。翌日,他便应约去冼星海家商议首次合作《高尔基纪念歌》……后来两人在延安共同创作了惊世名作《黄河大合唱》。
作为“五·四”以来优秀歌曲,《五月的鲜花》几十年来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中一再被人传唱。可是阎述诗从未透露自己是这首歌的曲作者,更令光未然深感遗憾的是,他与阎述诗同住北京这些年,竟然从未谋面,这更加勾起无限怀念之情。就在收到“诀别信”后,怅然提笔写下了纪念文章《关于五月的鲜花》。
光未然在全国解放前后,曾向音乐界的朋友多次打听音乐家阎述诗的下落,可是都没有结果。想不到直到阎先生逝世后,才知道他原来是北京第二十六中学的数学教师,而且是一位认真负责埋头苦干的老教师。这样一位谦逊而不好名的爱国音乐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历程。
1905年3月28日,阎述诗出生于沈阳小河沿一位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阎宅仁是当地颇负声望的数学老师,且是爱好音乐的基督教徒。任教之余,爱弹起风琴带领全家合唱圣咏自娱,阎述诗受此薰陶,自幼爱好音乐。至入奉天文荟书院,他在父亲的帮助下学会用风琴弹奏四部合唱,接着他又跟随父亲去教堂做礼拜,咏唱赞美诗,未及成年,他居然在教堂担任起圣咏合唱风琴伴奏来。
1923年,阎述诗转赴北平入汇文中学就读。两年后又考入燕京大学本科。两校都是重视音乐教育的教会学校,尤其是燕大,聘有美籍音乐教授范天祥(汉名),开设音乐理论选修课,组织学生合唱团,定期举办唱片欣赏,在北平教会学校首开新风气。阎述诗如鱼得水,在浩如烟海的欧洲近代音乐中尽情涉猎。一到课余,他总是不失分秒的读谱抄谱,搜集中外名曲。假期返家,他便携回自编的“藏谱集”、唱片,开动手摇唱机,边看乐谱边赏听唱片,日积月累,终于揣摩到欧洲近代作曲技巧,加上平时练弹练唱圣咏合唱,了解合唱曲的规律,于是借助风琴写成了《阳》《悲》《水滨》等第一批合唱曲。
1926年夏,他在燕大读完大一课程,便忍痛中止大学学业,返回沈阳,潜心从事中学教学。至1934年秋,他先后在文华中学、沈阳师范、同泽女中任教,由此开始了历时八年的音乐生涯。这是阎述诗一生的重要阶段。
在这八年中,他组织过音乐社团,曾吸收基督教神学音乐交际会、盛京医大、文华中学等校师生共30余人,创办谐和歌咏团(后更名谐和音乐团),举办不定期音乐会与一年一度的音乐交际会,公演中外歌曲,包括演出他自己的新作。
在这八年中,他还创办音乐期刊,先办《遏云》,共出过两期,都是他本人自写自编自题刊头自筹经费的。继又创办周刊《白雪》,共出过30期。
在这八年中,他创作了大量歌曲,既有抒情歌曲,也有学校歌曲;既有单旋律歌曲,也有四部合唱;既有少儿歌曲,也有艺术歌曲翻译歌曲,可惜的是,这些作品大多未能刊印于世。
在沈阳八年,阎述诗最具影响的一项活动,是创作歌剧。这些歌剧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与心声,目前已知的作品有《高山流水》《梦里桃源》《疯人泪》《孤岛钟声》《忆江边》《风雨之夜》,都由他本人领导谐和音乐团在沈阳公演,但是,未能留下完整的剧本,这是无可弥补的损失。
《高山流水》是阎述诗的歌剧处女作。全剧取材古代琴师于伯牙欣遇知音钟子期的传说,意在再现华夏古国音乐之盛况和人才之辈出。《梦里桃源》描写一青年愤懑于“吃人肉,喝人血”的反动统治,向往平等自由和平幸福的“世外桃源”。阎述诗主演青年寄萍,终场时舞台上彩绸飞舞,鲜花朵朵。大合唱“桃源在人间”频频而起,激励人们去创造“人间桃源”。翌年又再次重演,其余各剧,主题也皆“针砭社会,讽刺社会”,指导人生,锋芒指向反动统治者。
1934年夏,日本天皇之弟秩文宫宣布出使沈阳。日本当局为了迎接这一“亲善睦邻”活动,强令各校举行欢迎演习仪式,并派人逐一检查。当同泽女中被“检查”时,一学生仅因弯腰不足,当场便被日本检查人一顿毒打。阎述诗目睹学生遭此蹂躏,忍无可忍,勇敢地上前正告对方住手,不可用蛮横手段对待中国同胞!日方检查人无话可说悻悻而去。阎述诗却因此种下了祸根,被敌特列为监视对象。
这年秋天,阎述诗又创作了歌剧《风雨之夜》,领导谐和音乐团假沈阳东关礼堂公演。大幕拉开,天昏地暗,风雨交加,一群劳苦大众正在死亡线上拚命挣扎。阎述诗扮演主角登台,面对挣扎者大声高呼:“狂风暴雨自东来!”告诫人们:“风雨之夜”的祸首就是日本侵略者!激励人们奋起抗日,收复东北!正当场内观众群情激愤之时,场外敌特也在密谋行动,准备对阎述诗下毒手,幸被一挚友及时察觉,抢在终场前赶往后台传信,帮助阎述诗易服化装,随同观众一起散场。为了摆脱魔爪,阎述诗随即亡命北平,不久即到内迁于此的东北大学法学院任教。
1935年12月16日,北平万余学生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冲破国民党军警的包围,再次举行集会游行,队伍抵达菜市口,遭到武装军警镇压。一批批受伤者被送至东北大学。阎述诗带领学生收容伤员,他又和学生一道将重伤者转送至协和医院抢救。当他返回东大宿舍时,恰好东大文学院学生金肇野南下武汉归来,带回了光未然新作之独幕剧《阿银姑娘》和序歌《五月的鲜花》。金告诉他,《阿银姑娘》已被光未然领导的武汉拓荒剧团列入《国防三部曲》公演计划,只等序歌谱曲了!阎述诗慨然相许,他接过歌词,进入了配曲的创作。
阎述诗本人是从东北流亡到关内来的。他凭着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怀着满腔悲愤,在顷刻之间,就对歌词中说的“再也忍不住满腔的悲愤,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迸发出强烈的共鸣。随着感情的升华,他很快地构思好了“叹息———悲壮——怒吼——反抗”的音乐主题,选用主歌——间奏——主歌变化再现的三段体曲式,纵笔一挥而就,谱完了金曲。翌年5月,独幕剧《阿银姑娘》由拓荒剧团在武汉公演。《五月的鲜花》便作为救亡名曲,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荡于抗战救亡前哨。
1936年秋,在西安盛大的群众大会上,《五月的鲜花》被爱国青年热情传唱,迅速流传于西北广大军民之间。
1937年5月4日,北平新学联在北师大操场召开“五·四”运动扩大纪念会。会上,《五月的鲜花》被2000余大中学生同声高唱,歌声刚落,反动当局就派来暴徒手执木棒砖头,冲砸会场。
1937年5月30日,太原举行“五·卅”十二周年纪念大会。《五月的鲜花》又被3万余群众在集会游行时反复高唱。
作为救亡歌咏运动中心的上海,人们对它的推广宣传更是不遗余力。冼星海、张曙在群众大会上指挥教唱,极大地推动了这首歌的广泛传播。
上海有众多的歌咏团,如怒吼、正声、雏声歌咏团,自费刻印歌谱登报通知各界函索;
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举行赈灾歌咏大会,吕骥、孟波、麦新负责教唱的上海兆丰路第三女工夜校演唱《五月的鲜花》,荣获了冠军;
上海业余集团旅行社一行2000余人,分批分途抵达吴淞河边公园,整队高唱《五月的鲜花》,因遭“警官先生”严密监视,被迫令“预备好船只”提前离去;
上海19校学生在法租界亚蒙电影院举行赈灾游艺大会,未及开会,法国巡捕赶至剧场审查节目,因节目中有《五月的鲜花》,迫令大会停演。
面对国民党当局和租界当局的重重高压,《五月的鲜花》经过歌咏界的奋力推广、反复传唱,渐次深入到上海各阶层群众中去。至抗战前夜,它已跻身于上海抗日救亡歌咏第一线,当之无愧地与《义勇军进行曲》(聂耳曲)、《救国军歌》(冼星海曲)、《救亡进行曲》(孙慎曲)、《打回老家去》(任光曲)一起,成为上海群众最受欢迎的抗日救亡歌曲,在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
抗战爆发后,阎述诗寓居北平,甘愿放弃教鞭改业摄影,是为了避免为敌伪政权的奴化教育效劳。直到抗战胜利以后,他才重新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阎述诗长期在北京二十六中任教,默默无闻地献身于教育事业,为国家培育人才。1963年11月23日,终因积劳成疾,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他静听着肖邦的《葬礼进行曲》唱片,安然辞世。他的遗体被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上刻着挽联,概括了阎述诗一生的业绩:
“卅年辛苦育人才堪为师表,五月鲜花鼓斗志永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