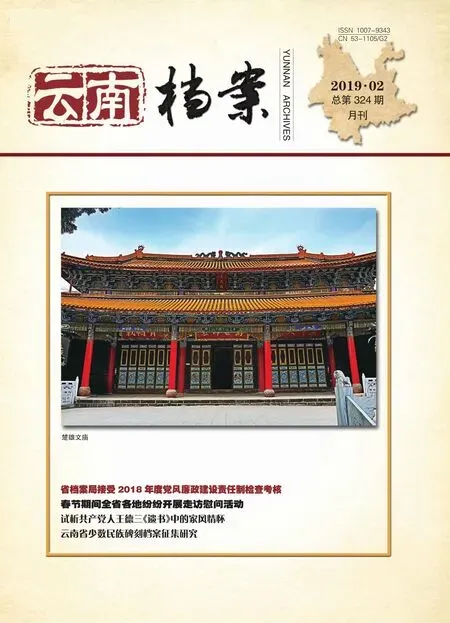故宫珍宝迁移记
2019-12-17王东梅
■ 王东梅
“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榆关的失守,华北门户洞开,古都北平已成为日军垂手可得的囊中之物。为了使我国数千年文明赖以维系的表征——珍藏于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处数以百万计的国宝免遭兵夺火燹之劫难,南京国民党政府从1933年春开始有计划地将这批文物南迁。从那时起,它们几乎是马不停蹄、席不暇暖,不断迁徙,直至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一部分精品被运到台湾为止。这期间,从1933年3月到1936年12月,这批古物曾辗转迁沪,在上海度过了近4年的光阴。
珍宝议迁
古物南迁之议,发端于1932年秋。当时,故宫博物院同人鉴于北平岌岌可危之局面,提出此议,并得到了国民政府行政院的核准。
对于珍宝南运,故宫博物院的同人中曾存在过意见分歧。这批古物多系明清两代帝王珍赏之物,藏之深宫,已有年数。自1925年10月起向外开放后,才得以一睹天日,深得社会公众及外国人士的拥趸。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正式颁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将该院直隶于国民政府,掌管包括清太庙、景山、皇史窚等处的文物、图书、档案的保管、开放及传布事宜。现在一下子要将这批难以数计的文物来个大迁徙,管理上的不便尚且不提,一旦路上有个差池,这个责任谁敢担当。何况古训道:神器不可乱。这批古物,多少具有象征意味,若是动辄迁徙,岂不落个不肖罪名。所以不少人都存观望或反对心理,只有院长易培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坚决主张南迁,以确保国宝免遭日寇之劫掠。
对此北平市民的心情是复杂的,这批被引以为豪的国宝既是北平的精华所在,也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却要迁移南方,其失落感是可想而知的。何况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北平早已成了座不设防城市,风声鹤唳,四面楚歌,此时若再度运走大批文物,影响人心太大了。在他们看来,政府方面可以放弃国土、遗弃人民,而惟独对这批文物感兴趣,这种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尽管文物南迁已是成命难收,北平市民在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于是大声疾呼,反对南迁,甚而有卧轨以示抗议者,颇有“与汝皆亡”之概。当时,凡是被指定参加南迁古物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接到匿名信和电话的,内容无非是攻讦威胁之词。由于有以上这层因素,所以每批文物的运迁,都被安排在半夜,从故宫到铁路西站间交通一律断绝,实行戒严。装车的当晚,全市的手拉平板车都被集中起来,运输车队见首不见尾,煞是壮观。
文物的选提,最费时光。原则上,南迁文物应是故宫中的精华部分,因为偌大一个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何啻百万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全数动迁,而文物的甄别鉴定最易见仁见智,意见无法统一,所以这项工作进行得很慢。当时,故宫中有古物、图书、文献3个馆,各馆下设许多陈列室。选提文物,原则上是先选陈列室中的展品,再选库房中的藏品。
从数量上来看,古物馆选提的文物最多,其中书画有9000余幅,瓷器7000多件,铜器、铜镜、铜印2600多件,玉器陈列室和库房所藏玉器被全部装箱。其他各展室因考虑到参观者的利益,尚保留一小部分艺术品,兼之故宫博物院正在编纂出版藏品集,有些珍品因制版需要得暂时保留下来,未随南迁,如唐代韩滉的《文苑图》、清雍正款的《珐琅彩锦鸡牡丹碗》等等,所以古物南迁后故宫尚能维持正常开放的局面。
文献馆藏品南迁的数量仅次于古物馆,达3773箱,它囊括了皇史宬及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和明清两代帝王的实录、起居注等,还有有关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的档案史料,其中内阁大库档案红本从乾隆五年到光绪廿四年连贯不缺,弥足珍贵。
图书馆所迁藏品有四库全书、各种善本书、刻本,虽然数量未及千数,均系不可多得的珍本,如雷峰塔倒塌后发现的五代刻本《陀罗尼经》,为公元975年所刊,是当时国内所发现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三馆文物选提后,故宫博物院秘书处还将各展室、库房重新查看一追,再度选提一批南迁。所以故宫南迁文物被分别标有4个部门的标记。
装运文物的木箱,除了一部分是故宫内钟粹宫、斋宫的(装运书画)和少数专装香烟的外(装文献、档案),绝大部分都是临时赶制出来的,长3尺,宽高各1尺半,文物装箱后,即用铁钉钉牢,封条。为确保一些瓷器、玉器、铜器之类易碎物品不受损伤,故宫古物馆同人还聘琉璃厂的古玩商人传授包装技巧,可谓慎之又慎。
辗转迁沪
1933年2月7日起,故宫文物开始分批南迁。第一批文物共计2118箱,由北平卫戍警备司令部派宪兵1连押运,故宫博物院秘书吴瀛随车南下,沿路均由地方军队派马队随列车驰骋。为了防止沿路日本人、土匪、韩复榘军队的骚扰和截留危险,列车舍近取近,取道京汉线到郑州,再破道陇海线到徐州,兜了半圈后再转京沪线,9日抵达京畿浦口,一切还算顺利。不想因为迁移地点延宕未决,在浦口车站耽搁了近一个月。押运古物的人戏称为“抬着棺材找坟地”。
且说当初故宫博物院在议决南迁时,通过了6万元迁移费预算案。文献馆长张继提出文献馆由他主持迁往陪都西安,迁移费1/3归他支配。此议后被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所否决,决定古物全部迁移上海。就在第一批古物南迁的日子里,身兼司法院副院长的张继趁宋子文逗留上海之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重提旧议,诡称托庇租界是耻辱,胁迫众人通过了分运洛阳、西安的议案。当然,此举无非是想从中渔利而已,所以连具体保藏地点都没有落实。后来,蒋介石提出将文献馆物品留存南京,宋子文又临时召集了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古物仍旧迁沪,张继的这一分润计划才未能得逞。而这么一拖,就是个把月,第一批文物只能在车厢中坐待,不得卸装。
到了3月3日,第一批故宫文物才分批运过长江,其中一半暂时寄存行政院大礼堂,后改储中央医院新厦,另一部分雇请上海招商局的江靖轮于4日下午先期运沪。5日中午船抵外滩金利源码头。从午后开始,这批文物由茂泰洋行(以后各批均由此洋行承办)的运输车辆陆续运到法租界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26号库房(位于天主教堂对面,今废)。一路上,法租界出动大批巡捕密切配合中方行动,进展甚快。
第一批抵沪文物,主要是文献、书画。有档案红本、四库全书等,特别是被乾隆帝奉为“三希”之一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最为引人注目。这批文物停藏的天主堂街26号,系一幢6层楼房,原来是仁济医院,已废置多时。行政院在议决故宫文物迁沪后,即以月租金3750两白银的价格择定了这幢楼房,并进行了加固维修,四周窗扉均装置了铁丝网,楼房四周竖以路障、围以铁丝,市公安局特派侦缉员多名与法租界一起把守。
继第1批文物平安南迁后,以后4批文物先后于3月21日、4月5日、4月27日、5月22日由招商局的快利、江天、建国、广利轮分别运抵上海,第1批暂存南京的古物也随第二批一齐运到。5批文物共计19557箱,达25万件之巨,其中故宫占7/10,其他则为北平各机关所收藏,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各种考古文物 (如甲骨文、陶器)70箱、颐和园藏品640箱、国子监11箱等。其中尤以内政部古物陈列所藏品最为众多,达5415箱。该所设于故宫的文华、武英、太和、中和、保和5大殿,所藏主要是热河,沈阳两地清代皇宫的物品。
国子监南迁文物是10只石鼓。这大概是这批古物中最为笨重的了。这组石鼓是中国最古的石刻。10块高度和直径约为2尺、重逾千斤的巨石上,分别以籀文刻有10首四言诗,记载着战国时期秦国公(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陪伴周天子游猜的情景。
石鼓最先被遗弃于陕西陈仓之野,故称“陈仓十碣”;又因其地在岐山之阳,也称“岐阳石鼓”。过了千余年,至唐代初年才被人发现,宋时迁至凤翔府学,宋徽宗大观年间又迁至汴京开封。为防止风蚀,特以金粉填没其字。金兵南下,将其掳至北京,又剔除金粉,置于大兴府学。入元以后才迁至国子监。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文字残损极为严重,其中一鼓已难见字迹。尽管这样,以其特有的文物、史料价值而为世人所重。这次南迁古物时,经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马衡等的大力鼓吹,才促成了这批石鼓再度举迁。
当时,这批石鼓已风蚀得相当厉害,用手一摸,就会有石灰粉末剥落下来。所以在装箱搬迁时,特别小心,特地用高丽纸把石鼓糊得严严实实,再裹以棉絮,装箱则聘请古玩商号达古斋经手。
第5批南迁古物中,本来拟议有北海团域玉佛,后因实在太重,经反复权衡后才决定不予南迁。随着5批古物的陆续抵沪,顾来天主堂街的库房已显得不敷使用了。所以第5批古物的绝大部分,被另外存放于由中央银行租赁的公共租界四川路(今四川中路)32号库栈的二楼库房(今元芳弄口北侧)其中主要是档案、图书。
盗宝要案
在故宫文物分批南迁的日子里,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故宫盗宝案”。这件事情在当时可说是沸沸扬扬,扑朔迷离。弄到最后,堂堂的故宫博物院长易培基不但丢了乌纱帽,且成为国民政府的通缉对象,最后只能隐居于津、沪租界以了余生。
却说故宫博物院自从成立后,因政府方面所拨经费有限,早在1927年中,即报请拍卖所藏金砂、银锭、食品(主要是药材、茶叶、火腿等),以维持浩大的支出。1929年10月,《故宫周刊》发行,以后又陆续有不少刊物、画册问世,故宫经费更为拮据,于是估价出售的物品渐渐放宽至绸缎、皮货。这批货物除了一部分供给军政要员、外国友好人士外,主要由故宫同人内部分割,尤以院长易培基及其女婿李宗侗秘书长等为大宗。照理是近水楼台,也属无可厚非,局外人也是知道的。
不想,在1933年5月1日,也就是最后一批古物南运的前夕,突有最高法院检查官朱树森到故宫调查拍卖处分货物的账目,结果查出有数百元有涂改之迹,并指责易培基、李宗侗等趁非公卖日(星期日)购卖皮货,言外之意有舞弊之嫌,当即立案侦讯。故宫同人开始以为是清朝遗老余孽从中作梗,寻衅阻挠古物南运,于是二位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以故宫博物院理事身份上书蒋介石及行政院长汪精卫,指责朱树森以天津高等法院介绍参观函来院,而到院以后,调查文卷、账目,携带法警,传集本院职员,临时开庭侦讯,声称“奉有密令,不肯宣示案由”,要求迅速制止这种非法行径。
事后,故宫同人从截获的电报中才得知,这件事的主持者乃是最高法院检察署长郑烈,而其幕后主使竟为故宫文献馆长张继及其夫人崔振华。造成易培基与张继之间的这种摩擦倾轧,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个人的恩怨和猜忌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内部的派系之争。这些就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的了。且说当易培基得悉此情后,极为愤慨,即诉诸舆论,分别上书中央临察委员会和行政院、司法行政部,指控张继、崔振华勾结郑烈等陷害忠良,要求将郑烈、朱树森解职。但由于缺乏有力的奥援,力量的天平已明显偏向张继一方。
10月15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开会,张继胁迫易培基引昝辞职。并另推马衡为院长。不几日,易培基在办完移交手续后,即打点行装,避居上海,一面养病,一面上诉。他已倍感胜诉的希望极其渺茫,同人们“皆以不揭黑幕,则事不可白;揭之,而张继为党国要人,未免难堪,且暴露司法独立之黑暗,防外人腾笑”,有个投鼠忌器的问题。而新闻媒介对此案的介入,又使司法当局成了骑虎难下之势。于是,易培基“在劫难脱”,本来是一桩微不足道的案子被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最后终于衍变成“故宫盗宝案”。
马衡继任院长后,奉江宁地方法院之命对沪故宫文物进行清点,先是聘请珠宝商对珠宝、玉器开箱检查甄别,继又延聘艺术家黄宾虹对书画、铜器部分进行鉴定,辨其真膺,以作为治易培基等罪的铁证。鉴定人员往返于北平、上海二地,经过一年的忙碌,初战告捷。1934年10月13日,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官孙伟正式提出公诉,被告为易培基、李宗侗等9人,罪由是他们自1929年以来,陆续将保管之珠宝部分盗取珍珠1319粒、宝石526颗,以假珍珠调换真珍珠9606颗,以假宝石调换真宝石3251颗,其余将原件内拆去珠宝配件计1496处。此外尚有将缉末珠流苏及翠花嵌珠宝手镯等类整件盗取,为数甚巨,均一律占为已有,并有妨害公务、毁人名誉之罪。一时间,罗网织就。
不难看出,这份起诉书是以鉴定商所得出的结论为依据的,而古物鉴定的随意性是很大的,再则招呼在前,有了先入之见,这就难保不出岔子了。如黄宾虹这位艺林巨匠,在鉴定存沪的故宫书画时,就曾误把真品南宋马麟的《层叠冰绡图》定为赝品。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批文物的清查,是以当初清室善后委员会移交的清单为凭的,当年由于时间仓促,只草草作了点查,而清宫内真膺混杂、监守自盗的情况是一向存在的。所以严格来说,以此为据并不能说明问题。退一步讲,这些调查结果是在易培基辞职办理移交手续后作出的,按理易培基完全可以不负其责。何况从法理上讲,捉贼拿赃,起诉书所称情形并无实据,易培基等最多只能属失职罪处分,哪里谈得上“侵占”、“盗取”之名,显然是欲加之罪,有失公理了。
易培基遭此一击,自知已回天乏术,无心恋栈,索兴隐匿于津、沪租界,闭户养病,冀希“使神州不陆沉,藐躬无恙,自信终有昭雪之一日也”。司法当局也深知穷寇莫追,目的既已达到,也就无所谓了。只有故宫博物院理事,3位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李右曾、吴稚晖颇为易培基打抱不平,专程西行,找蒋介石申诉评理,终因军事倥偬而并无下文。
1937年9月,易培基含冤病逝于上海法租界。司法当局并没有就此罢休,还要打一下这只“死老虎”。9月底,首都地方法院检察官起诉书发表,文中再次指控易培基等利用公务之便侵占古物,“计被侵占书画五百九十四号、古铜器二百十八号、铜佛一百零一尊、玉佛一尊”。这时候,距离易培基辞去故宫院长之职已近4年。
1947年底,张继暴卒。靠山既倒之日,正是易培基昭雪之时。不久,司法当局即对此案作出了不受理和免诉的决定。所谓轰动一时的“故宫盗宝案”,就这样在拖延了十几年后才算草草了结了。
故宫盗宝案,可说是故宫文物南运过程中一个不小的插曲。那么,南迁文物在上海的命运究竟如何呢?
“沪上寓公”
5批文物全部迁沪后,故宫博物院即在上海法租界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上赁屋成立了驻沪办事处,负责各种文物的造帐入册。院长马衡还指令将故宫4个部门的文物重新编号,古物馆为“沪”字号,图书馆为“上”字号,文献馆为“寓”字号,秘书处为“公”字号,连起来读,就是“沪上寓公”,颇有点苦中寻乐的意味。
当初,南迁古物因时间仓促未及仔细登记,只记品名和件数,极易造成疏忽差错,自从全部迁沪后,故宫同人即着手对每件文物进行详细登记造册。包括质地、色彩、尺寸、题款等。凡属纸质文物,均加盖“教育部点验之章”,折扇则在扇骨上贴上盖有监盘委员舒楚石名章(舒光宝)的小纸条。这也是吸取易培基案的教训而为。这项工作过去在北平也没有做过,因为那里的文物实在是太浩繁了,若是一件件过目,不知要做到猴年马月。仅仅故宫文献馆迁沪文物的点收盘验,就进行了近1年之久。这批文物经仔细登记后,编印成《存沪文物点收清册》。
存沪文物的2处库房,都戒备得异常森严,非故宫驻沪办事处的人员都不得进入。库房的每扇大门都装了2把锁,钥匙分别由故宫博物院同人及行政院所委托的中央银行保管。天主堂街库房的一楼办公室和第5层库房,分别装有警铃设备,直通法租界巡捕房。职员们如若开门,先要到旁边小屋把警铃线路切断,方能开锁,否则就会惊动法租界的巡捕。四川路的库栈也加设了警铃设备,每天有公共租界当局派驻二三个巡捕轮流站岗。库房大门并挂有一只象钟一样的玩艺,每过半小时须上一次弦,否则就会显示出红字来,稽察人员就可知道该巡捕擅离岗位了。一切安排可说是天衣无缝。从1933年9月起,故宫博物院还联合中央研究院、上海市政府、上海地方法院的有关人员成立监察委员会,随时随地负责抽查文物的保管情况。这期间,文献馆藏品清太宗实录初纂本曾被调至北平,由故宫博物院参照乾隆年间的重修本校勘,由大东书局摄制出版。随同一齐北运的还有舆图多幅。
故宫文物迁沪后,上海市民极度关切这些古物的命运,曾多次呼吁举办展览陈列,政府方面也有意进行公开展览,终因种种原因久未遂愿。直到1934年底,这件善事才初见端倪。
话说英国皇家美术学院从1927年起,几乎每年都举办一次国际性的艺术展览会,从各国公私藏家征集有关文物,以介绍各个国家的传统文化艺术。自举办以来,先后有芬兰、荷兰、意大利、波斯、法国及英联邦各国参展,引起国际上的广泛注目。自1934年举办完本国艺展后,几位英国的中国古物收藏家建议发起中国艺展,乃商诸中国驻英公使郭泰祺,希望下届主办国为中国,郭公使请示政府当局后,便应允了此事。
1934年10月,国内即成立了由国府要员、艺界名流组成的伦敦艺展筹备委员会,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主席,在筹委会召开的第2次会议上,决定在选展文物出国前先在上海举行预展会,将来伦敦艺展结束后再在南京展览一次,以取信于民。上海预展会的地址确定为外滩中国银行旧址。
本来这次英方发起人为民间人士,英政府无意加入。后经郭泰祺的反复动员,至年底才正式同意此请。于是中英双方联合组成了庞大的筹备阵容,赞助人为英王乔治五世、玛丽王后和中方国府主席林森。名誉会长为英首相鲍尔温、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和中方的蒋介石、汪精卫。名誉委员有各国驻英使节、瑞典王太子等。筹委会由英人李顿任主席,郭泰祺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分任副主席,委员由各国著名收藏家组成,成了名符其实的“超国界行动”。
选展文物,由筹委员会专设的审查委员会主持,征集物品原则上以故宫南迁文物为主,英方特派5名考古专家和收藏家来华负责终审。凡是选展文物一律摄成照片,一式3份,分别由行政院、藏品机关或个人及出国参展人员保存。参加文物选提的,多系富有经验的专家、学者,如徐悲鸿、叶恭绰、张昶云、马衡、唐兰等。
从1935年2月11日起,保存于上海的南迁古物陆续被提选出来。经过中英双方反复权衡,最后选定参加伦敦艺展的古物为1022件,其中有故宫735件、内政部古物陈列所47件、河南博物馆8件、安徽图书馆4件、北平图书馆50件、中央研究院113件,上海私人收藏家张乃骥也有65件玉器入选。
1935年4月8日晨,位于外滩的中国银行大楼旧址门前人头攒动,涌满了热望着的市民,门首一幅黄地绿字匾额格外引人注目,上书“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上海预展会”16个大字。从这天起,故宫南迁文物正式在上海公开展出曝光。
上海预展会的展品,共计10大类,按数量多寡依次为瓷器、书画、铜器、玉器、织绣、古籍、考古选例 (主要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品)、折扇、景泰蓝、漆器。预展会共设5个陈列室,分布于二层楼面。
展出的古物,上至商代,下迄清乾隆年间,时间跨度达3000多年,历代相沿,几无中断,足以代表我国古代文化艺术成就之一斑。以国画为例,其荦荦大端者,有唐李昭道的《洛阳楼阁图》、五代董源的《龙宿郊民图》(应作《龙袖骄民图》)、宋郭熙的《关山春雪图》、夏珪《长江万里图卷》、元倪瓒的《容膝斋图》、明沈周的《庐山高图》、董其昌《夏木垂阴图》、清高其佩的指画《庐山瀑布图》、石涛、王原祁合作的《兰竹图》,等等。
以前,我国古文物虽然在故宫等处陈列多年,但毫无系统,瑕瑜互见、散漫凌乱,不利于欣赏、研究。正如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常委膝固所称的那样:往往类同杂货摊,不能予人以明晰舒畅之感,“此次展览,陈列技术远胜于前,各地博物馆即应取法”,筹委会秘书唐惜芬亦称“我国集各代文化艺术之结晶公开展览,本会实其滥觞”。
故宫珍宝在上海的公开展示,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震荡,各种中西报刊、电台纷纷连续报道此次展会的盛况,艺界人士也撰文、讲演,盛赞古代文化之灿烂多姿和陈列技术之先进。著名记者曹聚仁在看到北平图书馆藏品明刻本《十竹斋画谱》和清刻本《耕织图》等后,大发感慨:“我们处在这粗制滥造的海派工艺圈子,看见了这手工业时代的精品,不禁有古今人不相及之叹!”
早在开幕前一日,汪精卫、于右任、孙科、戴季陶、孔祥熙等党政要人已麇集上海,一方面是先睹为快,另一方面是表示我国对这次伦敦艺展的重视。从正式开放以后,可以说每天都有闻人要员涉足浏览,至于艺界人士更是倾巢出动,展室每天都是人头攒动,观者只能随人流而动,无法一一仔细观赏。本市及各地的学校机关和艺术团体也纷纷组团参观。筹委会发售的中英文展品目录,更是一再加印,供不应求。最后,原定4月30日结束的上海预展会不得不延至5月5日落幕。
虽然这批展品集中了我国古代艺术的最高成就,但也还是有不少精品未能入选,如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这里既有安全保险方面的因素,也有中西审美异趣方面的原因。就后者而言,我方当时选中的不少参展作品被英方所否定,如元赵原的《陆羽烹茶图》、明仇英的《蕉阴结夏图》等。而英方所提出的增加内容,如考古选例等,又不为中方所欣赏。最后,还是由我方一一作了妥协。如清郎士宁的画,我方考虑到郎系西人,不足以代表我国文化,后屈从了英方的意见,增加了郎士宁的《女子采莲图》《拉萨克贡马图》。展品中体积最大的一组乾隆帝御用家具、文具,也是应英方的一再要求而添设的,原先上海预展会也不准备将其列入,后由于各方呼吁,才临时在预展会上专辟宝座文房陈列室陈列。这批御用器物共19件,家具中有一红木画案,四周刻绘有清人刘墉、翁方纲、金农、郑燮等名家书画;龙椅是紫檀木镶景泰蓝,附有描金漆脚踏。文具中有一件黄杨木雕臂搁,刻有董其昌的书迹。都是难得一见的宝物,引起了观众浓厚的兴趣。
从英方选展文物的倾向来看,偏重于帝王所赏之物,凡是有乾隆帝御印、御笔的字画,都在入选之列。实际上这并不能抬高这些文物的身价。
乾隆帝虽然精通书画,喜好附弄风雅,实质上他的鉴赏力也是很成问题的。就以这批南迁古物为例,石鼓系何时之物,现在虽然已有定论(系战国秦献王时物),但历史上向无定说,唐人张怀瓘、韩愈等主张为用宣王时物,是最早的一种说法,附会者甚众,乾隆帝也力排众议,钦定此说为一尊,并一手遮天,把其他各说打入了冷宫。更有甚者,他甚至不辨真假,把赝品当作真迹。这次被选中参展的一幅《富春山居图》,就是典型的一例。
这幅近12米长卷,系元代画家黄公望率意经营3年始成的代表作,被画界奉为至宝。历史上流传有绪,入明以后,由沈周而董其昌而吴正志(宜兴收藏家),吴再传子吴之矩。吴之矩嗜之如命,临死前要以此卷相殉,结果焚未及半,被他的侄子吴静庵从火炉中抢了出来,幸只烧去了起首一段,尚无大碍。以后,这幅真迹散落市廛,乾隆十一年被卖入清廷内府。当时清宫内已有同名的一幅《富春山居图》(系后人所摹),那批御用文人们对哪幅是真、哪幅是伪莫衷一是,最后请出乾隆帝裁定。乾隆帝反复对照赏玩后,结果将摹本断为真迹,残卷反定为摹本,并在摹本上面密密麻麻地题满了诗文,而真迹反而一字不题,被打入了冷宫。直到以后,残卷的前段流入民间后,这个冤枉官司才告翻案,大白于天下(现残卷前段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及摹本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虽然有以上这段曲直是非,英方选展人员还是把乾隆帝题满诗文的那幅摹本选中参展。在他们看来,乾隆帝的感召力是绝对的,兴师动众把乾隆一整套御用器物悉数列入选品,更是证明了这一点。人们可以联想起近代西方第一位出使中国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谒见乾隆帝时的情景,真有沧海桑田之感。当年清帝国尚处于鼎盛时期,乾隆帝根本不把那个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国度放在眼里,竟要这位使节行臣下跪拜之礼,后几经交涉,才行了单腿跪拜之礼。乾隆帝虽挽回了点面子,英使节却丢人现眼,被作为一则笑料而存史。而今,英方不计前嫌,慧眼独钟,这是很有用心的。可以想象当英伦观众看到那只乾隆帝坐的龙椅,遐想起当日马戛尔尼谒见这位皇帝时的窘态,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心态呢?
伦敦艺展
1935年6月初,上海预展会的展品共93箱国宝被陆续运上英国巡洋舰萨福克号。这艘军舰隶属英国海军亚洲舰队,载重量近万吨,长700余呎,有各种口径大炮12尊,并有直升飞机、鱼雷等装置,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特派唐惜分、庄尚严随舰押运。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锡作为我国政府特派员莅展。
7日晨,萨福克号满载珍宝从杨树浦招商局码头启碇,开始长达1个多月的海上旅程。7月25日,船抵英伦朴次茅斯军港,古物随即被汽车运往伦敦。
伦敦艺展从1935年11月28日开幕,到1936年3月7日结束,共14周。展会共陈列选品达3080件之多,是历次外国艺展中内容最丰富的一次。其中我国原选展1022件,在伦敦临时被筛去165件,计陈列857件,占陈列总数的35%。其他参展的中国文物分别来自17个国家的个人和机关团体的收藏,著名的有英皇宫白金汉宫的收藏品,如慈禧太后当年赠送给英国皇太后的三代古物铜觚等。
展览会设于伦敦皇家美术学院所在地伯令敦大厦,这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从19世纪中叶以来,曾接待了历次大规模的国际艺术展览会。
伦敦艺展陈列室计有10大室,展品以瓷器、书画居多,时代上溯夏商,下迄公元1800年。外国选展的古物,大多系从中国盗卖出去,不乏上品佳构。如展品中最大的隋代弥陀佛石像,重20吨,高达20英尺,系1915年被盗卖至美国。昭陵六骏之一的著名“飒露紫”石像,也由费城大学博物馆运来参展。这些作品以铜器、玉器为精,其中出自当日来华劫掠文物的考古学者斯坦因、伯希和的收藏尤引人注目。我国参展的乾隆帝一套御用器具被陈列于一所临时搭建的清代房舍内,是所有展室中最大的,四壁杂陈丝绣书面之类,而宋太祖画像却居于醒目位置,令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
艺展期间,尽管适值英王乔治五世逝世,观众仍达42万,平均每天超过4000人,大大超过上海预展会的人数。伦敦整个城市沉浸于中国古代艺术的氛围中,随处可见各种中国传统图案,宋太祖像被制作成宣传画遍布街市店铺,大出风头,艺展会吸引了欧美各国中国文化的仰慕、拥趸者,大批渡海来观,如丹麦、挪戚国王。瑞典皇太子除了献出所藏参展外,是艺展的常客;英国的皇室、内阁更几乎是倾巢出动,无一错过机会。正如一位皇家美术学院的成员对艺展所发出的感叹那样:“此乃余所日夜求之者,余觉余已虚度此生矣!”英国艺界人士一致认为,这次展会对于该国美术意境的新补充大有影响。
英国朝野由这次艺展而掀起的中国文化热在不断升温,各报连篇累牍地介绍艺展盛况,英国艺术界人士围绕中国艺术品进行了20多次讲演,虽然收费入场,还是场场爆满。可以说,西方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较深层了解并引起浓厚兴趣,实发端于此次艺展会。如著名华裔学者蒋彝,就是在这次艺展期间,以讲课形式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及研究中国的社团发表对于中国艺术的见解,并由此在西方第一次用英文出版了《中国书法》等书,使中国传统艺术在西方得以登堂入室。他在解释《中国书法》一书的写作动因时,曾这样写道:“1935至1936年在伦敦举办展览会的成功,表明很多人都渴望探索和理解中国艺术的重要性”。这是很值得国人引以为荣的。
伦敦艺展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仅从收支一项来看,艺展共计支出各项费用近3万英镑,而各种收入达4.5万英镑,最后,伦敦皇家美术学院和中国政府各分享了9千英镑的赢利。
艺展结束后,我国参展古物陆续装箱,由于一时联系不到合适的运输舰艇,决定改派英国邮船监浦拉号载送,沿途仍由英国海军舰只分站护送,以示慎重。不想,半途中还是遇到了麻烦,差一点酿成船沉宝失之灾。
1936年4月9日夜,蓝浦拉号在暮色中驶离伦敦乔治五世港,踏上了归程。14日午后,船至直布罗陀海峡,在靠近法国本土的浅海抛锚稍歇,不想一夜狂风劲吹,邮船慢慢飘移,竟至陷入淤沙之中。等到第二天清晨,船上人员才发现船已搁浅,无法启动。此处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大家一时都慌了手脚。幸亏英国海军舰只及时赶到,把邮船渐渐拖入深海,直到16日晚才摆脱困境,重新启行。尽管这是段有惊无险的插曲,但却被法新社记者捕捉到后加以渲染,一时西欧各报纷纷转载。国内新闻界不明真相,如矮子看戏、隔靴搔痒,大凑热闹,甚而危言耸听,称这批珍宝本来就是作为抵押借款之物,是一去不回的,船的搁浅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云云。直到5月17日篮浦拉号平安抵沪以后,这些谣传才不攻自破。
古物迁京
参加伦敦艺展的古物运回上海后,曾从6月1日起在南京考试院明志楼举办了为期3周的汇报展览,展览会结束后再度迁沪。
话说故宫珍宝迁沪藏藏,不过是权宜之计,一则是托庇租界毕竟有损国家尊严;二则上海远非理想之地,治安状况之差且不论(就在1935年5月24日的《申报》上,赫然登载了《暗杀南斯拉夫国王凶手在沪被捕》的新闻),特别是土地卑湿,潮气很重,对档案、书画的保藏极为不利。如1933年夏秋之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曾将迁沪的大内档案运回北平。所以早在1933年夏,故宫博物院理事会曾通过了在南京兴建分院和保存库的动议,但由于具体地点一直未能确定,一拖就是一年多。直到1934年底的第四次常务理事会上,教育部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理事长王世杰才提议将朝天宫划归故宫,并得到了行政院的批准。1935年7月,教育部将其所辖朝天宫拨交故宫。
朝天宫位于南京水西门内,是一组宫殿式建筑群,已几经变迁。古时先是吴王夫差在这里设冶铸作坊,东晋时为宰相王导的花园,后改建为寺院。明初,朱元璋把这里作为他教导臣下练习朝贺礼节的场所,放取名朝天宫。曾有种传说,称明太祖实葬于此,孝陵则为疑冢。到了清代中期,李鸿章将此处改建为学宫,后作为江宁府学所在地。
朝天宫占地近140亩,地势高亢平旷,是建筑档案文物库房的好地方。故宫分院的3层库房,择定在明伦堂后。地点选定后,故宫博物院投出建筑经费60万元,于1936年1月中旬在京沪二地开标召选承造厂商,最后选定南京的六合营造厂为建筑承包商。整个工程从3月开工,8月竣工。11月,行政院正式命令所属故宫博物院,尽快把存沪文物全部移送南京新址。
从12月8日起,保藏于上海近4年之久的各类南迁文物分批装箱运京,教育部特派专员舒楚石等监督装运,仍由茂泰洋行承办运输,沿途由中西巡捕布岗严加保护。每隔3日,或子夜,或清晨,由麦根路(今秣陵路)货车站发放专列启运。到17日止,始告完罄。
1937年1月,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宣告成立,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也随之结束。
这里有必要把这批南迁文物以后的命运交待一下。
国宝迁移后不久,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京畿告危。从1937年8月起,这些珍宝中的绝大部分(近17000箱)陆续由水陆二路迁移到大后方。随着国土不断沦丧、战火不断深入,这批古物几乎一直是飘忽不定、落脚无根。水运一路(共7285箱)由汉口而重庆而宜宾而乐山,陆运一路(共7286箱)由宝鸡而汉中而成都而峨嵋,参加伦敦艺展的近百箱精品由长沙而贵阳而安顺而巴县,所幸虽几经播迁,包括陷京文物在内(约2000余箱)均无大的损失。
抗战胜利后,这批古物由各地集聚重庆,从1947年起分批运回北平、南京。1948年12月到1949年2月,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国事蜩螗的微妙局势下,各处当年南迁古物由故宫博物院牵头分3批迁运台湾,总计4486箱,其中故宫文物计2972箱,虽然数量仅占南迁总数的1/4,但精品已被搜罗殆尽,其中包括参加伦敦艺展的几十箱珍品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西周青铜器《散氏盘》等。书画、铜器、瓷器、图书选中的比例甚高,都在半数以上;惟档案文献方面遗珠甚多,仅占全数的1/15。运台文物后来都归属于1965年成立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又称中山博物院)。
走笔至此,不禁为这批珍宝的坎坷经历而扼腕。古人常言: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信哉此言!但愿这批曾经与上海有过那么一段缘份的国宝能够早日再睹天日,为海峡左岸同胞所欣赏、所揣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