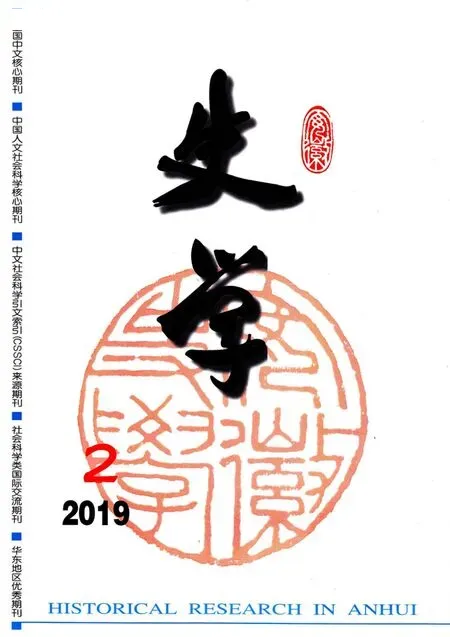抗战后惩治女汉奸的媒介话语解析
——以川岛芳子为中心
2019-12-17马晓驰
侯 杰 马晓驰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川岛芳子本名爱新觉罗·显玗。1913年,其父肃亲王善耆希望借助日本力量达到“匡复大清”的目的,将6岁的显玗过继给日本浪人川岛浪速。日本侵华时,川岛芳子先后参与策划和执行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满洲”独立运动和一二八事变,还在热河组织定国军骑兵团,自封护国军总司令。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国民政府在各地厉行肃奸运动。在中国公众看来,作为中国人,川岛芳子却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策划挑起事端,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川岛芳子就是汉奸的典型代表,应当严加惩治。
关于抗战汉奸问题的研究相当丰富[注]以下成果对相关研究做了分类概述,即:潘敏:《20世纪80年代以来惩治汉奸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徐志民:《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史学月刊》2015年第11期。,近年来,学者还将性别维度加入到对汉奸的研究,对川岛芳子等女性汉奸的生命历程、所涉忠奸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注]如陈雁在《性别与战争:上海 1932—194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中关注了“红色汉奸”关露和“误打汉奸”李青萍两位女性在中日战争中的命运沉浮。台湾学者罗久蓉在《她的审判:近代中国国族与性别意义下的忠奸之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第97册,2013年版)一书中,将川岛芳子等五位女性的跨越文化、国族界限的生命历程置于传统与现代的忠奸之辨脉络中加以检视,认为忠奸之辨是个体与群体在特定时空下通过互动而形成的特性,不应秉持“非黑即白”的判定标准。但综合来看,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舆论对女汉奸的态度。社会舆论对汉奸的态度,体现在其各类话语的建构、承载和传播上。而报刊媒体是建构、承载和传播话语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不仅将不同群体关于惩处汉奸的言论汇集起来,供读者进行选择性阅读以满足需求,而且还主动参与话语建构,不断表明自身的立场以发挥舆论效应、影响公众。在惩治汉奸的浪潮中,川岛芳子被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报刊媒体密集报道,成为备受公众瞩目的人物。[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8年川岛芳子被执行枪决,《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新闻报》等各类大小报纸、周刊、画报对川岛芳子的报道逾600篇。女性汉奸的惩治问题涉及性别因素,甚至与国族认同相纠缠,在报刊媒体的参与下,使得惩奸话语更加扑朔迷离。本文尝试以川岛芳子为中心,考察报刊媒体建构、承载和传播惩治女汉奸话语的方式,以丰富对女汉奸惩治问题的认知。
一、追求正义
汉奸一词的含义经历了复杂的动态演变过程,核心含义是投靠外国侵略者出卖本国或本民族利益的人。据多位学者考证,“汉奸”一词的含义至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超脱了汉族的范围,特指中华民族中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人。[注]相关研究参见李零:《汉奸的缘起和历史》,《读书》1995年第5期;林秋萍:《“汉奸”的词文解释与法律界定》,《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2期;黄兴涛:《抗战前后“民族英雄”问题的讨论与“汉奸”“华奸”之辩——以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影响为视角》,《人文杂志》2017年第8期;吴密:《“汉奸”考辩》,《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在抗战时期,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民族复兴意识的强化,国人既呼唤和赞颂奋勇御寇、勇于牺牲之民族英雄,更要惩治恶贯满盈的汉奸。抗战胜利后,随着侵略者的战败以及社会秩序的暂时稳定,特别是国民政府于1945年12月6日正式公布几经修改的《惩治汉奸条例》之后,大规模惩治汉奸成为可能。人们希望借由惩罚参与制造战争灾难的汉奸,重建正常的社会价值规范,从而令战时相对混乱的社会秩序在战后得到重整。因而,公众要求审判汉奸的呼声不断高涨,督促政府严惩汉奸的文字时时见诸报端,法院及司法部门也开展了对汉奸的审判和定罪工作。据1948年《中华年鉴》统计,从1944年11月至1947年10月,各省市法院及司法部门审判汉奸结案25155件,判处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注]中华年鉴社编:《中华年鉴1948》上册,中华年鉴社1948年版,第494页。
与此同时,报刊媒体掀起了法律之外的另一重舆论审判。其中,女性汉奸常常因其性别特征而备受瞩目,专门介绍、描写、演绎女汉奸经历的图书如《女汉奸脸谱》《女汉奸秽史》《女汉奸丑史》[注]《女汉奸脸谱》,光明出版社1945年版;《女汉奸丑史》,大公出版社1945年版;《女汉奸秽史》,大义出版社1945年版。等在各地畅销。单就川岛芳子而言,她长期因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受到报刊媒体的追踪。自20世纪30年代初进入读者视野至1945年10月被捕,报界已经对川岛芳子的行径进行披露,诸如《记川岛芳子——敌军主要间牒之一》[注]志文:《记川岛芳子——敌军主要间牒之一》,《同仇》1938年第5期,第8页。原文为“间牒”,应为“间谍”。《此亦“女杰”·川岛芳子由津到大连》[注]《此亦“女杰”·川岛芳子由津到大连》,《国防论坛》1934年第2卷第9期,第10页。《川岛芳子间谍工作忙碌》[注]《川岛芳子间谍工作忙碌》,《国防论坛》1934年第2卷第7期,第24页。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这一时段内相关报道有200余篇,其中既有专题叙述,也有花边新闻。经过演绎和传播,“生长于豪华家庭、受过武士道的训练、送给蒙王当妃子、手下爪牙四百人、舞女与王将军、情人满天下”[注]张居生:《名闻世界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秘史》,《联合画报》1946年第181—182期,第12页。等经历成为媒体对她的叙述重点和她特有的身份标签。1938年广东纪念九一八事变巡游中,组织者通过化装的方式来丑化和束缚川岛芳子的身体,藉此发泄仇恨、表达爱国之情。《女汉奸脸谱》一书作者将川岛芳子列入其中,甚至以“女妖”称之。[注]光明出版社编:《女汉奸脸谱》,第2页。凡此种种,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川岛芳子的认知。
被捕之后,川岛芳子被辗转押解,最后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媒体记者闻讯,纷纷寻找渠道赴监狱采访。记者将川岛芳子视作审视的对象,竞相窥探其狱中生活,仔细描绘她所处的环境和一举一动,满足着读者的偷窥欲。南京《中央日报》对川岛芳子狱中生活的这篇报道,用颇为暧昧的语词,建构了川岛芳子的公众形象。“这位奢华淫逸的人妖,将要在这四面徒然的拘留所内,度过寂寥的春天……川岛芳子仿佛获得了军官的心事似的,远远看来一种阴森的美。”[注]祝修誉:《川岛芳子的春天》,《中央日报》1947年2月25日,第4版。其中,“人妖”一词不仅描述了她雌雄莫辩的本性,也显现出其僭越社会道德底限的事实。记者形容川岛芳子有“一种阴森的美”,意在凸显其行踪诡秘、喜怒无常等特点之同时展现其凶残可怖的一面,即便是被囚禁在四面徒壁的拘留所内依然令人不寒而栗。
媒体还将她与一战中与其作用相似、手段相同的女间谍玛塔·哈丽对比。[注]玛塔·哈丽(Mata Hari):荷兰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红遍巴黎的舞女,更是一位周旋在法、德两国之间的美女双料间谍。1917年,她以叛国罪被处死在巴黎郊外。人们关注她们的容貌,但倾向于美化后者的形象,赞赏其“姿色倾城、雍容华贵”,而对川岛芳子的描述则是“口音嗓音若破竹,令人思及黑夜啼鸱,不寒而栗,走路姿势活像日人,口镶金牙,卷烟刻不离手。芳子有怪癖,好啃肉骨头,及炸雀等坚韧之物,撕咬为乐”。[注]春波:《川岛芳子的怪癖》,《国际新闻画报》1946年第61期,第1页。这种介乎事实描述和主观想象、判断之间的文字表达,对于读者来说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不仅能够满足他们想越过监狱的高墙一探川岛芳子真容的愿望,而且比艰深晦涩的法律条文更能够坐实她汉奸的罪名,舆论的参与对川岛芳子的审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媒体也通过描写川岛芳子对他人的欺压展现其作为汉奸的罪恶。因川岛芳子常延请梨园人士赴家中唱戏,其中不乏李万春、马连良等名角。在惩治汉奸的浪潮中,公众的愤怒聚焦于与她有干系的人。1945年,李万春在川岛芳子被捕后不久以通敌罪被捕[注]何基:《艺坛漫画(四)》,《吉普》1946年第21期,第6页。,马连良也因同样原因被揭发检举。[注]参见令人:《继李万春之后:马连良亦被检举!》,《文饭》1946年第1期,第7页。1946年3月15日,李万春受到了“徒刑二年半,褫夺公权二年,其个人及家属生活费用外,财产全部充公”[注]冰尼:《这是当汉奸的下场头,奸伶李万春反串“起解”!》,《京沪报》1946年第4期,第5页。的刑罚。
事实上,李万春的汉奸形象与媒体塑造不无关系。1935年,川岛芳子安国军总司令的职位被日军撤销后寓居北平,但她依仗人脉与北平的宪兵队及警察局有密切的沟通,也就因此间接掌握了大批梨园人士的生活来源。这是因为戏曲名角虽然广受社会欢迎,但社会地位低下,演出活动常常受阻,有人还被日本宪兵队拘留。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有川岛芳子能够依仗她的“金司令”名号和丰富的人脉关系加以营救。如此一来,一批伶人不得不投在其门下、认其为保护伞,“一般畸形社会中人,尤视金司令若神明若山岳,得其一顾一盼,引为无上荣幸”。[注]虎腰:《李万春与川岛芳子的浪漫史 把臂过市恬不为怪》,《海燕》(上海)1946年第1期,第3页。但尽管如此,媒体对李万春等人屈从于川岛芳子的原因选择了直接忽略,而是选择性、戏谑性地认为是他罪有应得。北京街头曾存在一种名为“抽汉奸”的幼儿游戏,李万春被视作“戏界汉奸”被抽打[注]《抽汉奸李万春》,《一九四七画报》1946年第3卷第1期,第12页。,可见“李是汉奸”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为共识,而极少有人调查具体事实或思考背后原因。然而,这也成为北平高等法院为李万春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
在公众看来,李万春的下场表明与恶女人川岛芳子交往的人难逃汉奸嫌疑,为法律和社会所不容。故而川岛芳子入狱后,无人探监,难以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她昔日的威风荡然无存,探监送饭的人一个人也没有”[注]平车:《川岛芳子:金璧辉坐牢遇见仇人》,《沪光》1946年革新第2期,第8页。,“每天仅仅吃她自己的那份‘囚粮’——即玉米面做成的窝头”[注]鹓:《川岛芳子案有新发展》,《新上海》1948年第46期,第4页。,“将窝窝头掷入便桶,一会又从便桶里拿出来”。[注]一知:《川岛芳子不安于狱》,《海潮周报》1947年第42期,第6页。就此事而言,部分媒体感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落脚点是强调她祸国殃民、罪有应得,体现出对正义的追求。
二、转换性别
川岛芳子少女时代,曾遭日本养父的强奸。这不仅令她产生自我厌恶的心理,而且强化了她对性别身份的自卑感。于是,川岛芳子采取一系列告别女性身份的戏剧性举动,她在日记中表明:“切记!十月十六日晚上九时四十分——是我与‘女’清算之时。”[注]川島芳子:《動乱の蔭に~私の半生記》,时代社1940年版,第71页。1924年,也就是“清算”之后的两年,川岛芳子开始剪掉头发、穿男装。
在参与日本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川岛芳子不停地穿梭于男女之间,进行着性别表演。她一方面利用自己爱新觉罗家族成员的特殊身份,到天津日租界末代皇帝的居所,将婉容接到东北,为溥仪“复辟”效力。同时,将女间谍“色诱”的传统继承下来并不断推向极致,通过出卖色相换取重要情报。另一方面,她也借助男性角色的扮演,行使和扩张权力,在成就感、荣誉感中陶醉,不能自拔。川岛芳子在男女性别之间的转换,成为报刊媒体关注的重点,主要表现是围绕她的性别特征展开了讨论。这其中不仅蕴含着对正义的追求,更体现鲜明的性别立场。
模拟男性身份还是她对周遭人士特别是男性进行性别压迫的有效工具。川岛芳子被捕之前,媒体对她的性别叙事限于其投敌、利用美色勾引军政要员。据20世纪30年代的报刊媒体披露:“留沪二月余,(川岛芳子)曾因密探工作而数度化装,充任舞女,改换男装,于日军攻闸北时赖伊之先侦之地形及我方军事布置……及至日军侵热,伊复北来工作,奔驰于长城一线。”[注]丽君:《川岛芳子:日政府的著名女密探》,《玲珑》1934年第4卷第9期,第527页。因而,文本书写者将其视作预防对象,号召其他男性不为其色所动,以使川岛芳子无计可施。“她所利用的手腕既然是她的色相,只要我们抱定宗旨,不为色迷,不为情动,那就怕一百个川岛芳子,会能刺探什么。”同样,被女汉奸利用的男性,则更为世人不齿,“被这为虎作伥的无耻的淫荡妇人所利用,那又是无耻中最无耻之徒”。[注]陈干华:《谈谈“川岛芳子”》,《服劳》1937年第1卷第3期,第12页。
被捕之后,媒体则连篇累牍地描述了一个强势、淫荡、逼迫男性满足其情欲的川岛芳子。在京、津一带蛰伏期间,川岛芳子曾供养多位面首,并借“做寿”之机大行敲诈。川岛芳子的面首也借助于她通过模拟男性而构筑的“权威”,压迫身边的无辜民众。“川岛面首虽多,而要算他最为得宠,后来一般人都喊他李爷爷。”[注]人人:《川岛芳子的第一号面首小白脸李春在青岛被捕》,《上海特写》1946年第20期,第1页。“芳子是野心勃勃的人,岂甘为六十老翁之玩物,所以她从此以后,也就人尽可夫,见男子就拉,以满足其性欲。”[注]《判处死刑的川岛芳子》,《大地》1947年第81期,第1页。“川岛芳子可称得上一代淫娃,她尤胜过潘金莲,到处吸引着她喜欢的男性,在她的诱惑之下,没有一个不成为她的入幕之宾。”[注]叶:《川岛芳子的一生》,《美光》1947年第1期,第1页。在以男性权力主导媒体立场的现实情境下,川岛芳子之恶在于她对传统妇德的僭越,在于对男性强势地位的颠覆。当然,对于私密的家庭生活,报界不可能全程跟踪观察,因而不能排除细致入微的描写是媒体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进行的杜撰。
描写其与李万春等伶人交往的情景时,媒体有意回避了李万春是迫于生计才与其交往的事实,批判李对川岛芳子女性强权的屈服,以彰显川岛芳子对社会性别秩序的僭越。一方面强调李万春是川岛芳子的义子,在身体及地位上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如“李万春克尽人子之礼,与川岛芳子出街”[注]虎腰:《李万春与川岛芳子的浪漫史 把臂过市恬不为怪》,第3页。,另一方面,媒体报道使李万春与川岛芳子的亲密关系成为公共话题,如“她跟名伶李万春所制造的桃色事件早已脍炙人口”。[注]九大山人:《川岛芳子的怪瘾》,《海星》(上海)1946年第20期,第4页。在男性叙事者眼中,川岛芳子“恶女人”的形象,也被纳入家庭生活的叙事体系之中,但被赋予谋夫、欺夫、御夫的共性。“像我这样的人,要是为了‘日满亲善’或什么有意义的事,那么对方即使是一个大傻子,也是要去结婚的。”[注]虎腰:《李万春与川岛芳子的浪漫史 把臂过市恬不为怪》,第3页。在评论者看来,川岛芳子选择婚姻对象,只是借助男性得到不正当的侵略利益,为人所不齿。
在媒体报道中,川岛芳子不仅通过控制男性满足欲望,而且还通过控制女性实现政治目的。从事
间谍工作时,她曾统领三组容貌美丽的女子作为情报下线,这成为媒体进行性别批判的来源[注]《“三个叛逆的女性”:金璧辉、石应华与川岛芳子》,《北方公论》1934年第76期,第11页。,也是凸显川岛芳子性别怪癖的依据之一,“听说她有个荒淫爱癖,即是颇爱同性,有男子也不能满足,所以她身边颇多娇艳少女,供她驱使”。[注]老道:《淋巴腺炎复发苦痛不堪,川岛芳子狱中发脾气》,《星光》1946年新第19期,第1页。川岛芳子驱使男性和女性,既对男性权力形成威胁,又在女性内部形成阶层和权力上的压制关系,在凸显丑恶的同时,一方面意在凸显她性取向上的异常,另一方面也是在影射她的性别越界。
性别装束的变化,往往代表着女性不同的情感寄托,也常常因为人物的具体行为被外界予以不同的解读。川岛芳子女扮男装,被称为“男装丽人”,因而成为与拥有经典女扮男装形象的木兰进行对比的人物。在《木兰诗》的性别叙事中,“当户织”的懵懂少女最终成为“策勋十二转”的英雄,在战场上拼杀十年的木兰,成就了很多男性也难以望其项背的功业。“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安能辨我是雌雄?”体现了强烈的性别意识。对于川岛芳子的男装,部分报刊媒体认为,“芳子要扮男装的目的,并不是像木兰代父从军那样出于纯良的忠孝的要求:反之,她是要尽‘孝’于这异族的养父,尽‘忠’于这异族的国家,做一个被提线的变装的木偶……不惜作践自己的身体,做着无所不为的最无耻的汉奸。”[注]碧泉:《川岛芳子的故事》,《妇女生活》1937年第4卷第6期,第36页。木兰女扮男装是纯良忠孝,是主动提出的具有忠孝意义的光荣行动,而川岛芳子扮男装则是投降敌国,摧残自己的身体,是在盲目尽忠。
媒体将川岛芳子视为规训和整治的重点,对她的罪恶行径、性别特征、身体形态展开审判和批评,成为公众表达愤怒、彰显正义的途径。个中原因,不仅在于她混淆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服务于日本侵略的恶劣行径,也在于打破了性别壁垒,挑战男性权威的同时也欺压女性。历经十四年战乱的民众极思重拾旧有的社会秩序,在这个意义上,公众都参与了这种形式的裁判,人们希望藉由惩处一位国籍、性别混乱的女性罪犯,重建一些与性别角色密切相关的社会价值规范。也就是说,因为川岛芳子是女扮男装的女性,人们对她的一些不同于男性的期许与要求,即便是捕风捉影的说法,都被认为有理。
三、媒体与司法机关的互动
政府及司法机关着意将审判引入公共空间,借助惩戒川岛芳子表达对正义的追求。河北高等法院除了寻求法律依据[注]《中华民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凡父母为中华民国国民者,所生子女为中华民国国民,而在中华民国领域内出生者,亦为中华民国国民。”1945年12月6日《惩治汉奸条例》的第二条第一项规定,只要“曾在伪组织或所属机关团体服务,凭借敌伪势力,作有利敌伪不利于本国或人民之行动”者,一律需要接受制裁之明确规定,认定汉奸罪的要素是被告与敌伪之间构成实质性的合作关系。坚持公开、公正审判外,还以游街示众等形式将法律对川岛芳子的惩戒公开展示在世人面前。媒体记录了她游街示众的场面:“七十六名奸像中,有三名是女犯。而金壁辉又名川岛芳子。她是中国人所熟知并最为中国人所痛恨者,尤引起市民的注意。大家回顾几年前她使东北的半壁河山变色,拱手送给日本出卖祖国的那种威风,到今天终不免沦于国法之下,人心为之一快。”[注]徐晶:《川岛芳子起解:“人山人海争看金司令,摸脸蛋受讥诮满不在乎”》,《时事新报》(上海)1946年7月11日。
审判时也不例外。1947年10月15日下午3时,北平地方法院后花园的露天临时法庭上,人山人海。外形宛若中年男子的川岛芳子被两位法警押解,正式接受审判。四五千名观众把法庭围得水泄不通,大批新闻记者不停按动相机、采写新闻,中电三公司的工作人员则架好设备拍摄新闻影片。现场群情激愤,人们不时高喊:“妖怪!不要脸的女人!狐狸精!”[注]吕洛:《川岛芳子在平待死》,《自由天地》1947年第2卷第10期,第14页。川岛芳子审判的强烈公众参与性,使得对川岛芳子所犯汉奸罪的审判不再仅仅局限在法庭之内,而是转移到广阔的公共空间,引发多方关注和参与,使之迅速转变为万众注目的公共事件与舆论关注的焦点。
这种公众参与性体现在报刊媒体进入审判的现场、形成的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交互影响、彼此渗透的局面。除了上文所揭示的在报刊舆论场进行的审判,还包括媒体追随采访的实质性进入,及媒体的观点影响了法官的裁决——这种潜移默化式的进入。一方面,随着媒体报导的逐步深入,来自四面八方详尽的信息和大量的细节随着审判的进行而渐次向公众展示出来并传播开去,使人们对审判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发表评论乃至形成公共舆论也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对于司法机关及其审判人员来讲,报刊媒体对案件的密切关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社会压力,迫使其不断地思考在这个正在形成并不断发展的媒体时代,如何对案件进行公正的审判才能经受住媒体人和读者、公众字斟句酌的审视和评判,符合正义原则和人们的普遍期待。毕竟,作为近代中国社会里的一个新兴且日渐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权威性的职业群体,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需要在公共舆论空间中展示他们捍卫人民乃至民族权益、主持公平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职责及其个人才能,树立个人乃至整个职业群体的威信。
因而,在川岛芳子案审判期间,承审法官们对公共舆论也非常重视,不仅接受媒体、舆论的监督,而且主动与记者合作,甚至积极争取媒体配合案件的审理。譬如在公审川岛芳子期间,主审法官吴盛涵曾多次对媒体记者发表谈话,从国籍认证和适用法律两个角度解答公众对川岛芳子案的疑惑,并强调:“金逆壁辉难逃一死,重罪如山无刑可减。”[注]《金逆壁辉难逃一死》,《新民报》(重庆)1947年12月6日。经由报刊媒体的传播,吴盛涵对案件的解读不但令案件的执法者在读者和公众的心目中成为维护民族利益的代表,更启发和引导公众对案件及其审理持理性的态度加以解读。
值得注意的是,司法审判与舆论审判的交互影响、彼此渗透也给被告川岛芳子提供了抗辩的空间和可能。特别是利用公共舆论将自身诉求告知公众的做法,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使案件的发展进程朝着有利于女性当事人的方向转变。因为公众对案件当事人的态度可以经过动员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足以干扰乃至影响司法审理的程序,质疑执法者的权威性,改变法庭内外的力量对比。为了洗刷自己汉奸罪名,川岛芳子也千方百计地争取报刊媒体的同情、理解,做有利于自己的舆论宣传。
自入狱以来,她就不断地借接受采访的机会发声并撰写自白书,向公众剖白自己在战争时期的心路历程。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某些对庭审细节求之若渴的报刊媒体之需要,不失时机地展示她本人的思想观念,同时尽可能地增加对公共舆论空间的渗透和影响,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判决。在川岛芳子看来,性别是其争取公众同情的有效武器。所以,她首先尽量使其自我言说符合女性叙事的一般特点,即以说故事而非说理的方式阐释自己的观念和情感,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其次,她按照上述策略“编排”自己的身世,将发动战争的举动说成是“合法的”民族复仇,而不是叛国行为:“满洲同乡会本是保护排日士兵遗族的会,而且我又不是总裁……北方中学的董事长——是为我们二代同胞而就职的。”[注]《川岛芳子大书自白,洋洋洒洒振振有词》,《新民晚报》(南京)1947年1月9日。再次,为了“昭雪洗冤”,一方面,她进行“性别表演”,不仅渲染自己的女性气质,强调其性格软弱、冲动,易于被男人操控。上海《新闻报》将川岛芳子受审时的表现描绘为“滔滔诡辩好像舞台演戏”。[注]《川岛芳子公审记详 滔滔诡辩好像舞台演戏》,《新闻报》(上海)1947年10月21日,第10版。在受审的时候,川岛芳子将自己的年龄少报八岁,证明自己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策动的一系列事变皆是受周遭男性的胁迫。[注]《北平特讯:川岛芳子自草自白书》,《中外春秋》1947年第13期,第5页。另一方面,她重申自己“比勇士还爱国”、“叫中国人打死也光荣”[注]《初晤川岛芳子》,《大公报》(上海)1947年11月20日,第3版。,希望展现出某种男性气概。她在致辩护律师的公开信中甚至公然说:“丁先生……我的官司无法子打,不必打了……死也没关系”[注]《川岛芳子自剖:长函一封致辩护律师》,《新民报》(南京)1947年12月4日,第3版。,表达了崇尚忠诚勇敢、推崇舍生取义的情怀。在法律证据明显于自己不利的情形下,川岛芳子借助各式各样的性别表演不仅减轻了她不得不面对公正审判的心理压力,而且还使其抗辩更具“说服力”,并收获了得到执法者和社会舆论同情、理解的某种希望。然而,川岛芳子的愿望最终并没有实现。虽然川岛芳子在法庭内外的表演,让法官和在场民众乃至公众进一步领略到她在嗜血与风光传说背后的内心恐惧与不安,但她在战争中所犯下的损害国家民族大义的各种罪行,使她的抗辩缺乏事实基础,更没有得到法官和公众的认同。
尽管法院对川岛芳子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存在并不完全符合刑事处理的一般原则等问题。如对于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川岛芳子的相关活动,法院在事实部分写道:“民国二十年被告至上海藉舞女刺探军事情报,以助上海一二八事变”,对于事实来源,判决书认定,“但查日人村松梢风所著之《男装丽人》及日本报道部管理情报之中佐山家主使李香兰就该小说主演为《黎明之晓》又名《满洲建国的黎明》。被告秘书小方八郎供称‘……听说这电影内幕也是描写川岛芳子做间谍的事’,被告亦称‘男装丽人是村松梢风瞎编的……’。……实足证明被告藉充舞女刺探中国军情,以助敌人上海之变属实。况被告身出贵胄,生计豪华,如无重大使命岂能执此贱业。”[注]《河北高等法院宣誓死刑判决》,档案号28,1947年10月22日。转引自李刚:《川岛芳子审判档案大揭秘》,万国学术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266—268页。可见,司法机关对川岛芳子犯罪事实的认定及判决存在着主观性强、证据证明力不足的情况。对此,已有研究者做出相关考证[注]李刚:《川岛芳子审判档案大揭秘》,第266—268页。,时人也有评论,虽然川岛芳子参与了伤害中国人民利益的行动,但程序正义是不可或缺的——惩治汉奸大案中,根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惩治汉奸条例》出台在后,无法用于审视已经发生的事实,而且几经修改的该条例存在条目混乱不清、“法律救济力不足”乃至误判、标准不一的现象。[注]丁作韶:《汉奸案检讨》,《为不能陈述心事的国民向父老同胞请愿及其他》,1948年印,未出版。
川岛芳子在收押期间借助与媒体交流为自己辩护,为洗刷自己战争罪行而精心策划“性别表演”;法庭的判决兼顾舆情,这一切都是抗战胜利后惩治汉奸案中所出现的独特的社会现象。然而,在惩治汉奸浪潮尤盛、感性大于理性分析、媒体广泛参与的审判之中,证据和审判程序并不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最终,川岛芳子于1948年3月25日被执行死刑。[注]时至今日,川岛芳子的话题性远远未结束。1948年3月25日行刑之日,一些媒体怀疑川岛芳子重金收买“替死鬼”从而潜逃。近年来,她传奇经历和复杂身份又引起关注,在行刑当日是否潜逃又成为争论的焦点。种种讨论,使川岛芳子的历史形象更加扑朔迷离,也正因为如此,川岛芳子的生命历程从“事件”成为“历史事件”,甚至变成了“历史故事”。
结 语
抗战胜利后,司法机关和报刊媒体、公众惩治汉奸的浪潮,反映出文化与社会集体的政治潜意识[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页。,即中国人民摆脱了被日本侵略的梦魇,出于对正义的追求,进而将惩治汉奸作为一大诉求。作为中国人为日本人和伪“满洲国”服务、恶贯满盈的川岛芳子,自然无法逃脱。
在审判过程中,媒体不仅肩负收集公众意见的任务,还扮演着引领公共舆论的角色。媒体表达的惩治女汉奸的主张,既是彰显正义,又表达了恢复社会性别秩序的诉求。这实质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中,从清末“贤妻良母”、“国民之母”到民国时期“女国民”、“新女性”的演变脉络之下,性别议题逐渐进入女性与国家关系的讨论范畴之内的趋势,关于女性的“忠奸之辨”也是重要的议题。抗日战争中,女性占有一定地位甚至发挥关键作用,更挑战了传统中国忠孝节义叙事下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报刊媒体和司法机关对川岛芳子的关注和道德、司法审判,使其走向公共空间。报刊媒体不仅参与披露女汉奸,展现或建构其丑恶的形象供公众批判,使其经历所蕴含的战争、性别等多重意味得以凸显并走向公共空间,以传扬正义、满足读者偷窥欲。更从男性视角批判了川岛芳子对传统妇德的僭越和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在此基础上,大量“性别新闻”展现了女性汉奸们恶女人的形象。但报刊媒体的局限性也在此显现出来,在缺乏确凿证据和理性调查的基础上,媒体不惜笔墨地遵循既定的话语模式建构特定女性群体的丑恶形象,凭借媒体的传播力,使不辨真相的公众在潜移默化中相信此种建构的话语,并不利于真相的发掘。
汉奸既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为侵略者服务的“川岛芳子们”陷入公众的批判狂潮以及忠诚与背叛的讨论中时,也成为司法、舆论共同审视和规训的对象。此过程也凸显了战争对女性的多重影响:战争使一部分女性成为捍卫民族利益的正义者,也使个别女性变成邪恶的背叛者,更使“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愿望无法实现,相反却从多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妇女与国家、民族等话语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