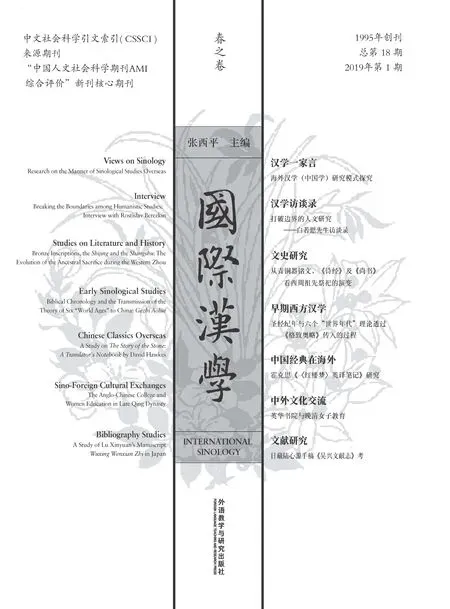往者可鉴
——读张西平先生著《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
2019-12-16蒋向艳
□ 蒋向艳
“明清之际的文化交流一开始就呈现出了双向性的特点,‘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同时进行”,①张西平:《东西流水终相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第14页。因此,对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不能仅偏于“西学东渐”一个方面,“中学西传”也是研究的重点。为研究者熟知的是,16、17世纪欧洲耶稣会士入华,一开始剃发、以僧服示众,而当他们意识到僧人并非中国社会的主流人群,儒家学者才是为社会所尊重的知识阶层时,便改服儒服、习儒书,以儒士面貌面对中国士人阶层,在向中国士人引介西学的同时,也为儒学西传欧洲掀开了历史的第一页。张西平先生的著作《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不仅细致地勾勒出了这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颇具新意的是,它还把长期掩盖于这一段历史幕后的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推到了历史的前台,还原了罗明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应有的地位。
本领域著作往往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视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伟大开创者和奠基者,而本论著则不落俗套,第一章“罗明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开拓者”从翻译《大学》、绘制中国地图、介绍中国、翻译“四书”等四个方面探讨罗明坚为中国古代文化西传所做出的贡献,明确了罗明坚这位一度被利玛窦的荣光掩盖的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称他为“耶稣会入华的真正开创者、西方汉学的真正奠基人和儒家文化西传的真正开创者”。②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页。
罗明坚1579年来华,1588年由远东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派遣返回欧洲,在华的时间仅有九年。1579年7月,罗明坚从印度果阿来到澳门,在范礼安的指示下,开始努力学习中文,后来达到能用汉语作诗的水平;肇庆期间,他和利玛窦共同编写了第一部中西文辞典——《葡华辞典》。从1583年开始直至去世的前一年即1606年,罗明坚绘制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地图。③宋黎明:《中国地图:罗明坚和利玛窦》,《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第112—119页。在澳门期间,罗明坚用拉丁文编写了一部教义问答手册。后来在中国文人的帮助下,罗明坚将其译成中文——《天主圣教实录》并于1584年刊行。这是第一部中文基督教义手册,在利玛窦的《天主实义》于1603年问世前是通行于肇庆、广受中国教友欢迎的教理手册。④徳礼贤著,谢明光译:《第一本中文基督教义手册的历史——汉学肖像》,《国际汉学》2016年第2期,第27—43页。罗明坚回到欧洲后,继续研读中国古籍,将“四书”翻译成了拉丁文。1607年,罗明坚在意大利萨勒诺(Salerno)去世。
如果说《天主圣教实录》是罗明坚“西学东渐”的代表作,那么《中国地图集》和“四书”的拉丁文翻译则是罗明坚“中学西传”的重要作品。事实上,正是罗明坚开启了儒家典籍的西译,迈出了儒学西传欧洲的第一步。在早期现代儒家典籍的西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部由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恩理格(Christian Herdtrich, 1625—1684)、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 1624—1676)和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四位耶稣会士一起翻译的作品,其中收录了《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翻译以及一篇有关孔子生平的文章。事实上,在这部名著出版于巴黎之前,已经有好几个节译本在中国各地出版,比如殷铎泽和郭纳爵(Ignace de Costa, 1599—1666)在江西出版的《大学》和《论语》的部分翻译,而罗明坚早在1593年便已翻译《大学》的第一部分,并收录在意大利耶稣会士波塞维诺(Antonio Possevino, 1533—1611)在罗马出版的《图书选编》(Bibliotheca Selecta)中。这是儒家经典第一次被翻译成拉丁文并在欧洲出版。这些儒家经典的拉丁文译本均为1687年《中国哲学家孔子》在巴黎的正式出版做好了铺垫。《大学》的拉丁译文是引起学者研究兴趣的一个关键点,张西平先生在论著中通过对罗明坚译文和其他几个译本的对比考察表明,罗明坚的译本不见得比《中国哲学家孔子》差。事实上,罗明坚的《大学》译文出版得如此之早,那时还不能引起西方读者足够的兴趣,致使这部译作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湮没无闻,几乎被彻底遗忘。然而,被历史尘封的记忆终有被发掘的一天。当这一天到来时,我们会发现,罗明坚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直觉性和敏感度有多高,他对《大学》这部中国儒家典籍的选择可谓独具慧眼,这使他在中国儒学西传欧洲的历史上扮演了“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角色。
这是张西平先生本部著作的一大重点内容,也是本书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彰显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尤其是儒学西传欧洲史上,罗明坚作为开启者和开创者的角色,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还原和恢复历史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真正认识罗明坚的汉学研究成果开辟了广阔空间。如今,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和“四书”的拉丁文译文都以手稿的形式分别保存在罗马国家档案馆和罗马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张西平先生在论著中透露,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罗明坚文集》有望整理出版,相信这一天到来时,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前景必将大为拓展。
本书的第二大重点内容就是上文已经提及的《中国哲学家孔子》(1687)这部在早期儒学西传欧洲史上举足轻重的著作,作者为此也专立一章。关于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文中有很多表述,比如称其为“耶稣会适应政策下产生的最高学术成果”“一本具有世界文化史意义的重要著作”,它“掀开了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思想翻译与研究的序幕”,“在中国典籍外译史上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和价值”,①《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第130—131页。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首先,这是最能体现在华耶稣会适应策略的一部著作,显示了欧洲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礼仪之争”的中期阶段。诚如张西平先生所说,理解《中国哲学家孔子》最重要的维度是“礼仪之争”,这不仅仅是就该著作诞生的时代背景而言,即自1627年嘉定会议发起对利玛窦适应策略的质疑、掀起所谓“礼仪之争”,到1667—1668年广州会议讨论中国礼仪、确定“四书”的翻译和注释工作,也是由于这场争论奠定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跨文化诠释特色——柏应理作为这部著作的一名译者和主要操作者,在具体操作中处处着意,显示了为在华耶稣会、为利玛窦路线辩护的用心。殷铎泽、柏应理为《中国哲学家孔子》所写的长篇导言阐释和宣扬利玛窦策略,认为古代中国人认识真正的神(the true God),②Thierry Meynard,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1687): The First Translation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11, p.189.这位神在中国古籍中的名字就是“上帝”,是“至高无上的神”(supreme deity),③Ibid., p.129.即基督宗教的“God”。比“上帝”使用更为频繁的“天”则是“上帝”的同义词,故中国古籍中的“上帝”和“天”都指基督宗教里的“God”。可以说,这篇长篇导言为“礼仪之争”中的译名问题是对利玛窦策略最好的辩护。
其次,这是第一部书名里包含“孔子”(Confucius)并附有孔子画像的西文著作,它使孔子作为“哲学家”(Philosophus)的身份传入西方世界并名扬天下。它所译介的《大学》《中庸》和《论语》作为中国经典哲学论著开始被西方人认知,并在耶稣会独具特色的跨文化诠释下呈现了一幅中国的理性哲学画图。这部著作与由罗明坚所开创的儒家典籍西译一脉相承,都以自身的实践说明,翻译是一种“交错的文化史” 。①《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第59页。“翻译意味着改写” ,②潘文国:《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33页。在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典籍英译这一背景下探讨此书内容,即耶稣会士们究竟怎么翻译和阐释儒家典籍,对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有何种启发等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比如,对《大学》篇名“大学”,从罗明坚到《中国哲学家孔子》就有多个版本的翻译:罗明坚译为“育人的方法”,殷铎泽译为“大人之教育”,柏应理等人在《中国哲学家孔子》中译为“大人,或者君主的教育”,③梅谦立将《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大学》的拉丁文译成英文,“大学之道”的英译文为“The great plan of learning,especially for men of princely rank”,即“大学之道”尤其指君主之人的学习大计。Meynard, op.cit., p.332.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s,1609—1677)则译为“伟人之学习方法”。比较这四种译法,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译文比较接近朱熹之解“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即“大学”并非为一般人、普通人之学,而是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大人”、君子之学。实际上,柏应理等耶稣会士在译注“四书”时,不仅坚持了忠实于原文的原则,同时也认真参考后儒包括朱熹的《四书章句》以及张居正的《四书直解》,在译文中结合了后二者的解释,使其译释文字十分饱满地阐释了原文内涵。不过译释文字的“饱满”并不意味着译文本身是“忠实可信”和“完美”的,相反,往往可以在译文中看到译者的“主体性”。比如对“明德”的翻译,是“自上天而来的理性”(the rational nature bestowed from heaven);朱熹《大学》章句称,“明德”与“亲民”“至善”“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是《大学》的一个核心概念,耶稣会士对它的翻译颇费了番工夫,译成“自上天而来的理性”,而“大学”就是要“除去各种邪恶欲望的玷染,让这自上天而来的理性回归原初的明净,就像一面明镜那般清晰明亮”,④“…so that this one (the rational nature), like the clearest mirror,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clarity, by removing stains of depraved desires.” Ibid., p.332.这番释义显然掺入了译者自身的文化背景,显示其从宗教立场出发的阐释,使得译文明显打上了译者的“烙印”。
同一文本有如此多样的译法,说明耶稣会士在面对儒家典籍时,首要的意图自然是“忠实”传达原文的含义,但实际上译文不可能做到完全忠实于原文,始终存在着译者的主动发挥,尤其是面对儒家典籍这样本身引起后儒各种注释的文本,耶稣会士也愿意加上自己的译释文本。潘文国先生在论及经典的翻译时指出,在中国,佛经的翻译传统是“放任翻译”,因为:
佛教重视的不是经典原文而是教义,它更看重的是传播的效果……中国的佛教经典中没有像《可兰经》和《圣经》那样定于一尊的经典,而是有无数的经典,翻译与撰述分不清楚,甚至佛教徒自己写的书也成了经典。⑤潘文国:《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是否必要?有无可能?》,《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12月,第23页。
这个情况或许同样适用于儒家典籍的翻译——不管是中国历代学者对“四书”“五经”卷帙浩繁的注释,还是由西方传教士所开启的中国典籍的西译。其实后者对儒家典籍的翻译并非是完全“放任”的,相反它有着自身强烈的“指导原则”——以《中国哲学家孔子》对“四书”的翻译来说,它是结合了原文、宋儒注释和当代(指明末)理解以及译者自身文化背景的结果。故《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译文,既非对原文原原本本的忠实对应,也非完全脱离原文的创造和发挥,而是如张西平先生所谓,“摇摆于欧洲与中国之间”,⑥《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第133页。是一种“之间”(between)的文本,是耶稣会士们试图沟通东西方思想的一个结果。就像前文的例子“明德”的翻译“the rational nature bestowed from heaven”(自上天而来的理性)也正是沟通中西方思想的结果。耶稣会士试图用这样的翻译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彰显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性本质,同时又告诉西方读者,这样的理性本质来自于“天”,赋予者是“天”,与西方的宗教神学非但不矛盾,反而是和谐一致的。用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关于文化相遇的方法论来说,这正是中西文化在相遇中互动和交流后的一个结果。①钟鸣旦:《文化相遇的方法论:以17世纪中欧文化相遇为例》,《清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73—74页。对学者来说,重要的是细致地描绘这一结果的形成过程,探索东西方思想文化中究竟各自有哪些部分参与了沟通,参与了新文本的“交织”(interweaving)②同上,第80页。。
本书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并不限于以上所重点指出的两方面内容。比如第二章“来华耶稣会: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西传的桥梁”将耶稣会作为儒学西传欧洲这一事业早期的主要承担者,因为客观上耶稣会成为儒学经典西传欧洲的传播者,而传教过程中发生的“礼仪之争”促使更多的中国文化经典被不断地翻译、介绍和传播到欧洲。“由于各修会都要为自己的传教路线辩护,这样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就成为各个修会的重要内容。”③《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第69页。第四章专门探讨经由罗明坚、利玛窦直至柏应理等人的《中国哲学家孔子》到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并且对中国思想在欧洲的影响做了深刻的反思;第五章则对16—18世纪中国传教士的汉学著作做了统计,对这一阶段中国典籍在西方的翻译和传播做了研究总结;最后在附录部分还收录了六篇长文,包括龙伯格(Knud Lundboek,1902—2002)的《欧洲最早的儒家经典翻译》《波塞维诺〈图书选编〉(1593)中的中国》《〈中国哲学家孔子〉中的〈中庸〉译文摘录》《卫方济〈中国六经〉法语转译本前言》等,很多资料都是首次披露和发表,既珍贵又富有价值。
总之,张西平先生的《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是一部学术含量极高的作品,不仅厘清了儒学西传欧洲史上的一些基本史实,并以清晰的章节结构和深入的论述分析,彰显了儒学西传欧洲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价值和意义,文中游刃有余的论述引发读者思考。就像书名所显示的,这是儒学西传欧洲研究的必读书目,相信它会启发和带领本领域的学者在这片学术领域继续稳步前进,将儒学西传欧洲研究推向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