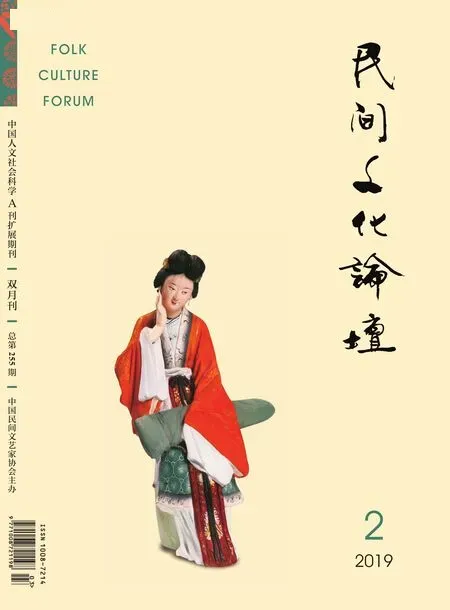重返“生土”世界:生土建筑营造技艺的复兴与乡村振兴
2019-12-15代改珍
代改珍
一、生土建筑营造技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国际交流与合作局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基础文件汇编(2016版)》。燕海鸣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遗产化”问题,提出“本质遗产”和“认知遗产”的概念,他认为判定一项“本质遗产”是否是“认知遗产”的标准取决于特定的“权威知识”②燕海鸣:《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遗产化”问题》,《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26日,第6版。。根据史密斯(Laurajane Smith)的分析,目前全球普遍使用的评判文化遗产的知识体系是以西方贵族审美观为基础的“权威遗产话语”。这种话语在她看来无益于遗产的真正保护:在“权威遗产话语”体系中,许多“本质遗产”被排除在名录之外,结果便是这些遗产最终失去了“遗产”的标签。③燕海鸣:《从社会学角度思考“遗产化”问题》,《中国文物报》,2011年8月26日,第6版。
生土建筑历史悠久,始于人工凿穴。早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游的氏族部落便开始用黄土来建造墙壁,同时用草泥或者木资源来创造半穴居住所④范鹭、姜立婷、赵剑峰:《基于历史引导下生土建筑的演变及其生态发展研究》,《建筑节能》,2018年第4期。。生土建筑及其原土和岩石是人类最古老的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⑤荆其敏:《生土建筑》,《建筑学报》,1994年第5期。,生土建筑包括窑洞、夯土建筑、土坯建筑,其技术包括夯土技术、土坯技术和烧制砖的技术。中国生土建筑中的窑洞营造技艺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认知遗产”,同时,还有大量的其他生土建筑技艺尚未被列入名录,但在民间广泛存在着,是一种“本质遗产”,其传承、创新和应用,与人们的生活和区域的发展息息相关。
河南新郑裴李岗村,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裴李岗遗址,是个比较典型的中原农耕文化村落,保存有类型多样的生土建筑,且有一支传承多代、技术过硬的生土建筑营造技艺队伍,打窑洞,夯土墙,做土坯房,样样在行,做出的生土建筑坚固耐用、美观实用。裴李岗的生土建筑营造技艺,作为尚未被权威认定为“认知遗产”的“本质遗产”,在近两年的乡村振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作为裴李岗乡村振兴的规划设计团队成员,同时也作为投资创业的“新乡贤”,全程参与了本阶段的乡村振兴实践。本文以参与观察的方式,呈现裴李岗村在乡建中如何挖掘、再现、放大其生土建筑营造技艺,构建乡村的历史文化主题场景,如何在乡村的产业振兴中挖掘香包、剪纸、虎头鞋等手工技艺,丰富乡村体验业态,提升游客参与体验,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
二、从裴李岗遗址到崖壁窑洞:裴李岗村生土建筑技艺的历史
裴李岗,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新郑市新村镇西部,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老村。1977年,在裴李岗村发现了重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年代为公元前5600年—公元前4900年,距今约8000年左右,被公布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对裴李岗考古遗址进行发掘,考古队发现裴李岗遗址居住区土层主要有三层,即黄沙土、红黏土和浅黄土,且土质中有零星的泥质和夹砂的红陶片以及残石铲、骨针和骨锥等。在居住区北部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不少含有草秸和带植物杆痕迹的红烧土,这些红烧土当为房屋的墙壁或房顶倒塌后的遗存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这些迹象表明这里曾有过比较完整的村落。通过研究表明,裴李岗文化的房屋均为半地穴式建筑,以圆形房屋为主,方形房屋较少,门朝南,有阶梯式门道②张之恒:《中国考古通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基于裴李岗遗址的发掘,新郑博物馆对裴李岗考古遗址发掘中的文物进行展示,并结合裴李岗遗址考古中对居住区发掘的建筑元素,对裴李岗文化中的房屋建筑进行场景再现。
如今,在裴李岗下属的西河李自然村南侧、双洎河北岸的台地上,沿着黄土崖壁排列着数十孔窑洞,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西河李村的大部分村民都居住在这些窑洞里。在目前村庄的老房子里,还有着大片的夯土墙,甚至整座房子的主题框架都由夯土构筑而成,大多已无人居住,濒于坍塌。裴李岗从5000多年前到现在的这些穴居或者崖壁居的窑洞以及土坯房、夯筑房都属于生土建筑的类型。他们在中国广大黄土地区长时期地广泛存在着,保存了黄土地区的历史、生活密码,也延续着地域独特的村落景观。
裴李岗文化属于全部都为地下文物的遗址型保护单位,转化为景观和产业的难度比较大,因此在多年的“河南省美丽乡村”评选中屡屡落选,给当地干部村民带来很大的挫败感,用当地有的人的话说是裴李岗“徒有其名”。
2018年初,新村镇主要领导和村干部们下定决心,以文化复兴为突破口,投入资金和精力,抓好裴李岗村的振兴工作,进而给全镇甚至全市的乡村振兴做出示范。于是,当地政府迅速在裴李岗开启了以乡建为切入点、以乡村业态和乡村旅游服务为主体的乡村振兴实践,紧紧把握住裴李岗村的包括窑洞在内的生土建筑技艺,进行乡村空间的营造和景观设计,促进了乡村独特场景和文化氛围的形成,提升了裴李岗人的文化自信,并进一步助推了裴李岗村在新郑乃至河南省乡村振兴中的地位,给当地发展带来了政策、名望等方面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生态建筑技艺的复兴:营造裴李岗独特的乡村空间和景观
“古村落景观”的意象表现为一定地域人群所创造的村落文化的空间形象, 一定地域人群的文化思想就通过这种独特的村落形象来表达。①刘沛林、董双双:《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向》,《地理研究》,1998年第1期。裴李岗的乡村振兴实践,在由设计师主导的阶段,就从生土建筑的大规模再现入手,营造古村落的黄土景观体系,试图构建裴李岗村从8000年前走来的历史感和独特文化地位。
2018年3月,裴李岗乡村振兴的乡村建设工作开始,政府专门从北京聘请了设计团队驻村参与。该团队构成丰富,有在乡建领域享有很高声誉的孙君,有多名建筑学、文化学博士,有熟于建筑施工对接的技术人员,所以,从设计到施工,裴李岗乡村建设的全过程都由该团队负责和主导,笔者以规划者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作之初,设计师基于裴李岗考古遗址报告和新郑博物馆中的裴李岗文化场景复原,通过现场踏勘、走访等形式,努力寻找裴李岗村的各类生土建筑,极力从裴李岗久远的生活痕迹中进行符号提炼、解读、放大、重复和叠拼,形成公共建筑、景观改造的符号语言,来唤起人们的乡愁记忆,建构裴李岗悠久的独特的历史空间感和景观体系。
前后两次,设计团队驻村20多天,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踏勘,搜集了30多项生土建筑技艺的素材,包括:西河李自然村南侧的崖壁窑洞,村民旧房中的夯土墙、夯土院墙、临时搭建的土墙柱,村落农田高架起来的水渠渡槽的黄土基底,甚至还包括正在进行中的裴李岗遗址扩大发掘中的作业纹理、层叠的土层。在与村民的走访座谈中,设计师们不断地引导老人们回忆以前的生活,尤其是生土建筑在生活中的使用状况,并描述其制作过程。设计方案以裴李岗遗址文化为品牌,从村落空间的梳理、地标性建筑的改造、公共景观的重构等方面,大规模地使用生土建筑,恢复村落的传统场景感和融于自然的生活体验感,彰显“八千回眸•根亲祖地”的主题。
在建筑景观改造中,设计团队重点把握了村口、祠堂、游园广场、村委会办公房、村诊所、公共厕所等节点,并选择了4户民居改造作为示范工程,以大尺度的黄土墙面、黄土立柱、黄土质感的雕塑、土木做旧的亭廊等,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力,将游客瞬间带入一种历史场景当中,增强对村落文化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同时,对于村民来说,村落本土文化的放大、强调,再经媒体传播出去,受到上级领导和周边村落以及外来游客的赞赏,很大地提升了文化自信和自豪感。
首先,利用黄土立柱及其变形、组合,设计裴李岗村的村标和村口景观。设计师在从北部、南部两个方向进入裴李岗村的道路入口处,设计了以加粗、加长的黄土立柱为主体、辅以木架,形成村庄标志,上面用隶书字体、锈蚀钢板材料,写上大大的“裴李岗”村名,并悬挂“八千回眸•根亲祖地”标识牌以提示其文化高地的特征。
其次,对于村落游园、景观广场,采用土、木、茅草、石材相结合的乡土材料,形成亭、廊、台、挡墙、地面纹饰,构建原始蛮荒之感。设计师在村落中安排了三处游园,以作休憩、交流、游玩、活动场所。在计算了本村活动人数、加上接待游客共享游园的数量之后,按照人均所需面积和功能进行了场地、空间规划,然后开始进行了以“土、木、水”为元素的艺术化装扮,包括6个圆形、八角形的茅草顶、木立柱的亭子,3面黄土挡墙,上面用石块刻字记录着裴李岗的村史,十多条木头长椅,以及若干个木质的跷跷板、土质的攀爬矮墙,这些乐园的地面大多以毛面的原石铺装,或者用大面积的透水砖铺设,以无动力的自然材料构筑出一片不知岁月的公共乐园,延续着游人的穿越感。
另一项重要的工程是选择村落重点公共建筑,进行精细的传统化改造。第一阶段,进入改造范围的是:李氏祠堂,村委会办公房,村诊所,公共厕所,4户居民经过协商、腾退的民居等。在设计师开始工作的时候,村中的李氏祠堂因为长久没有活动、无人维护,除了正堂紧锁,其他地方已经被村民承包用作养鸡,乱堆乱放,垃圾遍布,无处下脚。祠堂的建筑也是本村常见的灰砖单层,主建筑朝向也因为便于道路连接的考虑,为坐西朝东格局。此地为典型的中原文化地区,而且村落地势平坦,整个村庄的建筑格局呈街巷式、排列规整,祠堂的坐落、朝向按照传统的礼法要求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设计师大胆地将原祠堂建筑拆除,重建一个南北朝向、高墙高屋顶、土木青砖建材的旧式祠堂,祠堂沿主街面,即院落的东墙开一个次门,便于游客进出,但是祠堂礼制式的正门位于南部。村委会办公房是设计量最大也是投资额最大的一项改造,主要的理念就是以黄土筑墙艺术包装建筑外立面、以黄土立柱的变形及组合构建院落及公共景观,以将这座村庄内体量最大的建筑群营造出一种“原始、神秘”的感觉,以大规模的黄土艺术将观众和游客带入到一种遥远的文化意境中,以突显裴李岗文化的独特魅力。村公厕是最有意思的一项改造,因为面积较小,仅为80㎡,单层,层高2.8米,设计师大胆地使用黄土里面将整个建筑全部包裹、覆盖,公厕的入口处用低垂的黄土门廊、屋檐,完全遮挡了原有的门脸及其提示性文字,转而改用类似于原始岩画的符号来表示“男、女”区分。一个实用性极强的公共服务设施,变成了一件艺术品。来往人群驻足拍照,有游客的微信写着:这样的厕所,你还敢上吗?感觉里面藏着我们的祖先。一段时间内,这间公共厕所成为了裴李岗村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带着一种探访8000年前先人们生活场景的心态前来膜拜。在对4户重点民居的改造中,设计师没有一味地追求夯土住房技艺的艺术化彰显,而是主要地结合本地和周边近代建筑的特征,青砖灰瓦,在门、窗、屋檐、屋脊的处理上,突出厚重感,并结合旅游接待经营的需要,打开了部分空间,尽量做到室内外互通,增大庭院内的休闲空间,并进一步通过命名系统,强化空间的怀旧感。
此外,设计师把握住在裴李岗遗址中发掘出大量陶器这一历史,艺术化地再现在整个村落的景观营造中,在广场的挡墙当中会镶嵌进各种造型的陶罐,地面铺装中使用陶罐的残片,在墙面装饰中用陶罐残片进行图案拼组,在主要街道的房脚,看似随意地堆放做旧的陶盆、陶罐,并对其进行景观绿化隔离。同时,在村落中建起两孔陶窑,寻找掌握烧制陶器的老匠人,进行烧制实验,成功之后,开始常态性地设置陶器技艺培训班,成立了陶艺合作社,由师傅带领徒弟们钻研技艺、制作陶器,由合作社的经营者将这些作品作为景观设施、公共用品供应给政府和建设者,另一方面,作为旅游纪念品,提供给游客。制陶工艺在裴李岗的乡村振兴实践中,既营造了空间的文化感,又丰富了游客的产品参与体验性,更重要的,激发了村民学习、掌握、传承传统手工艺的热情,增加收入的同时,提升了他们的文化自信。
四、制陶、香包、剪纸、虎头鞋:乡村技艺的组织化复兴
在裴李岗乡村振兴中,伴随着生土建筑的大规模再现对于村落空间和景观的重构,以陶器、香包、剪纸、虎头鞋为代表的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也在政府鼓励、村集体组织和村民的积极参与下得到复兴,形成了乡村生活的热闹气息,也成为游客进村参观、参与、购买的主要物品。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以及开发商和乡建设计工作者等外界因素的“嵌入”下,裴李岗村乡村空间由传统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开始被打乱和重构,逐渐融入消费空间、文化展示空间、公共休闲空间等新的空间。乡村振兴促进了裴李岗乡村再生产,拓展了乡村再生产空间。伴随着新的消费空间、文化展示空间等的再生产,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被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和特色休闲业态也得以复兴再生,嵌入到裴李岗乡村振兴中来,如河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包、新郑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以及虎头鞋等的制作技艺等。
非遗是老百姓生产生活的“活化石”,非遗的生命在于生活,非遗复兴方式,尤其是非遗技艺的复兴,不是让它活在陈列室或者博物馆里,而是走进老百姓的生活里。制陶、香包、剪纸和虎头鞋等非遗被作为“乡愁”的符号和载体引入到裴李岗乡村振兴中来,它们通过文化展演和表演等较强参与体验感的方式以非遗精英(非遗传承人或非遗公司)文化展演的空间生产扩展到社群范围的社会消费空间生产,融入到裴李岗乡村生活中来,丰富了裴李岗乡村文化的内涵,在裴李岗乡村振兴实践中验证它的生命力,形成裴李岗的乡愁传统,扩大了非遗的影响力。制陶、香包、剪纸和虎头鞋等非遗(技艺)的复兴,是一个可以符号化、再现化的情感和文化记忆,在乡村振兴红红火火的场域中组合、叠拼、嵌入,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中,进一步将裴李岗村塑造成一个“乡愁的村庄”,让裴李岗村的乡愁更有乡味。在裴李岗的乡村振兴中,通过制陶、香包、剪纸、虎头鞋等非遗技艺的多元化复兴,促进了裴李岗村的乡村文化振兴。通过举办培训班等方式为广大群众提供了一个学习和传承非遗技艺的平台,结合非遗节庆活动的举办,既促进了非遗技艺的传承,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①杨利慧:《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从中德美三国的个案谈起》,《民间文化论坛》,2014年第1期。,又增强了裴李岗村村民对非遗的文化认同。将非遗与乡村旅游等相结合,推动非遗跨界融合,创新非遗文创产品,并充分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拓宽非遗文创产品的传播和销售渠道,为村民提供就业机会,带动裴李岗乡村振兴发展。
一是成立非遗传习所,开展非遗传承培训。在裴李岗乡村振兴中,在政府的组织下成立非遗传习所,政府免费举办非遗传承培训班、非遗活动月、非遗进乡村等一系列非遗主题活动,聘请新郑市非遗传承人为广大村民群众开展非遗技艺的培训活动,吸引和带动广大群众参与到非遗产品制作中来。一方面,传承非遗的制作技艺,促进非遗的传承和弘扬,增进村民群众对非遗的文化认同,增强了村民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让广大村民群众掌握一项技能,变成一种谋生手段,为村民群众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二是研发非遗旅游产品,发展非遗文化产业。在裴李岗乡村振兴中,通过“非遗+”的跨界融合,发展非遗文化产业,为非遗赋能,挖掘非遗的商业市场价值。一方面,将非遗与乡村旅游相结合,开展非遗体验之旅,成立非遗文创工作坊,打造非遗产品、非遗文创产品、非遗周边产品等一系列以非遗或非遗符号为主题的非遗旅游产品,让非遗产品与市场对接,通过市场流通实现非遗活态化发展。游客可亲自参与体验到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艺中来。在乡村旅游过程中,非遗会成为游客表达自己、与他人进行交流的资源,在环境中回流进入社会,重新成为鲜活的再创造的文化资源①杨利慧:《民俗生命的循环:神话与神话主义的互动》,《民俗研究》,2017年第6期。。同时要充分结合市场,创新非遗旅游纪念品的特色化和多样化设计,将非遗产品进行创意化包装与创新定位,加入现代消费理念,使其更加符合现代市场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将传统非遗与现代化设计相融合,通过非遗的跨界融合,让非遗走进当代生活,设计出符合当代人审美需求的非遗产品,从非遗自身的“创新”,到非遗与外界的融合,再到提取非遗元素或者非遗符号的“多样化诠释”来研发非遗文创产品,促进非遗在传承活化中焕发新生,挖掘非遗的文化魅力,发展非遗文化产业,提升非遗的价值。
三是充分利用互联网,拓宽非遗产品销售渠道。裴李岗村在乡村振兴中,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拓宽非遗产品的传播和销售渠道,互联网电商已成为产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为非遗产品的流通提供渠道和空间,让非遗产品进入到更多消费者的视野,激发消费者购买非遗产品的欲望,让非遗产品更好地融入消费者的生活中。
四是举办非遗节庆活动,传承非遗技艺。非遗不是静止的文化,而是动态的文明。非遗在生存与生活中,是不能脱离生活的“生活文化”,凝结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情感记忆和精神寄托。端午节佩戴香包是新郑当地的古老传统,因其具有美好的寓意。裴李岗的乡村振兴充分运用这一传统习俗,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举办以香包制作为主题的非遗节庆活动。一方面,邀请新郑非遗传承人现场制作非遗产品,通过非遗技艺的活态展演来展示非遗魅力,吸引广大群众关注非遗;另一方面呼吁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香包的制作中来,将非遗的传承深入到群众的生活中,潜移默化地促进了香包非遗技艺的传承。同时还举办非遗文创大赛,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到非遗文创产品的创意设计中来,推动非遗的创新发展。
五、非遗技艺的集体狂欢:裴李岗乡村振兴的主体实践
裴李岗乡村振兴是一个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的过程。国家在场、政府主导或参与、村干部带领、媒体推波助澜、乡建工作者积极参与、乡村精英重回主流、外来游客体验等等,多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共同参与②安德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民俗学的两难选择》,《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他们互相凝视,互相协作,他们是乡村振兴中非遗复兴的协作者,注重非遗“内在价值”及官民协作③杨利慧:《官民协作:中国非遗保护的本土实践之路——以河北涉县女娲信仰的400年保护历程为个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共同推动非遗复兴。
各级政府以决策者的角色主导乡村非遗复兴。在乡村振兴中非遗复兴,从上到下,各级政府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级政府以政策扶持、资金保障、编制规划和落地实施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非遗复兴中来,是非遗复兴的主要参与者和核心力量。宏观层面上的中央政府提供发展战略方向指导、政策引导和资金支持,以国家在场的方式参与非遗复兴。中观层面上的省市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扶持和资金保障,推进非遗复兴。微观层面上是县乡镇村级政府,他们是国家和省市相关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实施者,他们不仅在政策扶持和资金保障上予以推进,更是直接参与到非遗复兴具体建设中来,他们成立非遗传习所,举办非遗培训班,聘请非遗传承人来开展非遗培训,并举办一系列非遗节庆活动。非遗节庆活动是政府主办的,政府占据着绝对的权力地位,以行政手段和财政手段投入非遗节庆活动,赋予非遗新的文化意义,促进非遗复兴。
社会精英以特色专业优势引导非遗复兴。社会精英,诸如乡建设计师、乡村文化建设者、乡村文化艺术者、非遗传承人等等,他们以各自擅长的特色优势参与到非遗复兴中来。乡建设计师,受到乡政府的邀请,以其专业的视角和技术能力参与到裴李岗村的乡村振兴规划中来,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参与者。他们在编制规划时,在乡政府及村干部的帮助下获取裴李岗村的建筑资料、历史文化资料,并以专业的视角,融合地方政府和相关人员的思想,企图去实现他们构想的乡村振兴空间。
在裴李岗乡村振兴中,乡建专家孙君主导裴李岗乡村振兴的规划设计,派出专业团队进驻裴李岗,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参与到乡村振兴中的非遗复兴:
凝练村庄最传统、最古老的建筑符号,进行建筑风貌改造,再现生土建筑技艺。乡建设计团队通过寻找到村庄南部已经废弃的土崖窑洞,描绘窑洞外缘的轮廓、窑洞留存的黄土纹理等,在村庄建筑改造中大量地将黄土材质和痕迹斑驳的色彩以及窑洞的流线运用到外墙上,以及村落的公共景观中,力图营造一种历史感和岁月流变的沧桑感。在裴李岗的建筑风貌改造中,乡建设计团队建议政府,首先从村部、祠堂、村卫生所和村部旁边的四户民居开始,并加上村口景观、村民活动广场等几处,尝试着通过“点、线、面”的方式,迅速形成古老的、文明的裴李岗的视觉冲击力。
从“久远生活的痕迹”中提炼,用生土建筑技艺来建构公共建筑和景观改造的符号语言。乡建设计团队极力从裴李岗村“久远生活的痕迹”中提炼符号,如从窑洞壁、窑洞群、土泥墙、土墙柱和裴李岗遗址发掘现状进行符号提炼、解读、放大、重复、叠拼,形成规划设计中公共建筑、景观改造的符号语言。
解构与重构传统乡村空间,营造非遗的“文化展示和消费空间”。乡建设计团队通过对裴李岗村传统的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解构和重构,通过规划植入传统非遗休闲业态,如香包、剪纸和虎头鞋等,进一步融入消费空间、文化展示空间、公共休闲空间等新的空间,营造非遗复兴的“文化展示空间”和“消费空间”,唤起乡愁记忆。在裴李岗乡村振兴发展中,通过文化展示空间和消费空间的规划,引入传统休闲业态,如非遗香包、虎头鞋、剪纸等,既可以展示和消费非遗文创产品,又可以体验非遗产品技艺,从而促进了非遗的复兴。非遗进入旅游市场过程中,会涉及众多利益相关者,构成复杂的利益相关者关系圈①赵悦、石美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的三大矛盾探析》,《旅游学刊》,2013年第9期。。这些非遗文创产品,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非遗技艺,另一方面又吸纳设计师的创新思维,融合了新时代的工艺、创新和创意理念等,让非遗技艺融入当下生活和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促进了非遗产品的创新,为非遗发展带来全新动力,推动非遗的复兴和发展。
社会媒介以广泛宣传报道助推非遗复兴。在社会媒介广泛关注和宣传报道下,非遗被传播给广大社会受众,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催升了村民的文化自豪感,也强化了村干部、乡镇干部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决心。对此,村民和地方干部都深深地感到被鼓舞,纷纷将其转发、传播。在社会媒介的镜头下,以香包、剪纸、虎头鞋等为代表的非遗及其文创产品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结合乡村旅游的发展,非遗及其文创产品呈现出明显的旅游体验和消费导向,并作为一种旅游文化景观实现了再生,推动了非遗的复兴。
乡贤以示范者的角色带动非遗复兴。乡贤在非遗复兴中起到先锋楷模和示范带头的作用。一方面,乡贤们基于乡情乡愁情怀,更加容易且比较乐于学习和传承非遗技艺,并发挥他们的先锋楷模和示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村民共同参与到非遗的复兴中来。另一方面,乡贤们可以发挥他们在市场、技术、信息、资本、人脉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推动非遗及其文创产品的创新和发展,拓宽非遗产品的传播和销售渠道,推动非遗的复兴。
外来游客以消费者的角色参与非遗复兴。在裴李岗乡村振兴中,随着非遗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开设非遗文创店或者非遗体验工坊,以前店后坊的形式对外来游客产生旅游吸引力,吸引游客参观购买非遗产品或者参与体验非遗的制作技艺,他们以消费者的角色直接参与到非遗复兴中来。同时,为了更好地满足外来游客和消费者的需求,裴李岗非遗文创企业也会主动去了解潜在游客群体的消费需求来进行非遗文创产品的创新创意化设计,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此时的游客则可以说是间接参与了非遗的复兴。
本地村民逐渐以“文化自觉”的态度积极参与非遗复兴。本地村民无疑在非遗复兴中占据着很重要的角色,他们是非遗复兴的重要传承者和参与者。在裴李岗乡村振兴发展中,本地生活的“主人”——村民最初对非遗的复兴并未表现出直接的反抗,但也没有积极参与其中,而是持“不以为然”的旁观者态度。在快速见效的乡村振兴成果面前,在乡贤的示范带动下,村民们逐渐“乐在其中”,由被动变为主动,发挥起“主人”的角色,以“文化自觉”的态度参与到非遗复兴中来,既增加了村民对非遗技艺的传承和文化自信,又使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且增强村民对非遗复兴及非遗文创产品的认同。
在裴李岗的乡村振兴实践中,设计师和施工者以生土建筑的体系化复兴为基础,在空间上对乡村进行重构,形成景观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消费空间、生态空间,以黄土艺术为代表对村落景观进行了传统化实践①康丽:《从传统到传统化实践——对北京现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续现状的思考》,《民俗研究》,2009年第6期。,力图营造一种8000年从未间断的历史场景感,极大地塑造了与裴李岗遗址相适应的乡村文化地位。同时,以政府和村集体为主导,村民们积极参与到制陶、香包、剪纸、虎头鞋等乡村技艺的复兴当中,乡村的文化活跃度和感染力在增加,村民的文化自信也在媒体和游客的鼓励下迅速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