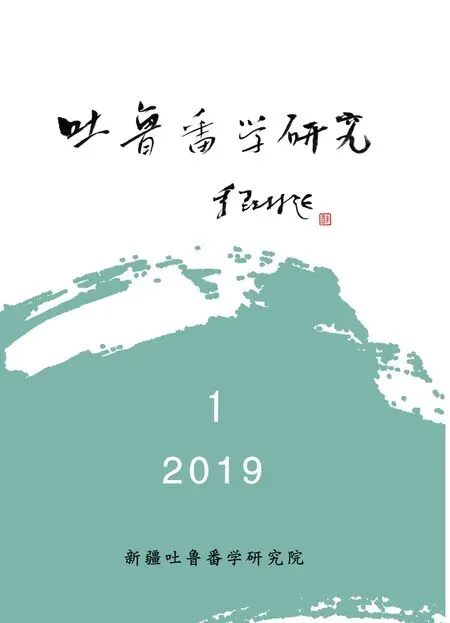发前人未发之微,阐前人未阐之实
——评杨富学《敦煌民族史探幽》
2019-12-14盖佳择
盖佳择
杨富学先生的新作《敦煌民族史探幽》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研究书系》中之一部,为其多年致力之敦煌民族史、维吾尔和裕固民族史研究成果之结晶,汇集了其发表过的十六篇敦煌民族学论文,可贵的是,杨先生在出版之前复对之一一增删、润色,更纠正部分旧说,适当增益其最新研究成果,为本书增色不少。
河西,特别是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华戎交汇、民族融合之所,有类于川藏地区之藏彝羌走廊,河西走廊亦为藏羌回蒙及古之月氏、乌孙、粟特、波斯等诸民族往来之大走廊,季羡林先生所道“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可谓至理名言。河西、敦煌以其博大的胸怀包容了通道上来来往往的各大民族,接受了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然又使之深深打上了汉地儒家文化的烙印。今观甘肃之版图,左为新疆,右为宁夏,上为内蒙,下为青藏,称一句“四面六蕃围”绝不为过。狭长的河西走廊,有如一道长城,隔开了诸蕃,将博大精深的汉族文化远远推向丝路的另一端。在各族文明汇聚河西之际,河西的汉族文明也深深影响了四围诸族:回鹘受汉地影响,转而信奉佛法;吐蕃经汉僧摩诃衍传法,接受了禅宗;粟特人大量在汉族的张氏归义军政权担任要职,对抗吐蕃、回鹘等各民族的侵扰,或有粟特血统的曹议金更是攀上汉族高门谯郡曹氏,以正宗汉家苗裔自居……这些现象在古代中国曾广泛存在,而于河西表现尤为突出,杨富学先生一向于此类现象多有探究,此书即其成果也。
杨氏此书主要探讨了少数民族对敦煌之贡献,敦煌与月氏乌孙先民之关系、敦煌与吐蕃、敦煌与回鹘、敦煌与裕固族等数问题,其中有历来困扰学术界之大问题,有恰才关注之新问题,多对学界成说提出新解,虽未必皆能终结疑问,然其证据扎实,论证周密,自圆其说已是绰绰有余。
一、敦煌学旧说新解
杨先生在探讨“少数民族对敦煌的贡献”时,首先对学界老生常谈之“敦煌”与“莫高窟”之名称来源做了一番发微。关于敦煌二字之释义,研究者可谓夥矣。自张骞归自西域,言月氏居敦煌、祁连间,东汉应劭又云其意为“敦,大也,煌,盛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更衍为“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数千年间人沿之不改。然近人于阅读敦煌文献之时不免产生疑问:张骞向汉武帝汇报河西边情时如何能够未卜先知,知敦煌之将来会无上辉煌,广开西域呢?更何况当时河西地区为匈奴属地,古或为三苗所居,鲜有汉人之踪迹,何来汉文之名?另外很多学者亦注意到了在《山海经》中记有敦薨之山、敦薨之水,恐即“敦煌”之原名,其字面义颇为不佳,为音译的可能性无疑很大,而张骞的原始语境下与其相连的“月氏”、“祁连”今已知为胡名音译,则“敦煌”独能例外乎?学界之中岑仲勉先生首抛假说,于《释桃花石》中提出“敦煌”或为“桃花石Taugus(Tabgac)”的对音①岑仲勉:《释桃花石》,《东方杂志》第33卷21号,1936年,第63~74页。,然其说漏洞颇多,故其不久即别撰一文否定该说②岑仲勉:《桃花石之新释》,《突厥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104~1059页。。海风的《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则以为或是源于希腊语,与生活于敦煌的塞种人相关③海风:《敦煌地名的来源及其他》,《光明日报》1986年10月26日第4版。;林梅村以为西域有一地名“单桓”,为《山海经》中“敦薨”之本,后其名移于敦煌④林梅村:《吐火罗人与龙部落》,《西域研究》1997年第1期,第14~16页。;史念海以为,“敦煌”与“祁连”等语皆为匈奴语⑤史念海:《河西与敦煌·上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年第4期,第64页。;李得贤以为其为藏语“朵航”即“诵经地”之意⑥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86页。;李正宇先生以为为月氏语⑦李正宇:《三危瓜州敦煌辩》,《丝绸之路》2013年第4期,第21页。,宫玉海先生以为为乌孙语⑧宫玉海:《敦煌的由来和乌孙的族属》,氏著《〈山海经〉与世界文化之谜》,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44~146页。;西方学者对此亦多有论述,如英国汉学家贝利以为“敦煌”当为围绕、堡塞,源于伊朗词Θruvan(druvana-)⑨H.W.Bailey,Indo-Scythian studies being Khotanese texts,VII,Cambridge,1985,p.100.;美国汉学家梅维恒提出敦煌来自佉卢文俗语drumga,可能也与某伊朗语词同源,向上可推到共同印欧语Dher,意为掌握,稳固⑩梅维恒撰,王启涛节译:《敦煌得名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9期,第219页。;匈牙利伊朗学家哈尔马塔亦认为其来自伊朗语词,意为大建筑,设围的城市,其认为敦煌与吐鲁番实即一名之转,意为围绕,坚固的堡垒⑪⑪ 梅维恒撰,王启涛节译:《敦煌得名考》,第219页。;法国汉学家列维认为敦煌源于窣利语(即粟特语),认为其对音为Drwn(Darwan),等于希腊语Throana⑫⑫ 伯希和:《说吐火罗语》,伯希和、列维著,冯承钧译《吐火罗语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139页。。而余太山、王欣、王宗维⑬⑬ 余太山:《古族新考》,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王宗维:《敦煌释名》,《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第61页。等所提出的“敦煌为吐火罗”说则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以上诸说,杨先生显然皆已周知,然心不认可之,复碍于篇幅,故寥寥数笔一带过之。杨氏认为钱伯泉先生提出“敦煌”源于古突厥语之说差似之其以为“敦煌”源于终南之“敦物”,为姜姓与允姓戎人游牧之地,其义为“连绵的大山”⑭⑭ 钱伯泉:《敦煌与莫高窟音义考析》,《敦煌研究》1994年第1期,第44~53页。,杨富学先生在其说基础之上提出敦煌为原始突厥语dawam(瓜)之意,盖敦煌古出美瓜,后又称“瓜州”,“瓜州”当即“敦煌”之汉译也。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详细论述,见于杨撰《“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⑮⑮ 杨富学:《“黑龙江”名出阿尔泰语考》,《语言与翻译》2000年第3期,第52~54页。,因收入另一文集⑯⑯ 杨富学:《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3~37页。而未复入本集。
至于“莫高”,其出较晚,窟于前秦方凿,名于隋时《莫高窟记》中方现,故学者多望文生义,以为因佛法“莫高于此”而得名,亦有因其又写作“漠高”而以为当为沙漠之高山(鸣沙山)之意,然亦多有学者推测其为胡名,具体而以突厥语最为可能。按李得贤以为为突厥语沙碛之意①李得贤:《敦煌与莫高窟释名及其他》,第88页。,钱伯泉以为乃突厥语“仆固”抑或“牟羽”即Bogu之转,意为“神圣”,盖因三危山常有佛光也。杨先生承之,并以三危山之古名“昇雨山”实为“牟羽山”之讹。
于此章中杨富学先生更探讨宋史上所谓“沙州北亭可汗”、“镇国王子”之来历,其认为,过往学者多认定其必为高昌(北庭)回鹘之可汗或王子,不然则为流亡之甘州回鹘,牵强其说,独无视史书中沙州回鹘大量朝贡记录,实是怪哉。其以详实证据考出沙州回鹘之真实存在及其与西夏相持年限,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关于“沙州回鹘”的相关考证,同可参见其书之第六章“关于沙州回鹘国的建立”。
杨富学先生曾在印度访学数年,熟谙印度两部大史诗,其考出敦煌文献中《罗摩衍那》的于阗语缩写本有三种、吐蕃文写本有六种、吐鲁番出土回鹘文写本两种。杨氏以为,“罗摩衍那”的胡语写本其繁简程度介于印度语言与汉文之间,它的出现,体现了敦煌及周边民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能动作用,其在一次讲座中更指出这些或繁或简的写本,可能都成为西游记成型中之一环,神猴哈奴曼的形象亦由此渐渐变为猴行者,更变为孙悟空。
二、杨富学先生的吐蕃、回鹘学研究
杨富学先生此书更对敦煌吐蕃文献反映之吐蕃前弘期的历史、摩诃衍禅法在藏地的流传以及吐蕃习俗之影响敦煌作了阐述。其关于西域及敦煌吐蕃佛僧饮酒风俗之探索颇有意趣。按说,酒乃佛家第一戒,无论小乘抑或大乘,酒戒皆极严,而吐蕃统治敦煌之前亦无文书记载其寺僧人饮酒。然自从吐蕃入主敦煌,寺院账中开始频频出现酒类。杨氏以为,这或与佛教戒律的推行大大晚于佛教的流行有关。早期吐蕃一直有信无戒,加之后来流行雪域的藏传佛教密宗以为酒对修上密之僧是一种方便,故其不以饮酒为破戒。另外,雪域高原极为寒冷,僧人信徒亦需酒肉御寒,顺利过冬,杨氏以为这或当亦为其不戒酒乃至不戒肉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饮酒在佛家中亦不算了不得的大过。饮酒属于遮戒而非性戒,即其本身并非恶行,但行此易乱性,或致罪生,故戒之。在佛法初兴时本不禁之,犍陀罗、中亚地方寺院酿酒属于常态,出土文物多见其图像,中古中国僧人饮酒亦不限于敦煌、西域,即长安寺院僧众饮酒乃至食肉亦比比皆是,亦颇有以酒斋僧者。玄宗开元十二年特颁令强调不得食酒肉之戒律,然仍禁不止。中古僧传中多记僧院酿酒,僧人饮酒事。而据部分文献所记,类酒而无酒色味之胡酒三勒浆、加入苦物之葡萄酒等,皆不被视为酒,可供饮用。而以酒入药,僧服用之亦非属破戒②孙英刚:《两个长安——唐代寺院的宗教信仰与日常饮食》,《文史哲》2019年第4期,第56~60页。。是故敦煌僧饮酒,非全因吐蕃之故。此似失察。
在关注出土文献的同时,此书亦体现出对传统史传等传世文献的利用,如其“论黠戛斯在西域的进出”和“摩尼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前者利用武宗朝宰相李德裕之文集,后者采《册府元龟》之朝贡记载,论证详实可信。
杨氏定义回鹘佛教为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此言精到。杨富学先生为回鹘佛教研究之大家,其学术生涯最初起步即在回鹘佛教研究。已出《回鹘之佛教》、《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等书数部,其在书中指出,所谓回鹘文佛教典籍原本最大量的实来自于汉地,多为汉文大乘经典、伪经和宗派著述(禅籍尤为突出),回鹘佛教壁画艺术亦多取法汉风,自身民族特色并不明显。其他诸如未来佛弥勒崇拜、观音崇拜、文殊与五台山崇拜等等亦多源自汉地。
作为一位杰出的维吾尔学家,杨富学先生对回鹘-维吾尔文深有研究。在第十四章《多种文字在古代维吾尔族中的行用》中,杨氏对回鹘文的来源进行了辨析,驳议了其源于叙利亚福音字母的假说,而肯定了源出粟特文之说,而回鹘文之创制,正与睿息等粟特摩尼师相关。由于回鹘人文化发达,故成为后来之蒙古统治者之师,促成了回鹘式蒙古文的形成,即所谓老蒙文;而蒙文与蒙古文化又深深影响了满族,满文即仿蒙文而创,而满文的行用又促成了锡伯文的形成。不仅如此,据杨氏考证,契丹小字的创制,亦确实借鉴了回鹘文的部分因素,其受到了回鹘语拼音法规则的直接影响,可见回鹘文化影响之大。只是在回鹘全面伊斯兰化之后,渐渐放弃了祖先的回鹘文而改从阿拉伯文。自此回鹘文在新疆被彻底摒弃,取而代之的是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所谓“察合台文”,进而演化为老维文。相反,回鹘语和回鹘文化在同文同祖的河西裕固族中则得以残留。
这里要说到的就是杨先生此书数个重要意义之一——呼吁复原回鹘文,倡导复兴回鹘文化。《裕固学与河西回鹘关系漫议》中提到,从最近发现的回鹘文文献看来,裕固族人晚至18世纪以后才彻底放弃回鹘文,至今其族有语言而无文字,而东西裕固语皆属粘连语,便于回鹘文的拼写。杨先生认为,古回鹘文化的研究,担子现在就落在裕固族与裕固学的肩上。杨氏此倡甚有其合理性,若果能成功,其为回鹘之一大功臣矣,是书是文亦堪为不朽矣。
三、杨富学先生的夏、元洞窟研究
杨富学先生对于西夏学、元史学特别是元代河西西域史地之学亦颇精通,近来研究多关注莫高窟、榆林窟、文殊山石窟、山嘴沟石窟等之夏、元壁画,颇有独到之心得。这在其《少数民族对敦煌文化的贡献》等章中得以体现。杨氏感于过往西夏学者多半误读真正的西夏艺术风格,又错将西夏晚期的艺术风格扩大化,且混淆了西夏和元代的界限,遂在多文中力辟之。其曾指出通常以为的“大红大绿”亦即继承曹氏归义军晚期风格的壁画艺术并非属于西夏,其与山嘴沟石窟、阿尔寨石窟等真正的西夏石窟画风迥异,而很多石窟出现的夏汉双文榜题则实属于西夏亡后元代的产物,多处可见的包括西夏文在内的多语种书“六字真言”,亦非流行于西夏时期,即过去被认定为属西夏的铁证——上师帽,如今看来亦非仅盛于西夏。
但话又说回来,回鹘、西夏与元风石窟之代际划分本就是困扰学界之大难题,回鹘(沙州回鹘)存在于归义军与西夏的夹缝中,虽其统治敦煌不过数十年,然其较高的文明程度深深影响了西夏,很多西夏上师,本皆回鹘僧人,乃至《西夏文大藏经》亦回鹘僧主持修撰。易代之后,西夏文明又深刻影响了元代,元代河西大部分文献仍由西夏文写成,石窟亦在西夏人的设计下施工,故二者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混淆不清。在此书形成早期,杨先生惑于成说,以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榆林窟第3窟等为西夏修成,而今书则体现其最新研究成果,将之归入元代,具体论证可见其新作《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①杨富学:《莫高窟第61窟甬道为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西夏学》2017年第2期。。
杨先生本治回鹘佛教与摩尼教文献,然因感于敦煌晚期石窟分期断代的混乱:本来各具特色的回鹘、西夏及蒙古时期洞窟被杂混在一起,故而今年投入精力于石窟甄别尤多,取得的成就也颇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除上述石窟分期著述外,近年来对伊斯兰教,特别是敦煌之伊斯兰文化亦有所涉及,此一问题也间接关乎敦煌晚期石窟的分期问题。此书首章第七节《敦煌各族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略为言之,其以为《莫高窟六字真言偈》和锁阳城之圆形城角足见伊斯兰文化对瓜沙影响之一斑。其具体论述可见其最新发表之《元代伊斯兰文化觅踪》②杨富学:《元代敦煌伊斯兰文化觅踪》,《敦煌研究》2018年第2期。。此亦旧稿未曾有之处,今特增益之。虽然保持收入论文集之旧论文的原始面貌为多数学者所遵从,包括杨氏另一部著述《回鹘文佛教文献研究》亦如此,然既有新证以推翻旧论,又何必墨守旧说,误导后人呢?斯为《探幽》一书胜于多数学者论文集之处。
四、一点缺憾
当然,杨氏此书也并非尽善尽美,个别陈旧的说法仍未改从新说,一些对古民族由来之推测亦不同于今日最新之考古结论。较为明显的一处见其书第九章《宗教与甘州回鹘之外交》,其第199页谈及张承奉的西汉金山国时,仍沿用唐天祐三年(906)建国之说,而事实上此说硬伤极多,并不合乎情理。按金山国建国时间假说极多,荣新江先生的910年说已为广大学界所接受;杨宝玉、吴丽娱的909年建国说由于有《皇极经世书》为佐证③(北宋)邵雍:《皇极经世书》卷六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第八〇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8页;杨宝玉、吴丽娱:《归义军政权与中央关系研究— —以入奏活动为中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3页。,亦得到一定认可;余与杨先生近日在《敦煌写卷“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一文中提出的908年建国④杨富学、盖佳择:《敦煌写卷落蕃诗创作年代再探》,刘进宝主编:《丝路文明》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36~138页。亦可备一说,遗憾的是杨先生不慎忽略了这个问题。而其第二章《河西考古学文化与月氏、乌孙之关系》或亦存在武断之处。杨先生关注河西之骟马文化、沙井文化,注意到它们都是兴起于公元前一千年前后,而其活动空间都落在了张骞所云月氏、乌孙二族所生活之“祁连、敦煌间”,故依据旧说试为定论:所谓“骟马文化”,当即乌孙之族,“沙井文化”,实即月氏之族。杨先生亦有一系列文献与考古学方面之证据支持其说。杨氏断沙井文化为月氏之证据主要有如下几点:月氏与沙井文化所处地域相同,又皆以定居畜牧业为主,且两者似乎皆非河西本地部族,推测或为自北迁来,而沙井文化中断于秦汉时期,据史书,是时匈奴霸河西,逐走月氏。两者于时空上的惊人吻合当为其是一非二之例证。而骟马文化所以为乌孙,则因二者皆为定居牧业经济,并辅以一定的简单农业,新疆昭苏发现的乌孙墓中出土铁铧与敦煌发现的西汉铜铧形制一致,亦堪为其证。而骟马文化所处地域虽与当地之四坝文化重合,然面貌各异,似亦佐证其为自外迁入,而其文化遗迹较之沙井文化为少,似亦印证了乌孙弱于月氏的事实。
然而据西北大学王建新教授及其团队的最新考古研究成果①见新闻《寻找大月氏》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6294749602240314&wfr=spider&for=pc等。,已初步确认古代月氏在中国境内的原居地应该是以东天山为中心的区域;约公元前500年至前200年期间,生活在东天山地区的游牧人群正为月氏人。王教授指出,《史记》“始月氏居祁连敦煌间”中之祁连,并非是指今天的祁连山,而是指天山,具体即东天山。东天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作“祁连山”“天山”或“祁连天山”。祁连山为音译,天山为意译,而“祁连天山”则为音译加意译之名称。今天的祁连山在汉代文献中被称为“南山”,昆仑山则称为“西域南山”。而在汉代文献中,南山和祁连山曾在一段话中同时出现,足见所指非一。经考察研究,其复发现,敦煌附近,草场贫瘠,空间狭小,诚难以支持一个或更多大部族生活,而东天山则恰好存在足够游牧部族发展繁衍的广阔空间。笔者深以为然。实按,张骞所谓“敦煌”,当即“敦薨”,而根据《山海经》,敦薨之山、敦薨之水皆在今焉耆附近,恰好临近东天山,泛义来说,“敦薨”或指焉耆、天山以至今敦煌的广阔地域。是故“祁连、敦煌间”实当理解为月氏、乌孙部族居于敦薨山与祁连(天山)之间——如此,近世学者诚误读张骞,误读《史记》多年矣。经过十八年的艰苦考古历程,王建新团队在东天山发现很多大型游牧聚落,故王氏据此得出结论:自公元前1000年以来,在东天山地区先后分布过两类游牧文化遗存,而月氏的文化即为其中之一,而另一种则或为乌孙。杨先生相关文章撰述较早,故而未能参考最新成果,诚为憾事也,但仍不失为很有说服力的一说,可与王建新之考古资料相砥砺,有助于推进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虽然其中亦难免有少数承袭旧误之处,但整体而言,这部著作是十分成功的,其所涉领域极广,其所论古国与古今民族甚多,所提假说极为大胆,多为前人所不敢论,论而无敢深入阐发者。作为国内回鹘学与裕固学之开路人之一,杨富学先生此书继续于此领域拓荒,对吐蕃、党项、契丹、蒙古诸民族的研究亦多有推进,其异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与独辟蹊径之探索思路,给予后辈学者之学术启迪必将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