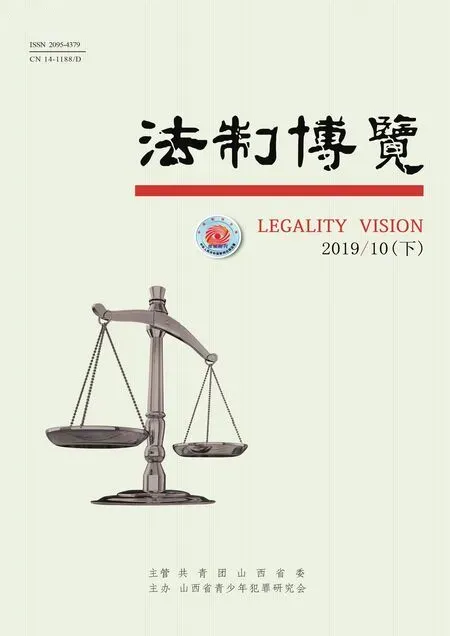关于古琴曲打谱者知识产权法律地位之考察
2019-12-13李根
李 根
国浩律师(天津)事务所,天津 300051
古琴曲的“打谱”指按照琴谱演奏出琴曲的过程。当打谱者的成果被他人未经许可使用时,便产生了该成果能否、如何以及何种程度上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问题。
一、关于打谱
古琴琴谱多由传谱、解题及歌词部分组成。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古琴传谱为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碣石调幽兰》谱,也是已知唯一的文字谱,即使用文字描述演奏法。宋代以降,特别是明清两代所辑琴曲多用减字谱记载。减字谱“字简而义尽,文约而音赅”,其以特定术语表示左手按弦指法和右手弹奏指法,沿用至今。减字谱一方面降低了记谱难度,相当大程度上促进了琴曲的流传,另一方面也给古琴演奏设置了极高的门槛。鉴于减字谱只记录弦位与演奏指法,而不记录节奏、节拍与音高的特性,打谱便成为古琴解读与演绎的必经之途与必学之技。
二、关于打谱是否产生知识产权法上的作品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相关理论研究中认为“作品”需具备下述三个要素:作品必须是人类的智力成果;作品必须是能够被他人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只有具有“独创性”的外在表达才是作品。打谱作为古琴曲演绎中的必要环节显然满足前两个条件,是否具备独创性便成了其能否成为著作权法上的作品的决定性因素。
目前,对打谱是否产生著作权法上的作品有两种看法:
(一)打谱者为纯粹的表演者,打谱不产生知识产权法上的作品
现出版界与法律界多持此观点。以案举例,古琴大师查阜西子女在2008年以文化艺术出版社等擅自出版《存见古琴曲普辑览》一书侵犯了查阜西的著作权为由提起其他著作财产权纠纷之诉,主张案涉书籍的著作权仍处于法律规定的保护期内,该著作财产权依据继承法转归二原告享有,后本案以调解方式结案。2015年,查阜西子女又因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在未取得其授权的情况下收录、出版了查阜西的古琴演奏录音,侵犯了查阜西的著作权为由提起诉讼;被告则回应表示,古琴曲自古流传至今,查阜西为演奏者而非作者,依现行法律不能主张著作权。后因原告之一、查阜西先生之子查克承去世,本案再未见消息,也因此未能借个案推动法律理论及实务操作上的进步。
(二)打谱者为古琴曲的合作作者,打谱产生知识产权法上的作品
也有学者指出,打谱者为古琴曲的合作作者。其认为打谱者属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者,打谱实质上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跨越千百年时空的“合作”,原谱之音符与诠释者创作之节奏的关系,相当于漫画中作画与对白的关系,单独把任何一项抽出来都无法成为完整的漫画作品。进而指出,打谱者作为古琴曲的合作作者,琴曲被打谱者诠释即形成了作品,故也应享有著作权。
三、笔者对打谱的理解
笔者认为,打谱为一种特殊的有限创作活动。理由如下:
(一)打谱的有限性
查阜西先生参与整理《琴曲集成》是目前编辑出版的最大规模的古代琴谱影印集成,其中收集了从唐代文字谱到清末民初千余年间的一百四十二种琴谱,包含琴曲数以千计。《琴曲集成》所辑古琴曲目中,大部是有曲名的,如为大众所熟知的《平沙落雁》、《梅花三弄》等。而多数曲目也都在传承与传播中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意境与意象,凡后世演绎者皆不能抛之而另立。
以《平沙落雁》为例,其最早的版本载于明末刊印的《古音正宗》。该谱中解题《平沙落雁》为“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后世对该曲解读也大抵如是,如清初《琴苑心传全编》解题“盖取清秋寥落之意,鸿雁飞鸣,秋中之景物也,故于此以写之”;清中期《萧立礼平沙落雁谱》则解为“按此曲本臞仙所作也。亦作有飞鸣吟、秋鸿、鹤鸣九皋诸曲,斯曲抑扬起伏疾徐之声,摹物理多、寡、聚、散、起、落、飞、鸣之神。”可见,对《平沙落雁》一曲的诠释,数百年来未离秋高气爽、风静沙平的意境,也未去秋雁成群、朝鸣夕宿的意象。不止《平沙落雁》,大凡粗通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提及“幽兰”、“梅花”等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较为固定的意象、情绪与氛围。
其次,作为文人雅趣的古琴曲打谱与演奏,必然受文人自身与文人群体审美取向的影响。中国两千余年尊崇经典的主流文化养成了文人的崇古情节,也使其在进行文化活动时,自觉或不自觉的与经典文化贴近。这也导致作为古琴曲演绎者的文人在打谱时,会在相当程度上驱动自身对琴曲的诠释更加贴近乃至完全还原琴曲命题者的本意,从而局限了打谱者仅从音乐审美出发对琴曲进行突破式创造的可能。
以上,琴曲的命题内涵与文人的崇古情节均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打谱者的自由发挥和打谱行为的“独”与“创”。即使是当代打谱者,大可将《流水》诠释为优山美地或波拉波拉,但绝无重新演绎成为西洋古堡或北海流冰的可能。无论从客观上还是主观上,打谱缺乏足够有独创性的表达,也当然不产生知识产权法律意义上的作品。
(二)打谱的创作性
如前述,打谱缺乏足够的独创性。但这决不意味打谱应被视为纯粹的表演。这是因为,打谱赋予古琴曲节奏,而节奏是“音乐”之所以成为音乐的基础。广义的音乐可以没有旋律与和声,但必须具有节奏。如格里格为诗剧《Peer Gynt》所写的《In the Hall of the Mountain King》一曲,仅随着节奏的加快,乐曲前后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又如崔健的歌曲,其和弦一般很少,甚至只有一个,但通过不同的节奏变化表现纤细或浩荡的情绪转折,也正是崔健歌曲的魅力之一。
因此,正是有了打谱者的创作,古琴曲的音符被有机组织起来,古琴曲最为人所称道的“韵”也随之诞生。尽管受琴曲命题与文人情节的限制,打谱也不是机械地将琴谱所载逐弦拨出,而也一定程度上融入了打谱者的个人思考,从而具备了一定的创作性。
四、打谱者的知识产权地位及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规定只有具备独创性的劳动成果才能成为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但对独创性中“创”的下限没有作出明文规定。前述查阜西案的“不了了之”也没能在法律实务上提供给从业者一个可参照分析的标准。故此,单从现行法律法规的角度而言,在尚无明确规定的前提下,直接将打谱者认定为作者或共同作者、以及认为打谱直接产生作品的看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然而,在党和国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如继续将打谱者看作单纯的表演者,则从鼓励创作、推广流传的角度来讲是不利的。为此,较为理想的解决方案,是从法律层面为以打谱为代表的特殊的有限创作活动设定权利并加以保护。
我国《著作权法》整体上接近大陆法系,区别了“著作权”和“邻接权”。如为上述特殊的有限创作活动设定权利,更为实际的选择是增加《著作权法》中邻接权的种类,而非将其认定为作品直接赋予打谱者著作权。原因在于,如将其视为作品进行保护,则必然导致个案处理时对作品独创性要求的模糊与混乱。同时,相比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我国《著作权法》中邻接权的种类明显偏少,已经难以满足当代社会知识产权多样态发展的要求。为以打谱为代表的特殊的有限创作活动设定新的“邻接权”,既可保护打谱者的劳动成果,避免“查氏争议”的再次发生;又可维护裁判中独创性标准的相对统一,使法律工作者以及相关从业者在面临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能够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