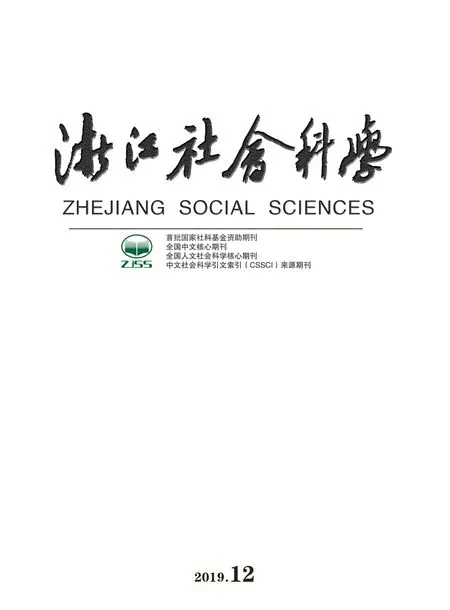天台山: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
2019-12-11胡可先
□胡可先
内容提要 集山水奇观与文化精萃于一体的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所在。由此可以从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唐代台州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空间、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特色、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唐人《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的意义、入唐僧圆仁与圆珍的行记与过所。综合起来可得出结论:作为浙东文化核心的天台山,是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南朝梁陶弘景《真诰》称:“天台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回八百里。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牛斗之分。以其上应台宿,光辅紫宸,故名天台。”①这是天台山命名的由来。东晋孙绰《游天台山赋》云:“天台山者,盖山岳之神秀者也。涉海则有方丈蓬莱,登陆则有四明天台,皆玄圣之所游化,灵仙之所窟宅。夫其峻极之状,嘉祥之美,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②孙绰为永嘉太守,即将解印以向幽寂,闻道天台神秀,令人图其状貌而遥为之赋,将天台山之秀美、媚丽与神奇和盘托出。以“佛宗道源,山水神秀”著称的天台山,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驻迹于此,留下了诸多华美的篇章。尤其是在唐代,天台山成为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
一、唐代台州的地理位置与文化空间
天台山在台州境内,台州也是因为境内有天台山而得名。台州与天台山在自然地理上紧密相连,在文化空间上更是融合无间。天台山的辐射意义更是超越了时空,产生了广泛的世界影响,其路径则为天台山——台州——浙东——全国——世界。而其集结点与交汇处则最为关涉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
(一)地理位置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台州》:“武德四年讨平李子通,于临海县置海州,五年改海州为台州,盖因天台山为名。……州境:东西三百九十三里,南北四百三十五里。八到:西北至上都四千五百里,西北至东都三千一百四十五里,正南微东至温州五百里,东至大海一百八十里,西北至越州四百七十五里,正西微南至处州四百九十里。……管县五:临海、唐兴、黄岩、乐安、宁海。”③这是关于台州地理位置较早而且是最为明确的记载。台州以境界有天台山,故以名州,而天台山就在台州所辖之唐兴县以北十里。唐兴县至宋代改名“台兴县”,又改名“天台县”,县名一直沿用到今天。
唐代中唐以后置浙东观察使,辖越州、台州、婺州、衢州、明州、处州、温州七州,治所在越州。台州是浙东观察使下属的一个州,治所在临海。天台山就地理空间而言,就成为浙东的一个标志,我们就唐代的东南驿路进行考察。
唐代通往浙东的道路,我们参考华林甫先生的《唐代两浙道驿路考》④,对于东南的驿馆进行梳理。唐代过了长江以后,通向东南的路程,其主要驿馆有:
通吴驿(润州)——秦潭驿(丹徒)——云阳驿(丹阳)——庱亭驿(丹阳)——常州驿——毗陵驿(常州)——望亭驿(苏州)——临水驿(苏州)——松江驿(苏州)——平望驿(苏州)——嘉禾驿(嘉兴)——石门驿(桐乡)——义亭驿(海宁)——临平驿(余杭)——樟亭驿(杭州)——西陵驿(萧山)——西亭驿(绍兴)——凫矶江馆(慈溪)——山源驿(奉化)——南陈馆(宁海)——宁溪馆(天台)——上浦馆(乐清)
东南的驿馆以长江与钱塘江为分界,形成了两个区域。从润州的通吴驿,向北过了长江就属于淮南区域,因此长江以南自润州开始就是两浙区域。从润州通吴驿到杭州樟亭驿是在浙西境内,樟亭驿在钱塘江北岸。过了钱塘江就到了萧山西陵驿,就进入了浙东境内。从西陵驿到乐清的上浦馆,就是唐代来往于浙东的主要道路,所谓“浙东唐诗之路”,其主要通道也就是在这一线。在这一通道之上,天台的宁溪馆就是一个关键的驿站。
在浙东区域的主要通道上,还有一条以剡溪为通道的水路,则是诗人经过浙东游览山水、领略风景的重要道路。这条道路在越州之前是与前面的驿站相同的,而过了越州之后,则走向曹娥埭,经过上虞江,到了剡县,再折入剡溪,更向天台山出发,中间经过新昌寨即今新昌县到天台山,进一步通向台州临海。在这条通道上,台州天台也是浙东道路的重要节点,而且在这条通道之上,留下的唐诗最多也最精彩。
(二)文化空间
台州以州中有天台山而命名,因而天台山文化就构成了台州文化的核心,由这样的文化核心又超越了台州扩大了半径而向整个浙东辐射。天台山之所以能够作为文化核心区域,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原因。
第一,文学创作的繁盛。东晋之时,章安令孙绰写下了著名的《游天台山赋》,成为“试掷地,当作金石声”⑤的千古名篇,自此赋问世之后,天台山文学与文化就源远流长。到了唐代,天台山更成为文学表现的重要空间,唐代诗人足迹遍布了天台的赤城、丹邱、华顶、琼台、石桥、瀑布、国清寺、桐柏观、委羽山、巾子山、括苍山、寒岩、楢溪等。吟咏这些名胜的诗篇在《全唐诗》等典籍中还留下了很多,成为天台山文学遗产的宝贵财富。
第二,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天台宗是中国汉地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对隋唐以后成立的各宗派很有影响。中晚唐时期,日本僧人最澄来华求法,将天台宗佛教传到日本,使这一宗派得到弘扬,一直到现在还不断扩大,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几个佛教宗派之一。到了北宋初年,僧人义天到宋朝求学,又把天台宗传到了朝鲜。
第三,道教南宗的发祥地。天台山是道教南宗的发祥地,也是全真派的祖庭,在中国道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道教由唐代的重外丹发展到宋代的重内丹,天台山道教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内丹学派创始于北宋的张伯端,他到天台桐柏宫修炼,能够融摄儒、释、道三教精华,并根据自己多年内丹修炼的体会,著述了《悟真篇》。这部书就完成于天台山桐柏宫,因此,桐柏宫成为道教南宗的祖庭,张伯端后来被尊为“紫阳真人”,成为道教南宗的祖师。
第四,中唐以后儒家文化的发达从而引导儒、释、道三者的融合。儒家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一是以陆淳为代表的台州长官是唐代的儒学宗师,陆质是《春秋》新学的代表,继承了赵匡、啖助的《春秋》学而对于唐代儒家革新起到重要作用;二是天台弟子梁肃等人也是儒学根基较深甚至深入骨髓之人,故成为以儒道为宗的中唐古文运动的前驱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台州是唐代儒释道融会程度最深的文化区域。
第五,唐代著名文人郑虔的遗迹和影响。郑虔因为安史之乱中被俘虏,唐肃宗于平虏之后,对于陷贼之人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处置,郑虔被贬为台州司户。台州的文化核心是天台山,因此,郑虔也就成为天台山文化的早期创造者之一。对于郑虔而言,被贬台州是很不幸的,而对于台州而言,则又是很幸运的。因为郑虔来到台州之后,对于台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人们纪念他,就建了郑广文祠,至今还在临海县城的望天台。我们也可以看出,台州以盛唐安史之乱为界,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史之乱北方和中原的战乱,也给南方带来了发展契机,人口南迁,经济南移,文化交融,这些都是重要发展方向。前些年,洛阳发现了《郑虔墓志》,为郑虔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原始材料,推动了郑虔研究的进展。
二、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与特色
唐代诗歌发达,浙东山水优美,文化鼎盛,加以佛寺道观繁多,诗人喜爱漫游访道,故而浙东成为诗人踪迹留存较多的地方,也是唐诗表现最为突出山水名胜之地。
(一)浙东唐诗之路的形成
浙东唐诗之路是唐代诗人由杭州渡过钱塘江之后,经行于浙东的通道。是融交通、风景、文化与诗歌为一体的地理空间和文化区域。在浙东留下诗歌的文人大致上具有这样四种类型:
一是漫游。唐代的诗人都向往浙东山水,大诗人李白、杜甫、孟浩然、高适、韦应物、刘长卿、戴叔伦、贾岛、姚合都有漫游浙东的经历,中唐时期的“大历十才子”至少有皇甫冉、李嘉祐、崔峒三人到过浙东。即如李白的《秋下荆门》《梦游天姥吟留别》《琼台》《天台晓望》《送杨山人归天台》,都是名垂千古的佳制。
二是隐居。因为浙东山水的优美,吸引着很多诗人隐居于此,甚至终老于此。比如晚唐诗人方干,是睦州桐庐人,属于浙西。应举不第后,即长期隐居于会稽镜湖。孙郃《方玄英先生传》云:“先生新安人,字雄飞。……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先生一举不得志,遂遁于会稽,渔于鉴湖,与郑仁规、李频、陶详为三益友。”⑥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七称他“湖北有茅斋,湖西有松岛,每风清月明,携稚子邻叟,轻棹往返,甚惬素心。所住水木幽閟,一草一花,俱能留客。家贫,蓄古琴,行吟醉卧以自娱”⑦。
三是做官。唐代文喜爱浙东山水,故而来到浙东做官,也留下了不少诗篇。即如元稹为浙东观察使期间,就写了很多诗篇,并结诗酒文会,接续东晋兰亭宴集的传统。有些来浙东做官者,本意非为做官,主要还是对浙东山水的向往。即如新近出土的《卢广墓志》记载他到剡县做官的情况:“补越州剡县尉。之官,遂吟曰:‘挂席日千里,长江乘便风。无心羡鸾凤,自若腾虚空。’时人望其止足之分,反若在丹霄之上。”⑧墓志表现出卢广一生崇尚道家的思想,其诗歌也表现出虚空出世的情怀。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作者对于浙东剡县风景的期待,其刚赴任时,即挂帆东去,乘江上顺风而一日千里,其赴剡县并不在于为官利禄,那么就有出世的情怀。
四是贬谪。唐代文人贬谪,以南方为多,湖南与岭南更是贬谪的处所。与浙东相关的贬谪文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贬到浙东做官的文人,如上文提到的郑虔就非常典型,他因为安史之乱陷入叛军而得罪,被贬为台州司户,作为宰相又兼诗人的王缙得罪后贬官括州刺史,再如像宋之问、李邕、徐浩等,都有贬谪浙东的经历;另一类是贬谪岭南的文人,经过浙东时留下了很多著名篇章,即如初唐时期王勃犯罪牵连其父贬官交趾,王勃随父赴官经过浙东即撰写了诗序多篇,再如宋之问被贬岭南经过浙东留下诗篇,后来遇赦北归又授台州司马,再后来由考功员外又被贬为越州长史,则是因贬谪与浙东发生多重关系的诗人。
唐代诗人漫游浙东,隐居浙东,为宦浙东,贬谪浙东,使得这一块区域文化发达,诗歌繁盛,据统计,唐代的剡县即现在的嵊州现存的唐诗就超过五百首,因此我们可以说,唐诗之路是唐代就形成的,是客观的,而且是永远留存的,是影响千古的。但“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却是当代产生的。
“浙东唐诗之路”概念是由浙东新昌地方文化名人竺岳兵先生于1991年5月提出的。是时他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研究会”上,提交了《剡溪——唐诗之路》的论文,认为沿曹娥江、剡溪至新昌、天台等地,是一个富有文化内涵的胜地。至1993年8月18日,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正式发函,同意成立“浙东唐诗之路”的专称。后来,竺岳兵自己又成立的“唐诗之路研究社”这一民间机构,对于新昌地方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随着唐代文学研究和区域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浙江省仅仅是一个县以下的民间机构研究浙东唐诗之路显然是不够的,因此,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指导下,在台州市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台州学院于2018年初专门成立了“浙东唐诗之路”研究所,并且与天台山文化、和合文化融为一体,整合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力量,这样就特别适合新世纪文化需求,也更与国家“一带一路”宏大规划完全合拍。而至2018年底,浙东各地即如绍兴、嵊州、新昌、仙居、金华等也都在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与开发上提出了各项实施计划。2019年11月3日,在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支持下,又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以浙东唐诗之路为重心,向全国诗路辐射。其成立大会就在新昌召开,同时确定第一次研讨会在将在台州学院召开。这就标志着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面向全国,走向世界。
(二)浙东唐诗之路的特色
竺岳兵在1991年提出唐诗之路以剡溪为中心,沿曹娥江、剡溪、天台等地。这样的提法当然有一定道理,而且“浙东唐诗之路”的命名权也理应归竺先生所有。但就唐代的浙东道路而言,这一区域也还有较大的局限性。我们知道,唐代东部地区的交通,都是以水路为主的,从杭州渡过钱塘江之后就到了浙东,根据水道和驿站的分布,自越州西陵驿到乐清上浦馆,无疑是浙东唐诗之路的重要通道。但从越州向东,沿钱塘江东行一直到明州,也是唐代诗人经行的通道,从杭州以西富阳对岸的渔浦潭开始入浦阳江又有一条通道通往诸暨、义乌向婺州方向,再到永嘉。即:渔浦潭——诸暨驿——待贤驿(诸暨)——双柏驿(义乌)——婺州水馆。因此,浙东唐诗之路从主要道路的分布来看,从杭州过了钱塘江进入浙东,就形成了一条干钱和两条支线的格局。这是浙东唐诗之路地理上的特色。
浙东迄今留下了超过1500首唐诗,是我们得以继承和弘扬的宝贵的遗产。即以越州而言,白居易《沃洲山禅院记》说:“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目。”⑨唐代越州,出现了不少著名诗人,骆宾王是临海人,贺知章是会稽人。他们在初盛唐诗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同时留下了吟咏越州的篇章。即如骆宾王《早发诸暨》诗:“征夫怀远路,夙驾上危峦。薄烟横绝巘,轻冻涩回湍。野雾连空暗,山风入曙寒。帝城临灞涘,禹穴枕江干。橘性行应化,蓬心去不安。独掩穷途泪,长歌行路难。”⑩而贺知章到八十余岁由秘书监告老还乡还作了《回乡偶书》二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销磨。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不仅越州本土诗人如此,流寓越州的诗人创作更为丰富。即如初唐时期的大诗人宋之问,曾被贬越州长史。尽管被贬,但到此乐土,仍然是幸运的,故言“虽叹出关远,始知临海趣。赏来空自多,理胜孰能喻”⑪。他“穷历剡溪山,置酒赋诗,流布京师,人人传讽”⑫。他尤其致力于律诗的创作,既精丽缜密,又流畅自然,达到情景交融的境地。如《泛镜湖南溪》:“乘兴入幽栖,舟行向日低。岩花候冬发,谷鸟作春啼。沓障开天小,丛篁夹路迷。犹闻可怜处,更在若邪溪。”⑬又《游禹穴回出若邪》后半:“石帆摇海上,天镜落湖中。水低寒云白,山边坠叶红。归舟何虑晚,日暮有樵风。”⑭此外,尚有《谒禹庙》《游法华寺》《早春泛镜湖》《游云门寺》《湖中别鉴上人》《游称心寺》诸作共二十余首。无论是越州本土诗人以其作品表达对于家乡的热爱,还是流寓诗人对于浙东的欣赏,无一例外地都受到越州山水美景的陶冶从而将真情流露于诗作当中。诗歌之外,散文如晋孙绰《游天台山赋》、王羲之《兰亭集序》之后,代有名作。小说自刘义庆《幽明录》所载刘晨、阮肇遇仙的故事也凄美动人,吴均《续齐谐记》亦收录这一故事,对于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是浙东唐诗之路文学上的特色。
浙东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魏晋以后,北方战乱,衣冠贵族大量南迁,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随着人口的南迁而与浙东文化融合,更使得越中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加以东晋门阀制度的盛行,士族势力,门阀势力,北方贵族,南方土著等各大利益集团汇聚在一地,组成了浙东文人集团。他们借江山之助,体物写志,留下了很多名垂千古的篇章。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东晋时期以王羲之为首的兰亭集会。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在会稽内史任,他和友人谢安、孙绰等聚于兰亭,饮酒赋诗,参加聚会者有官僚、文人与僧徒,都是一时名士。当时与会之人都有诗作,事后编辑成集,由王羲之作序与书写,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后来,每到三月上巳,越州多有修禊。唐代永淳二年,一批文士修禊于云门山王献之山亭,王勃作了《修禊于云门王献之山亭序》,其中有“永淳二年暮春三月,修祓禊于献之山亭也。迟迟风景出没,媚于郊原;片片仙云远近,生于林薄。杂花争发,非止桃蹊;迟鸟乱飞,有余莺谷。王孙春草,处处皆青;仲统芳园,家家并翠”⑮等描写,则很明显是与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脉相承的。谢灵运更在越中留下大量的诗作,名篇《石壁精舍还湖中作》《登池上楼》都是描写此中山水之作。宋代孔延之所编的《会稽掇英总集》,分门别类辑集了六朝以来对于会稽形胜与山水的吟咏,更可以看出六朝王羲之、谢灵运等人的流风余韵。这是浙东唐诗之路文化上的特色。
唐代浙东地区,是佛教和道教的圣地。天台山的国清寺、新昌的大佛寺、鄞县的天童寺,都是唐代甚为鼎盛的寺庙,沃洲山更是唐人景仰的佛教圣地,东晋高僧支道林曾于此“买山而隐”,养马坡谷,放鹤山峰,而沃洲禅院由白道猷开山,白寂然兴寺,白居易撰写《沃州山禅院记》,后世号称“三白堂”。道教胜地则有天台山的桐柏观,虽后来成为道教南宗祖庭,实则在唐代已经非常繁盛,迄今存世的唐代诗人崔尚撰写的《桐柏观碑》就是明证。这里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这里的佛教与道教融合无间,和合相处。这是浙东唐诗之路宗教上的特色。
唐代诗人自爱名山,喜欢漫游。李白《秋下荆门》诗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⑯,杜甫《壮游》诗说“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⑰,赵嘏《发剡中》诗说“南岩气爽横郛郭,天姥云晴拂寺楼”⑱,许浑《早发天台山中岩度关岭次天姥岑》诗说“来往天台天姥间,欲求真诀驻衰颜。星河半落岩前寺,云雾初开岭上关。丹壑树多风浩浩,碧溪苔浅水潺潺。可知刘阮逢人处,行尽深山又是山”⑲。这样的漫游影响了千年的浙东文脉。我们现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开发浙东唐诗之路,将文学与景观、山水融为一体,也是这一文脉的延伸。这是浙东唐诗之路旅游上的特色。
这样的五大特色,又集中于天台山一脉。因为天台山在唐代就汇集了山水美景的精萃,悬岩、峭壁、瀑布、幽谷,“穷山海之瑰富,尽人神之壮丽矣”;天台山是唐代诗人最为向往的地方,李白既有“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⑳的神往,又有“天台国清寺,天下为四绝”的赞叹;天台山文化源远流长,自晋室南渡,衣冠贵族如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庐江何氏、高平郗氏、北地傅氏、陈留阮氏、高阳许氏、乐安高氏、鲁国孔氏、颍川庾氏集聚于此,提高了当地的文化品位,促成了“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文风转变,唐代山水诗的兴盛也无疑渊源于此;天台山既是唐代佛教十宗之一天台宗的发源地,也是道教南宗的发祥地,其宗教影响不仅遍及国内,而且传至东瀛;天台山汇合了地理、山水、文学、文化、宗教之优长,对于当今的旅游开发也具有重要意义。以天台山为核心的浙东唐诗之路的特色,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图表形式(图1)表现其中的关联。

图1 浙东唐诗之路特色关系示意图
三、从台州到明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唐代浙东的海上口岸,是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其中从台州到明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当然,海上丝绸之路不止这一段道路,还有更南边的广州等地。比如1998年在南海发现的“黑石号沉船”载有唐代长沙窑瓷器,上面刻写不少唐诗,标志着唐诗由海上向全世界传播。而从台州进而到明州再向东亚各国的传播路线,是与浙东唐诗之路相关联和融会的海上丝路之一。
就台州与明州而言,从海上来中国的外国官员、商人、学生和僧徒,都要在台州或明州查验,发放“过所”才可以进行陆地上的各种活动。出了台州和明州口岸,向东可以到达日本,向南经过福建到达南海,出亚洲再向欧洲。我们这里重点谈一下与日本的交流。
纵观唐代将近三百年间,日本共派遣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包括“送唐客使”和“迎入唐使使”,而任命后成行者有十三次。这些遣唐使到达中国的登陆口岸大概分三个时期:7世纪30 至70年代,主要由北路进行,从日本滩波(大阪)登舟,沿日本内海到博多(福冈)出发,经过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在山东半岛口岸登陆,再西去洛阳到长安。7世纪70年代到8世纪60年代约一百年,因为日本与新罗关系紧张,故而遣唐使改由九州南下,经东海在长江口登陆,再沿运河北上去洛阳到长安。8世纪70年代以后,航线改由南路,也是由九州出发,向西南跨过东海,在长江口的明州、台州或苏州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三条航线,山东半岛最为安全,航行时间需30 天左右,但因国际关系问题,实际使用时间很短;长江口时间虽然也在三十天左右,但安全性不好,有时船只漂流到南海后倾覆。明州、台州登陆的时间较短,大约十天左右,但安全性与长江口岸登陆一样,都较为危险。这三个登陆口岸都连接中国和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国,我们都可以看成是海上丝路的起点,但其中只有台州、明州的口岸与浙东唐诗之路集结与交汇。
明州和台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应该早在盛唐时期。因为高僧鉴真和尚第四次东渡日本,在天宝三载(744年)从宁波经宁海,巡礼天台山国清寺,带去《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等天台宗的经典,这对于天台宗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但鉴真这次东渡并没有成功。到天宝十三载(754年),鉴真第六次东渡日本,才取得成功。到了日本以后,他大力弘扬天台宗教义,开辟了天台山与日本文化交流的新时代。鉴真弟子、台州开元寺(即临海龙兴寺)僧思托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第一位赴日的台州高僧。日本天台宗祖师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乘日本第十二次遣唐使藤葛野磨君的使船入唐,到天台山从行满大师学法。回到日本之后就创立了日本天台宗。后来继最澄衣钵成为日本天台宗祖师的圆仁、圆珍、圆载等,都曾入唐求法,得天台宗佛教精髓,回国后为日本佛教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出台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而这些入唐求法的高僧又以天台山为中心,台州天台山与日本的比睿山由海上通路相连,成为文化传播的最重要的标志。
明州是唐代的重要海港,外国使船从南方到达中国,主要从明州登陆,明州则成为主要贸易通道。由明州登陆后,再分散去全国各地。就贸易而言,明州港成为当时亚洲的三大贸易港之一。经过明州的日本遣唐使,重点是来唐学习先进文化,故而其核心访问区域也是天台山,实际上台州的天台山是日本遣唐使从明州登陆后从事文化交流最核心的地方。
四、唐人《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的意义
日本僧人来唐学法者众多,著名的高僧即有最澄、空海、圆行、圆仁、圆珍、惠远、宗睿、常晓,称为“入唐八家”。最澄学成返回日本后,在日本创立了天台宗。而最澄之所以能够创立天台宗,与其在天台山国清寺学法有着密切的关系。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是最澄于贞元二十一年返回日本国时,台州文武官员相送,并作诗饯别,留下了《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组诗。我们先根据相关典籍,将这组诗并序整理于下。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叙
过去诸佛,为求法故,或碎身如尘,或捐躯强虎。尝闻其说,今睹其人,日本沙门最澄,宿植善根,早知幻影,处世界而不著,等虚空而不凝,于有为而证无为,在烦恼而得解脱。闻中国故大师智顗,传如来心印于天台山,遂賫黄金涉巨海,不惮滔天之骇浪,不怖映日之惊鳌。外其身而身存,思其法而法得,大哉其求法也。以贞元二十年九月二十六日臻于海郡。谒太守陆公,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斑组二,火铁二加火石八。兰木九,水精珠一贯,陆公精孔门之奥旨,蕴经国之宏才,清比氷囊,明逾霜月,以纸等九物,达于庶使,返金于师。师译言:请货金贸纸,用以书天台止观。陆公从之,乃命大师门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写之,逾月而毕,邃公亦开宗指审焉。最澄忻然瞻仰,作礼而去,三月初吉,遐方景浓。酌新茗以饯行,对春风以送远,上人还国谒奏,知我唐圣君之御宇也。
贞元二十一年巳日台州司马吴顗叙
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
台州司马吴顗
重译越沧溟,来求观行经。
问乡朝指日,寻路夜看星。
得法心愈喜,乘杯体自宁。
扶桑一念到,风水岂劳形。
台州录事参军孟光
往岁来求请,新年受法归。
众香随贝叶,一雨润禅衣。
素舸轻翻浪,征帆背落晖。
遥知到本国,相见道流稀。
台州临海县令毛涣
万里求文教,王春怆别离。
来传不住相,归集祖行诗。
举笔论蕃意,梵香问汉仪。
莫言沧海阔,杯度自应知。
乡贡进士崔謩
一叶来自东,路在沧溟中。
远思日边国,却逐波上风。
问法言语异,传经文字同。
何当至本处,定作玄门宗。
广文馆进士全济时
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
来求贝叶偈,还过海龙宫。
流水随归处,征帆远向东。
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
天台沙门行满
异域乡音别,观心法性同。
来时求半偈,去罢悟真空。
贝叶翻经疏,归程大海东。
何当到本国,继踵大师风。
天台归真弟子许兰
道高心转实,德重意唯坚。
不惧洪波远,中华访法缘。
精勤同慧可,广学等弥天。
归到扶桑国,迎人拥海堧。
天台僧幻梦
却返扶桑路,还乘旧叶船。
上潮看浸日,翻浪欲滔天。
求宿宁逾日,云行讵隔年!
远将乾竺法,归去化生缘。
前国子监明经林晕
求获真乘妙,言归倍有情。
玄关心地得,乡思日边生。
作梵慈云布,浮杯涨海清。
看看达彼岸,长老散华迎。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诗歌为中心的中日交流活动,其地点在浙东的台州,又是最澄要启航归国的地点,故而可以说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因此,这组诗最重要的价值就是能够作为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的标志。与此相关,我们重点谈一下这组诗涉及的三个问题。
一是最澄的行历。最澄于贞元二十年(804年)七月六日,搭乘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第二舶石川道益之船从日本筑紫(今福冈)出发,航行五十余日,于九月一日抵达明州之鄮县。九月十二日,最澄前往台州拿到公验,十五日,与弟子兼译语僧义真、行者丹福成启程前往台州。抵达台州之后,即拜谒台州刺史陆淳,“献金十五两,筑紫斐纸二百张,筑紫笔二管,筑紫墨四挺,刀子一,加斑组二,火铁二加火石八。兰木九,水精珠一贯。”陆淳就是陆质,永贞革新的代表人物,其名因为犯唐宪宗李淳之讳,故改名陆质。最澄此行,目的在于“求妙法于天台,学一心于银地”。十二月,最澄随道邃上天台山,在修禅寺遇道邃同门行满法师,二人颇为投契,行满“倾以法财,舍以法宝”。十二月七日,最澄复至山下国清寺,并和义真一同受具足戒毕,《显戒论缘起》中还录有义真的戒牒。贞元二十一年三月,最澄结束台州的行程,四月返抵明州。但彼时离遣唐使团启航返日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于是最澄又向明州官府请求前往越州巡礼。四月中旬,最澄抵达越州,于越州龙兴寺遇顺晓法师,继而受善无畏三藏直传的秘密灌顶,又受其付法印记。五月,复返明州。五月中旬,最澄将在唐期间所获全部经论整理汇集,编制成一卷《日本国求法僧最澄目录》(即后来的《传教大师请来目录》),并求得明州刺史郑审则赐官方印记。五月十九日,最澄改乘遣唐使第一船,从明州望海镇(今宁波镇海)起碇归国,六月五日平安抵达日本的对马岛,为期将近一年的入唐求法之旅至此真正结束。
二是送行时的台州府官员、文人与僧徒。首先值得关注的是诗序当中提到的台州刺史陆淳,也是给最澄签发过所的长官。他是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焦点人物,同时也是与唐代政治、学术、文学都很有关联之人。就政治而言,因为他在罢任台州刺史之后被征为给事中,就入朝参加了在当时和后世极具影响的“永贞革新”,并为皇太子侍读,未几病卒。从学术上看,陆质是唐代著名的儒学大师,是《春秋》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研究经学,注重会通,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精神,其立足点是对旧学的否定,因而在当时和后世被视为“异儒”。著有《集注春秋》二十卷、《类礼》二十卷、《君臣图翼》二十五卷等。永贞革新的代表人物都是陆质的弟子。陆质《春秋》之学,是永贞革新的思想基础。从文学上看,当时从陆质学者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韩泰等都是著名的文学家,陆质即置身其中成为文学与学术兼长的代表人物。陆质的文章,《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全唐文补编》都有收录,尚存多篇。陆淳之诗,《全唐诗》不载只字,但日本比睿山无量院沙门慈本在文久二年(1862年)所撰的《天台霞标》第四篇第一卷收陆淳诗一首,诗名题为《台州刺史陆淳送最澄阇梨还日本》:“海东国主尊台教,遣僧来听妙法华。归来香风满衣裓,讲堂日出映朝霞。”这首诗是否为陆淳所作,近来学者有所怀疑。但就其所言情事,再与台州官员送最澄诗比照,作为陆淳所作,应该不是空穴来风。诗歌也写得很好,首句叙说最澄来台州的原因是因为日本皇帝尊崇天台山佛教,次句叙说最澄受日本天皇的委派来台州听授《妙法莲华经》的过程,三句则言最澄归国的情况,设想其香火旺盛,布满僧衣,四句设想最澄弘扬教义的情景,讲堂与朝霞相映,是对最澄最好的赞美。全诗语言朴素明畅,情景真切。
其他官员、文人及僧徒的诗作都是五言律诗,台州诗人以五言律诗的形式创作送赠最澄之组诗。从内容上看,这九首诗作皆以《送最澄上人还日本国》为题,虽作者不同,但在风格上却显示出高度的统一,表现出对于最澄入唐求法的赞美之情,对于最澄求法成功回归日本,既有祝愿,也表现出难舍难分的伤情惜别之情,更有对最澄求法而成的祝福与未来学佛之路的期许之情。我们举一首广文馆进士全济时的诗作以见一斑:“家与扶桑近,烟波望不穷。来求贝叶偈,还过海龙宫。流水随归处,征帆远向东。相思渺无畔,应使梦魂通。”这首诗首联写最澄居于海东之日本,近于扶桑,大海一望无际。次联言其为了求法而远过大海。三联言学成回国远随流水而征帆向东。尾联则由送行分别而表现出相思之情,不因大海的阻隔而与魂梦相通。
从这组诗产生的地点,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定位:它是一组群体所作的诗歌,其地点就在浙东唐诗之路最东端的大海之滨,同时这里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因此这组诗就远远超越文学、宗教的意义,而成为文化、地理等多方面集中的标志。
三是有关这组诗还可延伸考察的方面是最澄回国后,日本嵯峨天皇、仲雄王、巨势识人与最澄的唱和诗。最澄卒后,嵯峨天皇还作有哀挽诗。这些唱和诗和哀挽诗都与天台宗佛教相关。嵯峨天
皇《答澄公奉献诗》云:
远傅南岳教,夏久老天台。
杖锡凌溟海,蹑虚历蓬莱。
朝家无英俊,法侣隐贤才。
形体风尘隔,威仪律范开。
袒肩临江上,洗足踏岩隈。
梵语翻经阁,钟声听香台。
经行人事少,宴坐岁华催。
羽客亲讲席,山精供茶杯。
深房春不暖,花雨自然来。
赖有护持力,定知绝轮回。
又《和澄公卧病述怀之作》诗云:
闻公云峰里,卧病欲契真。
对境知皆幻,观空厌此身。
栢暗禅庭寂,花明梵宇春。
莫嫌应化久,为济梦中人。
又《哭澄上人》诗云:
吁嗟双树下,摄化契如如。
惠远名仍驻,支公业已虚。
草深新庙塔,松掩旧禅居。
灯焰残空座,香烟绕像炉。
苍生稍集少,缁侣律仪疎。
法体何久住,尘心伤有余。
仲雄王《和澄上人卧病述怀之作》诗云:
古寺北林下,高僧毛骨清。
天台萝月思,佛陇白云情。
院静芭蕉色,廊虚钟梵声。
卧痾如入定,山鸟独来鸣。
巨势识人《和澄上人卧病述怀之作》诗云:
吾师山上寺,托疾卧云烟。
猿鸟狎梵宇,鬼神护法筵。
涧花当佛咲,峰月向僧悬。
已觉非真有,观身自得痊。
这些诗当然都不是在唐土所作,而是在最澄回国后与自天皇到贵族之间的唱和,甚至在最澄死后,天皇还作诗哀悼表示其痛挽之情。这在当时的日本,应该是一件代表国家的大事。“在日本历史上,嵯峨天皇享有崇高的地位。擅长汉诗、书法,并且成就很高,连音律都有相当的造诣。……嵯峨天皇的传世之作,以现存《光定戒牒》《哭澄上人诗》等最负盛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诗中还呈现出受天台以至浙东佛教影响的痕迹。几首诗都表现了对最澄回到日本国创立和弘扬天台宗的赞美之情,对于最澄的卧病,更是给予了极大的关切和安尉,尤其是最澄死后天皇的哀挽诗,将其比之于庐山的高僧慧远和沃洲的高僧支遁,崇敬与哀悼之意蕴藏于字里行间。这首诗至今还有嵯峨天皇的墨迹流传,成为日本书法的珍宝。
五、入唐僧圆仁与圆珍的行记与过所
圆珍和圆仁都是“入唐八家”中的僧人,他们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中国接受了天台宗的佛法,并且在回到日本后大力弘扬,圆仁为日本天台宗的第三代宗主,圆珍成为第五代宗主。
(一)圆仁
圆仁(793—864),俗姓壬生,下野国(今枥木县)人。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创始人。开成三年(838年),圆仁以请益僧身份随遣唐使到中国求法,随后在扬州开元寺、五台山大华严寺、竹林寺习天台教义,抄写天台典籍。不久入长安,住资圣寺,又从大兴善寺元政、青龙寺法全、义真等受密法,历时10年。因武宗禁佛,故其于宣宗大中元年携带佛教经疏、仪轨、法器等回国,于比睿山建立总寺院,弘传密教和天台教义。卒后,清和天皇赐慈觉大师谥号。圆仁著作百余部,最著名的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四卷。该书详述其亲历唐文宗、武宗、宣宗三代所见的佛教情况,史料价值极高。而在巡礼行记中可以看出,求佛于天台是其本来的愿望。《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云:
八月一日早朝,大使到州衙见扬府都督李相公,事毕归来。斋后,请益、留学两僧出牒于使衙,请向台州国清寺,兼请被给水手丁胜小麿,仕充求法驰仕。暮际,依大使宣,为果海中誓愿事,向开元寺看定闲院。三纲老僧卅有余,共来慰问。巡礼毕,归店馆。
三日,请令请益僧等向台州之状,使牒达扬府了。为画造妙见菩萨、四王像,令画师向寺里。而有所由制不许外国人滥入寺家,三纲等不令画造佛像。仍使牒达相公,未有报牒。
四日早朝,有报牒。大使赠土物于李相公,彼相公不受,还却之。又始今日充生料每物不备。斋后,从扬府将覆问书来。彼状称:“还学僧圆仁、沙弥惟正、惟晓、水手丁雄满,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便住台州,为复从台州却来,赴上都去;留学僧圆载,沙弥仁好,伴始满,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便住台州,为复从台州却来,赴上都去者。”即答书云:“还学僧圆仁,右请往台州国清寺寻师决疑,若彼州无师,更赴上都,兼经过诸州。留学问僧圆载,右请往台州国清寺随师学问,若彼州全无人法,或上都觅法,经过诸州访觅者。”又得使宣称,画像之事,为卜筮有忌,停止既了,须明年将发归时,奉画供养者。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圆仁从开成三年(838年)六月十三日开始到宣宗大中元年(847年)返回日本国,前后长达九年。而圆仁的目的是要到天台山国清寺求法,但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朝廷和州府的批准,不得不在扬州住了半年多。无奈之下就想随同遣唐使一起回日本。但船到楚州的时候,他和新罗译语金正南说:“到密州界留住人家,朝贡船发,隐居山里,便向天台,兼往长安。”还是想暗中向天台山求法。但这个目的仍未达到,被迫搭乘遣唐使船回国,恰巧船在海上遇风,飘回了文登县赤山湾。因为巡礼天台山得不到唐代官府的批准,于是圆仁只好改变初衷,将目的地改为五台山。而他之所以要到五台山,实际上主要还是与天台佛教的关联。《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云:
三僧为向天台,忘归国之意,留在赤山院。每问行李:向南去道路绝远;闻道向北巡礼有五台山,去此二千余里,计南远北近。又闻有天台和尚法号志远,文鉴座主兼天台玄素座主之弟子,今在五台山修《法花》三昧,传天台教迹。……常闻台山胜迹,甚有奇特,深喜近于圣境;暂休向天台之议,更发入五台之意。
说明圆仁来唐志在学习天台佛教,虽未遂天台山巡礼之愿,但在五台山从天台和尚志远,亦得天台宗精髓。圆仁回国后登比睿山,设灌顶台,建根本观音堂、法华总持院,弘扬佛教天台宗和密宗,在日本佛教史和中日佛教交流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由《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记载的圆仁求法过程,虽然未得在天台山求法,但因天台山佛教的影响,仍然在五台山从天台和尚志远学习,而后在日本大力弘扬天台宗。这就足以说明天台山佛教成为中国佛教的核心地,其辐射不仅在全国各地,更达到了邻国日本。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圆仁书中所记的留学僧圆载曾在台州国清寺。圆载(?—877),日本大和(今奈良县)人,最澄弟子。唐开成三年(838年),其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巡礼,先在天台山国清寺求法,后来到长安青龙寺从法全学得两部大法,在唐三十九年。唐僖宗乾符四年,至吴淞江口的青龙镇隆福寺,准备搭商人李延孝船归国。当时吴地诗人皮日休、陆龟蒙、颜萱奉命相送,并作有送行诗,亦为中日交流史上的重要环节,也为唐代文学史留下了辉煌篇章。皮日休有《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诗,陆龟蒙有《和袭美重送圆载上人归日本国》《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以送》诗,颜萱亦有《送圆载上人》诗。但不幸的是,圆载在归国途中,遇大风暴,船被颠覆,溺水而死。
(二)圆珍
圆珍(814—891),俗姓和气,字远尘,赞岐国(今香川县)人,空海俗甥。他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寺门派创始人。圆珍的主要著作有《法华论记》《法华玄义略要》《大日经指归》《讲演法华仪》等,所著《授决集》二集。圆珍既是僧人,亦为诗人。圆珍即将赴唐时,在日本国的鸿胪馆作《昨日鸿胪北馆门楼游行一绝七言》:“鸿胪门楼掩海生,四邻观望散人情。遇然圣裂游上嬉,一杯仙药奉霄青。”又作《怀秋思故乡诗一首七言》:“日落西郊偏忆乡,秋深明月破人肠。亭前满露蝉声乱,霜雁天边一带长。尽夜吟诗还四望,一轮挂叶落四方。一年未在鸿胪馆,诗兴千船入文章。”尤其后者,情思悠远,怀乡之情与秋日之景融会,加以“折腰体”诗格的运用,形成前后映照,堪称诗中佳制。
圆珍的入唐行历,据日本学者佐藤长门《入唐僧圆珍: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有专门的考证,参考佐藤的考证,我们梳理出圆珍入唐所经之地甚多,而其与天台山的关系主要有两个时段:
一是圆珍于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四月十五日从平安京出发,但没有赶上遣唐使的船只,只好界住城山四王院等待。待到下一年闰八月,才有机会随遣唐使之船入唐。大中七年七月十六日出发,八月九日到流求(台湾)。后来经过海口镇(福清)进入福州,请求都督府公验。大中七年九月十四公验记录如下内容:“为巡礼天台山、五台山及长安青龙、兴善寺等,寻求圣教,来到圣府。”九月二十八日,又从海路前往温州,十一月初到达温州,住开元寺。二十六日,到达台州开元寺,遇到曾经同在贞元二十年十二月于国清寺受戒的老僧知建。十二月九日又从台州出发,抵达唐兴县,即现在的天台县。十三日到达天台国清寺。大中八年,圆珍在天台山主要是巡礼遗迹和抄写经典。二月九日,前往禅林寺,拜谒智顗、湛然、智晞禅师之墓,抄写了寺内的碑文。十八日,登上天台山华顶,数日后返回国清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抄写天台山教法两百卷。九月七日,前往越州。二十日,抵达越州城南门。三月十九日,越州都督府下发过所,圆珍开始前往长安。
二是大中十年六月四日,圆珍又由长安回到国清寺。这时主要是勤奋校勘《大日经义释》,并在国清寺止观院造止观堂。当时越州商人詹景全、刘仕献,渤海国商主李延孝、吴英觉等施钱四千文,建造住房三间,实现了祖师最澄的心愿。这些建筑统称为“天台国清寺日本国大德僧院”。大中十一年十月,圆珍编写了《日本比丘圆珍入唐目录》。十二年二月,前往台州拜访刺史严修睦。闰二月乞求台州刺史颁发回国公验,直至四月八日获批。此后开始编《入唐求法总目录》。大中十二年六月八日,圆珍辞别台州,乘坐李延孝的商船回国,二十二日回到日本太宰府鸿胪馆。圆珍回到日本后,于公元八六四年就任天台座主,大力弘扬天台佛法,成为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就任后与中国僧人的来往仍然非常频繁。因为圆珍的弘扬,日本天台宗佛教发展很快,而且源远流长。直到现在,京都附近的比睿山仍然天台宗佛教的圣地。
圆珍入唐后的公验和过所,现在还存留两则,这对我们研究中日文化交流意义重大。因为两则过所又都是浙东所发,更有助于对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而其本身也是海上丝路实物的见证。这两则过所,一是越州都督府颁发的过所,二是温州横阳县颁发的过所。这说明到了中晚唐时期,日本遣唐使者的往来以及登陆以后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浙东地区。
六、结语
举世闻名的天台山,集山水奇观与文化精萃于一体,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精华所在。以天台山文化为核心,以台州为中心的主要区域,是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这一区域以天台山为中心向四周辐射,而集中于现在的绍兴、宁波、温州,扩展到浙东,向内再向全国延伸,向外再向日本、韩国以及东亚地区,直至世界扩展。浙东唐诗之路,不仅仅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定位的地理之路与旅游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之路、经济之路、艺术之路、宗教之路。浙东唐诗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融会在一起,具有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这样从时间的纵轴来看,就能把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贯成一线,具有无限的延伸性;从空间的横轴来看,以天台山为辐射的中心,向浙东——全国——世界扩展,具有广袤的延展性。浙东唐诗之路的概念,虽然提出来有三十余年的时间,但迄至目前的学术研究,还处于初步的状态,仍集中于旅游开发与地方宣传的层面,这与浙东唐诗之路的实际文学成就和文化内涵很不相称。因此,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需要提高文化境界,加深学术内涵。同时,浙东唐诗之路研究,也不仅仅是浙东学者需要完成的使命,也是整个唐诗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浙东唐诗之路可以进一步拓展到全国唐诗之路的研究。
注释:
①(唐)徐灵府:《天台山记》,《唐文拾遗》卷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941页。
②(南朝梁)萧统:《文选》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93~494页。
③(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7页。
④华林甫:《唐代两浙道驿路考》,《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
⑤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第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⑥《全唐文》卷八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636页。
⑦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73页。
⑧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1页。
⑨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684页。
⑩(清)陈熙晋:《骆临海集笺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⑪(唐)宋之问:《景龙四年春祠海》,《沈佺期宋之问集校注》卷三,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517页。
⑫《新唐书》卷二〇二《宋之问传》,第5750页。
⑬⑭陶敏:《宋之问集校注》卷三,第513、511页。
⑮(宋)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二○,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
⑯(唐)李白:《李太白全集》卷二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23页。
⑰(清)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8页。
⑱⑲《全唐诗》卷五四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348、6091页。
⑳(唐)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李太白全集》卷一五,第7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