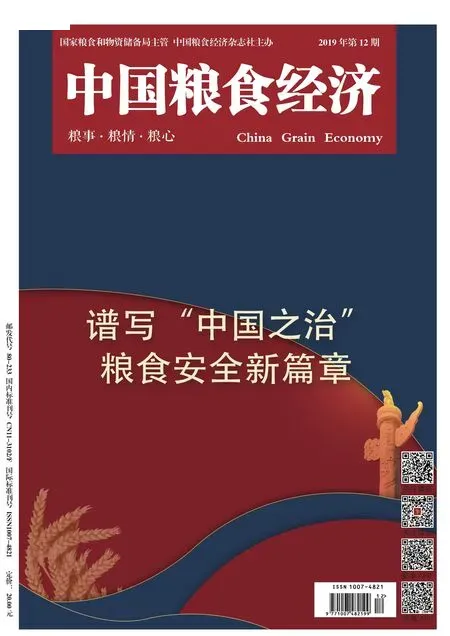麦香千里
2019-12-11方进
文/方进
栏目主持/刘博文
一、麦苗青青
我的家乡在皖中丘陵地带,盛产水稻,也种植小麦。小时候,生产队集体劳动,每年“三秋”(秋收、秋耕、秋播),庄稼刚刚收获,草木删繁就简,大地敞开胸怀等待新一轮耕耘播种,乡亲们便忙着种麦子和油菜。将新翻的泥土耙平碾细,整理成一畦畦地垄,用锄头在垄上勾出一个个小坑凹,撒点土肥,种上麦子和油菜籽,再用细土覆盖上,等待它们生根发芽。麦子对土壤和环境的要求并不高,村前、屋后、河边、路旁,哪里有空地,哪里都可种上麦子。于是,麦子与油菜一起孕育,一起生长。
当冬季来临,大地荒芜,万物萧条,麦苗和油菜破土而出,顶着风霜,冒着严寒,给冷酷荒凉的冬野增添一抹绿色,点燃一线生机。大雪纷飞,厚厚的积雪,为麦子盖上了一层御寒的棉被,不仅滋润了土壤,而且冻灭了害虫。“今冬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瑞雪兆丰年,乡亲们心里美美的,憧憬着来年的好收成。
麦苗和油菜新鲜细嫩,正是家禽家畜们的美味。守护麦田,是大人和孩子们共同的责任。离村庄很近的麦地,生产队组织人员用木条竹枝扎起篱笆,还安排专人看护,每片地块派一个人,各家各户轮流值守。儿时,我常常和小伙伴们利用假日,背着书包,拎着小竹椅,到麦地里,一边看书,一边看护着麦子和油菜,防止鸡鸭鹅猪等牲畜偷吃和糟蹋。
经过一冬的酝酿和积蓄,麦子在春天的原野上铺开一顷顷碧绿的诗行……一场喜雨过后,麦苗儿伸展着嫩叶,含着亮晶晶的雨露,像初生的婴儿,尽情地吮吸着大自然的乳汁。阳光下,叶子愈发光泽,像碧玉像翡翠,晶莹剔透,青翠欲滴。
乡亲们期盼已久,迫不及待走出家门,荷锄扛锹,顺着平整的地垄、笔直的麦行,小心翼翼地锄草、松土、施肥,为麦垄保墒、增温。望着一棵棵可爱的小苗,人们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地精心呵护,期盼着麦苗儿茁壮成长,拔节抽穗,早日成熟。
春江水暖鸭先知,麦苗青青百草迟。越冬的麦苗唤醒了初春的大地,带动了万物复苏。于是,小草绿了,野菜青了,竹笋出土了,柳叶发芽了,大地一片绿意。桃花、杏花、油菜花,以满眼新绿为画版,竞相涂抹着鲜艳的色彩,把春天装扮得姹紫嫣红、五彩缤纷。
嗅着麦苗的清香和百花的芬芳,人们纷纷外出踏青寻春。徜徉在麦丛间,用心去感受大地的呼吸,你会听到麦苗拔节的声音。微风吹来,麦田里泛起层层绿色的波浪,你的心海随之荡漾,感受春天的蓬勃,充满金色的梦想……
二、麦浪滚滚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每当听到这首歌,我就想起家乡,想起春夏之交麦子丰收的景象。“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麦子是一年中最早收获的庄稼,也是百姓最早的期盼。麦子熟了,人们再也不用担心青黄不接了。
麦收季节,再远再重的心事都放下,人们从四面八方回到乡间地头,男女老少齐上阵,热火朝天收麦忙。那满眼金黄的麦穗,像一束束火把,映红了农夫们古铜色的脸庞。镰刀飞舞,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收获从秋到冬、从春到夏农民付出的辛劳,收获风霜雨雪、日月甘霖大地呈献的精华,人们顾不上擦拭额头的汗水,顾不上拂去如刺的麦芒,怀揣着丰收的喜悦,一心想着颗粒归仓。
大人们忙着把麦子扎成捆、堆成垛,孩子们忙着拾起地上散落的麦穗,一边拾穗,一边唱着从广播里学会的儿歌:“我是公社小社员,手拿小镰刀,身背小竹篮,放学以后去劳动,割草积肥拾麦穗,越干越喜欢......”
男人们负责车拉肩挑将麦子运到打谷场上,女人们负责摊晒脱粒。在我的家乡,一直沿用着一种古老的打麦方式——连枷打麦。连枷,是由一个竹竿做成的长柄和一组平排的竹条(或木条)构成,“条子”扎在长柄一端,能360 度自由转动。打麦时,将连枷把上下甩动,使竹条旋转,拍打地上的麦穗,使之脱粒。连枷打不尽的,男人们牵来老牛拉着石磙碾压,使粘在麦秸上的麦粒脱落干净。
连枷打麦通常都由妇女们完成,将麦子整齐地摊在晒场上,麦穗对着麦穗,她们手持连枷,面对面站成两排,将连枷上的“条子”高高扬起,一人一下,此起彼落,有节奏地拍打,麦穗应声脱粒。打连枷是技术活,既要熟练掌握“条子”在连枷把上旋转的技巧,又要前后左右移动,边走边打,步伐整齐,你上我下,错落有致。
打麦时,为了统一动作和步调,人们常常喊着“连枷号子”,节奏明快,喊声悠扬。连枷拍打的声音“乒乒乓乓”,如丰收鼓乐,似喜庆花炮。“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铿锵的连枷声、高亢的号子声、还有石滚碾压的“吱哑”声,汇成一组欢庆丰收的交响曲,在小村上空久久回荡......
随着机械脱粒的普及,连枷打麦的生产习俗已渐渐远去,打麦场也不复存在。然而,那火热的劳动场景,淳朴和谐的乡风,还有打麦场上流传的故事,将永远印在小村和那一代人们的记忆里......
三、麦面飘香
麦子收获之后,乡亲们都要尝尝鲜。村里有一个大庭屋,里面摆放着一个大大的、圆圆的石磨,专门用来碾磨麦粉。夏季农活忙完了,乡亲们开始洗麦磨粉。石磨周边镶有两根木轴,可同时容纳三四个人推磨,还有一人专门往磨盘中间的圆孔里添麦子。添磨的活通常是由妇女来做,推磨有时也用耕牛代替,只是轻易不使唤,农闲时也要让它们休养歇息。磨盘转动时吱吱呀呀,石磨一响,全村的人们便知该有新面吃了。
南方人制作面食的方式很简单,不如北方的花样多,通常是做面汤。“面汤”是我们那里的一种叫法,其实就是手擀面。一时间,家家户户都开始揉面煮面汤,热气腾腾,香飘四邻,清新爽口,柔软绵甜。孩子们托着大碗的面汤,走出家门,相互炫耀。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的小村还流传下来做挂面的手艺,打我记事,村里几十户人家家家都会做挂面。每年立冬以后,田里的农活闲了,大家就开始忙起了做挂面。父亲是制作挂面的高手,小时候,我经常跟在他身旁,一边帮忙,一边学习。傍晚,父亲将面粉、水和盐按比例配好,放入面缸里,我卷起袖管帮父亲和面。和面需要力气,两只手在面缸里不停地捶打翻揉。约莫半个时辰后,父亲抓起一小块面团拉成薄薄的一层,对着光亮照一照,看看是否均匀,是否有粘性。
晚饭后,父亲将和好的大块面粑摊到面板上,用擀面杖推平压薄,用菜刀裁切成条状,然后双手搓揉,由硬到软,由粗到细,从面板上盘到簸箕中,再从簸箕中盘到面缸里。“盘”的过程,也就是由短到长、由粗糙到精软的过程,父亲的双手一刻不停地搓揉,重复着同样简单枯燥的动作。翌日鸡鸣时分,父亲早早起床,将面缸里的面绳缠到两根长长的竹筷上,放在面厢里,等待日出时上架。
早晨,温暖的阳光洒满村庄,父亲把门前的空地打扫得干干净净,摆好面架,将面厢里的面筷搬出屋子,挂在架上,有节奏地往下拉。拉面的过程很有技巧,力量小了拉不长,力量大了会断裂,需要悠悠地使劲,拉一节停一会,让面条有个缓冲的过程,然后接着再往下拉,一直拉到最底下的横档板,将面筷插到档板的一个个小孔中固定。微风吹来,长长细细的面丝像春天的杨柳,轻盈舞动,悠然飘荡。
制作挂面的过程看起来不算复杂,但起早歇晚非常辛苦,而且要注意观察天气变化,掌握面粉、水和盐的配比。盐多了太咸难入口,盐少了制作时容易断,还要把握好盘条、上筷、起架的时间。祖上什么时候传下这手艺,不得而知。记忆中家里每一次盖新房,都要留一间作面坊。在给父亲当帮手的过程中,我也渐渐学会了制作挂面这祖传的技艺,还指望着将来有一天能够派上用场,养家糊口。那时怎么也没想到后来我会变作城里人,告别那祖祖辈辈耕耘的黄土地,告别那充满温馨的挂面坊……
说来也怪,周围的村庄仅距半里路,甚至只隔几条田埂,邻村的人家都不会制作挂面。是他们不愿意学,还是我们村的手艺不允许外传?反正制作挂面的技术愣是没出村。逢年过节、贺喜祝寿,外村总会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村里购买挂面,有亲戚朋友,也有不熟识的,还有的挑着麦子来换面条。
每当冬季来临,站在村口望去,一排排整齐的挂面次第摆开,像千万缕银丝,又像飞来的瀑布,颇为壮观,形成小村一道亮丽的风景。有了这道风景,小村的冬天不会寒冷;有了这道风景,小村的日子红红火火......
四、麦行九州
走进粮校,打开粮油经济地理图,发现小麦并非我家乡的特产,皖北地区、华北平原、黄河流域,才是小麦的家乡。
那年夏天,我到位于皖北的蒙城县实习,帮助粮站收购小麦,一住就是20 多天。粮站周围,村村落落,到处都是刚刚收获过的麦地,到粮站售麦的汽车、三轮车、平板车排着长长的队伍,如一条长龙,从粮站院子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机耕路上。第一次到麦产区劳动和生活,一日三餐都是馒头和面条,对我这个以米饭为主食的南方人来说,刚开始很不习惯。粮站的李站长和李婶经常送来自己蒸煮的包子、饺子、煎饼、韭菜盒之类,热腾腾、香喷喷,让我大饱口福、大开眼界,没想到麦面竟能做出如此多的花样!从此,我对面食情有独钟。
有一种说法:“中国小麦看河南,河南小麦看新乡,新乡小麦看延津。”河南是全国人口第一大省,也是小麦生产第一大省,总产量占全国1/4。延津地跨黄河、海河两大流域,水资源充沛,土地肥沃,是全国优质小麦生产示范基地县,有着“中国小麦第一县”的美誉。那年麦收季节,我慕名来到延津县考察学习优质小麦订单收购。站在中原大地上,面对四面八方金黄的麦田、粗壮的麦穗,心潮澎湃。走进村民家中,看到家家户户都持有农业合作社社员证,这是在当地政府引导下,由粮食产业化龙头企业牵头,村民自愿加入的农业合作组织,从麦种优选、机械播种、田间管理,到机械收割、订单收购、精深加工,实现标准种植、科学管理、规范经营,不仅大大增加了农民收入,还有效提升了小麦品质,此举被业内称作“延津模式”。

人们常说“好吃不如饺子”。提起饺子,河南人最为骄傲,不仅因为“全国十个饺子有七个产自河南”,那些耳熟能详的著名品牌大多出自河南,而且他们认为饺子是河南人发明的。相传,东汉时期河南南阳人医圣张仲景在离开官场告老还乡时,看到很多穷苦百姓寒冬时耳朵冻烂了,他制作了一种药物叫“祛寒娇耳汤”,用羊肉、辣椒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熬煮,捞干切碎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下锅煮熟分给病人,病人吃过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烂耳朵很快就好了。人们为感激和纪念医圣,于大年初一仿“娇耳”的模样制作食物,称之为“饺子”,南方人还叫作“扁食”。如今,饺子作为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一种面食,早已遍及全国各地。
麦子的作用远不止能做饺子、馒头、面条,在全国粮食加工第一大市——山东滨州的粮食加工企业,人们看到,小麦的变身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谷朊粉、胚芽油、食用酒精、工业酒精、液体蛋白饲料等等,小麦转化的产品涉及养殖、医疗、新能源、航空航天等众多领域。一粒小麦,从初加工到精深加工再到综合利用,毫无保留,无私奉献。
我国地大物博,小麦栽培遍及神州,从黄淮海流域到大西北地区,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两岸,有的生长在春天,称为春小麦,主要在长城以北,岷山、大雪山以西;有的播种在冬季,叫作冬小麦,主要在长城以南,秦岭、淮河以北。而中原大地是我国最大的小麦集中产区,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以小麦为主粮生产生活,世代耕耘,繁衍生息。
五、麦作千年
众所周知,小麦原产自西亚,已有1 万多年栽培历史,公元前2000 年左右传入中国。专家认为,中国最早发现小麦种植遗址是在新疆的孔雀河流域,至今有4000多年,后来由黄河中游逐渐扩展到长江以南。
1955 年,考古学家在我的家乡安徽亳县(今亳州市)钓鱼台村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有炭化小麦种子,被中国科学院等有关单位命名为“中国古小麦”,迄今至少有3000 年。50 年后,在亳州以南200 公里的蚌埠禹会村遗址中,再度发掘出土小麦炭化物,考古测定遗址距今有4100 年的历史。这些发现足以证明,皖北地区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种植小麦的区域之一。
“我行其野,芃芃其麦”“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从《诗经》中可以遥想古时候中原大地小麦生长的茂盛景象,也可以看出那时麦子已是百姓生活中的主要食物。在唐宋诗人们的笔下,麦子也经常成为他们描摹和赞美的对象——“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唐·王维《渭川田家》);“五月江吴麦秀寒,移秧披絮尚衣单”(宋·范成大《夏日田园杂兴》);“小麦绕村苗郁郁,柔桑满陌椹累累。”(宋·陆游《闲咏》)......麦子不仅是人们重要的物质食粮,而且成为文人墨客歌咏生活借物抒情的重要具象。
小麦作为舶来品,虽然很久以前就传入中国,但很长时间里被看作是口味不佳的“杂粮”。《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东汉新阳侯阴就请井丹吃饭,“侯设麦饭葱菜,以观其意,丹推却曰:‘以君侯能供美膳,故来相过,何谓如此!’乃出盛馔。”可见当时麦饭只是粗食,并非“美膳”。古时候,麦子只是粒食,人们像吃稻米一样食用小麦,称作“麦饭”,颗粒坚硬,食之粗糙,味觉之差可想而知。
随着石磨的发明和发展,麦子由粒食变为面食,开始进入寻常百姓家。以面食为主的北方老百姓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蒸馒头、烙煎饼、擀面条、煮饺子, 五花八门。而面条,源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人类共同的美食。2013年,有关方面还举办了首届中国面条文化节,兰州牛肉面、武汉热干面、北京炸酱面、山西刀削面、四川担担面、吉林延吉冷面、河南烩面、杭州片儿川、昆山奥灶面和镇江锅盖面,被评为全国“十大面条”。这些各具特色的面条不仅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还带动地方产业经济的发展,成为一张张亮丽的名片,名扬海内外。
小小的麦子,漂洋过海,落户东方古国,在这片广袤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发芽、生长、结穗。麦子的外表又黑又粗糙,那是阳光和汗水调和的颜色,与农民兄弟的肤色完全一致;麦子的内心白玉般纯洁,雪花般通透,一尘不染。麦子朴实无华,热情奔放,锻造了北方人性格的豪气与直爽。小麦和水稻像一对孪生兄弟,共同编织神州的锦绣,共同创造大地的丰收,他们养育了华夏儿女,守护着舌尖上的健康,为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贡献无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