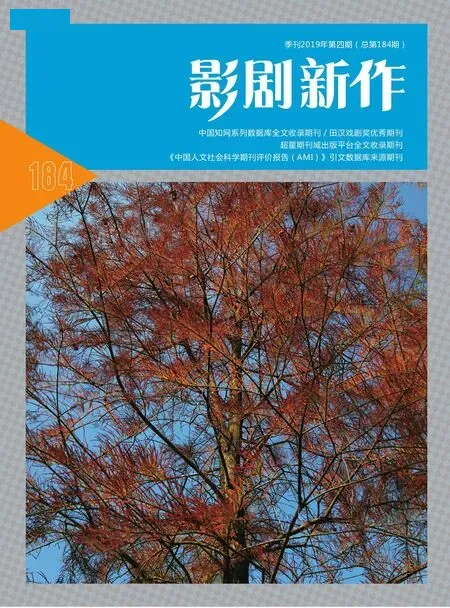从多媒体舞台剧《华山美少年》看对传统神话的现代叙述
2019-12-09陈燕华
陈燕华
陈燕华:江西省艺术研究院
责任编辑:吴建军
沉香劈山救母是一个有着悠久叙述历史的神话故事,其早期雏形来自于唐代《广异记》“华岳神女”篇,讲的是华岳三娘与书生私自结合的爱情故事;至宋元时期这个故事的情节进一步丰富,一方面加入“刘锡赶考”“落弟”“高中”以及“招婿”等反映时代特点的情节,另一方面还加入两人之子“沉香出生”“继母杨氏舍己子救沉香”“沉香寻母救母”等附属性情节,如宋代戏文《刘锡沉香太子》、元杂剧《劈华山救母》《沉香太子劈华山》等,已初具相对完整的故事形态和叙事结构;明代以后,随着民间世俗宝卷故事的流行,其和传统戏曲结合,开始形成独特的《沉香宝卷》故事,其中沉香救母情节的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与三娘和刘锡爱情故事地位相当、具有独立性的回合;到了清代,因宝卷故事强调宗法人伦的伦理教化要求的进一步突出,《沉香宝卷》中沉香的叙事地位又一次拉升,刘锡和三娘的爱情抗争部分的情节弱化,刘锡再婚杨氏等情节亦被删去,而叙事主题也由原来的爱情故事发展为孝子故事,这一变化基本奠定了我们今日所知沉香救母故事的主要形态和结构。
可以说,所有神话故事的成功,多多少少都是因为其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它们所处时代的某种共同的人类情感。沉香救母的故事,从古说到今,每一次成功的改编,始终是因为它能迅速地捕捉与反映时代思潮与观念的变化,并将其融入故事文本之中,使其与人们自身现实经验和文化价值认同相符,也只有这样的叙述才能拥有拨动人们心弦的力量。
继承了沉香故事基本主题和框架的话剧《华山美少年》还能不能打动今日的现代人?还能不能在两者之间找到情感的共振点?依笔者看来很难。《华山美少年》在故事结构上相比清代宝卷已有所改变,且这种改变明显受时代较为接近的动画改编电影《宝莲灯》的影响,如加入“部落缺水”“沉香帮助部落打败哮天犬而重获水源”等现代观众容易辨识的情节。但其思想内核仍继承了清代宝卷时期的特点,如以沉香的孝道为统领整个故事的立足点,而反映刘彦昌与三圣母的爱情以及刘彦昌本人经历的故事地位则基本无足轻重。一如电影《宝莲灯》的平庸,电影没有克服的缺陷在此剧中也仍然没有改变,如人物扁平单一没有鲜明的性格特征、语言平淡、情感表现无说服力等等,正面人物的好、反面人物的坏,全都直白地写在了脸上;而最主要的还是此剧在思想上仍固守时代久远的观念与认识,未能从清代宝卷所依循的传统伦理规范中越出一丝半步,做出有价值的现代意义上的思考与拓展。总体来说,虽然《华山美少年》讲述故事的形式从传统的戏曲、宝卷转变为现代的话剧,但其精神内质并未做出相应的改变,这仍是对传统神话故事做出的一次毫无新意的重述。
在笔者看来,贯穿于沉香救母故事的两个最核心的命题无非两个:代际关系和个体的成长,如果对这两个主题不能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表现,那么这部话剧不能说是成功的。而在这个传统神话故事的外壳之下如何表现以上两个主题,肯定不是运用清代人的大脑与情感,而必须要运用现代人的大脑与情感。要想写出现代人爱看的剧,必须要直面当下,找到现代人思想的焦点、情感的痛点。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古老的故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这一点上需要提到另一个较为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神话改编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这部电影取得了商业上的极大成功并非毫无理由,首当其冲的即是:同样是对代际关系和个体成长的表现,《哪吒之魔童降世》做到了让哪吒从一个古代人蜕变为一个现代人。在神话中,哪吒本是一位由本能驱使的反叛式英雄,虽热血但却鲁莽而简单,而在电影的处理中既保留了哪吒原有的性格特征,同时又颠覆性而又顺理成章地从中提炼出了“做自己的英雄”这一主题,讲述了哪吒这一独特心灵自我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的驱动力不是来自于外在的道德说教,而是对自我的一种痛苦粹炼,以及粹炼之后的重生,凸显了是人是魔都是一种自我选择,而不是天注定的主题。经历了这一系列转变之后,哪吒已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那一个”哪吒,他变成了“魔童”,是一个可以打动我们的现代人。也只有当下的现代人才能理解这一个哪吒,他所经历的困惑与挣扎,可能也是当下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在对代际关系的表现上,《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没有落入传统窠臼,时刻把一个“孝”字挂在嘴边,哪吒与父亲从误会到理解、宽容,是一种平等、健康的现代亲子关系,哪吒的母亲工作忙碌而内疚于不能陪伴儿子,像极了当下社会中的普通妈妈。
再回到本文的改编多媒体舞台剧《华山美少年》,在剥去了重重历史外壳之后,还能给我们剩下什么。这个空洞的故事,既失去了其产生于原本所处情境中的动人力量,也无法打动当下的人们。沉香救母故事的内核是中国传统的“孝道”思想,同时完成“孝道”的过程也是沉香个人成长的过程。儒家提出的“孝道”原本是一种积极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孝”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推己及人的精神品质。但是,儒家的孝道发展到后期,从一种建立于个体自觉基础之上的自我要求,逐渐变成了一种严厉的外在伦理规范。当“孝”从一种道德上的自我要求变成了一种制度性的强加于人,甚至于成了打人的棍棒,此“孝”可能就会变了味。不过,尽管如此,亲子之爱始终且永远是世间最美好的情感之一,我们也不能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彻底否定了“孝”,“孝”的本质是爱。脱去礼法的桎梏,凸显“孝”的内在本质,将让人无理由服从的“孝”转化为更具现代性内涵的建构于理解与宽容基础之上的“爱”,是今日的我们要做到的。在这一点上,《哪吒之魔童降世》显然更为成功, 这也是为什么《华山美少年》中沉香的“孝道”不是那样能打动我们的原因。因为沉香的“孝道”是一种纯观念性的、空洞的、抽象的东西,并不是沉香母子在抚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具体的“爱”,这种被传统伦理所规范的“孝道”在今日已无法引起人们的共鸣。现代社会对“代际关系”的认识深度可能早就远远超越沉香救母故事所产生的年代,不在剧本中将这种时代认识反映出来,则无法叩动当代人的心弦。
而谈到个体的成长,剧本中美少年沉香的成长历程是一个十分顺理成章的过程。虽然劈山救母这一任务对于一个少年来说看似异常艰难而几乎不可能完成,但是在每一个重要的时刻沉香都有贵人指点或相助,及时解决问题:饿了、病了有仙女小姑娘送来食物和药,没有方向有仙女小姨灵芝指点,没有本领有霹雳大仙倾力相教,神奇的六韬三略的本领也能靠几句俏皮话就轻松学到,顷刻间脱去凡胎,并获赠能劈山的萱花神斧……,诸如此类剧情事件,一切来得异常轻松,可以说沉香的成长是诸多外援合力的结果。这类成长缺少内在的压力和驱动力,也就使得角色失去了个性上的张力和说服力。反观魔童哪吒的个人成长历程,是一种经历了宿命不公之后的奋力反抗,是一种对自我进行深刻怀疑、拷问之后的自由选择。通过内在的挣扎与突破,哪吒的自我成长得以完成。而其中“做自己的英雄”“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魔是仙,我自己决定”的命题可谓直接喊出了压抑在人性深处的普遍渴望,这种渴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无力达到,但在故事中却可以随着主人公的热血与激情而得到短暂的释放。
总之,对传统神话故事的改写或重写,不仅仅是简单地重新叙述这个故事,还考验着我们对当下这个时代与人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