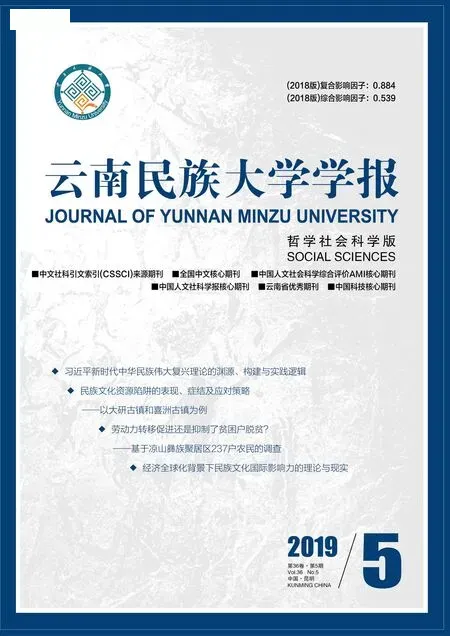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
——《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评述
2019-12-09冯洁菡邱慧心
冯洁菡,邱慧心
(武汉大学 国际法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2)
《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下文简称为“《塔林手册2.0版》”)是北约网络合作防御卓越中心继2013年编写《塔林手册1.0版》之后,为涵盖和平时期的网络行动而发起编撰的,其目的是澄清和发展现有习惯法规则在网络空间的使用这一“关键问题”(1)黄志雄:《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制定的新趋向——基于〈塔林手册2.0版〉的考察》,《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塔林手册2.0版》第八章阐述了适用于海上网络行动的相关规则,包括公海、专属经济区、领海、毗连区、国际海峡、群岛水域内的网络行动,以及虚拟登临、海底通信电缆和中立沿海国对交战国网络行动的义务等等。(2)《塔林手册2.0》第八章,规则45-54。参见[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黄志雄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271页。总体而言,《塔林手册2.0版》试图澄清物理空间的一般国际海洋法规范在网络空间的可适用性。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对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作了专门规定和评注。除此之外,有关主权、管辖权、反措施、公海、国际海底电缆以及航空法的相关规则也均与专属经济区内的网络行动相关。(3)分别参见规则5,规则11-12,规则20-25,规则45,规则54以及规则56。本文主要评述在航行自由语境下《塔林手册2.0版》中与低烈度(亦即低于使用武力门槛)(4)低烈度网络行动是指低于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门槛的网络行动,从而不构成对禁止使用武力规则的违反。参见Michael N. Schmitt, “Below the Threshold” Cyber Operations: The Countermeasures Response Op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Virgi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 54:3,2014, p.699; Nicholas Tsagourias, “The Law Applicable to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Low-Intensity Cyber Operations”, p.1, available at:http://eprints.whiterose.ac.uk/98561, 2019年4月15日访问。军事网络行动相关的规则,包括“和平目的”原则和“适当顾及”义务以及海上网络基础设施等相关规则,探讨这些规则是否客观地重述了“实然法”(5)[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黄志雄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以及这种澄清对未来有关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与沿海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范围的争议所产生的影响。
一、概览:《塔林手册2.0版》中航行自由语境下的网络行动
依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文简称为“1982年《公约“》)的规定,其他国家有权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以通常方式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海洋国际合法用途”(6)参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1款。。同时,其他国家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应“适当顾及(due regard)”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应遵守沿海国按照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7)参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8条第3款。但是,上述规定并未解决以美国为代表的海洋强国与发展中沿海国的如下争议:(1)专属经济区是否仅与资源相关,与安全无关?美国认为,专属经济区是一个邻接领海的与资源相关的区域,如其名称所示,其核心目的是经济性的。(8)例如,参见美国前总统里根1983年发布的“美国海洋政策声明”(President Ronald Reagan, Statement on United States Ocean Policy, 19 Weekly Comp. Pres. Doc. 383, Mar. 10, 1983),以及1983年美国《第83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83, The White House, Mar. 10, 1983)。此外,美国还将对与资源无关的专属经济区主张列入美国所认定的“过度海洋主张(excessive maritime claims)”范围,并每年对此采取军事性航行自由行动。分别参见1982年美国《第72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72, The White House, Dec. 13, 1982),1987年美国《第265号国家安全决策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265, The White House, Mar. 16, 1987),1990年美国《第49号国家安全指令》(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Directive 49, The White House, Oct. 12, 1990)。而一些发展中沿海国的实践和后《公约》时代的国际动态则表明安全正越来越成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关注事项。(9)具体参见下文“三”。(2)专属经济区内其他国家主张的航行自由边界是什么?哪些军事活动属于“航行和飞越自由以及与此有关的其它海洋国际合法用途”?美国认为,军事航行自由既包括军事机动自由,也包括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开展各种军事活动的自由。有关军事活动自由引起的争议最大,其中主要涉及到如何解释1982年《公约》中的“和平目的”原则与“适当顾及”义务。(3)水文测量(hydrographic surveys)等军事活动是否属于沿海国可行使专属管辖权的“海洋科学研究”范围?(10)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6条第1款(b)项(2)、第249条规定海洋科学研究属于沿海国专属管辖范围。美国主张军事测量/水文测量不属于“海洋科学研究”,因而无须沿海国事先同意。(11)参见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2007和2017年版),第2.6.2.2节。美国的理由是1982年《公约》第56条第1款(b)项(2)没有更一般性地指向“测量”或其他军事活动。参见James Kraska and Raul Pete Pedroz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Law,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p.286 (2013).而部分其他国家则认为,任何水文数据都不会仅用于航行安全或军事目的,而是对沿海国具有经济价值,应被视为“海洋科学研究”。(12)Ying Yang, The Prior Notification Issue of Military Activities in EEZ, in Gordon Houlden and Nong Hong (eds.), Maritime Order and the Law in East Asia, Routledge, pp 162-164 (2018).(4)安装军事设施、装置等军事活动是否违反了沿海国依《公约》第60条第2款对“设施和结构的建造和使用”的专属管辖权?美国主张应严格解释,沿海国只对用于经济目的的设施和结构享有专属管辖权,(13)参见James Kraska and Raul Pete Pedroz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Law, 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 p.279 (2013)而20多个其他国家的实践则对所有类型的设施和结构都主张管辖权。(14)参见下文“四”。
上述问题涉及到沿海国和海洋大国间利益的博弈和分配,1982年《公约》对此措辞模糊,而《塔林手册2.0版》则试图对上述问题做出部分解答。在《塔林手册2.0版》中,与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和网络行动相关的主要是规则47,该规则规定:“一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可实施网络行动,但必须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且相关网络行动必须用于和平目的,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同时,规则47的评注、规则45、规则46、规则54、规则56及其部分评注均涉及到对规则47的解读,相关内容主要包括:(1)依据1982年《公约》第58条第1款和第87条,所有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自由,以及与上述自由相关的其他国际合法用途。只要适当顾及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航空器和船舶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为航行和通讯目的使用网络设施。(15)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2。(2)军事网络行动本身并不违反应只用于“和平目的”这一原则。不涉及被禁止的使用武力的军事行动,属于《公约》第87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海自由和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范畴。(16)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5评注5。“和平目的”原则并不禁止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反措施,包括网络反措施。(17)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5。(3)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特定的主权权利(主要与资源相关)。《公约》未能提及专属经济区内的安全利益,军事活动通常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有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无关。相应地,在顾及沿海国权利的情况下,一国可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开展军事活动,特别是具备网络行动能力的军舰和军用航空器可在专属经济区内自由地航行和飞越。上述活动无须获得沿海国的同意。(18)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3和4。(4)专属经济区上空属于国际空域,一国可在他国专属经济区上空自由实施网络行动,而无须经沿海国同意。专属经济区上空可能涉及国家安全,沿海国可规定相关限制,包括禁止航空器实施网络行动,但不能对飞越而无意进入其领空的航空器施加任何限制。(19)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6评注2和9。(5)一国可以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自由铺设或授权其管辖下的公司铺设海底通信电缆,但也可能受制于沿海国的管辖权。实践中,有时会对沿海国的管辖权予以尊重,即便铺设或维持海底通信电缆属于公海自由的范畴。(20)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2,规则54评注9。
综合考察上述规则及其评注,《塔林手册2.0版》对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语境下的网络行动所持的观点可归纳为如下两点:(1)一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必须遵守“适当顾及”义务和“和平目的”原则,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2)只要履行“适当顾及”义务,一国的船舶和航空器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为航行和通讯目的利用其网络实力,自由开展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并可在专属经济区上空自由实施网络行动。因此,在网络空间环境下,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同样首先取决于对“和平目的”原则与“适当顾及”义务的解读,《塔林手册2.0版》对此有所着墨。
二、《塔林手册2.0版》对“和平目的”原则与“适当顾及”义务的解读
1.“和平目的”原则
和平利用海洋贯穿于1982年《公约》的始终。《公约》前言中指出,“认识到有必要……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促进海洋的和平利用……。”(21)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此外,《公约》第88条,第141条第1款,第143条第1款,第147条第2款(4),第155条第2款,第240条第1款,第242条第1款,第246条第3款和第301条也都涉及到和平利用海洋。另参见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684 (2017).1982年《公约》第88条规定“公海应用于和平目的”。依据《公约》第58条第2款,第88条适用于专属经济区。但《公约》并未对“和平目的”做出界定。理论上,对《公约》文本和缔约历史的不同解读,使得对“和平目的”的解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和平”意味着“非军事化”。例如,1976年厄瓜多尔代表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上发言指出“和平”代表全面地去军事化和排除所有军事活动。(22)参见1976年厄瓜多尔代表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上的发言。UNCLOS III Summary Record 67th Meeting [23 April 1976] UNCLOSOR vol V, 56.依此种主张,则未经沿海国同意不得在其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活动。第二种观点认为“和平”意味着“非侵略性”,即“和平目的”应依据1982年《公约》第301条进行界定,而该条界定的“和平利用”仅规定了国家不得从事违背《联合国宪章》的禁止威胁或使用武力的消极义务,因而并未普遍禁止公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所有军事活动。(23)参见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 1944 (2017). 在第四期会议上,对海洋的和平利用进行了专题辩论。大会主席指出,海洋的和平利用不能与其他场合关于裁军、非热核化和海底非军事化的谈判分离。参见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2页。第三种观点认为“和平”应依据《联合国宪章》和其他依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加以检验。(24)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63页。
《塔林手册2.0版》对专属经济区内的相关网络行动,使用了与“公海上的网络行动”(25)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5“公海上的网络行动”:公海上的网络行动只能用于和平目的,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大体相同的措辞,即“用于和平目的,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26)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因此,“和平目的”原则适用于在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的网络行动。规则45评注2进一步将“和平目的”的定义与1982年《公约》第301条挂钩,主张禁止的是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在此基础上,《塔林手册2.0版》评注认为,海上网络行动本身并不违反“和平目的”原则。不涉及被禁止的使用武力的军事行动,属于《公约》第87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海自由和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范畴。(27)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5评注5。《塔林手册2.0版》对“和平目的”原则的上述诠释,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第二种观点的支持,实际上体现的也是海洋强国的立场。例如美国就明确主张,“和平目的”原则并不禁止第301条之外和平时期的军事活动,并认为在1986年“尼加拉瓜案”中国际法院认定美国在尼加拉瓜领海之外进行的军事演习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也说明了这一点。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依《公约》第301条将“和平目的”原则界定为凡“非侵略性”的军事网络行动均可毫不受限地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则没有考虑到专属经济区不同于公海的自成一体性及其所具有的混合性和功能性特征,(28)Pascale Ricard, The Limitations on Military Activities by Third States in the EEZ Resulting from Environmental La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34, p. 147 (2019).从而有意忽略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军事利用的限制应大于在公海内对同样行为的限制。(29)Orrego Vicua,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Regime and Legal Nature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p. 111 (1989).
2.“适当顾及”义务
《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指出,一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必须“适当顾及”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和义务。这一内容主要参照的是1982年《公约》第58条第3款的前半部分。《塔林手册2.0版》规则47评注1对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作了进一步列举,指出在从事网络行动方面,应尊重沿海国:(1)在专属经济区内对自然资源以及利用海水的主权权利;(2)对建造和使用人工岛屿、设施和结构的管辖权;(3)对海洋科学研究的管辖权;(4)对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的管辖权。
实际上,1982年《公约》第56条第2款和第58条第3款规定了沿海国和其他海洋使用国在专属经济区的“适当顾及”义务,但并未对之做出具体阐释。依据相关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时,应履行的“适当顾及”义务具有如下性质:
(1)相互性。1982年《公约》第56条第2款与第58条第3款规定的“适当顾及”义务阐释了《公约》在解决潜在权利冲突上的原则性立场。这两个条款措辞十分相似,二者的结合使《公约》为两类权利主体共同创制了一个“相互的适当顾及义务”。(30)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 455 (2017).国际法院在“英国诉冰岛渔业管辖案”中明确了这一性质,并指出“任何一方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31)国际法院认为:“争议双方均享有被‘适当承认’的权利,在本案中即英国在争议水域捕鱼的权利与冰岛所享有的优先权。二者的权利都不是绝对的。”参见ICJ, 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 Iceland), Judgment of 25 July 1974, ICJ Reports (1974), p. 31, para. 71.。
(2)平衡性。专属经济区这一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即是在沿海国的权利和利益与其他国家的权利和利益之间保持适当平衡。(32)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页。在“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中,仲裁庭认为,英国秉承善意行事的义务,以及“适当顾及”毛里求斯权利和利益的义务,至少涉及到协商和平衡地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利益。(33)参见PCA,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ara. 534.
(3)程序性。无论是在“英国诉冰岛渔业管辖案”还是在“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中,国际法院与仲裁庭都肯定了争议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冲突是履行“适当顾及”义务的表现形式。(34)国际法院在“英国诉冰岛渔业管辖案”中认为:“对本案争议最合适的解决方式即是双方协商,其目的在于划分争议双方在权利与义务上的边界……”。参见ICJ, Fisheries Jurisdiction (United Kingdom v. Iceland), Judgment of 25 July 1974, ICJ Reports (1974), p. 31, para.73. 2015年“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的最终裁决也表达了类似意见。参见PCA,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ara.519.在后一案件中,仲裁庭还认为履行“适当顾及”义务应在善意的基础上及时开展磋商或协商,并在可能时提出和解建议。(35)参见PCA,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ara.528et seq. 但同案异议意见认为,适当顾及问题与第300条中规定的善意和禁止滥用权利规则并无充分联系。参见PCA,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Joint Dissenting and Concurring Opinion of Judges Kateka/Wolfrum, para. 89.转引自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 431, note 68 (2017). 也有学者指出,第300条中规定的善意和禁止滥用权利规则不涉及相互冲突的权利,而这正是适当顾及义务的主要目的。参见Geneviève Bastid Burdeau, The Respect of Other States’ Rights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ther Rights and Freedoms Set Out in the LOSC) as a Limitation to the Military Uses of the EEZ by Third Stat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34, p. 120 (2019).
由于涉及“适当顾及”义务的判例不多,且主要依个案具体情势考察,因此,目前仍很难确定“适当顾及”义务在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标准,(36)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 432 (2017).尽管2015年的“毛里求斯诉英国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案”裁决首次提出,顾及的程度取决于沿海国拥有的权利的性质、其重要性、预期损害的程度、从事行动的国家所考虑的行动的性质和重要性以及替代性办法的可获得性。(37)PCA, Chagos Marine Protected Area Arbitration (Mauritius v. United Kingdom), Award of 18 March 2015, para.519.不过从上述司法和仲裁意见中至少可以得出结论认为,“适当顾及”义务不允许从事网络行动的国家任意行事。首先,基于“适当顾及”义务的相互性,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的国家不能依据《公约》第58条第1款所规定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主张绝对的网络行动自由。其次,基于“适当顾及”义务的平衡性和程序性,在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网络行动的国家在行使自己相对的网络行动自由权利时,应进行自我约束,应对可能发生冲突的沿海国主权权利和管辖权进行平衡性考量,特别应避免不友好、挑衅性的或者恶意的网络行动。但也正如前文所述,当前的司法判例认为“适当顾及”义务主要是程序性的,因此只要实施网络行动的国家采取了适当的程序性行为,例如进行协商,便可被视为是履行了该义务。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塔林手册2.0版》将适当顾及的对象限定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而非顾及其“更为一般性的利益”,(38)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3。因而将安全利益排除在“适当顾及”义务的范围之外。同时,《塔林手册2.0版》也并未全盘复制1982年《公约》地58条第3款的所有内容。《手册》对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实施的网络行动,仅重述了《公约》第58条第3款前半部分规定的“适当顾及”义务,而并未提及与该义务并列的“应遵守沿海国按照本公约的规定和其他国际法规则所制定的与本部分不相抵触的法律和规章”的义务。
三、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
1.海上网络行动的类型
相较于《塔林手册1.0版》,《塔林手册2.0版》涵盖了和平时期的网络行动,即低于“使用武力”门槛的网络行动。(39)[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黄志雄等译:《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塔林手册2.0版》将“网络行动(cyber operation)”定义为:“利用网络能力在网络空间实现目标,或通过网络空间实现目标。在本手册中,这一术语通常在实施的语境中使用”。《塔林手册2.0版》对“网络活动(cyber activity)”的定义是:“任何涉及使用网络基础设施或使用网络手段影响此类基础设施运行的活动。此类活动包括但不限于网络行动”。因此,网络行动属于网络活动的子概念。(40)Michael N.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64 (2017).美国在2018年《美军联合行动指南——网络行动》中采用了与《塔林手册2.0版》相同的定义,并认为网络行动包括军事性和非军事性的。(41)参见Cyberspace Operations, Joint Publication 3-12, 8 June 2018, p.I-1.
根据《塔林手册2.0版》第八章“海洋法”前言第1段的表述,(42)[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黄志雄等译:《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页。海上网络行动可分为两大类型:(1)从(from)位于海上的网络基础设施实施的网络行动;(2)通过(through)位于海上的网络基础设施实施的网络行动。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手册》是以实施网络行动的媒介所在地点去界定海上网络行动类型的,包括实施网络行动的起点是位于海上的网络基础设施,例如,一国从位于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一艘船上对该沿海国或其他沿海国实施网络行动;或者实施网络行动是通过位于海上的网络基础设施,例如在陆地网络基础设施发起行动,通过位于专属经济区的船舶上的网络系统具体执行。
2.专属经济区内的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
《塔林手册2.0版》认为,低于使用武力门槛的军事网络行动,属于1982年《公约》第87条第1款所规定的公海自由和其他合法利用海洋的范畴。(43)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5评注5。《塔林手册2.0版》还援引了1986年尼加拉瓜案的判决,主张军事部署不违反禁止诉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44)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 v. US), 1986 ICJ 14 (27 June), para. 227.在此基础上,《塔林手册2.0版》进一步认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享有的特定主权权利主要与资源相关。《塔林手册2.0版》援引多数专家的观点指出,1982年《公约》未能提及专属经济区的安全利益,并且事实上,《公约》仅规定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而非顾及其更为一般性的利益。(45)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3。《塔林手册2.0版》继而详细列举了一国可以在另一国专属经济区内开展的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包括:军用航空器的飞越、海军特遣部队的部署、军事演习、监控、调查活动、侦查和情报收集,以及炮弹测试和射击等活动。具备网络行动能力的军舰和军用飞机可以在专属经济区内自由地航行和飞越。《塔林手册2.0版》评注还指出,上述活动无需获得沿海国的同意。(46)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3。此外,《塔林手册2.0版》还讨论了对于特定军事活动,包括与情报功能和网络行动相关的活动,是否涉及安全事项因而可为沿海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所禁止的问题。个别专家的意见认为1982年《公约》第58条第3款强调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将之理解为包括安全事项。而多数专家意见则认为,军事活动通常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有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无关。(47)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4。《塔林手册2.0版》在列举军事活动类型的同时,特别强调指出海洋科学研究,包括军队所开展的研究活动,需要获得沿海国的同意。(48)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4。对于在专属经济区上空实施网络行动,《塔林手册2.0版》指出,在不违反国际法上相关限制的情况下,国家可在国际空域中实施网络行动。(49)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6。《塔林手册2.0版》相关评注进一步认为,这一规则反映了习惯国际法。(50)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6评注1。由于“国际空域”是不属于国家领空的空域,任何国家都不能主张主权,因此专属经济区中与沿海国权利相关的规则对以展开网络行动为目的的飞越行为影响甚小。相应地,国家可以自由地在国际空域实施网络行动而无须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同意。(51)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6评注2。对于设立了防空识别区的国家而言,《塔林手册2.0版》认为,理论上,国家可以在属于国际空域的防空识别区内禁止航空器实施网络行动,或者禁止特定类型的网络行动,但只能是作为进入其领空的条件。而该条件不得妨碍公海上空的飞越自由。特别是,国家不能对因飞越国际空域需要而途经该国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包括军用航空器)施加任何限制。(52)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6评注9。
笔者认为,《塔林手册2.0版》中有关专属经济区内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的列举和相关评注,更多地体现为海洋强国特别是美国关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现行立场在网络空间的延伸,即:(1)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所享有的主权权利主要是经济性的,与资源相关,与安全事项无关;(2)专属经济区内的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是合法地利用海洋,无需事先获得沿海国同意;(3)海洋科学研究与情报收集和调查活动不同,前者需要获得沿海国的同意,而后者不需要;(4)专属经济区上空属于国际空域,他国可自由采取网络行动而无需沿海国同意,即使在防空识别区,也不能对途经而不进入沿海国领空的军用航空器施加任何限制。《塔林手册2.0版》的相关表述和评注,部分有创设“应然法”之可能,例如规则56评注1认为国家可在国际空域实施网络行动反映了习惯国际法;部分仅反映了美国的主张,例如有关军事网络行动无需经沿海国同意,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权利主要与资源相关,与安全无关等等;(53)参见前文。部分仅参考了美国的实践,例如一国只能要求进入其领空的民用航空器和国家航空器遵守该国设定的入境条件和程序,所援引的是美国国防部的《战争法手册》(54)Michael N.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09,footnote 672 (2017).,国家不能途经该国防空识别区而不进入其领空的航空器(包括军用航空器)施加任何限制,体现的是美国《海上军事行动指挥官手册》中的规定。(55)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2007年和2017年版)规定,“美国不承认沿海国有权将其防空识别区规则适用于无意进入其领空的外国航空器,美国也不会将其防空识别区规则适用于无意进入美国领空的外国航空器。因此,无意进入他国领空的美国军用航空器亦无须表明身份,或以其他方式遵守其他国家制定的防空识别区规则,除非美国已明确同意”。参见第2.7.2.3节。与此同时,则是有意地忽视了当前其他许多国家关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不同主张和实践。例如,孟加拉国、巴西、佛得角、印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和乌拉圭等国家在批准1982年《公约》时均已发表声明,主张未经沿海国同意,其他国家无权在其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上从事军事演习或调遣,特别是涉及使用武器或爆炸物。(56)Yoshifumi Tanaka,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95 (2015).另一些国家,例如缅甸、佛得角、印度、马尔代夫、朝鲜、葡萄牙和巴基斯坦等还通过国内立法对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进行限制。(57)参见Dep’t of Defense, Maritime Claims Reference Manual (MCRM), DOD 2005.1-M, June 2008. 转引自James Kraska& Raul Pete Pedrozo,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Law, MartinusNijhoff Press, pp 239-240 (2013).以及中国主张飞越防空识别区的航空器(无论军用还是民用),均应表明身份提交飞行计划。(58)参见中国国防部《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此外,1982年《公约》嗣后的相关国际动态,包括美国的国内规章,也表明安全正越来越成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的关注事项。例如,美国2007和2017年《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规定,为预防或应对在美国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内的对美国享有管辖权的个人、船舶或设施采取的恐怖主义行为,美国享有安全(security)管辖权。(59)参见《美国海上行动法指挥官手册》(2007和2017版),第4.5.2节。再如,2005年,在日本海洋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专属经济区 21 人专家组”公布了《专属经济区航行和飞越指南》,(60)EEZ Group 21: Guidelines for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The Nippon Foundation and Ocean Policy Research Foundation (OPRF), September 2005, Tokyo, pp 8-10, http: //nippon.zaidan.info/seikabutsu/2005/00816/pdf/0001.pdf, 2019年4月20日访问。其中详细规定了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限制,指出军事活动不应在任何情况下损害,或可能损害沿海国的安全、国防、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61)有学者指出,《指南》是由来自亚太地区战略利益各不相同的国家的专家们讨论通过的,因而具有客观性。其次,《指南》支持了专属经济区的军事活动应受到限制的主张。尽管《指南》没有约束力,但这份《指南》的通过,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参与制定《指南》的国家的实践和态度,也可作为1982年《公约》生效以来嗣后国家惯行的证据。参见[希腊]阿瑞斯-乔治·马盖里斯著,李途译:《美国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法律解释与实践——以中美战略竞争为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2期,第47页。
四、专属经济区内建造、运行和使用海上网络基础设施
《塔林手册2.0版》将网络基础设施(Cyber Infrastructure)定义为:“信息系统得以建立和运行的通信、存储和计算装置”。(62)Michael N. Schmitt (ed.), Tallinn Manual 2.0 o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to Cyber Opera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564 (2017).根据《塔林手册2.0版》第八章第1段,海上网络基础设施的来源包括:(1)海上的船只和潜艇(合称“船舶”);(2)海洋上空的航空器;(3)近海设施(installations);(4)海底通信电缆。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既包括固定在近海设施和海底通信电缆中的通信、存储和计算装置,也可以是在海上移动的船舶(包括潜艇)和航空器上载有的网络基础设施,如海上测量船载有的信息设备(63)叶卓文:《海洋调查船网络信息系统》,《中国测绘学会海洋测绘专业委员会第二十届海洋测绘综合性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9页。、军用舰载、机载网传感器及其他通讯设备(64)潘清等编著:《网络中心战装备体系》,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等等。
对于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建造、运行和使用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是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需经沿海国事先同意,《塔林手册2.0版》对此做出了部分解答。
1.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建造海上网络基础设施
据报道,2018年6月5日,微软在英国苏格兰奥尼克群岛附近部署的海底数据中心正式开始运行。该数据中心位于117英尺的深海海床,约为一个集装箱大小,通过与海底电缆连接实现运行,其目的是为沿海城市提供快速的数据云服务,并研究在世界任何地方部署模块化数据中心的可行性。(65)参见“微软拟部署潜艇式水下数据中心”,http://www.hellosea.net/Energy/2/2018-06-15/50913.html, 2019年4月25日访问。《塔林手册2.0版》规则45评注6认为,在公海建造海底数据中心的行为是合法的。但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此类中心的建造需经沿海国事先同意,其依据是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行使相关主权权利,并且该中心的运行可受到沿海国的规制与管辖。《塔林手册2.0版》同时援引了1982年《公约》第60条第1款和第2款,并特别强调沿海国可规制与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建造物应是用于经济目的的设施和结构。(66)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60条第1款(b)项规定,“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应有专属权利建造并授权和管理建造、操作和使用:(b) 为第56条所规定的目的和其他经济目的的设施和结构”。《手册》在多处强调了专属经济区的经济属性,如规则47评注3认为沿海国的主权权利主要与资源相关,规则45评注6脚注561认为沿海国可规制与管辖的是用于经济目的的装置和结构。
部分国家实践与此解读并不一致。例如,巴西、佛得角和乌拉圭在批准1982年《公约》时发表声明指出,未经同意不得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建造、操作和使用任何类型的设施和结构,无论其性质或目的为何。(67)巴西签署声明第六项及批准声明第三项,佛得角签署声明第六项,以及乌拉圭声明E项。参见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III.aspx?src=TREATY&mtdsg_no=XXI-6&chapter=21&Temp=mtdsg3&clang=_enJHJEndDec, 2019年6月12日访问。此外,据统计有包括日本、比利时、印度在内的20多个国家在国内法中规定对用于任何目的(不限于1982年《公约》第56条中规定的经济目的)、所有类型的设施和结构均行使管辖权。这些国家主张专属管辖权的理由在于,某些军事性的设施或结构具有高度争议性,可能会使沿海国的防御失效,从而对其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68)Sophia Kopela, The ‘Territorialisation’ of the Exclusive Economic Zone: Implications for Maritime Jurisdiction, pp 6-7, https://www.dur.ac.uk/resources/ibru/ conferences/sos/s_kopela_paper.pdf, 2019年6月12日访问。我国1998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也未限定可行使管辖权的设施和结构的性质或目的。(6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第八条。我国有观点认为,依据1982年《公约》第60条第1款(b)项和(c)项的规定,在不会干扰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权利的限制下,其他国家可以建造和使用用于资源和其他经济目的以外的设施和结构。参见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3页。
综上所述,《塔林手册2.0版》实际上重述了1982年《公约》的相关规定,并据此将之解读为完全排除了沿海国对在其专属经济区内建造用于非经济性目的(例如军事或政府目的)的海上网络基础设施的专属管辖权,并未考虑存在不一致意见的部分国家实践。但无论如何,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建造此类用于非经济性目的的海上网络基础设施,应不在1982年《公约》第58条第1款中所明文列举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的范围之列。(70)Alexander Proelss ed.,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 Commentary, Hart Publishing, p. 472 (2017).而且,依据1982年《公约》第60条第1款(c)项,对于可能干扰沿海国在区内行使权利的设施和结构,沿海国可行使专属管辖权,这类设施和结构也应包括用于非经济性目的的设施和结构。
2.无人水下航行器作为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时的法律地位
关于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法律地位,目前尚属1982年《公约》未予规定的领域。2016年,中美就美军“鲍迪奇号”在我南海专属经济区投放的无人水下航行器的法律地位产生争议。中国国防部和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指出该装置属“不明装置”。(71)参见“2016年12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t1425293.shtml, 2019年4月25日访问。美方认为该装置属于船舶,用于政府目的,依1982年《公约》第32条享有主权豁免。(72)James Kraska and Raul Pete Pedrozo, China’s Capture of U.S. Underwater Drone Violates Law of the Sea, December 16, 2016, https://www.lawfareblog.com/chinas-capture-us-underwater-drone-violates-law-sea, 2019年4月25日访问。美方的主张显然不符合国际法关于船舶是“水上运输工具”的定义,也不满足《公约》第29条关于“军舰”的定义,因为该无人装置并未配备船员。(73)参见Mark J. Valencia, US-China Underwater Drone Incident: Legal Grey Areas, January 11, 2017, https://tribunecontentagency.com/article/us-china-underwater-drone-incident-legal-grey-areas, 2019年4月25日访问。
当无人水下航行器构成“通信、存储和计算装置”时,不排除其构成海上网络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因为《塔林手册2.0版》在叙述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时并未排除可移动的装置。依据《塔林手册2.0版》相关规则及评注,当无人水下航行器作为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时,其法律地位需要依据其所有权属性及用途确定。如果该装置属于私人财产,依据专属经济区的相关规则,其部署需要沿海国的事先同意,且沿海国可行使相应地管辖权。(74)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5评注6。该评注的脚注561中特别提及关于专属经济区内建造的问题,参照1982年《公约》第60条第1款和第2款。如果无人水下航行器是作为具有政府性质的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且完全用于政府用途(75)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评注2。时,对此类装置可主张豁免:当此类装置位于军舰或政府船舶上时,由于其未与作为主权豁免平台的军舰或政府船舶相分离,因而可以主张主权豁免,以及免于他国的执行管辖。(76)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评注1。当此类装置与军舰或政府船舶相分离时,由于其具有政府财产的属性并用于政府目的,亦可主张管辖豁免,包括执行管辖和司法管辖豁免。(77)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12评注8。
3.使用海上网络基础设施从事军事数据(情报)收集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当无人水下航行器或数据中心作为海上网络基础设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情报收集和数据传输等军事性质的网络活动时,是否应征得沿海国的事先同意?在未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是否违反“适当顾及”义务?《塔林手册2.0版》对这一问题做出了部分回答。首先,《塔林手册2.0版》认为,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享有的主权权利主要与资源相关,并且事实上仅规定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而非顾及更为一般性地利益,从而排除了沿海国基于安全利益行使管辖权的主张。(78)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3。其次,《塔林手册2.0版》回避了此类活动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的争议,而是直接表述多数专家的意见认为,军事活动通常与沿海国在专属经济区内行使有限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无关。(79)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47评注4。第三,《塔林手册2.0版》暗示性地主张,在用于军事用途或政府用途时,无需经沿海国事先同意。(80)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5评注2与规则45评注6脚注561,后者特别提及可受沿海国规制与管辖的应是用于经济目的。
笔者认为,上述解读更契合美国的观点。美国主张,是情报收集所获数据的用途而非数据本身决定了是否需要经过沿海国的同意。如果是用于军事目的,或用于确保航行安全,而非用于经济目的,那么就属于“海洋其他国际合法用途”,无须沿海国同意。(81)Raul Pete Pedrozo,Preserving Navigational Rights and Freedoms:The Right to Conduct Military Activities in China’s Exclusive Economic Zon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1. 1,No. 9,pp 21-22 (2010).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认为,这种区分将不可避免地造成海洋大国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开展军事活动,而沿海国家很难确定这些搜集的海洋数据最终和真正的用途。(82)[希腊]阿瑞斯-乔治·马盖里斯著,李途译:《美国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法律解释与实践——以中美战略竞争为视角》,《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2期,第32页。而且,随着海洋科考技术设备的升级以及军民两用技术的普遍化,区分两者的难度极大。(83)余敏友、雷筱璐:《评美国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妨碍航行自由的无理性》,《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16页。澳大利亚知名学者山姆·贝特曼 (Sam Bateman) 也指出,鉴于这些数据很可能用于针对沿海国的军事行动,它就与1982年《公约》第58条“各国在专属经济区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相违背,这种行为可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84)Sam Bateman,Hydrographic Surveying in the EEZ: differences and overlaps with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Marine Policy, Vol. 29, No. 2, p. 172 (2005). 转引自:[希腊]阿瑞斯-乔治·马盖里斯:《美国对专属经济区军事活动的法律解释与实践——以中美战略竞争为视角》,李途译,《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年第2期。
五、结论及展望
在《塔林手册2.0版》中,国际专家组一致认为,国际海洋法可适用于从海上网络基础设施或通过海上网络基础设施而实施的网络行动。(85)[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黄志雄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页。而且,《塔林手册2.0版》也郑重表明,其目的在于客观地重述“实然法”,避免反映“应然法”。(86)[美]迈克尔·施密特总主编,[爱沙尼亚]丽斯·维芙尔执行主编:《网络行动国际法塔林手册2.0版》,黄志雄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9页。但考察其中有关专属经济区内军事网络行动的相关表述,笔者认为,《塔林手册2.0版》选择性地重述了部分国家对实然法的主张,同时也部分反映了“应然法”。由于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一揽子协定,本身的规定存在着诸多的模糊性,例如对“和平目的”“适当顾及”等均语焉不详,因而对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合法性问题,在实践中存在着相对立的立场和做法。但《塔林手册2.0版》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表述,一方面,并未考虑专属经济区不同于公海的自成一体性,从而有意忽略了在专属经济区内对军事利用的限制应大于在公海内对同样行为的限制;另一方面,《塔林手册2.0版》的相关表述也没有体现1982年《公约》缔结后的国家实践对“航行自由”的限制。1982年《公约》缔结之后的国家实践表明,《公约》中规定的“航行自由”日益受制于非传统安全、海洋生态和环境保护、海洋资源的养护与利用以及国家安全等因素的制约。例如,沿海国日益以传统和非传统安全为由,对包括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内的海域主张管辖权,限制航行自由,有14个国家和1个地区在毗连区主张设立安全区或主张安全管辖权,有18个国家主张限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包括对所有或特定类型的船只通行施加限制。反之,《塔林手册2.0版》主要反映的是海洋强国特别是美国的主张和实践,例如纳入了1982年《公约》中并不存在的“国际水域”和“国际空域”概念,(87)例如,参见《塔林手册2.0》,规则11评注5,规则56评注2。认为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主要与资源和经济目的相关,“适当顾及”义务无关安全利益,专属经济区内的低烈度军事网络行动,是合法地利用海洋,无需事先获得沿海国同意等等。因此,《塔林手册2.0版》的相关解读是在《公约》的文字性规定基础之上,更多地参考了与美国立场一致的国家实践,尽管美国并非1982年《公约》的缔约国。
《塔林手册2.0版》的制定体现了一种跨国法律进程,即通过认知共同体(学者)解决网络空间的法律问题,调动精英和支持者与各国政府进行互动(解释规则,赞成或质疑),并将某种得到接受的解释内化。但这种认知共同体是经过选择的,法律规则的解释和重构均建立在这种选择的基础之上。这种造法方式和进程值得关注。正如我国参加编撰《塔林手册2.0版》的国际法学者所指出的,“在网络空间确立和适用何种国际法规则,直接关涉各国对信息网络资源的控制和支配,关涉各国在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并反过来对现实世界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产生影响。”(88)黄志雄:《国际法在网络空间的适用:秩序构建中的规则博弈》,《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3期。通过《塔林手册2.0版》对海洋法相关规则适用于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选择性重述和解读,通过在网络行动国际法规则领域主导性的话语权,传统海洋法领域有关军事利用专属经济区的分歧,会在网络行动领域有倾向地以准软法的形式固定,继而通过国家实践,包括通过政府声明以及实际行动等方式加以巩固,或者是为发展新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做准备,或者是重构现有的习惯国际法规则。这会对未来发展中国家在专属经济区内以安全为由应对军事性网络行动构成障碍。因此,笔者建议,一方面在顶层设计上需要更加重视国际法的多元造法进程,特别是软法或准软法造法进程,并为此结合国家战略需求打造高层次多元化的国际法人才队伍,以在国际法规则制定层面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另一方面,也需要更加重视国家立法和实践在国际法造法进程,特别是形成和发展习惯国际法规则中所发挥的作用。例如,针对本文讨论的主题,在国内立法和执法管辖层面,扩大对专属经济区内与网络行动相关的军事活动的管制,在与此相关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形成的过程中,确立自有的国家实践应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种国家实践,无论是作为习惯法规则形成过程中的支持者,还是作为一贯反对者,都会对国家未来的国际法主张提供有利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