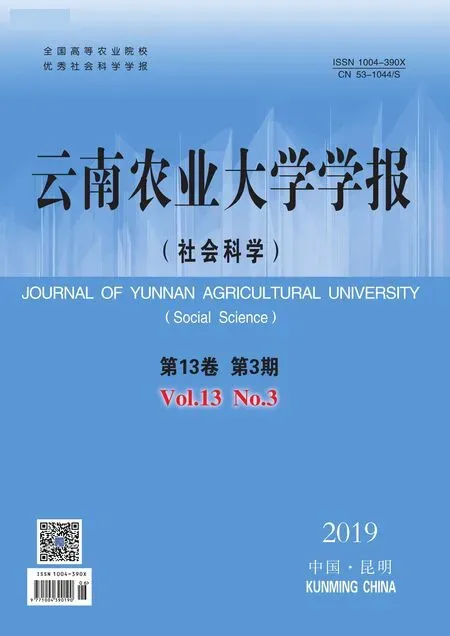脱贫攻坚背景下云南乡村治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2019-12-08吴艳
吴 艳
(云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脱贫攻坚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关系到2020 年我国小康社会目标能否实现,也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进程。乡村治理状况也会影响脱贫攻坚的成效。在我国脱贫攻坚的大背景下,云南省作为贫困面积最广、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主战场之一,乡村治理面临多重矛盾,任务艰巨而又繁重。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云南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针对脱贫攻坚背景下云南乡村治理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云南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乡村治理的内涵
“乡村治理”作为当下流行词,颇受学术界普遍关注,要了解乡村治理内涵,得先从治理说起。“治理”一词原意基本等同于“掌控”,也就是控制、操纵的意思。治理创始人罗西瑙认为:“治理是在一种共同目标支持下的活动,治理主体不一定是政府,也不需要靠国家强制力量来实现。”[1]全球治理委员会于 1995 年在《我们的全球之家》研究报告中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在管理共同事务时所采用的方式总和,是在调和各种社会冲突和利益矛盾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性过程。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和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2]。这个解释几乎表达了治理的内涵,在西方理论界更具有权威性。20 世纪末以来,国内学者也对治理理论进行研究。俞可平将治理定义为:指官方的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3]。根据上述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理论的阐释,笔者认为治理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政府并不是唯一治理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公共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等等,主体之间共同主动参与分工、合作、协调进行活动,最终实现利益共享。二是治理方式主要是多元主体根据科学规范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通过沟通协商平等参与活动。三是治理目标主要是实现治理的法治、公平、效率、参与、责任,最终实现“善治”。乡村治理作为治理理论的延伸,也具有治理特征。乡村治理概念是徐勇教授率先于1998年所提出,主要涉及:乡村治理的主体、权利配置措施、治理的目标和对应的过程。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的重点事实上也就是通过何种方式针对我国乡村加以管理,抑或是乡村通过何种方式达到自主管理,有助于落实乡村社会的科学建设和发展[4]。党国英则提出,乡村治理是国家基层的政府机构即乡村政府,结合乡村一系列权威部门所供应的服务,从而向乡村社会供应一系列相关公共产品的行为[5]。总结上述学者对治理、乡村治理内涵的解读,笔者认为,乡村治理是指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村党组织、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干部和村民等多元主体在科学规范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指引下,共同主动平等地参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共商共建共享过程,实现乡村社会有序发展,最终达到乡村“善治”状态。
二、脱贫攻坚背景下云南乡村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扶贫过程村民参与少
乡村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包括政府、社会组织、自治组织、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都将成为新的治理主体。他们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彼此间的分工与协作、沟通与配合,结成乡村治理的立体性交叉网络[2]。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提出实现精准扶贫要“要强化领导责任、强化资金投入、强化部门协同、强化东西协作、强化社会合力、强化基层活力、强化任务落实”[6]。习近平总书记的“七个强化”与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不谋而合,意味着扶贫治理包括政府、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等多元主体之间实现资源协作,形成合作互补的参与格局。但是,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的模式主要是“乡政村治”,乡村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其他治理主体相对比较薄弱。根据课题组对云南省部分贫困村调查发现,部分贫困群众“等、靠、要”思想特别严重,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存在“跑死县干部、累死乡干部、闲死贫困户”的现象,甚至还有扶贫干部亲自为贫困村打扫卫生。加之常年在村里的老年人和儿童占 71%,年轻人仅为 34%,留在村里大多是老年人和儿童,这就决定了村民很难参与到扶贫过程中,只能被动接受扶贫干部的安排,从而影响脱贫效果。另外,即使有年轻人在家务农,对扶贫也是知之甚少,更别提参与到扶贫过程了。在本次调查中,村民了解扶贫政策仅占8%,不了解扶贫政策的占 43%,只了解一些扶贫政策占 49%。加上扶贫行为几乎完全由地方政府把控, 未能把村民纳入其中,村民们理应在扶贫中具有话语权, 村民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审视扶贫政策的可行性,但云南贫困村的现实情况是村民往往只能被动地接受扶贫干部对整个扶贫行为的普遍性安排,从而导致扶贫效果不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贫困户对自己什么时候脱贫也不了解。
(二)乡村干部和村民法治意识淡薄
由于云南省集边疆、民族、山区和贫困四位一体,贫困村缺乏法治文化土壤,乡村干部和村民法治意识淡薄,致使脱贫任务之艰巨。一方面,因乡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致使扶贫领域侵害群众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上演。根据杨巨帅在文章《除“蝇贪”侵蚀助脱贫攻坚 ——从 325 起典型案例看扶贫领域突出问题及其治理》中对当前扶贫领域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总结归纳来看,在325 起典型案例中就有 218 起案例是“村官”涉腐,占67%;有61起涉及乡镇干部,占19%;有30起涉及县区干部,占9%;另外,还有13起案例涉及社区干部,3起涉及地市相关部门的干部[7]。另外,在调查中也发现云南省贫困村存在多起优亲厚友、套取挪用扶贫资金、贪污挪用旧城旧房改造资金等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村民法治意识淡薄,致使乡村干部有可乘之机腐败。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村民了解扶贫政策仅占8%,竟有 100%村民未参与过讨论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仅有 22%的村民知道成为低保对象的条件,不知道成为低保对象条件的村民占到78%。这些数字足以说明绝大部分村民对扶贫政策不了解,不知道如何维护自己权益,更谈不上对乡村干部的监督了。
(三)扶贫治理制度不完善
由于扶贫制度不够细化,致使部分地方“援助诱惑”“ 任人唯亲”扶贫等问题不断涌现。首先,因贫困户识别较为抽象而不具体,导致一些真正贫困户很难被确定为扶贫对象,享受国家扶贫资源。当前识别贫困户政策是先分配贫困人员名额指标再筛选贫困户,当贫困户名额指标下放给乡(镇)、 村之后,贫困户的识别工作就由基层扶贫干部来操作,此时的他们有很大的裁量权,这主要突出表现为收入在贫困线左右的村民对贫困户身份的争夺。因为云南贫困村属于熟人社会,部分基层扶贫干部就会受血缘、亲缘、友缘等关系的影响,这就造成识别出的贫困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扶贫对象。比如:云南大理永平县龙街镇贵口村党总支部原书记阿宏张、村委会主任杨利明、副主任阿群师及驻村扶贫工作队长、村党总支部第一书记张海金,把不符合贫困户识别条件的余某某等12户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围[8]。其次, 由于扶贫考核制度不完善,致使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大量耗费基层干部精力的形式主义不同程度表现。通过对云南贫困村访调查得知,经常要求扶贫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回头看、上报各种表,另外也多次让贫困户填表。近期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有一篇题为《50 元 1 头,扶贫观摩点上演“租牛迎检”闹剧》的文章引起广泛关注,这是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委县政府为深入推动全县脱贫攻坚工作,探索开展了“比进度、看特色,比突破、看亮点”活动,这样一场旨在激励大家在脱贫攻坚战中当先锋、作表率、创佳绩的活动,竟然发生了租牛充数、忽悠检查的闹剧[9]。这让扶贫检查在基层走了形、变了味,扭曲了检查考核的初衷。虽然扶贫考核引入第三方评估,使考核结果更具有客观性,但整个考核机制仍有不足,就是仅仅关注考核期内贫困户的收入是否增长,并且每次考核都与扶贫干部利益密切相关,这就难免会出现策略性扶贫和虚假脱贫。
三、脱贫攻坚背景下云南乡村治理的对策
(一) 构建村民参与扶贫过程机制
虽然政府广泛动员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等多元化主体参与精准扶贫,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作为扶贫直接受益人的村民,却没有话语权、参与权,从而导致扶贫效果大打折扣。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村民参与扶贫过程机制:一是引入村民参与贫困户、脱贫户识别机制。首先,因村民对于本村贫困户、脱贫户具体情况一目了然,所以,应该让村民对申请的贫困脱贫户进行公共评议;其次,由村干部严格依据贫困线来确定贫困脱贫人口数量;最后,由基层扶贫干部对已选出的贫困户和脱贫户进行多方了解调查等方法,最终确定贫困脱贫人员名额。二是引入村民参与扶贫决策机制。首先,对村民进行有关如何利用好扶贫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进行培训,让村民知道哪些政策、项目、资金适合自己脱贫。其次,建立项目评选、实施、监督和财政管理制度,由基层扶贫干部组织专家、村民对项目评选、实施、监督和财政管理制度进行民主讨论,确保村民的决策权。最后,村民参与对项目实施过程、资金使用进行监督并公开。三是引入村民参与扶贫考核机制。扶贫工作的效果如何,贫困户村民是最有资格进行评价的,因此,村民应当参与到扶贫考核中来。
(二)增强乡村干部和村民的扶贫法治意识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认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10]。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影响,“权大于法”等理念仍然扎根于村民心中。要想增强乡村干部和村民的扶贫法治意识,将会是一条充满挑战的漫长之路,因此,也要对贫困村进行法治扶贫。首先,由司法机关扶贫工作人员对乡村干部、村民进行法律和扶贫政策宣传,通过讲座、电影、小品等方式进行宣传,让乡村干部对法律望而生畏不敢贪,让村民维护好自己合法权益而尽快脱贫。其次,开展法律实践。“一次良好的法治实践本身就是最好的法制宣传教育,且效果远远胜过百次空洞的说教。”[11]所以,法院在审理土地纠纷案件、邻里纠纷、扶贫案件等时,可将法庭搬到贫困村进行审理,扶贫干部组织乡村干部、村民到现场进行旁听。最后,在贫困村成立法治扶贫中心机构。法治扶贫中心主要由律师、省级政府扶贫办等人员组成,主要职责是解决村民的扶贫投诉、法律咨询、扶贫监督、贫困户需求表达等问题。这个机构专门为村民在扶贫过程中遇到问题进行解答并处理,这既调动了村民参与扶贫工作的积极性,也减少了贫困户对扶贫项目资金的疑虑,从而为扶贫之路扫清障碍。
(三)完善扶贫制度扶贫政策
在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首先,完善识贫机制。从识别贫困户来看,扶贫基层干部要严格依据贫困线来确定贫困人口数量,引入村民参与确定贫困户,再分析每个贫困户致贫原因,并制定适合该贫困户脱贫的方案,做到“一户一策”。从识别脱贫户来看,对脱贫户的识别工作由地方政府、独立第三方机构、村民共同进行评估,这既要看贫困户是否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也要看其收入是否处于长期稳定状态之中,还要防止出现虚假脱贫现象,评估人员要对评估情况的真实性负责。其次,完善扶贫考核评价机制。针对扶贫领导频繁填表报数、迎评迎检、陪会参会等形式主义问题,国务院发文通知要求各地要减少填表报数量和减少检查考评干部考核,这样为扶贫干部减轻了负担并能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中。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上级政府应该对每个基层扶贫干部职责进行细化以及达到何种目的,对扶贫干部职责也要因村因户因人而异,不能搞一刀切,年终考核时要逐条对细化的职责和目的进行考核,考核周期一般为一年,最多为半年。另外,村民对扶贫干部做了什么具体之事,有什么效果最知晓,因此,对扶贫干部的考核还要引入村民参与制度进行民主讨论,而不能从材料到材料、会议到会议进行考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