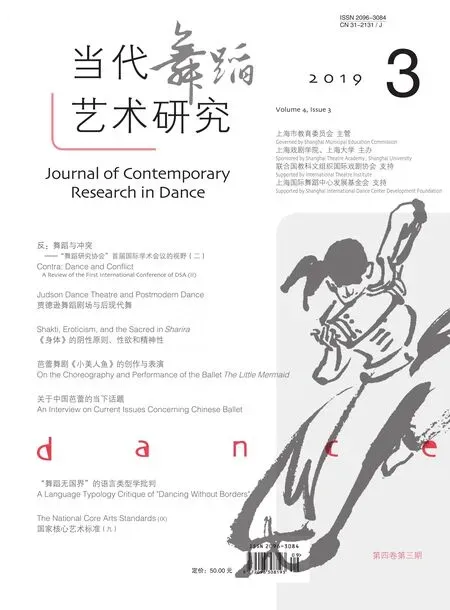“舞蹈无国界”的语言类型学批判
2019-12-08刘建
刘 建
2019年初,新华社发表图片新闻:“1月20日,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霍夫堡宫隆重登场,以中奥友谊为主题,弘扬两国传统乐舞文化。数百名中奥各界嘉宾和青年舞蹈艺术家出席活动。图为舞蹈演员表演首部芭蕾和国标舞相结合的舞剧《海河红帆》经典片段。”[1]图片中的舞者有穿大褂的、牛仔服的、学生装的、工人装的、华尔兹裙的、旗袍化芭蕾裙的,还有梳抓鬏、戴棒球帽的……他们都在用力挥拳,但不知在跳什么。“跳什么”涉及舞蹈身体语言,而语言的社会性决定了它交流的属性,但要跨国交流,则需要翻译,否则不同类型语言间交流就如同听天书。因为以自然的身体作为语言媒介,所以舞蹈身体语言的交流会比语言易于沟通。但同时我们又看到,芭蕾的“外开”是“荣耀上帝”,婆罗多舞的“外开”是“迎接众神走下大地”,它们要进行跨国交流,必须经过同样的翻译,才能由能指的舞种形式知其所指。
长期以来,中国舞蹈界的“舞蹈无国界”说其实并不是在考究此类语言学的问题,而多是用于自我辩护——辩护中国舞蹈可以从外国拿来,也可以改造加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中潜藏着某种难言的自我后殖民的集体性无意识。由于掌控话语权的舞蹈“大法官”在场认定,这种无意识后来就爬升为意识。
推算起来,“舞蹈无国界”说大抵在近代中国的“西风东渐”时便已起范儿。伴随着已无话语权的裕容龄的《双剑舞》《菩萨舞》的式微,和炮舰、西服、英语一同进入中国的舞厅舞、芭蕾舞、现代舞同时获得了话语权和语言权,遍地生根。所以即便到了抗战时期,这种舞蹈“借词”表达的现象也是方兴未艾:国统区舞剧《嫦娥奔月》和《木兰从军》用的都是西洋舞蹈语类;解放区“新秧歌运动”外更时髦的是苏联的《海军舞》《乌克兰舞》和由斯诺夫人传授的美国踢踏舞。当代以来,芭蕾舞、现代舞、国际标准舞乃至街舞更是逐渐成为主流,或成为中国“学院派”舞蹈的重点学科,或是在北京舞蹈学院的“黑匣子”中建立了研究中心;与之相伴的,是理论家们用后设理论建构的“舞蹈无界”“舞蹈跨界”“走向世界”云云。于是,更大范围的“推广”式交流便成了一种社会形态。
一、语言类型学的“身体安检”
语言是行为科学,为人类特有。人类存在某种预设的行为程序或一些内在、天生的语言能力,对这种“程序”或“能力”的探索是本体语言学的追求目标。于此之中,“语言类型学主要关注那些可观测的、有形可见的语言形式,并通过不同规模的采样调查,发现它们在世界语言中的分布模式(如发生频率、相互间的组配关系、区域分布以及历时演变等)”[2]526。在舞蹈身体语言学中,这些关注点也异常重要。我们可以看到,中非舞蹈、西欧舞蹈、东亚舞蹈,它们不仅有各自自然“粗身”的天生程序或能力(比如黑人的肤色和爆发力)、规训“细身”的可观测的有形形式(比如白人的“开绷直立”),还有表达“业身”的相互组配关系(比如黄种人东亚舞蹈“手眼身法步”的匹配)。也就是说,舞蹈身体语言类型学至少是关乎语境、语源、语支和语种一体性的学问。其功能是能区分出舞蹈交流中的“主位”与“客位”①,以达到从宏观到微观的异质身体文化与审美的交流。
早在21世纪伊始,韩国就创办了“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力图以“主位”的身份建立东亚舞蹈中心(其背后是现代、三星等财团的支持)。这一“舞蹈无国界”的比赛分设两大类别——传统舞蹈和现代舞蹈。前者包括西方古典芭蕾(Ballet Dance)和东方的民族舞蹈(Ethic Dance)赛场——民族舞蹈中大传统舞蹈文化的古典舞,诸如日本雅乐、韩国呈才等(小传统舞蹈文化的民间舞蹈不在此列),其目的是借以保持东西方不同类型古典舞的平衡。后者赛场的命名实则指现代舞。在欧美人眼中,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由他们主导的西方文明对与之不同者,特别是东亚传统文明所进行的否定和改造过程,舞蹈也是如此。为了防止类似“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严复语)的困局,赛事主办方坚定地设立了传统舞蹈与现当代舞相联系的语源框架。比如民族舞蹈赛场中,传统的“萨尔朴里”作为第一轮比赛内容,在被认可之后,才能进入下一轮的由此延展的当代舞“萨尔朴里”创作。也正是在此舞蹈身体语言类型学的原则下,由以芭蕾和体操训练为基础而构成的“中国古典舞”《良家妇女》在第一轮就被韩、日评委请出了传统舞蹈赛场——尽管它在国内获得了“桃李杯”中国古典舞组别的奖项。
历史与社会原因之外,由于传统得到应有的保护、传统舞蹈得以垂直传承,日本人比韩国人更沉着一些。近现代以来,他们的雅乐、能乐、歌舞伎等古典舞蹈多以语支保证了其语种——舞种的类型辨识,为国舞之重器。因此,哪怕是日本现代舞“舞踏”,也能见出雅乐、能乐的痕迹,见出其传统舞蹈“主位”转向;而不像近现代以来中国舞蹈“主位”的180°转换。“转向”和“转换”是不同的概念,用日本学者的比较来说,转向法则支配下的文化与转换法则支配下的文化,存在着结构上的差异;日本文化就类型学而言是转向型文化,而中国文化则是转换型文化。②也就是说,舞蹈身体语言类型的“转向”是梅兰芳先生所说的“移步不换形”,不换“自我”“主位”;而“转换”则是“移步换形”,换成“他者”“客位”。
由于转换成为“他者”或者准“他者”,无论是传统舞蹈还是现代舞蹈,中国舞蹈身体语言类型都处在一种混合语的“假晶状态”,形成“不辨牛马”的形式直观,所谓“舞蹈无国界”说,便是由此而生:一方面,可以为西洋舞的输入寻找托词;另一方面,则可以为自我后殖民化(自己把自己西洋化)的舞蹈身体语言混搭类型的输出进行遮饰。从舞蹈文化“输入”来讲,我们几乎一直处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的被动态,把外国的舞蹈直接插秧于中国的土地;从舞蹈文化“输出”来讲,无论国内外,我们都很少给世界提供身体文化与审美“主位”的食粮,以致在维也纳中国新年舞会上《海河红帆》送上的也是芭蕾舞混搭国标舞的盛宴。
韩国人和日本人在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上“主位”的自信,在于其身后各自特有的“库藏空间”(inventory space)。从东亚到南亚,印度舞蹈之所以能走向世界,也在于其鲜明的舞蹈身体语言类型及其身后的“主位”的语料库库藏。在语料出库成为语篇后,它们施之于本土并与世界共享。从语言类型学来讲,这些舞蹈形式和功能意义之间的关联对立关系及其组成的层级架构体系,可称为“库藏结构”,并可用“分类树”直观地呈现出来[2]530。像印度古典舞风格鲜明的7个流派,它们也是历经半个世纪建设而成的。仅就舞蹈教学的“舞蹈无国界”而言,一个有趣的比较是:在中国舞蹈院校中,我们会见到诸多执教西洋舞的西洋教师;相反,在印度舞蹈院校中,我们则会见到诸多学习印度舞的西洋学生。
中国舞蹈类型的“主位”确立,也必须依赖于自身层级架构体系的“库藏空间”或“库藏结构”。王蒙先生曾有《天下归仁:王蒙说〈论语〉》《与庄共舞:人生的自救之道》等文章,强调了“中华文化是以汉语与汉字为本位的文化”“汉字是中华儿女的精神家园”的命题:所谓中国传统文化,从学理上是儒家与儒道及与其他各家的互补;从语言文字上看,是汉语与汉字文化,是概念崇拜、概念互联、概念递升、终极概念的追求与整体判断。③语言类型的定型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内语言”;舞蹈是审美的身体语言类型定型,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外语言”。它们都凭借着自己的语料库形成“主位”,与作为“客位”的世界交流。如同联合国文件的5种语言中必须有汉语文本一样,在世界舞蹈之林中,也应该有中国舞蹈“主位”的大树。大树有枝杈,即便在国界以内,这种主客位的界限也有“分类树”,不能轻言“舞动无界”:汉族舞蹈与藏族舞蹈有界,藏族舞蹈的康巴舞蹈与安多舞蹈有界,青海玉树地区康巴舞蹈“卓”有宗教性的“新寨卓”与世俗性的“白龙沟卓”分界;由于信仰藏传佛教,所有这些传统藏舞都会与“上帝死了”的现代舞地面动作划清界限。
如此,舞蹈不仅有国界,而且在一个民族国家中还有民族的界限、区域的界限、大传统舞蹈文化与小传统舞蹈文化的界限、生活舞蹈中世俗生活与信仰生活舞蹈的界限……它们都需要在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上一一确立与辨识,以备跨界交流。
二、“身体描写”与跨界交流
舞蹈身体语言的类型化在于身体的细致描写,而后才能以身体语篇(文本)实现跨界交流。中国舞蹈而今年产量世界第一,尤以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的舞剧为突出。仅古代题材,就从先秦的《霸王别姬》《孔子》一直跳到清代的《红楼梦》《情天恨海圆明园》。出国巡演时,这些舞剧每每遇到观众的抱怨:节目单的说明太复杂,演出期间电子屏幕的文字说明太干扰。凡此国内观众几乎习以为常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尚未能凭借类型化的“身体描写”达到“Body to Body”(身体对身体)的交流。如此,语言类型学中的“新描写主义”(New Descriptivism)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思考框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研究取向和学术价值观,新描写主义是在跨语言比较的视野下,追求以理论的眼光和科学分析工具,对微观的语言事实进行细颗粒度的刻画和描写,其特点主要为“本着‘从一颗沙子看世界’的精神,摒弃无法证实的假设,遵循认识的确定性、描写的完整性、问题的真实性和理论的创新性四大原则,认识到心理内容和形上内容的实在性,面对具体的语言事实,从单维度的低阶描写入手,必要时过渡到多维度的高阶描写”[3]549。它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重视语言学理论工具的建设,二是强调跨语言比较,三是注重微观语言事实以及显性或隐性结构的细颗粒度描写,四是力求通过微观描写、刻画和分析来揭示语言的共性与个性。
在上述第一、二两个方面,长期以来,中国的舞蹈理论往往迁就实践:或因自身的不充分即登台预设出某些“理论”(比如“中国古典舞”“中国民族民间舞”概念的提出),或因实践不明而比附发明某些“理论”(比如“中国舞剧”“原生态舞蹈”概念的滥用)。“舞蹈无国界”等说法包括前后者,是逐渐扩张开的非学理性概念,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舞蹈的发展,使其“主位”的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一直处在混沌状态,特别是亟待建设的中国古典舞。
和语言类型学一样,舞蹈身体语言类型研究也可以采用两种证据进行确立与辨识——“内部证据与外部证据”[4]。当我们知晓《良家妇女》的舞蹈身体是以“芭蕾+体操”的内部方式训练出来的时候,其“中国古典舞”类型的名实就值得怀疑;而当它在“韩国首尔国际舞蹈比赛”中被淘汰出传统舞蹈类的“民族舞蹈”赛场时,这一外部事实就更加使我们明了它不是“中国古典舞”类型,不能以“舞蹈无国界”为名代表“国舞”走出国门——它甚至在国内都无法获得一致认同。凡此,在新描写主义的理论眼光中称之为一种实证主义研究路向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5]—— 被证伪的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不具备跨界交流功能,因为它脱离了“主位”应有的范式。
在《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第七章里,卢梭用兴奋的笔墨讲述了他沉迷于植物学分类并得到最终升华的经历,这有益于我们对舞蹈花园的“鲜花”类型与功能的理解。与鲜花因不同类型而烂漫缤纷一样,世界的舞蹈也是这样构成的——从古典舞到民间舞,从传统舞蹈到现代舞蹈,从传统舞蹈中古典芭蕾的流派到现代舞中玛莎· 格莱姆与皮娜· 鲍什舞蹈的风格差异。在此意义上,《良家妇女》其实大可不必为“中国古典舞”作伪证。中国古典舞草木深深的大地上本有先秦西施、汉代赵飞燕、唐代杨玉环、元代“十六天魔舞”中的舞女、清代裕容龄等这些“妇女”起舞,她们的舞蹈重建应该成为中国古典舞女性身体语言类型的确定性事实,而且还能够确立“时间的一段儿,空间的一块儿”的中国古典舞的分类树,借以进行“舞蹈无国界”的跨古典舞比较。同样在21世纪初,法国人在巴黎歌剧院举办了世界古典舞展演,印度古典舞奥迪西流派的舞王和他的女儿就曾以一台节目与古典芭蕾俄罗斯学派的《彼得大帝》进行对话,可惜在这一“舞蹈无国界”的专属舞种交流中,没有中国古典舞的身影。
这样,我们就需要进入第三方面的微观语言事实的描写。比之从宏观现象出发而进行概览式、概略式研究,微观语言事实的研究可以明确限定研究范围,精准控制研究对象,易于聚焦研究问题。新描述主义追求对语言事实或现象的细颗粒度的微观描写和刻画。它从个别的微观事实描写入手(比如古典舞的题材与主题原则和程式化的表现手法),旨在通过局部描写勾勒整体(比如从词篇、句篇到语篇),遵循认识的确定性、描写的清晰性原则,从低阶的单维度句法描写,走向多维度高阶描写。正所谓“从一颗沙子看世界”(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由此,才能揭示出第四方面宏观的语言类型的共性与个性规律。
与杂技、体操、冰舞的身体展示(炫技)不同,作为身体语言的舞蹈是以“身体描写”为己任,其间第一要有描写之“事”(叙事),第二要有叙事之“舞”(舞种技术)。平日我们评价舞蹈的好坏排序是“有事有舞”为第一等,“有事无舞”为第二等,“无事有舞”为第三等,“无事无舞”为第四等。现在还应该加上一个限定:其“事”其“舞”都需要有百花齐放的植物学那样的分类,使一体化的描写(创作与表演)和解释(表演和接受)构成完形。在韦伯的概念当中,“宗教”是一种“集体行动”,世界各大宗教塑造了人类的主要文明,艺术家则用建筑、美术、音乐和舞蹈使这些文明中的神性得以流淌人心。古典芭蕾舞剧《吉赛尔》的基督教宽恕精神是在童话传说和精致的“疯舞”“鬼魂舞”“墓地大双人舞”中得以呈现与感知的,这是“古典芭蕾”的事与舞。当代芭蕾舞剧《红色吉赛尔》灌之以同样的基督教精神,其事其舞却指向了红色革命以及“红色土风舞”和非程式化的变形的双人舞,因为它是“当代芭蕾”。由此,“古典芭蕾”和“当代芭蕾”的共性与个性规律被揭示出来。其他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亦然。
在这样的一体化描写与解释中,描写先于解释——甚至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依赖描写而放弃解释”,因为新描写主义认为解释寓于描写之中,深度刻画和描写就是解释,解释已先在地内化于高阶描写,其描写的“本体论”和解释的“认识论”已然合二为 一[3]540,543。我们以古典芭蕾(古典舞)和当代芭蕾(当代舞)为参照来批评(或证伪)《良家妇女》的非中国古典舞性质,就是批评它在“事”和“舞”上均不是从微观的舞蹈身体语言类型出发,从而导致了失去语类限定的舞蹈语篇的失控。就“事”而言,《良家妇女》之妇女没有“什么人在舞”的历史身份、社会身份、阶级身份、家庭身份;没有“为何而舞”的古典思想资源、叙事动机、调度及身体投射言说,属于“没事找事”。就“舞”而言,其跳、转、翻、控制、技术技巧,完全是芭蕾、体操、毯子功的混编组合,属于“为舞而舞”。因此,它便成了缺乏历史与语类实证主义的“假装”的古典舞④,无法与日本的《兰陵王》、韩国的《春莺啭》对话。
比这种“假装”装得更高级一点的是批量的用古典题材创编的中国舞剧,从《霸王别姬》到《红楼梦》。就“事”而言,因为有司马迁和曹雪芹的文学文本撑腰,其所叙之事不能不说是古典,此外还有服装道具、音乐舞美的帮忙;但就本体的“舞”而言,其舞种类型不明的技术其实就是《良家妇女》的翻版,外加同样源自西方的双人舞、三人舞技法——换言之,只要“良家妇女”改换一下服饰,她就可以去跳“虞姬”、跳“黛玉”。故事是中国的故事,舞蹈却不是中国的舞蹈。也正因为如此,这些舞剧无一被冠名“中国古典舞剧”,因而它们也无法进入“舞蹈无国界”的巴黎歌剧院的世界古典舞展演。
结 语
中世纪晚期,欧洲的国王和贵族领主倾向于将脏器和遗体分离安葬,其身体地理学的分布表明了一种“贵族行为”:死后象征性地确认和昭示对领地的权力。这种行为后来演化为法国国王灵柩落葬时礼仪官高呼的仪式化用语:“国王已死!国王万岁!”此时,作为自然之体,小写的、可朽的国王故去了;作为政治之体,大写的、不朽的国王(即王权)得以延续,通过拟人像庆祝那在棺材之上显露出来的不朽和王权的尊荣。⑤这种身体地理学的分布在中国汉代以多重个体的安葬而通行,并且还带着贵族们所喜爱的舞蹈画像砖石一同安葬,使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地的汉画舞蹈各显千秋地遗存下来。自然身体的安葬引出了文化与审美的身体的“陪葬”,形成所谓的“不同的贵族已死,不同类型的汉画舞蹈万岁”。如此,与古代欧洲贵族舞蹈不同的舞蹈语类就留在了中国,不仅与中国历史上前此的周代和后此的唐代舞蹈划分出了语言类型差别,而且还通过“身体描写”划分出了自己的语类——从建鼓舞到盘鼓舞。它们中精致的存在与激活,即是中国传统舞蹈中的古典舞,可以参与到世界古典舞身体地理学分布的对话中。
分布依托并见出类型。有同一类型的分布,如欧洲之芭蕾、东亚之雅乐;有不同类型的分布,如中国汉族舞蹈与少数民族舞蹈;还有同一类型中子类型的分布,如芭蕾之四大流派、雅乐之日本、韩国与中国之别……不管何种类型,它们都是一种身体语言范式,有实践范例,有价值标准,并依靠着大量的积累而使范式具有了稳固性,我们所说的传统舞蹈即归于此。一旦这种范式发生改变或变异——包括对于这种范式视而不见的“假装”建设,其舞蹈身体语言类型便被转换或消解,“主位”的自主改换为向“客位”的“借词”。在中国当代舞蹈的话语权中,这种行为常被美其名曰“舞蹈无国界”。
于是,我们最终回到了舞蹈身体语言政策的问题上,特别是对那些被中断或濒危的传统舞蹈身体语言类型的“主位”确立问题上。在语言学领域,近年来,濒危语言问题不断引起多学科领域的关注。例如,201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濒危语言政策与规划》(Policy and Planning for Endangered Languages)一书就表明:当前的濒危语言问题不只是语言学、社会学领域关注的话题,还需要结合语言教育、语言歧视和去殖民化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当然,这还需要在微观层面进行建设,如科学记录濒危语言的语音与文字,建设濒危语言语料库。[6]凡此,与中国传统舞蹈的建设在学理上是一脉相通的。换言之,没有这种语言类型的思考与实践,“舞蹈无国界说”无异于滥竽充数时发出的音响。
【注释】
① “主位”(Emic)和“客位”(Etic)两术语源于语音学中的“音位”和“音素”。人类学将其用于田野工作的“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把被研究者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客位研究”则是指研究者从自身角度去研究对象,把握对象存在环境的客观标准。我们这里使用“主位”是指跨界交流中的主体性;“客位”是指交流对象的客体性;无主体性“主位”,即无所谓“客位”,也无所谓跨界的“舞蹈无国界”。
② 参见:韩东育.东亚的近代[J].读书,2018(8):102.
③ 参见:崔建飞.从“皓首穷经”到融会贯通[J].读书,2018(8):104.
④ 新描写主义把“假装”看成是“反叙实动词”,预设了假装是一个行为,认为“假装”类动词宾语的真假,跟宾语的“情状类型”直接相关: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动作时,该宾语为真;当宾语的情状类型为状态时,该宾语为假。简言之,判断真假的标准可以表述为:在“假装”后面,动作为真,状态为假(参见:杜世洪.新描写主义与“假装”的高阶描写[J].当代语言学,2018(4):546.)。具体到舞蹈身体语言类型学的动宾结构,即是“跳中国古典舞”之“跳(舞)”之动作为真,“中国古典舞”状态为假。
⑤ 参见:恩内斯特· 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M].徐震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553 —— 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