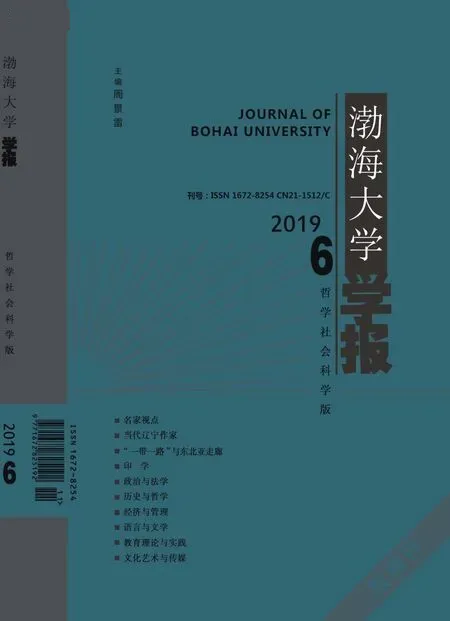边界向外,想象向内
——浅谈苏兰朵中短篇小说集《白熊》
2019-12-04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文学编辑部天津300384
崔 健(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文学》编辑部,天津300384)
在苏兰朵早期的中篇小说《女丑》中,作家塑造了一个侠气十足的女性形象碧丽珠。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北方女性——大气、执拗、豪爽、江湖气。碧丽珠身后的隐形叙述者苏兰朵在个人阅读感受中,她一贯的“文学形象”几乎与碧丽珠这个人物是吻合的。她的小说文字冷静、克制,鲜有在文字间可以察觉到她的性别。小说题材也从早期她较为熟悉的广播电视领域逐渐拓展到更多生活领域。正因如此,在集中阅读苏兰朵一系列小说之后,便能察觉出作者创作体验带来的飞翔感。她已脱离了自己有限的直接经验进入更为广阔的间接经验的创作阶段,可以娴熟地处理和把握似乎并不贴近自己生活的小说素材,进入到成熟作家的自觉创作时期。
一、“故事修辞学”与叙述的困境
苏兰朵并不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个人观念,她用故事来表达一切。故事是她所追求的小说技巧的核心,她把自己对事件本身的态度与观念隐藏在叙述中。故事线条处理得相当凝练、优美,她通过改变和调试小说的速度、节奏、语气来把控故事的进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不仅是讲故事的高手,更是一名强势的游戏制定者。
“有一种快感来自了解了单纯真实,有一种快感则来自了解了真实并不单纯。两者都是文学效果的合乎逻辑的来源,但它们不可能两者都同时充分实现。在这一方面,也想在其他所有方面一样,艺术家必须有意无意地进行选择。……”[1]就这一点来说,苏兰朵大概更倾向于选择前者。无论是否处于作家的自觉,苏兰朵都在小说技巧方面显示了更高的技艺。她更执着于“如何”讲好一个故事,也对讲好一个故事的规则和方法相当在行。在她的创作谈中,她说道:“在我的小说中,始终有个核心词——故事。在这一观念的笼罩下,我的小说,从开始创作时,就是有意识写作,非常注重传统小说的基本元素,比如结构、人物、故事、环境、思想,以及叙述。……”[2]她区别于同时代别的作家的地方便在于此。她相当迷恋构建一个相对封闭和自足的文学空间,自己如上帝之手,从一件空荡荡的房间开始,建造起一草一木、人物时间。
在《白马银枪》《雪凤图》《三月人偶》中,苏兰朵显然已经能够相当娴熟自如地迅速搭建故事的主体,并在主体之内完整优秀地讲述一个好听的故事。《白马银枪》的“白马银枪”白靠行头和《雪凤图》中的吕纪“雪凤图”几乎成为了小说的核心。《白马银枪》由偶然再次与早已遗失的“白马银枪”相遇作为起始,在与另一位竞争买家的接触与交流中,作为情节主要推动者的吕彤围绕着行头的来历,不断地怀疑和追问,慢慢揭开了自己和整个家族的身世之谜。每一次故事的转折和发展,都几乎需要或者说必然要在“白马银枪”的引导下推进。而另一个相似题材的小说《雪凤图》则是由一幅来历不明的名画引起,“雪凤图”不仅在,同时也深藏着上一辈人感情的创伤和家族隐痛。两篇小说都借助了某种文学意义上的“道具”完成了完整的叙事。借助道具来完成小说叙事是一种在短篇小说中非常常见的写作手法,“道具”是打开虚拟空间大门的钥匙,遇到匹配的门锁扭动钥匙就会照见一间干净纯粹的房间。钥匙所能提供的东西有很多,比如制造矛盾与动机,比如引入新的人物和推动新的情节,再比如将故事的一切歧途和转折带回最初。这是一个很好用的机关。苏兰朵在创作之初选定了道具的时候,其实几乎就已经选好了有关小说的一切——道具与“故事”是一体的,道具就是故事本身。正因为如此,《白马银枪》和《雪凤图》的意蕴也止步于两个道具本身所带来的事件因果,在紧贴道具的同时失去了某种选择的空间与多义阐释的可能。即使在短篇小说中,道具的运用也应更加轻盈,不能真正代替故事发生时事件主体的动力,成为小说叙述的全部。
作为故事背后的隐藏叙述者,苏兰朵在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中对于“描写”是相当吝啬的,近乎于冷血。仅有的描写更多地体现在对事物形态、颜色或者是气味的描摹,以便使事物在虚构的空间中看起来还是他们原本的样子。
比如在《白马银枪》中父子的第一次见面:
“吕彤打量着这位老人,中等身材,很瘦,虽然拄着拐杖,背却挺得笔直,从五官上看,五官上应该有着鼻直口方的英俊容貌,只是现在面色晦暗”。
躲藏在吕彤背后的叙述者并没有越矩。初次见面的老者,在吕彤眼中所能观察与感受的,正是这样客观与冰冷的五官描摹。而第二次未与白胜堂见到面,却对他的秘书林小姐有了一番观察,写道:
“……白净、高挑、直发,一身休闲套装穿得随意又低调,从做工和面料上看,价格应该不菲”。
苏兰朵作为隐藏的叙述者完全藏身于故事第三人称的背后,用小说人物的语气、心理来说话和思考,在这一点上,苏兰朵几乎做到了无懈可击。
在与竞争买家的第一次见面时,简单的几句对话就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实不相瞒,这套行头是我家的祖传之物”。
……
“这东西原本是我外公用过的,后来传给了我的母亲。对我们一家来说,它的意义非同一般。……”
……
“吕先生今年有……47?”
作家推动情节发展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作为道具的“白马银枪”已经由此顺利地和家族历史实现了关联,她将一次孤立的对话内容转化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工具。节奏陡然变快。在《叙事的本质》一书中是这样界定故事与情节的:“故事是叙事形式中代表性格和行动的笼统概念,而情节则作为一种更为具体的术语仅仅意指行动本身,而把针对性格的关照降至最低限度。”[3]讲述一个成功的故事,在故事的组成方面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自然都是必不可少的,但作为动态连接的情节显然是故事能够被顺利讲述直至终结的唯一动力。苏兰朵在《白马银枪》和《雪凤图》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力量,表现在没有采用在《女丑》《初恋》《白裙子》中对人物性格本身的着笔,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将情节更合理地推演和布局上。在这几部作品中她都将情节的推动作为主要的任务,她所要实现的是如何在一个平凡的素材里不断裁剪与翻新,如何在现有的经验里形成一种更加严密的写作规范。
读者在作者既定的规则中游弋,自主的想象努力和偶发的阅读意外都会随之碰壁,身处故事的迷宫之中,读者听命于作者的声音,作者也要听命于有限的想象空间,这显然会带来写作的困境——当想象穷尽,故事的边缘显露,再强大的造物主也无力把控笔下主人公的人生时,作家会先于读者表现出软弱与妥协的一面。在自己的创作谈中,苏兰朵谈到正尝试着使用美国创意写作的方式进行新的创作,所以故事结构整体看来显得空荡,小说的边缘也会过于明确清晰,丧失了因模糊而带来的多意性。但另一方面,情节的逻辑推演却无懈可击,它足够稳定,就像一笔精准完美的数学证明演算,用一种最简单但却最难的推理方式来证明命题的合理性。创意写作课程所提供的原理和规则在写作故事本身的操作上固然是有效的,但受过创意写作训练的写作者如何能够突破这种虽有效但顽固的故事模式才是真正的写作难题。虽然由这种方式创作出来的故事符合读者阅读的某种趣味或者快感,但容易丧失文学的原味和作者真实的情感力量,转而向着小说通俗化的趋势发展,这正是苏兰朵在小说创作中应该提防和警惕的。
二、想象的“边界”
苏兰朵在小说创作中一直表现出一种罕见的单纯,即她在有限经验的想象之下穷尽一个故事的所有可能。她的故事是有边缘的,高度提纯的,这种单纯部分源自她对自己创作的足够把握或者说是严格控制。当然从另一角度说,这也使得她在题材选择上受制于创作的手段而丧失了某种复杂的不确定,这也必然暗含着有限经验下的想象局限所带来的隐患。在“能指”被不断提升的过程中——通过写作的各种训练(在创作谈中她曾谈到叙述能力、结构能力、挖掘思想性的能力、设计和刻画人物的能力、衍生故事的能力、环境描写的能力、语言能力,等等,都是经过自己有意识的写作锻炼的),“所指”也有被消耗或者偏离的危险。电影《楚门的世界》中,男主角终于发现自己的现实生活是一场受人摆布的真人秀,他最终选择跳出生活的“边界”面对真实生活的未知。作为造物主的作家,就如楚门一样,在既定的想象边界之内,很快就发现边界对于想象本身的约束,预设的想象是无法穷尽一切生活的可能的,更无法完美再现真实命运的复杂与变化。
于是,苏兰朵开始向“科幻”题材(或者未来可能由此展开的更广泛的类型小说的创作尝试)创作靠拢。我并不感到意外,科幻小说给予想象以足够宽容与理解的空间,无疑是可供她发挥的一个更为安全与舒适的方向。在小说集《白熊》中的两个作品《白熊》与《嗨皮人》就几乎验证了苏兰朵这一类小说创作的尝试策略。
苏兰朵的“科幻”题材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幻小说,小说本身并没有足够严密的科学理论作为创作基础,可能更应该被称为是软科幻小说或者幻想小说。但小说在苏兰朵强大的素材支配和小说结构能力之下形成了脱离现实而合乎自身逻辑的完整的时空空间。在小说《白熊》中,苏兰朵创造了做爱机、度假程序、传达情绪与感觉的传感线等现实生活本不存在的未来之物。在未来世界由人工智能带来的人类自主情绪的缺席几乎被这几种幻想出来的仪器所全部代替了,它们几乎可以完成现实生活人类能够想到的绝大部分行为能力。有趣的是,苏兰朵并没有在这个已经被她完美塑造的幻想世界停留得太久,而是在一次貌似出现的错误度假程序中将主人公陈木送回了“原始世界”(这个原始世界其实与之前的世界相比更接近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但是原始世界(其实可以看做现实世界)反而呈现出了“虚幻”色彩,苏兰朵通过对白熊岛环境场景的“陌生化”处理,让“白熊岛”这个本就是人类生存现实本源的地方成为了远离尘嚣的“科幻”想象。现实是什么呢?哪一个才是现实呢?在这里,苏兰朵几乎模糊了现实与虚幻的界限,也模糊了幻想与写实的界限。在《白熊》中,她笔下的陈木极力想避免现代势力对原始纯粹的入侵,却又难舍对现代生活的依恋,陈木是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中的所有当代人的写照。
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嗨皮人》却进入了另外一个幻想空间,人类可以摘除自己不想存在的记忆,而记忆的不可逆,注定会将人类抛入更为可怕的境地。主人公艾米小雪就是在一次记忆摘除手术的意外之后,体会了这种生不如死的失忆状态。更为虚妄的是,在小说结尾艾米小雪无法掌控自己的记忆,更无法得知自己失去了记忆,失去了怎样的记忆,她真正失去的其实是“失去”本身。这已不是一桩个人的恩怨,这更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失忆,它更像一场人类的集体失忆事件,被抹去了记忆,也被抹去了存在的痕迹。
科幻小说虽然是架空在现实之上的想象之作,却并没有办法摆脱现实生活的逻辑基础,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里,与苏兰朵的创作一样,即使是更优秀的科幻作品也依然在想象的世界中承载着对现世的失望与期待,表现的依然是人类现实生活中已存在的精神高度。苏兰朵的作品更是如此,在《白熊》中的自省、在《嗨皮人》中的失忆的人类孤独,在她其他小说中也多有所表现。所不同的是,她用了一种更为独特的表现手法,将这种情绪或观念的表达推向了前台,用一种夸张、变形的手段,表现得更为戏剧化和剧烈。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主体总是带有想象性的。如果从主体自身看,主体对‘自我’的想象性自恋关系就是一种想象关系;如果从主体与他人的关系看,两个主体间的相似关系(如性吸引)也是建立在想象关系上的,因为这种心理上的相似性,在拉康看来,只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自我就是想象中的他人,他人就是想象中的自我。”[4]在苏兰朵的小说创作中,似乎照见的就是她的另一个自我。这种小说文体上的尝试看似是苏兰朵的又一次小说技巧的试练,但更深层次未必不是来源于她自身对“小说”这种文体本身一直以来的一种并不确定的怀疑。传统小说(纯文学作品)与类型小说(通俗文学作品)之间究竟存在着多大的距离?而这种距离是否是可被跨越或消解的?
三、想象向内
边界出现之后,苏兰朵的写作空间却被真正打开了。
如果说小说集《白熊》中的《白马银枪》《白熊》《嗨皮人》等篇是苏兰朵有意识的在小说写作文体上做出的对打破边界的尝试的话,那么在中篇小说《歌唱家》中,苏兰朵则展现了故事内部复杂的层次递进。
《歌唱家》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真儿子与假父亲达成合作的协议处。在儿子杨十月的眼里,冒名顶替著名歌唱家浩良的素人王春生是一个“可能比父亲更像年轻时的浩良”的人。这种叙述是耐人寻味的,苏兰朵不断在用虚假和真实做着对比,却让虚假一再胜出而模糊了它与真实的界限,借此矛盾的升级不断加深对于因时代、阶层、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深层追问。
在被邀请演出的过程中,依然可见杨十月的骄傲和自尊,但“父亲的名字”是有比“父亲”更值得尊重的价值。成长于一个光鲜的家庭却并未享受过这一切所带来的特权,自尊在实际的生活面前显得如此无力和匮乏,也因此如此浅薄而功力——“炒股的成就感是孤独的,而浩良给他带来的,除了钱,还有久违的被关注”;假浩良王春生是小说中最为实际和聪明的人,他所唯一缺乏的是阶层上升的路径,而一旦获得,随着行头的变化,他“整个人的精气神马上不一样了,接着是神态、言谈、举止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原来的卑微、低俗之气消失了,一种带点倨傲的自信从他的体内散发出来,甚至比从前的浩良更像一位著名歌唱家”。这个时代定义“歌唱家”的标准在哪呢?不是唱腔或者情感,反而是因资本注入而带来的产品价值的升值;作为真实“浩良”的杨石柱,却时时刻刻想从“浩良”的壳子里爬出来,“声音翻过山岭,从他的喉咙里奔跑出来,嘶哑,苍凉。这声音不属于浩良。”而他认为自己“只是个会唱歌的果农”。
在这个荒诞的故事里,一个“浩良”终于碎裂成为了三个——一个纠结的杨石柱却并不“成功”的歌唱家“浩良”,一个活在“在罗美英和儿子的心里,浩良就应该一直长成这副样子”的标本浩良,还有一个40年前《十月金秋飘果香》里王春生自以为模仿得惟妙惟肖的历史“浩良”。苏兰朵巧妙地将真假浩良的身份倒错处理成作为时代符号的“浩良”的身份错位,“浩良”谁也不属于,“不属于他王春生,也同样不属于杨石柱。浩良本就是个历史的误会”。
历史的虚无感在年老多病的杨石柱心底蔓延,而他更为具象的个人的一生,在巨型的历史命名面前显得如此微不足道;而他曾经所珍视的名誉价值、所背负的巨大的精神重担就这样被轻易地替换重构,浮夸廉价地重新包装上架,这才是真正使他绝望而无奈的。“如果人生真的能那么简单,反倒好了”,轻描淡写的一句自嘲,却沉重至极。在这里历史的叹息终于真正派上了用场,它不是《白马银枪》中那一场谈起来确凿却缥缈虚幻的历史事件,也无须再以无妄天真的姿态去抨击它,让一切反思与内省都显得那么轻易和矫情;相反,当人世遭遇和时间真正开始产生作用,当他回首、反思,他看到的是那个具体不过的“人”,在历史的风中颤抖的也不过是那个“人”。
四、结语
谢有顺在分析“70 后”作家群体所呈现出的代际特征时,认为“70 后”写作体现出一种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接续,他认为“具有诗性和抒情性的小说家……他们面对历史,撬动的是那些深藏不露的缝隙,从而找到和自我相关的联索;他们热爱现实,但在现实面前没有放弃想象的权利,在看到现实的残酷的同时,也学习在情感上如何把隐忍变成一种力量”[5]。苏兰朵是极为珍视个体情感体验的小说家,在《女丑》之中正是强大的情感能量和生命色彩支撑着碧丽珠的形象;到了《歌唱家》以及 再后来创作的《诗经》,个体英雄迟暮的悲壮、时代历史沧桑变迁的无情,取代了《女丑》中女性世界的孤决想象,成为了作家借助作品对个人、对生命质量的一次重评与自省。小说家苏兰朵完成的不仅是技术上的日臻完善,更进一步的是,想象的触角被真正引向了生活与历史的深处,在她现实主义题材的创作中,她重新走入“故事”的内部,重头开始打量人生,让一切想象都成为更广阔的、也更真实的“故事”。
苏兰朵在进入到《白熊》小说的创作开始,越来越体现出她文体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正因她在创作中所遇到的想象边界的限制而显得尤为切实。这也正是她一直以来对于自身惯性写作的反思与质询、对于“小说”作为一种创作体裁而非完全情感表达的理解。但她的理解所引起的创作尝试却是内部与外部同时进行着的剧烈的改变。她不断在常规想象之外发现创作新的故事的隐喻,也在想象之内向内、向下挖掘更深层次与复杂的生活本质。而如此这般,也是另一种对于文学的深情。对于苏兰朵今后的小说创作,我满怀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