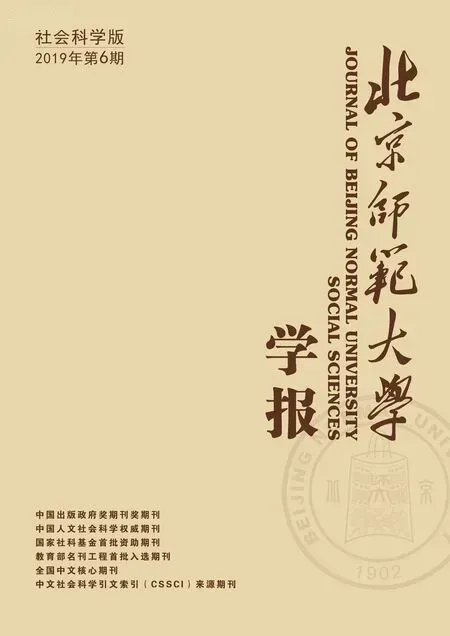从“逆后”到“贼臣”
——戊戌己亥年间康党宣传的策略调整
2019-12-04贾小叶
贾小叶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戊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朝廷颁发训政上谕,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随后,康党主要成员陆续成为清廷捉拿的要犯,或被诛戮,或仓皇出逃,是为“戊戌政变”。此后,为证明政变的倒行逆施与自己出逃的合法性,从而获得列强的支持,康、梁利用国内外报刊,进行了大量宣传。在这诸多宣传中,有些是恒定不变的,如强调康党是因为变法被追捕,光绪帝是因为变法被废,康党出逃是为了奉诏求救等;而有些则是前后不一,甚至相互矛盾的,如对政变主角的宣传,便经历了从戊戌年的“逆后”说到己亥年“贼臣”说的转变。这是康党依据戊戌、己亥年的不同形势作出的策略调整。长期以来,学界对康梁的研究多关注其戊戌变法中及庚子之后的思想与活动,对戊戌政变至庚子间的思想缺乏深入研究。近年来,学界开始重视康梁政变后的史料作伪,并通过细密的史料考订揭示出康梁作伪的种种细节,但此种研究的落脚点仍在于还原戊戌变法中真实的康梁,忽视了政变后康梁历史书写背后的真实思想状态(1)戚学民的《〈戊戌政变记〉的主题及其与时事的关系》一文,是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之一。该文通过解释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初版九卷本的成书过程,特别是通过考察书中的新政“本末”与政变“原委”的主要观点的形成、变化和定性过程,说明此书与康梁师徒1898年末至1899年初流亡日本时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书中关于戊戌变法的宏观陈述框架和关键细节的形成过程受到了作者政治活动和当时舆论的影响(见《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81—126页)。此外,桑兵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一书,追溯了戊戌庚子间的朝野政局,涉及康梁的救上、保皇与勤王等应对时局的主张,但没有作深入的研究(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56页)。。而事实上,己亥年康梁的思想即蕴含于此种历史书写之中,上承戊戌,下启庚子,是一个重要的过渡,不了解此期康党的所思所想,便无法理解庚子年康党的所作所为。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康党的机关报《知新报》、《清议报》为中心,探究康党在戊戌己亥年间宣传策略的前后调整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弥补现有康梁研究存在的重戊戌庚子、轻己亥的缺失。
一、戊戌政变之初:塑造“逆后”形象
戊戌政变发生后,康、梁对时局作出的最初判断是光绪帝将很快被废,甚至被杀。为了给自己的出逃正名、获得列强的支持,康党决然与太后对立,并迅速形成了自己的宣传策略:诋毁慈禧太后,说明她发动政变的不义;强调奉诏出逃,说明康党海外求救活动的合法性。于是,“逆后”形象便成为此期康党着力塑造、宣传的内容。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十日(9月25日),康有为在吴淞口外的英国轮船上接受班德瑞的采访,首次就政变发表看法。其中,他谈到了政变的主角、政变的原因,说:“诏书是西太后和旗人一派伪造的,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并包括所有的旗人高级官吏,按照他们的权位轻重大小,列序如次:西太后、荣禄(能干)、刚毅(无能)、庆王、端王、怀塔布、立山。当他们发觉皇上走向革新的路子上,因而要求西太后重新当政。”此时,政变刚过五天,康有为尚不知道光绪帝的生死,对慈禧太后的评说也比较平和,没有任何诋毁与攻击之词。而荣禄也只是作为旗人中的一员出现,没有太多褒贬之意,更没有后来的天津阅兵行废立之说。谈及帝后关系,他认为:“现在的废立问题,纯粹是旗人闹家务,因为西太后和一些旗人高级官吏都反对革新而且亲俄……而所以突然引发政变的主因,是由于皇上最近下过一道改革诏,宣布依照西洋的服式,改变中国的服装。”同时,康有为也谈到了两道密诏,但只是说七月初一日、初二日他分别接到光绪帝的两道密诏,尚没有后来的“奉诏求救”之意(2)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7页。。两天后,康有为与英国公使窦纳乐的谈话坚持了上述说法。
但随后发生的两件事极大地刺激了康有为,使他改变了上述平和的态度。一是八月初十日(9月25日),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公布了光绪帝的病情,并征召御医,称:
朕躬自四月以来,屡有不适,调治日久,尚无大效,京外如有精通医理之人,即著内外臣工切实保荐候旨。其现在外省者,即日驰送来京,毋稍迟缓。(3)《清实录》,第57册,卷四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01页。
这道谕旨是对八月初六日太后训政上谕的补充,其目的有二:一为太后训政提供依据,说明太后训政的合法性;二为太后进一步的废立行动作铺垫。明眼人很快便窥破了慈禧的用意,皮锡瑞日记记述了桂念祖对该上谕的看法,曰:“桂云:临朝后五日,始有圣躬不豫之文,先所谕并未言,足见是托辞,诏医生亦掩饰人耳目之语。若再有魏主之变,则人心更不服,将有河阴之祸矣。”(4)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1897—1898)》,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二日,湖南人民出版社编:《湖南历史资料》,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辑,第154页。废立之谋既已显露,是谕一出,中外惊疑。据苏继祖记曰:“下召医进京之旨。此时京中议论汹汹。有太监云,皇上有病,正须静养,不能接见臣下;当轴大臣有谓,皇上因服康药病危甚;又有言上已大行。”(5)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348页。《字林西报》刊出消息称:“谣言传说,皇帝之被幽禁仅仅是在等着继承人选的决定,一旦决定好了,便立即将他毒死,然后公布他因病而死的消息。”(6)《最近的局势》,《字林西报》,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四日,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第496页。康有为自然明白召医上谕对光绪帝意味着什么!
二是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包括康有为弟弟康广仁在内的六君子被清廷不审而诛。
清廷对上述事件的极端处理,无疑激怒了康有为。既然光绪帝已经朝不保夕,六君子已经被诛,康有为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顾忌的了,遂公然诋毁慈禧太后,揭露帝后矛盾,宣称自己奉诏出逃,是为了寻求列国营救光绪帝。这从八月十五日(9月30日)康有为写给李提摩太的信中看得很清楚。他说:
四日一别,并言敝国宫廷之变,仆是日受皇上密诏,令设法求救,而贵公使不在,事无及矣。五日即有大变,致我圣明英武、力变新法之皇上被废,并闻旋即弑矣。呜呼痛哉!伪临朝太后,淫昏贪毒,守旧愚蔽,乃敢篡位幽弑,自称训政。夫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安有临政二十四年天子,英明变法如此,而待训政者哉?我国经义,帝者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太后在同治则为生母,在今上则为先帝一遗妾耳。岂可以一淫昏之宫妾,而废圣明之天子哉?淫后毒死我显后,酖死我毅后,忧怒而死我穆宗,今又废弑我皇上,真神人所共愤,天地所不容者也。向来阻抑新政,及铁路三千万,海军三千万,皆提为修颐和园。(7)《戊戌与李提摩太书及癸亥跋后》(1898年9月30日),《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集,第12页。
显然,经历了召医入京和六君子被杀之变后,康有为对时局的判断不同于前,认为光绪帝不仅会被废,且将“旋即弑”。基于此,他对慈禧太后的诋毁也趋于激烈,所谓“伪临朝”、“淫后”,所谓“淫昏贪毒”“篡位幽弑”、“毒死我显后,酖死我毅后,忧怒而死我穆宗,今又废弑我皇上”,如此种种,其对太后的诋毁可谓刻毒。尽管康有为的这封与李提摩太书,属于私人信件,然而已清楚显示了康有为诋毁太后、塑造“逆后”形象的宣传基调,此后他公开宣传的内容万变不离其宗。
四天后,即八月十九日(10月4日),康有为接受了《中国邮报》记者的采访,其中谈到此前他不愿接受记者采访的原因:“他的兄弟被杀,而且光绪帝也有被害的讯息,所以他非常沮丧。过去两星期中的焦虑与刺激,使他精神不宁。因此他不愿意接见任何人,或讨论那些迫使他不能不自北京出走的事情。”兄弟被杀和光绪帝有被害的信息,极大地刺激了康有为,也正是在此刺激下,康有为确定了其对政变的宣传基调。《答〈中国邮报〉记者问》可以说是康有为在光绪帝有被害信息与兄弟被杀后第一次公开谈论政变。
此中,康有为重点谈了自己如何进入光绪帝的视线并被光绪帝重用,并及政变的主角慈禧太后,他说:“慈禧太后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且性情非常保守。对于给皇帝以统治帝国的实权,她是不愿意的。一八八七年曾决定拨出三千万两银子,作为建立一支海军的用处,但……太后就把剩余的钱拿去修造颐和园去了。不久以后,当拨付或筹聚另外三千万两银子,作为修筑铁路之用的时候,她又滥用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每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铁路与海军,是国家富强所必需的最重要的东西。但太后却不顾一两个人的忠告,只图满足自己个人的欲望,拒绝实现预定的计划。”此外,他还透露了长麟、汪鸣銮当年奏折的内容,说他们“曾经奏请皇帝把国家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来。因为太后不过是他的伯父咸丰帝的一个贵妃,按照中国的法律,是不能正式称为母后的……皇帝自此认识到,太后并不是他真正的母亲……自从皇帝开始对国事表示自己的兴趣以来,太后便在计划要废黜他”。这里,康有为所透露的帝后矛盾及太后挪用海军经费等,均见诸他写给李提摩太的信中。此外,康有为还谈到了荣禄,说怀塔布、李鸿章等被免职的官员们“邀同一起去朝见太后,跪在太后面前,求她协助……随后他们又跑到天津去找荣禄设法,因为荣禄是太后最亲信的人。谣言很盛,说皇上打算废黜太后。因此太后决定叫荣禄发难,先发制人,当时是九月十四号或十五号”(8)《答〈中国邮报〉记者问》,《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19—25页。。此时康有为笔下的荣禄,仍然没有太多的阴谋,不过是太后发动政变的助手,更没有天津阅兵行废立的说法。
九月初五日(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刊出了康有为的“公开信”,其中康有为将其精心塑造的“逆后”形象首次公之于众。随信公布的还有康有为修改过的两道密谕。信中,他如是说:
天祸中国,降此奇变,吕、武临朝,八月初五日遂有幽废之事。天地反覆,日月失明,天下人民,同心共愤。皇上英明神武,奋发自强,一切新法,次第举行。凡我臣庶,额手欢跃。伪临朝贪淫昏乱,忌皇上之明断,彼将不得肆其昏淫,而一二守旧奸臣复环跪泣诉,请其复出。(以革怀塔布之故,此事皆荣与怀赞成之者)天地晦冥,竟致幽废。伪诏征医,势将下毒,今实存亡未卜。此诚人神之所公愤,天地之所不容者也。伪临朝毒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废我皇上,罪大恶极,莫过于此。仆与林、杨、谭、刘四君同受衣带之诏,无徐敬业之力,祇能效申包胥之哭。今将密诏写出呈上,乞登之报中,布告天下。(中文报不能登,则西文报亦可)皇上上继文宗,帝者之义,以嫡母为母,不以庶母为母。伪临朝在同治则为生母,在皇上则先帝之遗妾耳。《春秋》之意,文姜淫乱,不与庄公之念母。生母尚不与念,况以昏乱之宫妾而废神明之天子哉!若更能将此义登之报中,中西文皆可,遍告天下,则燕云十六州未必遂无一壮士也。(9)《国事骇闻二十六志》,《新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初五日。
此中,康有为对太后的诋毁与给李提摩太的信中所言如出一辙,公然将母仪天下的太后说成是毒后幽上、罪大恶极的贪淫之徒,令人触目惊心。这样的“逆后”形象同样见于康有为的《致日本(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及《奉诏求救文》中。
在《致日本(英国)驻华公使照会》中,康有为如是说:
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则为生母,在大皇帝则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正,垂裳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嬖,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款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戳,事已暴扬。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10)《致日本(英国)驻华公使照会》,《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31、33页。
《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对“逆后”的描述更加详细,称:
皇天不吊,我中国我四万万人,不类不祥,诞有伪临朝太后那拉氏,毒害我家邦,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五日,遂有幽废我皇上之事。日月黯明,天地震动,呜呼痛哉!……乃伪临朝那拉氏,蛇虺为心,狐蜮成性,向怙大权,久思幽废。长麟、汪鸣銮之贬谪,文廷式、安维峻之放流。皇上名为垂衣,实同守府,幸能遵晦,故获少安。顷以圣明英断,猜忌更深,与其私人荣禄,公然废我神主,幽我民父。举清四万万之人民,而鬻为奴隶。举中国四千年之文治,而悉加灰灭。夫废我二十四年之圣主,实亡我二万里之大清也。非惟亡我二万里之大清,实以亡我四千年之中国也。自开辟以来之酷毒,岂有过此者哉!(11)④ 《奉诏求救文》,《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35、37页。
随后,康有为又罗列了慈禧太后的十大罪状,诸如“毒我显后、鸩我毅后,忧愤而死我穆宗、今又幽废我皇上”均在其列。在康有为看来,求医诏的颁发预示着皇上凶多吉少,“试问列朝故事,有求医之诏乎?三月勤政,似多病之躬乎?其如何鸩毒,虽不可知,而预为谋弑,道路共见……自古废立,岂有免于幽弑之祸者哉?”既然皇上被弑已不能免,他便无所顾忌,罗列慈禧罪名,以期得到日英的同情与支持,慈禧太后也就成为大恶不赦的政变罪魁。在《奉诏求救文》的末尾,康有为再度公布两道修改过的密谕,从而将光绪帝牢牢地与他绑在一起,以证明其出逃、求救的合法性。
耐人寻味的是,在《奉诏求救文》中,康有为谈到荣禄,对荣禄的评价多了猜测、诋毁之辞:
荣禄以奸雄狡险之才,有窥窃神器之志,显则深结武曌以倾庐陵,徐思明去王后以为新莽。当督直隶出天津时,沥陈地方办事情形,有折上伪临朝,而无折上皇上。无君之心,已骇听闻。及皇上严旨申饬,震畏英明,迫于自在,遂辅篡废。④
这里,康有为虽然认为荣禄在政变中扮演了“辅篡废”的角色,但对荣禄“辅篡废”的原因分析,却颇多猜测之词。他先言荣禄“有窥窃神器之志”,后又说“迫于自在”,两厢比较,后者似乎更近实情。与政变初发的几天相比,此处康有为对荣禄的评价刻薄了很多,但在戊戌年,荣禄尚非康有为攻击的主要对象,如此评价也只是偶尔见及,他攻击的核心目标是慈禧太后。
综观康有为的上述宣传,可谓是一篇篇讨伐慈禧的檄文,在行文上深度模仿了骆宾王代徐敬业起草的《讨武曌檄》,意在塑造“逆后”形象,以期达到神人共愤、中外共讨的目的,正如他在《奉诏求救文》中所言:“凡我大夫君子,志士仁人,咸为大清之臣民,其忍戴异姓之淫子乎?君父之仇,不共戴天。鬻国之恶,岂同履地!《春秋》之义,不讨贼则非臣,不复仇则非子。凡我臣庶,沐浴恩泽,浸濡圣教,咸知尊君而保上,岂肯颜而事仇?”(12)《奉诏求救文》,《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37页。作为康党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宣传奠定了政变之初康党对于政变的宣传基调,“逆后”不仅发动政变,而且大恶不赦,必须讨伐。而荣禄在政变中的角色不过是“辅篡废”而已。
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创刊的《清议报》第一期即刊出了梁启超的《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其中他以对话的形式论及政变主角,说:
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之垂帘,皆因嗣君之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复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卒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皇上即位既二十四年,圣龄已二十九岁矣,临御宇内,未闻有失德,勤于政事,早朝晏罢,数月以来,乾断睿照,纲举目张,岂同襁袍之子,犹有童心者,而忽然有待于训政何哉?且彼逆后贼臣之设计,固甚巧矣。废立之显而骤者,天下之人皆得诛其罪。废立之隐而渐者,天下之人皆将受其愚。……倘他日或有大故,则逆后贼臣,且将以久病升遐告于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将信之乎?(13)③ 梁启超:《论戊戌八月之变乃废立而非训政》,《清议报》,第1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第3—4、4页。
这里,梁启超以“逆后”指代太后,认为其政变的目的与武则天“易唐为周”同。同时,他将辅佐慈禧行政变的大臣称为“贼臣”,且没有明言贼臣是谁。在梁启超看来,既然西后已篡位,必须讨伐,而六经即是讨伐慈禧的宪法:“中国之政,向来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即为中国之宪法也。书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礼言夫死从子,有言妇人不与外事。春秋因文姜之淫而不与庄公之念母。然则母后临朝,为经义所不容,有明证矣。《论语》:君薨听于冢宰。寻常幼帝之立,母后临朝,犹为六经所不取,况今日之实为篡逆乎?”③公然以讨伐太后为号召,显然是不再顾及光绪帝的安危、生死,换言之,康党已认定光绪帝必将被弑。
随后,梁又在《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一文中,历数西后揽权营私、反对变法之淫威,指出:“皇上以变法被废,仁至义尽,其委曲苦衷,罕有知之者。乙未年,上欲变法,旋为后所忌,杖二妃,逐侍郎长麟、汪鸣銮及妃兄侍郎志锐,褫学士文廷式,永不叙用,皆以诸臣请收揽大权之故。太监寇良材请归政,则杀之。于是上几废,以养晦仅免,乃能延至今岁。”“忍之十年,淫肆听之,土木听之,纵宦寺、开货贿听之,任权奸、用昏谬听之,尽亡属国听之,丧师辱国听之,遍割边地听之,尽输宝藏、尽失利权听之。”然而一旦厉行变法,却仍遭幽废。这里,梁启超提及天津阅兵幽废之事,说“皇上誓不为天津阅兵之行,盖亦留以有待矣”(14)梁启超:《论皇上舍位忘身而变法》,《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4-5页。。
不久之后,《清议报》又刊出《戊戌政变记》第五篇,一一列举“现行政府”推翻新政与穷捕志士之事实,其矛头所指仍然是慈禧太后(15)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清议报》,第2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6-11页。。随后,《戊戌政变记》连续刊载于《清议报》,对慈禧大加诋侮,历数太后“将其历年以改革之费,作娱乐之事”,指出:“盖西后之心,只知有一身,只知有颐和园,只知有奄竖,而不知有国,不知有民。既不知有国,不知有民,而欲其为国民图幸福,乌可得也。且友邦信其面从忠告之言,而冀其他日之能改革,是亦不察情实之甚者耳……西后及顽固大臣之政策,以敷衍为主义,内则敷衍公牍,外则敷衍外国,但求目前之无事足矣。”对于慈禧太后将来之政策,梁启超断言她不可能进行改革:“凡物必有原点,然后体质生焉。龟之不能有毛,兔之不能生角,雄鸡之不能育卵,枯木之不能开花,彼其无原点也。夫皇上能行改革之事者,有忧国图强之原点也,有十年读书之学识在也。今西后,则除一身之娱乐,非所计也。除一二嬖宦之言论,无所闻也。”(1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清议报》,第3册,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第7、6页。
总之,梁启超在《清议报》进行的一系列宣传都秉承了康有为的说法。可以说,戊戌政变之初,康党有关政变的宣传都集矢于慈禧太后,攻击其幽废光绪帝、反对新政、株连新党,刻意塑造“逆后”形象,虽偶及荣禄等顽固大臣,但他们不过是“辅篡废”而已。逆后、密诏,康党大张旗鼓地向全世界宣传这一切,意在为其出逃、求救提供合法性支撑,引起中外共愤,以期得到日、英等列强干涉。
遗憾的是,康党的这些宣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甚至还引起了中外同情者的反感,因为这样做的直接后果便是激怒太后,使光绪帝的处境愈加危险。当康有为将“公开信”及密谕在上海《新闻报》公之于众后,国内竟然没有其他新党报刊予以转载,这显然是出于对光绪帝的保护。而后,康有为又将其求救于英国的照会寄回国内,并在《中外日报》刊出,郑孝胥读后于十月二十日(12月3日)日记中记曰:“观《中外日报》,有康有为求救于英国书(不全)及中国士民上英领事书,意主煽惑华民。然诸人误上深矣,今乃为此,岂为上计也。”(17)郑孝胥:《郑孝胥日记》,劳祖德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册,第698页。从郑孝胥的评论中可见,康有为的这些宣传效果不佳,关键在于他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光绪帝的安危,因而郑孝胥发出“诸人误上深矣”的慨叹。
康党诸如此类的宣传是铺天盖地的,不仅寻求报刊的刊发,而且在日本大量印制,分送给日本友人,但其效果同样不佳。时在日本的孙淦曾致函汪康年说:“迩来日本无甚所闻,唯初到时,日人皆谓奇特之士。近来日著论说,以为谩骂,又印康工部求救文,分送各处,见者轻之,想亦无能为矣。”(18)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51页。可以说,从当时的伦理价值观念出发,康有为诋毁太后的宣传是不成功的,因为没有考虑光绪帝的处境,故没有赢得太多的舆论支持。
或许是时人的批评引起了康党的重视,也或许是慈禧迟迟不废、弑光绪帝引起了康党的反思,总之,进入己亥年后,康党逐渐调整了宣传策略,“贼臣”取代“逆后”,成为康党笔下发动政变的罪魁。
二、己亥年:“贼臣”取代“逆后”
时至己亥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太后虽再度听政,且有废立图谋,但却一直没有废、弑光绪帝;康党虽殷殷期待列强干涉,但列强干涉的希望却随着康有为被迫离日化为泡影。在此背景下,康党也被迫调整宣传策略,即:由塑造“逆后”形象以期神人同愤、中外共讨,逐渐转变为诋毁“贼臣”荣禄,调和两宫,为促成太后归政、皇上亲政制造舆论。于是,“贼臣”荣禄取代“逆后”慈禧,成为发动政变的罪魁祸首。
康党此一宣传的转变是以康有为思想的转变为前提,又与他被迫离日密切相关。戊戌年底,为了不影响与清政府的关系,日本政府派人劝说康有为离开日本。康有为答应了日本政府的要求,决定游历欧美,但这对康有为无疑是个沉重打击,在指望列强干涉已不可能的情势下,康有为的思想随之转变,这在他写给日本思父的信中有所反映。他在信中说:“夫伪临朝之篡废,非欲为帝,有所牵迫为之耳。其始则太监李莲英曾被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杀之,乃日造谤言于西后前,谓皇上将废之。积毁销金,西后信之。荣禄素媚李莲英,又藐视皇上。其出督直隶,有沥陈地方办事情形折上西后,无折上皇上。皇上知之,严旨申饬。荣禄畏上英明,乃迫西后以废立之事。然则西后之废立,但为群小所牵,率以保存性命耳。若夫大国剀切,能与之立约,亦非不归政也。”(19)《致日本思父书》(1898年11月后),《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45页。这里,康有为对政变原因的解说大异从前,认为慈禧发动政变是“为群小所牵”,以保全性命而已,“非欲为帝”。这是康有为对慈禧太后评价的重大转变。不过此时,康有为对胁迫太后“群小”的考虑还不太成熟,荣禄之外还包括李莲英在内,而且此种解说尚停留于私人信件,没有公之于众。
己亥年一月,康有为在与近卫笃麿的笔谈中再及此说,称:“盖西后年六十余,自营颐和园,费数千万,日陈百戏,以娱晚年,非欲治国也,非欲办事也……盖此次政变全出荣禄之心,多方造谣,云上将废后,故迫不得已而为之。”(20)《与近卫笃麿》(1899年2月13日),《康有为全集》,姜义华、张荣华编校,第5集,第107页。至此,康有为关于政变主角的叙述已经明确,荣禄取代太后成为政变的主角,李莲英已不在其列。康有为这一思想的转变为此后康党的宣传奠定了基调。
很快,《知新报》便出现了类似的宣传,二月初一日(3月12日)刊出的《皇上病重正谬》一文,对光绪帝“病重”的起因与不被废黜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文中称:“皇上之死,死于贼臣之心,皇上之病,病于贼臣之手,特借此以观国民之意向与夫各国之举动耳。”“无如天下之大、之不易欺也,各公使之奔问圣安也。”(21)《皇上病重正谬》,《知新报》(影印本),第80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5—1126页。将皇上之病归咎于“贼臣”,而非“逆后”,这是“康党”宣传发生转向的重要信号。
之后,《清议报》刊出《傀儡说》,矛头所指同样由慈禧太后转向荣禄,称:“我皇上口之所言,不能如其心;身之所行,不能以自主,然而引见召见,朝仪依然,如丝如纶,王言仍旧,是西后以皇上为傀儡也。西后不过一妇人,所眈者娱乐耳,非必篡位幽主,然后快于心也。荣禄蓄异志,觊非常,惮于动天下之兵,乃借后势以箝人口。其实所颁伪诏,未必皆西后之言。所行暴政,未必尽西后之意。荣禄自积操莽之威,而西后代任牛马之劳,是荣禄以西后为傀儡也。”(22)《傀儡说》,《清议报》,第9册,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第3页。政变之初,康党笔下大恶不赦的“逆后”、“淫后”,此时不再恶毒,“不过一妇人”,非必篡位幽主,所颁伪诏、所行暴政“未必尽西后之意”,不过是替荣禄“任牛马之劳”。而且,在慈禧、光绪与荣禄的关系中,康党将荣禄排在最强势的位置,慈禧成了荣禄的傀儡。
三月二十一日(4月30日),《清议报》复刊《明义中篇:论西后所处之危》,进一步分析了手握重权的荣禄对太后的威胁,认为:“西后所恃者,非荣禄也哉!然荣禄以慓悍无赖之姿,阴蓄野心,妄窃神器,练兵待时,历有年所,深结内监李联英,以媚西后,遂躐重任,日夜招聚亡命豪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因以图功,其意以为非操兵柄,不能举大事,举大事不能无假藉。西后者秽德彰闻,天下所切齿,而最恶忌皇上者也。假之以废皇上,则大权在握矣。大权在握,徐而扫除西后,自即大位,天下恶西后之所为,必不汝瑕疵矣。名助西后,实欲以天下之恶归西后,已因而代之,此实卓莽操懿之故智也。迩者羽翼觊觎于宫闱,腹心结于内外,而又全国之兵,听其掌握,俯仰顾眄,则天业可移。”(23)《明义篇中:论西后所处之危》,《清议报》,第13册,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一日,第1—2页。按照康党的逻辑,荣禄实际上是在利用太后废皇上,然后再扫除太后,“因而代之”,这正是卓莽操懿之故智。可见,与政变之初康党集中诋毁慈禧太后不同,己亥年康党的火力已瞄准“贼臣”荣禄。
面对来自荣禄的威胁,太后如何才能自保?对此,《清议报》在《明义篇下:论西后宜自筹安全之法》一文中,为太后出谋划策,提供自保良策,认为:“西后安全之策,无过于复皇上之位。”只有皇上复位,才是太后谋求安全最有效的途径。该文从公、私两个角度分析了皇上复政,对太后有利无弊。于私,太后归政之后,可以极尽人间之乐,“夫西后者,身历三朝,贵盛无匹,前极椒房之宠,后崇国母之尊,徽号之隆,伊古未有,而且洞房清宫,朝歌夜弦,欢乐未央,以燕以食,颐和园之日月方长,万寿山之冈陵永护,享人间之极乐,娱暮景于桑榆,何其乐也。”于公,亲政后的皇上与太后互不侵权,“两保其权利,大清之祚,永无极矣,此天下万国所日夜翘首而望者也。”但如果太后坚持不归政,则后果不堪设想:“遍观万国,纵览历史,其衅生骨肉者,莫不自尽根株,大之宫闱蹀血,为异姓之驱除,小之怨毒伤心,致同枝之剪伐。亡家破国,职此之由。虎狼睞,自戕以速亡,觉罗氏之宗,危乎危乎,于皇上何尤?呜呼,西后其悟哉,呜呼,西后其悟哉!”(24)《明义篇下:论西后宜自筹安全之法》,《清议报》,第14册,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一日,第1—4页。可见,太后归政,于私则有利无弊;于公则势在必行。
如果说政变之初,康党公布密谕、发表“公开信”及各种谈话,意在塑造“逆后”形象、为自己的流亡活动正名、以期得到列强干涉的话,那么,此时的康党则极力调和两宫,非但不再诋毁太后,反而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其直接目的在于通过舆论的力量促成太后归政光绪帝。为了缓和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康党便将发动政变的罪行强加于荣禄,于是荣禄取代慈禧,成为康党笔下的政变罪魁、谋逆“贼臣”。
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在日本政府的逼迫下,康有为离开日本,随后的英国之行也彻底打消了康有为依靠英国的念头。在此背景下,康党调和两宫的意图更加明确,他到加拿大后所作的各种演讲、谈话,都将荣禄视为政变罪魁。五月初一(6月8日)、十一日(6月18日),《清议报》连续刊出《康南海在鸟喴士晚士咑演说》。六月初一日(7月8日),该文复见于《知新报》。其中,康有为谈及政变的主谋,荣禄首当其冲:“荣禄守旧,为上所恶,乃欲废上,以觊觎大位,西后误听其谗,先使荣禄出天津统兵,欲于阅兵时为废立之举。皇上知之不肯行,遂于八月六日废上。”(25)《康南海在鸟喴士晚士咑演说》续前稿,《清议报》,第18册,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十一日,第6页;《知新报》(影印本),第92册,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初一日,第1324页。荣禄“觊觎大位”之罪,这是康党己亥年加在荣禄身上最新也是最大的罪状。
六月十一日(7月18日),《知新报》刊出《康南海与西士语》,康有为仍持此说,认为:“西后年六十七矣,亦不欲置皇上于死地,但其人贪权势,嗜逸乐……今亦不敢举动,恐人行刺”,而荣禄才是废立的主谋:“盖废立之举,皆荣禄主之。故荣禄之罪,浮于西后。然荣禄之权,今亦大于西后。当未政变之日,荣禄使其私人伪言变法,然彼非有变法之意也。荣禄未识外国之人,凡外国学问政治理想,无一知之,焉能变法哉!八月之变,荣禄实为罪魁,彼不敢遽下毒手于皇上者,诚恐义民之四起耳。然又不敢奉皇上复位,恐于己不便。故皇上非得外国臂助,将不得复政。若英国助之,则亦英之利也。盖皇上复政,中国之维新有断然者。”(26)《康南海与西士语》,《知新报》(影印本),第93册,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第1341页。荣禄替代慈禧升格为政变的罪魁,不仅荣禄之罪浮于太后,而且荣禄之权也大于太后。
然诋毁“贼臣”、调和两宫并非康党的终极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舆论宣传,施压太后,归政光绪,进而重启新政。因此,在修正攻击政变祸首策略的同时,鉴于此前寻求列强干涉无望的事实,康党遂直接利用报刊舆论,借为光绪与太后祝寿之际,大力推动并宣传海外各埠华人的归政奏请。这也是康党海外保皇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六月二十八日、十月十日分别是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的生日,各地华人纷纷一面为皇上、太后祝寿,一面吁请太后归政。七月十一日(8月16日),《清议报》刊出横滨华人为皇帝祝寿的《皇上万寿圣诞记》;八月初一日(9月5日),《清议报》再刊《美洲祝圣寿记》。各埠华人祝寿皇上,意在对太后施加压力,以遏制其废黜光绪的图谋,进而促使她归政于皇上。八月十一日(9月15日),《清议报》在《逆谋未息》中谈到了各埠华人电祝圣安对慈禧的警示作用,称:“自去年以来,西后及贼臣等,无时不以篡废为志,然内惮于百姓之爱戴,外惕于各国之干涉,故暂止其谋,闻六月间,此议复起,使人探各国公使意见,皆不谓然。嗣又值皇上万寿,时南洋各埠商人,联名电祝圣安,复有忌惮,不敢迳行。”(27)《逆谋未息》,《清议报》,第27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第11页。九月初一日(10月5日),《清议报》刊出十八行省等臣民《拟布告各国公请皇上力疾亲政文》。九月二十一日(10月25日),《知新报》刊出《记南洋电请圣安事》。(28)《记南洋电请圣安事》,《知新报》(影印本),第103册,光绪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第1498页。十一月初一日(12月3日),《知新报》刊出《新嘉坡华商电祝慈寿并请归政原稿》、《吉隆华商电祝慈寿并请归政原稿》、《巴城华商电祝慈寿并请皇上圣安及亲政原稿》。(29)《知新报》(影印本),第107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日,第1564页。随后,《知新报》刊出《纪华商祝寿请归政事》,其中提到英属域多利埠华人电贺慈寿,并请其归政于皇帝,称:“此埠之外,又有温哥华、尼摩埠,另旧金山大埠、满地奥路、檀香山及美属各小埠,华人众多之区,皆各发同式之电,然则康有为在此诸埠,倡设保皇帝会之功效,显有证据矣。”(30)《记华商祝寿请归政事》,《知新报》(影印本),第110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第1618页。如此奏请,前后多达三十余起(31)《北京要事汇闻》,《知新报》(影印本),第111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第1630页。。可见,各地华商祝寿并请归政的背后正是保皇会的策划与推动。这在康有为为保皇会作的会例中有清楚的说明,其中“上书救主”一条称:“本公司先上书太后,请归政皇上,各埠分上,次则电奏,再次则合各埠签名千百万,公请归政,陈说利害,人心拥戴。西后已悔,当肯相从。否则亦畏人心,不敢害皇上。同志再行设法签名,以多为贵,此事但请归政,并无得罪,宜争忠义,万世流芳。”(32)《东华新报》,1899年10月28日。该资料由张启祯老师提供,在此致谢。此中,康有为不想得罪太后,只想通过上书制造舆论,迫其归政。应当说,己亥立储之前,保皇会的基调是与康有为调和两宫的策略相吻合的。
值得注意的是,己亥年康党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新党舆论的配合与呼应,这与戊戌年康党诋毁慈禧太后、宣传帝后矛盾时新党报刊的沉默无语,截然不同。这种配合可以从他们对“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皇太后书”的报道中见及。八月十一日(9月15日),《知新报》刊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那拉后书》。该上书为杭州驻防瓜尔佳氏金梁所作,内容以诛杀政变祸首荣禄为旨归,与前述康党的宣传如出一辙。(33)《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那拉后书》,《知新报》(影印本),第99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第1434页;《杭州驻防瓜尔佳氏上西太后书》,《清议报》,第28册,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第21页。内容上的高度相似已显示出时人对康党宣传的认可,而各大新党报刊的纷纷刊发与转载更显示出新党与康党的联合。就在《知新报》刊出该上书的同一天,《中外日报》、《中外大事报》同时刊出,四天后,即八月十五日(9月19日),上海《新闻报》加以转载,八月二十日(9月24日)天津《国闻报》转载。如此多的报刊几乎同时刊出或转载此文,对大学士荣禄大加诋毁,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康党与新党的有意为之。稍后,编修沈鹏所上恳请太后归政的奏折,同样得到了康党及新党报刊的合力宣传。沈折以弹劾荣禄、刚毅与李莲英“三凶”为主要内容,其终极目标在于太后归政。(34)《编修沈鹏应诏直言折》,《知新报》(影印本),第108册,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第1579页。
康党关于太后归政、皇上亲政的宣传,同样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与支持。新党报刊除大量刊发南洋、美洲华商的祝寿之电外,还刊发论说呼吁太后归政。八月初一(9月5日)、初六日(9月10日),《中外日报》即连续刊出《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提出太后归政皇上的四大理由:一,“为安民心计,其必当归政”;二,“为弭后患计,其必当归政”;三,“为蔚成圣德计,其必当归政”;四,“为杜塞流言计,其必当归政”。此文对皇上久病不愈的现状提出质疑,称:“皇上寝疾,已及一年,何以武断致病,何以久而不愈,何以视朝如故,何以遣归医士,地阍高远,安得尽人而喻之?”而且,同治年间,太后垂帘尚名正言顺,时至今日,“又非昔比,撤帘何期,归政何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皇太后虽享天下之养,究有三从之义,何以在朝臣工,不闻胪举经谊,上陈□□。宜乎异域之舆论,率土之王臣,不敢缄口噤舌,贴然无异词也”(35)《宜恭请皇太后归政议》,《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初一日、初六日。。这里,作者质疑的是慈禧训政的合法性。只有归政皇上,方能止息流言。
不仅如此,新党还趁己亥年夏秋之交北京久旱不雨之机,大作文章,呼吁太后归政皇上。九月初二日(10月6日),清廷面对京城旱灾,发布谕旨《近因雨泽稀少朕躬修省,在廷诸臣各抒谠论,以迓天和由》(3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151),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第521页。,不仅表示“朕躬修省”,而且谕令“廷臣各抒谠论”(37)⑦ 《清实录》,第57册,卷四五〇,第937、939页。。此一话题遂引发了新党报刊的持续讨论,但与谕旨中的光绪帝自省不同,新党舆论则要求慈禧太后自省归政。九月初五日(10月9日),清廷再发上谕,提出“首以恤民为本意”以“应天之实”,要求畿辅对未清之讼狱、吏治不修、民生日蹙加以清理、整治。⑦在新党看来,这种反省显然无法“应天之实”。《中外日报》针对此一上谕发表评论,认为:“初五日诏书,我皇太后皇上以京畿久旱,兢兢以恤庶狱为念,且曰务令实惠均沾,可谓兼殷汤之仁,包和熹之德。”但何以上天不应呢?原因在于“抱奇冤、负大屈者,或未邀于宽典,纵有原释等诸虚文,求伪而应实,无是理也”(38)《恭读初五日上谕书后》,《中外日报》,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十六日。。“抱奇冤、负大屈者”自然是指光绪帝。换言之,之所以求雨不灵,原因在于太后不归政。
据此可见,公然呼吁太后归政并非康党的独唱,而是得到了其他新党舆论的呼应与声援。而新党舆论之所以与康党遥相呼应,是与己亥年清廷对康党、光绪帝乃至新政的一系列政策密切相关的。
三、余论
上述分析表明,从政变之初到己亥年末,康党的宣传策略发生了变化,即由政变之初的塑造“逆后”形象,转变为己亥年的调和两宫、塑造“贼臣”形象;由政变之初求助于列强帮助光绪复位,转变为己亥年疾呼慈禧归政。而新党舆论对康党宣传的配合与支持,则显示出己亥年新党与康党舆论的联合。
但反观清廷的政策,无论是继续缉拿康党,还是图谋废立,都较之戊戌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清廷不但多次公开发布上谕缉拿康梁,而且为拿获康梁暗中布局,先有刘学询、庆宽使日,后有李鸿章督粤,其命意都在康梁。而己亥年末的立嗣上谕更是彻底击碎了康党与新党实现太后归政、光绪亲政的梦想,不免令人发出“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在此背景下,康党的宣传也逐渐转向武力勤王,“逆后”、“贼臣”共讨之(39)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康党大规模宣传勤王开始于己亥年末庚子年初,但康有为的勤王思想却早于此,这显示出康有为思想的变化与康党宣传之间的差异。对此,我将另文撰述。。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亲历政变的康党便“书写”了不同版本的政变史,这不免令人惊叹。但康党成员毕竟不是史官,而是政治家,他们笔下的政变不是信史而是政治宣传。只要回到戊戌己亥年的历史现场,便可发现,康党这不同的历史“书写”既是出于自身生存的不得已之举,也是根据时局变化作出的主动调整。在被迫流亡的困境中,康党没有固守政变初的宣传话语,而能于己亥年主动调整策略,调和两宫,呼吁太后归政,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且,这种宣传又得到了新党舆论的呼应,从而成为制衡清廷政治退化与衰败的重要力量。而康党、新党于政变后“培养”出来的对抗朝廷、监督朝政的意识,在庚子以后的政局中继续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这在戊戌—庚子渐趋不堪的清朝政治中,无疑是一个显著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