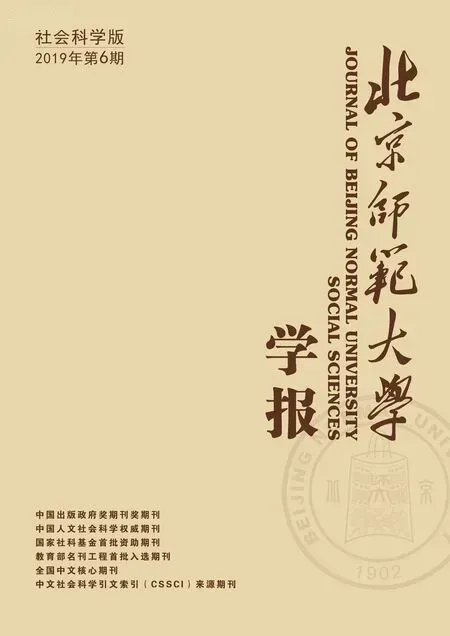对“过程”的发现与探究
——设计人类学的内在转向与理论范式
2019-12-04陈昭
陈 昭
(东京大学 综合文化研究科,东京 1680082)
一、设计人类学的缘起与分类
对于“设计”的研究,并非是人类学的专利。设计人类学作为学科分支出现之前,设计研究(design studies或design research),就已经形成跨学科的规模建制。这些研究与设计人类学有一定交叉,但各有侧重。设计研究的关注点更为微观,侧重探讨设计过程中认知方式与沟通模式,以抽象出普适性模型;而设计人类学的大部分研究关注点相对宏观,侧重讨论设计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
从人类学内部来看,设计人类学是非常年轻的分支。人类学关注“设计”,确切地说将“设计”(而非传统工艺、传统艺术、建筑等)作为研究对象的概念代称,大体是1990年代以后的事情。作为学术分野获得一定发言权,是2010年以来的事情。2010年,英国设计史学家克拉克(Alison Clarke)出版了《设计人类学》的著作合集。同年,欧洲第十一届社会人类学家协会双年会,正式提出“设计人类学”的概念和议题。2012年、2013年以设计人类学为题的两本论文集陆续问世,标志着学科分支的正式确立。2014年之后,在日本设计人类学专业课程陆续有了教学反馈。2016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年度大会开设了设计人类学分会。这些学术动态,勾勒了设计人类学不容忽视的发展势头(1)近年来,我国也有少数关于设计的民族志研究诞生,如周莹有关民族服饰设计的博士论文,因篇幅有限,本文对国内的设计人类学研究不做详细介绍。从研究方法来看,我国现有的研究主要基于象征分析的手法。周莹:《意义、想象与建构》,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那为何近年设计人类学“火”了起来呢?
设计人类学的发展,一方面源于设计产业的发展。产业细分促使设计界内部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生产。特别是“参与性设计”实践的积累,是设计人类学发展的一大基石。2012年、2013年陆续出版的两本设计人类学论集,标志着学科分支的确立。其中寄稿者大多都是来自于北欧活跃于参与性设计一线的实践者。
另一方面,设计人类学的发展是当代人类学学科转型探索下的结果。瞬息万变的当代社会,对以往以“文化与社会”为核心概念的结构化方法提出挑战,而“设计”恰恰是人类学新语法体系探索的契机。随着研究对象的转化,人类学的透镜开始由所谓的“他文化/他社会”转向“自文化/自社会”。那些人类学家曾经视为异域风情的事物,那些看似不变的、恒定的异国物件,艺术、建筑等等,或作为文化资源,或作为全球设计产业的全新资本,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当下人类学的研究,不再以一个“异国他乡”的想象为前提,不再单纯依赖于“传统”、“原生”等概念作为思考的工具,人类学家开始尝试用另一套语法来解释我们的世界。设计行为内涵的复杂关系(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复杂关系下的生产性(如何调和不同的参与主体,朝着设计达成的方向协同运作),以及生产性背后蕴含的诸如权力、制度、媒体、流通等多方面的议题,与人类学一贯的兴趣不谋而合,成为了人类学新思考酿成的土壤。如此,在设计产业发展和人类学学科转型的共同作用下,设计人类学发展了起来。
按欧美文献中常见的分类方法(2)分类方法主要参照以下文献:Wendy Gunn(eds.),Design and Anthropology,Farnham:Ashgate,2012;Wendy Gunn(eds.),Design Anthropolog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Bloomsbury,2013;Keith Murphy,“Design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 45(2016), pp.433-449。,基于设计实践发展起来的人类学研究,常被统称作“为了设计的人类学”(AnthropologyforDesign)(3)此段落for、of英文斜体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本文称这种类型研究为“应用性设计人类学”,是率先以设计人类学自居并致力于推动分野建立的研究群落。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研究,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民族志等运用于设计产业的研究,以参与性设计为基础,落脚点在设计。应用性人类学研究运用于挖掘设计需求,协调设计过程,生成设计概念,促进设计产生。与此相对的是“有关设计的人类学”(AnthropologyofDesign)(4)在既有分类中(参考脚注①)还有第三个类别,即“为了人类学的设计”(Design for Anthropology)。意在通过探讨人类学的研究过程与设计产生过程中的异同,尝试将设计的逻辑衍生与行为组织方式应用于人类学研究。第三个分类,与其说是研究类型,不如说是一种概念性的引导,是对于人类学与设计两种互动关系的新尝试,是对人类学新的可能性的新探索。因篇幅有限,本文不对其展开独立论述。,本文称其为“批判性设计人类学”。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的发展直接推动了设计人类学分支的确立,那么“批判性设计人类学”,是设计人类学分野在自我发展中,尝试在人类学历史脉络下确立学科坐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批判性设计人类学研究可以追溯到文化人类学发展初期;而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类型的研究则集中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
上述分类方法以“设计”和“人类学”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但并未关照“设计”一词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内涵。“设计”一词,其本质包含设计的结果(design)和设计行为、过程(designing)两个方面的含义。纵观设计人类学整体研究,设计人类学呈现了一种研究视角的转换,即早期将“设计”作为一种“结果”加以探讨,近来表现出对“设计行为过程”的关注。这种由“结果”向“过程”的内在转向,不仅仅是设计人类学发展中呈现的特点,也是设计人类学发展内在动力的一种体现。有关“过程”设计的研究范式问题,更与我们思考当代社会人类学发展内在相通。我国现已刊发为数不多的设计人类学的综述研究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作为综述,未能全面解答“设计人类学有什么研究”,二是未能揭示“内在转向”的研究范式的变化,难以回答“设计人类学如何研究设计”。针对这两个问题,本文将首先以设计的两种含义为分析轴承,将物质、艺术、建筑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作为素材,以人类学自身发展历史为辅助线,梳理和勾勒设计人类学的发展脉络。其次,本文将从社会思潮出发,进一步揭示设计人类学的内在转向从何而来。最后,聚焦最新研究成果,探讨设计人类学如何探究作为“过程”之设计的理论范式问题。
二、发现“过程”的设计:设计人类学素描及其内在转向
对“设计”的最初探寻,可以追溯到摩根时代的古典人类学。因为早期人们对于自身行为和秩序的探索(5)John Powell,“Esthetology,or the Science of Activities Designed to Give Pleasure”,Am.Anthropol,1(1899),pp.1-40;John Powell,“Philiology, or the Science of Activities Designed for Expression”,Am. Anthropol,2(1900), pp.603-637;John Powell,“Sophiology, or the Science of Activities Designed to Give Instruction”,Am. Anthropol,3(1901), pp.51-79.,可以理解为对“神”——这位终极设计师——消解的适应(6)Keith Murphy,“Design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45(2016),pp.434-435.。此后,“文化”逐渐替代了神,成为人类自我探索的钥匙(7)Edward Tylor,Primitive Culture,London:J.Murray,1920(1987).。对于“物”的思考,是人类学对于设计(的结果)最早也是最广义的关照。19世纪博物馆制度的确立,殖民地格局的铺开,对“奇珍异宝”的搜集与收藏在欧洲成为风潮。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人类学发展了起来。物质形态(物体、动物等)在宗教(8)Arnold van Gennep,The Rites of Passage,translated by Monika Vizedom and Gabrielle Caffe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社会、经济(9)Marcel Mauss,The 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translated by Ian Cunnison,Glencoe,Ill.:Free Press,1954.等范畴中,作为社会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得到重视。至19世纪中叶,物质文化研究成为了人类学不可分割的内容。
20世纪30年代,马林诺夫斯基之后以参与观察为方法论的人类学确立以来,人类学对于原始社会“艺术”与“建筑”的理解,成为设计人类学的主要篇章。20世纪初到中叶,人类学得到制度化的发展。在此期间,对于具体“物”的关注减弱,对于抽象的社会关系、文化符号、表象系统等的兴趣取向(10)床呂郁哉,河合香吏,「なぜ「もの」の人類学なのか?」,『ものの人類学』床呂郁哉,河合香吏(編),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11,pp.1-21。增强。人类学兴趣发生转移,物质文化研究一度衰弱,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再次以消费、生产、现代性(11)Arjun Appadurai(ed.),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Daniel Miller, Material Culture and Mass Consumption, Oxford, UK: Blackwell,1987.等议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再次受到关注的物(物质性),被置于更复杂和精致的概念网络中,但仍更多作为一种设计的结果,研究焦点在于这种结果的使用、流通与现代性的关系,而非关注设计行为本身(12)对于生产的讨论,虽可说是对“设计过程”的关注,但其更多侧重作为制度的生产关系,而非实际的设计生产过程。。
对艺术之形这一设计结果的探究,与博厄斯学派相关。博厄斯从绘画、图案、造型等艺术表现形式出发,探寻地理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历史发展关系(13)Franz Boas,Primitive Art,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55.。这种以设计为“形式”而非设计为“行动”的概念特权,成为人类学此后数十年内思考设计的主导框架(14)Keith Murphy,“Design and Anthropology”,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45(2016),p.436.。其弟子本尼迪克特更是超越了具象的美学之“形”,构建了抽象的“文化之形(型)”理论(15)Ruth Benedict,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Tokyo:C.E.Tuttle,1946.。从设计的视角看来,可以说博厄斯学派对于“文化”概念的发展(16)Marshall Sahlins,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p.67-68.,是建立在对(作为设计结果的)艺术之“形”的概念抽象之上的。
有关建筑的研究,是设计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学一直对人的居住空间有着很大的兴趣。初期具有代表的有1935年乔斯林的研究,他通过当地居住空间分类来解释印度尼西亚的社会结构(17)P.E.デ=ヨセリン=デ=ヨング[ほか],『オランダ構造人類学』宮崎恒二[ほか]訳,東京:せりか書房,1987。。乔斯林以1930年迪尔凯姆和莫斯的共同研究(18)エミール·デュルケーム,『分類の未開形態』小関藤一郎訳,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1980。为基础,此研究确立了以“分类”以及“集体表象”为分析概念的研究手法,启发了此后的结构主义建筑研究。同样受到迪尔凯姆和莫斯的影响,拉瑟斯对爪哇建筑空间进行分割,解读了空间与爪哇男女性别之间的对照关系,由此分析当地社会的双分制(19)W.H.Rassers,Paji,The Culture Hero:A Structural Study of Religion in Java,The Hague:Martinus Nijhoff,1959,pp.219-297.。谢拉在南婆罗洲岛(South Borneo)的研究中指出,家屋的建筑方位体现了宇宙的神圣性,是神观念的体现(20)Hans Schärer,Ngaju Religion:The Conception of God among a South Borneo People,translated by Rodney Needham,The Hague:Nijhoff,1963,pp.67-73.。此后空间分割和方位观念,成为居住象征分析(宇宙观解读)的主要着眼点,并在坎宁翰1964年的研究中(21)Clark Cunningham,“Orderin the Atoni House”,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Deel 120,1ste Afl.,Anthropologica Vi(1964),pp.34-68.得到最终确立,后期的居住象征分析多以此为范本(22)佐藤浩司,「民族建築学/人類学的建築学(上)」『建築史学』12(1989),pp.106-132。。居住象征论关注作为“设计结果”的建筑结构,并将其作为社会制度与宇宙观解读的途径。这种手法在印度尼西亚的家屋研究中得到集中发展,并在其他地域的建筑研究中普及开来(23)汉弗里用一种简洁的结构主义方法,描述了不同社会时期的蒙古人的室内空间的使用方式,分析社会主义工业化对于构成蒙古人室内空间物质元素以及认知变迁的影响。Caroline Humphrey,“Inside a Mongolia Tent”, New Society,31(1974), pp.13-14。。
居住象征论,假设“社会”是静态而孤立的存在,并默认社会结构必然会投射到建筑物上,因而通过解读具体的建筑空间结构,我们可以分析抽象的社会结构。这种研究手法的科学性,在1980年代受到质疑,认为艾伦批判,象征分析手法,只不过是一种将某种碎片,生搬硬套到某种唯一正确形态上的“拼图游戏”(24)Roy Ellen,“Microcosm,Macrocosm and the Nuaulu House:Concerning the Reductionist Fallacy as Applied to Metaphorical Levels”,Bijdragen tot de taal-,land-en volkenkunde /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f Southeast Asia,Vol.142,1986,p4.而已。1990年代后,受到列维斯特劳斯“家屋/家”(house)概念的启发,建筑人类学开始尝试突破既有的研究框架,构建更全面的学科格局(25)James Fox(ed.),Inside Austronesian Houses:Perspectives on Domestic Designs for Living,Canberra: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93.。建筑研究开始囊括更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件(26)Setha M.Low and Erve Chambers(eds.),Housing,Culture,and Design: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Denise Lawrence and Setha Low, “The Built Environment and Spatial Form”,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19,1990,pp.453-505.,建筑开始被看作是居住者生活“过程”的一部分(27)Janet Carsten(eds.),About the House:Lévi-Strauss and beyo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36-37.,建筑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28)〔美〕维克托·布克利:《建筑人类学》,潘曦、李耕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8年版,第64页。得到关注。1990年代以后,建筑的过程性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
对于“过程”的发现,同样带来了1990年代艺术人类学发展的转折点。吉尔在其遗作中指出,“物”能不能成为艺术品要放在这个艺术品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来看待(29)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98.。吉尔的研究传递了一种全新的艺术人类学视角,艺术不再是一种(设计的)物化结果,而是一系列能动关系作用下的动态产物。这启发我们从“社会性过程”的角度重新审视“设计”。1990年代以后,作为“过程”的“设计”得到进一步的发掘。以建筑研究为例,受科学技术建构主义的影响,一种试图超越某种意义解读(象征分析)的实用主义哲学手法逐渐确立(30)Albena Yaneva,Made by the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An Ethnography of Design,010 Uitgeverij,2009;Albena Yaneva,The Making of a Building: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 Bern, Switzerland : Peter Lang,2012.。建筑不再只是设计结果的容器,建筑设计实践过程本身,成为了我们思考社会文化生成的概念工具。
设计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在200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结果”的设计向“过程”的设计的内在转向,是“科学”和“艺术”两个领域发现“过程”的共振结果。这种共振,表达了21世纪以来人文社科领域对现代性的根本反思。“科学”一直是个黑匣子,被视为绝对理性。20世纪中叶,古典的社会知识社会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构建了一种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即认为科学技术是理性理论活动的产物,并不受到外界条件的拘束。20世纪60年代,这种本质主义的科学观,受到了库恩范式理论的挑战(31)库恩认为,范式是构成科学研究框架的著作、概念、理论等。当既有的范式内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新的理论就会出现,挑战旧的理论,新的范式随后推翻旧的范式,前一个范式下积累的研究概念知识等都存在不再适用的可能(比如从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种范式更迭,是断裂式的革命,推动科学阶段性前进。范式革命的提出,挑战了本质主义科学观,不再将科学作为基于理性的时间上的线性积累。Thomas 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受库恩的影响,以拉弗茨的研究(32)Jerome Ravetz,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为开端的1970年代,迎来了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发展,SSK强调科学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科学研究的社会性内涵。1970年代后期受到SSK影响,“技术的社会构成主义思潮”逐渐兴起。技术的构成主义认为技术和科学一样,都是由复杂的社会要素构成的。社会性要素不是技术系统的外在环境,而是技术系统内在的一个部分。因此,构成主义对于科技的研究,关注技术到底为什么成为了现在这个样子,分析技术生成变化的过程。
1980年后,在ANT(Actor-Network Theory)理论指导下,实验室民族志研究(33)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兴起。这进一步在方法论上,引导我们发现与观察“科学过程”。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实验室研究,向我们展示科学真理的生产过程,描绘人与非人要素(如数据、实验器具等)如何互动变化,进而勾勒科学真理“构成”之动态。实验室民族志研究呈现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三个转化:一是研究焦点的转化,由“结束了的科学”转化为“现在进行时的科学”,将科学视为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二是研究对象的转化,由“理论知识”转为(理论知识探寻过程的)“实验活动”。前两个转向下必然引发第三个转向,即研究手法(或称研究目的)的转化。因为科学总是发展变化的,科学研究的手法(或目的)由讨论真伪科学这一命题,转变为对科学过程的描述与记录。这也是新的科学观下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在要求。实验室民族志研究所带来的转变,意味着对科学技术“过程”的研究范式的确立,而这无疑是我们探索“设计过程”的范本。2005年之后受实验室民族志研究的影响,一批关注设计过程的设计事务所研究诞生。ANT理论的出发点与基于此发展而来的民族志研究手法,无疑是当下设计人类学探究“过程”设计的重要参考。
纵观科学社会学的发展,是人类逐步打开“科学技术”这一黑匣子的历史,是解构了一个“绝对客体性结果”的科学技术,发现了一个“相对主体化过程”的科学技术的历史。这一历史与现代性批判思潮共鸣,是推动设计人类学打开“设计”这一黑匣子,发现“过程的设计”的根本思想动力。与ANT并行,启发设计人类学“发现”“设计之过程”的另一脉社会思潮,则是以英戈尔德为代表的对于艺术与创作的反思(34)Tim Ingold,Making:Anthropology,Archaeology,Art and Architecture,London:Routledge,2013.。英戈尔德在其对于艺术人类学的批判中指出,人类学关注作为物(object)的艺术,而忽视了对于创作(making)过程的探索;在这种对于物的理解中,常存在一种形质对应论(hylomorphic model)——黏土与瓦片的对应——的思维模型;这种过于简化的模型,无法真正理解艺术生成的过程;只有理解生成的过程,我们才能理解物质的二重性(物质本身以及物质的含义);我们需要的是从艺术生成的过程“内部”出发,关注艺术生成中的参与要素之间“相呼应相交融相互构的生成关系(correspondence)”(35)引号之内的内容,是本文对于correspondence概念的意译,并非对于英戈尔德的直接引用。此意译,整体参考了概念出处的Making一书,重点参考英戈尔德在论述correspondance时,与interaction作概念区分的重点段落(P107)。从全书来看,correspondance可以从两层含义来理解:一是指创作过程中的生成关系,二是指生成关系下诞生的形态、材质、人调和的状态(亦可理解为一种存在的方式)。通观全书,不对这两层含义做刻意的切割,而用一个correspondance的概念来涵盖两层含义,确切地说是两层含义间的律动,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此处采用如此意译,一方面是契合本小节设计过程发现的议题,一方面是为了方便展现其语言背后概念本质。其次,通过“相呼应相交融相互构的生成关系(correspondance)”这一概念,英戈尔德强调的是在创作过程中要素之间边界消融,相互呼应(如手艺人的手与编制材料之间的互动),一种超越主体或主体性不明确的,同时又充满偶发性的状态。意译中的“相呼应相交融”由此而来。同时,在这种主体边界消融的生成过程中,作为设计结果的物被创造了出来,意译中“相互构”意在表达形态、材质、人整体的变化与形塑的结果。。
英戈尔德对于创作过程的思考,对于设计过程的特性——“内在参与要素之间的,相呼应相交融相互构的生成关系”——的概念化,在根本上指出了设计研究中象征手法的局限性。象征手法,简而言之以解读物质所代表的含义为意识前提,如缺乏对于物质生成过程内发性的探讨,物质与其所对应的含义的象征解读,容易陷入空论。这恰恰印证了对于居住象征论的批判。英戈尔德所倡导的对于过程的回归,本质上是对超越象征的尝试。英戈尔德的思想在设计界也获得极大反响,设计人类学中的大量研究都多受其影响。如上文中所提及的标致着设计人类学创立的论文集,主编之一的甘恩(Gunn)即是其学生,英戈尔德的思想在论文集中也起到了理论升华,统筹各经验研究的作用。
同样是对“过程”的发现,拉图尔的思想实验以自然科学实验室为发端,其“过程”指向了对社会这个概念,以及这个概念下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新定义(36)也可称“重组社会”。相关用语可参考:吴莹、卢雨霞、陈家建、王一鸽:《跟随行动者重组社会——读拉图尔的〈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第218-234页。此处的“重组”,源于拉图尔Ressembling the Social一书书名的释译。中文“重组”一词难免让人有“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新的聚合实体”的联想,但需注意此处并无对实体的强调之意。Bruno Latour,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英戈尔德则由手工艺创作中身体与素材彼此消融的现象学描述(37)英戈尔德对设计的论述,多基于手工制作的案例以及原住民史料,未将实际设计实践作为经验性材料,因此必须承认其思想在理解产业行为的设计实践时有一定局限性。但作为思考设计的概念引领,其对于物质性与创作过程的反思,无疑是具有价值的。出发,其“过程”指向了人之于环境超越主客体二分的存在方式(38)英戈尔德的存在观,总的说来就是,人是活在一个打开的世界中的。或者说生存,是以打开的方式存续的。打开的世界,是指物质、人、或者二者之间的交互,都不是静止的,而是以流动的状态存在。而这种流动是人与物质媒介混合的流动。譬如,风不以风本身存在,我们能感受到风是因为风在吹,而“吹”,就是人物质媒介混合下人感知的结果。亦可参考本文关于correspondance的脚注。Tim Ingold,“Earth,Sky,Wind,and Weather”,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Vol.13,2007,pp.S19-S38.。拉图尔的思想是基于实验主义哲学的对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全面批判,英戈尔德的思想则与存在论(本体论)转向的哲学思潮相通,两者都在解构僵化的人类学研究框架上具有意义。瞬息流动的当代社会,日渐程式化的“社会”“文化”概念,不断失去效力。二者的思想不仅对“过程”设计的探讨具有参考,也对思考未来人类学的研究范式具有价值。
三、探究“过程”的设计:设计人类学的理论范式
设计人类学的内在转化,一方面是1990年后学科发展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是推动设计人类学分支确立的直接动因。由“结果”向“过程”这一内在转向,不仅意味着设计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由设计的“结果”转变为设计的“过程”,更意味着研究方法论的内在转向。方法论的转变,从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是文化人类学由“观察者”转向“参与者”的角色转换;从批判性设计人类学的角度来说,“设计”不仅仅是封闭的物质性结果,还是过程开放的社会性过程。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研究,致力于创造出更“社会”的设计产品;批判性设计人类学则侧重探讨在设计过程中“社会性”的诞生。
那么设计人类学到底如何探究作为“过程”的设计呢(39)本文重点分析批判性设计人类学对“过程”设计的研究范式。?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应用性设计人类学是率先扛起学科分支的重要发声者,设计人类学发展中参与性设计的积累起到关键作用。应用性设计人类学研究,将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运用于挖掘设计需求,协调设计过程,生成设计概念,促进设计产生。比如,设计工作坊就是此类实践常见的类型之一。社会公众被邀请参与到设计决策的过程中来,人类学家作为不同文化背景沟通的专家,在设计过程中扮演协调员,参与工作坊的构想企划,引导公众更好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并与设计师一同从这些表达中提取设计的灵感与概念(40)Mette Gislev Kjrsgaard,(Trans)Forming Knowledge and Design Concepts in the Design Workshop,In Design Anthropology:Theory and Practice,edited by Wendy Gunn,Ton Otto,Rachel Charlotte Smith,London:Bloomsbury,2013,pp.51-67.。当然,人类学的参与远不止于工作坊本身。将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运用于目标使用者人群,将民族志的记叙和描述作为设计灵感的来源,也是常见的手法(41)常与ethnomethodology的研究手法相融合。。
另一方面,批判性设计人类学研究则以“符号学理论”(42)Keith Murphy,“A Cultural Geometry:Designing Political Things in Sweden”,American Ethnologist,Vol.40,No.1,pp.118-131;Keith Murphy,Swedish Design: An Ethnograph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与“ANT理论”(43)Bruno Latour and Albena Yaneva,“Give Me a Gun and I Will Make All Buildings Move:An ANT’s View of Architecture”,In Explorations in Architecture:Teaching,Design,Research,Basel:Birkhäuser,2008,pp.80-89;Albena Yaneva,“New Voices in Architectural Ethnography”,Ardeth,No.2,2018,pp.17-35.为主要理论方向。两者都不将设计作为客体化结果,强调设计生成中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符号学理论是对此前象征主义手法的一种批判性发展,继承了象征手法的符号学出发点,批判象征主义空间研究中对于形和意义关系的过于僵化的本质化的处理,强调形态与含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是政治艺术经济等一系列社会过程的产物。与此相对,ANT理论是反符号学的,是一种实用主义(44)AlbenaYaneva,The Making of A Building: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Bern,Switzerland:Peter Lang,2012,pp.3-11,p.25.视角,即不通过对某种现象背后的所谓“含义”的探究来认识现象的理论出发点。换句话说,ANT理论下的设计过程,不假设物和其意义的区分,也不单纯地探讨物和含义之间的关系问题。ANT理论下对于设计过程的讨论重点在于,设计中人与非人的行动项之间如何作用,设计形态如何转化的问题。ANT理论不将文化传统、社会习俗等作为行动项,是因为ANT理论认为,“文化(的/性)”“社会(的/性)”本是学者创造出的概念范畴。这些常被安逸地用于解释其他社会现象的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本就无法言明。而尝试用这些概念去说明需要被说明的对象,也终归是空对空的徒劳。因此ANT理论倡导,不以既有的“自然”“社会/文化”概念作为前提,回到一种“行为作用的能动性”本身,而ANT理论正是提供代替的研究方法。
让我们进一步通过民族志研究来理解这两种理论范式。墨菲有关瑞典设计的民族志(45)Keith Murphy,Swedish Design:An Ethnograph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5.,是符号学理论范式的代表。一提到瑞典设计,我们常会联想到一种极简功能性的设计风格。墨菲研究解释了这种设计风格如何形成,又如何通过一系列的表象和展示品牌化。墨菲提出“形之线/视觉之线”(设计的形态特征)与“声之线”(设计的意义内涵)这对概念。通过对瑞典艺术史与社会改革政治思想的梳理,墨菲首先指出瑞典设计中非圆即方非曲即直的视觉特征(形之线),与关注家庭、倡导平等福祉的瑞典社会民主理想(声之线),之间存在一种共鸣。并通过设计事务所日常工作、设计展览等描述,进一步描绘这种历史性的共鸣,如何在瑞典国内再生产和传播,并最终形成全球设计产业格局中属于瑞典的名片。墨菲对设计事务所的研究手法,显然受到了ANT理论的启发,但与ANT理论不同的是其理论归结。墨菲尝试从“形态/视觉/物质”与“意义/言论/非物质”的符号学互动中,找到对“过程”设计的理论途径——用墨菲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文化几何学”(46)Keith Murphy,“A Cultural Geometry:Designing Political Things in Sweden”,American Ethnologist,Vol.40,No.1,pp.118-131.。这种几何学,如同德勒兹评价福柯的“权力概念”那般,是一种融合言语与物质的“图示(diagram)”(47)Gilles Deleuze,Foucault,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eán Hand,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具有形塑一个社会的张力。由此瑞典设计的文化几何学,是认识瑞典社会的透镜。
符号学理论对“过程”设计的设定,有着相对宏观的时空维度,而ANT理论对“过程”的设定则更为微观。ANT理论启发的设计民族志,多以建筑设计事务所内的设计过程为时空范畴。这些研究,共同呈现了一个与教科书中介绍的单线流程截然不同的设计动态。亚内瓦在著名建筑师库拉斯的OMA设计事务所展开的民族志研究(48)AlbenaYaneva,Made by the Office for Metropolitan Architecture:An Ethnography of Design,010 Publishers,2009;Albena Yaneva,The Making of A Building: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Architecture, Bern Switzerland:Peter Lang,2012.,有意地拒绝做出对库拉斯建筑思想的任何解读,相反选择追溯一系列2D-3D模型的变化,追踪设计师如何通过文字以及模型图表来认识场地的一系列过程的轨迹(trajectory)。乌达特的有关隈研吾设计事务所民族志,其日译文主标题——“微小的节奏”(49)这种回归细节的态度也获得了隈研吾本人的正面回应。乌达特民族志的日文版中,隈研吾亲自撰写了后记。他表示所有曾经来采访他的人,都一直在追问设计中是否有戏剧性的情节,那种突然改变设计的瞬间,然而结果令他们失望。设计的日常本就是琐碎的。反复细小的节奏,才是设计的真实。ソフィー·ウダール(Sophie Houdart),港千尋,『小さなリズム:人類学者による「隈研吾」論』加藤耕一 [ほか]訳,東京:鹿島出版会,2016。——同样清晰地表达了ANT理论下对于设计过程的切入口。意图性地拒绝聚焦建筑大师的理念在设计中的作用,体现了ANT与符号学截然不同的态度。建筑(设计)不是设计结果意义上,对于更广义社会文化环境的符号隐射,建筑(设计)是一个实验性摸索的过程。设计,是充满反复和细节的过程,是不同参与者与不同物质材料、计算机设计软件等工具不断交涉的过程。ANT理论范式下的设计人类学,不仅继承了ANT理论指导下实验室研究中的民族志书写风格,同时也继承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即设计的过程,是一种知识的获取、形变、传播、生产的过程。
墨菲通过历史学的方法揭示了瑞典社会形态与含义融合的动态,刻画了设计的文化几何学如何定义一个社会。但正如有学者评价的那样,以“形与含义的统一”为终点的“过程”性描述,仅是对于符号学本身的回归,未能对实际的设计实践的动态有深入地剖析(50)Jrn Guldberg,“Swedish Design:An Ethnography,by Keith M.Murphy”,Design and Culture,Vol.9,No.1,2017,pp.110-112.。符号学用于设计实践行为分析之上的理论缺陷,源于符号学理论自身的特性,即任何符号意义上统一性的形成,是以漫长的时间性为基础的,当我们放大时间刻度,聚焦统一性背后存在的摇摆与振动,尝试描述更微观动态的设计过程时,其理论不免难以适用。
ANT理论将对于文化和社会的概念性解构带入对设计过程的考察。但从高产的ANT理论派的设计研究来看,必须要指出不少对于ANT理论的援引,仅流于形式性的“过程中转变”的记叙。对于ANT理论修辞学的消化,使得设计中的Actor的过程性转变的描述成为一种风潮,但却缺乏对设计实现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资源重组等权力性关系的思考(51)比如Ahlam Sharif有关绿色建筑的研究,借用ANT理论中“转化(transform)的概念,描述了空调系统从设计到使用过程中,因为赶工期,在未满足要求的运行测试期限的情况下投产,后在使用中产生诸多故障的案例。并引用“翻译”概念解释了使用者对于这种故障的不同理解和应对。在绿色建筑的实施过程中,新技术投产引起的不确定性,以及围绕设计实现不同行动项之间的博弈,是核心的议题。而Sharif的研究仅仅提供了一个建筑界老生常谈的现象描述,未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Ahlam Sharif,“Ethnography of Transfer: Exploring the Dynamism of Sustainable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Masdar”, Ardeth,No.2,2018,pp.157-175.。ANT理论虽然在其表述的修辞学中,不直接将权力性的问题项本身作为actor,但是其根本意图在于通过网络内的转化和传递的追溯,跳出概念本身的自我循环,而直接对生成动态进行剖析。在ANT理论设定里,网络是可以无限延伸的。但我们无法直接认识这样一个无限延展的网络,ANT理论应用必须基于一个边界(actor world)的设定。与其理论目标设定存在巨大差距的是,理论应用中的边界划定,往往造成研究对象扁平化,同时在篇幅有限的学术成果展示中,学者往往只能实现描述形变的过程,也客观上造成了ANT理论形式性应用与其理想设计之间的落差。
总之,对于“过程”的设计探究,符号学理论长于描述更宏观的过程,ANT理论长于刻画更微观的动态。两者各有缺陷,但却可相互弥补。当然,在设计的生成过程中,不仅是符号的再生与网络的重组,还有难于言语表达的身体性议题,如环境感知、感官体验等等。如何理论化设计中难以言语化的部分,是今后设计人类学有待发展的方向。
四、结语
近年来,设计人类学在我国也逐渐获得关注,本文对海外设计人类学的基础性引介,所及有限,但求为关注该领域的同仁提供参考。设计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需要发掘其原生动力,并建立核心的使用语境。参与性设计,是海外设计人类学的主要推动力与使用语境,而在中国,相关产业上积累相对薄弱。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设计人类学的发展基础。比如,近年来在中国备受关注的“社区营造”,即是基层治理的问题,同时从本文的视角出发,也是社会秩序如何协调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运动的“设计”问题。另外与美丽乡村建设有关的乡建运动,就是中国乡土空间的“参与性设计”。这些都是中国发展设计人类学的土壤。
设计是具有伸缩性的概念。从一个物件的设计,到建筑景观等街区的设计,再到抽象的某种制度层面的设计,各个尺度下,设计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决定了设计人类学在各个尺度下研究对象的选取和理论射程的确立。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设计的本质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秩序的人为意图的介入。因此有关设计的人类学研究,最终都需要讨论目标秩序的实现与现有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来看这种紧张关系,是设计人类学在中国发展的根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