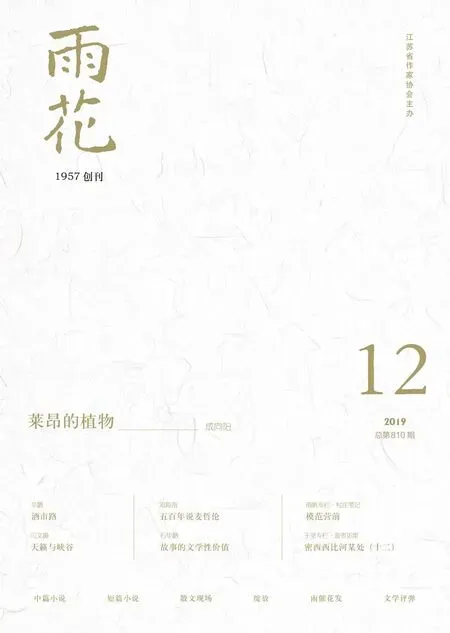悼梁公归智先生
2019-11-23王春林
王春林
夜深了,我还不想睡!无法自控的泪水还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尽管早在意料之中,早有心理准备,但今天晚上21 时在微信朋友圈里看到我的朋友安裴智先生发出的一条关于著名红学家梁归智先生于2019年10月21日晚20 时11 分因病不治,在大连不幸仙逝、遽归道山的消息,却还是让我倍感震惊,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相信这一残酷的事实。
我最早是在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赵勇先生的微信往来中得知梁归智先生身患重病的消息的。从赵勇处证实,梁归智先生不仅已经被确诊为不治之症,而且预期情况极其糟糕,即使采用最先进的医疗手段,恐怕也只剩下三个月的生存时间。查阅微信时间,那一天正好是8月30日。此后不久,梁归智先生的公子梁剑箫又主动和我联系,从他那里,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梁先生的病情,而且得知先生的实际境况并不算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心心念念地想要找时间去看望一下先生。
等到9月8日的时候,我终于可以抽出时间前往大连探望内心牵挂已久的梁先生。那一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就匆匆忙忙打车从学校赶到了机场。等到飞机准时在大连周水子机场降落的时候,时间正好定格在了8 点45 分。一下飞机,我打了个出租车,一刻也没有停歇地直奔大连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而去。
等我顺着医院的指示标志摸到C区22 层肝胆胰外二科的时候,梁先生的爱人,被我们尊称为梁老师的一位先生,已经迎候在病房门口了。一进病房,虽然早已打过预防针,但一下子撞入我眼帘里的清瘦的梁先生,还是让我不由得暗中吃惊。我记忆中的梁先生,虽然似乎从来也没有胖过,但也一向是壮壮实实的。一下子便消瘦到形销骨立的地步,肯定是可怕的病魔作祟的缘故。我在进门的时候,梁先生的手上正输着液体。由于病体难支,一贯注重礼数的梁先生没有能够起身迎我,但看到我背着双肩包走进门来,梁先生还是勉力地挺起身来和我打招呼。
聊天的过程中,我才得知,梁先生的病情是在7月22日早晨因小便颜色异常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并确诊的。从那个时候算起,到我专程前来探望,梁先生事实上已经与可怕的病魔斗争了一个半月。虽然一直饱受病魔之苦,但或许是药物作用的结果,又或者更主要的,还是梁先生的心目中早已勘破了生死大碍的缘故,在与我前后长达两个多小时的交谈过程中,我其实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感觉到他是一个重病在身的病人。正如同以往我们见面时的情形一样,虽然是在医院里,但我们聊天的主题却始终都逃不出一贯兴趣所在的文学和学术领域。尽管离开太原已经长达二十年的时间,梁先生仍一直牵挂着山西文学的发展状况。从李锐、蒋韵、葛水平,一直到吕新、王祥夫、孙频以及杨遥,就梁先生对这些作家如数家珍般的熟悉与了解程度来说,他一点也不像搞古代文学的,倒像是一个专门研究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当然,其间也少不了会穿插一些他所供职过的(也是我至今所在的)山西大学文学院的近况,以及他所在师门(梁先生是著名学者姚奠中先生的高足,而姚奠中先生的老师,又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先生)的一些情况。不知不觉间,时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恰恰也就在这个时候,梁先生的亲家公也匆匆忙忙地从外地赶来看望他了。一方面,是因为有他人在场,我们的话题不好再继续深入下去。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看到梁先生在畅谈了差不多两小时之后,尽管仍有兴致,却也面露倦色。我实在不忍心就此作别,然而,还是恋恋不舍地起身告辞了。对了,还有两个重要的细节,无论如何都应该记下来。一个是,在聊天的过程中,梁先生特意让他的夫人取了他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禅在红楼第几层》,另一本是《浪子风流说元曲》,用微微颤抖的手认真地在上面写字,题赠与我。再一个是,临行前我主动提出,要借用梁公子的手机给我和梁先生留一张合影。因为我预感到,这可能是我和梁先生最后的一次合影机会了。
就这样,尽管满心的不情愿,我还是眼看着梁先生清瘦的面容,一步一挪地走向病房门口。我知道,要想再一次看到梁先生,恐怕是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了。
从那一天之后,虽然日日都是各种繁忙的事务,然而,一旦偶有闲暇,我便会情不自禁地记起躺在病床上的梁先生,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祈福。但终于,到了今天,到了这残忍的一天,早已在意料之中的噩耗,还是从遥远的东北海城大连传来。我一向尊敬有加、我一向视作很好的兄长的梁先生,终于还是没有战胜病魔,驾鹤西行了。
坐在已有寒意的书斋里,我的心更是感觉冰冷。面对着已经写下的一行行如蝌蚪般的文字,眼前闪现出的却是一幕幕关于梁先生的往事。往事并不如烟,其中的几个场景大约会永远地留存在我的记忆中。
一个场景,是我与梁先生的最初结识。我是在1996年初由原来所在的单位吕梁高专(现为吕梁学院)调动到山西大学来工作的。那个时候,梁先生研究生毕业后在山西大学任教已经有很多年了。由于初来乍到的缘故,原本话就不多、有一点讷言的我,除了完成日常的教学任务之外,几乎什么话都不说,整日里只要一有时间,便会泡在系里的阅览室里翻阅各种书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一天,梁先生走进阅览室后,停在了我的面前,出乎我预料地开口问道:“你是王春林吧?”“嗯,我是。”我当然是一下子就站了起来。说老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梁先生是怎么知道我的。也因此,在当时很是有一点诚惶诚恐。当时还说了一些什么话,现在全都想不起来了。梁先生大约是询问了一些调动过来的情况。反正,自此以后,我和梁先生便逐渐熟悉起来。
再一个场景,是我和梁先生,以及哲学系的安希孟先生,还有几个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在一起的情形。那几个同学分别是中文系的孙静,哲学系的王瑞兵、李春安、刘伟。孙静是我的学生,大约就是在日常授课的过程中,由于她的潜心向学,我们便慢慢地熟悉了起来。而孙静,在平时,又和前面提到的哲学系的几位同学有颇多来往。从专业方向上看,梁先生是搞中国古典文学的,专研《红楼梦》,是所谓“探佚学”的首创者,亦是率先积极实践者。安希孟先生是专研西方神学的一位学者,不仅从事神学的翻译和研究工作,而且一度与刘小枫过从甚密。而我,则是一位主要以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为关注对象的文学批评工作者。三位研究方向各不相同的学者,就这样,因为数位志趣相投的学生在其中彼此勾连的缘故,日渐亲近起来,最终成为了非常要好的师友。如此一种密切交往的过程,必然会结出一些相应的果实。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还有这么两件事。一件是,在一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曾经一起去留学生的宿舍,一块度过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节日。尽管我是英语的门外汉,自始至终都没有能够听懂一句英语。另一件是,在日常讨论的基础上,梁先生曾经与王瑞斌合作,联手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这篇很是有些见地的文章,后来发表在了《红楼梦学刊》上。
还有一个场景,那就是梁先生肩挎一个草绿色的书包,急匆匆地行走在校园里的道路上,难道梁先生是在赶着去上课吗?非也,他是要赶着去听课。到后来,我才慢慢了解到,原来,梁先生是一位十分好学上进的人,因为置身于大学校园里,听课便利,只要遇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不管是哪个院系,只要有可能,他就会赶到教室里,如同一名求知若渴的大学生一样,规规矩矩地坐在下面听课。当然,其间也肯定少不了会有当堂向相关授课老师请教的场面。一位早已在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能够以这样一种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不断进步,至今想来,都令我感慨良多。
就这么一幕一幕地,我的思绪最终定格在了梁先生的学问事业上。虽然由于从事的学术领域不同,对于梁先生的学问事业,我不敢轻易置一词,但对于标志着他一生学术研究高峰的《石头记》探佚,我自己觉得还是有一点心得,想趁便写在这里,以求教于方家。既然要从事探佚学的研究,那梁先生所依据的,除了《石头记》的八十回文本外,恐怕就是脂砚斋的批语了。然而,以我的私心揣度,要想真正使得探佚学的研究有所成就,在实际探佚的过程中,恐怕无论如何都少不了另外的两个东西。一个是小说创作的内在艺术逻辑,另一个则是人物形象的内在人性逻辑。只有把以上数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所谓的“探佚学”才可能真正地有所作为。而且,在我的理解中,梁先生实际上就是这么做的。
开始写这篇饱蘸热泪的怀念文章时,时间是10月21日的晚上,谁知由于杂务缠身的缘故,等到我拉拉杂杂地即将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时间已经是10月24日的上午了。按照梁公子知会我的情况,到这个时候,在遥远的东北海城大连,梁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应该已经结束,他的身体与灵魂已经化作缕缕烟雾,正飘散在广袤无际的天空中。梁先生,我的好兄长,我好怀念你!写着写着,泪水再一次模糊了我的眼眶。真心地希望梁先生一路走好!希望他的灵魂在天堂早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