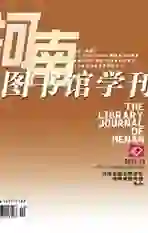唐代辨伪释例
2019-11-22孙新梅
孙新梅
关键词:唐代;辨伪;柳宗元;释智升;刘知己
摘 要:唐代的辨伪较之两汉、魏晋有了很大发展,这一时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辨伪学者,他们对四部典籍进行深入考辨,并且取得了重要成果。孔颖达、颜师古、长孙无忌、刘知幾、释道世、释智升、柳宗元等人是其代表,这其中又以刘知几的《史通》与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涉于辨伪者最具典型意义。文章以刘知几、释智升、柳宗元为例,探讨了唐代的辨伪成就。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9)10-0138-03
隋唐是经历了五胡乱华和南北朝之后,形成的两个大一统王朝,唐代又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唐代学者在辨伪方面已取得了诸多进步。中晚唐出现的刘知几和释智升两个辨伪学者,更是我国辨伪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1 刘知幾《史通》之辨伪
刘知幾(661—721),唐代著名史学家、辨伪学家。刘氏所著《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全书主要包括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个方面。前者是关于史书体例、编纂方法、作史原则的论述,后者是关于史书得失、史事正误的考订。
1.1 《史通》之《疑古篇》
《疑古篇》主要是针对《尚书》的怀疑,认为古圣人、古帝王的贤德功绩大多是后人粉饰的结果。云:“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加以古文载事,其词简约,推者难详,缺漏无补。遂令后来学者莫究其源,蒙然靡察,有如聋瞽。今故讦其疑事,以著于篇。凡有十条,列之于后。”刘知幾胪列《尧典》《舜典》《汤誓》《微子之命》《金縢》等篇中的说法,逐一进行驳斥。兹举二例。云:“盖《虞书》之美放勋也,云‘克明俊德。而陆贾《新语》又曰:‘尧、舜之人,比屋可封。盖因《尧典》成文而广造奇说也。案《春秋传》云:高阳、高辛二氏各有才子八人,谓之‘元‘凯。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举。帝鸿氏、少昊氏、颛顼氏各有不才子,谓之‘浑沌‘穷奇‘梼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尧不能去。缙云氏亦有不才子,天下谓之‘饕餮,以比三族,俱称‘四凶”而尧亦不能去。斯则当尧之世,小人君子,比肩齐列,善恶无分,贤愚共贯。且《论语》有云:舜举咎繇,不仁者远。是则当咎繇未举,不仁甚多,弥验尧时群小在位者矣。又安得谓之‘克明俊德‘比屋可封者乎?其疑一也。”刘氏以尧不用贤者八元、八凯,而又不惩罚四恶,质疑尧哪里具有超人的美德。又云:“《尧典序》又云:‘将逊于位,让于虞舜。孔氏《注》曰:‘尧知子丹朱不肖,故有禅位之志。案《汲冢琐语》云:‘舜放尧于平阳。而书云某地有城,以‘囚尧为号。识者凭斯异说,颇以禅授为疑。然则观此二书,已足为证者矣,而犹有所未睹也。何者?据《山海经》,谓放勋之子为帝丹朱,而列君于帝者,得非舜虽废尧,仍立尧子,俄又夺其帝者乎?观近古有奸雄奋发,自号勤王,或废父而立其子,或黜兄而奉其弟,始则示相推戴,终亦成其篡夺。求诸历代,往往而有。必以古方今,千载一揆。斯则尧之授舜,其事难明,谓之让国,徒虚语耳。其疑二也。”刘氏以诸书记载不一,而质疑尧禅位于舜的真实性。他还提出了辨识伪说的方法:“今取其正经雅言,理有难晓,诸子异说,义或可凭,参而会之,以相研核。”取各家之说,参核异同,判别是非,这是比较科学的类比法。刘氏还分析了近古之史与远古之史的区别,以及远古之书对先圣帝王溢美的原因,云:“夫远古之书与近古之史,非唯繁约不类,固亦向背皆殊。何者?近古之史也,言唯详备,事罕甄择。使夫学者睹一邦之政,则善恶相参;观一主之才,而贤愚殆半。至于远古则不然。夫其所录也,略举纲维,务存褒讳,寻其终始,隐没者多。”近古史书记载较详,对于人和事不论好坏全部记下,便于后人知道这些人和事的好坏两个方面。远古史书所记多为梗概,书史者对于心目中的好君主,就带着颂扬的态度记录他们的丰功伟绩,同时不惜为其隐恶。
1.2 《史通》之《惑经篇》
《惑经篇》认为《春秋》因袭旧文,体例并不完善,非孔子先定义例而后作,不应受到世人的过分推崇。刘知几在审查《春秋》文义时,提出了十二点疑问。此兹举二例。云:“赵孟以无辞伐国,贬号为人;杞伯以夷礼来朝,降爵称子。虞班晋上,恶贪贿而先书;楚长晋盟,讥无信而后列。此则人伦臧否,在我笔端,直道而行,夫何所让?奚为齐、郑及楚,国有弑君,各以疾赴,遂皆书卒?夫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凡在含识,皆知耻惧。苟欺而可免,则谁不愿然?且官为正卿,反不讨贼;地居冢嫡,药不亲尝。遂皆被以恶名,播诸来叶。必以彼三逆,方兹二弑,躬为枭獍,则漏网遗名;迹涉瓜李,乃凝脂显录。嫉恶之情,岂其若是?其所未谕一也。”刘氏列举《春秋》不能秉笔直书,记事使用多重标准的诸多例子,而质疑《春秋》的体例。又云:“案齐乞野幕之戮,事起阳生;楚比乾溪之缢,祸由观从。而《春秋》捐其首谋,舍其亲弑,亦何异鲁酒薄而邯郸围,城门火而池鱼及。必如是,则邾之阍者私憾射姑,以其君卞急而好洁,可行欺以激怒,遂倾瓶水以沃庭,俾废垆而烂卒。斯亦罪之大者,奚不书弑乎?其所未谕二也。”刘氏继续举证了《春秋》记事没有做到不虚美不隐恶。他还考察了世人对于《春秋》溢美的来源,并指出每个人面对史书都要有自己的判断,云:“考兹众美,征其本源,良由达者相承,儒教传授,既欲神其事,故谈过其实。语曰:‘众善之,必察焉。孟子曰:‘尧、舜不胜其美,桀、纣不胜其恶。寻世之言《春秋》者,得非睹众善而不察,同尧、舜之多美者乎?”这些溢美之辞,基本上是由儒家学者传授相承的,为了神化孔子,他们在宣讲时就会言过其实。
2 刘知幾辨《孝经》郑玄注之伪
开元七年三月,唐玄宗敕群儒讨论《孝经》郑注与孔传诸书之长短。刘知幾于四月七日上《孝经老子注易传议》申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提出了《孝经》非郑玄之注的十二条证据。《唐会要》卷七十七《论经义》:“谨按今俗所传《孝经》,题曰郑氏注。爰自近古,皆云郑即康成,而魏晋之朝,无有此说。至晋穆帝永和十一年,及孝武帝太元元年,再聚群臣,共论经义。有荀昶者,撰集《孝经》诸说,始以郑氏为宗。自齐、梁以来,多有异论。陆澄以为非玄所注,请不藏于秘省。王俭不依其请,遂得见传于时。魏、齐则立于学官,著在律令。尽由肤俗无识,故致斯讹舛。然则《孝经》非玄所注,其验十有二条。据郑君自序云:‘遭党锢之事,逃难注《礼》。党锢事解,注《古文尚书》《毛诗》《论语》。为袁谭所逼,来至元城,注《周易》。都无注《孝经》之文,其验一也。……魏晋朝贤,辨论时事,郑氏诸注,无不撮引,未有一言引《孝经》之注,其验十二也。凡此证驗,易为考核。而世之学者,不觉其非,乘彼谬说,竞相推举,诸解不立学官,此注独行于世。观夫言语鄙陋,固不可示彼后来,传诸不朽。”同时,刘知幾也对《孝经》孔传做了评价,比较了郑注与孔传的优劣,云:“至如《古文孝经》孔传,本出孔氏壁中,语其详正,无俟商榷,而旷代亡逸,不复流行。至隋开皇十四年,秘书学士王孝逸于京市陈人处,置得一本,送与著作郎王劭,以示河间刘炫,仍令校定。而更此书无兼本,难可凭依,炫辄以所见,率意刊改,因著《古文孝经稽疑》一篇。劭以为此书经文尽在,正义甚美,而历代未尝置于学官,良可惜也。然则孔、郑二家,云泥致隔,今纶音发问,校其短长。愚谓行孔废郑,于义为允。”后人皆重刘氏此说,宋邢昺《孝经御制序疏》照录此文,清阮元在《孝经注疏校勘记序》中说:“郑注之伪,唐刘知幾辨之甚详。”
3 释智升《开元释教录》之辨疑伪经
释智升,唐代高僧,生平不详。唐玄宗开元间居长安崇福寺,于开元十八年撰成《开元释教录》,该书多辨疑经与伪经。释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在佛经目录中地位甚高,后世评价谓之精严。智升在篇首阐述了目录对于辨伪的重要性,云:“夫目录之兴也,盖所以别真伪、明是非,记人代之古今,标卷部之多少,摭拾遗漏,删夷骈赘。欲使正教纶理金言有绪,提纲举要历然可观也。”
3.1 《疑惑再詳录》
《开元录》卷十八之上为《疑惑再详录》,记载疑伪待考的经书,云:“疑惑录者,自梵经东阐年将七百,教有兴废时复迁移,先后翻传卷将万计。部帙既广寻阅难周,定录之人随闻便上,而不细寻宗旨理或疑焉。今恐真伪交参是非根涉,故为别录以示将来,庶明达高人重为详定。”此录记载尚待考定的经典共十四部,凡十九卷,即《毗罗三昧经》二卷、《决定罪福经》一卷、《慧定普遍国土神通菩萨经》一卷、《救护身命济人病苦厄经》一卷、《最妙胜定经》一卷、《观世音三昧经》一卷、《清净法行经》一卷、《五百梵志经》一卷、《法社经》二卷、《净度三昧经》三卷、《益意经》二卷、《优娄频经》一卷、《净土盂兰盆经》一卷、《三厨经》一卷。其于《五百梵志经》下注云:“右《毗罗三昧经》下八部九卷,古旧录中皆编伪妄,大周刊定附入正经。寻阅宗徒理多乖舛,论量义句颇涉凡情,且附疑科难从正录……仍俟诸贤共详真伪。”于《净土盂兰盆经》下注云:“右一经新旧之录皆未曾载,时俗传行将为正典,细寻文句亦涉人情,事须审详且附疑录。”
3.2 《伪妄乱真录》
《开元录》卷十八之下为《伪妄乱真录》,云:“伪经者,邪见所造以乱真经者也,自大师韬影向二千年。魔教竞兴正法衰损,自有顽愚之辈恶见迷心,伪造诸经诳惑流俗,邪言乱正可不哀哉!今恐真伪相参,是非一概,譬夫昆山宝玉与瓦石而同流,赡部真金共铅铁而齐价,今为件别,真伪可分,庶泾渭殊流无贻后患。”《伪妄录》登记伪经三百九十二部,凡一千零五十五卷。此三百余部中智升本人辨其伪者仅三十七部,“从《佛名经》下三十七部五十四卷,承前诸录皆未曾载,今《开元新录》搜集编上”。智升在《伪妄录》中借鉴了许多前人的成果,他毫不掠美,一一表出。如东晋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右《定行三昧经》下二十五部二十八卷,苻秦沙门弥天释道安录中伪疑经。”
对于一些抄辑众经而别有题名的经书,智升采取了详细说明、附于伪经的做法,这是一种不欲侵犯原作者著作权的非常审慎的态度。例如,智升于《佛法有六义第一应知经》《六通无碍六根净业义门经》下云:“右二部二卷,梁僧祐录云‘齐武帝时比丘释法愿抄集经义所出,虽弘经义异于伪造,然既立名号则别成部卷,惧后代疑乱,故明注于录。”于《佛所制名数经》下云:“右一部五卷,梁僧祐录云‘齐武帝时比丘释王宗所撰,抄集众经有似数林,但题称佛制,惧乱名实,故注于录。”
4 柳宗元辨七部子书之伪
柳宗元(773—819),不仅是一位文学家,还是第一个对子书进行系统辨伪的人。虽然他辨识的伪书数量不多,但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使用了丰富的辨伪方法,如考察称谓的方式、考镜源流的方式等,以及对于后世宋高似孙、明宋濂等人的影响。
《辩列子》:“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记》:‘郑繻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四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其称夏棘、狙公、纪渻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余故取焉。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柳宗元以著者早于书中所载,辨《列子》之伪。同时,他分析了刘向致误的原因,即刘向将鲁穆公误作了郑穆公。柳氏还能客观看待伪书的价值,评价《列子》“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提醒读者在使用时要慎重一些。除《辩列子》外,柳宗元还有《辩文子》《论语辩(上篇)》《辩鬼谷子》《辩晏子春秋》《辩亢仓子》《辩鹖冠子》等辨伪著作,这些辨伪著作都充分展现了柳宗元的辨伪精神。
5 结语
唐代的韩愈也是一个颇具疑古精神的人,他在《答李翊书》中言需“识古书之正伪”。对于这个观点,清代的阎若璩甚是膺服,阎氏云:“呜呼!事莫大于好古,学莫善于正讹。韩昌黎以识古书之正伪为年之进,岂欺我哉!”辨伪学在经历了先秦至于隋唐这个漫长时期的积累与铺垫后,到了宋代就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
参考文献:
[1] 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54-386.
[2] 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63-1665.
[3] 李隆基,注.邢昺,疏.孝经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21.
[4] 释智升.开元释教录[M].北京:中华书局,1992:1-398.
[5] 刘真伦,岳珍.韩愈文集彙校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700.
[6]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11.
[7] 柳宗元.柳宗元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07-108.
(编校:崔 萌)